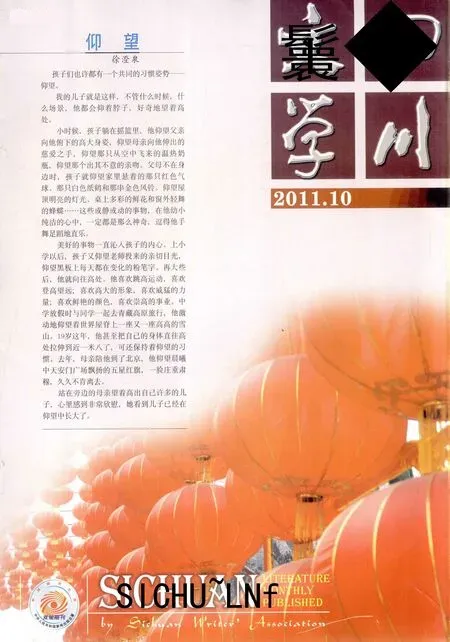谜样乡音
□袁瑛
谜样乡音
□袁瑛
长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用汉字写不出我的乡音。
母亲有个儿时伙伴嫁到双流,每次回来,母亲她们几个就会揪着她说话的腔调不放:哦呀,人嫁过去了,连口音也嫁过去了,别腔别口的!这个“别腔别口”,彭山话音为“pie qiang pie kou”,音我会,字却完全不知道是哪几个字——幼年,甚至到少年时期,我根本没有想过母亲、外婆、外公嘴里的“话”能用汉字写出来。乡音于我,是谜面晦涩的谜语,不知从哪个字开始可以解开。
有这样一句古云:白首如新,倾盖如故。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两个人认识的时间长到黑发熬成白发,心情还是崭新的,崭新到互相无法触碰;驾着马车在行色匆匆的途中,偶一转头,就觉彼此是故人,硬要停下赶路的脚步,投缘得把车盖都压弯了。语言的魅力是一颗颗浅浅的清波漩涡,刚惹得你欢喜便了无痕迹。我和我的乡音,很长时间内是“白首如新”的状态。我从未认真仔细地打量过它们,我用自己一岁时就学会的方言说话,用五岁时学会的汉字思考写字。方言是乡音,汉字是知识是文化;乡音是日常生活,文化是精神思考。我自作主张地这样分开它们。
其实我对乡音是非常敏感的,我知道乡音里每个字的发音位置,是从喉咙里出来还是从牙齿缝里出来,是张开嘴出来还是闭着嘴出来。我也知道每个音怎么说是什么样的情绪,拧紧了多少条肌肉。只要他开口,我就能判断这个人是否是我的乡邻,甚至,是东山片还是西山片的乡邻。在某一个业务工作会上,某县的代表发言,他刚一张口我就疑惑:这个县的人说话的口音不是这样的,难道他不是这个县的人?接着,疑惑升级,他的口音听来全是彭山味道,而且,还是彭山北边乡镇的口音味道,说不定,跟我一条街呢。兴奋和亲切劲儿一下就上来了,会议的枯燥、环境的陌生蛇样逶迤爬走。他的发言越说越顺溜,顺溜中彭山腔调,彭山语气,彭山神态,彭山姿势,我断定,他肯定来自彭山。饭桌上一打听,果然,他是彭山青龙人。
改乡音是直不起腰杆的事。贺知章是懂得的。你看,他回乡后特别写道“乡音未改鬓毛衰”。母亲的儿时伙伴也是懂的,她每次总会奋力解释:我没改口音我没改口音,在那边人家一听就晓得我是彭山人!母亲她们几个得理不饶人:你看你看还说没改,这块“没”字我们这边是你那样说的啊?那个外嫁的阿姨说的每个字每句话,都被母亲她们当被单一样抖伸展晾在晾衣竿上,几双眼睛一行行刷过经纬线,挑出那些她们不满意的丝缕。乡音是什么?乡音是根!是生活在同一匹山同一片坝同一座城市的人的集体无意识,是找寻童年找寻亲人找寻过去的信物,是祖先给我们的印记。
口中的乡音,是一匹祖传的华丽织锦。这匹织锦出自蜀地,自秦而来,经过汉,到达唐,遇见过李密,记录过彭祖,最后被我那慈祥爱我十多载的外公外婆传递给我。这些,就是乡音要揭示给我的谜底吗?
直到我从电视上偶然邂逅一个叫吴军伶的北京女人,乡音与我终于从“白首如新”走到“倾盖如故”的状态。这个少了一只手的快乐而勇敢的女人对着记者的话筒阔朗地聊着自己致残、创业的历程,讲到曾经因为创业差点让两个孩子煤气中毒的事情。她说,她大妈嚷了她,说她再拼命也要顾孩子啊,要是孩子没了还为什么拼。再顽强终究是母亲,吴军伶边说边抹眼泪,我也陪着流泪,这时,就是这时,那个字,那个“嚷”字,北京话的“嚷”字电击了我一下,我就像是金庸古龙小说中资质平庸的学武青年,连番偶遇,吃了灵药圣果,巧结世外高人,终于喜获神功——原来我的乡音我的方言里的“挨嚷”,就是这个“嚷”啊!我从小听大人们说“挨嚷”,听老师说“挨嚷”,但我一直没把彭山话里的“挨嚷”用汉字写出来,表达出来。写到“挨嚷”,我会写成“责备”、“训斥”、“教训”。“责备”、“训斥”、“教训”,意思准确清晰,可是一板一眼的,冷冰冰的,跟袋装酸菜一样,生产于机器厂房。你看我们的“挨嚷”,是顺着开满紫云英花的田埂上走出来的,是高声武气的村妇嘴里狠狠飞出来的,捋着袖子,挽着裤角。这个“嚷”,带着活泼泼的热闹气。乡人是喜欢闹热的,你看,“挨嚷”分明带着一丝轻松劲儿。顺着挨嚷的线索,我迅速用汉字写出很久以来我只会说不会写的彭山话:牙尖舌怪、叔伯(bai)的、匪头子、造孽、闹热……
从来没有过谜语,乡音就是乡音。
本栏目责任编辑 牛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