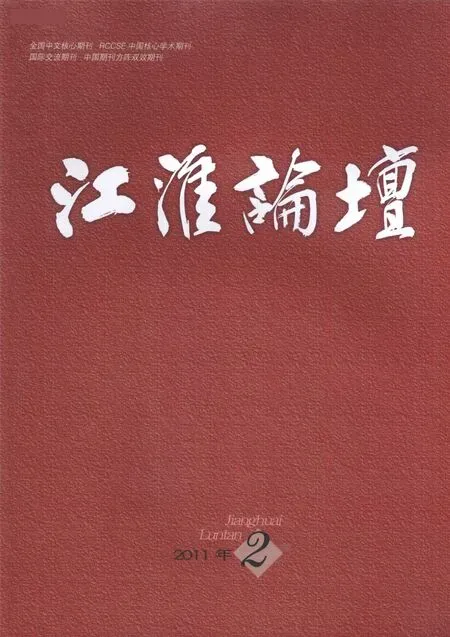钱谦益在清初诗学观念的新变
张永刚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南宁 530006)
钱谦益在清初诗学观念的新变
张永刚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南宁 530006)
身兼东林党魁与文坛盟主于一身的钱谦益在入清后,政治上蒙受着贰臣的耻辱,在立德、立功未就的情况下,寻求立言以求得道德上的自赎。政治上的失意,促成了其诗学观念的新变,即“言为事功”、“诗以存史”、“以史证诗”、“出入宋元”,分别通过《投笔集》、《列朝诗集小传》、《钱注杜诗》、《有学集》等体现出来,彰显了其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
钱谦益;清初;诗学观念;新变
由明入清的钱谦益在政治上承受着贰臣的耻辱,宦海沉浮,三十余年入阁为相的雄伟抱负已经在接连不断的党争中化为了泡影,惟有失节的无尽忏悔需要道德上的自赎。言为心声,政治上的失意,并不影响其在文坛上的创获,反倒激起其更大的创作热情,以抒写自己的心路历程,求得精神上的释放。身为“四海宗盟五十年”的文坛盟主也需要其有所担当,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关捩点上,起到了总结前明,导引后清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其诗学观念体现了四个方面的新变,分别通过四部著作有所彰显。即“言为事功”的《投笔集》、“诗以存史”的《列朝诗集小传》、“以史证诗”的《钱注杜诗》以及“出入宋元”的《有学集》。
一、言为事功——《投笔集》
《投笔集》[1]创作于顺治十六年(1659),终于康熙二年(1663),历时五年,是钱谦益晚年具有诗史性质的诗集,共存诗一百零八首,其中和杜甫《秋兴》韵一百零四首,分为十三叠,每叠八首,其中第一叠题名《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第二叠起,均题名《后秋兴八首》。主要是汲取杜甫指陈时事的现实主义诗旨,关涉反清复明运动的进展,表达自己忧时伤世的情怀及积极进取的心态。因此,其既可称得上是描写时事的文学佳作,也可谓是一部作者曲折的心灵史。陈寅恪先生对此诗集评价很高:“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 ”[2]1193
《投笔集》以隐讳的笔法记录了自己从事反清复明运动的进程,作者以此为自己人生最后的事功,以消抵身为贰臣所带来的无尽的懊悔,以至置死生于不顾,屡犯险境。顺治十三年(1656),钱谦益为与海上郑成功联系便通,移居白茆,“白茆之芙蓉庄即碧梧红豆庄也,在常熟小东门外三十里,先生外家顾氏别业也。白茆为长江口岸之巨镇,先生与同邑邓起西、昆山陈蔚村、归玄恭及松江、嘉定等遗民往还,探刺海上消息,故隐迹于此,一以避人耳目,一以与东人往还便利也。”[3]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约集张煌言大举北上,五月,抵达崇明,在白茆驻有舟师。八月八日,钱谦益冒着生命危险,夜探郑成功的驻军。《钱牧斋先生年谱》载:“八月八日国姓(郑成功)至崇明,而某将军有伏舰百余在常熟之白茆港。先生盖夜渡白茆港耳。十三日,蒋国柱、梁化凤追师至,而某将军去。”诗人在《后秋兴之四》中记录了自己这段冒险的经历。
菰乡芦渚路逶迤,菰乡芦渚路逶迤,竹杖迢迨度葛陂。陌柳未纾离别绪,庭梧先曳却回枝。途危只仗心魂过,路劣才容脚指移。(自注:梦度险岸,劣容脚趾。江乡夜行,光景宛然。)莫道去家犹未远,朝来衣带已垂垂。
诗人以八十之老迈身躯倚着竹杖,深夜行进在曲折的沼泽地里,如此艰难的行程只能靠着毅力来支撑走过,虽然离家不远,但在早晨返回的时候,已经是衣带松散,狼狈之极。然而,此行并不顺利,由于郑成功的这支军队败走,诗人转道松江再会马进宝,这无疑又是一次冒险之旅。因此时,马进宝作为苏松常提督,与水师提督梁化凤共同抵御郑成功的北伐,如能争取他的合作,那么北伐就有可能取得胜利。诗人对此间形势了如指掌,在这敏感的时机,欲策反马进宝,为北伐扫清道路。《后秋兴》之七将诗人的心迹坦露出来。
此行期奏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自许挥戈回晚日,相将把酒贺春风。墙头梅蕊疏窗白,瓮面葡萄玉盏红。一割忍忘归隐约,少阳原是钓鱼翁。
诗人希望自己此行游说能够达成所愿,以使北伐取得成功。并且表达了自己虽然老迈,但欲效铅刀一割,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郑成功的挥师北伐牵动了诗人的神经,为之胜利欢喜,为之失利惆怅。当郑成功水师抵达南京城下时,诗人忍不住唱起了中兴的凯歌。《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其五云:“箕尾廓清还斗极,鹑首送喜动天颜。枕戈席藁孤臣事,敢拟逍遥供奉班。”诗人甚至想到了光复之后,自己要向新天子负荆请罪,可见,其对此次北伐寄予的期望之高。章太炎先生说:“郑成功尝从受学,既而舟师入南京,皖南诸府皆反正,谦益和杜甫《秋兴》诗为凯歌,且言新天子中兴,己当席藁待罪。当是时谓留都光复在俾倪间,方偃卧待归命。”[4]然而,好梦不长,郑成功由于缺乏必胜的信念,行动缓慢,贻误了战机,导致最终的失败。诗人苦心经营多年的努力付诸流水,内心的伤悲陡然而生,“起手曾论一着棋,明灯空局黯生悲”,在他心中依然洋溢着对明政权的归属感,“自丧乱来余破胆,除君父外有何心”,因此,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南明君主能细细思量他的“楸枰三局”的计划,“腐儒未谙楸枰谱,三局深惭廑帝思。”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诗人的一厢情愿,腐败的南明政权在党争内讧中耗尽了元气,最终逃不脱败亡的命运。
郑成功北伐失利后,钱谦益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偏安西南的永历政权上,这是继弘光、隆武之后的又一个南明政权,自顺治三年(1646)到康熙元年(1662)持续了十六年的时间,是南明存在最久的一个政权,一度使明遗民看到复国的希望。心急的诗人更是迫不及待地想飞抵永历帝身边,为恢复故国出谋划策。“愿同筰马扶车辇,欲傍旄牛听鼓笳。”然而,西南边陲终究与中原相隔万里之遥,年迈的诗人只能梦想着为国建功。“梦到红云深殿里,玉皇新点侍家班。”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驾崩,幼帝康熙即位。诚如张煌言所云:“今虏酋短折,孤雏新立,所云主幼疑国者,此其时也。”这无疑是复明的大好时机,诗人兴致异常高涨,夜宴述古堂。虽然顺治新丧,全国哀悼,但诗人仍然张灯夜宴,赋诗庆祝,“碧天朗朗见余晖,把酒前除酹太微。”诗人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前景一片大好,“阁道新移鹑尾斜,朔南寰宇仰重华。”然而,残酷的现实不久便击碎了诗人的美梦。由于郑成功不听指令,转而经营台湾,又一次失去了复明的良机。诗人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从白茆红豆庄迁回了常熟故居。“廿载光阴四度棋,流传断句和人悲。冰凋木介侵分候,霜戛风筝决战时。觚竹悬车多次舍,皋兰轻骑尚逶迟。灯前历历残棋在,全局悠然正可思。”康熙元年(1662)三月二十三日,诗人得到了永历帝遇害的消息。悲痛之余,写下了《后秋兴》之十三: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俺银轮哭桂花。
明祚既亡,天地翻覆,无所归依的凄苦表达了诗人的心境,浓郁的悲凉情调黯然而生,“大临无时,啜泣而作”,诗人岂止是在悲痛永历帝的遇害,更是对故国无法恢复的哀悼和对自己二十余年复明努力的埋葬。
因此,可以说《投笔集》是一部钱谦益晚年从事复明运动,努力事功的告白书,也是其对于失节忏悔的自白书。归庄深知其师的苦衷:“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其赉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即享耄耋蚁。 呜呼! 我独悲其遇之穷。 ”[5]卷八
二、诗以存史——《列朝诗集小传》
《列朝诗集》的编纂始于天启初年,“山居多暇,撰次国朝诗集凡三十家,未几罢去。此天启初年事也。越二十余年而丁开宝之难,海宇板荡,载籍放失,濒死颂系,复有事于斯集。托始于丙戌(顺治三年),彻简于己丑(顺治六年)。乃以其间,论次昭代之文章,搜讨朝家之史乘,州次部居,发凡起例,头白汗青,庶几有日。”[6]678可见,《列朝诗集》由于时值鼎革,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才完工,初名为《国朝诗集》,然而,明已经亡国,称为国朝甚为不妥。于是钱谦益后来在与毛子晋的书信中说:“集名‘国朝’两字,殊有推敲。一二当事有识者议易以‘列朝’字以为万妥,更无破绽,此亦笃论也。板心各欲改一字,虽似琐屑,亦不容以惮烦而不为改也。”[7]299是书体例仿造元好问 《中州集》,寄寓了作者以诗存史的意图。“鼎革之后,恐明朝一代之诗,遂致淹没,欲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选定为一集,使一代诗人之精魂留得纸上,亦晚年一乐事。”[6]236论者由此认为其论诗为次,而存史为主。“虞山其为今之后死者兴起欤?吾不得而知,而特知其意不在诗。”[8]卷八钱谦益在《书徐布政贲诗后》云:“余撰此集,仿元好问《中州》故事,用为正史发端,搜摭考订,颇有次第。 ”[9]然其体例与元氏《中州集》又有所区别,钱谦益自述:“余近辑《列朝诗集》,厘为甲、乙、丙、丁四部,而为之序曰:遗山《中州集》止于癸,癸者,归也。余辑《列朝诗》止于丁,丁者,万物皆丁壮成实,大盛于丁也。盖余窃取删诗之义,顾异于遗山者如此。 ”[6]771陈寅恪先生认为钱谦益《列朝诗集》的体例安排“实寓期望明室中兴之意”。这无疑和钱谦益当时反清复明的心态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列朝诗集》已经不仅仅是存诗的价值,同时也是用来存有明一代之史,以表明作者的心志。这一意图尤其体现在《列朝诗集小传》上。
《列朝诗集》共81卷,集中编选了明代近2000位诗人的代表作,并逐一作小传。《列朝诗集》刊行后,周容等人将《小传》抄录单行,引起士人的关注。康熙初年,虞山诗人钱陆灿将《小传》刊印行世。《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云:“合之诗,则钱氏之诗序也而可;离之诗,则续《初学》、《有学》之后而可。否则,孤行其书,为青箱之本,枕中之秘,无不可。”《小传》其价值不仅在于体现了钱谦益的诗学思想,而且对于作家人物的传记、历史事件的发生颇具史料价值,可备正史之补。《明史·文苑传》很多传记就是以钱谦益的《小传》为蓝本,加以删节而成。特别是尤侗所撰的《文苑传》初稿,只是略加删节,几乎全部照搬钱谦益的原文。因此,后来汪由敦在《史裁蠡说》中说:“文苑则取其制作可传者,或关系一时风气,如前后七子、袁宏道、钟惺之流,略为论列流派。否则不必滥收。未可以钱谦益、曹能始之品题据为定论也。 ”[10]但是细加观察,就可以发现,即使修改后的《文苑传》定稿也多相似之处。此以何良俊的记载为例: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何孔目良俊》:“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筴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字叔皮,同学。叔皮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九逵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年,复买宅居吴门,年七十始归云间。元朗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于今日也。吴中以明经起家官词林者,文徵仲、蔡九逵之后二十余年,而元朗继之。元朗清词丽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谨自励,蔡以谿刻见讥,而元朗风流豪爽,为时人所叹羡,二公殆弗如也。元朗集累万言,皇甫子循为叙,又有《何氏语林》、《四友斋丛说》行于世。”
尤侗《明史·何良俊传》初稿:“良俊,字元朗,华亭人。少而笃学,二十年不下楼,或挟荚行游,忘堕坑岸,其专勤如此。与弟良傅同学。良傅举进士,官南祠部郎,而良俊以岁贡入胄监。时宰知其名,用蔡羽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好谈兵,以经世自负,浮沉冗长,郁郁不得志,每喟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东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鼎彝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归。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数载,年七十始归云间。良俊风神朗澈,所至宾客填门。妙解音律,晚畜声伎,躬自度曲,分寸合度。秣陵金阊,都会佳丽,文酒过从,丝竹竟奋,人谓江左风流,复见今日也。 所著《文集》及《语林》、《丛说》行于世。 ”
《明史·文苑传三·文徵明》:“其后,华亭何良俊亦以岁贡生入国学。当路知其名,用蔡羽例,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良俊,字元朗。少笃学,二十年不下楼,与弟良傅并负俊才。良傅举进士,官南京礼部郎中,而良俊犹滞场屋,与上海张之象,同里徐献忠、董宜阳友善,并有声。及官南京,赵贞吉、王维桢相继掌院事,与相得甚欢。良俊居久之,慨然叹曰:‘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遂移疾归。海上中倭,复居金陵者数年,更买宅居吴阊。年七十始返故里。”
这三则材料足可以证实钱谦益《小传》的史料价值,其“以诗存史”的创作意图显而易见。
作为东林后期党魁,钱谦益纠缠于党争三十余年,直至明亡,也没有实现其入阁拜相的愿望,尽管他在弘光政权期间,不惜谄事政敌马士英、阮大铖,然终究没有能够改变其失败的政治命运。那么,针对这段历史,涉及到党争双方的人物,其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是如何表现的呢?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王考功象春》:“象春,字季木,新城人。万历庚戌,举进士第二人,与笤上韩求仲名相次也。季木每叹诧:‘奈何复有人压我!’其语颇为时所传。而求仲科场议大起,遂以季木为讦己,党人用壬子北试,移师攻季木,牵连谪外。”
这段记载的是庚戌科场事,也是钱谦益步入仕途所卷入的第一次党争事件。万历三十八年,钱谦益参加庚戌科考,主试者为赏识钱的东林党人王图、萧云举等人。因此,在发榜之前,就已传出状元为钱谦益的消息。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状元为浙党中人韩敬获得,钱谦益仅列第三名探花。当然,次年的辛亥京察,东林党人主计,实施报复,弹劾了汤宾尹、韩敬。由此,引发了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激烈对峙的局面,正如钱谦益所云:“万历中之党议,播于庚戌而煽于辛亥。 ”[11]1474天启间,钱谦益受命典试浙江,陷入了韩敬等浙党所设的圈套,最后生成了浙闱关节案,一直影响到崇祯间枚卜入阁,由于温体仁以浙闱事弹劾钱谦益,钱谦益虽在入阁推荐名单之列,却被罢黜,最终没有能够入阁,失去了他仕途中最好的机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围绕钱谦益的一系列党争的始发点即在庚戌科场案。因此,钱谦益一直耿耿于怀,直至去世前一年,在具有自传性质的《病榻消寒杂咏》中,仍然念念不忘庚戌科场案。“砚席书生倚稚骄,《邯郸》一部夜呼嚣。朱衣早作胪传讖,青史翻为度曲訞。炊熟黄粱新剪韭,梦醒红烛旧分蕉。卫灵石椁谁镌刻,莫向东城叹市朝。 ”[6]645诗中所提到的《邯郸梦》是汤显祖的剧作,讲的是卢生的黄粱美梦:卢生科场试卷落选,以重金贿赂权贵,结果落卷被翻出,点为状元。这个故事情节和庚戌科场案的情节如出一辙。有这样的情结在,钱谦益对韩敬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直白地表露出来,而是通过王象春之口,巧妙地置身世外,以第三者的身份来记录这件事,却又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钱谦益这一因人论世的手法不可谓不高明,这或许是其久谙党争,而提炼出的攻击政敌的一种斗争方式。同样的手法也应用于对待他的政敌阉党余孽阮大铖身上。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阮邵武自华》附见《阮尚书大铖》:“大铖,字集之,坚之从孙也。万历丙辰进士,天启间官吏科给事中。坐阉党,禁锢。弘光登极,召拜兵部尚书,督兵江上。乱后不知所终。”
阮大铖可谓是东林党人的死敌,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但钱谦益这段描述依然是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娓娓道来,表面上仅仅是客观的叙述,并不带有怎样的感情色彩,这或许让人觉得其对阮大铖的评价是客观的。然而,细加思考就会发现,这段论述模糊处理了阮大铖误国和降清的罪行。而实际上,阮大铖的这两大罪行都和钱谦益有关。为了能够有机会入阁拜相,钱谦益以东林党魁的身份举荐阮大铖,从而背叛了自己的党派。弘光政权覆亡后,钱谦益降清,并招抚了阮大铖。因此,在这两件事上,钱谦益为了避免受到别人的攻击,不给别人留下噱头,巧妙地处理了阮大铖的小传。
与对政敌的处理方式不同,钱谦益对东林党中重要人物直接采取了褒扬的态度。如《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赵尚书南星》:“梦白公忠强直,负意气,重然诺,有燕赵节侠悲歌慷慨之风。……梦白抗议竖节,身为部党之魁,人以为门庭高峻,不可梯接,不知其通轻侠,纵诗酒,居然才人侠士,文章意气之俦也。”寥寥数语,展示在我们面前的赵南星既是一位政治上坦荡的斗士,同时又是一位文学上潇洒的才子,令人不得不心生仰慕。对于自己的座师东林党人孙承宗更是采取了大量的篇幅来予以颂扬。“公铁面剑眉,鬚髯戟张,声如鼓钟,殷动墙壁,方严果毅,嶷如断山,开诚坦中,谭笑风发,望而知其为伟人长德。……有军国大事,大珰传语问难,阁臣相顾失色。公拂衣奋袖,矫尾厉角,指画其是非可否,众人各有所挟持,无以夺也。”在钱谦益看来,孙承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是值得推崇的国士,如此的美化体现出了钱谦益非常直白的爱憎分明的态度。
钱谦益对党争的态度,依然可以在《列朝诗集小传》中找到表述。如丁集中《李尚书三才》:“(李三才)功高望重,颇见汰色,时论以外僚直内阁,如祖宗故事,意在推戴道甫,党人乘其间,交章论劾,道甫盛气陈辩,不自引去。顾宪成自林居贻书阁部,力为洗雪,于是,言者又乘间并攻东林,物议纠缠,大狱旁午,飞章钩党,倾动朝野。从此,南北党论,不可复解,而门户之祸,移之国矣。”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钱谦益对于东林党争的缘起及危害是非常清楚的,可以说其是痛恨党争的。同样的态度在丁集《沈少师一贯》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与宋州同辅政,而门户角立,矻矻不相下,妖书之狱,宋州及郭江夏慬而得免。人谓少师有意齮龁之,海内清流,争相指摘,党论纷呶,从此牢不可破。雒蜀之争,遂与国家相终始,良可为三叹也!”
三、以史证诗——《钱注杜诗》
《钱注杜诗》二十卷为钱谦益晚年用力甚勤之作,从崇祯六年(1633)始至康熙二年(1663)去世前一年方告完成,历时几三十余年,承袭了孟子“知人论世”的文学观念,采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将唐代史事同杜甫诗歌互相印证,考察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以此揭示杜甫的创作心态,阐明诗意。陈寅恪先生评价甚高:“牧斋之注杜,尤注意诗史一点,在此之前,能以杜诗与唐史互相参证,如牧斋所为之详尽者,尚未之见也。”[2]1193郑庆笃等《杜集书目提要》评价较为全面:
钱注杜诗,侧重以史证诗,以钩稽考核历史事实,探揣作意,阐明诗旨为务。《冬日洛阳城谒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钱自谓“凿开鸿蒙”,最有创见者。钱笺杜诗虽难免有考核失当,穿凿附会之处如朱鹤龄所讥评者,然毕竟瑕不掩瑜,是杜甫诗集影响极大的注本之一。清代注解杜诗者,鲜不受其影响,论者谓钱、朱二书既出,遂大启注杜之风,而钱氏之功尤著。[12]
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首先,钱注杜诗侧重采用以史证诗的批评方法,其中以《冬日洛阳城谒玄元皇帝庙》等诗是钱谦益自认在实践此方法上笺注最有创见者;其次,钱注与朱注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再次,钱注杜诗对清代注杜之风影响甚大。
钱谦益于文学之外,也致力于史学。《有学集补·答吴江吴赤溟书》自谓 “三十余年,留心史事”,今存《开国群雄事略》、《太祖实录辨正》、《明史断略》等史学著作,皆考核谨严,具有相当的史学研究价值。弘光元年(1645),曾上《请修国史书》,遭到拒绝,遂私自修史。奈何顺治七年(1650),绛云楼失火,其《明史》手稿付之一炬。 但其史官意识和行为得到了时人的称许。黄道周就义之时曾言:“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 ”[6]686不仅如此,钱谦益还提倡“诗史同源”,“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也,《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 ”[6]800这就为其以史证诗的方式注杜提供了理论基础。至于缘何选中杜诗,则是由钱谦益对唐以来诗歌发展的历程进行总结所定的基调。“自唐以降,诗家之途辙,总萃于杜氏。 大历后以诗名家者,靡不由杜而出。 ”[11]929在钱谦益看来,杜诗不仅集唐之大成,而且为大历以后诗家的源头,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是宋、元、明三代以来笺注杜诗者多有谬误,有进行匡正的必要。“自昔笺注之陋,莫甚于杜诗。伪注假事,如鬼冯人。剽义窜辞,如虫食木。而又连缀岁月,剥割字句,支离覆逆,交跖旁午。如郑昂、黄鹤、蔡梦弼之流,向有条例破斥,亦趣举一二而已。今人视宋,学益落,智益粗,影明隙见,熏染于严仪、刘会孟之邪论,其病屡传而滋甚。人各仞岂所解以为杜诗,而杜诗之真面目,盘回于洄渊漩复,不能自出。 ”[6]699但他同时也注意到注杜并非易事,“杜诗非易注之书,注杜非小可之事,生平雅不敢以注杜自任,今人知注杜之难者鲜矣。 ”[7]224因此,他在注杜过程中努力做到“慎之又慎,精之又精”[6]1351,即至临终前,仍然为杜诗某章句之疑义不能释怀。钱曾回忆说:“此我牧斋笺注杜诗也。年四五十即随笔记录,极年八十书始成。得疾著床,我朝夕守之。中少间,辄转喉作声曰:杜诗某章某句,尚有疑义。口占析之以属我,我执笔登焉,成书而后,又千百条。临属纩,目张,老泪犹湿,我抚而拭之曰:而之志有未终焉者乎?而在而手,而亡我手,我力之不足,而或有人焉,足谋之而何恨。而然后瞑目受含。”[13]可见,其笺注杜诗是抱着很严肃的态度来进行的。在注杜的过程中,为了确保诗、史联系的客观性,其对杜诗进行了编年,并附之以年谱,列时事、出处、诗等条目,“大意专为刊削有宋诸人伪注、谬解、烦仍、春駮之文。 ”[6]1350另外,其究明史实,以窥杜甫的创作心态在诗中的反映,呈现出以史证诗的注释方式。“谦益之与杜集最注意者,多在考证事实,以探揣杜陵心事。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则考开元末制为老子立玄元皇帝庙,而杜诗乃讥其不经也。如《洗兵马》则考李泌、房琯之罢相皆出于肃宗之疑忌,而杜诗则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用父之贤臣也。如《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则考安史乱后各藩镇有拥兵自固之势,乃劝其各效法李、郭尽心为忠臣孝子。如《诸将》五首,则考代宗时诸将,而杜诗皆有刺责之意也。”[14]清代杜诗学家黄生对此有较高评价,他在《聂耒阳》诗后说:“钱牧斋笺注杜诗,引据该博,矫伪鈲伪,即二史(《旧唐书》《新唐书》)之差谬者,亦参互考订,不遗余力,诚为本集大开生面矣。 ”[15]卷四
钱谦益对杜诗《洗兵马》的笺注颇能实践以史证诗的方法,并充分展示出其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同时也用以借古讽今,对自己所处明末的政治状况予以讥评,因而具有推陈出新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杜甫《洗兵马》诗云: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日报清昼同。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祗残邺城不日得,独任朔方无限功。京师皆骑汗血马,回纥餵肉蒲萄宫。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司徒清鉴悬明镜,尚书气与秋天杳。二三豪俊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东走无复忆鲈鱼,南飞觉有安巢鸟。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鹤禁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誇身强。关中既留萧丞相,幕下复用张子房。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遇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青袍白马更何有,后汉今周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隐士休歌紫芝曲,词人解撰河清颂。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淇上健儿归莫懒,城南思妇愁多梦。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
钱谦益笺注云: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首叙中兴诸将之功,而即继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銮之地,安不忘危,所谓愿君无忘其在莒也。两京收复,銮舆反正,紫禁依然,寝门无恙,整顿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灵武诸人何与?诸人徼天之幸,攀龙附凤,化为侯王,又欲开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岂非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贱而恶之之辞也。当是时,内则张良娣、李辅国,外则崔圆、贺兰进明辈,皆逢君之恶,忌疾蜀郡元从之臣。而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琯、张镐。琯既以进明之谮罢去,镐虽继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谆复言之。青袍白马以下,言能终用镐,则扶颠筹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忧之也,非寻常颂祷之词也。张公一生以下,独详于张者,琯已罢矣,犹望其专用镐也。是时李邺侯亦先去矣,泌亦琯、镐一流人也。泌之告肃宗也,一则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则曰,上皇不来矣。泌虽在肃宗左右,实乃心上皇。琯之败,泌力为营救,肃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辞还山,以避祸也。镐等终用,则泌亦当复出,故曰:‘隐士休歌紫芝曲’也。两京既复,诸将之能事毕矣,故曰:‘整顿乾坤济时了’。收京之后,洗兵马以致太平,此贤相之任也。而肃宗以谗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贤臣,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13]卷二
杜甫《洗兵马》大约作于乾元元年(758),在诗作的前一年,即至德二年(757),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安史之乱基本平息。虽然邺城仍未收复,但河北一带逐一收复。前方的捷报,让在长安的杜甫兴奋不已,遂作此诗来唱起中兴的凯歌。就“洗兵马”题意来看也是表示洗刷兵器,此后不再有战事发生。后人一般因此认为这首诗为颂歌,而钱谦益独有不同,以“刺肃宗也”为诗的主旨,认为肃宗既不能“尽子道”,又不能“信任父之贤臣”,颇有借古讽今之意。钱谦益的这一笺注与写于崇祯七年的《读杜二笺》内容基本相同,可以视作是对当时情境的一种表述,其所讽喻者当为刚愎自负,充满猜忌之心的崇祯皇帝。崇祯元年,东林党重要人物相继殉难,钱谦益以党魁名声大噪,拟枚卜入阁,一了夙愿,然为奸臣温体仁以天启浙闱事纠劾,崇祯皇帝信其言,而将钱谦益革职,后以温体仁为相,尽黜朝中正人君子,小人得势,国事糜废,危如累卵。笺注中,钱谦益以房琯自比,称颂其为“贤臣”,倘能用之,太平可致。崇祯不能任用“贤臣”,最终也只能落得国破身亡的悲惨结局。对于钱谦益的这一笺注,后人争论颇多,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清人潘耒《书杜诗钱笺后》批评说:“《洗兵马》一诗,乃初闻恢复之报,不胜欣喜而作。宁有暗含讥刺之理。上皇初归,肃宗未失子道。岂得预探后事以责之,诗人以忠厚为本,少陵一饭不忘君,即贬谪后,终其身无一言怨怼,而钱氏乃谓其立朝之时,即多隐刺之语,何浮薄至是,噫,此其所以为牧斋与?”浦起龙也说:“钱笺此等,坏心术,堕诗教,不可以不辩。予岂为肃宗曲护哉?”[16]卷二胡小石却给予了较高评价:“昔钱牧斋作《草堂诗笺》深得知人论世之义,高出诸注家。关于《洗兵马》一篇,即发扬玄、肃当时宫闱隐情。”[17]比较而言,萧涤非先生的评价较为公允:“钱谦益以为‘刺肃宗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是有见地的,但句句都解作刺肃宗,却未免‘深文’,且不近人情,违反诗的基本情调。 ”[18]
四、出入宋元——《有学集》
《有学集》为钱谦益入清后的作品,共50卷,其中诗歌13卷,存诗900余首,分别为《秋槐诗集》、《秋槐诗支集》、《秋槐诗别集》、《夏五诗集》、《绛云余烬集》、《高会堂诗集》等,另有《序》8 卷,《赠序》1 卷,《寿序》3 卷,《记》2 卷,《墓志铭》6卷,《神道碑》2 卷,《塔铭》1 卷,《传》1 卷,《书》3卷,《疏》1 卷,《赞》1 卷,《杂文》2 卷,《题跋》4 卷。邹式金《牧斋有学集序》云:“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罅锤,北地为之降心,湘江为之失色矣。”[1]952钱谦益出入宋元的诗学观念已普遍为后人所认可。如乔亿《剑溪说诗》亦云:“自钱受之力诋弘、正诸公,始缵宋人余绪,诸诗老救之,皆名唐而宗宋,此风气一大变也。 ”[19]钱谦益由此被认为是清初开宋风之先者。早在启、祯间,在程嘉燧的影响下,钱谦益已开始沾染宋风,“仆少壮失学,熟烂空同、弇山之书。中年奉教孟阳诸老,始知改辕易向。孟阳论诗,自初、盛唐及钱、刘、元、白诸家,无不析骨刻髓,尚为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剑川、遗山。余之津涉,实与之上下。 ”[6]1359至于入清后的《有学集》即是钱谦益这一诗学观念的理论和实践的范例,其原因大略有三个方面。
首先,遗民情结。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宋亡于元与明亡于清有着类同的演进轨迹,宋遗民以哀伤的笔调抒写着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这让明遗民心有戚戚焉。清初邵廷采曾说:“于乎!明之季年,犹宋之季年;明之遗民,非犹宋之遗民乎?曰:节固一致,时有不同。”正是这种自觉的身份认同,使明遗民对宋遗民的生存状态及所为歌诗生出由衷的亲切感。因此,自诩为明遗民的诗人们在经历鼎革的伤痛之后,以宋诗为旨归,聊以慰藉对故国的怀念。涉足宋、元的钱谦益倡导“宋存而中国存,宋亡而中国亡”[6]1343的民族思想,鼓吹“宋之亡也,其诗称盛”,并列举了诸多遗民诗,称赞其可以“续史”:“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沍寒,风高气傈,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6]800可见,其对宋遗民诗的重视。于是其有感于元人吴立夫所撰宋遗民事为 《桑海余录》,因欲作《续桑海余录》。“元人吴立夫读龚圣予撰文履善、陆君实二传,辑祥兴以后忠臣志士遗事,作《桑海余录》,有序而无其书。本朝程学士克勤,取立夫之意,撰《宋遗民录》,谢皋羽已下,凡十有一人。余惜其仅止于斯,欲增而广之,为《续桑海余录》。 ”[6]1607在《张子石六十寿序》中,钱谦益甚至将谢皋羽、龚圣予等宋遗民诗人与殉国的文天祥、陆秀夫等民族英雄相提并论,为世之“砥柱”。“嗟乎!天之生贤才也,固不欲使之虚生浮系,无所系于斯世也。不幸而值阳九百六,晦冥薄蚀之期,而其所系于斯世者有异。有以一身百口,血肉涂炭而系之者,文履善、陆君实之徒也。有以寸管尺幅,笔舌啸歌而系之者,谢皋羽、龚圣予之徒也。……世有皋羽、圣予其人,诚令与履善、君实比志而系功,其为斯世之砥柱则一也。”因此,其对南宋诗人陆游慷慨悲壮的诗风颇多推崇,自认“余生晚景,良可师法”[6]930,颇有英雄相惜之感。
其次,摒弃俗学的需要。在《李贯之先生存余稿序》中,钱谦益说:“宋、元以来,学者穷经读书,确有师承,幼而学,壮而成,老而传端序。经纬精详,次第具在。宋学士之誌曾鲁者,如金科玉条,不可更易。世降道衰,教学偏背,烦芜之章句,熟烂之时文,剽贼傭赁之俗学,耳食目论,浸淫熏习,而先民辨志敬业之遗法,不可以复考矣。迨其末也,世益下,学益驳,謏闻曲见,横骛侧出,聋瞽狂易,人自为师。世所号为魁士硕儒,敢于嗤点谟诰,镌夷经传大书浓抹,以典训为剧戏。驯至于黄头邪师,弥戾魔属,充塞抗行,交相枭乱,而斯世遂有陆沉板荡之祸。呜呼!学术之失也,以其离圣而异躯,捐古而近习。方其滥觞也,朱黄丹铅,鑽纸弄笔,相与簸弄聪明,贸易耳目。而其极也,经学蠹,人心玘。三才五常,各失其所。率兽食人,于是焉始。古者谓之非圣无法,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者,诛不以听,岂过也哉!”[6]784在这段话中,钱谦益把明亡之因归咎于俗学之失,致使学风败坏,以至于“经学蠹,人心玘”。反之,宋、元之学者“穷经读书”,“经纬精详,次第具在”。钱谦益认为:“末学之失,其病有二,一则蔽于俗学,一则误于自是。”对此,欲挽回学风,必须反经正学。“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6]1314对于李贯之为学能够“以六经为根祗,以程、朱为绳尺”,表示称赏:“其殖学以六经为根祗,以程、朱为绳尺,当斯世邪说横议,横流沦乱之日,仞其师说,强立不返,没身而已者也。”[6]784在《顾麟士诗集序》中,钱谦益对顾麟士究明宋儒之学的作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可为“儒者之诗”。“麟士于有宋诸儒之学,沉研钻极,已深知六经之指归,而毛、郑之诗,专门名家,故其所得者为尤粹。其为诗搜罗杼轴,耽思旁讯,选义考辞,各有来自。虽其托寄多端,激昂俯仰,而被服雍雅,终不诡于经术。目之曰儒者之诗,殆无愧焉”,“余故特为之论著,庶几后之论诗者,于经学芜秽,《雅》、《颂》废坏之后,而犹知有儒者之诗,则自余之目麟士始也。”[6]823对于顾诗的称赞,体现了其反经正学,以学问为诗的诗论观念。晚年的钱谦益追慕苏轼诗歌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眉山之学,实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演迤弘奥,故能凌猎千古。 ”[6]1359
再次,反复古的需要。尤侗《彭孝绪诗文序》云:“大抵云间诗派,源流七子,迨虞山著论诋諆,相率而入宋、元一路。”[20]卷三钱谦益对于宋诗的倡导,从文学自身革新的角度而言,是出于反复古的需要。《有学集》卷四十七《题徐少白诗卷后》云:“余之评诗与当世牴牾者,莫甚于二李及弇州。”可见,钱谦益的诗文革新是建立在反复古的基础上的。针对复古派限隔时代的静态文学观,钱谦益提出了文学发展的动态源流论,其以唐宋文为例,解释说:“是故论唐文、于韩、柳之前,未尝无陈拾遗、燕许、曲江也,未尝无权礼部、李员外、李补阙、独孤常州、梁补阙也,未尝无颜鲁公、元容州也。元和以还,与韩、柳挟毂而起者,指不可胜屈也。宋初庐陵未出,未尝无杨亿、王禹偁也,未尝无穆修、柳开也。庐陵之时,未尝无石介、尹洙、石曼卿也。眉山之时,未尝无二刘、三孔也。眉山之学流入金源,而有元好问;昌黎之学流入蒙古,而有姚燧,盖至是文章之变极矣。”在钱谦益看来,文随时变,“夫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 ”[6]1343因此,历代文学各有优劣,不能一概而论,“唐人如岑嘉州、王右丞、钱考功皆与老杜争胜毫芒。晚唐则陆鲁望、皮袭美,金源则元裕之,风指秾厚,皆能横截众流。”基于文学发展观的的角度着眼,他认为诗歌“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嗟夫,天地之降才,与吾人之灵心妙智,生生不穷,新新相续。有三百篇,则必有楚骚;有汉魏建安,则必有六朝;有景隆、开元,则必有中、晚唐及宋、元。 ”[6]1563因此,宋诗的存在是有价值的。在宋代诗人中,钱谦益推崇苏轼,因其政治遭遇与自己略同,由于党争而宦海起伏。他曾有《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其一云:“朔气阴森夏亦凄,穹庐四盖破天低。青春望断催归鸟,黑狱声沉报晓鸡,恸哭临江无壮子,徒行赴难有贤妻。重围不禁还乡梦,却过淮东又浙西。 ”[6]9此组诗作于顺治四年丁亥(1647)三月,时钱谦益正于家中礼佛,而突然被捕,柳如是沉疴在床,毅然随之北上,誓以死救之。在狱中,感于时事,于是有诗寄柳如是,以作诀别。
综上而论,钱谦益在清初诗学观念发生了新变,体现了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彰显了易代之际政治危亡大背景下文人的心路历程及立言救赎的复杂心态。
[1]钱谦益.牧斋杂著[M].钱牧斋全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M].钱牧斋全集(8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42.
[4]章太炎.别录甲[A].訄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A].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钱谦益.列朝诗集序[A].有学集[M].钱牧斋全集(5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钱谦益.与毛子晋[A].钱牧斋先生尺牍[M].钱牧斋全集(7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8]金堡.徧行堂集[M].清康熙间刊本.
[9]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汪由敦.汪文端史裁蠡说[A].明史例案[M].徐蜀.明史订补文献汇编[C].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11]钱谦益.曹公神道碑[A].初学集[M].钱牧斋全集(2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2]郑庆笃.杜集书目 提要[M].济南:齐鲁书 社,1986.
[13]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4]洪业.杜诗引得[M].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 社,1985.
[15]周采泉.杜集书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8.
[17]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A].胡小石论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8]萧涤非.杜甫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10.
[19]乔亿.剑溪说诗[M].清乾隆间刊本.
[20]尤侗.西堂全集[M].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金阊聚秀堂刻本.
(责任编辑 岳毅平)
I207.22
:A
:1001-862X(2011)02-0171-09
张永刚(1977-),男,山东枣庄人。复旦大学博士后,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晚明政治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