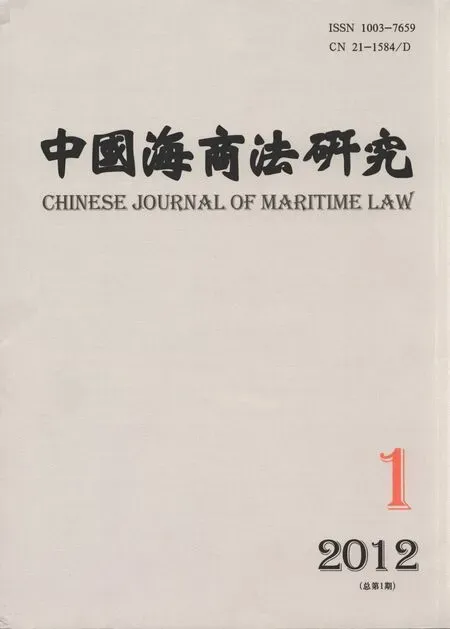“最先受诉法院原则”与禁诉令的博弈*
张丽英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北京 100088)
依欧盟法院2007年在the“Generali A ssicurazioni Generali Spa v.West Tankers Inc”案(the“Front Comor”案)①参见West Tankers Inc v.RA S R iunione A driatica di Sicurta Spa(The“Front Comor”)[2007]1L loyd’s Rep 391。中的判决,英国法院的禁诉令与《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布鲁塞尔公约》(B russels Convention on J urisd iction and the Enf orcem ent of J udgm ents in Civil and Comm ercial Matters,简称《布鲁塞尔公约》)中的“最先受诉法院原则”不符。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的规定,“相同当事人就同一诉因在不同缔约国法院起诉时,首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主动放弃管辖权,让位于首先受诉法院受理。需放弃管辖权的法院,在其他法院的管辖权被提出异议时,得延期作出其决定。”该规定即为,由最先受理的法院决定谁有管辖权,在其做出裁决之前,后受理的法院必须中止本国法院的诉讼。《布鲁塞尔公约》的“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只涉及解决欧洲境内的管辖权冲突问题,近期有数个涉及英国仲裁与中国司法管辖权冲突的案例,英国法院并不考虑“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尽管中国当事人已在中国某法院进行了起诉,英国法院还是向中国当事人发出了禁诉令。笔者拟就相关管辖权冲突的解决、“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禁诉令”的效力等问题进行论述。
一、英国法院对中国当事人发出的“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
近年来,英国法院不断向中国当事人发出禁诉令,以“禁止”中国当事人在中国的在先诉讼。最近的案例是2011年“N iagara海运公司诉天津钢铁集团”案①参见N iagaraMaritime S.A.v.Tianjin Iron&Steel Group Co.L td.,[2011]EWHC 3035(Comm)。,该案中的N iagara海运公司与天津钢铁集团订立了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由N iagara海运公司将天津钢铁集团的一批货物由巴西运往中国。航次租船合同中约定适用GENCON 94,GENCON 94中包含“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提交英国仲裁”的条款。运输中N iagara海运公司的船舶与他船相撞搁浅。天津钢铁集团为了能顺利收货,支付了救助费用。后天津钢铁集团以N iagara海运公司未能将货物安全送达目的地为由,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N iagara海运公司赔偿已经支付的救助费用。N iagara海运公司则认为本案应当依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英国仲裁,当天津钢铁集团拒绝在英国仲裁后,N iagara海运公司向英国王座法院商事法庭提出签发临时禁诉令的紧急申请,限制天津钢铁集团及其保险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在中国的诉讼。N iagara海运公司则向中国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
在2007年英国法院处理的另一起案件中,英国法院也向中国当事人发出了禁诉令。2007年的the“Starlight Shipping Co.v.Tai Ping Insurance Co.L td.”案②参见Starlight Shipping Co.v.Tai Ping Insurance Co.L td.(HubeiBranch),[2007]EWHC 1893(Comm)。,英国法院也是依该条规定,向中国保险人签发了紧急临时禁诉令。法院认为,如英国法院不及时发出禁诉令,中国法院即会开始对案件的实体审理,因而无法阻止在中国法院的诉讼程序。根据英国法院的判例,通常在保险人向船东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法院才会对保险人签发禁诉令。法院认为保险人虽然不是合同的当事人,但是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限制。
上述两案都是在中国的诉讼在先,但英国法院还是签发了禁诉令。对于在此种情况下英国法院发出的禁诉令,中国法院一般不予承认。例如,在宁波海事法院(1996)甬海商初字第207号民事判决书中,1996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河北省分公司诉塞浦路斯瓦塞斯航运有限公司(V ysanthi Shipping Co.L td.)海难救助费用分摊一案,该案涉及同一诉因,既在中国进行了诉讼,又在英国进行了仲裁。宁波海事法院认为,本案收货人中国饲料进出口公司与被告塞浦路斯瓦塞斯航运公司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但本案涉及的是救助费用的追偿,故不应适用提单约定的伦敦仲裁条款,依最密切联系原则,收货人因海难救助费用的追偿可在中国法院向承运人提起诉讼,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保险人作为收货人的保险公司,依保险合同赔付收货人承担的救助费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有权向有责任的承运人追偿。该案与上述2011年的案例非常相似,均涉及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是否受提单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的问题。此类案例,如接到禁诉令的中国保险人在英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就会面临强制执行的危险。
二、先后之诉是否为同一诉因的争论
2011年“N iagara海运公司诉天津钢铁集团”案涉及航次租船运输合同中的伦敦仲裁条款是否适用于救助之后的保险人代位求偿关系。关于此类关系是否属于同一诉因并因此受运输合同的仲裁条款约束的问题,the“Starlight Shipping Co.v.Tai Ping Insurance Co.L td.”案是目前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一个案例。该案中,Starlight运输公司与T ransfield公司签订航次租船合同,合同中约定,因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提交英国仲裁解决。T ransfield公司向货主签发了并入租约的提单。后“A lexandros T”轮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导致船舶和货物都灭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武汉分公司)因赔偿了武钢集团而取得代位权,在武汉海事法院起诉Starlight运输公司和T ransfield公司,要求其对货物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两被告对中国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同时,Starlight运输公司向英国法院申请签发禁诉令,认为中国的诉讼程序违反了提单中的仲裁条款,并主张,依英国《1981年最高法院法》第37条(1)的规定,即使仲裁程序没有开始,法院也有权利签发禁诉令。但太平洋保险公司及武钢集团认为,依中国法,提单中的仲裁条款是无效的,中国法院不会承认英国仲裁庭或英国法院的裁决。但英国法院支持了Starlight运输公司的主张,认为当事人选择适用了英国法,则提单和航次租船合同均应适用英国法。武钢集团是提单的持有人,应遵守并入提单的仲裁管辖条款,不可将争议提交除英国仲裁以外的其他纠纷解决程序。除非受诉法院有强烈的管辖理由,否则英国法院当然可以限制在非合同选择的法院起诉。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4条:保险人行使代位请求赔偿权利时,被保险人未向造成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提起诉讼的,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该第三人提起诉讼。而英国则通过判例法将保险人应当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规则确定下来。虽然太平洋保险公司不是合同的当事方,但根据英国判例,在代位求偿问题上是以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人主张权利的①参见James Nelson&Sons L td.v.Nelson L ine(1906)2 K.B.217.O riental Fire&General Ins.Co.v.American President L ines(1968)2 L loyd’s Rep.372.The Esso Bernicia(1989)1 L loyd’s Rep.8。。因此,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时也应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海事关系比较复杂,而且具有流动性的特点,如随着提单的转移,会涉及提单中的管辖条款对非运输合同当事人,但却是提单持有人的收货人是否有效的问题。在保险人对货损作出赔偿后,会产生提单或租约中的管辖条款是否对合同外的第三人产生效力的问题。关于运输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对保险人有约束力的问题,已有案例判决保险人在代位求偿时也受提单中仲裁协议管辖条款的约束②参见Insurance Co.of N.America v.S/S Contract Voyager,1983 AMC 2895(S.D.N.Y.1983);A llied Chem ical Inter-American Corp.v.Piermay Shipping Co.,1978 AMC 773(A rb.N.Y.1977);Newport Tankers Corp.v.Phillips Petroleum Co.,1973 AMC 666(S.D.N.Y.1973)。;在提单上所载的货物被救助之后,会涉及有关救助的争议是否也属于与提单有关的争议,从而使救助人也要受提单中的仲裁条款约束的问题等。实践中,有的案例中判决提单中的管辖条款对担保人有效③参见Compania Espanola de Petroleos,S.A.v.Nereus Shipping,S.A.,527 F.2d 966,1975 AMC 2421(2d Cir.1975);In re TransrolNavegacao S.A.,782 F.Supp.848,1992AMC 1831(S.D.N.Y.1991),O&Y Landmark A ssociates v.Nordheimer,725 F.Supp.578(D.D.C.1989)。,也有的案例中判决提单中的管辖条款对抵押权人有效④参见Wells Fargo Bank Int’l Corp.v.London S.S.Owners’Mutual Ins.A ss’n 408 F.Supp.626,1976 AMC 592(S.D.N.Y.1976)。。这些案例的共同点是:提单的效力是否会外溢继而涉及到非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关于提单或租约中的管辖协议是否约束其后产生的新协议关系的问题是有争议的:肯定说认为,新协议是为了保证原协议履行而设的,因此应属于原协议的延伸或组织部分。否定说则认为尽管新协议是为保证原合同的履行而设,但当事方围绕该协议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已远远超出了原协议的约定,因此,应视为当事人间具有独立意义的新协议,当然也不受原协议中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的约束。双方争诉的问题也可能因法院认为不属于管辖协议的范围而否定协议管辖⑤参见Son Shipping Co.v.De Fosse&Tanghe 613 F.Supp.916。。由于海事关系的复杂性,海事合同管辖条款的效力范围常常受到质疑。
三、禁诉令的法律效力
上述几案均涉及在中国已有在先诉讼,英国法院还是签发了禁诉令的问题。禁诉令是在管辖权冲突的情况下,本国法院发布的禁止当事人在他国法院提起或继续诉讼的命令⑥参见Castanho v.Brown and Root(U K)L td.[1981]AC 557。,违反禁诉令则可能因藐视法庭而受到惩罚。希望在本国诉讼的当事人可通过该措施有效稳定已取得的管辖权。在认为外国法院为不适当的法院时⑦参见British A irways Board v.Laker A irways L td.,[1985]AC58(HL)。,为了防止出现国内和国外相互矛盾的判决,英国普通法允许在外国诉讼的被告向国内的法院申请“禁诉令”(anti-suit injunction),命令原告退出该外国的诉讼⑧参见The“Angelic Grace”,[1995]1 L loyd’s Rep.87。。可见,禁诉令在肯定本国管辖权的同时,其矛头也指向外方当事人。此时便会涉及该禁诉令的域外效力问题,实践中,该命令的效力往往得不到外方当事人所在国法院的承认。当管辖权发生冲突时,中止在本国的诉讼是可行的,而制止在外国的诉讼,就有不尊重他国主权或者干预他国法院审判权之嫌。对此,英国法院认为,当法院通过禁止令制止在外国的诉讼时,并非试图指令外国法院。因为“禁止令不是针对法院的,而是对当事人发出的”。禁止令从效果上会影响另一个管辖法院的诉讼。因此,禁诉令的签发要十分谨慎①参见Logan v.Bank of Schtland(No.2)[1906]1 K.B.141.Settlement Corporation v.Hochschild[1966]Ch.10,15。,只有在避免严重的不公正,或违反了排他的司法或仲裁管辖协议的情况下才可使用②参见ContinentalBank NA v.Aeakos Compania S.A.,[1994]1 L loyd’s Rep.505。。同时,应避免不适当干预另一个国家法院管辖权的情况出现。[1]
英国法院是否能针对在境外的当事人签发禁诉令是比较复杂的,在the“T ropaioforos(No2)”一案中③参见The“Tropaioforos(No2)”,[1962]1 L loyd’s Rep.410。,原告认为,英国法院无权制止未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在外国的诉讼。而英国判例则认为,只要该外国当事人违反了在英国的仲裁协议在外国诉讼④参见Tracom in S.A.v.Sudan O il Seeds Co.L td.(Nos 1 and 2)[1983]1WLR 1026。,或依英国《最高法院规则》第11号令可以向其送达,即可对居住于境外的人发出禁诉令⑤参见The“Tropaioforos”,[1962]1 L loyd’s Rep.410。。实践中,从欧洲国家的态度来看,尽管依英国普通法,禁诉令并不是针对外国法院的,但德国法院始终拒绝承认和执行英国法院对德国自然人或法人发出的禁诉令。德国法院认为,英国的禁诉令侵犯了德国的司法主权。当德国人在英国居住或者在英国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可认为英国的禁诉令是对当事人发出的,是为了禁止当事人在其他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但如果当事人在英国既没有住所也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时,英国法院的禁诉令则明显是对德国司法主权的挑战和威胁。[2]可见,禁诉令的效力并不稳定。只有在禁诉令所指向的对象在禁诉令发出国拥有财产时,该令的强制执行力才有所显现。
四、禁诉令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
一国法院发出的禁诉令实际上针对的是另一国的一个在先受理案件,是希望在另一国的当事人能停止在别国的诉讼,这就产生了禁诉令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冲突。“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给予了在先受诉法院审理案件的“优先权”,而禁诉令的目的则是制止先受诉法院的诉讼。禁诉令是由后受理案件的法院签发的,目的是使境外的当事人停止在境外的诉讼。在the“Gasser”案⑥参见Erich Gasser Gmbh v.MISAT Srl[2005]。中,被告Gasser认为,“如果根据一国内国法律某一非先诉法院针对案件享有排他性管辖权时,该非先诉法院并不应当根据“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放弃其享有的管辖权”⑦参见Opinion of AG Léger in Case C-116/02 Gasser[2003]ECR I-14693,para 83。;此外被告Gasser还请求内国法院对对方当事人实施禁诉令。这一主张亦得到了欧洲一些学者的支持,因为“禁诉令制度存在的价值基础便是保证拥有排他性管辖的内国法院的管辖权不被另一方当事人为推迟或者延缓诉讼而恶意利用”。[3]即如在先诉讼是为了拖延的目的,或是为了避免在其他合理的地点的诉讼,则不应适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此时,后受理案件的法院可以签发禁诉令,制止在境外的在先诉讼,坚持后受理案件法院的管辖权。欧洲法院认为,禁诉令制度与欧洲理事会No.44/2001号条例中对“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框架规定不一致;禁诉令制度不适用于民商事领域,该领域属于欧洲理事会No.44/2001号条例调整的范畴;且认为如在领域内适用禁诉令制度将导致司法程序效率的低下⑧参见Case C-116/02 Gasser,Para 51。。欧洲法院认为“布鲁塞尔公约体系”的基础是成员国的互信和互惠,所以在此基础上适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是理所应当的⑨参见Case C-116/02 Gasser[2003]ECR I-14693;Case C-159/02 Turner[2004]ECR I-3565;Case C-14/07,Weiss und Partner[2008]ECR I-3367;Case C-185/07 A llianz[2009]。。
(一)“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文本基础
“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在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处理一事多诉问题时均有所体现。欧洲区域性公约对“最先受诉法院原则”规定得更为具体明确。如1968年9月27日,欧共体(EC)当时的六个成员国签订的《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欧洲共同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在瑞士的洛迦诺签订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执行公约》(Convention of16 S ep tem ber 1988 on J urisd iction and the Enf orcem ent of J udgm ents in Civil and Comm ercial Matters,简称《洛迦诺公约》)。在上述两个公约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加强欧盟内部的司法合作,欧洲理事会推动一系列立法措施对《布鲁塞尔公约》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在2002年3月1日公布实施了欧洲理事会No.44/2001号条例[Council R egulation(EC)N o.44/2001 on J urisd iction andthe R ecognition and Enf orcem ent of J udgm ents in Civil and Comm ercial Matters]。上述公约针对欧盟内部的司法管辖权争议之确定以及判决之执行提供了实践操作的法律基础,也是欧洲法院解决冲突法问题的重要法律渊源。因《布鲁塞尔公约》为最基础的公约,上述三公约也称为“布鲁塞尔公约体系”。公约对“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实现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并且以《布鲁塞尔公约》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相对可以付诸实践的体系。其中,最早为“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打下基础的是《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并由此衍生出了关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具体适用方式、限制等具体规定。
依《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规定,“相同当事人之间就同一诉因在不同缔约国法院起诉时,最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当主动放弃管辖权,让最先受诉法院受理。”这是国际社会中首次出现关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明确条文表述,且该表述也为其后的《洛迦诺公约》继承发展。根据《洛迦诺公约》第21条第2款:“如果受诉在先的法院确有管辖权,则受诉在后的法院应放弃对案件的审理。”对比两个条文可以发现,在具体表述上,《洛迦诺公约》对先受诉法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定,认为先受诉法院要优先于后受诉法院,其必须“确有管辖权”。这就意味着《洛迦诺公约》规定的后受诉法院的让位力度要小于《布鲁塞尔公约》。此外,当与案件有关的几个国家规定了专属管辖的时候,后受诉法院也要让位于先受诉法院。依《布鲁塞尔公约》第23条规定:“属于数个法院有专属管辖权的诉讼,首先受诉的法院以外的法院应放弃管辖权,让首先受诉法院审理。”对此,《洛迦诺公约》第23条也有同样的规定。
(二)“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适用形态
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适用上,《布鲁塞尔公约》对非先诉法院如何放弃管辖,进而实现先受诉法院优先也进行了规定,主要有以下三种形态。
其一,非先诉法院主动放弃管辖。根据《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及《洛迦诺公约》第21条第2款,如果后受理案件的法院发现时间顺位在前的法院先受理了该案件,则非先诉法院应当主动放弃管辖权,亦即非先诉法院通过主动放弃管辖权来实现“最先受诉法院原则”。
其二,非最先受诉法院的审理延期。延期有两个方面:第一,针对正在一审状态下的延期。《布鲁塞尔公约》第22条规定:“如果有关联的诉讼案件在不同的缔约国法院起诉时,除第一个受诉法院外,其他法院在诉讼尚在审理时,得延期做出其决定。”《洛迦诺公约》第22条也有同样的规定。第二,针对案件尚未开庭时的延期。对此,《布鲁塞尔公约》没有规定,而《洛迦诺公约》第21条则进行了明确,其中规定“如果相同当事人就同一标的及同一诉因向不同缔约国的法院提供诉讼,则受诉在后的法院在受诉在先的法院确定管辖权之前,应暂缓做出开庭审理决定。”
其三,受诉法院的合并审理。依《洛迦诺公约》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在本国法律允许对案件合并审理且受诉在先的法院对审理的两个案件均有管辖权的条件下,受诉在后的法院应当事人一方的请求,也可放弃管辖权。”此条文主要是针对两个以上相关联案件的管辖权确定问题,即如果某一关联案件的当事人将案件中的一个诉讼请求先行诉至某一法院,则应当事人一方之请求,该法院可将后诉案件合并审理。
(三)“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适用限制
“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在适用中还受到了一些条件的限制。首先,只有存在未决诉讼时才援用该原则①参见Gam lestaden Plc v.Casa de Suecia S.A.and Thulin[1994]1 L loyd’s Rep.433。。即《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只适用于存在两个以上未裁决的诉讼的情况,如先受诉法院在另一国法院受理案件之前就已经做出了判决,则第21条不予适用。因为此时不存在未决诉讼,其涉及的将是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其次,在先受诉法院的原告申请撤诉的情况下,也不适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因为诉讼竞合制度要求存在着平行的、可竞争的有管辖权的法院,一旦首先受诉的法院失去其管辖权,那么受诉在后的法院也就不再受第21条的约束②参见InternationalNederland en Aviation Lease B.V.(A Corporation established under the law s of the Netherlands)and O thers v.the CivilAviation Authority and Another(unreported)High Court,13 June 1996。。
“最先受诉法院原则”还受“不方便法院原则”(non convenience forum)的限制。该原则要求对涉及他国或他法域的民事诉讼,如法官认为他国或他法域受理案件更为合适,则可自由裁量不受理该案。[4]在该原则的影响下,如果先受诉法院认为自己为非方便法院,则应当主动中止审理案件,后受诉的缔约国法院无需根据第21条因受诉在后而放弃管辖权。不方便法院原则充分考虑了当事人、法院及与案件相关的诸多因素。可见,最先受诉法院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在某些情况下,先受诉法院应当让位于“更方便的法院”。
此外,“最先受诉法院原则”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两公约均未对何谓受诉在先的法院进行规定,而是留待各国的国内法去解决,对此各国的规定不一。依英国判例,以将起诉状送达被告人的时间确定最先受诉法院①参见Dresser U K L td.v.Falcongate L td.[1992]1 Q.B.502。。而瑞典法院认为,只要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则该法院就为最先受诉法院②参见Swed.Code of Jud.Proc.,ch.13,s.4(discussing a variety of rules that either ignore foreign litigation or allow discretion to stay the local case)。。[5]欧洲各国国内法在这方面规定的差异,致使当事人竞相择地诉讼,有时会演变为双方争夺诉讼地点的赛跑,如一方当事人已在英国起诉,但还没有完成送达诉讼文书,而被告可立即向瑞典法院起诉,如瑞典法院受理的时间早于英国法院完成送达的时间,瑞典法院就成了先于英国法院受诉的法院,英国法院就不能继续其诉讼程序。由于有关国家对“受诉在先的法院”的定义不同,仍会出现两个国家的法院都认为自己是受诉在先的法院的情况,管辖权的冲突仍然没有解决。
五、对“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挑战——“意大利鱼雷”式诉讼
由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强调受诉时间优先的法院优先享有诉讼案件之管辖权,实践中便出现了当事人恶意利用此原则进而拖延、规避预期对自己不利的诉讼的情形。其原因就是上述公约在处理管辖冲突的问题时主要考虑的是时间因素,给予先行受理的法院以优先权。例如,在实践中就出现了恶意利用该原则的“意大利鱼雷”(Italian Torpedo)式诉讼,即当事人为防止案件在其他法院审理,首先在其选择的法院恶意提起确权诉讼,其恶意选择的法院往往程序复杂,使得案件审理非常缓慢,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由于有最先受诉法院的限制,无法再诉诸其他法院。[6]此种利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作法,由于是根据意大利司法程序缓慢的特点被精心策划出来的,也被称为“意大利鱼雷”式诉讼。这是一种恶意适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表现。这种“鱼雷式”诉讼策略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③参见Gesellschaft fur Antriebstechnik mbH&Co.KG(GAT)v.Lamellen und Kupplungsbau Beteiligungs KG(LuK)(C-4/03)[2006]E.C.R.I-6509;Roche Nederland BV v.Primus(C-539/03)[2006]E.C.R.I-6535;在企业信贷领域有:JP Morgan Europe L td.v.Primacom AG and O thers[2005]EWHC 508;ContinentalBank NA v.Aeakos Compania Naviera S.A.[1994]1W.L.R.588。。在the“A ngelic Grace”案④参见The“Angelic Grace”,[1995]1 L loyd’s Rep.87。中,租约中有一个概括性的伦敦仲裁条款,船舶在意大利靠泊时将承租人的泊位碰坏,承租人在意大利法院起诉船东,而船东则向英国法院申请禁诉令,英国法院认为,该案的争议属于租约中的仲裁条款的范围,承租人一方在意大利诉讼有恶意选择法院之嫌,因此发出了禁诉令,制止承租人继续在意大利法院的诉讼。
尽管“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受“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限制,但“不方便法院原则”由于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不能很好地起到限制最先受诉法院的作用,先受理的法院是不是适当的法院似乎并不重要。[7]为了使“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适用更具有灵活性和合理性,1999年《海牙民商事管辖权与外国判决公约(草案)》[简称《海牙公约(草案)》]对“最先受诉法院原则”进行了修改。
首先,《海牙公约(草案)》吸收了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适用时已采用的不方便法院原则,规定对于依据相同诉因提起的诉讼,推定最先受理法院优先于其他法院享有管辖权,但在例外的情形下,如能证明第二受诉法院或其他法院明显更适于审理解决该纠纷的话,可推翻上述推定⑤参见1999 Draft Hague Convention,art.21.and art.22。。
其次,对恶意适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防止。在《布鲁塞尔公约》的适用中,出现了当事人恶意利用该原则,进行“意大利鱼雷”式诉讼的做法,该行为的目的是使被告抢在原告的前面选择法院进行诉讼,促使案件不能在一个自然方便的法院审理。[8]为避免恶意利用先诉法院原则的发生,《海牙公约(草案)》起草委员会在2001年6月召开的外交会议中达成了一个文本,对此进行了限制。[9]依文本第2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就相同诉因向不同缔约国的法院提起诉讼时,如果最先受诉法院根据公约规定拥有管辖权,且预计该法院做出的裁决能够在第二受诉法院所在国家得到承认的情况下,第二受诉法院则应中止诉讼程序。文本第21条第3款和第6款是关于防止恶意利用“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限制规定。依第3款,如原告未采取行动促使最先受诉法院对案件进行实质审理或最先受诉法院未能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做出判决,则第二受诉法院可以继续审理本案。第6款又规定,如果最先受诉法院的目的只是做出一个消极的确权诉讼,则通常情况下的未决诉讼规则就不能适用了。在当事人的申请下,如预期第二受诉法院做出的判决能够依该公约得到承认,此时先受诉法院应中止诉讼程序。简而言之,首先仍推定最先受诉法院有管辖权,但在最先受诉法院恶意提起确权诉讼的特殊情形下,该原则不能适用。
再次,案件合并审理的扩大。《海牙公约(草案)》不仅规定了关于最先受诉法院的优先管辖权以及对此管辖权的限制,而且还允许在平行诉讼的情况下,采取合并诉讼程序。并扩大了最先受诉法院可以放弃管辖权的情形。该草案规定,如某些诉因相关的诉讼在不同的法院均未审结,而且通过合并诉讼对当事人有利,最先受诉法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通过自由裁量权,将该案件移送一个更适合法院,由其合并审理整个案件。
尽管欧洲法院在实践中对“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反复适用,但是学界也未停止对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质疑与批判。由于“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管辖权的确定主要依赖于时间顺位上的优先,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恶意利用该原则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这同时也是学界对该原则诟病的主要原因。
“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产生为解决一事多诉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该方法最初的规定比较简单,于是产生了恶意利用的情形。后来的发展使该原则更加完善,更具有灵活性。该原则的缺陷之一是在其适用前提上,该原则只适用于相同的“未决诉讼”中。《布鲁塞尔公约》和《洛迦诺公约》的第21条将“未决诉讼”界定为“相同当事人”和“相同诉因”的诉讼。则在适用该原则前,得先确定是否为“相同的当事人”以及“相同的诉因”。何为“相同当事人”和“相同诉因”实际上是由法院来自由裁量的,因此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欧洲法院对“相同诉因”含义的解释是:基于相同合同关系而产生的诉讼,且诉讼标的也是相同的①参见The“Tatry”[1994]ECR I-5439。。有的案例中判决,仅有相同的诉因,但没有相同的目的仍然不属于“相同诉因”,而拒绝中止在后的诉讼②参见ContinentalBank NA v.Aeakos S.A.,[1994]1WLR 588。。在“相同当事人”方面,当事人为了避免因属于相同的未决诉讼而被中止,通过增减当事人或诉因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避免被纳入未决诉讼。再有,英国有案例认为,《布鲁塞尔公约》并不适用于对物诉讼③参见The“Deichland”,[1990]1 QB 361.The“Indian Grace”,[1996]1 L loyd’s Rep.12。,因为对物诉讼的被告并不是自然人或法人。但欧洲法院持有不同观点,认为《布鲁塞尔公约》第21条同样适用于在英国的对物诉讼与在他国进行的对人诉讼之间的冲突④参见The“Tatry”[1994]ECR I-5439。。对上述相关问题的不同理解仍然给一事多诉留有余地。
五、结语
尽管“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有诸多缺陷,该原则仍有一定的可以借鉴的地方,特别是“最先受诉法院原则”的新发展,对恶意适用该原则已有了一定的遏止作用。该原则最大的缺点是先受理的法院可能被恶意利用。[7]经过《海牙公约(草案)》修改后的最先受诉法院原则很具有借鉴的意义。“最先受诉法院原则”机械的一面应当去除,应将该原则与“不方便法院原则”结合使用,对于依据相同诉因提起的诉讼,可以先推定最先受理法院优先于其他法院享有管辖权,但如果第二受诉法院被证明更适合于审理解决该纠纷,上述推定将会被推翻。对于“相同诉因”,应规定一定的法定判断标准,以避免在判断上的不确定性。有条件地给予最先受诉法院以优先的管辖权,也符合“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如果某一案件的同一要求已由某国法院受理,或者已作出有效的判决,另一国法院就不应该对该案件的同一要求再予受理,这是国际上公认的一条原则。经过发展的“最先受诉法院原则”也对中国解决与他国法院的管辖权冲突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D ICEY A V,MORR IS J H C.D icey andMorris on the conflict of law s[M].London:Sweet&Maxwell,1980:250.
[2]F ISHER G.A nti-suit injunctions to restrain foreign proceedings in breach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J].Bond Law Review,2010(1):1-25.
[3]CLARKE A.The differing approach to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and the courts of England andWales[M].N ew York:A spen Publishers,2007:101,105.
[4]FR IENDEU THAL J H,KAN E MK,MI LL ER A R.Civil procedure[M].2nd ed.N ew York:West Publishing Co.,1993:87-89.
[5]FAWCETT J J.Declining jurisdiction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M].A lderley:Clarendon Press,1995:34.
[6]MOORE K A.Rethinking forum shopping in cyberspace,symposium on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the role of national courts[J].Chicago-Kent Law Review,2002(77):1325-1358.
[7]FL ETCHER I F.Conflict of law s and European community law: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ommunity conventions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M].Am sterdam:North-Holland Pub.Co.,1982:133.
[8]DREYFU SS R C,GI N SBURG J C.D raft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judgment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matters[J].Chicago-Kent Law Review,2002(77):1065.
[9]BRAND R A.Comparative forum non conveniens and theH ague Conventionon jurisdiction and judgments,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forum shopping[J].Texas InternationalLaw Journal,2002(3):467-4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