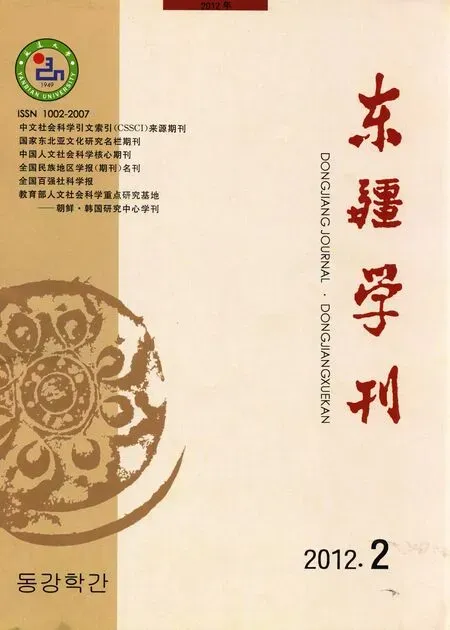《西京诗话》作者生年及成书时间补正
甘春妍
《西京诗话》作者生年及成书时间补正
甘春妍
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编纂的《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太学社,首尔,1996年),是东亚汉诗文献整理的重要著作。然而其中解题尚有未为尽善者,实白璧之微瑕。笔者在此补证其中《西京诗话》作者金渐的生年及《西京诗话》的成书时间,以求正于诸位中外专家学者。
《西京诗话》载《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第十三册,赵氏题解曰“金渐(生平未详)。”[1](569)前此赵氏在其博士论文《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中有介绍:“《西京诗话》三卷,补录一卷。金渐(生平不考)撰。此书姑未刊出。唯一钞本收藏于故汉城大学郑炳昱教授书斋。撰者金渐不知何许人,唯有自序两篇,以为‘戊申孟夏盆城金渐叙’,又有‘癸丑仲秋初吉再书’,则自戊申至癸丑有五年,可知此书成于五年余之期间,但不知戊申、癸丑为何年,只待他日考证而已。”[2](287)
依赵氏上述介绍,虽然作者生平未详,成书时间不确定,但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考证的线索:考索出金渐的生存年代,则成书时间之戊申、癸丑即可断定。那么,金渐生存年代的最好内证就是《西京诗话》中金渐的交游。
《西京诗话》卷一曰:“近日词场自文山外,一方觚墨之士特为彬蔚。余所获师友者,吾箕则李骑省时恒,中和则林司艺益彬,德川则许上舍徽,义州则金员外楚直,殷山则康员外侃。或以诗显,或以赋称,惟林、李二丈最为知己。”[1](581)考李时恒生于1672年,林益彬生于1680年,许徽生于1682年,金楚直生于1683年,康侃生于1700年。据金称,李时恒、林益彬为“二丈”,则金渐年岁小于林、李二人。那么,1680年以后的戊申年只有1728年,癸丑年只有1733年。则《西京诗话》只能成书于1728至1733年间。
另外一条内证,《西京诗话》卷二:“近世……高承宪七十,俱以明经得第。”[1](615)查朝鲜《承政院日记》,英祖丙午(1726)七月十六日:“平壤人高承宪,癸卯年登第,未分馆而死。”此癸卯乃1723年(景宗四年)。则成书时间戊申亦为1728年,癸丑为1733年。
关于金渐的生年,还有一条内证。《西京诗话》卷一:“李耳鸣斋仁采善实,少负精敏,生支干与余同,入国庠盖又同榜也。”[1](581)查李仁采字善实,号耳鸣斋,平昌人,居平壤。生于1695年乙亥,景宗元年(1721,辛丑)增广试进士三等第一。金渐言“生支干与余同”,又言“岁辛丑,余侥幸成进士,诣太学,谒先圣。”[1](581)则金渐亦应于1695年乙亥生,以1721年登进士。
以下再从外证考察。
查《辛丑圣上即位增广别试司马榜目》,金渐,乙亥生,二等第十名。则金渐生于1695年无误。
另一条外证,稍晚于金渐的蔡济恭(1720-1799),号樊岩,其《樊岩先生集》卷之五十五《李忠伯传》有:“樊岩子曰:李忠伯特狗屠之雄,然其勇敢亦不世出者欤?余自幼少闻有李忠伯者,撄朴烨之怒能不死,颇壮之。及为关西伯,阅箕城文士金渐所为文,其叙忠伯事颇详。然惜其杂之以琐节三四段,使大侠 弛之风反为所 。遂点窜为《李忠伯传》。”
按《西京诗话·补录·谐谑》:“李佥枢忠伯,人畏之如虎。惟为李山人景业作弄器,愤之。一日晨,白山人入门,李突出骑其腹,唤友国忠:‘趣持剑来,今日杀此竖子。’山人怡然曰:‘国忠勿持剑来,吾与若主未知孰死?’李笑而起。”[1](669《)西京诗话·补录·标致》:“康公后说威容穆穆,乡党见之如神。尝从李忠伯贷白金百两,过期不还。李屡趣之,康意殊落落。一日,李早作,戟手大骂曰:‘我见康,其必刃之。’遂诣康,略叙数语,潜发所佩刀以拟康。康忽一顾,李不觉手栗,即奉头长跪曰:‘好宝剑,敢以献左右。’终不能及银事。”[1](660)此二则皆有损李忠伯形象,与蔡文“杂之以琐节三四段,使大侠 弛之风反为所 ”合。
综上考证,《西京诗话》作者金渐生于1695年,《西京诗话》成书于1728年(戊申)至1733年(癸亥)之间。
[1]赵钟业:《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首尔:太学社,1996年。
[2]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4年。
(甘春妍,女,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