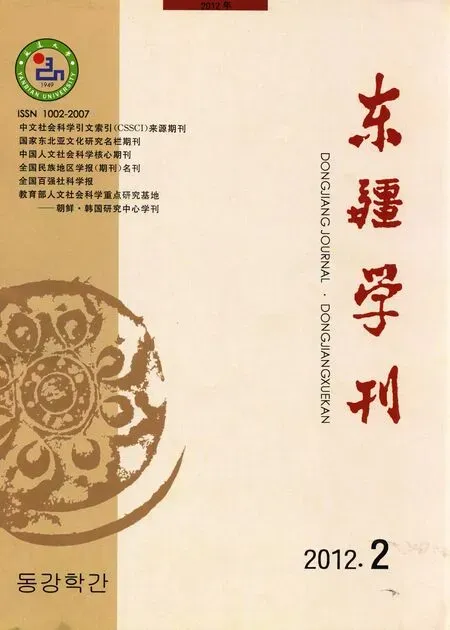经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门诠释学
曹洪洋
经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门诠释学
曹洪洋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诠释学已成为这个时代哲学的“共通语”。能否借鉴西方诠释学成果或者透过其理论视域来思考经学的有关问题,是一个颇具意义的话题。然而,自“诠释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以来,操用诠释学的术语和理论来谈论中国学术问题的学者尚未真正抓住诠释学的主题,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诠释学的存在论内涵的忽视。我们无法仅从经学本身所必定包含的文本理解与解释的因素就简单地判定经学是一门诠释学,而是应该紧紧把握诠释学所展开的“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认识理想”的批判来看待经学研究本身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否立足于“一种对方法论合理性的遗弃”,是经学诠释学是否可能的理论基点。
诠释学;经学;经;章太炎
一
2010年8月4日的《中华读书报》刊载了李学勤先生在“经学:知识与信仰”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名为《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他谈到,“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儒学是主流,它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特别大,而经学又是儒学的核心。不研究经学,不了解经学,应该说就没有把握住我们传统文化的主流和核心的部分”;同时他又指出,“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研究经学”,对于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做明确的回答,需要大家作广泛的探讨。[1]根据我们的理解,李学勤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其主旨在于提醒我们,不应把“经”视为已经“死亡了”的东西,只做一种纯粹的考古学的研究,而是应该立足于时代,提取其本身在当下所应当具有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怎样研究经学”这个问题直接与经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相关。
从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文化和思维就已处于继“认识论转向”和“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第三个转向——“诠释学转向”之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诠释学已成为这个时代哲学的真正的“共通语”。[2](5)在这种背景下,能否借鉴西方诠释学所取得的成果或者透过其独特的理论视域来思考经学的有关问题,着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我们认为,诠释学与经学是否能够汇通成一种“可通约的”(commensurable)学术话语,并不依赖于一种建立所谓经学诠释学的“良好意愿”(the good will),而是要立足于诠释学所提倡的那种基于问答辩证法的对话,即能够真正透过经学与诠释学的视域进行彼此观照的学术对话。在这种情况下,能否真正把握诠释学的内涵将成为进入这种对话的一个前提。
二
现实中对诠释学有一种偏离其哲学背景的“通俗的”理解,即只是将其视为一门关于“诠释”的“学”,亦即某种解释理论。然而,本文认为,在当代学术话语中所使用的“诠释学”一词,并不是指那种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解释活动,而主要是指一套具有普遍的理论形态的观念体系——作为哲学的诠释学。人们一般以1960年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出版作为哲学诠释学诞生的标志。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哲学诠释学根本地意识到,认识者与那种向他表现和展示为有意义的东西以一种不可解开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它不仅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认识理想进行了批判,而且同样也对形而上学传统展开了批判。”[3](527)应该说,在哲学诠释学与战后西方哲学,无论是英—美分析哲学传统还是以现象学为主脉的大陆传统之间并没有一种断裂,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共同的思想动机。[3](3)然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之所以能够展开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两个批判,其直接的思想来源要归于海德格尔。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则绝不可能有《真理与方法》的出现,伽达默尔通过他这本著作所表现出的绝大部分思想,只不过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进一步阐发而已。虽然海德格尔说过,“诠释学哲学——这是伽达默尔的事业”。[4](2)
海德格尔将人的此在的生存结构规定为“存在理解”(Seinsverstandnis),把“理解”看作“此在存在的基本方式”(a fundamentalmode of the being of Da-sein),认为“理解始终挂念着在世之在的整体”(understanding always concerns thewhole of being-in-the-world),使诠释学回到其“源始含义”(the original signification)而成为“此在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Dasein),[5](134,142,33)从而将诠释学“由所谓精神科学的基础问题而移置到哲学的中心”,[3](519)实现了诠释学的所谓“存在论转向”。在前期弗莱堡阶段,海德格尔在1921年-1922年的冬季学期发表了题为《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诠释——诠释学处境的说明》的讲座;在1923年夏季学期发表了题为《存在论:事实性的诠释学》的讲座;1923年转任马堡大学之后,他又于1925年的夏季学期发表了后来名为《时间概念史导论》的讲座;1927年出版了著名的《存在与时间》,同时发表了题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讲座;1928年回任弗莱堡大学后,海德格尔屡屡就“形而上学”问题发表演讲,在1935年的夏季学期发表了总结性的题为《形而上学导论》的讲座。如果没有海德格尔这一系列的努力与探索,诠释学与哲学在多大程度上能融和一致,还是个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哲学”一词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经过海德格尔重新诠释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基础存在论”(the fundamental ontology),也就是他所谓的“现象学的诠释学”或者“诠释学的现象学”。[5](30,34)
保罗·利科曾在一篇名为《现象学与诠释学》(Phenomenology and Her-meneutics)的文章中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存在论转向”之后的诠释学(哲学诠释学)之间的关系做出论述。利科指出:一方面,哲学诠释学是针对现象学的观念论——亦即胡塞尔的观念论(Husserlian idealism)——的批判,从这个方面来说,哲学诠释学与现象学处在相互对立的位置;另一方面,现象学为哲学诠释学的发展提供前提,从这个方面来说,现象学与哲学诠释学具有一种亲近关系。就哲学诠释学对胡塞尔观念论的批判而言,它基于在世之在的基本形式揭示出理解的存在论视域,站在这个立场上,哲学诠释学指出胡塞尔所追求的终极的科学性理想的有限性,并且对先验主体本身提出质疑。就哲学诠释学与现象学的亲近关系来说,现象学的直观与哲学诠释学的解释具有一致性,它们都是对在“生活世界”或“世界视域”中展现出来的意义的“发现”,同时也指明了意义的语言特性。[6](101~128)通过将“存在”的问题归结为“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又进一步将意义的问题归结为意义的语言性的问题,诠释学正是在这里实现了所谓的“存在论转向”,实现了与“哲学”的结合。
在《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对一位日本学者谈到了他接触诠释学的整个过程。按照海德格尔的自述,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于理解《圣经》典籍话语与思辨神学思想之间关系的需要,海德格尔从神学研究的角度了解和熟悉了最初的诠释学;第二个阶段,海德格尔在狄尔泰的历史学精神科学的理论中“重新”发现了诠释学,这时的诠释学,已经从施莱尔马赫那里的一种“正确理解他人的话语(特别是文字话语)的技艺”,发展成为泛指一切关于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学说了;第三个阶段,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在一种“更广的”意义上使用了诠释学这个名称。按照海德格尔本人的说法,这种在“更广的”意义上使用的诠释学,“既不意指关于诠释技艺的学说,也不意指诠释本身,而是指一种尝试,即首先根据诠释学因素来规定诠释之本质。”[7](95~97)
那么,这种“根据诠释学因素来规定诠释之本质”的诠释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赫尔墨斯作为诸神的信使,向人间带来命运的讯息(the message of destiny),因而,希腊文动词“∈ρμην∈ν∈ιν”(“hermēneuein”)是指那种带来命运的讯息的“展示”(Darlegen)。“展示”这个词的意思在这里是指某物向外界的开放、某物的被暴露和被揭示。在古希腊,这种命运的讯息是依靠行吟诗人的道说才被揭示出来、才被公之于众的,所以诗人本身就是“诸神的使者”。由此,诠释就与“命运的讯息”或者说人生“此在”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诠释就此被海德格尔赋予了存在论的意义。按照他的基础存在论的观念,“诠释”实际上成为了存在的自我显现的一种形式。根据海德格尔,存在者之存在的显现是一种语言性的自我显现,作为在场的存在从来不可能成为语言表达的“对象”,也始终不是自我意识的“对象”。从而,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诠释并不是对某一个对象的诠释,它本身即“意味着带来消息和音信”。[7](117)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在本源意义上的诠释学的内涵。
至此,我们已经表明,诠释学的目标并不是要去构建一门“诠释学科学”,无论后者是指向具体的诠释技术还是一般的诠释理论,而是指向诠释学经验的普遍性。所以利科指出,“诠释学(一直)努力使自己成为一门科学。除非它的这种实际上的对认识论的牵挂让位于对存在论的全神贯注,否则诠释学反局部化的趋势将没有终点(可言)。而理解为了使自身成为存在的方式(a way of being)以及成为与存在者和存在实现关联的途径,也将不再只是显示为一种单纯的‘认识模式’(a mode of knowing)。”[6](44)正是因为诠释学对存在论的全神贯注,它“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认识理想的批判”以及“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才成为可能。
理解,而不是对某物的某一理解,这才是哲学诠释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理解本身之所以成为哲学诠释学的焦点,就在于此在只有通过理解这种生存活动对其存在始终有所理解,才能与其他诸“是者”(beings)相区别,进而才能提出并揭示关于存在(“是”)的问题。也只有深入到理解的这种源始性层面,诠释学的基本问题(理解、解释与应用)才能得到真正的回答。就目前来看,坚持从这种立场出发来看待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以及丰富资源的诠释传统的学者还很少。如果从事诠释学问题研究的学者脱离西方诠释学尤其是经历了“存在论转向”之后的哲学诠释学的理论背景来谈论诠释学或诠释学问题,那么不仅极易在不熟悉西方诠释学内涵的读者中造成误解,而且从一开始就会使其本身在其“私人理解”基础上所从事的中国诠释学的研究工作误入歧途。在“诠释学”这个概念正式进入中国近30年的今天,当我们重新检视在此期间曾经出现的一些冠以“中国阐释学”、“中国古典诠释学”等名称的研究成果时,我们不幸地发现,所谓的“中国诠释学”不仅没有初具规模,它其实根本就未曾上路。如果汉语语境下的研究者仅从“顾名思义”的角度,站在“诠释”的立场上去看待这样一门“学”,那么就会简单地把文本诠释理论或思想(至多是一门“诠释学科学”)当成诠释学的基本内容,从而完全忽视在“hermeneutics”这一名称后面所蕴含的深邃的哲学内涵,将本来是深入到最根本处做一彻底、纯粹的“思”的“诠释学”给予平板化。在这方面,从事经学诠释学研究的学者尤其需要具有高度的理论敏感度。
三
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等奉旨拟成《初等小学堂章程》、《大学堂章程》等,经光绪帝审定颁布,合称《奏定学堂章程》。据此章程,大学堂分为经学科大学、政治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等8科,其中位居首位的经学科大学设立学门(也就是专业方向)11个,具体而言有:《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理学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章程还例举《周易》,就各学门的研究路数做出规定,“研究《周易》学之要义:一、传经渊源;一、文字异同;一、音训;一、全经纲领;一、每卦每爻精义;一、十翼每篇精义;一、全经通义;一、群经证易;一、诸子引易者证易;一、诸史解易引易者证易;一、秦汉至今易学家流派;一、易纬;一、易经支流;一、外国科学证易;一、历代政治人事用易道见诸实行之实事;一、经义与后世事迹不相同而理相同之处。”根据这个章程,对于这些研究方法,“诸经皆同”。[8](3-4)在这里,清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将“经学”所涉及的内容一网打尽。换句话说,凡是与“经”有关的研究,都纳入到经学的范畴。这也正是传统的经学观念的体现。
秉承这种观念,所谓经学,就被笼统地界定为“儒家经典之学”。[9](序)详细一点说,经学就是“关于这些(儒家)经典的训诂注疏、义理阐释以及学派、传承、演变等等的学问”。[10](2)然而,这种涵盖一切与儒家经典有关的学术和思想活动的经学,并不简单地与诠释学在学理上具有互通关系、能够产生共鸣。换句话说,我们无法仅从经学本身所必定包含的文本理解与解释的因素,就简单地判定经学是一门诠释学。
那么,经学与诠释学在思想上的深层契合点到底何在呢?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如何确定经学诠释学这个命题可能成立的理论基点呢?还是让我们先回到本文最初所提到的那两个批判,即“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认识理想”的批判,以及“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诠释学是否能够展开这两个批判(它据此与其他一切冠以“诠释学”名称的理论产生有根本的区别),根据伽达默尔的理论,就在于它是否立足于“一种对方法论合理性的遗弃”。[11](1)我们认为,这也是经学诠释学是否可能的根本立足点。
按照学术惯例,“经”一词的英文对译词是“classics”,而“经学”一词的英文对译词是“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这种将“经”等同于一般的经典而不是所谓“圣典”(scripture)的做法,其实已经包含了一种方法论的观点。我们对经学诠释学是否可能的讨论就从这里开始。
根据现有资料,最早对“经”这个字做出解释的人是东汉的许慎,他在《说文解字》中认为:“经,织从(纵)丝也。从系,声。”[11](644)许慎的这个解释不知被经学与经学史研究者引述过多少次,但是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义。值得我们发问的是,许慎(公元约58年—约147年)生当所谓“经学极盛时代”,[13](101)他本身又是经学大家,解字遍引五经与传、记、说及其他解经之作,为何对“经”字的解释却反倒与“五经”无涉?
我们知道,自董仲舒对策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来,两汉经学大家将五经与五常联系起来,已为通识。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4](2523)比许慎稍早的班固(公元32年—92年)在《白虎通》中说道:“经所以有五者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15](447)比许慎晚出的刘熙(虽具体生卒年不详,但生当汉末桓、灵之世)在《释名》中也谈道:“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16](211)即使许慎被后世列为所谓专重“名物训诂”的经古文学大师,也不会违背当时的通识,仅将“五经”之“经”解释为“织从(纵)丝也”。我们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经”作为单独的一个字与“五经”之“经”并不具有相同的内涵。因而追溯“经”这个字的“本义”(the original meaning),对于我们理解作为儒家经典的“经”的内涵并没有太大帮助。
我们以《说文解字》中对其他字的解释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比如:王。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先引《白虎通》中的解释,认为“王”乃“天下所归往也”;后又引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说法,认为“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12](9)这无疑是公羊学家的发挥。然而从甲骨文“王”字原初字形看,它是斧的象形,斧在上古既是工具、兵器,同时也是祭祀的仪仗与权力的象征。如果我们按照“王”字象“斧”形的“本义”来理解“王”这个概念,就根本说不通。
再如:武。许慎引述《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载的楚庄王的话,认为“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12](632)然而根据甲骨文,“止”乃象“脚趾”之形,引申而有前进、进取之义,“止”与“戈”的组合并非“制止干戈”之义,而是“舞戈前进”之义。从这一点来看,倒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对“武”字的解释合乎其“本义”,后者直言“‘武’者,伐也。”[17](21)但是,“止戈为武”并非后世经学家普遍接受的定见,几乎与许慎同时的郑玄(公元127年—200年)就将《诗经·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中的“武”字解释为“迹”。[18](528)
可见,“本义”之说只不过是一种方法论构造而已。然而根据“本义”来确定“经”的语义,已然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做法。其代表人物即我国经学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谈到,“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真。”按照他的观点,“经者,编丝缀属之称”,经书之所以名为“经”,只不过是因为古代的书是用绳索将竹简联贯起来而已。[19](72)他一直坚持这种看法,在《国学讲演录》中说:“经者,今所谓线装书也。”[20](211)在《国学概论》更是认为:“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古代记事书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21](9-10)
既然“经”只不过是书的一种通称(“线装书”)而已,那么,“经学”也便成了纯粹的以实物——“经”——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科学了。按照这种逻辑,章太炎对“经学”与“儒学”做出区分。他认为,“说经之学,所谓疏证,惟是考其典章制度与其事迹而已,其是非且勿论也。……其用在考迹异同,而不在寻求义理。……其学惟客观之学。”而“儒学”与“经学”不同,“为主观之学,要在寻求义理,不在考迹异同。”他还说到,“儒学”“既立一宗,则必坚其说,一切载籍可以供我之用,非束书不观也。虽异己者,亦必睹其籍,知其趣,惟往复辩论,不稍假借而已。”[22](217)
其实,章太炎的上述说法并非是无可置疑的客观真理,他之所以持有以上观念,还是立足于他自身的“诠释学处境”。我们认为,章太炎经古文学派的立场,就是他将“经”解释为“线装书”、将“经学”解释为“考迹异同的客观之学”的诠释学处境。许寿裳说,“章先生治经典,专崇古文。”[23](93)钱玄同更是认为,章太炎是一位“专宗古文,痛诋今文”的“纯粹的古文家”。[24](225,226)章太炎本人也承认,“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康成亦不能阿好也。”[25](469)章太炎“专崇古文”的立场本源于清代考据学(或曰汉学)传统。章太炎认为,“清时之言汉学,明故训,甄度制,使三礼辨秩,群经文曲得大通,为功固不细。”他又说:“清儒研精故训,上陵季汉,必非贾、孔所能并。”对于弟子黄侃所言“清儒说经之根柢全在注疏”,章太炎虽不完全赞同,但也表示其说“是亦十得六、七”。[26](408)由此看来,他对于考据学一派“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的宗旨,[27](146)恐怕是颇为拥护的。
然而与清代考据学家,尤其是为考据而考据的末流相比,章太炎明显高出一筹。侯外庐认为,章太炎成熟期的学术“已经不同于乾嘉学者所谓之‘实事求是’,仅限于文字训诂间的是非”,而是在“进一步提倡理想主义”;“太炎之为最后的朴学大师,有其时代的意义,他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而是抽史以明因果,覃思以尊理性,举古今中外之学术,或论验实或论理要,参伍时代,抑扬短长,扫除穿凿附会,打破墨守古法……”[28](851)以上论述也许有溢美之辞,然而其中“抽史以明因果”的说法却实在精当。
我们前面曾谈到,章太炎将“经”从今文家所言“圣人制作”的崇高位置上拉下来,只是视之为古书的一种——“线装书”。因而研经之学便也一化而为稽古之学,经学遂与史学相提并论,不复有神圣之意味。他指出:“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人的经。”[29](46)所以经学便也应遵循求真务实之道,“惟为客观之学”。具体而言,“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妍者媸则失矣,使媸者妍,亦未得也。”[30](154)所以,章太炎在小学、经学、子学以及文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其实都是为他的史学而服务的。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章太炎对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吸收,他的史学已经迥异于中国传统史学。后者以“载道”与“羽翼经训”为目的,而前者“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31](167)也就是侯外庐所说的“抽史以明因果”。
我们认为,章太炎这种史学观念是在广泛吸收、利用西方新学基础上形成的。比如:章太炎曾经运用生物学、地质学、细胞分裂、人体学以及医学等知识来解释八卦,运用“堆垛”、“开方”等数学方法来解释《易经》,引入天体演化和进化论等学说对儒家传统天命观进行批判,他对诸子学的考释更是集中引述和使用了来自西方的有关天文、地质、物理、化学、数学、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和理论。[32](30~31)所以,他的经学研究其实已经处在为哲学诠释学所批判的“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认识理想”的统摄之下了。
运用一些本来得自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理论的营养,来重新解读、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这在章太炎那一代学者身上有着普遍的共性,而且也体现了时代要求和进步精神。我们不能苛求当时学者像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以及他的现象学前辈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那样,能够敏锐地发现西方近代科学传统所造成的客观主义危机,并希望通过自身的哲学努力改变这种把科学理性误认为人类的终极理性的错误观念。然而,始自章太炎的那种“抽史以明因果”的客观主义史学观念以及将五经视为古代文献资料、将经学等同于历史研究的经学研究观念,却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遵循的研究范式。应该说,周予同在解放后“重建中国经学史学科”的一系列工作都是沿着这一条道路前行的。
按照周予同的观点,“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像医学者检验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甚是青年学生去崇拜,好像教徒对于莫名其妙的《圣经》一样。……如果你们顽强的盲目的来提倡读经,我敢作一个预言家,大声地说:经不是神灵,不是拯救苦难的神灵!只是一个僵尸,穿着古衣冠的僵尸!”[33](946)周予同将“经”视为“一个僵尸”,所以他的经学研究只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才获得一种学理的支撑;而他抱着“检验粪便”的愿望来从事经学史研究的思想,则与章太炎视经学“惟为客观之学”的思想完全一致。在这种研究范式的作用下,“经”其实已经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全无干系,换句话说,“经”对于我们而言已经毫无意义。
四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把西方近代客观主义危机的根源揭示为近代科学对“知识”(episteme)与“技艺”(techne)的混淆。所谓“知识”,是对立足于“我觉得”、“在我看来”等见解方式的个人“意见”(Doxa)的批判,因而总是意味着对一种“总体性”的追求。这种“总体性”的“知识”为每一个见解都提供了一个秩序,通过这个秩序,个人见解不仅相互适合地构成一个统一,而且将自身向其他有别于己的见解开放。而“技艺”则是指在制作一个物或实现一个目的时所使用的合理的方法,这种方法含有技巧的成分。人们拥有“技艺”的目的总是为了克服“自然”(physis)所带来的“障碍”,这与“知识”的“非功利性理解”完全相左。每一种“技艺”都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它首先意味着在制作之前对所制作的对象的一种“规定性的前瞻”,这种“规定性的前瞻”将引导整个制作的进行;其次它还意味着对所使用的技巧的确定,人们总是有能力设想出达到他们目的的途径和条件。[34](5~6,25~27)然而,近代科学的发展不仅放弃了对“总体性”“知识”的追求,甚至也遗忘了“技艺”作为一种“规定性前瞻”的内容,结果使科学本身丧失大部分内涵而只是保留了纯技术操作方面的内容,难怪胡塞尔要把客观主义科学称为一种“单纯的技艺”(bloBe techne)了。在他看来,这种科学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它甚至已经完全忘却了自身的目的。[35](7)
胡塞尔对客观主义科学的批判和反思,无疑给现象学传统打上了一个深刻的烙印,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的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看出他对这种批判和反思的继续,这种来自现象学传统的影响也体现在伽达默尔本人身上。伽达默尔在谈到胡塞尔后期建立在“生活世界”基础上的思想时这么评价道:“对于胡塞尔来说,一个哲学家应是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家,是一个从科学的基础问题开始并扩展到人类生活一切问题、试图对自己的一切思想和信念作出最后解释的人。”[36](188~189)对胡塞尔的这种充满道德理性色彩的思想,伽达默尔深表赞同。在他看来,如果科学对于我们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事情,那么,这种作用并不是我们人类所需要的,因为它并没有预先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伽达默尔指出,“人类的未来不仅要求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事,而且要求我们为自己应该做的事作出理性的解释。”[36](197)
基于这种认识,伽达默尔对诠释学的思考立足于人类理解的普遍性,不仅突破了艺术和历史地解释科学的范围,甚至也突破了与“文本”相关的理解与解释的范围。他最终将诠释学的任务确立为“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也就是说,找到一种能够与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进行对话的语言。[11](4)通过这种语言,我们不仅可以从事“哲学的思考”,“思考对一切自然和社会的科学——技术统治所设置的界限”,而且可以把握作为普遍视域的世界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存在的真理,为我们自身的存在打开意义的无限空间。正像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面对近代的科学概念而捍卫这些真理,这就是哲学诠释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3](141~142)
以上论述,为我们思考经学诠释学的建立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基点。哲学诠释学或诠释学哲学——它体现出诠释学的真正要求,与其他一切自身冠以“诠释学”名称的时髦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立足于“一种对方法论合理性的遗弃”。所以,如果我们把经学视为某种诠释学(如,中国诠释学或者中国诠释学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可能性的基础,首先就必须建立在我们是以诠释学而不是以认识论的方式来从事经学研究。
伽达默尔极为看重诠释学对哲学所具有的作用。众所周知,所有学科或知识都建立在概念语言所构成的语言基础上。然而,与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按照知识确定性标准来衡量概念有效性不同,哲学本身的概念除了哲学自身之外别无其他基础,哲学概念的有效性问题只能依据哲学传统本身才能得到解决。所以说,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概念史。伽达默尔一再提示,哲学并不像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那样通过对象化思维构造自己的“精确”概念,而是在其本质揭示为对话的语言中展现哲学思考的统一性。[3](95)
我们反观经学,它又何尝不如此呢?经学(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统一性并不建立在一个个的单独存在的概念的基础上,相反,源于这种统一性的概念整体却为每一个概念提供意义的可能性。在诠释学的视域下,经学的统一性具有始终向未来敞开的特质,这使其本身及其概念整体也相应地具有一种无限性。从而,对经学及其概念的理解与解释也就成为一项永远也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在语言的“活生生的”存在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在真正的对话(话语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把自身所使用的概念与“存在”的真理相互联接,也才能直接将自身展现为对“存在”的“思”。因此,经学与哲学一样,都是一项需要不断地对自身所使用的语言进行理解、不断地突破语言困境的事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经学是一门诠释学。
[1]李学勤:《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华读书报》,2010年8月4日第15版。
[2][德]伽达默尔,杜特:《诠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德]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4]Jean Grondin;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H erm eneutic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P,1994.
[5]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T im.A lbany:State Uof New York P,1996.
[6]PaulR icoeur:Herm eneutics and Hum an S ciences.Cambridge:the P Syndicate of the Uof Cambridge,1981.
[7][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8]唐明贵:《论语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9]黄开国:《经学辞典·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1][德]伽达默尔:《论哲学解释学的起源》,于严平编:《伽达默尔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
[12]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13]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15]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16]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7]苏舆撰:《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18]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9]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0]章太炎:《章太炎讲国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
[21]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
[22]章太炎:《诸子学略说》,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3]许寿裳:《章太炎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24]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见于《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5]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6]章太炎:《汉学论》,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27]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8]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上海:生活书店,民国36年。
[29]章太炎:《经的大意》,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30]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章太炎全集(四)·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1]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32]张秀丽:《近代自然科学与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33]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后记》,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34][德]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孙周兴编,倪梁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35][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36][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Astudy on What Aspects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Can Be Called Hermeneutics
Cao Hongyang
(Chinese Department,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It is hermeneutics that turns to be the kine of the philosophy of our times since 1960s of last century.Whether the achievement in the field of hermeneutics can be borrowed or referenced to study on Confucian classics(“Jingxue”)becomes a significant topic.However,since hermeneutics is introduced into China,many Chinese scholars who try to use hermeneutical terms and theory on Chinese academic study haven’treally grasped the key points of it.The misunderstanding comes from the ignorance of its ontologicalmeaning.We cannot call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ermeneutics just because the study itselfincludes the elements oftext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Instead,the dialectical critique of hermeneutics based on physicalistic recognition of objectivism and positivism in history should be used for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Whether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can be called hermeneutics is based on the reasonable abandons of methodological idea.
hermeneutics,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Jingxue),Zhang taiyan
I206.2
A
1002-2007(2012)01-0031-08
2011-12-20
2007-2010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课题项目“比较诗学:经学与中国解释学思想的现代研究”,项目批准号:EYH3801023。
曹洪洋,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文艺学与中西比较诗学。(上海200433)
[责任编辑 全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