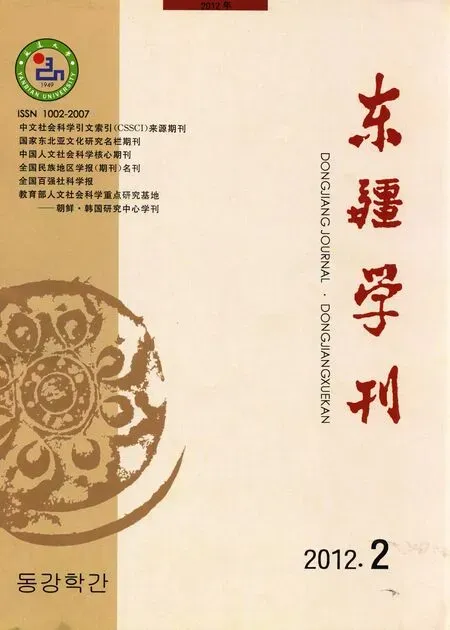论日本的武士、武士政权及武士道
潘畅和,张建华
论日本的武士、武士政权及武士道
潘畅和1,张建华2
日本武士在平安时代多源头产生后,在镰仓时期形成了武士政权,德川时期确立了武士道。武士道乃武士之道,是日本社会产生的独具日本文化特色的行为文化形态,它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及思维方式。“死的觉悟”和“迎战必胜”的思想是武士道的两大观念支柱。
日本武士;武士政权;武士道
日本武士出现于平安时代,武士政权建立于镰仓时代,发展于室町时代,成熟于德川时代,而武士道最终确立于德川时代。
一、武士
在日本,“武士”一词最初出现在《续日本纪·养老五年》中:“诏曰:文人武士,国家所重;医卜方术,古今斯崇,宜擢于百僚之内。”[1](84)在此,武官是指在律令官中与文官相对的武官,且和医卜方术同列,并不指称特定的身份。作为特定身份的武士是自平安时代中期的10世纪起,随着中央律令制的松弛,从国家体制之外多源头形成并最终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形成武士的多源头中,源自皇族的和从中央走出去的军事贵族成为武士集团的栋梁。
源头之一是降为臣姓的皇子及其子孙。从8世纪的桓武天皇(781-806年在位)以后,由于天皇的子孙日益增多,日本皇室不得不将多余的皇子赐以臣姓,降为臣籍,并授予一官半职,下放地方。赐姓之初,桓武天皇的子孙赐姓平氏,桓武天皇的儿子嵯峨天皇(809-823)的子孙赐姓源氏。自此以后,历代天皇大都继续只以平、源二姓作为皇室之后的标志对降臣的子孙赐姓。几百年后,源、平二氏布满全国。由于是皇室血统,具有先天优势,来到地方后迅速成长为半官半地主的地方豪强。作为豪强,他们不仅自身弄刀舞剑,还豢养兵丁,逐渐成为一方霸主,乃至于连官粮都拒不缴纳。[2](200)正是这些人的势力成为地方武士及武士团的重要来源。
另一源头是直接在本土生长的武士。日本律令制度下的土地占有形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农民从国家租用的班田,一般以6年为限;另一种是朝廷颁给特权阶层的封田,基本上成为世袭。班田制的核心是土地和农民的“公有”。大化革新后建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经济基础,是以土地国有制为前提的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因此,国家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征收租庸调和杂役,实现超经济剥削。在这种形态下,农民是无个体人身隶属关系的国家“公民”。但是,这种状况至9世纪末10世纪初基本结束。随着公田日益减少,私田日益增多,原为国家“公民”的农民,越来越多地被网罗进私田(庄园)主及以各种名义事实上占有土地的地主门下,成为与他们有着人身隶属关系的“私民”,而这些地主及其私民就成为武士的直接来源。而且8世纪初,国家因土地不足,不能如数班田;又因手续复杂,不能如期班田,班田制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国家为了增加税收,只能奖励开垦,遂于743年发布了“垦田永世私财法”,承认按身份地位规定的限额之内开垦的土地可以永久私有。自此,有权有势有财的人争相通过圈占公田或借“垦田开荒”等手段,占有大量私田。至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初,以“自垦地型庄园”为主流的领主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面对大量的私有地,国家采取了由国司承包缴纳租税并代之以统治其国的政策。而国司为了保证征收租税,又将田地转包给有实力的农民。在承包时,为了明确耕地所有权,把土地记在承包人的名下,土地承包人就成为了“田堵”。这些田堵中的一部分人,再与国司勾结进行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而成为大名田堵。这样,不仅郡司等地方豪族通过垦田等手段扩大庄园而成为名主,而且在庄园内进行耕作的农民中也有一部分人从原来的人身隶属关系中独立出来,扩大自己的土地而成为中小地主。这些中小地主为了在国司或其他强大领主的压迫和干涉中保住自己的土地,将自己的所有地寄进给中央贵族或寺社,将他们奉之为领主,称之为“领家”,自己则成为庄官。如果领家以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抗衡,就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者,并奉之为“本家”,而“本家”成为更高一级的领主。10世纪开始,这种自下而上的“庄官—领家—本家”的寄进式庄园很普遍,并与前期的自垦地庄园类型明显相区别。[3](33)随着各类庄园的广泛兴起和律令制的进一步崩溃,地方的土地所有制及统治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多的庄园以“不输不入”的特权事实上成为私有地,而围绕土地的冲突,进一步导致了地方政治的混乱和治安的恶化。出于应对措施,国衙的在厅官人、郡司、庄园内具有实力的名主以及凡有私利需要保护的人等,都各自将自己的宗族子弟(“从者”)和非宗族子弟(“郎党”或“郎从”)以及随从、农民等武装起来,对内加强统治,维持秩序;对外反抗国司等势力的干涉、掠夺,保护领地。从中产生了武士及其集团。
再就是军事贵族转变成了武士,并成为武士集团的栋梁。日本在律令制下实行的军制是卫府军团制。其特点是中央集权的常备兵制和征兵制。但这种制度于792年实行改革,除边塞的奥羽、九州外,都废除了军团,代之以募兵为特征的健儿制,遂使中央集权的常备兵制被取缔。然而,虽然中央集权的常备军团消失了,但被保留在边要地区的强大军事力,由于虾夷的不断叛乱和海贼的肆意横行仍未得到遏制,继续得到加强。因此,边要地区仍存在有组织且集中的武装力量,而且这些强大武力的统帅都是出身于皇族或中央贵族的军事头领,曾经受皇命镇守边要和维持治安。这些人或是已被赐予臣姓的皇族,或是受到“排挤”的中下层贵族,所以,他们的生存根基并不在中央。这样,在边要日趋“无事”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选择回到京都,而是“或加入地方豪族和权门势家一方,与国衙对抗;或自己成为受领,编成国衙的军力,借以扩大公领,压制庄园;或作为‘侍’,充当摄关家或院厅的私人卫士;或作为政府的正式军力,以对抗恶僧,出征平定地方反乱等。总之,凡是需要武力的地方,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称为‘兵’或‘以会战为职业者’”。[4](14)就是说,他们这些人原本是作为国家的常备军,受朝廷之命离开中央来到边要镇守边疆的,但他们在长期参与地方事务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国家常备军的性质而更多地成为私人请托性的包揽地方军事事务的军事贵族,乃至于由国家专用的武力,转化为适应社会变化之需要的武力包干者——武士。这些从国家的常备军转化而成的军事力量,要比其他源头的武士成熟,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所以也就成为了武士集团的栋梁。决定日后日本历史发展命运的武家栋梁——平、源二氏,正是从他们中产生的。
可见,在日本,武士是与日本古代国家律令体制的衰落过程同步、多源头产生的。从10世纪至12世纪,国家中央体制内的政府事务、职位进一步走向分化和世袭;班田制名存实亡,土地日益走向私有化;国家常备军团解体,军事武力日益掌握在军事贵族手中,所有这些都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多元势力、多重矛盾。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方面,在体制外,是降为臣姓到地方的新贵族、郡司等累世的地方豪族、寺社,或在垦地中新成长起来的农民中小地主等;另一方面,在体制内的朝廷,摄关家、皇族等权贵家族,国司等朝廷命官等,都相互结为既联系又对立的势力,各自为守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而进行争夺和角逐。武士及武士团就是在这种无权力核心可言的多元社会中多源头产生的,而武士们的精英、栋梁又大都源自皇族和中央贵族的血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的天皇朝廷是皇室的“嫡系”政权,而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是由皇室的“庶系”打造的。
二、武士政权及其特点
平安时代(784-1192)后期,地方争斗和反乱迭起,朝廷内部皇室与摄关家的矛盾、上皇(法皇)与天皇的矛盾以及藤原氏内部的矛盾加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促进了武士及武士团势力的增长。因为,朝廷自己基本没有可支配的常备军,镇压叛乱只能借助地方武装,朝廷内部的矛盾也需要拉拢各种势力,这就使朝廷不得不承认国家体制之外存在的武装力量的合法性,并开始公开启用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的矛盾又纠缠在一起,这种复杂的诸多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1156)朝廷内部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1159)源、平二家相斗的“平治之乱”。“保元之乱”加速了武士登上政治舞台的历史步伐,而“平治之乱”决定了在源、平二氏中由平氏捷足先登的历史结果。最初登上政治舞台的平氏,将自己的权力安插在朝廷贵族政治集团和政府的文官部门中。结果,一方面,由于平氏集团排挤了朝廷贵族而招致贵族的怨恨,而且以武士身份进入贵族系统形成了被动的依赖性,加上武士所特有的蛮横,贵族化生活导致的腐败等都大大削弱了平氏集团在文官贵族朝廷中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平氏集团由于掌权后成为新贵,庇护公家,失去了武士阶层的支持,自身也因迎合贵族文化而丧失了武士的生命力。
在打败平氏过程中重新崛起的源赖朝,总结平氏的兴亡经验,选择了远离朝廷、另立“中央”的道路。他“谢绝”接受朝廷对他的种种奖赏与任命,固守在关东地方,从事巩固根据地的艰苦工作。他通过御家人制度等方式建立自己的稳固基础后,先后于1180年在镰仓设立“侍所”,1184年设立“公文所”,1185年任总追捕使(武警头领),1190年成为总守护(各国总的武装首领)和总地头(即武装的土地总管),1192年接受征夷大将军之职,从而在京都之外的镰仓建立了与朝廷并立的武士政权,形成“文”令从京都朝廷出、“武”令由镰仓幕府下的二元政治结构,从此开始了日本历史上公武两重政权并存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看,源赖朝的这种选择,在日本历史上具有类似中国的秦始皇摈弃封建诸侯制而行郡县制那样的重大意义,致使源赖朝确立的公武二元体制成为其后不断被效法的基本模式。
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权,镰仓幕府(1192-1333)和朝廷是对立的。但在共同维护封建秩序的前提下,两者又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最初的权力分配也使二者相辅相成,即幕府的权利范围面向大部分地区的军警事务,朝廷则面向行政和司法。然而,承久之乱(1221)打破了这种权力平衡,皇室的权力和权威进一步被幕府所剥夺和践踏,甚至于皇位的继承和朝廷官职的任免也都要经过幕府的同意。镰仓幕府与皇室朝廷的这种日渐倾斜的关系,到了室町幕府(1333-1603)时期发展得更为严重。室町幕府干脆把自己的政所设在京都,将皇室直接置于自己的眼皮底下,致使镰仓时代以来的公武二元体制或“公武两重政权”基本上失去了实际意义。不过,室町幕府虽然确立了对皇室朝廷的绝对优势而成为日本国事实上的统治者,但他自己的统治基础却不很牢固。一方面,朝廷的无能为力破坏了原来公武二元体制赖以运转的法律和制度平衡,造成了诸多混乱;另一方面,将军属下力量过大,各守护大名的独立性也过强,致使室町幕府实际上处于与其他多元势力很不稳定的联盟之中。“日本六十八州(日本称之为国),其中五十三州由一百四十二氏争夺占据。”[2](387)因此,整个室町时代充满了你争我夺,就连第六代将军足利义教(1394-1441)也死于他的手下武将手中。这样,室町幕府在足利义满(1358-1408)统治的鼎盛期结束后,权势日渐式微,终于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日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战国时代(1492-1603)。
1467年,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1436-1490)的家臣细川胜元和山名持丰两家,因将军的继嗣问题发生争执,最终酿成京都城内的武装冲突。将军义政无法控制,号令其他守护镇压。结果,足利氏分裂为两大派,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守护大名也随之分为两大阵营卷入战争,展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拼杀。在这一过程中,代表旧势力的宫廷、寺社、贵族更加衰落,室町幕府也名存实亡。这样,在旧势力相继解体的基础上,新的战国大名纷纷崛起。新崛起的这些大名大多是原来的领国统治者的下属或臣子,他们在乱世中,凭恃自己的实力,通过各种机会,迅速成长为战国大名。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独立制定领国法,组织家臣团,建设城下町,直接控制领内的农民和土地,保护工商业,注意发展生产,振兴经济,[5](614)将其领地建设成一个个的小独立王国。
这种独立王国遍地割据的局面,由织田信长(1534-1582)、丰臣秀吉(1536-1598)通过武力破除,并最终由善于忍耐而且更善于等待的德川家康(1543-1616)于1603年实现统一,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德川幕府。德川幕府作为武士政权,继承了前代武士政权统治的方式,在社会结构上置皇室朝廷为顶端,而自己的绝对统治权来自于顶端之朝廷委任,继续以受命于朝廷的将军身份实行统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织田信长特别是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禁止农民佩带武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士农工商不得转换身份等的政策,创造性地发展了高度集权且又整齐分散、分权的幕藩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组织体系,将泛滥成灾的武力长久地冻结了起来,使日本这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6](33)的国家在尔后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和平和稳定的发展。
纵观日本从1192年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建立镰仓幕府,到1867年德川庆喜“奉还大政”并辞去将军职的近七百年间,产生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包括战国时期)、德川幕府等武士政权,而诸政权又都具有各自的明显特征。
镰仓幕府的特点。(1)二元政体的产生。源赖朝在京都朝廷之外的镰仓另立幕府的“公武”二元结构,很好地适应了日本在分隔的地域中进行分管的政治逻辑的基本特点,为日本的政治、经济内耗较少的发展找到了有效的运行机制。因此,此二元结构成为了日本政治体制的范本被后世不断沿袭。(2)御家人制度。源赖朝建立的御家人制度典型地反映了武士集团的行为规则。即武士的献身建立在感性的私人关系和具体的物质利益这一前提和“奉公”与“受赏”的基本原则之上。这种前提和原则决定了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武士道极具生命力但不可能升华为面向终极关怀的超越精神。(3)北条氏的治家原则。北条氏执权统治对外通过地头、地头请等制度很好地维护了御家人的利益而没有失去自己的统治基础;对内通过《贞永式目》等武士内部法典规范了武士的行为,倡导俭朴、禁止奢侈、注重练武,加上有别于公家贵族的武家特有的生活理念,使镰仓幕府始终保持了武人的风格,并稳定地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因此,尽管镰仓末期社会内部也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元朝两次大规模的侵入彻底打乱了武家的统治秩序,镰仓幕府也许还能维持相当一段的历史时期。
室町幕府的特点。(1)室町幕府政治基础薄弱。与镰仓幕府建立在总领制基础之上不同,室町幕府建立在守护领国制基础之上,造成守护大名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因此,室町幕府“实际上是足利氏一族与诸多守护大名的联合政权。……嘉吉之乱后,将军已成为各强大守护大名之间为维护势力均衡而拥立的傀儡。应仁之乱后,幕府权威日衰,几乎成了京畿一带的地方政权”。[5](646)(2)武家文化的形成。室町武士长期生活在京都的贵族文化圈中,自觉不自觉地吸收贵族文化,形成了不同于恪守武士风格的镰仓文化和纯粹贵族化的中央公家文化的武家文化。前期以足利义满为代表的北山文化和后期以足利义政为代表的东山文化就是典型。(3)文化的庶民化趋势。由于武士文化天然地非贵族化,加上当时宋元文化的传播和庶民经济的发展,室町文化以武家文化为轴心,与禅僧、町众和庶民文化合流,呈复合型、庶民性。可以说,近世庶民文化的基础正是由室町文化奠定的。
战国时期的特点。(1)战国大名的独立性。战国大名是在室町幕府名存实亡,宫廷、寺社、贵族等旧势力极度衰落的情况下,主要在旧权力的次核心中崛起的新领主。他们与室町时期的守护大名不同,彻底摆脱了幕府的束缚,以武力创建自己的领国,且具有真正独立性的领主权。(2)武力的无限扩张。武士原本就是力的象征,而战国时期权力及权威核心彻底消失,大大小小的割据领域并存的局面,更使武力得到了无限扩张,乃至于丰田秀吉在基本实现国内统一之后,继续将战火烧到国外的朝鲜半岛,其目标直指中国。(3)信义的极度脆弱和“人质”这一新的武家游戏规则的产生。虽然“奉公”与“恩赏”这一武家社会的基本规则反映了功利性的契约关系,但是武士对主君无代价的忠信和自我牺牲精神也是武士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但从镰仓末期开始,随着主从关系中的情感因素相对淡薄和武士个体独立意识的增强,加上战国时代情况多变的客观条件,武士的背信弃义和反复无常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忠诚和信义极度脆弱的战国时期,以自己的妻室、子嗣或主要臣属为人质的新的游戏规则应运而生,而这一规则对德川时代的演化形成的“参觐交代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川幕府的特点。(1)武士职业的转化。以往的武士靠打仗卖命实现自身价值,靠在战场上的功名得到认可和封赏。而德川时代,德川家康打造的幕府靠自身的绝对强势和有效的行政统治手段,冻结了社会武力,实现了长久的稳定与和平,致使占人口5%-6%的佩刀武士[6](60)在没有了实质性战争的情况下,作为世袭的社会统治阶层,从原来的职业战斗人员转变为武装的社会管理者。(2)武士生存根基的变化。过去,武士的生存依赖于土地和主人的封赏。随着德川幕府彻底地实行兵农分离政策,武士离开具体的领地和主人,集中到城下町并归属于“抽象”的主人——藩主、将军,成为领取幕府和藩国俸禄的“公务员”,从而使武士的生存根基从原来的具体的主人和土地转向抽象和统一的社会系统。(3)武士自主性的丧失。武士被集中在城下町成为领取俸禄的“公务员”,意味着彻底断绝了与土地和具体的依赖关系,也意味着武士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加上德川幕藩用藩国和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把封闭在日本列岛上的每个人固定和束缚在具体的区域和等级里,使得武士也像棋子一样被整齐地安放在幕藩体制的各个位置上,永远作为随时听命于幕府和藩国召唤的武士生存,不然就成为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浪人,无家可归。正是这种外在的用武之地的丧失,使武士将个体内在的最高技能——“死”推到了极至,并在这一过程中最终确立了武士道。
三、武士道
何谓武士道?颇为“经典”的《武士道》的作者新渡户稻造认为,武士道是“武士在其职业上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守之道。用一句话来说,即‘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7](27)也有学者认为,武士的用刀技术加上武士的道理及伦理就是所谓的武士道。对于武士道,本文拟从个体的行动层次、社会外在的规范层次和主体内在的精神层次加以诠释。
从个体的行动层次看,武士道应该指武士政权成立之前的武士之道。如上所述,日本武士具体产生于自垦地的出现和古代国家统治衰落的过程中。平安时代,私有地的保护需要集结武士,国家统治的衰落需要借助私人武装从而助长了武士的集结。因此,此时期的武士以自卫和公家之“侍”为特征。他们主要是为了一命的执行和一地的保护使用武力,此时的武勇来自于自卫意识和执行命令,忠诚来自于朴素的乡土的、血缘的、上下级的连带意识,而且停留在具体的、功利的、非规范的个人和小群体的行动层次上。因此,虽然有武士之“事”,但这些“事”都受自发的潜在规则的制约,尚无抽象认识可言,即还没有形成“武士道”的概念,武士之道还处于朦胧阶段。
镰仓幕府成立后,武士集团成为社会的掌权者。武士之“事”就不再只是个体的或小集团的行为体现,而是要受到社会体制的规范和制约。特别是武士作为与贵族和平民不同的社会阶层,要遵守相应的与贵族和平民不同的行为道德规范。这种明确的社会需要,促使武士社会建构了以“御家人”制度和《贞永式目》为核心的自己阶层特有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它主要包括武勇为本、忠诚至上、重名轻死、崇尚俭朴等内容。对武士行为道德的这种特殊要求,意味着武士之“事”已经开始被抽象化为“武士之道”。到了战国时期,武士的武勇虽然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武士的忠信几近奢侈品,各路名将出人头地的背后充满了权术和背信弃义的事实充分说明这一点。可见,武士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受到了严重挑战,武士之道外在的行为规范必须成为内在的主动要求。这种时代要求,为武士道概念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武士道一词的实际流行,也正是武士最没有信义和道德可言的战国末期和江户初期。武士道一词,首先流行于当时的武将们口中,他们作为武士的首脑,捕捉到了时代的要求,开始训诫自己的子孙要保持武家的风格,并制作“家训”要求代代铭记。这些“家训”特别指出,武士要保持自己特有的风格,这种风格与文弱的“公家风(贵族风)”和斤斤计较的“町人风”相对立。这种特别为自己圈子的人规定的“家训”,其内涵已经与单纯的外在行为规范有了区别,是一种对武士生存本质的价值追求。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武士道概念的确立。而此概念的核心主要还是与社会外在规范相一致的内在要求。
不过,此时的武士道可以说还不是基于恒定的价值观或基于普遍原理的行动规范。因为,实际战争的存在,武士道还只是作为战斗者对自我的规定,它还没有上升为一种超越的精神实践。所以说,真正的武士道及其理论体系的确立,即作为主体内在精神层次的武士道的确立,是武士失去了自己的生存基础——战争——的德川时代。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是假设德川时代与前期的武士政权没有区别,保持了战争,那么,武士道也许仍停留在以外在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游戏规则上而不能实现超越,即它不会发展为我们今天所要费力诠释的武士道。因为,在实际的战争中,武士的价值判断只能来自于现实的、多变的利益或命令,而不是恒定的价值或理念。正是没有战争却要保持武士尊严的社会环境,最终把武士道推到了对超越利益或命令的主体精神的价值追求上。由于德川时代长久地冻结了武力,武士不可能再用疆场上的功名实现自身价值。但是武士作为武士的主体身份没有改变,因此,武士还要以武士的身份实现自身价值,而外在战争环境的缺失,逼迫武士转入主体内在的观念战争中实现自身价值。武士们在观念战争中拼杀出来的精神世界是由两个观念之柱支撑的:
一是对“死”的觉悟。尽管德川时代已经没有了战争,但是只要是武士就必须随时准备奔赴战场去死。当然,对死的觉悟从武士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形成,然而在没有战争的德川时代,对死的觉悟和追求更成为武士的最高目标和至上境界。因为在有战争的时候,武士始终与死相联系,随时都可以在战场上以死来证明自己,所以死是廉价的,随时可以发生的。然而,没有战争却仍是武士的生存境遇,对“死”的觉悟就成为特殊的课题。因为,正如黑格尔所说,人的欲望首先是被人承认的欲望,而武士要想被人承认为真正的武士,只有通过突出死来证明自己。于是,非自然死亡的战死,尤其是需要付出重大痛苦的切腹之死,就成为证明自己、被人承认的绝对方式。因此,这种方式就具有了神话般的魅力而被趋之若鹜。所以说,日本武士的剖腹自杀现象,在本质上讲就是武士要求被人承认的欲望通过彻底毁灭自身的方式达到的目的,即武士的价值——对“死”的觉悟得到了证明和承认。这样,武士现实地失去自己的价值基础——战斗后,转向了观念性的战争。在观念中与“死”搏斗,作为武士要得到不怕死的价值承认,即不怕死是武士最值得追求的名誉。这种不怕死是无条件的,不稀罕任何同情。所以为主君报仇的请死和伏法的愿死(如忠臣藏中的四十七义士)作为武士都是非常名誉的事情,因此只有死才能真正证明武士道的最高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武士道就是“死之道”。如果因为主君报了仇而可以免死,就等于说武士的死是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替换的,那么,用其他替换而可以不死的武士道的死的境界就不是纯粹和神圣了的。因此,武士道的最高境界只能用死来实现。换句话说,死本身就是武士道,武士道就是“死之道”,追求死就是武士道的核心精神。
这种精神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敬业——到达终点,即不管过程如何艰苦,不管手段如何恶劣,达到目的就是一切。由此产生武士道的第二个核心观念——“迎战必胜”的思想。如果说“死的觉悟”是通过死证明自己并得到他人承认的观念方式,那么,“迎战必胜”的思想是自己证明自己、自己承认自己的观念方式。德川初期的兵法家宫本武藏为了在没有了战争的时代仍执著于“战斗”而提出了新的参战形式——为赢而斗赛。宫本武藏本人就自十三岁开始,周游全国与他者进行了60多次的胜负决赛,而且一次也没有失过手。[8](509)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制服对方并取胜是武士行兵法之道的根本。无论是一对一的决斗或是集团之战,都要赢,都要必胜,从而为主君、为自己赢得名誉。在这种逻辑的支配下,甚至于会直接挑战人性。武士道的经典著作《叶隐》就讲,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五岁时就得斩杀狗,十五岁时开始斩杀死罪者。一般武士,也多从十四五岁开始实习斩首。这就是说,武士与其他三民不同的核心价值就是杀得起人,即能够“战胜”人性,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杀人,这就是最好的自我确认。乃木希典(1849年-1912年)置备自己和两个儿子的三口棺材出征,并用“肉弹攻击法”在人类近代战争史上留下极其血腥残酷的一页,就是自我确认武士能够战胜一切,包括人性的典型表现。
日本武士道正是在转入观念战争之后,在上述的两个核心观念之下真正确立起来的。如此确立的武士道,尽管表现了极大的精神力,也升华为某种境界,但终究没有超越狭隘的功利性目的。
总之,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与前期的个体行为层次的、武士社会外在行为规范层次的武士道不同。首先,它不只是武士个人或武士阶层内部的行为规范。德川时代的武士作为位居农工商三民之上的统治者、指导者,他们的行为直接面对三民而具有垂教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其次,在没有了实质性战争这个具体的物质条件之上建立起来的武士道,是基于抽象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并更多地要求在精神理念上加以实践的道德规范。因此,它与过去武士的具体的目的动因或武家社会外在的游戏规则不同,是以内在的精神力为主要特征的,而且它是借助了宋明理学的理论体系及价值原理而最终确立起来的,尽管它对宋明理学的吸收进行了解构的和工具性的选择。
[1][日]《续日本记·前篇》,东京:吉用弘文馆刊行,昭和五十四年九月。
[2]汪公纪:《日本史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刘建强:《新编日本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4]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5]吴杰:《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李文:《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7][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8][日]《国史大辞典》(第十三卷),东京:吉川弘文馆,平成四年四月。
B313.2
A
1002-2007(2012)01-0009-07
2011-12-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东亚儒家文化圈价值冲突研究”,项目批准号:06JJD720016。
1.潘畅和,女,朝鲜族,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日韩儒学比较研究。(延吉133002)2.张建华,男,黑龙江省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哈尔滨150022)。
[责任编辑 全华民]
——读张崑将《电光影里斩春风——武士道分流与渗透的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