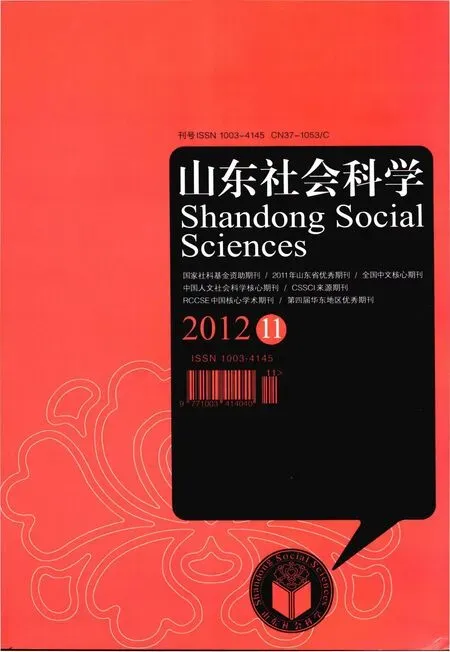华文新文学的域外传播与流响——新马华文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
苏永延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 361008)
一个国家的语言或文学传播到另一个国家之后,常常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接受、改造、融合、发展,并加入了所在国的语言或文学等因子,才逐渐形成具有独特风貌的语言或文学,其间历时长久不定,这就是语言与文学传播、发展的一种常见形态。另外,在另一国家成长起来的文学,一定程度上也会与母语国文学产生呼应效果。如英语文学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传播与对英国文学的呼应就是如此,这使得文学的传播与流响显得绚丽缤纷、多姿多彩,文化与思想观念的传播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扩大,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我们考察华文文学发展过程的话,也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富有启示性意义的问题,本文拟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来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
所谓“新马华文文学”,一般是统称20世纪初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诞生的华文新文学,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为“马华文学”;1965年以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分别被称为“新华文学”与“马华文学”,人们合称之为“新马华文文学”。新马华文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学思潮影响下诞生的,既承继着中华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因子,也在当地与其他语言的文学一起,成为所在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王瑶先生曾对这一发展过程作了十分精辟的分析,“20世纪,一方面是被压迫民族的独立,现代民族国家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关系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各民族国家及其文学互相交流、影响、渗透并在保持各自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形成某些共同特点的过程。”①王瑶:《中国作家笔下的东南亚》,载《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新、马作为新兴的民族国家,其文学发展道路也一样有过文学的交流、影响、渗透等诸多因素。新马华文文学经历了从中国移植,到落地生根、茁壮成长的艰难历程,与中国新文学有着紧密的互动联系。
新马华文新文学,既有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因子,也与所在国文学各因素不断交融,形成中华文化开放在异域的奇葩。现拟从文学思潮、创作潮流及作家队伍这三个层面,来阐明新马华文是如何在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下,由依赖移植进而逐步本土化,并最终茁长起来,且与中国文学产生一定的呼应的。
一、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海外回响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曾在马来亚这块热土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但有较大文学影响应自清末始,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邱菽园等文化人士,曾在此地播洒下中华民族文学的种子,功不可没。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潮流,随着一批批文化人的南渡,在出版、交通逐渐发达的时代逐步外传,马来亚地区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影响力。1919年《新国民日报》刊登了具有现代新文学意味的小说,由此正式拉开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帷幕。从此,中国的文学思潮也在海外有了回响与呼应,也因此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世界华文文学思潮。
二战以前,马华新文学思潮与中国文学思潮保持着大致同步的波动。其原因有两大方面,一个是活跃在马华文坛的作家,大都是从中国去的,他们要在马来亚传播华文新文学,自然会密切关注中国文坛动态。其二,马来亚社会背景与中国的情形十分相似: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马来亚则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也为马华新文学思潮的诞生及发展提供了较为厚实的土壤。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五四时期的中国新文学,追求个性解放的启蒙主义思想,呼唤民主、自由与科学的精神,马华文学也有同样的诉求。在马来亚,大量华工在胶园、矿场、工厂等地,进行艰难的拓殖垦荒与辛苦劳作,他们身上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也不时显露出封建思想的某些落后保守根柢。虽然守旧、落后思想影响,远不如中国大陆那么强大,但要清除也非朝夕之功。刚刚萌发的马华新文学,一开始就向旧文化思想宣战,林穉生、张叔耐、精进等作家,在理论上大力抨击旧文化的落后,如张叔耐的《辟顽固家之谬论》就是一篇充满战斗意味的反封建檄文。
五四时期,文学流派纷呈,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表达了不同理想追求的人们心中的诉求与愿望。马华文学也不例外。1925年,纯文学刊物《南风》、《星光》创刊,以后又有《沙漠田》、《先驱》、《浩泽》等文艺刊物纷纷面世。这不是事物的巧合,而是发展的必然。当然,小文学团体的自发行为,没有充裕经济基础支持,是难以持久的。于是,像中国五四时期的团体、刊物鲜有长期存活一样,马华纯文学团体、刊物也很快就销歇了。因为读者人数、市场大小等因素影响,马华文学团体、刊物在规模、影响上,也远逊于中国文学团体、刊物的影响力度。
1927年中国北伐战争失败,宁汉合流,阶级矛盾斗争也日益尖锐,中国文坛开始分化。一部分文化人在各种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影响下,南渡新、马。从1928年开始到30年代中期,马华文坛掀起了反映工农大众反压迫、反剥削的新兴文学运动,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的发展状态颇为相似。《新国民杂志》由永刚主持的《新兴文艺》副刊,其内容大致与上海创造社等团体提倡革命文学初期理论相似;槟城的报章副刊《荔》、《海丝》等刊物也有类似的倾向。如潘衣虹的《新兴文学的意义》、《新兴文学的问题》、《新兴文学的历史使命》,孙艺文的《混沌初开》,依夫在《椰风》、《曼陀罗》上发表的《充实南洋文坛问题》等文章鼓吹新兴文学。新兴文学理论与创作风靡马华文坛,同时大众语和拉丁化的推行运动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大众语运动发端于30年代的上海,主要目的是反对复古主义者的恢复文言论,也欲改革欧化色彩的白话。陈望道提出大众语“总要不违背大众说得出,听得懂,写得顺手,看得明白的条件”①陈望道:《关于大众语的建设》,《申报·自由谈》1936年6月19日。。这个运动是从语言的角度,来纠正白话文运动过程中的不足。拉丁化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探求文化现代化道路的一种尝试,以卢赣章的活动为发端,他在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厦门话方言课本,掀起了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五四前后,人们又提出“汉字革命说”;30年代是“拉丁化中国字运动”,首倡者是瞿秋白,鲁迅、陈子展、陈望道、胡愈之等大力提倡,于是形成了空前的、自发的全国性运动。大众语与拉丁化运动的初衷是普及文化知识,对于普及和提高马来亚华工的知识文化水平,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华文坛也就被带动起来了。《星州晚报》的《出版界》的若干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宣传与实践的工作。由于纯粹的语言文字运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制度、人们的思想认识等方面触动不大,无法扭转整个社会大局,这两个运动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至于1936年中国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马华文坛也同样受到影响,作者们经过争论,同意这两种口号都可以并存。
由于诞生的环境不同,马华文学思潮也并不只是被动地呼应中国思潮,马华作家们也开始进行一些探索,他们根据新兴的文学理论要求,并结合马来亚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关注身边的世界和社会,对“南洋色彩文艺”的提倡自然顺理成章。
1927年《荒岛》、《文艺三日刊》、《椰林》等杂志同人提倡创作“南洋色彩文艺。”如《荒岛》较早从理论角度上提出“把南洋色彩放进文艺里去”;《文艺三日刊》的曾圣提则力倡“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椰林》的陈炼青提出“创造南洋文化”。其实在理论家们提出“南洋色彩文艺”问题之前,马华文学早有这类作品,只不过理论家把这种创作倾向加以进一步强化罢了。“南洋”毕竟是比较大的范围,它一般指的是东南亚地区,并未特指马来亚。1933年丘士珍首次在《狮声》上提出“马来亚地方文艺”这个名称,标志着“马来亚文学本位”概念的形成。
从“南洋色彩”到“马来亚文学本位”概念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兴文学思潮为理论家审视社会、历史、文学等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标志着一个新兴民族国家意识觉醒的萌芽。
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被迫卷入了一场救亡图存且旷日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洪流之中,许多文艺界人士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以各种方式唤起各阶层民众的抗日热情。其中,有一大批作家奔赴海外各地,进行抗战宣传。郁达夫、胡愈之、高云览、汪金丁、冯伊湄、王莹、金山、王纪元、杨骚、王任叔、沈兹九、陈残云等先后抵达新、马,他们通过编报刊、创作、演出,多方筹赈救亡,宣传抗战理论与救国纲领,与广大新马华文作家一道,构筑起海外华侨的“抗日长城”,马来亚的抗战文艺就此蓬勃迅猛地发展起来。
从1937—1942年新马沦陷前,这是马华抗战文艺运动蓬勃兴旺的时期。虽然此前有不同口号,如“南洋战时文艺”、“华侨救亡”、“战时华侨救亡文学”等,但经过一段时间讨论之后,人们逐渐形成共识,只要是有助于抗战救亡的,都是“抗战文艺”。其中有三项重要的运动,即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马华诗歌大众化运动。
“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由《狮声》于1938年11月发起,在各种文学体裁及语言形式方面下工夫,推出大量通俗化作品;“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由铁亢发起,曾形成一个覆盖马来亚的规模不小的团体;“诗歌大众化”由吼社部分诗人发起,1939年初成立,1940年中消沉。马华抗战文艺运动与中国的抗战文艺运动也十分相似:中国抗战文艺采用街头剧、歌谣、快板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激发鼓舞大众,促使他们投身实际的救亡斗争中去;马华的抗战文艺除了鼓励华侨回国抗日外,还以各种文艺形式号召广大爱国华侨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祖国的抗战,成为当时文坛的主要政治及文艺创作热点。
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时,前途变得不明朗,各种消极苦闷的思想也渐次浮出,为了鼓励广大华侨的战斗信心,1940年初《新国民日报》副刊《新流》发动“马华文化现实运动”,继续推动马华“抗战文艺”的发展,使之由单纯反映中国抗战生活转为反映马华社会支援抗战的生活,于是又朝马华文学本土化迈进了一大步。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大战转变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抗战文艺”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而是支持全世界一切正义的战争。马华文坛适时提出“反侵略文学运动”,这是抗战文艺的深化与延续。但几个月后,日军入侵马来亚,实行严酷的法西斯白色恐怖统治,“抗战文艺”也因大批文化人被残杀和流亡出走而迅速沉寂。
“抗战文艺”是马华文学在中国抗日战争影响下的一次巨大的文学共振,如果说在此之前的马华文学思潮,是为了获得中国新文学的滋养而自觉不自觉地输入中国文坛信息,提升文学水平的话,那么马华抗战文艺则是马华文学有意识地全方面呼应中国文学大潮,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加以调整,在血与火的熔炉煅烧下,马华文学得到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辉煌业绩,并迅速走向成熟。
二战之后,英殖民者重返马来亚。作为华族共同关注热点的“抗战文艺”思潮退隐了,马来亚各族的民族、民主意识日渐觉醒,文学思潮在舆论方面倾向民主宪政,无形中契合了中国大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争取民主运动的思潮。然而,英殖民者并不容许民主运动在马来亚展开,1948年颁布的“紧急法令”,驱逐大批来自中国的文化人,斩断了马华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交流渠道。从此,马华文坛在1947年开展“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之后不久,遂走向一条风雨飘摇而又遍布荆棘的独立发展道路。
马华文学虽然被迫与中国大陆断绝来往,但是文化交流往往是阻隔不了的,港台文学思潮一定程度上也对马华文学思潮产生过影响。即使是新、马分家后,港台文学对新马的影响轨迹依然清晰可鉴。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兴起的现代诗写作浪潮,引发了新、马两地关于“现代派”与“写实派”的激烈论战;港台的言情、武侠小说,新马不少报章纷纷给予转载。但我们也要看到,无论是“现代派”的影响,还是港台的言情武侠文学潮流,都无法像二战前的中国大陆思潮那样,能深刻地左右新马华文文学的走向了。新马华文文学在二战前后所逐步确立的本土化文学道路,经过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在新、马两地深深地扎下了根,反映并服务于新、马的社会与人民。
从文学思潮的发展轨迹来看,马华文学在文学思潮从开始的模仿、借鉴到合作响应,乃至最后的被迫隔绝、自立发展,可以看出本土化的趋势也在逐渐加强,最后成为所在国独立发展的文学,而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潮内容、方向,也与新马文学需求越来越远,是新马文学独立发展的明证。
二、现实主义创作主潮汹涌奔流
新马华文新文学继承了我国古代文学“文以载道”的优秀传统,其创作潮流从总体上讲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体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胆地面对现实社会、人生,要对社会的现实与进步有益,并能够指导人生,这是我国古代“感时忧世”积极入世思想观念的生动体现。自古以来,孔子的“兴观群怨”、荀子的“宗经、征圣、明道”以及汉儒的“诗教”说等文学主张莫不注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现实的联系,启示后人以文学作为反映、批判现实的武器,有着积极的意义。这种传统历传数千年,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创作的宝贵传统,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马华文学的创作潮流继承了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特质。自近代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凌辱,有志之士为寻求各种救国方策而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于是,文学政治教化的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就生动地体现了文学所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由于民族的苦难延绵不断,文学的社会功能注定责无旁贷。所以中国新文学是与中华民族一道,从血泪与战火中,杀出生路来的。因此,从五四时期就移植过去的马华新文学创作,也在马来亚各族人民国家意识形成的过程中,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这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注祖国的动态、民生的疾苦,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出路。许多作家到了马来亚以后,虽身居异域江湖,却心存魏阙,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可见一斑。邹子孟的《师长》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忠实的《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写北伐前后的农村革命斗争,东方丙丁的《一百五十个》歌颂中国军人的爱国热情,流冰的《金门岛之一夜》、叶尼的《伤兵医院》等则是盛行一时的抗战戏剧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戏剧,不少取材于中国的事迹。一方面原因是作者刚从中国来,带着大量故国的记忆,不自觉地在创作中表露出来;另一方面则是作家对民族命运的关注之情,不能自已。有评论者曾指出:“马华文学早期文学史的特点乃是在自己乡土上高搭‘浮脚屋’,而丝毫建立不起本地色彩的文化创作风。”①[新加坡]林也:《解放的新世界》,载《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这对当时的现状而言,有一定的道理,同时也无法避免。当时去南洋的华侨极少数愿意在那里落地生根,因为这一带大都是殖民地,并未形成独立主权的国家,更谈不上国家、民族的认同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继承了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的马华文学,并不会长久注视遥远的中国故土,他们把创作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反映马来亚华人的生活上,传达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关注华族命运前途及华族文化的发展动向,这在马华文学创作上有着极为生动、详细的体现。
在小说方面,马华小说与中国的五四文学创作相似,是从“问题小说”开始启步的。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开启了马华问题小说的先河。苏正义、精进、林独步等,所走的大抵也是类似的道路。李垂拱的《一个车夫的梦》,带着积极浪漫主义色彩;而李西浪的《蛮花惨果》则写了一段华工的早期生活;依夫的《猎狗》、梅子的《红溪的故事》、浪花的《生活的锁链》等,都极富南洋色彩。
30年代所提倡的南洋色彩,实际上是南洋的乡土文学创作,其中具有影响的作品是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蔡增建的《雪影》、枕戈的《他的美梦醒了》、饶楚瑜的《囚笼》、林参天的《浓烟》,生动描绘了马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情景。马华的抗战小说则写得气势昂扬、铿锵有力。如乳婴的《新衣服》、《八九百个》,陈南的《金叶琼思君》,铁亢的《试炼时代》,是抗战时期马华各界心态的生动再现。
诗歌方面,早期的诗歌作者如林独步、胡鉴民、子淳、石樵、天铎等创作的诗歌,带有积极进取之志;依夫的《原始遗民》,连啸鸥的《火车驰过铁桥》、《都市和荒郊》等,已有很浓烈的南洋生活底色。抗战文艺运动兴盛时期,涌现出大量的诗人,如静海、东方丙丁、李蕴郞、刘思等吼社诗人,澎湃社则有清才、蓬青、野火、三便等。他们创作的诗歌,其中如椰青的《战争底风》、呢喃的《来唱歌》、清才的《向远方》、静海的《荆棘篇》、野火的《快枪八条》等,传达出了广大爱国华侨同仇敌忾的心声,激发了他们的赤子情怀。
戏剧方面,如1931年槟城有“南洋新兴戏剧运动”,着重于表演艺术上的倡导与提高。静海的《夫妇》、《凄凄惨惨》、《女招待的悲哀》,陈旧燕的《往死路上跑》等,写出了马华各界人民的思想现状;而抗战文艺时期,富有南洋色彩的创作如《巨浪》、流亡的《觉醒》、啸平的《忠义之家》、悸纯的《龌龊的勾当》、朱绪的《教师》等,可以看到抗日卫马时期华人生活的一面。
从以上创作情况来看,在战前,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虽不少,但更多的是与马华社会相关的题材。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一部分虽然直接描写正面战争情景,但描写广大华侨如何筹款救国的作品屡见不鲜,本土化的色彩日益加强。1948年以后,马华文坛有大批文化人返回中国,但仍有一大部分选择留在当地,他们与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一道,构成了马华文学的中坚力量。新、马分家后的一些重要作家,如马来西亚的方北方、韦晕、原上草、吴岸、云里风等,以及新加坡的李汝琳、李过、赵戎、苗秀、姚紫、柳北岸等,都是五六十年代新马文坛上的重要力量。
二战以后,新、马两地的文学创作本土化的地位已经确立,新华文学、马华文学就成为描写新、马两地华人生活及情感世界的主要方式,是他们心灵世界的最直接生动的记录。虽然新华文学与马华文学已分道扬镳了,但大量作家依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使之成为服务于当地华人的文学艺术模式,有关中国的题材、内容则渐次化为背景的衬托。
当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方法并不是作家们必须固守的刻板理论教条,在不同时代,现实主义方法总是在与各种不同理论的冲突、论辩中,不断融汇而发展起来的。新马华文文学曾经受到台湾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并不等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行不通,其中的缘由还得从马华、新华文学所接受的台湾现代诗影响说起。
1956年,台湾诗坛受西方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现代派”渐渐流行,台湾的“现代派”诗社主张知性和诗的纯粹性,打倒抒情,主张超现实主义和反理性,偏重于自我内心表现和人的潜意识探索,并采用多种艺术门类的表现手法。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留学台湾的马华青年作者接受台湾现代派“要横的移植,不要纵的继承”口号,开始从事现代诗的写作,现代诗主要的作者有温任平、淡莹、王润华、沙禽、温瑞安、方秉达、赖瑞和、子凡、李有成、归雁、赖敬文、陈慧桦、蓝启元等。从现代派的创作来看,马华现代派创作主要集中体现于技巧上的变化,在内容上反映的依然是马华社会急遽变迁时期青年们的迷惘苦闷心态,从精神气质上看,没超出现实主义的范畴。新华文坛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派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争。但是不久以后,两派在争论中互相取长补短,因其所争不过在语言与技巧上,这一点犹如30年代初的大众语与拉丁化运动一样,表面上轰轰烈烈,实质上并不深入,难有成效。因此,“现实”(或写实派)与“现代派”的论争,还是有许多共同的理论基础的。
七八十年代以后,新、马两国华文文学依然以现实主义文学为创作主潮,但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新加坡经过独立后一二十年的现代化、工业化建设,迅速转变为一个国际化都市,新华文学笔下的风景多为写字楼、厂房、组屋等典型都市化场景,乡野的泥土气息渐次退隐成记忆中的一抹痕迹,离生活也越来越遥远了,而对于现代都市人们在激烈竞争环境中所流露出来的焦虑、孤独、寂寞感等“现代病”,则有较深刻的表现。马来西亚不仅有有繁华的大都市,也有大量的森林、沼泽、农田、矿山,于是马华作家笔下,交织着山芭的泥土气息,混杂着热带雨林特有的幽深神秘,也不乏直指“现代病”的尖锐与泼辣,显得异彩纷呈、五光十色。
三、落地生根坚韧不拔的文学队伍
在新马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思潮与创作潮流变化只能反映其发展的大势,如果还要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动力的话,还须了解文学队伍的状态与变化,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新马文学中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作家队伍的结构与变化决定了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盛衰,中国南下作家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大而言之,如果没有大量南下作家的参与,马华文学的诞生乃至成熟至少还要再经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光阴。南下作家的主要作用在于壮大马华作家队伍及培养文艺人才、编辑文艺刊物推动马华文运上。
华人开发东南亚时间很长。自从唐宋以来就有人零星地移居东南亚,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移居,并在那里落地生根,但他们很快就被同化了,只能存有若干传统习俗,其后世被人称之为“峇”。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为了在东南亚垦殖拓荒,急需大量劳工,于是就有源源不断的华人契约劳工或“猪仔”被送到这酷热之地从事采矿、种植等繁重的工作,虽然在劳工们中间曾产生“过番歌”一类的民谣,但是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加工的毕竟很少。19世纪末,始有一些文化人及革命者开始在南洋活动,他们或为革命或为政治避难,其文学创作,仍属旧文学的范畴。
因此严格地说,新马华文文学的早期作家,其基本队伍都是源于中国。只是有的去得早,有的迟;有的留在了那里,变成了马华本土作家;有的离开,成为马华文学的过客。如果说马华文学是一片森林的话,这些树的成长并非全由这块土壤的种子萌发而成,大都是通过嫁接移植而形成的。从中国南下的作家,自身就是一棵棵移植过来的树,有的扎下了根,有的被拔离。一批批作家源源不断地来到了这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片文学之林,并从此之后繁衍生发。二战前,马华历史上有两大批中国文化人南渡新、马。
第一批是从五四以后至1937年间,我们不算南下而又扎根的作家,单算来到新加坡又走的作家就有洪灵菲、巴金、老舍、徐志摩、许杰、艾芜、马宁、吴天(叶尼)等。他们或因政治避难,或因经济原因,或为扶持马华文运而南下。如洪灵菲,他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到通缉而不得不流亡南洋。他的“流亡三部曲”所写的就是在新加坡的所见所闻。艾芜30年到新加坡,次年就回中国,他的《南行记》中记载着他在新加坡的踪迹。老舍从英国来新时,则是出于经济原因,他写出了《小坡的生日》,在思想认识上有了很大的转变。许杰南下出任《益群报》主编,编《枯岛》副刊,成为中马一带新兴文学的发动者;吴天在新、马十分活跃,除了在《星州日报》的《晨星》、《文艺》上发表散文、报告文学、评论,编写戏剧之外,还为《星中日报》编《星火》,为马康人主编的《南洋周刊》大量撰写稿子,著有《论战时文艺》,指出“战时文艺作品必须成为一种救亡的武器”,“应该有暴露和报告的能力”,“有大众化、适应大众的需要”等主张。
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作家,更多的是来了以后就在当地定居,二三十年代的新兴文学运动就是在这批作家们的宣传之下而蓬勃开展起来的。
中国作家第二批大量南下是在抗战时期,即1937—1941年间。这一时期,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还有一些是怀着强烈的救亡目的,团结广大爱国华侨,激发他们的救亡热情,所以这个时期的作家阵营强大、目标明确,并深入马华文坛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编刊、创作,还领导华侨救亡抗日等具体活动,这也是马华文学的社会影响最为广泛深入的时期。这批作家除了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等名家之外,还有高云览、汪金丁、冯伊湄、王莹、金山、王纪元、杨骚、沈兹九、陈残云等一大批人。
郁达夫1938年底举家抵新,编辑多种报章副刊,如《星州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还编《星槟日报》的《文艺》,负责《星光画报》的文艺栏编务等。他还模仿中国曾经编过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中国之一日”的做法,提倡编纂“马来亚的一日”。胡愈之是中国另一位在南洋文坛的重要人物,他于1940年12月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日据时期流亡印尼,1946年任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的社长、《风下周刊》的主编。杨骚是中国诗歌会的重要成员,参加过左联文学运动,他于1941年到新加坡,主编《闽潮》半月刊,发表大量的评论文章。王任叔为《南洋商报》的《狮声》和《闽潮》半月刊写稿,并曾为《狮声》撰写《给文学青年》等文章,讨论文学问题,普及青年的文学知识等。金山于1939年抵达新加坡,组织了“新中国剧团”进行演出宣传,1940年7月在新加坡结束义演,又到全马作巡演,1941年2月回到中国。金山的戏剧活动,对于推动马华戏剧的演出水平提高,影响甚大。
二战以后中国大陆面临着内战危机,文艺阵营分化为两部分。1945—1948年南下的作家就少了,主要的作家有杜运燮、夏衍、岳野、马宁、金丁、米军等。杜运燮创作的散文集《热带风光》成就颇大;岳野随中国歌舞剧艺社南下,以新加坡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两部戏剧并演出,他带来了中国崭新的话剧形式,对战后马华戏剧界的影响较大。
抗战时期的中国南下作家重振了因殖民者压制而日渐消沉的马华文坛,在他们的推动下,马华文学的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经过抗战的磨砺,一些本土青年作家也迅速地成长。这是中国作家最后一次大规模南下推动马华文艺,培养了一支坚韧顽强的文学队伍,为新马文学将来的独立发展作了队伍上的准备,意义非凡。一些马华本地出生的作家就是在这些来自中国的作家提掖培养下成长的。如郁达夫在新加坡时,文学青年如苗秀、倩子、冯蕉衣等都是因写作关系而与郁达夫接触并逐渐成长的。许杰、胡愈之、王纪元等在主编报章时,也是如此,他们通过这种方法,锻炼了新马华文文学的接班人。
也正因为有了大批中国南下作家的辛勤耕耘,1948年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新、马之后,在新马文学被割断与中国大陆文学往来的岁月里,那些留在新、马的中国作家和本土作家就成为新马文学的中坚力量,开始在椰风蕉雨的国度里顽强地生存了。
对新、马华文作家而言,文学创作只是一种业余的爱好,很少有人以此作为谋生的职业,所以作家队伍相对不稳定。但是他们中不少人出于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热爱与执著,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的华文作家队伍也有了细微的分化。
新加坡由于实行教育制度改革,70年代以后英语成为主要语文,华文被降为第二语文,许多学生到了高中,几乎不再修读华文了,更别说进行华文阅读或写作了。几十年下来,造成新加坡的整体华文教育水平大滑坡,华文文学队伍青黄不接,形势严峻。90年代中期之后,不少中国大陆人士陆续移居新加坡,他们中爱好文学的人士与新加坡本土作家一起,形成了目前新华文学作家队伍的主要力量。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拥有从小学到高中的一整套华文教育体系,虽然屡经政府同化教育政策的冲击,面临着不小的生存压力与困难,但是马华社会依然不放弃华文教育,本土作家也在这一教育制度的影响下,一代代地成长起来。
中国南下作家对马华作家队伍的影响还体现在文艺刊物的编辑及对文运的推动上。由于马来亚的殖民政策规定以及马华文学环境的原因,在二战以前,90%的作品都由报章副刊来容纳,所以报章副刊兴则文坛旺,副刊萎缩则文学衰,这是当时马华文坛的晴雨表。许多南下作家对马华文学的影响也都往往通过编报章副刊、杂志来达到文学理想。如郁达夫、胡愈之等文化人在抗战时期南渡新、马,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文化中继站”,启迪后学,以使民族文化的传统能够薪尽火传,他认为:“文化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结晶,民族不亡,文化也决不亡,文化不亡,民族也必然可以复兴的。”①转引自王瑶:《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东南亚》,载《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文学事业,乃是千秋伟业、泽被后世的,所以早期新、马文化人选择办刊物,也是十分明智的选择。
在1925年以前,马华文艺主要发表在综合性的副刊上,如《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叻报》的《文艺栏》(后为《叻报俱乐部》、《椰林》),《南洋商报》的《商余杂志》,《光华日报》的《光华杂志》,没有纯文学的刊物。1925年秋,南下作家拓哥创办的《南风》,谭云山、周钧、邹子孟、段南奎、邱国庆、常问梅等文学青年创办的《星光》,标志着马华文学纯文学刊物的正式出版。在这两个刊物停刊之后,“南下作者谭云山、吴仲青、黄振彝、曾圣提、许杰等人继续开垦新马这块文艺的‘沙漠田’、‘浩泽’、‘荒岛’、‘枯岛’”②郭惠芬:《中国南来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此后的郁达夫、胡愈之、王纪元、吴天、杨骚、沈兹九、张楚琨、许杰等都以编辑过文艺副刊而蜚声新、马,在他们的努力下,使这块本是酷热荒芜的文艺园地上的幼苗茁壮成长,居功自伟。
中国南下作家不仅在理论宣传创作及编务活动上建树良多,他们还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为推动新马文运而勇立时代潮头。如1941年珍珠港事变发生后,英美对日宣战,二战进一步扩大。新加坡文化界成立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为副团长,王任叔为宣传部长,王纪元、汪金丁、杨骚、沈兹九也积极参加工作。这说明了中国作家在抗战时期,实际上居于文艺界的领导地位,对于马华文运走向影响甚巨。
作家们在编辑报刊杂志的同时,也时时注意介绍中国的文艺界最新动态。从1934年底开始,中国新出版物销售到南洋为数不少,许多报刊也有专栏加以介绍,如《槟城新报》的《轮》、《光华日报》的《槟风》、《星中日报》的《星火》、《星州晚报》的《出版界》、《新国民日报》的《新路》等,都很注重对中国新书出版的评介。
当新华、马华作家被迫与中国大陆作家隔绝几十年后,80年代的交往才逐渐恢复。如改革开放之初,姚雪垠、秦牧等先后访问新华文学界,新加坡文艺协会四次组团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交流,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以云里风为团长的马华作协曾应中国文联邀请来中国访问。90年代之后,新马文坛与中国文学界的交往更趋频繁了。不过,这种互动交流是在新马华文都已独立成长之后的事了。
从作家队伍的发展情况来考察马华、新华文学界时,我们会发现,中国作家的影响在早期是全方位的,从初期以中国作家为主体,到逐渐培养本土作家,直至他们完全成熟、自立,期间也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这对于一个个体的生命而言,似乎是漫长的,而对于一个种族的文学发展历程来说,则简直是一个神话。这一切,都是与新马文学界拥有一支能落地生根坚韧顽强的作家队伍分不开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在中国新文学与新马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新文学无疑占据着交流中的主动、领导地位,这也是新马文学发展初期常见的形态。但反过来,我们也会发现新马华文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大陆文学形成呼应的效果,虽不算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影响。
二战之前,新马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陆产生影响,一般是通过作品在大陆发表、印行来实现的。许杰曾南下编报,归国后著有《椰子与榴莲》,林参天的《浓烟》反映教育界的阴暗面,在中国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这一类充满着浓厚南洋色彩的著作,以异域风情的特异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带来了不小的反响。还有一种是南洋环境对作家思想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莫若老舍,他在新加坡期间为时虽不长,却使他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人生观、世界观有了很大转变,这也是南洋独特的社会氛围及思想状况对作家的刺激。艾芜、高云览等在新加坡生活的经历,对他们以后的创作影响也是有迹可寻的。当然,二战前新马文学对中国大陆的影响,著作还不多,真正产生影响的是还是在1980年代之后。
马华文学方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黄崖的小说《迷濛的海峡》、首都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新马诗选《半世纪的回眸》、现代出版社有《异乡梦里的手》、《阳光·空气·雨水》,鹭江出版社有《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大系》、中国妇女出版社有戴小华的《沙城》,朵拉的不少著作除了在大陆的报刊上发表外,还有的在台湾出版。至于单篇著作被大陆报刊转载的就更多了。
对新华文学而言,除了骆明、风沙雁等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过《骆明文集》、《风沙雁文集》之外,辽宁教育出版社还出了骆明的散文选集《九月进香》;尤今的著作曾在苏杭一带热销,掀起一阵“尤今热”,大陆出版社已出版了尤今的50种作品,而且重庆师大还设有“尤今研究中心”;福建人民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选编了多种周颖南作品选,《周颖南文库》还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馆;漓江出版社有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和姚紫的《咖啡的诱惑》,此外厦门大学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20多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多种有关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研究著作。①详见庄钟庆:《中国当代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新文学之交》,载《新加坡等华文文学在前进中》,新加坡文艺协会2003年版。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80年代以来新马华文在中国大陆的出版情况的一些例子,其实还有更多未被统计进来,说明新马华文正以其地域性色彩在世界华文文学的园地里占有一席之地。
从新马文学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规律性问题。它说明了一种文学想要在异域传播、发展,至少要形成的向点认识。
首先是文学发展的艰巨性。新马文学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是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披荆斩棘艰难成长起来的,其间历经消沉、压制、兴盛、沉寂、潜伏、衰弱等诸多发展状态,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才确立起来,将来也会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继续接受考验,可见生存之不易。
其次是文学存在因素的重要性。文学存在的因素很多,但有两方面很重要,一个是读者,另一个才是作家。没有足够数量与阅读水平的读者,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寂寞而孤独的;有阅读群体而无创作者的社群,则是令人悲哀的。这其中又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教育制度的培育,华文的读者与作者迟早将一并消失;华文教育水平低落了,文学创作也难以提高。欧美近年的华文文学创作虽然热闹,但作家大抵是“离散”的,因为许多华人的后代早已被当地文化同化了,作家的创作只能在自己的祖籍国得到些许的回声。这与新马文学落地生根的生存发展状态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是文学交流的必要性。新马文学的发展,是大批文化人源源不断南下,并与当地热爱传统文化的华人一起合作的结果。缺少必要的文学交流,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也会迟滞许多。而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一旦能独立生存并获得发展,则将以特异的面貌为华文世界增添异彩。
中国文化形象在世界的展示,还只处于起步阶段,从新马华文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