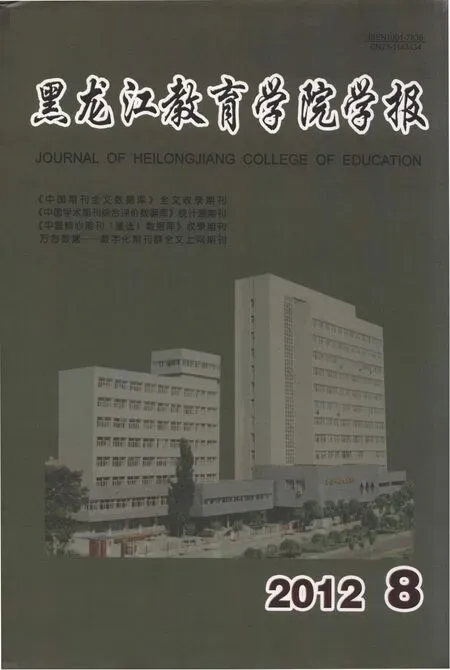唐宋文人笔下的“干越”图像
陈小芒
唐宋文人笔下的“干越”图像
陈小芒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西 赣州341000)
“干越”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唐宋文人在干越地域留下了众多文学佳话,内容丰富,异彩纷呈。干越文学不仅具有自然山水、民俗乡风的绚烂图画,而且还演绎为政治失落的无奈和贬谪迁流的感慨。历代文人流连栖息于干越这块土地,干越的文学成就无疑得益于它那独具特色的优越地理环境。
唐宋;文人;文学;干越;图像
“干越”,乃今江西余干县之别称。自古以来,“干越”、“于越”之名往往掺杂使用,唐代诗人李嘉祐《至七里滩作》诗句云:“迁客投于越,临江泪满衣。”据傅璇琮先生考证,李嘉祐乃初次贬谪于鄱阳,“‘迁客投于越’的‘于’字有误,原来应是‘干’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江南西道饶州馀干县有干越亭,云:‘在县东南三十步,屹然孤屿,古今游者多留章句焉。’刘长卿又有《负谪后登干越亭作》(《刘随州诗集》卷六)。”[1]236关于“干越”,陈正祥先生亦有详细的考证文字:“干越亭即于越亭。干越为越王勾践国土的西界,即今江西余干县。唐代的馀干和现在的余干同一地址。王先谦《汉书补注》引王念孙云:‘于越,本作干越;干越者,吴越也。’”[2]7本文所云“干越”者,不仅指“干越亭”,而是带有广义色彩的干越地域。按《新唐书》卷四十一记载,饶州鄱阳郡,所属县四,即鄱阳、馀干、乐平、浮梁[3]1069。本文试图考察“干越”独特的地理环境,以便探寻唐宋文人在该地域所留下的足迹、思想以及文学图像,为了叙述的方便,文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饶州、鄱阳、安仁以及赵家围等相关地域。
一、“干越”地域具有厚重的人文历史和人文风景
“干越”可谓历史悠久,人文鼎盛。据考古证实,远在新石器时代,县地即有人类繁衍生息。“县地河流古称‘馀水’,居民利用馀水灌溉,结馀水两岸居住。自居民点的形成,经聚落以至城邑的建立,均在馀水流域,即馀水之涯,故称其城邑为馀干(干,解作涯)。”[4]47《常谈》云:“《荀子》谓越为干越,《汉书·货殖传叙》谓为于越。颜师古谓于发语声也,戎蛮之语则然,于越犹勾吴耳,此说为有理然。说者又以干为越地名,今鄱阳有馀干县,而《淮南王上书》亦言,越人欲为变,必先由馀干界中。而《地理志》谓豫章郡有馀汗,汗音干,盖干乃越之地名,而非可尽以越为干越也。于越为干越,特传写之误,而后世见鄱阳有馀干,即以干为是。《春秋》作於越,於于声相近。”[5]第864册243以上所载资料十分翔实,故学界普遍认同“于越”乃是干越的误写。干越,又称“邗越”,系古代扬越的分支,主要活动于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滨东面,早在西周时期,干越首领建立方国,都城在今江西余干县一带。《舆地广记》云:“馀干县,故越之西境,所谓干越也。二汉曰馀汗,属豫章郡;晋宋齐梁陈隋属鄱阳郡;唐属饶州,有馀水北流入赣江。”[5]第471册424其实,干越历史,源远流长,封建王朝时期,干越不仅是江南重要的交通要道,而且还是经济、军事重镇。远在夏禹时代,大禹治天下江河,即“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墨子·兼爱》中第十五)。西周末期,周王大起九师伐越,东至九江,包括干越之地。至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二十五年),秦始皇取岭南诸地,遣尉屠睢发兵五十万,分五军前行,其一军驻扎于馀干之水。
“干越”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而且在文学的领域里给我们留下了众多佳话。唐宋时期,如刘长卿、独孤及、顾况、张祜、张浚、范成大、朱熹等一大批文学名家,或因仕宦或因迁流,他们在干越地域徘徊流连,演绎出了一曲曲动人心魂的“唐风宋韵”。公元758年至765年之间,诗人刘长卿多次往来并逗留于余干,留下了众多诗篇。760年,刘长卿赴南巴(今广东电白)初次途经余干,巧遇迁谪夜郎遇赦东归的李白,该年李白六十岁,由洞庭,返江夏,下浔阳,在余干,与刘长卿相会。李白《寻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有诗句云:“摇扇及于越,水亭风气凉”,刘长卿亦有诗《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记载相会。另外,刘长卿还有诗作《馀干夜宴奉饯前苏州韦使君新除婺州作》,韦使君即韦元甫,累迁苏州刺史、浙江西道团练副使,公元766年拜尚书右丞,韦氏由水路途经余干,并与刘长卿夜宴干越亭。公元1164年,抗金名相张浚在判福州时与子张栻、张杓途经余干,张浚客逝余干。史云“或勉浚勿复以时事为言,浚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弗言。上如欲复用浚,浚当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为辞。如若等言,是诚何心哉!’闻者耸然。行次余干,得疾,手书付二子曰:‘吾尝相国,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讣闻,孝宗震悼,辍视朝,赠太保,后加赠太师,谥忠献。”[6]11310此外,南宋文人如范成大、王十朋、姜夔等均曾来往于余干,他们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词。如范成大《清音堂与赵德庄太常小饮在余干琵琶洲旁,洲以形似得名》云:“曲浦湾环绕县清,一杯闲客雨飘零。琵琶不语苍烟暮,山水清音著意听。”赵彦端仕宦余干三年,晚年仍定居余干,范成大于1173年行次余干,拜谒赵君并与其畅饮于琵琶洲清音堂,故有此诗。
在干越众多人文景观中,“干越亭”堪称为干越地域的文化或精神象征。自唐初县令张彦俊始建干越亭,后世几经兴衰,其中正如《名胜志》所云“兴元中李德裕为令时建,(然)观文房留题诗,当由卫公重葺也。”[5]第514册350北宋文人杨亿曾慨叹云:“(干越亭)前瞰琵琶洲,后枕思禅寺,林麓森郁,千峰竞秀,真天下之绝境。”刘长卿、黄鲁直、张祜等人皆有诗作吟咏《干越亭》,其中张祜诗云:“扁舟亭下驻烟波,十五年游重此过。洲咀露沙人渡浅,树梢藏竹鸟啼多。”大致描绘再现了干越亭当年环境清美、文人流连的场景。干越亭之外,如琵琶洲、白云亭也是唐宋文人时常吟咏的题材。宋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载:“饶州余干水口有洲,形如琵琶,谓之琵琶洲。”[5]第850册677《太平寰宇记》则云:“琵琶洲,盖江山抱回积沙而形状如琵琶焉。”[5]第470册145韦庄有“琵琶洲水斗牛星,鸾凤曾于此放情”(《饶州余干县琵琶洲感旧》)之句。白云亭,“在县西南八十步,旁对干越亭而峙焉。跨古城之危,瞷长江之深。随州刺史刘长卿题诗曰‘孤城上与白云齐’,因以白云为号。”[5]第470册145刘随州之后,像黄庭坚、米芾等文人均有诗吟咏白云亭。
二、“干越”文学呈现出多样的山川图景和迁谪心境
干越物产富饶,山川秀美。《汉书》云:“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7]1666余干进士都颉《七谈》叙干越风土人物,“其一章,言澹浦、彭蠡山川之险胜番君之灵杰。其二章,言滨湖蒲鱼之利,膏腴七万倾,柔桑蚕茧之盛。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饶,水草蔬果之衍,鱼鳖禽畜之富……”[8]892在文献典籍中,不乏此类具体生动地记载余干秀美环境和温润山水的材料:
云锦溪在安仁县(今余江县锦江)治前,源出福建光泽县。宋晁补之上干越,见滩水清见,毫发其中,石五色若可掇拾者,从县令借图志阅视,溪曰云锦,村曰玉石。因有“行尽江南最远山,却寻干越上清滩”之句。(《江西通志》)[5]第513册387
杨文公亿登干越亭叹曰:“长洲茅屋,曲水渔罾,楼阁参差,峰峦远近。或白云,或返照,或残雪在树,或微雨弄晴,朝暮掩映,诚绝境也。予自饶城陆行,南至余干,良田流水,平林远山,触目蔼蔼。干越亭久废,今为学宫,下临琵琶洲,朱子注楚词之地。溪水自玉山来者,汇在十里外,宛有退避之意。”(《俨山外集》)[5]第885册117
上面两段文字显然是杨亿、晁补之初次踏上干越地域的生动印象,他们这种对干越山水田园的描摹是真实、痴迷且怦然心动的,文人们以怡然之情来抒写山林之景,主客观融为一体,真可谓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自然山水或民俗乡风在唐宋文人笔下常被描绘成为一幅幅绚烂的图画。饶州所辖安仁县,皇朝开宝八年(975)以余干县地置安仁场,端拱元年(988)升为县。杨万里一生多次经过安仁,先后作有《舟过安仁》、《过安仁岸》、《余干溯流至安仁》等诗,如“南风作雨北风休,岂是春云得自由。只者天晴过湖得,长年报道不须愁。”(《舟过安仁》)描写了余干春季乍雨还晴、变幻不定的天气,作者盼望天气晴好,以便赶回金陵上任。南宋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因谗罢相知福州,朱熹前来余干,与赵汝愚会于金溪寺并作诗相送。朱熹多次亲临东山书院(位于余干县城冠山羊角峰)讲学,在云风堂潜心注述《离骚》并最终完成了《楚辞集注》的编纂。朱熹《访赵忠定过金步》云:“行穿侧径度荒原,又踏泥沙过野田。路转忽然开远望,眼明复此见平川。江烟浦树悲重叠,楚水闽山喜接连。税驾有期心转迫,棱棱瘦马不胜鞭。”“赵忠定”即赵汝愚,“金步”即今余干县黄金埠镇,作者此次乃山行两日至金步复见平川,前半叙山行之后喜见平川,后半则叙返回家乡之悲喜,该诗有“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开阔境界。南宋隆兴二年(1164),张浚贬经余干,龙图阁学士王十朋前来余干探望张浚,浏览了干越亭并留下了千古传颂的《七月三日至鄱阳》,全诗云:“我来鄱君山水州,山水入眼常滞留。绝境遥通云锦洞,清音下瞰琵琶洲。干越亭前晚风起,吹入鄱湖三百里。晚来一雨洗新秋,身在江东画图里。”(《御定宋诗》)此诗描写干越优美的湖光山色,境界开阔,语态清新,因而在后世无可替代地成为鄱湖地域的形象名片。
然而,在那些客寓文人眼中,“干越”往往又演绎为贬谪迁流的叹息和政治失落的无奈。洪迈《容斋随笔·琵琶亭诗》云:江州琵琶亭,下临江津,国朝以来,往来者多题咏,其工者辄为人所传……吾州余干县东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刘长卿、张祜辈,皆留题。绍兴中,王洋元勃一绝句云:“塞外烽烟能记否,天涯沦落自心知。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真佳句也[8]500!
洪迈在文中记载了江州琵琶亭与干越琵琶洲的地理形势,并作《琵琶亭》诗以申述白乐天流落湓城的迁谪之意。王洋,字元渤,山阳人。绍兴初累官起居舍人、知制诰,直徽猷阁,历典三郡。王氏诗云“眼中风物参差是,只欠江州司马诗”,诗句佳则佳矣,然琵琶洲“只欠江州司马诗”倒不符合实际,因为历史上如白乐天类的迁谪流人,他们在干越或滞留或行次者也不在少数。自肃宗至德三年(758)至肃宗上元三年(761)刘长卿三次行次且滞留于余干。四十四岁被贬南巴,首次途经余干;四十七岁自南巴北归浙江,再次途经余干;五十岁之春又至余干,并逗留至秋日。在历代文人吟咏干越的丰富作品中,刘长卿是以迁谪主题著称的。他先后写有《负谪后登干越亭》、《将赴南巴至余干别李十二》以及《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等诗,其中,《负谪后登干越亭》乃是其代表作,《唐诗品汇》评曰“(干越亭)古今留题者百余篇,而刘此篇绝唱也。”诗云:“天南愁绝望,亭上柳条新。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生涯投越徼,世业陷胡尘。杳杳钟陵暮,悠悠鄱水春。秦台悲白首,楚泽越青蘋。草色迷征路,莺声伤逐臣。独醒空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牢落机心尽,惟怜鸥鸟亲。”诗人心情极为痛苦,故诗作用语偏于悲凄,因为忠直,故不见用于朝廷,诗人愤懑不已,该诗形象地再现了封建“逐臣”苦闷且抑郁的情感。其实,晚唐诗人罗隐的《干越亭》诗也充溢着前程的黯淡和心境的悲凉:“……岸下藤萝阴作怪,桥边蛟蜃夜欺人。琵琶洲远江村阔,回首征途泪满巾。”罗隐一生落拓不已,他奔波依附于藩镇诸侯,处处碰壁,他漂泊江湖,慷慨沉郁,故其诗作寄寓有较多的人生感喟和无奈。就外放迁谪者而言,抗金名臣李纲也是典型代表,他为投降派所挤,屡遭贬斥,如靖康元年先责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后再谪夔州,其后,绍兴五年至七年又任江南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纲一生屡入江西,他善借江西山水以抒迁谪之情:“我今谪官此中行,何事恬然风浪止?”(《彭蠡》)“梦想庐山三十秋,却因谪宦得重游。”(《余幼尝一到庐山再游已三十年矣感怀二首》其一)李纲笔下的《余干》诗云:“岁寒迂路过江乡,叹息飞蓬堕渺茫。云锦洞深烟水远,琵琶洲转暮滩长……”,显然,诗人是借凄迷之景来写贬谪之情的,其间不难看出政治失落之后的徘徊和忧伤。
三、“干越”文学寓含着独特的地理因素和地理图像
“干越”的文学成就无疑得益于它那独具特色的优越地理环境。在历史地理的版图上,干越地处“吴头楚尾”,北濒江淮,南连闽粤,它将南北、东西两条驿路干线紧密相连,因而它在历代政客、商贾以及文人心目中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图经印象。
秦汉至隋唐,因为政治军事的需要,“出豫章,下横浦”,由长江经鄱阳湖入赣江南溯章水,翻越大庾岭以达岭南,这是中原通往岭南的南北交通干线。随着北宋王朝的覆亡,南宋政府驻跸临安(今杭州),临安——广南交通成为中央王朝沟通岭南或西南的重要干线。这条东西干线在江西境内的走向是“利用信江、赣江及袁水水运之便而置,借水运之利而通。驿路自信州起分为两路:一路沿信江过鄱阳湖而至洪州,此为水路;一路自信州经抚州而至洪州丰城县,此为陆路。”[9]99江西城由广信府过玉山至浙江水的具体行程为“江西南昌府。六十里赵家围。六十里瑞虹。六十里龙窟。八十里安仁县。百里贵溪县。八十里弋阳县。八十里铅山县河口。八十里广信府。百里玉山县。陆路,四十里草平驿。今革。四十里常山县。下水,八十里衢州府。八十里龙游县。八十里兰溪县。九十里严州府。西去徽州。东五十里钓台、子陵祠。三十里桐庐县。九十里富阳县。九十里钱塘江。十五里杭州府。”[10]203“赵家围”,今南昌县滁槎镇东面赵围;“瑞虹”,今余干县瑞洪镇;“龙窟”,信江流经余干称龙窟沙;“安仁县”,今余江县东北锦江镇。
干越地处江州——大庾岭驿路、信州——袁州驿路和洪州——建昌军驿路的交叉点上,余干西北之瑞洪镇,顺水而下四里便是赣江、抚河、信江的汇合之处。由洪州府走赣江南支进入鄱湖或抚河、信江流域,赵家围、康郎山、瑞洪是三个极为重要的交通地理据点。在此不妨以明清文人的行踪及其文学活动作一描述。明代王慎中、文嘉都曾经过赵家围,王慎中留有《晚行赵家围》诗(《遵岩集》)[5]第1274册47,文嘉《鄱阳湖》则云:“彭蠡茫茫欲渡愁,赵家围畔系孤舟。”(《文氏五家集》)[5]第1382册534罗洪先是江西吉水人,明代杰出的地理制图学家,一生致力于地理学的研究,他在《夏游记》中记录赵家围的行踪极为详细:“初六日,午过赵家围,登舟尾望彭蠡,宿瑞虹。初七日,午至龙窟,龙溪易舟,漏下十刻泊余干上三十里。”(《念庵文集》)[5]第1275册136康郎山,“在余干县西北八十里鄱阳湖中,明初,舟师救南昌与陈友谅,战于此,后建忠臣庙于其上。”(《大清一统志》)[5]第479册511宋杨万里《诚斋集》中有《阻风泊湖心康郎山旁小舟三宿作闷歌行》、《明发康郎山下亭午过湖入港小泊棠阴砦回望豫章两山慨然感兴》二诗以记行踪。清初文学家彭孙遹,浙江海盐人,与王士禛齐名,康熙五年(1666)彭孙遹三十六岁,初夏自岭南游历之后返回,五月北归,在江西境内,他先后作有《章贡台》、《樟树》、《康郎湖》、《饶州东湖》、《由浮梁抵祁门道中》等诗记述行程(《松桂堂全集》)[5]第1317册382。由康郎山出发,“东南至瑞虹八十里,道出安仁及抚州”(《舆程记》)[5]第479册511,这是宋元之后文人东进西出的必经之途,他们在文中每每多有记载。如清代朱彝尊,浙江秀水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届六十四岁的朱彝尊由玉山进入江西,途经铅山、弋阳、贵溪、安仁、瑞洪、赣州、南安等地,以再游岭南,沿途他以地名为题,写下了大量纪游诗作。其《瑞洪》诗云:“余干江路永,回首失崭岩。市酒难为醉,罾鱼乍解馋。湖宽舟愈小,峰远日初衔。渐识宫亭近,分风及布帆。”[5]第1317册577诗人在颈联末尾注云:“自玉山至安仁,捕鱼多用鸟鬼鱼皆无味,至此始用罾。”到了瑞洪古镇,朱彝尊欣喜地看到乡人用渔网捕鱼,乡情美味让他流连忘返。
唐宋文人行走于以“干越”为中心的东西或南北驿路间,极为精彩的是以日记体式的游记来纪录描摹他们自己的行踪。如唐代李翱,他在《来南录》中形象地记载了行走信江、余干线路的情形:
……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岭,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阳山,怪峰直耸似华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担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岭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花。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乙丑,与韩泰安平渡江,游灵隐山居。辛未,上大庾岭。明日,至浈昌。……[2]6
宪宗元和三年(808),岭南节度使兼广州刺史杨於陵聘请李翱为观察判官,李翱于次年正月十八从洛阳出发,循洛水,入黄河,转汴梁,沿江南运河抵杭州;溯钱塘江转信江,渡鄱阳湖入赣江,翻越大庾岭顺北江南下广州。担石湖,即鄱阳湖。作者经过余干时,游览了干越亭,可惜该篇作品叙写文字过于简约。
宋代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的记载描述却是详尽精彩的:……十八日,过常山县,宿蒋连市。十九日,宿信州玉山县玉山驿。二十日,宿沙溪。自入常山至此,所在多乔木茂林,清溪白沙,浙西之所乏也。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泊信州。自此复登舟。二十四日,舟行,宿霍毛渡。二十五日,过弋阳县,宿渔浦。二十六日,过贵溪县,宿金沙渡…… 二十七日,过饶州安仁县。吏士自信州分路陆行者,适方渡水,取抚州路会余于南昌之宿港。二十八日,至余干县。前都司赵彦端德庄新居在县后山上,亦占胜。同过思贤寺,清音堂下临琵琶洲,一水湾环,循县郭。中一洲,前尖长,后圆润,如琵琶,故以清音名此堂。从昔为胜处,晁无咎书其榜,前贤题诗满梁壁。琵琶洲一名鳖洲。野人相传,“长沙当旱,占云‘余干新涨一洲,如鳖,远食兹土’,潭人信之至,遣人来凿洲,今有断缺处”。又云“岁涝,洲不没。大甚,仅浸琵琶之项,后人谓‘浮洲’”。余干之名,见前《汉书》。县有干越亭……[11]47
《骖鸾录》是乾道八年(1172)范成大以中书舍人出知静江府时所作的一部笔记体游记,作者自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出发,赴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上任,上面所录一段文字是其自浙江常山至江西余干的行程记载。范成大的游记文字善于模山范水,他对沿途的自然景观及人文景观皆能作详尽的描写。该段文字再现了作者与赵彦端诗酒相交、雅聚清音堂的场景,对于琵琶洲的自然环境及其人文传说,描述细腻,记载生动,同时也兼顾有余干县名以及干越亭的考证记载。
[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236.
[2]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M].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
[3][宋]欧阳修,等.新唐书(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69.
[4]余干县志[K].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5]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6]宋史·张浚传(卷361)[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汉书·地理志(卷 28)[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宋]洪迈.容斋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2005.
[9]宋三平,等.论两宋江西地区的交通及其影响[J].南昌大学学报,2009,(6).
[10][明]黄汴.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11]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2.
The Image of“Ganyue”Created by the Literat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HEN Xiao-mang
(School of Literature,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 341000,China)
“Ganyue”,a time-honored place,boasts numbers of renowned personalities.Scholars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eft Ganyue a large sum of various literary classics with abundant contents.Ganyue literature not only gets gorgeous views of natural landscapes and folk custom,but also expresses the helplessness of political frustration and sigh of demotion and elapse.Literati in the past dynasties enjoyed the place there.No doubt that Ganyue's great literary achievement benefits from its superior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Tang and Song Dynasties;literati;literature;Ganyue;image
I206.2
A
1001-7836(2012)08-0111-04
10.3969/j.issn.1001 -7836.2012.08.043
2012-02-28
2011年度江西省社会科学艺术学项目“赣鄱流域名胜文学与名胜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陈小芒(1963-),男,江西石城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地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