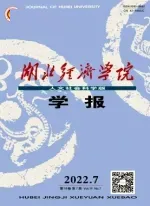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格诉求
——生态人格的探寻与构建
张炎
(漳州师范学院 政法系,福建 漳州363000)
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格诉求
——生态人格的探寻与构建
张炎
(漳州师范学院 政法系,福建 漳州363000)
生态危机叩响了人们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大门,在人们努力寻求解决外部自然生态危机的同时,首先应该寻求内部自然生态危机的解决。因而,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构建已破坏的人格系统,而生态人格作为反映生态文明时代痕迹的人格样态,对于生态危机的解决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生态人格;伦理维度;美德维度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在其《合法化危机》中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内部自然生态危机两个方面,前者导致的是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的是人类学和人格系统的破坏[1]。现代社会自然的生态危机是伴随着人类的心态危机而发生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最具前提性与价值意义的不应是伦理规则,而应是人类主体的品质。人们首先应追问的是“如果我们肆意地破坏自然环境,那么我们将就成什么样的人”。因此,优化人类人格体系,建立人格生态是生态文明时代所必须具备的生态智慧。但人格的优化绝不能理解为人与自然简单分化乃至分裂。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这只是人格生成与优化的第一步,分化之后的综合或走向新的“一体化”,才是人格优化的更高的理想境界。优化是“分化”与“综合”的辩证明统一,是人类意识与其智慧和意志的产物。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高水平更加理智地走向自然、适应周边环境始终是其“优化”的主旋律。
一、生态人格是对传统道德人格的拓展与升华
所谓生态人格,即个体人格的生态规定性,是伴随着人类对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的发展,基于对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的把握和认识而形成的作为生态主体的资格和品格的统一;或者说是生态主体存在过程中的尊严、责任和价值的集合[2],塑造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人格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实质指向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主导价值观,认为环境问题是由于人类过渡地强调与使用自已的主体权利而造成的,以他们的这种观点,自然界应具有工具性的外在价值和以自身为目的的内在价值。其试图通过赋予自然界以权利,扩展道德关怀的范围来解决问题。所以,他们主张不但人是权利的主体,而且自然界也是权利的主体,主张在“自然价值论”、“自然权利论”的基础上来解决环境危机。在这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指责中,因其只从人与自然的“主体—客体”的关系结构中去思维,造成了对环境问题思考的表面化,从而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忽略了对人本身的思考。也就忽略了人类精神世界,忽略了对人本身的环境美德的培养。从而缺失了应当去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样(品德)的人倾向于破坏自然环境”。“传统环境伦理研究是一种脱离现实而非关注人类的价值或权利的抽象论证。这种抽象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强调非人类的价值或权利没有与公众的品质培育有效地联系起来,最终使保护环境的呼吁或倡导流于形式,环保的道德要求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换言之,传统的环境伦理强调非人类的内在价值,忽视了公众关注环境的动机资源。”[3]生态美德伦理暗含着外部自然生态危机的解决应建立在内部自然生态危机解决的基础上,而解决内部的自然生态危机就是要优化人类人格系统,构建具有生态美的人格,即生态人格。
传统的道德人格系统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来讨论和生成人格,其缺了自然这个重要的维度,把自然排除在道德的视野之外。而生态人格的生成不仅要把人放置在人与人的关系系统中,更重要的是要将自然纳入人格系统的生成因素中,其所要求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来探寻和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自然之思的基础上来构建人伦关系。因此,无论从价值的维度,还是从伦理的维度,生态人格都是对道德人格的超越与升华。
二、生态人格的神性之维
生态人格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对生命的敬畏之心、诗性智慧和栖居意识[4]。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体现了生态人格的神性之维,即通过凝视自然、敬畏自然来育化人的精神。现代社会的人们在伦理生活上正处于信仰层面与操作层面的分离,其表现为人类精神陷入“祛魅”的困境之中。对物的征服极大地削弱了人类想像与思维的空间,人类精神忙碌于现实,因而不能转向内心,回到真实的自我。人类信仰生活也在世俗化。物欲的膨胀使人类自身不再是目的,而被沦为了利用的工具。“在重占有的生存方式之中,在我与我所拥有的东西之间没有活的关系。我所有的和我都变成了物,我之所以拥有这些东西,因为我有这种可能性将其据为已有。可是,反过来说关系也是这样,物也占有我,因为我的自我感觉和心理健康状态取决于对物的占有,而且是尽可能多的占有……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死的,没有生命力”。[5]物欲的占有是以神圣的退场为代价的。启蒙以来理性的发展思维逐渐将人类精神从原来浑然一体的统一体中剥离出来,理性关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神性通道和精神之魅。自然失去了人类投射于其中的精神因子,对神圣敬畏消失必然导致人类思维由超验之维到经验之维的转化,由不可控制到可控制的转化。这种由理性导致的转化是人类精神的与人格层次的下降。
敬畏生命体现的是一种生态道德信仰,是对生命神圣性的一种类似信仰的体认,但是这是一种不同于一般宗教信仰的特殊信仰,其奉行的是生命至上的伦理法则,它信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其将生命生活本身视为对某种神圣东西的实际经验和践履。过程哲学家怀特海认为,个体诞生并进入一个现实的实有世界,每天与现实的实有世界打交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以自已的活、丰沛生命实际感受、体悟自然和生命本身之神秘、神圣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人类之生态人格不断提升的过程。
三、生态人格的美德维度与伦理维度
较之于传统的环境规范伦理,生态美德伦理更加注重的是个体人类付诸道德实践的精神锁链,其试图通过诉诸个体人类的美德来指导人类的生态道德实践,人类不同的文明时代都有其相适应的美德涵养。在人类农业文明阶段,勤劳、勇敢、团结是其核心美德。到了工业文明阶段,其主流美德表现为忠于职守、遵守契约和创造财富。人类的这些美德是人类文明发展所依靠的核心精神资源。在人类文明的转型之际,拓展和提升人类美德,确立和发展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态美德,是文明转型时期的客观需求。作为生态人格的基本特征之一的诗性智慧,其向我们展现的是这样一种真实的存在面目:自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事物,而是一个拥有人类心灵与目光投射的自然,它是人类情感的凝聚体。人自身也不仅仅是一个只体现主观情绪的存在体,而是通过自然来确认自我生命的天人合一体。诗性智慧体现的是人类对自然和生命的柔情,一种能转化为美德的柔情,同时也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精神化的生态敏感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一种价值关系,在两面者之间,还存在审美关系。根据康德对理性能力的划分,在人与自然物间,可以建立起来的直接关系包括三个维度:“即认知关系、功利关系和审美关系”。[6]生态文明时代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的重新构建,通过把自然当作一个“美”的存在物来唤醒深藏于人们心底的德性,即美德。同时借助美德这种存在于人们身上最稳定的品质来维护自然之美。个体人类自觉自愿地善待自然的可能性只可能植根于人类自觉的生命意识,而这种理性的自觉的生命意识是成就个体人类美德的基础。生态人格的培养应注重美德意识,注重基于内在美德精神的品质和仁爱。个体人类向善应表现为美德与超越,即个体人类应追求那些终极性的、稳定的方面,这就是自身的道德品质,也即成为一个好人所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也就是做到“生态化的自我”,用生态道德来调节自身,从而建立生态人格。
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审美关系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伦理关系的基础。“伦理行为的发生取决于伦理主体——人,而不取决于伦理对象的伦理能力,也就是说,是否能够在人与自然之间直接建立起来伦理关系,并不取决于自然物本身,而仅取决于发端于人自身的审美能力。”[7]审美关怀下的自然物,不是与人无关、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物,而应当是在人的审美目观的所笼罩下的有“人性”的自然物,它不再是没有精神与生命的“死物”了,因而不再是自在的自然物,人们在对自然物的审美过程中,并在自身伦理法则的支配下,欣赏被人所给予的“美”或“崇高”,并对其景仰。人类伦理对象的扩张何以可能?这仍植根于人类自身的审美能力。把自然当作道德关怀的对象需要人类个体美德的培养与塑造,在缺少美德这个重要维度的基础上来呼唤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只可能是镜花水月,也是一种空洞的理论。人们只有不断追问自身与自然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并深刻认识与自然之间最真实的关系时才会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求善求美。伦理的求善,与审美之美相结合才不会使美善判若二分,才不会使审美观念暗渡陈沧。因此,化善为美,美善结合的人格样态,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人格诉求,也应成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主导人格。
四、结语
生态人格体现的是“适然世界”的生存人格样态,“适然世界”不同于“实然”与“应然”世界,它所体现的是一个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统一了的人的主客矛盾的人的 “价值世界”,同时也是体现着人格生成与发展规律的现实生活世界,因此也是伦理价值追求可靠依据所在的人格世界。“适然性”是人的价值生命追求与实现的根本特性之一。具体地说,“适然”是一个与“本然”和“应然”相对应的概念。“本然”强调的是世界的自在性、客观性、必然性,“应然”强调的是世界的自为性、主观性、或然性,“适然”则是“本然”与“应然”二者矛盾的辩证统一。“适然”世界重视的是相对于人的合理性和属人世界的真理性。“适然”是在世俗本然与逻辑应然基础上的统一与超越,人类通过改造自然,在人与自然关系之思的基础上将自然纳入人的“价值世界”并塑造主体生态人格样态。生态人格作为一种道德人格,是人类对自身理性反思的结果,是一种深层次的道德价值,它建立在生态理念的基础上,体现为环境道德实践与个体的道德实践的统一,是人类生态智慧光芒的照射。它要求个体人类在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将自然视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把生态危机与人类自身的心态危机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加以解决,实现自然生态与人类精神生态的双重救赎,并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双重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1]陈振明.技术、生态和人的需求[J].学术月刊,1995,(10):98.
[2][5]彭立威.论生态人格的缺失及其价值指归[J].道德与文明,2011,(4):117-121.
[3]高辉.生态美德及其文明价值[J].道德与文明,2011,(2):135-137.
[4]王茜.可持续发展与生态人格的培育[N].中国教育报,2004-10-18.
[6][7]邹之坤.何雪.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1,(3):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