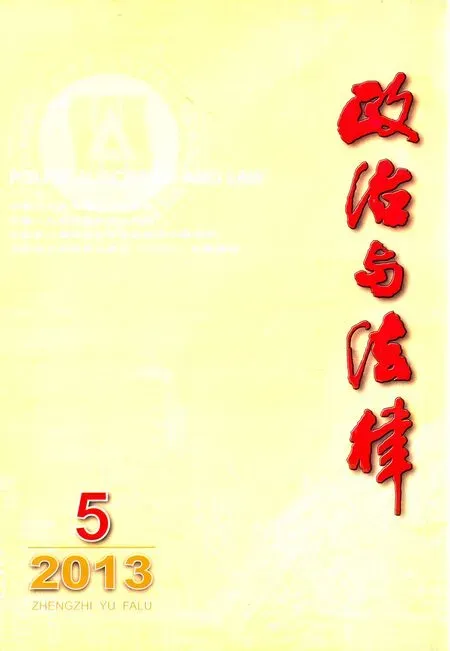如何解决个案量刑时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冲突*
王瑞君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一、个案量刑时报应刑和预防刑之间的冲突及困惑
2012年9月,媒体报道了空姐李某走私化妆品案。被告人李某曾任某航空公司空姐,在淘宝网上开有一家网店,多次以客带货从无申报通道大量携带从韩国免税店购买的化妆品入境而未申报关税,偷逃海关进口环节税达113万余元。法院一审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于该案,社会公众认为量刑过重,司法界人士则认为这一量刑合乎法律规定。量刑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却为何与社会公众的一般公正观念相悖?具体而言,该案件如果根据案件的数额,依据立法及司法解释对李某判处11年有期徒刑并无不妥,但如果根据李某的行为方式、主观恶性,11年有期徒刑则显得偏重。根据基本的刑罚原理,犯罪的数额与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有密切关系,通常来说,数额的大小是反映行为人已然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行为方式、主观恶性既反映行为的危害轻重也可以用来判断对行为人再犯罪的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因此,该案反映出来的问题最终应还原为如何协调报应刑(数额大、主观恶性轻的报应刑)与预防刑(特殊预防必要性较小)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刑法学者和司法裁判者较难处理的。从上世纪80年代的姚锦云案到本世纪初的张恩举案,再到近年来的王斌余案、许霆案、孙伟铭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和民众围绕这些案件的量刑轻重问题的争论,均绕不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报应与预防的关系如何协调。姚锦云案、张恩举案的共同特点是行为人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后极为后悔,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较小。这两个案件提出的问题是:依报应刑应判处死刑,能否因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而改变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在孙伟铭案中,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判决对孙伟铭改判无期徒刑,除了对其罪行的严重程度有新的定位和评价之外,还采纳了孙伟铭及其辩护律师在二审控辩中提出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小的因素,即真诚悔罪、良好履历、事后补救等。可以说,该案的二审判决,体现了动用预防刑对报应刑进行调节的效果。王斌余案、许霆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案件起因、被害方过错等因素有一定关系,但绕不过的问题仍是:法官既要基于犯罪人罪行考虑报应刑,又要考虑对罪犯的预防必要性的大小来裁定刑罚的量。如果将上述案件以及司法实践中个案量刑时的报应与预防的关系进行整理,可归纳出如下几种常见的情形。
其一,某甲犯A罪,与之相应的报应刑假设为死刑,如果甲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不判死刑就足以预防其再次犯罪,那么,对甲可否宣告其它较轻的刑罚(包括死缓)?
其二,某甲犯B罪,B罪的危害性要远远超出A罪,与之相应的报应刑为死刑(这个显然比A罪的死刑要重,甚至重之又重,表述为“重罪死刑”),如果甲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不判死刑就足以预防其再次犯罪。那么,暂对甲可否宣告其它刑罚(包括死缓)?
其三,某甲犯C罪,与之相应的报应刑假定为10年有期徒刑。如果甲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很小,仅判处5年有期徒刑就足以预防其再次犯罪(假定该罪的法定最低刑是3年),那么,对甲的宣告刑是10年还是5年或其它刑期?
其四,某甲犯D罪,与之相应的报应刑假定为10年有期徒刑。如果甲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很小(并且小于犯C罪的某甲),假定该罪的法定最低刑是3年,那么,可否直接低于3年来宣判甚至免除刑罚?如果可以,是否应该有条件或者底线的限制?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对常见量刑情节,有的规定为减少基准刑的情节,有的规定为增加基准刑的情节,尤其是该指导意见将“累犯”、“有前科劣迹的”、“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的”、“在重大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犯罪的”规定为增加基准刑的情节,为什么这些情节是增加基准刑的情节?这里引出另一个问题,即这些情节是影响报应刑的情节还是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对后面的问题如果不给出合理的解释,就很难回答“为什么这些情节是增加基准刑的情节”这一问题,从而会影响判决的可信度。
为此,有必要对报应刑和预防刑在个案确定刑罚量时的冲突问题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且,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改变实践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对影响责任刑还是影响预防刑的情节不加区分、不讲究情节适用的逻辑顺序、量刑情节混杂不分或简单地予以抵销的现象,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各国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冲突的理论学说及实务选择
(一)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冲突的理论学说
在量刑根据上,存在报应刑论与预防刑论的论争。当前,单纯主张报应刑论或者单纯主张目的刑论的学者已不多,融合报应刑和预防刑的并合主义是当今关于刑罚根据的主流观点,不仅如此,在并合主义内部,以报应刑为主、预防刑为辅同样是基本的共识。但是,关于报应刑论与预防刑论之间的关系在个案中的具体运用,仅靠关于报应刑论与预防刑论之间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的抽象定位,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思路和方法,以有效地解决对行为人的最终量刑问题。
针对量刑时报应刑与预防刑之间的冲突,国外有的学者主张分阶段进行报应刑和预防刑的分配。如德国刑法学者汉克尔(Henke)主张以分配说为基础,倡导位置价值说,他认为,“可以将科刑现象分为三个阶段,即刑的立法、刑的量定、刑的执行。而将各阶段分配为一般预防、赎罪(恢复原状)、特殊预防的刑罚目的”。1有的学者主张对二者进行调和,这里又有幅的理论与点的理论的不同。幅的理论也被称作“范围理论”,点的理论也被称为“唯一刑理论”。“范围理论(Spiel raumtheorie od.Schuldrahmentheorie)认为不能决定与责任一致的正确的刑罚,刑罚在其下限和上限上有其适合的范围。故为一种在该范围内考虑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而裁量刑罚的理论。与此相反,唯一性理论或者点刑理论(Theorie der Punktst rafe)称,责任往往是大小固定的,故正当的刑罚只能是一个。与责任一致的刑罚可以由其它刑罚目的来修正,却不能超过责任。”2“幅的理论是德国判例的基本观点和刑法理论的通说。”3日本存在幅的理论和点的理论的激烈的争论,如小野清一郎主张幅的理论,城下裕二则主张点的理论。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20世纪初德国学者弗朗克首创规范责任论、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威尔策尔提出目的行为论,心理责任论向规范责任论转变,他们的研究创立的以非难可能性为核心的责任理论,替代了结果责任论和心理责任论,如今,以消极的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刑罚根据理论成为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的通说。按照通说,量刑以责任为前提,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和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在确定刑罚的量时,以责任刑制约预防刑。点的理论和幅的理论的争论尽管仍在继续,但是,量刑以责任为前提,区分影响责任刑的情节和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在确定刑罚的量时,以责任刑制约预防刑的观点,为许多刑法学者所主张,并且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乃至英美法系许多国家的做法。
迄今,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可分两类:一类是仅就这两个原则之间的的关系进行抽象的定位;一类是试图解决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二者在具体运用中的关系。前者如周振想等学者的研究,后者以邱兴隆教授、张明楷教授、冯军教授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邱兴隆教授将报应与功利相统一的规则设计为报应与功利兼顾、报应限制功利、报应让步功利、报应与功利折衷四项。其内容概括起来包括: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兼顾报应与功利的要求;在报应与功利相冲突而不可调和的情况下,如果报应要求刑罚作出有利于个人的选择而功利要求作出不利于个人的选择,应该是报应限制功利,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出报应所允许的限度而作出不利于个人的选择;如果报应要求刑罚作出不利于个人而功利要求作出有利于个人的选择,应该报应让步于功利;在报应与功利的冲突具有可调和性的情况下,应该折衷调和,折衷调和的结果只能是有利于个人的选择。4邱兴隆教授设计的这些规则,是以有利于个人的选择、注重个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关于如何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的二律背反问题,上述规则的设立至少解决了如下问题。其一,基于功利即预防的需要,任何情况下不得超出报应所允许的限度,即以基于报应确定的刑罚的上限作为最高的刑罚。其二,如果预防的必要性小,可以作出低于报应刑的刑罚判决。但是,上述规则遭遇个案时,在邱兴隆教授自己的分析中却没有贯彻到底,如他关于姚锦云案件判决的分析中这样写道:“本案属于报应与一般预防需要死刑但个别预防不要求死刑的情况,而相对于个别预防,报应与一般预防的意义要大得多,它们构成刑罚的主要根据。以报应与一般预防需要死刑为由而对姚锦云判处死刑,即符合报应限制功利的原则,又合乎舍次(个别预防)求主(一般预防)的功利法则,因而是完全正当的。”5既然“报应与一般预防需要死刑但个别预防不要求死刑”,那么,按照他前面设计的规则,应该是报应(死刑)对姚锦云不利,而特殊预防(不适用死刑)对姚锦云有利,报应让步于功利,结论是对姚锦云不适用死刑。可见,他本人关于姚锦云案件判决的分析与他前面的观点出现了前后矛盾的现象。6
张明楷教授根据消极责任主义的点的理论来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的二律背反问题。他主张量刑应贯彻责任主义,与责任相适应的刑罚只能是正确确定的某个特定的刑罚(点)而不是幅度,在确定了与责任相适应的具体刑罚(点)之后,只能在这个点以下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并且,不能因为一般预防的必要性大而在责任刑(点)之下从重处罚,如果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大,可以从重处罚,但是要在责任刑(点)之下从重处罚。7按张明楷教授的主张,责任刑(点)是基于任何功利的理由均不能突破的限度,不论是出于一般预防的需要还是出于特殊预防的需要,都必须在责任刑(点)之下来科处刑罚。这一主张彰显了突出强调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的立场。
冯军教授借鉴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中的功能责任论来解决责任与预防的冲突问题。他认为现今的责任论已经由“规范责任论”演变为“功能责任论”,“只有采用功能责任论,才可能克服综合刑论在处理责任与预防的关系时所产生的破绽。……在科处刑罚时,是否需要考虑某一因素,在需要考虑某一因素时,该因素是使刑罚更重还是更轻,都应该根据功能责任论来决定”。按功能责任论,“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责任,要根据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忠诚和社会解决冲突的可能性来决定。在行为人忠诚于法规范就能形成不实施违法行为的优势动机,就能战胜想实施违法行为的动机时,行为人却实施违法行为的,就要把行为人解释为实施违法行为的原因,行为人就对其实施的违法行为负有责任;在社会具有更好的自治能力,即使不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也能解消行为人引起的冲突,也能维护法规范和社会的稳定时,行为人就无责任”。8在笔者看来,“功能责任论”尽管对“责任”的内涵和外延有新的解释,对判断某事由能否作为量刑情节与以往的责任理论有所不同,但也只是换了一种理论来解说刑法意义上的“责任”的涵义,当涉及责任与预防之间的关系时,仍然摆脱不了二者在个案量刑时的二律背反问题。
我国也有学者主张阶段说。如夏勇教授认为:“各国刑法都承认:犯罪事实与犯罪人两方面因素都影响量刑,前者体现刑罚的报应根据,后者体现刑罚的预防根据。然而,如果一个案件的犯罪事实危害很严重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或者犯罪事实相对较轻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量刑其实无法既体现报应又体现预防。报应与预防是对立的刑罚价值,从根本上不能调和,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量刑的根据应当是报应。这并不意味着不顾预防,但应当放到行刑阶段去考虑。”9夏勇教授的阶段说,将量刑的根据限定为报应,其意味着,量刑时与预防有关的因素即事前和事后情节均不能予以考虑。这一学说将量刑活动简单化,忽视了量刑的复杂性,同时,分不同阶段设定刑罚所作出的直接选择和判断的根据何在,其难以说明。
(二)有关预防刑和报应刑二者关系的立法及其立场导向
在对量刑根据及预防和报应二者关系进行规定的立法中,一般采纳的是报应刑和预防刑的并合主义。这些立法中,有的明确地体现了以责任刑为主、预防刑为辅的立场导向,“罪责”或“责任”是量刑的基本立场。如《德国刑法典》第4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的罪责是量刑的基础。10《瑞士联邦刑法典》第63条关于“量刑的一般规定”中规定:“法官根据行为人的罪责量刑;量刑时要考虑到被害人的犯罪动机、履历和个人关系。”11《奥地利刑法典》第32条规定:行为人的责任是量刑的基础;法院在量刑时,应权衡对行为人有利和不利的情况,还应考虑到刑罚和行为的其他后果对行为人将来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12
即使是只对量刑的根据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国家或地区,对具体个案中报应刑与预防刑之间的冲突由刑法理论来解决,理论上采纳的也是以责任为中心的量刑根据原理。“量刑应根据刑罚的目的来决定。因此关于刑罚目的的折中说,在量刑上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责任,也要考虑刑罚的目的。但是支配刑罚的最高原理是责任主义,故量刑的基础和界限应该是行为人的责任。即预防的目的只在行为人的责任一致的范围内考虑,为特别预防和一般预防超出责任的范围而裁量刑罚是不容许的。”13
美国关于量刑的目的和根据,也体现了以责任为基础的立场。美国法律协会《示范刑法典修正案》(2007年5月16日起适用)在第1.02(2)节将应得惩罚原则规定为首选的分配原则,但也允许遵循威慑、改造、使丧失犯罪能力、恢复能力和重返社会的原则,只要它们可行并且不与应得惩罚原则相冲突。其规定如下:“本法典中定义量刑的规定适用于所有量刑体系中的公职人员,量刑的一般目的如下:(a)有关个人犯罪的量刑:(ⅰ)根据犯罪严重程度、对被害人造成伤害大小及罪犯应负责任实施量刑;(ⅱ)在不违背(a)(ⅰ)规定且合理可行时,达到改造、一般威慑、使危险的犯罪人丧失犯罪能力、犯罪受害人及社区恢复,犯罪人重返法律容许的社区的效果;(ⅲ)为达上述(ⅰ)(ⅱ)目标,量刑不得重于必要性要求。”14该规定本身就体现了责任为基础的基本立场,并且,其不仅体现了责任与预防的并合主义理念,同时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了刑法典。
三、以责任为基础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在个案量刑时的冲突
从对各国理论学说和立法的分析可以看出,融合报应与预防的并合主义是当今关于量刑根据的主流观点,并且,以消极的责任主义为中心的刑罚根据理论是当今刑法理论的共识和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乃至英美法系许多国家的做法。消极责任主义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用消极的责任主义指导量刑活动,对准确地确立量刑基准、协调罪刑均衡与犯罪预防之间的冲突、规范量刑情节的提取和认定以及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点的理论与幅的理论相比较,点的理论比较可取。或许,责任刑的点可能并不十分精确,但与责任相适应的刑罚应该是确定的,否则对犯罪人的最终宣告刑也谈不上是确定刑种和刑期。“点的理论是消极的责任主义在量刑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不能违反责任主义,不得将被告人作为工具这样的观念,显得尤为重要。责任主义的核心是保障行为人的自由与权利。采取点的理论,意味着法官在考虑预防必要性大小之前,必须确定责任刑这个点。即使确定这个点比较困难,所确定的点也可能并不十分精确,但这个点的确定,可以限制法官对预防刑的考虑,防止法官量刑的恣意性,从而保障行为人的权利。”15基于消极的责任主义和点的理论的立场,本文第一部分提出的几个问题应做如下解答。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可以”。理由是,消极的责任主义反对基于一般预防或者特殊预防的需要而突破行为人的责任刑的上限来判刑,但不反对并且主张如果预防的必要性小,可以判处较轻的刑罚,基于点的理论,在责任刑(点)之下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恰好是消极责任主义在量刑上的具体体现。同理,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对甲的宣告刑可以是5年刑期。
关于第二个问题,如果根据消极的责任主义,对甲同样是可以宣告其它较轻的刑罚(包括死缓)的。但是,对甲未必不再适用死刑,换言之,对甲未必只有判处低于死刑的刑罚才是恰当的。理由是:此种情形与甲犯A罪情形不同,犯B罪的甲,罪行十分严重,即便法官在量刑时考虑了预防的必要性相对较小,对甲从轻甚至减轻处罚,也未必最终一定能够改变死刑判决,因为其责任刑是“重罪死刑”,在其责任刑“重罪死刑”之下判处刑罚,可能由“重罪死刑”降到“死刑”,但未必一定能够降低到无期或者死缓。姚锦云案、张恩举案即为适例。在这两个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是没有考虑到其悔罪的表现,但是,犯罪人已犯罪行极其严重,如果因为其事后的悔罪表现,大幅度地降低责任刑,判为其它刑罚,等于过分强调特别预防的功能,换成大白话就是“一个人可以卯足劲干坏事,事后只要悔改,就可以免除死刑或者较重的刑罚”。这种过多地追求功利价值的做法,会严重损害报应正义,并且损害国民的“守法意识”。
同理,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应该有条件或者底线的限制”。因为这会导致刑罚被不当地减少,产生量刑失衡,同时会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事实上,刑罚的一把预防作用与下列两个因素紧密相连。即刑法规范的内容和刑事制裁不可避免性程度。……就刑事制裁的有效性而言,有一点很清楚:一种刑法制度如果不能保证对其规定的可罚行为进行起码的制裁,那就根本无一般预防的功能可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本就不相信刑法规范所包含的威慑)。”16可见,贯彻责任主义,以责任为基础进行刑罚的量的确定,仍然要注意妥当处理责任刑与预防刑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要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以行为人的责任作为量刑的基础和界限,尤其不能基于预防必要性大轻易地突破责任刑的上限确定宣告刑。责任主义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刑法运作中的机能,“不仅是归责的责任主义,是犯罪成立的必要条件,具有犯罪论上的机能,而且是量刑的责任主义,是适用刑罚时确定刑种、强度及其极限的基准,因而具有刑罚论上的机能。”17尽管根据关于刑罚目的的折中说,在量刑上不仅要考虑行为人的责任,也要考虑预防的目的。但责任主义是支配刑罚的最高原理,故量刑的基础和界限应该是行为人的责任,预防的目的只在行为人的责任一致的范围内考虑,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超出责任的范围而裁量,刑罚原则上是不容许的,尤其是,基于一般预防的需要,不可突破责任的上限。“将人作为人来尊重,就意味着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不允许把任何人作为实现与其本人无关的目的的手段。”18刑法所指向的是一般人与一般事件,立法环节对具体罪规定的法定刑就考虑了一般预防的需要,对特殊预防的考虑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一般预防的效果。因此,量刑时只要罪刑相应,罚当其罪,就是这一环节实现一般预防的最好的选择。如果为了预防他人犯罪而对此犯罪人判处超出其责任应该承担的范围的刑罚,就意味着,为了防止乙犯盗窃罪,对犯罪的甲判处超出其盗窃罪责的刑罚。这明显意味着让甲作为实现一般预防目的的工具,是不公正的。
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需注意,如果某事由可基于多重量刑根据成为量刑情节,该事由作为量刑情节的适用,要有顺序,已经作为责任刑考虑的情节不可再次作为预防刑考虑的情节,避免同一事由既作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来适用又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情节来适用。以作案手段为例,作案手段能够说明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因此是影响责任刑的情节,但作案手段也能够通过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反映,显示对行为人特殊预防必要性的大小,从而可以作为预防刑情节。但是,犯罪手段已经作为影响责任刑的情节考虑过,就不可以再次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情节予以考虑,否则是一个事由重复被利用作为量刑情节,影响量刑公正。
第二,贯彻责任主义,也要避免不适当地减轻责任刑。不适当地减轻责任刑的表现之一是将应当作为责任刑考虑的因素当作预防刑因素予以考虑,从而不适当地减轻责任刑。以杀人未遂为例,某甲杀人未遂,但却给对方造成了伤害的实际损害结果,另有某乙杀人未遂,未给对方造成伤害等实际损害结果,那么,不仅未遂犯本身不适合作为影响预防刑的情节,同时对甲的量刑要考虑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后果,如果无视甲造成伤害的后果,就会忽略甲造成伤害的后果对应的责任刑,使得责任刑对应的刑罚量被不当地减少,无法体现甲、乙二人量刑应有的不同,不同案件同样的判决也是量刑失衡的表现。不适当地减轻责任刑的另一个表现是过于抬高犯罪人悔罪等事后情节的地位,如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赔偿、被害人谅解对量刑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新的《刑事诉讼法》也充分肯定了事后赔偿、谅解的作用。过于提升事后情节的影响量刑的作用,等于过分强调特别预防的功能,这种过多地追求功利价值的做法,会损害国民的“守法意识”。因此,尽管可以因为预防的必要性小而在责任刑之下判处刑罚,但不能没有程度的限制,更不能随意突破法定刑的下限。除非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不得随意放弃对犯罪人的刑事追究。
第三,关于责任主义的例外情形。有原则就有例外,责任主义作为支配刑罚的最高原则,也有例外。以张明楷教授、邱兴隆教授的观点为例,可以说两位教授提供了以尊重个人人权理念支撑的逻辑上严谨、体系完美的答案。但这种答案忽略了下面的问题:任何原则都有例外,许多唯美主义的体系性思考和设计常常被现实需要所打破,因而例外的存在也是客观的,原因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总是现实的,其要不断地面临新的社会问题的挑战,必须及时回应社会现实,解决问题,满足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立法者和司法者眼里,个人人权的保障要与惩罚犯罪兼顾。
累犯的处罚即是很好的例子。尽管学界的质疑声不断,但是立法者却不为所动。迄今除了德国于1986年4月13日删除累犯加重的规定之外,日本刑法、法国刑法、意大利刑法、韩国刑法、瑞士刑法、奥地利刑法、荷兰刑法中均有累犯加重的规定。如《日本刑法典》第57条,“再犯的刑罚,是对其犯罪所规定的惩役的最高刑期的二倍以下”。19对累犯从重处罚,是否违反责任主义?在日本,刑罚的加重减轻方法,使累犯加重的规定违反责任主义。但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即使符合累犯加重的要件,就后罪而言,也难以认为其行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严重到超出通常的法定刑范围的程度。即使肯定类型性地责任加重,也不能说明现行法所认可的这种大幅度的刑罚加重。所以,应当从刑事政策的见地将累犯规定理解为责任主义的例外的一种制度。”20哈格认为,“规定惩罚的立法者并不唯一关注功用,分配刑罚的法庭也不将自己仅限于正义。”“偶尔,法律本身可能为了其他社会价值或需要而牺牲正义。”严格责任虽然不正义(因为它主张对没有罪过的行为施加刑罚),但在立法上得到了确认。这是立法上刑罚基于公理的需要而不受报应限制的明证。21而为了剥夺具有构成累犯的严重危险的罪犯的犯罪能力而施加超过罪刑相适应所允许的刑罚,则是司法上刑罚不受报应制约的明证。22古典学派的体系上、逻辑上完美的责任主义,同样有例外。社会现象是变动不居的,社会不会按照学者所设想的自给自足的规范体系来发展,社会的管理者要始终面对社会难题,当棘手的现实问题出现时,学者表现的通常比较保守、可以理性地慢慢地论证和分析,但立法者和司法者总是现实的,立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回应社会现实,解决其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因此,再完美的体系也存在例外,就如同原则与例外的关系,有例外不等于说原则的价值受损,也不等于否定原则的普适性和确定性,而是约束例外的方向和范围的尺度。累犯作为责任主义的例外,固然有突破责任主义的特点,但为了限制这种突破,各国规定了加重处罚的范围,其用意就在于此。当然,为了与责任主义相协调,通过增加成立累犯的条款来缩小累犯加重的范围,从而解释累犯加重与行为责任相一致,即为了协调累犯加重和责任主义,不应把累犯的刑罚无条件加重,而应由于再犯加重谴责时为限加重刑罚比较妥当。
至于其它的在基准刑之上的量刑情节,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规定的“有前科劣迹的”及“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的”、“在重大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犯罪的”,为协调这些情节与责任刑之间的关系,也要尽量缩小其影响基准刑的度。当然,“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孕妇等弱势人员的”及“在重大自然灾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期间犯罪的”等情节原本基于责任主义,依据罪刑均衡的原则,也是应该考虑的因素,但我国的“基准刑”是“根据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所以原本应该依照责任主义考虑的情节未在确定“基准刑”的环节予以考虑,在之后的环节予以考虑也是正当的,并未违背量刑中的责任主义。
注:
1[日]阿不纯二:《量刑之位置价说》,余振华译,《刑事法杂志》1993年第2期。
2、13[韩]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韩相顿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第515页。
3、7、15张明楷:《责任主义与量刑原理》,《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4、5邱兴隆:《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26页,第328页。
6本文认为,应判处死刑的案件,其行为人危害程度仍然有很大的量的不同,死刑案件中考虑从轻,不等于就一定不判死刑,一定降为死缓或者无期徒刑,有的犯罪极其严重,即使考虑从轻,仍然无法改变死刑的判决,原因就在于犯罪的危害是无穷的,都是死刑,但所惩治的罪行的轻重程度仍然是不同的。姚锦云案之所以仍适用死刑,是因为即使考虑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但是仍不足以降低到不判处死刑而改为死缓或无期的程度。
8冯军:《刑法中的责任原则 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
9夏勇:《关于量刑根据的反思》,《法治研究》2012年第4期。
10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1《瑞士联邦刑法典》,徐久生、庄敬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12参见许久生译:《奥地利联邦共和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4[美]保罗H·罗宾逊:《刑法的分配原则——谁应受罚,如何量刑?》,沙丽金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9页。
16、18[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6页。
17梁根林:《责任主义原则及其例外——立足于客观处罚条件的考察》,《清华法学》2009年第2期。
19《日本刑法典》,张明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20[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总论》,有斐阁2008年版,第558-559页。
21 Ernest Van Den Haag,Punishing Criminals:Concerning A Very Old and Painful Question,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 ishiers,1975,pp.27-28.
22 Ernest Van Den Haag,“Punitive Sentences”7Hofst ra Law Review,1978,PP.13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