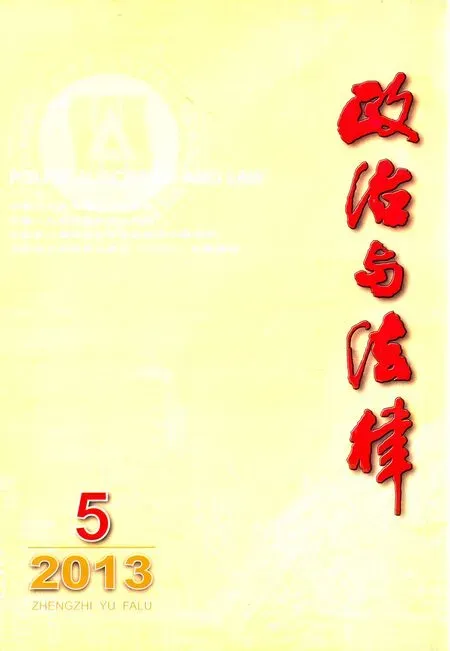证人出庭作证例外的裁量性标准问题探析*——基于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第187 条、第188 条的分析
何邦武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0000)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和实施,已使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从过去的正当性论证转向如何使该制度真正走进司法实践,成为“行动中的法”的实行性思考。与这种从文本到实践的转向一致,对有关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范的理解与适用,正成为研究的热点。其中,探究《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第188条中有关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例外的裁量性标准,显得尤为迫切。这是因为,受制于既有的刑事司法体制,加之书面证言如何限制使用尚未明确,实践中将极易导致强制作证例外适用对象的扩张,从而使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则本身虚置,并最终颠覆该规则所欲达到的目的。
有鉴于此,本文将立足法教义学的立场,1以建构的方式,通过对既有条文的适当反思和调整,经由对裁量性标准的解释克服其缺陷:在规范性语句和有关证人强制作证例外基本法理的双重约束下,依循既定条文的意义脉络,阐明既定规范的意义并使之精确化,以此完成对有关强制出庭作证例外的既定条文“语义空缺”或曰“规范漏洞”的合目的性弥补,并最终推进有关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例外在实践中的运用。
一、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例外及其裁量标准存在的不足
可以充分肯定的是,就一般法理而言,在刑事诉讼中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既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价值,也有利于保障被告的质证权(包括对质与询问两项权利),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价值。因而,尽管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是基于发现案件真实的初衷,但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对被告质证权的保护,2其进步意义不容否认。就此而言,该规则的出台可视为是对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所增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之新刑事诉讼原则的积极回应。
根据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款的规定,对于强制出庭作证的裁量,规定了三个条件:(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2)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3)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该条的合理解释是,由于我国尚未设立传闻证据规则,未能明确书面证言如何限制使用,3因而在刑事审判中,一般情况下,证人无须出庭作证,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证人,才有到庭作证的义务,可以被强制出庭作证。而在这三个条件中,法院认为是否有必要又居于三者中心。换一个角度,对这三个条件也可以作这样的解读,即虽然诉辩双方对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但如果法院认为“没有必要”,该证人也可以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由此构成了第一种类型的强制出庭作证的例外。与此相关的是,第188条第1款又规定,需要到庭作证的证人如是“有正当理由”的,法院可以免除其被强制出庭作证的义务。如果将这两条结合起来,有关证人最终是否出庭作证,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的过滤,一是对本应出庭者作出“没有必要”出庭的裁定;二是对即使应当到庭的证人,作出“有正当理由”不出庭的裁定。
不难预见,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无论是对证人作出“没有必要”到庭作证的裁量,还是对其作出“有正当理由”从而排除其到庭作证的判定,都将产生裁量性标准如何把握的问题。由于我国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而非以审判为中心的线型刑事司法体制,且如前所述,在宽泛的证人概念下,证人庭外陈述如何使用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则,4这两类情形的判别将留给法院过大的空间(甚或沦为一种恣意)。其中的焦点,即是究竟哪些已有庭外陈述的证人可以免予被强制出庭作证。由于仅据目前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三个条件和不出庭作证的“正当理由”标准,实难以确知其“可预期性”,这无疑将给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带来新的难题,可能会影响甚至违背该法所追求的通过强制证人出庭实现程序正义的价值目标,亟待作出规范。
鉴于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要求,在新法甫定时再作较大的修改不合情理也不经济,因此,经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种“媒介行为”,实现对“没有必要”出庭作证和“有正当理由”免予出庭作证情形含义的精确化,确立在可以被强制出庭作证的证人中,符合特定条件的庭外证言可以被使用的例外,划定应当出庭作证证人的范围,使“没有必要”及“有正当理由”条款更加明晰并具有可操作性,应该是当下必要且恰当的解决路径。并且,这种解释的方法既合乎逻辑,也符合我国的司法实情和既有的司法惯例。
需要说明的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法官适用法律并在此过程中进行法律解释不同,我国的法律解释一般来说既非附属于司法裁判权的一种活动,也非附属于立法权或法律实施权的一种活动。这种解释在法律上被单列为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而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的分配,则构成了一种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法律解释体制。5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其性质即属于此种。同样被赋予这种解释权的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因为这里的“没有必要”出庭作证及“有正当理由”属于法庭审判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故而解释的权力应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存在许多法理正当性问题和争议,但这种解释体制一直相沿不替,而且,由于宪法及其实际运作机制尚无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将来对《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这种解释体制将得到沿用。故本文也将有关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置身于该种解释意义上进行探究。
二、传闻规则法理之于我国强制出庭作证例外理论的借鉴
传闻证据规则(the hearsay rule),又称反传闻规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系英美法系重要的证据规则,是指在审判中一般不能采纳传闻证据,已经在法庭上提出的,不得交陪审团作为评议的依据。传闻证据,是指用以证明所主张事项真实性的庭外陈述,包括口头、书面及有明确意思表示的叙述性动作等三种形式。英国证据法学家Phipson认为,传闻规则是“非诉讼当事人的人和没有被请来充当证人的人所作的口头或书面陈述,不能予以采纳以证明所说的事实的真实性”。6为了防止因排除所有传闻证据所带来的证据使用上的负面影响,传闻规则在以排除传闻证据为原则的同时,还以必要性(necessity)和可信性(rel iabil ity)为准则,规定了许多容许采纳传闻证据的例外。
所谓必要性即指,存在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对质询问的客观情况,同时也无法找到具有同等证明价值的其他证据资料代替,因而不得不使用庭外陈述。按照证据学家威格摩尔的论述,必要性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原陈述人已经死亡,或不在法院管辖区内,或因疾病,以及其他不能接受交叉询问的情况;二是原陈述人难以再度获得,或由于其他资料难以证明,或难以获得与原陈述有相等证据价值的资料。可信性则指,从庭外陈述产生背景等情况来看,该陈述具有高度可信性,即使不给当事人对质询问机会,也不致损害其利益。可信性的情况有三种:一是在陈述当时,足以认为陈述人吐露真情,言辞准确,没有虚构意图;二是纵使陈述人在陈述当时可能有虚构的意图,但这种危险容易被发现,或陈述人惧怕虚伪陈述会导致惩罚;三是陈述是在公开的情况下作出的,该陈述如有错误很容易被发现并改正。7根据必要性和可信性基本原理,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3条、第804条、第807条即规定了不能出庭、无须出庭及剩余可裁量的例外等共32项例外情形。
近年来,围绕该规则的争议不断,改革呼声日高,甚至出现如达马斯卡所言的赞同排除传闻证据的声音迅速弱化这样的传统证据规则和惯例被腐蚀的局面。8但就其基本法理而言,该规则所蕴含的诉讼机理以及对抗制下的人证制度精神具有超越法系的价值。就其有利于发现案件真相而言,传闻规则排除了案件事实在传递过程中被扭曲的可能,保障了交叉询问制度的实施及审判者审判中的亲历性。而就其维护程序正义而言,传闻规则有利于维护控辩双方的平衡,保障了被告的对质询问权以及程序参与权的实践。9尤其是该规则对刑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护的意义,与刑事司法国际化的一些价值诉求具有同质性,为英美法系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所认可,并被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直接引入,或者被吸收转化为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例外。10此其一。
其二,就该规则所设置的例外来说,其例外的可采性以可信性和必要性为原则,这将使如何采信例外的传闻证据有明确的原则约束,为法官在准予例外的裁量中设定了第一道屏障。而且通过明确规定一系列具体的例外可采性规则,使庭外陈述的使用有明确可适用的规范,可以更加有效地抑制法官的恣意,规范其自由裁量权,并充分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公正审判权等诉讼权利,推进了程序法治。换言之,无论是必要性还是可信性情况下对传闻证据的例外采用,都可视为为了发现案件真相,不得已牺牲被告诉讼权利,而以严格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为限制则又表明:这两种例外在适用上是有限度的,否则将造成对刑事被告诉讼权利的过度侵越,打破刑事诉讼在发现真相与维护程序正义之间的适度均衡。质言之,例外的适用是在对传闻规则的向心力与离心力均衡作用下的结果,与规则追求的价值目标有内在的一致性,不应视为对该规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即发现案件真实并维护程序正义的悖离,即便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807条所谓的“一网打尽”(cast al l)的“其他例外”,也规定了真实性保证的条件。因此,主张由于传闻规则的例外已形成该规则的特色,该规则本身已不成规则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修订时,已确立了“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重新配置了控、辩、审的职能,增加了庭审的对抗性,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护得到加强。一系列朝向现代刑事诉讼法治目标的改革,“意味着我国庭审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开始发生”。112012年的修订是对1996年刑事诉讼改革目标的延续,无疑是向着刑事诉讼法治目标的又一次接近,尽管还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12而关于特定情形下的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则进一步加强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符合证据制度和刑事庭审规则的基本法理。因此,虽然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设立传闻证据规则,但司法实践中并不排除对传闻证据的使用,可以断言,新法对特定情形下的证人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表明其对刑事诉讼法治及其价值目标的追求,与传闻证据的诉讼及证据法理有暗合之处。而其第187条、第188条有关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两种例外情形的规定,其依存的法理则理当与传闻规则例外蕴涵的内在机理具有一致性,即例外的裁量仍应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所追求的目标为归依,不能成为豁免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无条件恣意。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在对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例外条款存在的“规范漏洞”进行建构性解释时,应当参酌传闻规则及其例外的基本法理,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规则乃至整个《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目标为准绳,对“没有必要”及“有正当理由”的例外进行合目的性解释,使其成为规范命题,为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例外规范的实施厘定明确的范围和对象。只有按照这样的解释方法,才能合乎制度改革的逻辑,并使法官在面对要不要传唤证人、被害人等出庭作证,如何解决证人、被害人当庭陈述与其庭外陈述或询问笔录之间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能够坚守刑事法治的精神,禁绝裁量中的恣意。
此外,这里的证人除了《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所指的狭义上的证人和被害人外,还应包括第187条第2款规定的在执行职务时目击犯罪情况的人民警察。对于此种情形下的警察作为证人在必要情况下被强制出庭作证,笔者认为,不应再生疑议。至于共同犯罪中的被告人作为证人作证问题,由于共同审理,不存在强制出庭问题,故无须讨论。
三、创制我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例外情形与规则的构想
根据前文所主张的解释方法,有关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例外的解释,应当既要实现对例外的规范性阐述,也要使其成为一种合目的性的表达。前者要求的是,对例外的解释应使其成为一种可操作性规范,后者则要求这种经解释形成的规范应同时符合刑事法治的目的。因此,在具体的解释过程中,宜遵照上述要求,按照司法实践中,法官裁量的逻辑顺序,首先明确“没有必要”的例外,其次是明晰“有正当理由”的范围。
(一)关于“没有必要”的例外
根据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款关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这一规范的语义脉络,“没有必要”出庭的范围应仅限于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没有异议,且对案件定罪量刑无重大影响的证人证言。但这样的例外范围显然过于狭小,因此,应在立足该条语义的基础上,结合传闻证据例外的必要性和可信性原理,对“没有必要”的例外情形作扩张解释,确立以下几种情形的例外。
其一,控辩双方同意使用庭外陈述时,证人无须出庭作证。这一情形相当于传闻规则中同意的例外。13设定此项例外的理由是如果对某项庭外陈述同意其于法庭上使用,则该陈述已取得证据能力,而相对方已放弃对其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但其证明力仍待法庭调查后确认。14
其二,证人、被害人陈述是在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时作出的陈述。这里仅限于此人后来没有死亡的情形,如其后来死亡,应属于“正当理由”的例外。但二者都建基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一般信念。此类庭外陈述的例外在普通法系有着悠久的传统,属于前述威格摩尔氏所述的具有“可信性”保障的例外。而在适用时,可参照关于使用该证据的通行规则,提出证据的一方应当向法庭证明此类陈述的前提条件:一是证明陈述是在陈述者意识到自己即将死亡时作出的;二是陈述者当时的意识是清楚的。15
其三,陈述者于事发当场有关其感觉、印象的即时陈述,即陈述者察觉事件或情况之时、或之后立即作出的,描述或解释该事件或情况的陈述。本项例外可借鉴传闻规则关于此项例外的一般理论,即事件发生与陈述作出基本处于同一时间,可以排除故意或有意告知不实的可能性。
其四,激奋状态下脱口而出而来不及细想的陈述,即在某一惊人事件或情况引起陈述者激奋难抑时作出的、关于此事件或情况的陈述。适用该例外时,首先必须有足够令人吃惊的事情或事件发生,以致观察者来不及作正常、仔细的考量;其次该陈述是陈述者对该事情或事件的本能性反应。16在具体判断陈述者是否处于激奋状态时,应综合考量以下因素:事件与陈述之间的时间间隔;陈述者的年龄;其身体或精神状态;事件的性质以及陈述的内容等等。17本项例外和前述第三项例外的区别在于这里的陈述者,其精神心理受到刺激而处于激奋状态。
其五,当时存在的精神、感情或身体状况的陈述。本项陈述系陈述者关于当时的心理、感情、感觉或身体状况(如意图、计划、动机、构想、精神感受、疼痛、以及身体健康)的陈述。根据普通法关于此项例外的传统,该例外只允许表达当时状态的陈述,但不允许将导致这种状态的原因的陈述作为本项例外,除非后者本身符合其他传闻规则的例外。例如,在R.v.Horsford案中,死者对医生的临终陈述是:“我中毒了,(被告人)给我下的毒。”在对被告人谋杀案的审理中,该陈述的前半部分被采纳,但是后半部分关于谁给她下了毒的陈述被排除了。18
其六,出于医疗诊断或治疗目的而作的陈述。本项例外系借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即缘于医疗诊断或治疗目的需要而作出的、描述医疗史;或者过去或现在的症状、疼痛或者感觉;或者病因或外界的病源的初始症状及一般症状的陈述,但限于依照情理与诊断或治疗有关的范围内。适用本例外时,该陈述不一定是向医生作出的,也包括向医院人员、救护车司机甚至向家庭成员作出的陈述。并且,该陈述既可以是当前身体状况的陈述,也可以是过去身体状况的陈述。
其七,已被记录的关于某项事件的回忆。这是因为当目睹事件发生者对事件的发生记忆犹新时,他对事件所作的记录比当庭作证还要准确。19普通法中关于适用本例外的条件可资借鉴:证人必须要具备关于事件的第一手知识;书面陈述必须是在事件发生之时或之后不久、证人具有关于事件的清楚和准确的记忆时作出的原始记录;必须是证人目前对事件缺乏记忆;证人必须保证书面备忘录的准确性。20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这种记录只能作为帮助回忆的材料来使用,而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直接证据。
其八,证人、被害人不利于己的庭外陈述。在适用条件上,参照英美等国家的相关规定,对自己不利的陈述还要作以下一些限制。首先,陈述者意识到其陈述将不利于其所有权或金钱利益或其他重大利益;其次,陈述者作出陈述之时或之后意识到其陈述有损其利益;再次,陈述者是依据个人经验就事实所作的表达,而不是推测或者意见;最后,陈述者没有说谎的动机。适用本例外时,还要与利益冲突当事人之间的承认相区分。后者系一方当事人在不一定知情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未必违反自己利益的陈述,且不存在不能出庭作证的情形。但前者必须不能出庭作证,且在知悉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的违反自己利益的陈述。另外,在陈述的理解上,必须持狭义的立场,即只能是一份单纯的陈述和评论而不是一份报告或描述。21
其九,先前其他程序中的陈述。在另一相同或不同诉讼程序的听证中作为证人所提供的“证言”,或者在同一或另一诉讼程序中遵照法律作证所提供的“证言”。传闻规则关于此项例外的理由是,该证言现在所针对的当事人或者民事诉讼活动或诉讼程序中其利益的前手,已经拥有机会和类似动机,以直接询问、交叉询问或再直接询问的方式质询过该证言。而且,由于该证言是经过宣誓后作出的,如果证人不诚实或者作伪证,他会因此受到惩罚。结合《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关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及查办案件中有关证据的规定,可将这种先前程序扩展至行政执法程序。
其十,关于个人或家庭的历史的庭外陈述。此类陈述具体包括:关于陈述者的自身出生、收养、结婚、血缘关系、收养关系、婚姻关系、家世、其他有关个人或家庭历史的类似事实的陈述,即使陈述者无法就所述事项取得亲身知情;以及关于他人的前述事项以及死亡的陈述,其条件是该陈述者与此人有血缘关系、收养关系、婚姻关系,或者该陈述与此人的家庭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以至于他能够对所述事项获得准确的信息。22
上述各项例外中,第一项例外可理解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款条文本身的意义而推断的狭义上“没有必要”的例外,其余各项例外则基于庭外陈述具有“可信性”保障原理。
(二)关于“有正当理由”的例外
与“没有必要”出庭作证例外不同,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有正当理由”的例外,可借鉴传闻规则“必要性”原理,确立“有正当理由”例外的基本适用条件:第一,由于存在客观的现实障碍,无法对原始人证进行对质询问;第二,无法找到具有同等证明价值的其他证据资料代替,因而不得不使用庭外陈述。
结合其他国家关于必要性例外的规定,可将我国“有正当理由”的例外界定为:(1)证人、被害人死亡或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作证;(2)证人、被害人因路途遥远或现居国外,无法到庭作证;(3)证人、被害人下落不明,经过努力仍未能找到。
此外,还应借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中“一网打尽”即“其他例外”规则,对虽然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经过审慎审查,确实符合“没有必要”及“有正当理由”的情形,由法官作出裁量,准予不出庭作证,但应严格限制。对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关于此项例外的适用条件颇具启发意义。其第807条规定,法庭在依照传闻规则的例外裁定适用某项证据时,应当确保:第一,该陈述是作为一项重要的事实证据而提供的;第二,该陈述在所证明的问题上,比建议者通过合理努力能获得的证据具有更强的证明力;第三,如果将该陈述作为证据采纳,则本证据规则总的宗旨和司法公正将得到最佳效果。但是,除非建议者为了向对方当事人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准备面对该陈述,而在审理或听证前足够早的时间内通知对方当事人知悉,通知的内容是指提供该陈述的意图、陈述的细节,另包括陈述者的姓名与地址在内,否则,不得根据这一例外规则采纳该陈述。有学着将其归纳为三项实质性限制条件:同等程度的对可信性的情况证据保证、必要性和通知。23
(三)书面形式的庭外陈述在制作程序上的要求
除了符合一定例外条件而具有证据资格的实质要件外,对于控方制作的书面形式庭外陈述,还应规制其制作主体及制作程序等形式要件,防止其制作非法。辩方提供的书面形式庭外陈述不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限制之列,因此,只需要符合一般文书书写要求即可,但应证明确实是在上述两种例外条件和三类情形下制作的。
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的特点,笔者认为,对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其他行政机关调查搜集的庭外陈述者,应当遵循《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54条及第122条法定程序禁绝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且一旦发生程序瑕疵或非法的争议,应依照第57条的规定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在具体制作程序的限定上,可参酌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21条的规定,将制作庭外陈述笔录的主体限定为受诉法庭以外的法官、检察官和具有一定警衔的警察,且每一种类主体制作有效笔录的条件亦不同。24
此外,为回应实践中证人在法庭上作证具结的做法,证人庭外陈述还应要求证人具结,对于被害人则不宜作此规定。
以上关于两种类型的出庭作证例外及书面形式庭外陈述的制作要求是法庭裁定是否准予例外采用的基本裁量标准,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庭外陈述,可视为“没有必要”出庭作证或“有正当理由”而免除原陈述证人或被害人等到庭陈述的义务。此外,当出现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款规定情况时,则可启动强制出庭作证程序,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或者,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78条第3款“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法庭对其证言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的,该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的规定,规范证人出庭作证,接受质询。
四、结语
实现强制出庭作证例外的制度化,形成对法官裁量的羁束,离不开其他诉讼和证据制度的有效实施。除了前文所说的庭外书面陈述的规范化制作外,增强该庭审中的对抗性,以赋予被告人诉讼权利为中心,完善交叉询问制度等,25将是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而且,对传闻规则的借鉴,还面临着我国刑事审判中尚无明确的“审判中心主义”制度安排的问题,而这正是传闻规则发挥其规范作用的必要制度环境。弥补此项制度空缺,较为稳妥且必要的方式应当是:基于刑事审判的基本原理,按照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要求和本文所指示的法教义学进路,重新解释《刑事诉讼法》有关庭审制度的规定,尤其是公、检、法三部门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界限。26在制度之外,仍需要法官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高尚的职业操守,摒弃传统的刑事治罪理念而代之以现代的以保障诉讼人权为根本的刑事法治理念。
还应说明的是,证人等免予强制出庭作证与证人主张因与被告人有特定关系或特定情形如作证将自证其罪而拒绝作证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是公权力对证人出庭作证义务的酌免,后者则是基于证人的权利主张而产生。故对于后者,如果证人放弃拒绝作证特权或证人在被豁免其罪刑情形下作证,且同时符合上述拟定解释的例外情形时,也可以不被强制出庭作证,但如果不具备上述情形,即应在强制出庭之列。新修订后《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关于被告人配偶、父母、子女可免于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将其视为强制出庭作证的例外,实有将二者混淆之虞。
注:
1这里借用德国法学家拉伦茨先生关于法教义学的定义:“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的答案的学问。”[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2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其作为权利赋予被告,因为从其第59条的内容来看,法律虽然确立了当庭质证制度,但其是从质证有利于协助法官审查判断证据的真伪这一角度出发的,没有将其定位为被告的基本权利,而是作为一项技术性规则。另外,该条将对证人证言的法庭调查由原来第47条规定的由双方讯问、质证改为质证,似使原来的规定转而变得笼统。
3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证人庭外陈述的使用上没有明确的规范,但关于鉴定的证据资格,已有类似传闻证据规则的规定。这说明立法者对庭外陈述的真实性问题已经有所思考。下文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所存在的弊端。
4已经过两次较大规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一直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尽管该原则用语本身缺少法律语言的意蕴因之很难作精当的分析,但置身于中国“威权式”诉讼理念指导下的刑事司法语境,由于“任何规范都无法排除价值判断”(拉伦茨),对此原则文本的文义释读只能是:我国刑事诉讼系一种有特定倾向即以“治罪”为旨归的“政法体制”,公、检、法三家为实现“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目标,在分工、制约之下,实行的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受此原则约束,加之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阙如等,有关证人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则迟迟难以出台,因为在现行刑事诉讼体制下,证人在公安或检察机关所作陈述也是证人证言,由此降低了证人出庭的必要性。因此,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关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作证的规定,并不能被解释为拒绝作证权,因为该类作证主体是基于正当理由而被免予出庭作证的,并没有将其作为此类人员的权利,与基于人权保障原则而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特权的规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此外,他们完全可被要求在庭外向公安、检察机关甚至法官作证(第60条是直接的依据)。因此,所谓新法有了亲属拒证权的说法,实属一种误读。此种情形通过比较可知。例如,在德国,如果证人在庭审中主张拒证特权,则其庭外证言将不能在法庭上宣读(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52条)。同样的原因,现行《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在有关庭外证人陈述的使用规则上,难以觅到大陆法系直接言词审理原则下的证人证言使用规则或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
5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的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该著作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各解释主体的解释形式、基本特点及该解释体制存在的原因。
6转引自沈达明:《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1996年版,第99-100页。需要注意的是,在传闻证据的适用范围上,根据英美证据法理论,该规则仅适用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审判阶段,至于刑事和民事诉讼审前阶段及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运用,则不适用传闻规则。而且,在有陪审团审判的刑事诉讼中,传闻规则仅适用于定罪程序,在量刑程序的证据听审中,传闻证据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证据使用。参见何邦武:《刑事传闻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内容提要”部分及第10-31页。
7 John Henry Wigmore,Wigmore on Evidence(3rd ed,1940),Vol.v.pp.204,212-214.
8[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刘晓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
9详尽论述可参见何邦武:《刑事传闻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8-67页。
10在传统上注重发现案件真实的大陆法系,传闻规则与其制度的交集应当主要在其程序价值之中。有关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事传闻规则的引入情形可参见何邦武所著《刑事传闻规则研究》中第六章及第七章的分析论述。大陆法系对传闻规则的引入在德国较为典型,例如,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3条至第225条的规定,如果证人、鉴定人因疾病、路途遥远或其他事实上障碍而不能于审判期日到场者,可由受托或受命法官代为讯问。其第251条至第256条则规定,在不可能直接询问或者没有必要直接询问的例外情况下,可以以宣读笔录或者书面陈述的方式替代。在德国,上述情形是作为直接言词审理原则的例外出现的,前者属形式直接性例外,后者属实质直接性的例外。参见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1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12有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所追求的目标及依此而进行的修订情况可参阅王兆国:《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说明》,http://www.npc.gov.cn/huiyi/l fzt/xsss fxg/2012-03/08/content_1705548.htm,2013年3月15日访问。然而自该次修订以来,一直有质疑之声,本文对此不拟展开评述。但总体而言,笔者的判断是,在取得进步的同时,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权力优位的格局尚无根本性改变。
13例如,根据英国《1996年刑事诉讼与侦查法》,在移送审判程序中提出过的所有证据,如不需要进一步证明,可在审判过程中作为证据加以宣读……除非诉讼的某一方当事人提出反对。
14日本学界对此类证据的研究甚为详细,并提出了同意后证据性质的各种观点。可参见彭勃:《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322页。
15 See Wi lson v.State,Supreme Cour t of Nevada,1970.
16[美]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37页。
17 See Morgan v.Foretich,846 F.2d 941,947(4th Cir.1988).
18 R.v.Horsford(1898)The Times,2 June 1898.
19 Owens v.States,67 Md.307,316,10A.210,212(1887).
20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将有关条件放宽,例如,将记录必须在事件发生很近的时间内准备或制作以保证其准确性的要求,放宽为“证人在记忆犹新且能准确反映其知情时制作或者采用的”。参见何邦武:《刑事传闻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
21 512 US 603(1994).
22参见何邦武:《刑事传闻规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23有关该三项条件的详尽讨论可参见[美]约翰·W·斯特龙:《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3-614页。
24参见孙长永:《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3页。
25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后,法庭审理过程的对抗性增强,具备了交叉询问制度的雏型,但与当事人主义意义上的交叉询问制度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是:直接人证调查有限度、交叉询问本身系“技术方法型”而非“权利技术型”,以及法庭审问制仍然存在等等(参见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6-310页)。这种状态在本次修订中仍然延续着。
26对三机关权力界限依据宪政和刑事法治的基本原理进行的解释,参见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