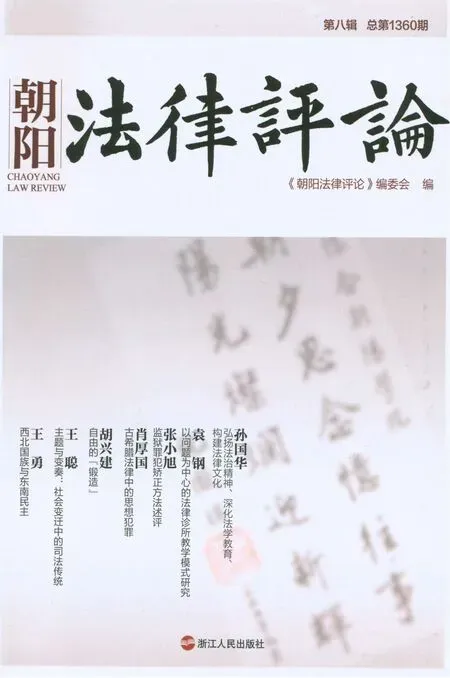霍布斯的“恐惧”
——以主权恐惧替代自然恐惧
张洪亮
霍布斯的“恐惧”
——以主权恐惧替代自然恐惧
张洪亮*
从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分野的视角观察,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可谓开天辟地。这一“开天辟地”主要表现在霍布斯以“恐惧”这一现代激情为基点构筑其“利维坦”,即在自然状态下,自然人之间由于身心平等且欲望无穷导致个人之间相互恐惧;为自我保全、超越相互恐惧,霍布斯力倡建构利维坦,从而以主权恐惧替代自然恐惧,以社会状态替代自然状态。主权恐惧进而成为巧设与维续利维坦的拱心石,形形色色的恐惧也因而贯穿于利维坦的前世今生。
一、霍布斯的“恐惧”
(一)霍布斯思想中恐惧的地位
主权问题即“谁应该来统治”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对此,古典与近代开示出的答案可谓南辕北辙。古典哲人认为,以法为治,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力。这也与自然法的原意相契合。按照自然法观点,法是蕴含于自然之中的理性的最高形式,它指示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个理性,当它牢固地扎根于人类心灵之中,并充分地发展于人类心灵之中的时候,就是法。因此,以法为治就是要实行理性之治。以理性制约非理性、以较高理性制约较低理性便是古典时代的最佳统治模式。
然而,霍布斯极力否认人与人之间在理性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认为,“按照天性每个人都拥有同等的理性;一些人能通过后天学习、生活经验的总结所能获得的理性优势也是无足轻重的”①[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2—93页。。鉴于此,我们必须任意地指定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理性,来充当标准的理性,并以此对某个人或某些人天然的理性优越性的阙如,加以人为的弥补。而那个人或那些人就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理性的荏弱无力,使得它有必要为最高权力所取代。出于同样的原因,法律也失去了尊严,取而代之的是自然权利。自然权利与理性相一致,但是支配它的那个力量却并非理性,而是恐惧。
由于霍布斯首先以无比清晰确切的语言,对依附于自然权利的近代政治哲学施以原创性阐释,因而被誉为“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而霍布斯并不局限于主权问题所关涉的狭小空间,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政治规则也进行了颠覆性的重造。霍布斯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规则的正当性与可行性已做出了精妙绝伦的设计,但是其对政治规则的施行运用(有效性)方面却不甚了了。政治规则单凭自身难以发挥效用,民众绝不会为了奉行的缘故而去奉行。为了弥补古典政治哲学遗留下的缺陷,他便转而求助于历史。因为“通过记叙实例,拓宽人的经验,揭示准则是如何被人遵循或被人无视的,昭示由此而来的成败得失,从而较之传授准则本身,更为有效地使人能够在具体的情势下,奉行那些规则”②[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而这些恰好承续了历史的任务。借助历史,霍布斯认识到人生应该如何指导安排。他试图通过对历史的综合归纳,窥探现实世界中的人实际上如何行为,实际上是由哪些力量在支配他们的行为,以总结提炼出政治规则得以运行的法则。他的回答掷地有声,“各种激情就是支配人们行动的力量。在各种激情之中,他特别强调虚荣自负与恐惧”①指导着这个选择的着眼点,在于激情与理性的关系,或更确切地说,在于各种不同的激情,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或不适合于对荏弱无力的理性加以取代的功能。因为,虚荣自负是一种使人盲目的力量,恐惧是一种使人明目的力量。这样,他就得以这两种激情,同人类共同生活的各种基本形式(公共领域与隔绝独处)明确无误地相互协调起来,并且回答了关于国家的最佳形式的问题(君主政体无条件地最为可取)。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57页。。
霍布斯的论述重心虽然在政治规则的施行运用(有效性),但他对政治规则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的论述也不乏妙见。柏拉图等古典哲人将政治规则的两种理性原因加以区分,分为善的与必要的。②于浩:《正义之殇——苏格拉底之“死不足惜”》,载付子堂主编:《经典中的法理》2011年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而“霍布斯则只承认一种,即必要的理性原因。这就导致霍布斯只能在必要性的框架内,去思考善与必要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对他来说,善的问题就成为界定什么是典型的必要性这样一个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我保存(避免死亡)就是典型的必要性之所在,也就是善之所在”③[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9页。。因此,死亡便被他视为恶之所在,甚至是首要之恶。
综上所述,恐惧被界定为接续古典与近代,连接主权问题与政治规则,勾连法律与自然权利的核心问题,亦即“恐惧”问题作为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思想的一把钥匙。因而对霍布斯的恐惧进行系统的梳理显得颇为必要。
(二)霍布斯思想中恐惧的生成背景
霍布斯的“恐惧”诞生于英格兰土崩瓦解、内战频仍的时代。那时,英格兰世俗政治势力与宗教势力互相对垒、冲突不断。既有的英格兰国教制度,也远远不足以对付清教与天主教势力。在辽阔的英格兰领地上,各种势力纷繁复杂,矛盾盘庚错节,冲突激烈异常,英格兰民族危在旦夕。为了摆脱内战,避免民族衰亡,“霍布斯写下了政治哲学的奠基之作——《利维坦》,它不仅建立了一种有关现代性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主流政治哲学,而且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伦理——一种自我主张的伦理观。世界成为一个个人可以追逐自己的愿望,计划自身的和社会的目标,发挥自己的能力的舞台。霍布斯说,不论宇宙的最终权力是什么,我们都能够管理市民社会,建设某种政治工具以便实现我们的目的和利益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我们首先创造了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①[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霍布斯在对人性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在“利维坦”中尝试达致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②王利:《简述近代政治的正当性: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例》,载《学海》2007年第2期。霍布斯认为:英格兰人民发生了普遍的腐化,以致不服从国家者反倒被视为爱国者。在探寻人民为何腐化时,霍布斯列出了七大罪魁祸首,并将“大众对臣民义务的普遍无知”作为万恶之源。有论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恐怕万人之中也难觅一个,能够懂得别人有命令自己之权,能够了解有必要存在国王或国家,哪怕这样付出违逆自己意志,上交自己资财的代价;相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所拥占的一切他人都休想觊觎,即便是出于公共安全之需,若无他的同意也断无可能从他那里拿走分毫。他们认为,国王不过是个最高的荣衔,就像士绅、骑士、男爵、公爵、伯爵一般,只要有钱财的帮助,便可一步步攀爬到那个位置上去;他们不念衡平之规则,只信先例或习惯;如果他碰巧是个最为反感国王特别津贴及其他公共支出的家伙,就会被认作智慧超群,被选入议会再合适不过”③孔新峰:《〈比希莫特〉与霍布斯的政治教育》,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8期。。
此时,大众的臣民义务荡然无存,主权者的权威也不知所踪。民众死心塌地跟随着各路牧师、乡绅抑或是他们的直接领导者,就连对抗主权者的法律也在所不惜。臣民与主权者之间的庇护与臣服关系因此遭受重创。“如果没有庇护和臣服的关系,任何秩序、任何理性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均无从存在。庇护与臣服乃是国家的第一原理。人类的本性和神圣的权利均要求不容置疑地遵循这种关系。”④[德]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芸芸众生打破了对主权者的臣服,在顷刻间变得英勇无敌和无所恐惧。
恐惧既是霍布斯一生生活的写照,也是霍布斯论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激情。它根植于人性之中,勾描出人类生活的基本面貌,并弥散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间,它既是政治社会得以建立的根源,也是政治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它甚至成为霍布斯抨击教会势力的“武器库”。
(三)霍布斯思想中恐惧的内在意涵
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在考察极端情形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全部道德和政治学说;他的自然状态理论所依据的经验是内战时期的经历。正是在极端情况下,当社会结构完全被摧垮时,一切社会秩序最终所必须依托的稳定根基就呈现在人们眼前了:那就是对于暴力的恐惧这一人类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①[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0页。。
在《利维坦》的第6章关于激情的论述中,霍布斯为“恐惧”下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义。他认为“当人们具有对象将造成伤害的看法时,嫌恶就称为恐惧”②[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9页。在现有中译本中,霍布斯的Fear有时被译作“畏惧”,有时则被译作“恐惧”。本文沿用对霍布斯的通行讨论,采用“恐惧”译法。为求统一,在本文引用时,亦将“畏惧”替换为“恐惧”。。因此,欲知霍布斯的“恐惧”,我们必须理解“嫌恶”和“伤害”这两个词。“嫌恶”是指意向避离某种事物。相反,“欲望”即当意向朝向引起它的某种事物。“嫌恶”和“欲望”都是由“意向”来加以连接的。“意向”依照霍布斯的论述即人体中这种运动的微小开端,在没有表现为行走、说话、挥击等可见的动作以前。“伤害”在霍布斯看来主要是指对身体的伤害,未知事物带来的伤害以及手段方面的恶。因此,恐惧是一种特定类型的嫌恶,是一种和被伤害有关的嫌恶。同时,恐惧也必然意味着对个人欲望的否定。
恐惧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怯懦即对妨害不大的事物的恐惧;二是恐慌即在不了解原因或状况的情况下产生的恐惧;三是宗教即对于不可知、不可见力量的恐惧。
从古典与现代分疏的视角看,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思想无疑是开天辟地的。这一“开天辟地”主要表征为霍布斯以“恐惧”为基点建构其“利维坦”。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由于身心平等且欲望无穷导致相互间的恐惧。为自我保全、超越相互恐惧,霍布斯力倡建构“利维坦”,以主权恐惧替代自然恐惧,以社会状态替代自然状态。主权恐惧进而成为建构与维续利维坦的拱心石。形形色色的恐惧因此贯穿于利维坦的前世今生。
二、霍布斯思想中的自然恐惧
(一)自然恐惧的人性理论基石
人性理论作为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关乎对霍布斯的恰当理解。霍布斯将其人性理论归纳为两条确凿无疑的人性公理。
第一条人性公理是“自然欲望”,即渴望攫取、占用他人皆有共同兴趣之物。这一欲望根源于人的动物性,但是人之欲望原初就是无穷无尽的,而动物的欲望只不过是对外在感性知觉的反应。人类欲望的观念是自然主义的。人类渴望权力,并本能地、无休止地渴望更为强大的权力。权力欲一泻千里,而并非是由无数孤立的感性知觉,唤起无数孤立的欲望,最后积累汇合而形成的。“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还要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①[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2页。因此,对权力的追逐既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非理性的。“对权力的理性追逐是可以被允许的,其本身也是有限的。受理性指引的人,往往都安分守己,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对权力的非理性追逐则是不被允许的,其贪婪成性,无穷无尽。对权力的非理性追求,即人的自然欲望,其本质上是追逐优越于他人及他人对此认可的各种激情,其基础在于人在端详他自己的权力时,所体验到的欢愉满足,也就是虚荣自负。”②[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霍布斯曾在《利维坦》中详细叙述了对权力的理性追逐和对权力的非理性追逐。“由于有些人把征服进行得超出了自己的安全所需要的限度之外,以咏味自己在这种征服中的权势为乐;那么其他那些本来乐于安分守己,不愿以侵略扩张权势的人们,他们也不能长期地单纯只靠防卫而生存下去。其结果是这种传统权的扩张成了人们自我保全的必要条件,应当加以允许。”[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3页。因为用虚荣自负为人的自然欲望下定义必然导致道德判断,而人的自然欲望在本质上源于人的动物性,他的本性并不邪恶。所以霍布斯越来越把虚荣自负推向幕后。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第二条人性公理,即自然理性公理便日渐凸显。
第二条人性公理是“自然理性”,它教导每一个人逃避反自然的死亡,这是自然所主导生发的最严重危害。在霍布斯看来,“幸福是最大的善,但是不存在至高无上的善;而死亡是最大恶,是至高无上的和首要的恶。在没有至善的情况下,死亡作为至恶,是唯一的绝对标准。只有凭借死亡,人才可能有个目标,因为只有凭借死亡,他才可能有一个胁迫性的目标,一个被死神的影子强加给他的目标,也就是逃避死亡的目标”①[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当他谈到作为至恶的死亡时,他心中没有别的,只有被他人手中的暴力所造成的死亡。
由于霍布斯将人的自然欲望归结为虚荣自负,他就别无选择地只能将对暴力造成的死亡恐惧作为唯一的道德原则。因为,如果人的自然愿望是虚荣自负,也就是说,自然人出于天性,力求胜过他的所有同类,使他们都承认他的优势,他便从中体验自我满足。自然人皆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永不落幕的追名逐利竞赛中,他们完全无暇兼顾对首要之善的依赖,即对生命的保存。自然人无法认知其人身需要,而只体验虚幻中的快乐与哀伤。只有当他遭受人身伤害,切身感受到现实世界对他的拒斥时,他才能从这个梦幻世界中幡然醒悟,重返他自身。自然人如此陶醉于名利的虚幻之中,只有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才能让其从梦中惊醒。“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望对他有利的事,躲避邪恶的事,首先躲避最首要的自然邪恶,就是死亡;他凭依一种必然的自然本能躲避死亡,完全就像一块石头向下坠落那么必然。所以,一个人用尽他最大的努力,保存并保卫他的身体及其器官,使之不受死亡和不幸事件的侵害,这既不荒谬,又不应受指责,也不违背真正的理性的命令。可以说,不与真正的理性相悖,就是按照正义和权利去行事的。”②[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二)自然状态中的自然恐惧考察
霍布斯认为:“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平等,以致有时某人的体力虽则显然比另一个人强,或是脑力比另一个人敏捷;但这一切总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大到使这人能要求获得人家不能像他一样要求的任何利益,因为就体力而论,最弱的人运用密谋或者与其他处在同一种危险下的人联合起来,就能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杀死最强的人。”③[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2页。至于智力,因为它往往是经验的化身,等长的时间通常可以使人们在从事同样的事物中获致等量的经验,所以人与人在智力方面着实是相当平等的。
从能力上的平等出发,就会产生欲望满足的平等。因此,当任何个人若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却不能同时享有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或出于自我保全或出于获取利益或为了求得名誉。①自然人不择手段自我保全的权利基础就是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因为自然权利的出场和存在就意味着自然状态,意味着冲突和战争。自然权利坚硬的暴力内核必须经受文明的洗礼。政治就是一场文明行为。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转变,是对自然尤其是人的自然的降低,却是对作为驯化暴力的政治的肯定。自然权利必须经受实质转化,祛除暴力特征,摒弃战争权利,实现规训和服从,成为受到国家保护、获得法律承认的政治权利。”参见王利:《从政治哲学角度看自然权利的力量》,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在他们之间充斥着竞争、猜疑和荣誉。由于欲望的疯狂性、能力的平等性以及资源的有限性,自然人在达到这些欲望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征服抑或摧毁对方。这种自然状态下的绝对平等实际上是“杀戮能力的平等”。②[美]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7页。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最合理的生存之道就是“先下手为强”,亦即“用武力或机诈来控制一切他所能控制的人,直到他看到没有其他力量足以危害他为止”③[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3页。。虚荣自负的人笃信自己比别人更优越,但是这无法得到他人认可,相反还会蒙受轻怠和蔑视。受到轻怠的一方,心存芥蒂,睚眦必报。冲突伊始并不是以死亡为目标,而是以制服敌手为目标。冲突过程中,人身伤害,肉体痛苦,唤起了对丧失生命的恐惧。恐惧减缓了愤怒,使蒙受轻怠的耻辱退却到次要位置,但是复仇的欲念,顷刻间转化为憎恨。怀恨者此时要做的,已经不再是扬眉吐气,而是置敌于死地。经历一番殊死搏斗,他虽得偿所愿地置敌于死地,但这只是须臾之快。因为人人都是他的敌人,他刚杀死第一个敌人,旋即面对来自别人的同样危险,并循环往复。“更为重要的是,在霍布斯的论述中,所强调的一直都是‘相互的恐惧’,即处于‘致命的平等’状况下的个人之间彼此的恐惧。公民社会之中固然‘人对人是上帝’,但一旦公共权威不复存在,即会出现‘人对人是狼’的局面。”④孔新峰:《霍布斯论恐惧:由自然之人走向公民》,载《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1期。因而,“人们相互恐惧的原因,部分在于他们自然的平等,部分在于他们想彼此加害。因此,我们就无法预期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或确保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打量任何一个成人,都看到,人的身体结构是多么的脆弱,若果失去了它,人所有的力量、活力和智慧都会随之而去。而哪怕是一个体质最弱的人,要杀掉比他强壮的人又是多么的容易。无论你对自己的力量有什么样的信心,你都完全无法相信你天生比其他人强”①[英]霍布斯:《论公民》,应星、冯克利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由此可知,在没有公共权力让大家慑服之时,人们便处在每一个人对每一人的战争状态中。自然人始终处于恐惧的包围中,他们恐惧自己的财产被人抢走,恐惧自己的妻儿被人掠去,恐惧自己的生命遭受侵犯。而“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②[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
综上所述,自然人处身于自然状态下的恐惧生活惨不忍睹。因而这种生存状况需要被超脱。“一切情感中最强烈的乃是对死亡的恐惧,更具体地说,是对暴死于他人之手的恐惧;不是自然,而是自然的可怕对头——死亡,提供了最终的指南。然而此种死亡依然是人对之能够有所作为的,亦即是人们可以避开或进行报复的死亡。死亡取代了目的。或者,为了保持霍布斯思想的含混性,我们可以说,对于死于暴力的恐惧最深刻地表达了所有欲求中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亦即最初的、自我保全的欲求。”③[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84—185页。
三、利维坦——对自然状态下自然恐惧之超越
(一)超越自然恐惧——利维坦的诞生之道
自然人为了摆脱这种自然恐惧状况,一方面依靠理性,另一方面依靠激情。“在霍布斯看来,正确的理性不是一种永不出错的能力,而是一种特殊而真实的推理行为,这种推理行为与智慧相去甚远。”④[美]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而推动自然人摆脱恐惧状况的激情首先是“对死亡的恐惧”。“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就其起源而论,是先于理性的,就其作用而论,却是理性的;根据霍布斯的学说,正是这种恐惧,而不是自我保存的理性原则,才是国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全部道德的根源。”⑤[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1页。此时,“自然状态的恐怖驱使充满恐惧的个体聚集到一起;他们的恐惧上升到了极点;这时,一道理性闪光闪现了,于是乎,新的上帝突然间就站在我们面前”①[德]施密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70页。。而这个新的上帝就是利维坦。“在霍布斯那里,自然状态是一种反常处境,其正常化惟有在国家中才能得以实现。国家是一个理性的王国,它把战争状态改变成国家公民间的和平共存。”②[德]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
霍布斯认为利维坦的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按约创造利维坦”;一种方式是“以力取得利维坦”。“按约创造利维坦”最根本的前提是人们的同意。其过程大致是“当一群人确实达成协议,并且每一个人都与每一个其他人订立信约,不论大多数人把代表全体的人格的权利授予任何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集体时,赞成和反对的人每一个人都将以同一方式对这人或这一集体为了在自己之间过和平生活并防御外人的目的所作为的一切行为和裁断授权,就像是自己的行为和裁断一样”③[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3页。。缔结社会契约的每一个人都得承认这人或集体,并放弃他们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集体,但条件是其他人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④对于社会契约问题,卢梭亦有着精到的论述。具体参见于浩、张洪亮:《立法的技艺——基于〈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史考察》,载付子堂主编:《经典中的法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与之相对应,“以力取得利维坦”即利维坦是以武力得来的。“所谓以武力得来就是人们单独地、或许多人一起在多数意见下,由于畏惧死亡或监禁而对握有其生命与自由的个人或议会的一切行为授权。”⑤[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3页。这种方式根源于自然状态中,自然人拥有的力量差异,弱肉强食,由于对强力的恐惧,力量大者因此成为主权者,力量小者不得不沦为臣民。
“按约创造利维坦”虽然最初源于人们的同意,但利维坦的实际统治力却同“以力取得利维坦”一样取决于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可见这两类国家的产生,都是建立在人们出于恐惧而服从的基础之上。国家的起源是出自对死亡的恐惧,也就是出自情感上的对死亡不可避免的,因而是必然的和确定无疑的厌恶。这个恐惧是一种相互的恐惧,是每个人对每个他人作为自己的潜在谋杀者所怀有的恐惧。此外,当我们对比理性与恐惧对于国家建构的作用时,霍布斯认为,即使我们穷尽一切情况,理性的说服力对于国家的建构仍然非常有限,因此人们服从主权者的根本原因不过是对主权者的恐惧。①“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公民社会的主权者或国家?按照霍布斯的思路,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原因:其一是自愿,其二是被迫。从前者说,一个人在公民社会中虽然不可能获得占用和统治一切的自然权利,但他的自我保存和安全的政治权利却能够得到保障,所以出于理性的计算,他会自愿地服从主权者的统治。从后者说,一个人即使不愿意服从主权者的意志或法律,但他根本没有权力同主权者或国家的权力进行对抗,所以只能被迫服从。考虑到理性的说服力对人来说始终非常有限,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认为,一个人服从主权者或国家权力的根本原因仍然不过是对权力本身的崇拜和恐惧。”参见吴增定:《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的“权力之恶”问题》,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3期。
(二)建构主权恐惧——利维坦的维续之道
自然人为了摆脱对暴死的恐惧,维护对生命的保全,在理性和恐惧的双重作用下,相互订立契约,放弃致命的平等与绝对的自由。但是,这个所有人相互间的契约此时仅仅停留在言词的层面上,顶多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契约”。②[德]施密特:《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这种契约仅仅具有言词上的约束,而言词的约束又总是过于软弱无力,根本不足以使人履行契约。霍布斯认为,在人的本性之中,只有两种助力可以加强言词的约束力:一种是对食言所产生的后果的恐惧,另一种是因守约而感到的光荣。而后一种情形在追求自我保全、利益和荣誉的人中极为罕见。因此,可以依靠的就仅剩恐惧了。“我们按照我们的希望许以诺言;我们根据我们的畏惧信守诺言。”③[美]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申彤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如果没有某种强制力量的恐惧心理存在,订约者必定会要么出于野心、贪欲、愤怒等激情违反契约,要么会时刻处于恐惧对方失约的心理阴影下,而这两种情形都必然导致契约的失效。“霍布斯承认,在放弃自然权利、建立国家之后,在国家的绝对权力的严格统治之下,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很愉快的,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这种国家统治之下的不愉快比自然状态下由战争和灾难所导致的悲惨境遇要好一些,人们只能在自然状态和国家统治这两种情况中进行比较和选择。他指出,这一契约之所以有约束力并不是由于其本质,而不过是由于畏惧毁约后所产生的某种有害后果。他实际上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恶,国家因此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产物。”①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从此人们恐惧的对象由自然状态中,任意的且不确定的自然人变成了惟一的且确定的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并没有消除恐惧,因为“霍布斯的利维坦进行统治,只能是通过公民对利维坦的恐惧感,而不是通过具体的政府为达到其目的而依靠或向往的品质。”②[美]曼斯菲尔德:《驯化君主》,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页。通过利维坦的巧设,霍布斯完成了以恐惧替代恐惧的创设——前一个恐惧是以利维坦及其绝对权力为依托的确定性强制;而后一个恐惧则是指自然状态中人们对繁衍生息的不确定性迫害。通过这一替代,人们彻底摆脱了对暴死的恐惧,他们从此仅受主权者的庇佑与管辖。“建立政治社会虽然不能一劳永逸地从根本上解决人生困境,然而自然状态普遍化的全面恐惧毕竟得以消弭,公民放弃了自然之人的恐惧与焦灼,换取一种非常特定化的恐惧——害怕死于主权者的司法之剑底下。”③孔新峰:《霍布斯论恐惧:由自然之人走向公民》,载《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1期。
在《利维坦》最重要部分的结尾,霍布斯重申,“写到这里为止,我已说明了人类的天性,他们由于骄傲和其他激情被迫服从政府;此外又说明了人们的统治者的巨大权力,我把这种统治者比之于利维坦;这比喻是从《约伯记》第四十一章最后两节取来的,上帝在这儿说明了利维坦的巨大力量以后,把他称为骄傲之王。上帝说: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上作王”④[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8—249页。。在利维坦与国家之间作比较所昭示的第三个因素,不是任何强大的力量本身,而是能制服睥睨一切人的那个强大的力量。把国家跟利维坦相类比,是因为只有它才是那些唯我独尊的自然人的国王。从长远看,只有国家才能制服骄傲;而人的自然欲望是骄傲、野心和虚荣自负。除此之外国家确实没有别的理由存在。而国家之所以有如此之威力,全系于其主权恐惧。
令人惊愕的是,虽然霍布斯处心积虑、百般周折地企图通过以主权恐惧替代自然恐惧实现自我保全。但是,许多情形已经表明,身体的恐惧比之于上帝的恐惧,其力量微乎其微。只要人们还信仰不可见的力量,也即只要他们还受到对于实在的真实性质的幻觉的支配,对于不可见的力量的恐惧就比对于暴死的恐惧更加强烈。只有人们得到启蒙,对于暴死的恐惧才会充分发展。这就有待于一种取向上的彻底转变,此种转变只有由世界的祛魅,知识的传播或者大众的启蒙才能带来。只有通过对大众的启蒙,才能实现霍布斯以主权恐惧替代自然恐惧,建构利维坦,实现自我保全的伟大事业。
(初审编辑 颜丽媛)
Hobbes's“Fear”:with Sovereignty Fear Replacing Natural Fear
Zhang Hongliang
*张洪亮,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