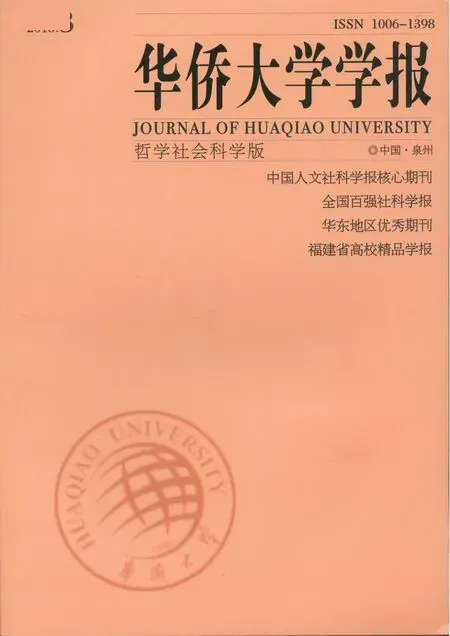论 《小草斋诗话》的诗学观
○郑小雅
(泉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福建泉州362000)
谢肇淛 (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福建长乐人,一生大致与万历朝相当。他是闽籍著名学者,长年宦游在外,与当时许多著名诗人皆有交游,视野比较开阔,于学无所不窥。晚年所著《小草斋诗话》集中表达了他的诗学思想,在明代诗学观点各异的历史背景下,占有一席之地。《小草斋诗话》体依《庄子》,分内、外、杂三篇。内篇是全书精华所在,主要介绍了该书的写作宗旨及作诗的原则、方法等一些诗学基本理论命题。外篇、杂篇主要评点“宋、元以来近人佳句遗事”,其内容不免驳杂,但不乏精当之论。全书共385条目,这些条目长短不一,互不连属,灵活而生动地表达了谢肇淛的诗学观点。
一 诗宗盛唐,推尊情性
放眼明代诗学论争,可谓众声喧哗,热闹异常。究其根本,都是围绕着不同的宗法典范产生的。置身于这样一个分门立户的诗学时代,谢肇淛要构建其诗学观,首先必须确定其诗学的基本立场。
在这一点上,谢肇淛服膺闽中先贤严羽,论诗力主盛唐。谢肇淛说:“严仪卿论诗,勃窣理窟,深得三昧;高廷礼选唐,扬榷精当,境界无遗。”[1]372严羽的《沧浪诗话》以妙悟言诗,其最终理论落脚点在于“以盛唐为法”。在《诗辩》中严羽认为盛唐诸公乃是“大乘正法眼者”,而宋代“正法眼之无传久矣”,此实“诗道之重不幸”,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他以禅为喻,“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2]24-25可以说诗歌发展到盛唐,种种具备,创新的可能性很小了,宋人只能在语言技巧等方面下功夫,于是宋人以理为诗,以文为诗,力图走出一条创作新路。然而宋诗的追求在文学观念上已发生偏差,违背了诗歌抒情的本质规定性及比兴托物的表现法则。对于严羽矫宋诗之弊的良苦用心,谢肇淛引为同道:“严仪卿曰:‘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此言矫宋人之失耳。”[1]358进而谢肇淛明确指出“宋人诗远不及唐”的根本原因:“唐以诗为诗,宋以理学为诗”[1]370,而“作诗,第一对病是道学,何者?酒色放荡,礼法所禁,一也;意象空虚,不踏实地,二也;颠倒议论,非圣非法,三也;议论杳妙,半不可解,四也;触景偶发,非有指譬,五也;宋时道学诸公诗,无一佳者”[1]369。其批评甚至直指苏轼、黄庭坚诸公。至此谢肇淛“宗唐”之基本立场已了然于目。可贵的是谢肇淛这一诗学立场并非对前贤简单的随声附和,而是建立在自身的诗歌审美体验上。他曾经对比唐刘禹锡与宋黄庭坚的同题诗《君山诗》,指出“二诗机轴相似,才气亦敌,而第三语则唐、宋分然,法眼自当辨之,不必言其所以然也”[1]383。刘禹锡的“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巧用比喻,纯然写景,注意诗境的营造,奇思妙喻令人叫绝。而黄庭坚“可惜不当湖水满,银盘堆里看青山”,在化用前人诗句时,荡开君山灵秀之景,着重表达惋惜之意、豁达胸襟,由写景转入议论。由此唐诗之情韵与宋诗之思理判然有别。
正是“宗唐”这一基本诗学立场,使谢肇淛在诗歌选集上唯推高棅的《唐诗品汇》。高棅在《唐诗品汇·凡例》中明确表明自己选诗“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方外异人等为旁流”[3]14。高棅的选诗原则深受严羽“以盛唐为法”的诗学理论影响,形成将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而以盛唐为正宗的思想。尽管谢肇淛对高棅的诗才不无批评,但对他选诗宗唐的标准大加赞赏:“元诗所以一变乎宋者,谢皋羽之功也。明诗所以知宗夫唐者,高廷礼之功也”[1]370,“然其扬扢千古,陶铸百家,一经品题,无不破的。此其精识朗鉴,当是古今第一流法眼也”[1]389。
至此,似乎可以说谢肇淛不过是明代文学复古大军中的一员,其诗学理论与前后七子很是接近。前后七子针对明初以来萎靡不振的文学现状,以复古求革新,重新构筑文学的主情理论,寻求文学发展的新出路。他们立足“格调理论”,谈诗论文高调主张“文必先秦,诗必盛唐”。尽管前后七子内部在理论表述及审美倾向上有所不同,推尊盛唐的复古立场却始终如一。这一点谢肇淛与之相似。但谢肇淛诗宗盛唐,却不完全排斥汉魏、初唐和中晚唐,他认为诗歌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在具体诗体的学习上不必拘于一时一人,而应集思广益,甚至“参之中晚以尽其变”:“五言古,学汉、魏足矣,即降而为陈拾遗、韦苏州,不失淡而远也。七言古,学李、杜足矣,即降而为长吉、飞卿,不失奇而俊也。五言律,学王、孟足矣,即降而为幼公、承吉,不失警而则也。五、七言绝,学太白、少伯足矣,即降而为牧之、国钧,不失婉而逸也。惟七言律,未可专主。必也以摩诘、李颀为正宗,而辅之以钱、刘之警炼,高、岑之悲壮,进之少陵以大其规,参之中、晚以尽其变。如跨骏马,放神鹰,虽极翩跹游扬,而羁绁在手,到底不肯放松一着,然后驰骋上下,无不如意,方是作手。”[1]362这显示了谢肇淛较之前后七子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而且前后七子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由于缺乏创新精神及真情实感,他们由复古走向拟古,陷入了模拟蹈袭之泥潭。在《小草斋诗话》中,谢肇淛肯定七子派“一变为雄声,天下翕然从风而靡,亦小白之霸也”[1]370的移风易作之功,同时他指名道姓批评七子派领袖人物,“献吉继之,几于活剥少陵,高处自不可掩,而效颦之过,亦时令人呕哕”[1]370,“于鳞饶歌、乐府,掇拾汉人唾余,而云‘日新之谓盛德’也,将谁欺乎?”[1]365,“元美取材虽广,择焉不精”[1]370,“干局似之,而终不类也”[1]372。在《小草斋文集》的相关篇章中,谢肇淛对七子派的批评更为严厉:“于鳞天造草昧,立汉赤帜,至今执櫜鞬者什九北面,然其滥觞也,务气格而寡性情,刻音调而乏神理,顿令本来面目无复觅处,则英雄欺人,济南不无惭德焉”[4]657,“唐以后无诗,非诗亡也,操觚之士不得其情性而跳号怒骂,又其下者,刻画四声之似以剽掠时名,于是去之愈远。国朝作者具在,迪功希纵汉魏,北地摹刻少陵,郑吏部超然远诣,犹多质胜,降而中原七子,以夸诩为宗,绘事为工,虽然中兴,实一厄矣”[4]654。这里,谢肇淛批评那些不得“情性”之人的剽掠之习,指出徐祯卿学习汉魏、李梦阳模仿杜甫的实质,对于后七子,更直指为诗坛“一厄”。从以上引文我们可以看出,立足于“情性”,谢肇淛严厉批评复古派过于拘泥汉唐法度格调而遗弃汉唐文学关注现实、情韵兼备的优良传统。这显示了谢肇淛与七子派不同的理论立场。
在《小草斋诗话》中,谢肇淛多处论及“情”在诗歌创作中的本质地位,强调“诗情贵真”[1]359,认为情感是诗歌创作的灵魂。“诗者,人心之感于物而成声者也”,“故感于聚会眺赏、美景良辰,则有喜声;感于羁旅幽愤、边塞杀伐,则有怒声;感于流离丧乱、悼亡吊古,则有哀声;感于名就功成、祝颂燕飨则有乐声。此四者,正声也。其感之也无心,其遇之也不期而至,其发于情而出诸口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1]356他指出无论何种风格的文学作品都是特定环境下人内心情感的真实表达。情的抒发必须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无病呻吟、刻意模仿,只能徒得其形似,而不肖其风神。“近之学杜者,无病而呻吟;学李者,未言而号叫;学六朝者,男作女吻;学汉、魏者,少为老态。学之弥肖,去之愈远,则亦效颦之过,而非古人之罪也。木无风而响,石不击而鸣,人不以为妖乎?”[1]356这些学习者缺乏真情实感一味效颦,结果只能是无病呻吟、扭捏作态,让人作呕。在此,谢肇淛还做了一个比喻,情感的抒发如同自然界事物激于风雨而鸣一样,必须自然而然。在《小草斋文集》的诸多序言中,谢肇淛也一再强调诗歌创作“不离情性”。可以说,重情贵真是谢肇淛评判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在这点上,他的诗学理论又近于晚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二 由学而悟,不废法度
在诗学宗尚立场上,谢肇淛服膺严羽的“以盛唐为法”。那从何入手才能师法盛唐呢?严羽以禅喻诗,提出“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2]10。受其影响,谢肇淛论诗也很注重“悟”。他说:“‘悟’之一字,诚诗家三昧”[1]358,“诗无悟性,即步步依唐人口吻,千似万似,只是做得神秀地位,较之獦獠,尚隔数尘在”[1]359。诗当宗唐,但如无悟性,千似万似的结果只是模仿蹈袭。谢肇淛也赞同诗禅相通,但他认为“人非生知,理难顿悟。” “顿悟不可得矣。即渐悟者,穷精弹神,上下古今,发愤苦思,不寝不食,一旦豁然贯通,一彻百彻,虽渐而亦顿也。譬如盲子,终日合眼,不见天地,一旦开目,从眼前直至天边,一总得见,非今日见一寸,明日见一尺。若不思不学而坐以待悟,终无悟日矣。”[1]359我们知道,“妙悟”是严羽诗学思想的基本原则,其所倡之“悟”要求创作者排除一切世俗情感,使自己的妄情妄见归于寂静,以达到明心见性的“透彻之悟”的境界。这种“悟”是一种顿悟,与“学力”无必然联系。严羽说:“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2]10而在谢肇淛看来,“悟”没有顿悟、渐悟之分,而且要达到豁然贯通的“悟”的境界,必须日积月累、发奋学习思考,不思不学终无悟日。在此,谢肇淛肯定“悟”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指出“悟”的基础——学力。
在《小草斋诗话》中谢肇淛反复强调学力的重要性—— “功非一日,悟非偶然矣”[1]359。他说:“作诗如采花成蜜,酿药为酒,胸中无万卷书,咀嚼酝酿,安能含万象于笔端,罗千古于目前?故未有不明经、不读史、不博古、不通今,而能矢口成章者。”[1]355谢肇淛不仅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学力的重要性,而且点出了学习的内容,要求经、史、古、今都应融会于心。谢肇淛甚至进一步为学诗者制定学习计划:“吾教世之学诗者,先须读五经,不然,无本原也;次须读《二十一史》,不然,不知古今治乱之略也;次须读诸子百家,不然,无异闻异见也。三者皆于诗无预,而无三者必不能为诗。譬之种秫田,汲泉水,而后可以谋及曲糵也。”[1]360不能不承认谢肇淛的观点颇有见识,经、史、子虽于诗“无预”,却是作诗者必不可少的学术修养,正如有粮有泉才能酿酒一样,有了丰厚的学力积累,创作时才能“化而出之,使人共知,又使人不知”[1]358。在经、史、子中,谢肇淛特别重视《诗经》。《小草斋诗话》多次以“三百篇”为正面例子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诗经》中不同的字法、句法、章法乃至语言风格、表现手法,指出“熟读神会,久当自见。似疏极密,似易极难,断非经圣人之手不至此,此作诗之大门户也”[1]357。将“熟读神会”“三百篇”视为“作诗之大门户”,此一见解深契《诗经》的文学史地位,确实难能可贵。
那么,是不是学富才高就一定能悟出好诗呢?当然不是。如果积累学力的过程中不懂得融会贯通,其结果只能是“才弥高者,去之弥远”,“学弥富者,用之弥滞”。“盖高于才者,为才所使,往往骛外而枵中,如李广行师,不设刁斗,可袭也。富于学者,为学所累,往往跋前而疐后,如符坚大举,士卒嚣乱,易败也。故善用才者如驭骏马,虽越山蓦涧,而衔辔不失。善用学者如制名香,虽料剂纷杂,而气吐空清。”[1]359谢肇淛认为由学入悟有一个关键条件就是“善用才”、“善用学”。什么才是“善用学”呢?对此,谢肇淛没有做出明确解答,但联系《小草斋诗话》上下文我们可以找到答案:“缘彀率以求中,循绳墨而入巧,深心积渐,当自得之。”[1]356换言之,就是不废法度。
谢肇淛生活的万历年间,公安派渐起,他们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5]211。虽然公安派一扫七子派模拟涂泽之病,却过分强调任情而发、信口而谈,不屑于学,不师于法,其诗风不免流于浅俗粗鄙。对此,谢肇淛一言点中要害:“今人藉口于悟,动举古人法度而屑越之。不知诗犹学也,圣人生知,亦须好古敏求,问礼问官,步步循规矩,况智不逮古人,而欲以意见独创,并废绳墨,此必无此事也。昔人谓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今则未见鱼兔而尽弃筌蹄矣,尚何得之冀乎?”[1]358他沿用庄子的筌蹄之喻,批评“今人”尽弃诗法而妄谈作诗的错误做法,指出“诗以法度为主,入门不差,此是第一义”[1]358。为此,在《小草斋诗话》中谢肇淛不厌其烦地罗列诗中诸体 (如乐府、五古、歌行、七古、七律、绝句)的师法对象、创作要求、创作难点,提出许多诗歌创作的一般性法则。为了便于初学者入门,谢肇淛还总结出诗法的几个主要方面:“故学为诗者,首之宗旨当审也,途辙一差,则终身难挽也。次之典则当存也,体裁不辨,则尚论无由也。次之搜材当广也,见闻寡陋,则取舍无择也。次之律度当严也,步趋无法,则仓促易败也。至于神情高远,兴趣幽微,似离而合,似易而难,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也。”[1]356这里涵盖了宗旨、体裁、选材、律度、情境五个方面。前四个方面有一般规则可依,最后一方面则需作者在长期的揣摩中意会体悟。当然诗法是丰富精深的,就像轮扁斫轮一样难以尽言,尤其是“气、骨、神、情、理、趣、色、调”等命题,更是难以入手,需要学习者“深心积渐”。但是“苟擅其一,足以名家,而胶于一,未有不病者”[1]358,法度很重要,擅长其一就可以成为名家,但胶于法度不知变通也是万万不可的,将带来诗道大病。正如他批评宋人“抵死学杜”,“正坐此病”。总的来说,谢肇淛重视“法度”,又主张不拘泥于法度,此一观点相比于七子派过分强调继承前人的法度格调而走向模仿抄袭的做法,显得更加通脱客观。
三 诗境贵虚,婉逸为上
谢肇淛关于法度的辩证认识显示了他通脱高明的理论眼光。在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作诗应该注意五个方面:宗旨、体裁、选材、律度、情境。这五个方面分为两个层次,前四个方面属于技法层次,有法可依且熟能生巧。第五个方面是更高层次的诗境追求:“神情高远,兴趣幽微,似离而合,似易而难,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也。”[1]356对此,谢肇淛又提出一个命题——诗境贵虚。
他说:“‘夜半钟声到客船’,钟似太早矣。‘惊涛溅佛身’,寺似太低矣。‘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阴晴似太速矣。‘马汗冻成霜’,寒燠似相背矣。然于佳句毫无损也。诗家三昧,政在此中见解。”[1]363从生活真实的角度审视这些佳句,其破绽显而易见,但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能等同,这些句子都是诗人借助想象突破生活逻辑进而造意造境的佳句,如果过于求实,纠结于这些描写的真伪,只会破坏诗歌的情思意趣。正如“摘雪中蕉以病摩诘之画,摘点画之讹以病右军之书,论非不确,如画法、书法不在是何!”[1]363艺术创作中虚能胜实,这才是“诗家三昧”!
对诗歌艺术而言,虚实关系的处理颇为讲究。谢肇淛通过品评唐诗提出“虚实相半”说。“《琵琶》、《长恨》,虚实相半,犹近本色。”[1]359所谓“虚实相半”,并不是说虚与实各半,而是有虚有实,虚实结合,符合情感表达的需要。对此,谢肇淛《五杂组》中有一段话可作为佐证:“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6]323这里明确指出判断作品是否成功,关键看其虚实结合是否符合“情景造极”这一尺度,即是否与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或人物形象相适应,实现艺术真实的创作目标。且不管谢肇淛这一提法是否精当,最起码他在理论上反复强调了虚境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谢肇淛所追求的虚境,从审美特点上说,要求诗歌具有含蓄清远之美,“神情高远,兴趣幽微,似离而合,似易而难”。在《重与李本宁论诗书》一文中他以“风韵婉逸”一词简而概之。如他评五言古诗:“须有澹然之色,苍然之音,象外之意,言外之旨。虽不尽袭汉魏语法,亦不当作齐梁以后色相。”[1]361又如论咏物诗:“咏物一体,而赋、比、兴兼焉。既欲曲尽体物之妙,而又有意外之象,象外之语,浓淡离即,各合其宜。”[1]372对于这样一种似离而合的诗歌之美,谢肇淛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诗如美人,风神体态,骨肉色泽,件件匀称。铅华妆饰,亦岂尽卸不御?至于一种绰约流转,天然生机,有传神人所不能到者。今人赞画像,动曰形神酷肖,只少一口气耳。不知政这一口气,千难万难。”[1]359他说诗歌之美如同女人之美,即使骨肉色泽件件匀称,如缺少那种“绰约流转,天然生机”的神气,这美人就不具有活泼泼的生命力。可这样一口“绰约流转,天然生机”之“气”却又“千难万难”,“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也”。
基于这样的诗境追求,在《小草斋诗话》中谢肇淛论唐诗首推王维:“王右丞诗,律、选、歌行、绝句,种种臻妙,《离骚》、表、启,罔不擅场。至于音律、图绘,皆独步一时。尤精禅理。晚居辋川,穷极山川、园林之乐,唐三百年诗人仅见此耳。”[1]367我们知道王维的山水诗善于捕捉那种虚空不实、寻常又奇妙的自然之景,巧妙融入自身的生命感悟,创造出恬静清远的诗歌意境。寻常的风景、寻常的人物一经王维简笔勾勒,便具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远意味,这深契谢肇淛之审美意趣。而对于唐诗双杰李、杜,谢肇淛常有微词:“太白如神童,时有累句者,为才所使也。少陵如老吏,时无逸句者,为律所缚也”[1]367,“太白选诗所以不及子昂者,稍涉豪放耳。如《赠何七判官》、 《月下独酌》等篇,语虽奇崛,终非本色。子美往往入别调”[1]367,“少陵以史为诗,已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声,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1]370。谢肇淛视李白之“豪放奇崛”与杜甫之“以史为诗”皆为“非本色”,其原因就在于他欣赏的是“风韵婉逸”的诗歌意境。可以说“谢肇淛‘诗境贵虚’的提出,上承严羽‘盛唐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论,而下启清初王士祯的神韵说,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7]373。
四 推扬闽派,复振风雅
仔细阅读《小草斋诗话》,我们会发现书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品评闽派诗人及其创作。谢肇淛本人就是明后期闽中诗坛的领军人物,虽长年宦游在外,但他有很强的桑梓情怀。他不仅热情为福建地区诗人诗集作序,在整理乡邦前贤遗作、勉励闽派后学等方面也出力甚多,因此他对闽地诗人诗作颇为熟悉。谢肇淛有明确的复振风雅、推扬闽派的意识,其好友马欻在《小草斋诗话序》中说:“余友谢在杭《诗话》一帙,分内、外、杂三篇,大都独抒心得,发未所发,而归宗于盛唐,以扶翼正始之音余……闽三山诗自林子羽高第二玄称吾家诗后,作者不乏,虽瑕瑜相半,要皆共得唐宗。万历之季,渐入恶道。语以唐音,则欠伸鱼聣;语以袁、钟新调,则拊髀雀跃。在杭是编,功固不浅。”[1]353由此可知谢肇淛写作此诗话目的在于“归宗于盛唐”,使闽派风雅传统得以延续下去。因此《小草斋诗话》用了大量篇幅介绍闽诗的发展,品评闽派诗人诗作,为振兴闽派不遗余力。这也使《小草斋诗话》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域文学的意义。
谢肇淛论闽诗上宗林鸿、高棅,中尚郑善夫,近推徐熥、徐 和曹学佺。他说:“闽诗莫盛于国初,林鸿、王恭,上国武库、天府琅球,常与高启鼎足而立,馀子琐琐,勿论也。高廷礼才虽不逮,然其扬扢千古,陶铸百家,一经品题,无不破的。此其精识朗鉴,当是古今第一流法眼也。他如王偁、周玄、郑定、王褒之徒,出其剩语,亦足先鸣。虽其声华未能宏播,而此道规矩准绳,独能心传口授,不至背驰,即诸家之烨然者,不敌也。”[1]389我们知道,明初在福州一带以林鸿为中心的数位闽籍诗人相互唱和,理论上尊宗盛唐,一时之间才俊辈出,彬彬风雅,闽诗坛呈现一派盛况,后人称之为“闽中十子”。在此,谢肇淛极力肯定他们的历史地位,将林鸿、王恭视为与明代著名诗人高启鼎足的三家,盛赞高棅选诗之精鉴,对于其余诸子在诗歌创作上宗唐的“规矩准绳”也力挺为“诸家之烨然者不敌”。谢肇淛还作过《读闽诗三首》,分论林鸿、高棅、郑善夫,高度评价他们在变革诗风、复振风雅方面的历史功绩。郑善夫诗主学杜,气格悲壮,在弘治、正德年间确实别开生面,谢肇淛评之为“一洗铅华,力追大雅,盛矣”。在《周所谐诗序》中谢肇淛还将郑善夫与李梦阳、徐祯卿并列,说“国朝作者具在,迪功希纵汉魏,北地摹刻少陵,郑吏部超然远诣,犹多质胜”[4]654,批评徐祯卿、李梦阳流于摹刻的同时肯定郑善夫的“超然远诣”,其褒扬之情溢于言表。除此之外,谢肇淛盛赞曹学佺诗作自有盛唐风韵:“曹能始诗以浅淡情至为工,不甚学盛唐,然其《送西安太守》诗云:‘长安西望路漫漫,泰华峰阴日色寒。长乐故宫秦荤绝,未央前殿汉钟残。月明渭水浮三辅,花满骊山绣七盘。京兆风流谁不羡,时从闺阁画眉看。’大历以来,罕见斯语。”[1]391
在谢肇淛看来,嘉、隆以来闽中诗坛更出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嘉、隆以来,则有郭郡丞文涓、林明府凤仪、袁太守表,皆余先辈。陈茂才椿、赵别驾世显、林孝廉春元、邓观察原岳、陈山人仲溱、徐孝廉熥、熥弟 、陈茂才价夫、孝廉荐夫、曹参知学佺、袁茂才敬烈、林茂才光宇、陈茂才鸣鹤、王山人毓德、马茂长欻、陈山人宏己、郑山人琰,皆先后为余友,皆有集行世。其中豪宕不羁,挥斥八极,则凤仪为之冠;秀润细密,步趋不失,则袁、赵名其家;才情宏博,多多益善,则徐氏兄弟擅其场;其他诸子,各成一家,瑕瑜不掩。然皆禘汉宗唐,间出中、晚,彬彬皆正始之音也。南方精华,尽于是矣。”[1]390这里一口气列出20人,指出他们风格不一但各成一家,有的“豪宕不羁,挥斥八极”,有的“秀润细密,步趋不失”,有的“才情宏博,多多益善”,大有南方英才尽在闽地的自豪之情!其下文更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品评诸多闽地诗人。
值得赞赏的是,在推扬闽诗的同时谢肇淛并没有一味谀美。他将文坛中“毁誉狥乎爱憎,媺刺视其同异;意之所私,款段诧谓逸足;心之所忮,结绿訾其多瑕”[1]355的不良批评风气视为“一厄”,所以对于闽诗派他能认真审视,既肯定闽诗派在理论宗旨上的正确立场,也批评其创作实践中的某些不足,如他一方面盛赞高棅选诗的精鉴眼光,另一方面批评高棅“今试以数十百篇之诗,隐其姓名,以示学者……辨尽诸家,剖析毫芒,方是作者”的说法是“英雄大言欺人尔”。[1]366谢肇淛认为“鸿运升降,虽天不能齐;声气变趋,虽圣不能挽。醇醨巧拙,得世道之关;浓淡偏全,定人品之概,足矣”[1]366。诗歌创作不仅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同一人的作品也时有高下之分,“以纸上陈言,邃欲定三百年之人物”实在不切实际。即使对他非常崇敬的闽诗中坚人物郑善夫,谢肇淛也毫不客气地批评:“然掊击百家,独宗少陵,呻吟枯寂之语多,而风人比兴之谊绝。”[1]390指出郑善夫的诗歌在学杜上存在思想情感不深、艺术手法不精的不足。评价好友徐熥也是褒贬有度:“才情声调,足伯仲高季迪,所微憾者,古体稍不及耳。”[1]391总的来说,谢肇淛对闽诗人的品评都比较公允,他“看到闽中诗派在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弊端,甚至加以批评,目的不是为了彻底去改变这一诗派,不是为了改变诗派宗唐的宗旨,而是为了改善它,从而促进这一诗派能向比较健康的方向发展”[7]326。
综上所述,谢肇淛的《小草斋诗话》有着丰富而独到的诗学见解。立足于对明代文学创作困境的深入思考,谢肇淛的诗学理论于晚明复古派和性灵派皆有所涉,又不尽相同,力图合两派之所长,显示出更为融通开阔的理论特点。他诗宗盛唐,推尊性情,追求婉逸清远的诗境,创作上主张不废法度,由学入悟。其理论最终目标乃是进一步明确闽诗派风雅传统,推动闽诗往健康方向发展。这也决定了《小草斋诗话》在福建文学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
[1] [明]谢肇淛.小草斋诗话[M]∥张健,辑校.珍本明诗话五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 [明]高棅,编选.唐诗品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 [明]谢肇淛.小草斋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5] [明]袁宏道.序小修诗 [M]∥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明]谢肇淛.五杂组[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7]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