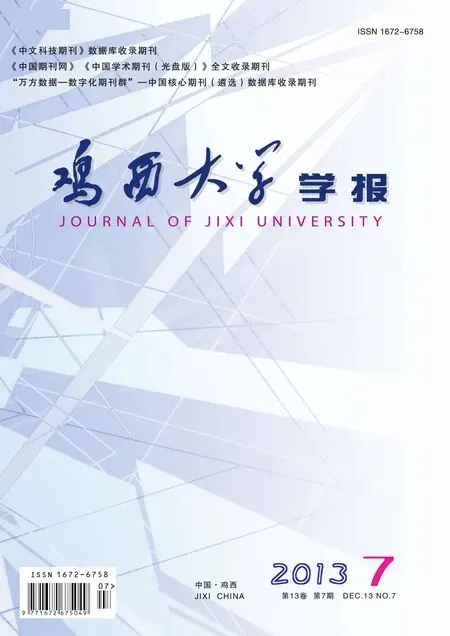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士人妆饰时尚现象之探讨
吕晓洁
(安徽大学,安徽合肥 230039)
时尚是社会的产物。时尚的发展,离不开事物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时尚并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魏晋南北朝时代,男子傅粉施朱,剃面熏香成为名士们的时尚,追求病态的女性美的时尚之风大兴,一个名士只有当他美得如同一个貌美的女子时才会被人们称赞。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中提到魏晋时代的人“沉醉于人物的容貌、器识、肉体和精神的美”,崇尚“人格的唯美主义”。魏晋南北朝名士为我们展示了魏晋人的“美姿容”与“好神情”,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对于仪表美的赞赏与迷恋。社会混乱、政权更替频繁,此时的名士们意欲进取,又畏惧宦海浮沉,只有寻求自我解脱。他们除了饮酒、服药、谈玄,更在妆容、服饰上寻求宣泄。男子敷粉施朱、披发、“丫髻”、“褒衣薄带”等时尚大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妆容、服饰时尚概述
1.妆容时尚。
最古老的妆粉有两种成分,一种是以米粉研碎制成,古“粉”字从米从分;另一种妆粉是将白铅化成糊状的面脂,俗称“胡粉”。因为它是化铅而成的,所以又叫“铅华”,也有称“铅粉”、“粉锡”的,两种粉都是用来敷面,使皮肤白皙。妆粉本为女人饰物,男子只有皇帝身边的诽优弄臣才傅粉施朱。《汉书·佞幸传》言“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鵔鸃,贝带,傅脂粉。”东汉末期,士人也有傅粉者,《后汉书·李固传》言其“胡粉饰帽,搔头弄姿”;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士比汉朝士人更爱傅粉,傅粉之风已普遍流行于上层士族之间,成为一种时尚。
皮肤的颜色是最直观映入人们眼帘的部分。魏晋时对男性的审美是以白为美。皮肤白皙的代表,首推何晏。何晏被称为“粉侯”。“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何晏皮肤异常白皙,魏文帝曹丕怀疑他傅粉,化过妆,就想验证一下。“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篇》)可见当时傅粉已成为名士的时尚,不然魏文帝曹丕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不仅何晏,曹植也是引领傅粉潮流的时尚达人。《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中记载:“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白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诽优小说数千言讫”。这种傅粉风气一直延续到齐梁,而且愈演愈烈。《颜氏家训·勉学篇》云:“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伺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展,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男子傅粉施朱成为魏晋南北朝社会的时尚,男子通过傅粉将自己的皮肤变得白皙,容颜变得美丽,如同一个美貌的女人一般,这是在崇拜病态女性美的社会风气下形成的。
在魏晋南北朝社会,名士若仅仅美姿容,还不足以引领时尚。名士们要妙神韵,风度翩翩,情理并茂才能在名士中得到青睐。“时人目王佑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从外在看,他们外表的美几乎可以与女子相提并称,而又有着由内散发出来的洒脱飘逸的气质,两者完美地结合,使魏晋时的男子出现了有别于任何其他历史时期都难以呈现的风韵气度。这里“所谓“神情”“雅韵”“风神”“神采”“神仪”“神明”“神情”等等,就是魏晋南北朝士人最赏爱、最心仪的美。
2.服饰时尚。
魏晋南北朝以前,统治者对于服饰有着严格的要求。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级穿着不同的服饰。服饰的颜色、样式、上下衣的长度、宽窄都有严格的要求。中国古代的服饰制度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制度,体现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传统思想。
汉末以来,各种有违常态、有悖礼制的奇服出现。正如葛洪《抱朴子·讥惑篇》所记:“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诀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勿,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辈贵大眉,远方皆半领也。”尽管服饰款型多种多样,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选择仍有一个基本方向,即服饰朝着逐渐宽大、松散,趋于自然、舒适。所谓“褒衣博带”,乃是魏晋风度在服饰方面最合适的注脚。“褒衣博带”最早见于文字,是在《淮南子· 氾论训》:“古者有鍪而綣领,以王天下者矣,……岂必褒衣博带,句襟委章甫哉?”《汉书·隽不疑传》:“不疑冠进贤冠,带櫑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
服饰在魏晋时越来越宽博,并且成为一种时尚。《晋书·五行志》记载:“晋衰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放,舆合成俗”这种风气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时期,刘宋时,周朗上书宋孝武帝,即称当时“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宋书·周朗传))《颜氏家训·涉务篇》也载:“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温。”《世说新语·企羡篇》:“王恭乘高舆,披鹤氅裘。”《南史·张融传》:“王敬见融革带宽,殆将至 ,谓曰:革带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带何为?’”正因为这种服饰宽松随意,更能显示出名士们潇洒飘逸的精神气质,因而很受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喜爱。一时之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名士,都以宽衫大袖为尚,“褒衣博带”成为魏晋南北朝名士流行的时尚服饰。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妆容、服饰时尚原因探析
时尚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一种行为方式,是社会中的人的一种认知和表意方式,因而它必然反映出一定社会阶级的心态,从而成为一个时期内人们社会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时尚的流行作为社会产物,它的全过程以及每个阶段效果如何,也就直接取决于社会生活。那么,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期会有这些时尚现象出现呢?这其中必然有着或隐或显的原因,本文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1.生产方式的转变。
汉末大动乱,政权更替频繁,统治了中国四百年的汉朝大帝国土崩瓦解,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央集权的大汉天子失去了神圣的权威,世家大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筑起坞垒堡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组织武装,进行生产。广大劳动人民在战乱的社会中,失去了土地家园,为了生存,纷纷投靠世家大族,成为他们的佃客。在此基础上,世家大族的庄园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劳动人民依附于世家大族,重新与土地相结合,有利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些庄园成了一个个自己自足的小社会,世家大族经济上自己自足,物质上所需要的粮食、日用品都可以自己供给。《颜氏家训·治家篇》记载:“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庄园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世家大族提高了富裕的物质享受。他们不必再为了仕途而苦读经书,他们不必为物质生活而担心。世家大族在生活上和思想上都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他们有大量的自由的时间关注自己的外表、服饰。这些活动不再是为了政治上的目的,而变成了纯粹的审美活动。因为门阀世族拥有优越的地位,即使在不参加政权的情况下,也有保证他们生存的经济、军事实力,并不需要依赖已经当权或未当权的政治势力,他们可以超然于现实政治之上,转而追求肉体的欢愉、感官的快适、容貌的秀美、服饰的光鲜,这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2.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宗白华曾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魏晋南北朝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东汉末年,政局更替频繁,社会处于无秩序的混乱状态,上到世家大族,下到平民百姓,都无法回避战乱带来的不自然死亡。人们对生命和前途感到悲哀与无望。士人对儒家思想的反动已经逐渐成熟,对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说产生怀疑,被人们遗忘已久的道家思想又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再次被人们拾起。道家思想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它只是提出了问题,却没能解决这个带给人们无边苦痛的问题。现实生活中,人们即便了解了道家对于生死问题的观点,也很难达到把“生”当做赘物,将“死”当做解脱这样高的境界。所以老庄的生死观,和人们的现实感受联系起来,给人们带来的只是更多的痛苦。佛教的盛行是在东晋以后,是无法给此时的士人精神带来慰藉的。人们失去了对长寿的企盼,所以对此刻拥有的生命就更觉得宝贵。士人们放弃对生命长度的追求,转而去增加生命的密度。《列子》一书,其中大半是谈论生死问题的。《杨朱篇》记载:“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尽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忧惧,又几居其半矣。”从汉末至魏晋,士人既产生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痛苦的感伤与思索,但又并未完全堕入悲观主义,仍然有着对人生的执着和爱恋。这种为了“生之难遇而死之易及”,于是尽量地把握住现在的这一刻,尽量去享受人生的态度,这种重视自己姿容、服饰的时尚现象,其背景正是时光的飘忽和人生的无常。对死亡的极端恐惧和无奈,使得魏晋南北朝士人对于生命本质意义进行重新思考。人们不再着意于外在的事功,而是执着于对生命的强烈欲求和留恋。人本身被重新重视,人的容颜、服饰、举止都成为被品评的对象。因而,魏晋南北朝士人对妆容、服饰的狂热追求,相对于儒家礼法下个体完全淹没在群体中,是人的精神觉醒的表现。
3.玄学的兴起。
汉末,自然灾害频繁迭起,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皇帝由神圣的天子沦为各个军阀手中的玩物。儒家礼法遭到轻蔑,传统经学被摒弃。在汉朝统治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道家思想冲破儒学、阴阳五行、谶纬等重重帷帐,重新进入士人视野。随着汉献帝时期天人感应的神学系统的全面崩溃,魏晋玄学在综合儒道的基础上酝酿而生。
魏晋玄学是魏晋士人面对社会动乱时的心灵支柱,魏晋玄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心态、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玄学是在继承老庄道家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道家追求的“真人”、“至人”、“神人”无不具有美好的容颜,飘逸的气韵。老庄的审美观是以自然为美,人的美是一种将身体之美与人格之美相统一并融入个体生命意识的美,是一种实现了生命无限自由的广度和深度的美。《庄子·逍遥游》塑造的“藐姑射之山神人”是魏晋士人的审美理想。“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种审美理念影响到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时尚生活。他们纷纷对这种女性化神人形象进行模仿和追求,并以此当做品评男性美的标准。魏晋南北朝士人崇尚皮肤白皙,容貌秀丽、飘逸自然的风度均与此直接相关。如《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或以方谢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马曰:“诸君莫轻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弹琵琶,故自有天际真人想。”“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世说新语·企羡篇》)
魏晋南北朝士人在玄学的影响下追求生命个体的自由、任诞,将自我的情感、个性以一种真实自然的方式展现出来。魏晋南北朝士人崇尚真率的为人风格。真,即诚实不欺骗;率,即直率无隐藏。不造假,不做作,一切发于自然。惟其真率,故能任性而动,超越世俗。魏晋南北朝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让生命回归自然,让人的自然之本性、生命之情感、生理之需要从伦理道德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以一种不经事务的超然态度对待现实,以期达到超凡脱俗、任诞放达的精神境界。而当他们对现实中的黑暗腐朽接触越多,认识随之越发深刻,他们就越发任诞放达,并毫无保留地表现在独特的言行举止、妆容服饰上。当这种审美行为被社会上众多人所接受并模仿时,就形成了当时时尚妆容和时尚服饰。服饰上,人们求新求异,纯粹从个人审美及喜好出发,想怎么穿就怎么穿,想怎么修饰自己的容颜就怎么修饰,不再受传统儒家礼教的束缚。男子的傅粉施朱、褒衣博带都受到魏晋玄学的影响。
4.选拔标准的转变:由德、才变成审美。
汉末魏晋时期士人仪容的品评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重视礼仪的传统。儒家强调人们在社交中要注重仪容,使外在表现的仪容和人的身份地位相符,体现人的尊严、教养,仪容问题因而也成为当时人物评论的重要方面。《论语·述而》中说:“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儒家的这种评论虽然以“礼”和仁义道德为根本原则,但因其直接和人的容貌、举止、风度等相关,因而带有明显的审美性质,对后来魏晋时期人物品藻重视姿容有一定影响。
但儒家对仪容的重视又与魏晋时期有很大的差别。先秦儒家和汉儒将“仁义礼智信”奉为圭臬,仁义道德被视为最重要的品质。人的才能、智慧、姿容都必须让位于仁义道德,只有符合仁义道德标准才有被选拔成为官吏的可能。《论语·泰伯》便记录了这一现实,“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备其余不足观。
曹魏政权时期,曹操的求贤令和曹丕颁布的“九品中正制”将选拔官吏的标准由“德”转向“才”。曹操对才的强调,同时也是对人的个性的肯定。但新生的曹魏政权尚不稳固,为了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人才优劣的评价标准实际上是被世家大族所掌控,社会上随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况。于是,以政治需求为目的对士人德行、才能的评论便转变成了对士人容貌、举止风度的品评。人物品评的政治性色彩大幅度减弱,转而发展为审美的评判,在很多情况下对士人的外貌风度、举止才情进行欣赏、赞叹。因审美与人的形体、外貌、服饰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人物之形象美、姿容美、服饰美等诸多因素获得了更为突出的意义。随着门阀士族力量的不断壮大,士族和庶族之间的区分越来越严格,士族大家把自己看作社会中的精华,十分注重自己的风度与教养。梁代袁昂的《古今书评》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爽爽有一种风气。”
三 结论
时尚的流行是人类文化生活的认知和表意形式,因此时尚必然会反映出社会特定阶层的心态。时尚的形成与流行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有着联系。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导致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产生巨大的变动,同时孕育了任何一个朝代所不能呈现的自由状态。从当时男子的妆容、服饰时尚现象中可以了解到名士们的精神追求。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傅粉施朱与当时重视容止之美相符,是一种与先秦两汉儒家重善轻美的道德审美相悖的时尚,是对传统礼制的挑战。名士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去观察自然、社会,重视人自身的价值。褒衣博带的服饰的流行时尚是老庄、玄学尚自然通脱思想的体现。时尚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风貌。魏晋南北朝男子妆饰时尚展示了那个时代男子的特点,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去了解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现实情况。
[1]汪婷婷.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服饰研究[D].湖南工业大学,2009.
[2]王麒越.“魏晋风度”下的男性美容现象探讨[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2).
[3]杨瑞璟.中古社会的容止观与士人服石之风[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2).
[4]李芽.中国历代妆饰[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5]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8]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9]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