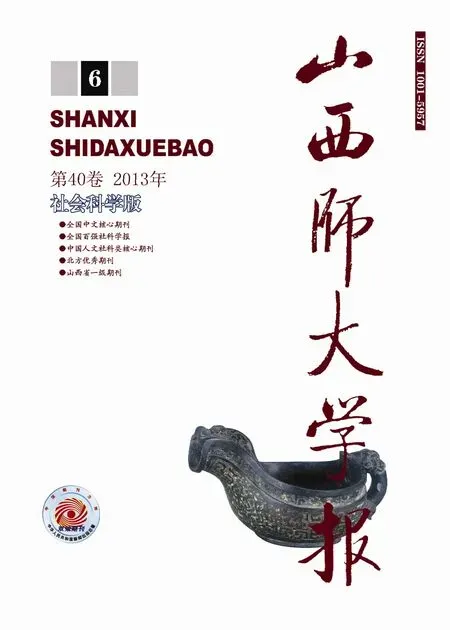鲁迅与茅盾对“五四”新文化的不同理解
聂国心
(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广州510006)
鲁迅与茅盾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的重量级人物,他们的名字是与“五四”新文化铭刻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化哺育、造就了他们,他们也为“五四”新文化增添了光彩。后来,他们又都接受了阶级论,先后走进了左翼文学的营垒。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现实,他们对“五四”新文化的理解产生了分歧。
一
鲁迅看“五四”新文化,侧重的是“文化革命”。他虽然对它也有一些批评,如目标不够明确,缺乏持久有力的抗争等,但对其核心价值观,如对“人”的理解与尊重,对旧恶势力的批判意识与反抗精神等,不但给以充分的肯定,而且认为在新的形势下更应该发扬光大。也就是说,鲁迅是把“五四”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左翼文学的精神追求看作是同一性质的,认为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面对的现实环境不同,所采取的斗争方式不一样而已。
1933年初鲁迅在写给上海《涛声》杂志的一封信中,就周木斋责备北京大学生在日军进攻面前纷纷逃难,进而感慨“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已经销尽一事发表评论。鲁迅不能同意周木斋所说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的观点,而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鲁迅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北伐成功”以后的“党国”社会环境已经与“五四”时代完全不同。“五四”时代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段祺瑞执政府向请愿的学生开枪,但人们“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1]472。现在如果学生还这样做,那就会被人诬陷为“为‘反动派’所利用”,被枪杀的学生也都是“自行失足落水”了,“连追悼会也不开”[1]473。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十来天之前”,北京就“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1]475第二,大学生既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也没有任何武器。他们在与中国“兵警”的斗争中都属于毫无抵抗能力的被镇压者,现在日军压境,“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1]473第三,要求赤手空拳的大学生慷慨赴难,除徒增流血牺牲,至多成就一本“烈士传”外,“于大局依然无补”[1]474。
鲁迅用嬉笑怒骂的文字,借为北京大学生“逃难”辩护的事由,一方面展示出国民党的统治比“五四”时代更为黑暗,人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他珍惜生命维护人权的苦心,在一个连人的基本生存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代,“逃难”是可以理解的,无谓的牺牲完全没有必要。同时,鲁迅又巧妙地借用国民党政府认为“五四式是不对了”,要求学生“进研究室”[1]473等做法来反衬出“五四式”的正确,表达他对“五四”新文化的肯定。其实,鲁迅信中犀利的批判性笔锋本身就是一种“五四式”的反抗精神。
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鲁迅又从梳理小品文的兴衰历史入手,不但充分肯定“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认为这种传统对于现今以至于将来的文学都有学习和借鉴的作用。
鲁迅认为,中国的散文小品几经起伏,“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其原因最根本的就在于它具有源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挣扎和战斗”的精神。它的“幽默和雍容”,“漂亮和缜密”,也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2]576因为在鲁迅看来,“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它当然“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2]576—577
但令鲁迅感到忧心的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鲁迅说:“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2]576于是,鲁迅感叹道:“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2]576从鲁迅对“小品文”兴衰历史的描述来看,他所谓的“小品文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的危机。他呼唤人们重视“五四”时期的散文小品,也是在呼唤一种“五四新文化”的精神。
在《〈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中,鲁迅更是直接将“五四”“文学革命者”与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者”并列在一起来谈。鲁迅是这么说的:“这新的小说的生存,却总在不断的战斗中。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迫压和陷害。大约十年之后,阶级意识觉醒了起来,前进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学者,而迫害也更加厉害,禁止出版,烧掉书籍,杀戮作家,有许多青年,竟至于在黑暗中,将生命殉了他的工作了。”[3]20不少学者在引用这段话时,只注意到鲁迅说的“大约十年之后”作家的“觉醒”与“前进”,多少忽略了鲁迅更为强调的两者所共同具有的遭受压迫的命运以及奋起反抗的精神。其实,只要联系鲁迅在此前后的思想状况仔细阅读这段话,就不难明白鲁迅的侧重点所在。
二
茅盾本来也是从文化革命的角度维护“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他还称“五四”为“划时代”的运动,情不自禁地赞美“那时候的初觉醒的人心的热力!”[4]197认为“五四”与“五卅”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但却有着“精神上”的传承关系。甚至连“活跃于‘五卅’前后的人物”,也是“‘五四’产儿中的最勇敢的几个”。他原本的结论是:“没有了‘五四’,未必会有‘五卅’罢。……历史是这样命定了的!”[4]198
但在加入“左联”后,茅盾对“五四”新文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典型的是他在1931年3月发表的《“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再从文化革命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不再强调“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现实意义,而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把“五四”新文化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它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不应该忽略的”,但不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因为随着“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5]231。于是,他对“五四”新文化的结论性意见便变成:“‘五四’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组织民众意识的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所以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时仍须注力于铲除封建势力,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历史上曾尽了革命作用的思潮或运动,到后来成为反革命的,比比皆是。‘五四’亦复如此。”[5]247
显然,茅盾在这篇文章中用以分析“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观,是以阶级斗争为轴心,认为社会历史是遵循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这么一种“线性发展”的规律的。虽然他也承认“社会的进化,决不是机械的。虽则历史已经滑进了新阶级,然而旧时代的渣滓总还有若干沉淀在新社会的基层”[5]247。但他所要否定的,不是“五四”新文化未能彻底清除的封建思想和势力,而是“五四”新文化本身。他把“五四”新文化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称“‘五四’的一切思想及其口号都成了时代落伍”[5]244,呼吁人们“扫除这些残存的‘五四’”[5]248。
这种历史观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一脉相承。当年创造社太阳社就是以这种历史观为理论武器来否定“五四”新文化,并与鲁迅、茅盾展开激烈论战的。到后来茅盾自己也拿起了这个武器。这是他自觉改造自我,力图证明自己不落伍的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与茅盾在创作中常常表现出矛盾的状况相类似,茅盾运用这个理论武器来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也同样存在着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阶级性质阶级斗争的角度,具体分析了“五四”时期几个主要阶级和团体产生的基础、理论主张及其内在矛盾,没有当年创造社太阳社分析历史问题时那么抽象和机械,另一方面,却又同样武断地得出了像“‘五四’的一切思想及其口号都成了时代落伍”这样错误的结论。再一方面,他与对“五四”传统和鲁迅的评价比较谨慎的冯雪峰、瞿秋白比较接近,他的这篇文章就是应瞿秋白的要求而写的,如果把它与冯雪峰的《革命与智识阶级》,与瞿秋白在“左联”时期写的几篇文章如《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作一比较,就更能看清他们之间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的一致性,比如,对“五四”新文化反封建精神的有限度的肯定,对鲁迅《呐喊》的谨慎的赞美,等等。但同时又没有冯雪峰、瞿秋白那么鲜明的阶级和政党意识,在具体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希望做些文化方面的学理探讨,因而理论上自相矛盾的情况就比较突出。
冯雪峰、瞿秋白都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考察“五四”的。冯雪峰认为,“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五卅”,都是中国“国民解放运动”中的几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只有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国民解放运动”才“第一次的认识了社会的阶级冲突”,才“积极地开始进行着与封建势力的必要的斗争”。这是“中国智识阶级做工做得最好的”阶段。“五卅”以后,“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主要”的,“继续与封建势力斗争”变为“次要”的。[6]289瞿秋白则对“五四”传统本身也有褒有贬。瞿秋白赞扬的是“五四”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和“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7]22,贬斥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此基础上,他既强调“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又特别强调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继承“五四”“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和“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的“革命的倾向”[7]23。他特别关注的是要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
茅盾则是把“五四”学生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归结为一个整体,认为“‘五四’这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为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5]235。并把“这时期”分为三个阶段:“最初由白话文学运动作了前哨战,其次战线扩展而攻击到封建思想本身(反对旧礼教等等),又其次扩展到实际政治斗争——‘五四’北京学生运动。”[5]231茅盾这样做,显然流露出了想把“五四”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解剖的愿望。
问题是,茅盾写作此文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政治斗争,他所希望得出的结论,也是一个充满着政治利益和政治倾向的结论。于是,自相矛盾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他把“五四”新文化的演化过程既看作是一种不断“扩展”的过程,又看作是一个实际上不断衰落的过程,也即是他所说的“下火”的过程。尤其是,他把造成“五四”新文化不断衰落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实际政治的斗争”中的“动摇”和“妥协”[5]236。按此逻辑,如果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能够坚守自己的立场,那“五四”新文化就不会走向衰落。那么,应该否定的就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妥协”,而不是由他们所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价值观念。但这种思想显然又是不符合茅盾想整体上否定“五四”新文化的结论的。
更为显明的矛盾还表现在,茅盾一方面不但承认“五四”“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至少是破除封建思想这一点,是有它的历史的革命的意义的”,而且也承认“中国的封建势力,直到现在,还是根深蒂固,打倒封建势力还是革命工作之一面”[5]247;另一方面却又坚决地“论定‘五四’早已送进坟墓”[5]248,否定“‘五四’到现在还有革命的作用”[5]247。
不过,无论茅盾对“五四”新文化的认识存在多少矛盾,无论他与当年创造社太阳社,与冯雪峰、瞿秋白等人对“五四”新文化的看法存有多少差别,在整体上否定“五四”新文化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综上可见,同样接受了“阶级论”的鲁迅和茅盾,他们在对待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五四”新文化传统这个敏感问题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1]鲁迅.论“赴难”和“逃难”——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鲁迅.小品文的危机[A].鲁迅全集:第4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茅盾.读《倪焕之》[A].茅盾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A].茅盾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冯雪峰.革命与智识阶级[A].雪峰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7]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A].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