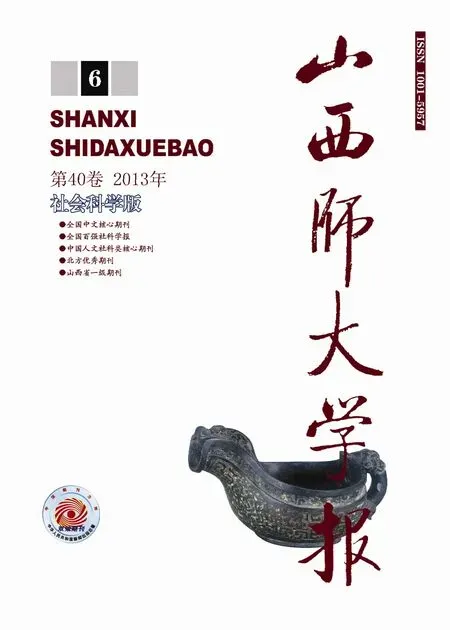机器与“暴力”
——论卡夫卡《在流放地》
郑 薇,曾艳兵
(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300387)
《在流放地》这篇小说是卡夫卡在1914年8月4日至18日创作的,它叙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机器杀人”故事。1916年10月11日,卡夫卡在给出版商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中说:“为了说明最近的这篇小说,我只补充说一句:并非只有它(即那个时代)是苦难的,而毋宁说,我们的普遍时代以及我的特殊时代,同样亦为苦难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苦难的,而我的这个特殊时代甚至比普遍时代有着更为持久的苦难。”[1]第7卷189小说表现的似乎是时代或人类的苦难,然而,导致这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战争杀人、理性杀人、机器杀人。一切都指向机器暴力问题,这在今天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今,机器杀人发展到了高精尖的水平,无人战机杀人根本无需面对杀戮对象,也无需直面杀戮的惨景。电子屏幕将其过滤得仿佛只是一个虚拟世界,杀人行为甚至只需点动一下鼠标。杀人的简单造成了杀人的随意,间接杀人又使得其责任难以或无从追究。这必然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和混乱。随之而来是道德、伦理问题,乃至宗教、信仰问题,最后必将关乎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卡夫卡一个小小的短篇竟引发出如此严峻的问题,“小说通过它的写作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对事实的感觉,你可以自由解释它,自由创作。”[2]123卡夫卡的小说总是被置入了太多的内容,以至于永远也不能只从一个方面去理解。故而我们完全有理由和必要从“机器与暴力”这一视角重新思考和探讨这篇小说。
机器为人所设计、制造、运用,原本以人为目的,为人所用,但在其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的过程中,它反倒渐渐成为目的,人则沦为机器的手段或工具,这就是“异化”。而机器对人的控制、戕害、毁灭常常伴随着暴力,对于那些对机械文明持乐观态度的人们而言,这是可以忽略或改进的,但对于敏感而忧郁的卡夫卡却是悲观的,甚至是致命的。机器对谁实施暴力?何以能实施暴力?又怎样实施暴力?《在流放地》似乎可以看作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尽管其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暴力”一词。作者只是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一架“行刑机器”。无疑,读者的心灵震颤通常也是由行刑机器在杀戮过程中呈现的“暴力”景观引发的。
一、机器与“身体暴力”
小说的内容并不复杂:在某个流放地,一位旅行家应该地司令官之邀,在一名军官的陪同下参观了对罪犯的刑罚。这名罪犯因不尊重上级而被判刑,执行刑罚的却是一架机器。军官向旅行家介绍了行刑机,并追忆起前任司令官对它的迷恋与使用,以及观众在行刑期间的热情,故而请求旅行家向现任司令官夸饰这架机器,以恢复往昔的“行刑盛况”。可旅行家却因刑罚的残忍拒绝了这一请求。之后,军官用这架机器对自己施行了处决,但它却因运转故障在极短的时间内杀死了军官。旅行者随后离开了该地。
什么是“暴力”?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如此界定:暴力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词,因为它的主要意涵是指对身体的攻击”。“Violence最接近的词源为古法文 violence、拉丁文violentia——指热烈(vehemence)、狂热(impetuosity)。可以追溯的最早词源为拉丁文vis——意指力、力量。从13世纪起,violence具有‘气力’意涵。1303年时,violence被用来描述对神职人员的痛殴。”[3]511—512看来,暴力的最基本的意涵就是对身体的攻击、残害,甚至毁灭。
在此意义上,小说集中描写的就是“对身体实施暴力”:一是军官对犯人身体施行的刑罚;二是军官对自己身体施行的刑罚,也即“对他人身体施暴”和“对自我身体施暴”。富有意味的是,这两者都是在机器对肉体进行践踏、摧毁中实现的。何以如此?探讨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卡夫卡写作该小说的时代。
20世纪的开头二十年,本雅明称之为“机械复制时代”。“我们技术手段的惊人增长,它们所达到的适用性和精确性,以及它们正在制造出来的理念和习惯使得这一点变得确切无疑:在美的古代工艺之中,一场深刻的变化正日益迫近。”[4]231卡夫卡对此亲眼目睹并深有体会,他在工伤保险公司几乎整天同机器和受伤工人打交道。1910年卡夫卡为保险公司提交了一份《防止电锯事故的报告》,对电锯上的安全轴作了详尽描述(附有精确的机械制图8张),并提出了改进的办法:
插图所示是四角轴和圆轴在安全性能方面的区别。四角轴的刀片(图一)是直接用螺丝固定在转轴上的,锋利的刀刃以每分钟3800至4000转的速度旋转。对于工人来说,刀片与桌子之间过大的空隙是十分危险的。[5]110
卡夫卡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各种机器伤害身体事件,他熟悉机器给人类带来的便利和效率,同时也在工伤保险公司和自家的石棉厂里看到了机器对人的戕害、扭曲和异化:
昨天在工厂。女工们穿着令她们难以忍受的肮脏不堪的松松垮垮的衣服,像是刚睡醒似的那样披头散发,她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不断发出躁声的传动装置和分散的、虽然是自动的、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停下来的机器,面部表情木然。她们好像不是人,没有人向她们打招呼,要是有人冲撞了她们,也不道歉一声,叫她们干什么,她们就干什么,她们干完事便又立即回到机器房。别人对她们颐指气使,她们俯首帖耳干活。她们穿着衬裙站在那里,受着最小头目的任意摆布,她们从不从容不迫地冷静地去理会这些头目,她们只是用目光和鞠躬去默默忍受和顺从。[1]第6卷199
对机器,乃至对小头目的顺从使这些女工失去生气;而一旦离开机器,她们便微笑雀跃,又变成了人。从人性到异化,从自由到奴役,从理性到荒诞,从科学到杀人,机械社会从一开始就颠倒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显然,《在流放地》中卡夫卡选择“机器”作为实施暴力的主体隐喻了现代工业社会中令人望而生畏的物质力量对人造成的压抑,以及人在物化过程中对自身价值的贬斥。机器发展带来的技术一体化以暴力的方式泯灭了个体的血肉灵性。不难预见,在技术的帮助之下,文化、政治及经济都将演变成为一种统一的体系,吞噬并排斥所有其他的选择性,个体在以机器为依托的技术理性的控制下被逐渐异化为“单向度的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系列令人振奋的重大新发明:大海轮、无线电、电影院、摩天大楼、汽车、飞机及其背后有关动力机器制造的抽象观念,改变了都市生活,为现代主义提供了动力”[6]91。科技发明在推进了现代化的同时也点燃了欧洲大陆的火药桶:1870年普法战争,1911年意土战争,1912、1913年爆发了两次巴尔干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两天后,他开始创作小说《在流放地》。“1914年不仅仅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彼此对战。1914年以前的军备竞赛就制造了巨大的战争机器,战争也工业化了。人员和物质都按照精心制订的时刻表用火车运输到前线附近。各式各样的新技术和战斗、战术大大提高了每个人的死亡危险性。”[7]126卡夫卡显然预料到了工业化时代的战争必然伴随大规模的屠杀与死亡。《在流放地》中行刑机造成的血淋淋的身体暴力正指向了战争作为杀人机器对人类肉体无情的毁灭。在小说的尾声中,军官用直接、残酷的方式施暴于自己:“他禁闭着双唇,睁大眼睛,神情与生前一模一样,目光镇定而自信,那根大铁钉的针尖则穿透了他的前额。”[1]第1卷104这也许正是在物质永恒的进步之中,在人类对同类的残忍伤害之中,以自我施暴的方式表现出的对生命充满绝望的报复。卡夫卡的小说当然不是战争的原因,但似乎可以看作是其酝酿和爆发的间接结果。
二、机器与“法律暴力”
如上所述,暴力就是对身体的攻击,然而,其理由和合法性是什么?这就涉及到规约、制度和法律等问题。在一个所谓的文明时代,暴力的实施常常与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规约、制度和法律其本意应该是避免和消灭暴力的,但在实施过程它们自身也在制造暴力,以至于自身也成了暴力的体现和象征。这一点与人们制造机器,最终又被机器所戕害是同一道理。
约翰·加尔顿把暴力定义为“任何使人无法在肉体或思想上实现他自身潜力的限制”。他将暴力区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直接暴力的形式是指杀戮、残害、肉体折磨等;结构性暴力着眼于压迫,包括剥削、渗透、分裂和排斥四种因素;文化暴力则是指文化中那些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8]189这种文化暴力体现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就是军规或法规的暴力,我们在这里统称为“法律暴力”。“卡夫卡的作品的实质在于:机器、话语和欲望都隶属同一套配置(assemblage),这套配置为小说提供动力和不受限制的对象。……他的理想的藏书室只有工程技术和操纵机器方面的书籍,以及一些法学著作。”[9]83“这台机器并非完全技术意义上的机器,具体些说,它是一种刑具,而在深层意义上,它是与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传统,或者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运转机制的象征。”[10]
在《在流放地》中,犯人由于触犯法律而被送上行刑机,他不知道对自己的“判决”,甚至“压根儿没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护”[1]第1卷83。不管在旅行者眼中,还是在读者眼中这都是不合常理的。然而,这正是长期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刑事诉讼过程甚至秘密判决的真实写照,法官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绝对的排他权力。法律如一架运转中的行刑机,确保了对犯罪的惩罚——用残暴来克服残暴,用恐怖来消灭恐怖,用血腥来洗刷血腥,最终成为一种维护杀戮并使之合法化的“暴力”。而犯人需要通过伤口来辨认对自己的判决,繁复的文字使他无法辨认清楚,最终“精确的”按时死去。基于法律产生的、被精细地度量过的痛苦刑罚以被极刑延长的时间来增加死亡的次数,犯人应根据量化了的“罚”而知晓自己所犯下的“罪”——这逻辑倒错的荒诞中蕴含着现实生活的真实。刑罚实践与法律条文因果倒置无疑是对成为“文化暴力”的法律做出的深刻嘲讽,即便“罪”与“罚”的先后次序并未倒错,何种“罪”与何种“罚”是完全对等的呢?军官正是在文化暴力遮蔽下不假思索地接受和习惯了这套法律机器的人们的代表。法律暴力以隐蔽的方式渗透进人们的思维习惯之中并制造出一种一维的文化和思想方式,使得每一个个体毫无知觉地成为保证其运转的机器零件。
《在流放地》中,军官不仅希望行刑机器能够永久运转下去,更希望人们能恢复观赏公开处决的热情。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了权力微观物理学的观点,他认为,用公开酷刑来捕捉肉体的刑罚体现了一种权力政治学,“这种权力正通过自己展示为‘至上权利’而获得新的能量”[11]62。在新司令官时代行刑机器将遭到弃置,而这是否意味着法律作为“文化暴力”机器的面孔被民众识破?答案是否定的。新司令官废止了刑罚机器,却依靠固定地召开毫无意义的“会议”重新聚集和展示了自己的权利。消灭肉体的形式被改造肉体的形式取代,在“人性”的名义下将酷刑重建为对人们日常行为、活动的监督和改造[12]164。“法律暴力”通过对表象的改造更深地嵌入社会之中。在“人性”、“公正”、“自由”的包装之下,个体的思维被预先规定了,不再可能产生反抗的意愿。就这样,社会理性发展可能造成的对直接暴力的不满被法律暴力“合理”地消解掉了,同时,对直接暴力的不安和焦虑也被消解掉了——这正是《在流放地》中的现任司令官试图达到的目标。法律暴力犹如一袭看似华丽的道袍将个体肉身的曲线遮盖起来,进而通过行刑机对其进行扭曲和戕害。在揭开道袍的那一刻,残破的个体肉身将会是触目惊心的。
三、机器与“语言暴力”
暴力是对身体的攻击,这种攻击以法律为依据,而法律又必然体现在语言文字上,因此,所谓“身体暴力”必然源于语言的暴力,并必然以其方式呈现出来。卡夫卡的小说通过极为细腻素朴的语言呈现了暴力实施的过程。
《在流放地》中行刑机器致人死地的方式是将文字刺入犯人的身体。由于行刑过程就是将犯人触犯的法律刻在他身上的过程,因此,处决就是被书写。所谓判决,“只不过是用耙子把犯人触犯的诫条写在犯人的身上”。“在这当儿,被耙子刺伤的部位贴在棉花上,由于棉花是特制的,马上就止住血,并为进一步加深刺文作好准备。”[13]第4卷114“刺伤”是卡夫卡自创的复合词“wundbeschriebene”。在德语中有一个谐音的复合词“wundgeriebene”,意为“身体的某个部位被摩擦(gerieben)而受伤(wund)”。卡夫卡将这个词后半部分替换成读音近似的“beschrieben”,意为“被刻画”、“被书写”。卡夫卡“通过把‘被伤害’(wund)和‘被书写’(beschrieben)复合成一个词,以图实现‘判决’和‘刑罚’的同时性”[14]156。卡夫卡这里的别出心裁还同《圣经》有关:“耶和华说:‘我要将我的法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利米书》31:33)
“被书写”就是“被伤害”,语言的暴力必定转化为对身体的施暴。《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六节中有一句名言:“字句叫人死”,哈代将这句话写在《无名的裘德》的扉页上。因此,谁掌握了语言,谁就掌握了权力;谁掌握了法的语言,谁就掌握了法。要服从法律的精神就得先掌握有关法律条文的知识。如此,“法”的问题就成了语言问题。人们开始用崇拜语言来代替崇拜上帝,从遵从上帝的意旨变成了遵从法律。然而,知识又培育起怀疑精神,并且,当法律条文引发出无限的模糊意义时,解释就成了人类永恒的任务。“这些法律由来已久,且非常古老,为了解释它们已经做了几百年的工作,而且这种解释也许已变成了法律本身。”[1]第3卷411谁拥有对法的解释权,谁就拥有法;那些不懂法的语言的人,其实就是不懂法,最终成为法的牺牲品。
果然,在卡夫卡的小说里,“一切都是为着文字设计的——但文字本身却是无法读懂的。”[15]114在机器运转的轰鸣声中,旅行家无法听清军官的话,军官说话甚至连自己都听不清楚。且小说暗示出存在三种不同语言:犯人的语言、军官的语言和机器的语言。军官与旅行家的对话采用的是犯人无法理解的语言,而犯人遭受刑罚是由于他的语言冲撞了上级。最终,犯人将在行刑机的语言书写过程中被施以刑罚直至死亡。语言交流的障碍、语言等级的高低以及行刑机用文字杀人等均表现了卡夫卡对语言暴力的担忧与焦虑。
卡夫卡所处的时代,布拉格正处在多民族的分裂冲突之中。“少数民族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与有生气、有民族主义抱负的绝大多数捷克人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尽管知识界做了一些理想主义的尝试,以图达到合作的目的,但布拉格的状态仍然是四分五裂的——犹如一座特殊的温室,在这里,诸如社会主义、犹太主义、德国民族主义、玩世不恭的思想、人道主义,以及一切虚假的世界主义等各种信念都相互冲突。”[16]109政治、经济、军事的冲突必然会反映到文化领域,而在文化领域,冲突表现得最为集中的恐怕要算是有关语言的争端。“1891年布拉格街道上的德语标志突然都被换成了捷克语,城里的气氛一时变得非常紧张……1897年,‘十二月风暴’在布拉格爆发,一场反德国的新语言法运动变成了三天的反犹太人暴乱。”[15]74卡夫卡就处在这种语言暴力的中心。当代法国语言学家海然热曾严肃地问道:“仅就本世纪而言,为什么语言问题往往成为暴力冲突的导火线?”他的回答是,因为“语言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藏而不露的力量,……语言的实践反映一种并未公开宣布的霸权。”“任何语言政策都利用最忠诚的支持者玩弄权力游戏”[17]265—267。
卡夫卡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布拉格犹太人,他对自己所属的语言身份非常敏感和焦虑。他说:“语言是故乡的有声的呼吸。可是我是个严重的哮喘病人,因为我既不懂捷克语,又不懂希伯来语。两种语言我都学。但这好像梦似的。我们在外面怎么能找到应来自内心的东西呢?”[1]第5卷439卡夫卡对语言宰制所导致的悲剧有着切肤之痛。的确,语言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决定了主导性语言群体和非主导性语言群体之间的关系。不同语言在交际功能上是平等的,但由于权力的介入它们的现实地位却呈现为不平等。“企图在国家的全部领土上强制推行单一语言常常意味着强加一种霸权式的国家认同于全体公民,强化国家是优势群体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其自治权利的思想。”[18]45《在流放地》中军官、犯人的不同语言赋予了他们不同的地位。犯人在言语上冲撞其上司进而遭受刑罚,这表明低位语言对高位语言造成的无意冲撞,以及随之而来后者通过语言暴力或霸权对前者的压迫与宰制。“暴力为了在保持暴力的状态下成为语言,不能用工具行使暴力,必须用‘机器’行使暴力。由于工具发展成‘机器’或妄想系统,同样暴力也变成了与系统语言相似的形态。”[14]156语言终于具有了与保证暴力实施的行刑机器相似的形态,行刑机用文字杀人使人们明白了“什么是语言暴力”。
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以行刑机器直接作用于身体的“暴力”使人们在视觉的想象中感到肉体的震颤,而在看似荒诞的叙述中所寄寓的“法律暴力”和“语言暴力”所带来的震颤则是灵魂上的。中国当代作家马原曾编选过一部名为《大师的残忍:我最喜欢的恐怖小说》选集,其中就收录有这篇小说。在《序》中马原写道:“单看本故事,你会以为它的作者一定是一群冷酷无情的家伙,十足的虐待狂。而熟悉的读者如果不曾读过如下篇什,同样不会想到——你所熟悉的大作家,何以还有如此残忍的一面!”[19]1许多受到卡夫卡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如余华、马原、格非等都曾以“暴力叙事”的手法进行写作,看来亦并非偶然。也许正因为机器暴力的“真实”就在于它的神秘、晦涩和意指的不确定性之中,“暴力”之后的灵魂震颤或许就是卡夫卡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到末了,以行刑机器隐喻“暴力”的《在流放地》本身也在无意中成为一架“行刑机器”,它以人们永远无法完全解读的文字构成了一套精密的装置,它不停地运转着,发出阵阵轰鸣,刺入人们的灵魂之躯,人们终将在自己身上读到对自己的审判。
[1]卡夫卡全集[M].叶廷芳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叶廷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4](德)汉娜·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5]Stanley Corngold,Jack Greenberg and Benno Wagner,ed.,Franz Kafka:the office writing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6](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M].紫辰,合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7](德)福尔克尔·R·贝格哈恩.自杀的欧洲——1914年的6月28日萨拉热窝[M].朱章才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
[8]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9]Gilles Deleuae and Felex Guattari,Kafka: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10]王炳钧.传统无意识考古——论弗兰茨·卡夫卡的《在流放地》[J].外国文学,1996,(1).
[1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2]汪民安.福柯的界限[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3]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14](日)平野嘉彦.卡夫卡——身体的位相[M].刘文柱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15]曾艳兵.卡夫卡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6](英)马·布雷德伯里,詹·麦克法兰.现代主义[M].胡加峦,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17](法)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M].张祖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18]郭友旭.语言权利的法理[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19]马原选编.大师的残忍:我最喜欢的恐怖小说[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