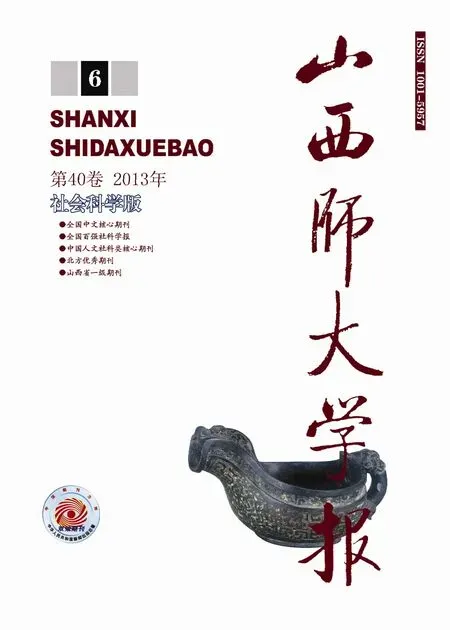1950年代国家对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改造与重构
肖 扬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北京100730)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发展的重要历史节点。伴随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改革运动,实现了对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关系的改造与重构。这种改造与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传统和规制,延续至今。因此,深入分析和探究这一变革过程的利弊得失,总结和反思其间值得汲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当今先进性别文化与平等性别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借鉴和启迪作用。
一、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对传统性别文化和社会性别关系的改造
男女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妇女运动的目标,也是实现其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20世纪50年代初,新生的红色政权在夺取全国胜利后,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对传统性别文化和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改造。在妇女受压迫最深的婚姻家庭领域,通过颁布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对封建婚姻制度及家庭关系进行全面改造;在经济领域,土地改革法和土改运动使中国妇女第一次享有土地所有权,成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政治上,1953年颁布的选举法,赋予了妇女与男子同等的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使妇女参政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在法律保障方面,1954年颁行的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各项权利,体现出国家对妇女人权的尊重。为维护妇女的人格尊严,荡涤社会积弊,中国政府采用强力手段革除社会痼疾,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妓院,改造妓女,扫除数千年的娼妓制度。国家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和社会行动维护妇女的特殊利益,如对女职工实行“四期”保护,通过推广新法接生和开展扫盲运动,增强了广大妇女对新政权的认同。通过以上对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大历史事件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首先,中国共产党按照其社会变革理想和男女平等的图式,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的制定,从政治、经济、婚姻家庭、社会风俗等各个领域发起了对传统性别文化和不平等性别关系的改造,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动摇了父权制统治的根基,使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其次,伴随国家强有力的社会文化宣传,男女平等理念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得到群众尤其是妇女的高度认同。“反对大男子主义”、“男女平等”、“反封建”、“妇女翻身解放”、“不能重男轻女”等话语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时尚广泛传播,对民间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和歧视妇女的话语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促进了传统性别文化和观念的改变。
第三,这一时期国家对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改造采用了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方法,并将对性别关系的改造纳入到社会改造和民主改革的进程当中,以启发阶级觉悟、诉苦思甜、宣传教育、深入发动等多种方式,使妇女参与其中,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妇女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平等和解放,进而支持和投身到这一改变自身地位的变革之中。
第四,国家的法律保障使妇女获得了参与社会生活的合法性,妇女成为平等国民的主体参加到对传统性别文化的改造之中,并逐步发展成为谋求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重要力量。由于建国初期制定的一系列体现男女平等的法律,挑战了父权制的核心,是对数千年男权统治的颠覆,因此,上述每一项法律的贯彻实施,都经过了持续数年的努力,遭遇了来自男性和传统性别文化的强烈抵制和反对。政治、经济、婚姻家庭领域中每一种性别关系的变革都是一场革命,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和较量。仅以婚姻法的贯彻为例,许多妇女是冒着被打、被杀的决绝态度冲破封建家庭束缚的,也有不少妇女在谋求婚姻自由的道路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26—27由此说明,建国初年的土地改革、参政选举、婚恋自由乃至妓女改造,如果没有广大妇女的觉醒、参与和斗争,男女平等性别关系的构建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妇女不仅仅是“恩赐”的对象和被解放的客体,而是这场变革的主体力量。正是由于广大妇女参与了国家各项法律政策的落实过程,男女平等的原则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实施,新型的性别关系才得以逐步建立,并具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五,新中国建立初期,以男女平等为目标的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建构,为后来共和国在建设、改革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性别关系改造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男女平等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国家的制度安排,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传统和规制,延续至今。同时,国家对传统性别关系的改造也成为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造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国家对社会性别关系的改造与建构
1956年,伴随国家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党和国家遵照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建设新中国的现实需要,运用多种手段动员妇女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劳动。截至1956年底,已有1.2亿多的农村妇女参加了农业合作社的集体生产劳动,至1957年,中国城镇女职工已达 328.6 万人,占职工总数的 13.4%。[2]13妇女大规模地参加社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促进了妇女的经济独立,是对数千年传统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一种改造。
但随着城乡妇女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妇女感受到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的双重负累,许多男性也为此深感焦虑。从1956年起,全国民主妇联主办的《中国妇女》杂志就不断接到读者来信,询问“职业妇女是否可以离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还算不算独立和解放?”1957年《中国妇女》杂志第1期刊登了读者马文治的来信——“职业妇女可以离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吗?”信中反映他的妻子是保育员,他们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两个大孩子进了妻子单位的托儿所,小的在家请保姆照看。妻子每月的工资在支付保姆费用后仅够自己生活,作者每月工资要负担三个孩子和他自己的全部费用,经济上入不敷出。妻子单位离家较远,每天带着两个孩子早起晚归挤公共汽车,疲惫不堪。作者为此算了一笔帐,如果妻子离职回家照看孩子,辞掉保姆,靠他的工资可以维持五口人的生活,每月还能有些节余,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孩子也能得到照顾和教育,同时妻子离职还可以给其他需要工作的同志创造一个就业机会。为此,他建议妻子暂时离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等孩子长大了再去工作。当他提出这一想法后,身边的人反响强烈,莫衷一是,使他无所适从,特此致函《中国妇女》杂志寻求解答。[3]马文治的来信集中反映了职业妇女的角色紧张和男性的焦虑,他提出的职业妇女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基本理论,关系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性别分工和新型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同时又是一个广大妇女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在马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编辑部就收到了来自全国近百封来信,对此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针对这一情况,当时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和全国民主妇联书记处决定通过媒体的公开讨论、撰写文章和发表重要讲话的方式来阐述对这一问题的认识。1957年,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章蕴在《中国妇女》杂志第5期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职业妇女是否可以离职回家从事家务劳动的问题,应该由她们自己回答。她认为,在现阶段,无论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只要尽自己所能从事的劳动,都是光荣的。与此同时,全国民主妇联主席蔡畅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文章。她强调社会制度不同,家务劳动的性质和意义也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的性质不再是为父权制统治的旧家庭服务,而是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服务,是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劳动,是非常光荣和有前途的。对于什么是社会劳动,蔡畅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都是社会劳动;所以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的一部分。”[4]43她进而批评那种把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划分为公私两个领域、分为不同等级、认为从事家务劳动不光荣的观点,“托儿所、食堂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服务的,在家里做饭带孩子,不也同样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服务吗?同样的饭,同样的衣服,都是给职工吃的穿的,为什么在食堂商店里做饭做衣服同在家庭里做饭做衣服要有光荣不光荣的分别呢?这没有道理”。[4]45她还批评那种认为“家务劳动没钱挣就没有价值”的观点是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为使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和职工家属切实感受到尊重、光荣、是有前途的,1957年6月全国总工会和全国民主妇联共同召开全国职工家属会议,来自全国的1300多名职工家属(大部分是家庭妇女)齐聚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的接见表明了国家对家务劳动社会价值的高度认同。历来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家务劳动和没有社会地位的家庭妇女在新中国给予了崇高的荣誉,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通过家庭妇女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义务奉献和政治荣誉的补偿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
由此,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成为超越公共和私人劳动之上的一种劳动。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劳动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工也不再是判断社会性别关系和妇女解放与否的标志。用社会性质来判断家务劳动的性质,无疑使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都在“社会主义劳动”的大旗下消解了,家庭内外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权力关系也由此被遮蔽,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国家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构,同时也是根据中国国情,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种探索。
事实上,在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家高度重视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加紧对人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明确提出“人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国家对社会性别关系的改造也从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构建,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封建主义性别文化的批判也主要是通过对妇女和男性、个体和集体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完成的,即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乃至政治运动的方式,着力把妇女和男人改造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把各阶层妇女的社会身份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妇女”,并“引导妇女用社会主义思想原则理论来对待改造家庭”。在“建设社会主义成为全体男女公民的最高利益”的原则下,男女/夫妻的两性关系成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同志,并以此作为对传统性别文化的改造和对社会主义社会性别关系的建构。在这里,男女两性不再是两个独立的利益群体,即使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也成为共建社会主义大业的革命同志。在急于摆脱一穷二白落后面貌,尽快建成先进工业国家的“大跃进”中,男女两性同样被视为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平等劳动者,性别的差异也由此被抹杀或遮蔽,成为“去性别化”的认识论基础。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逐步升级与建设社会主义高于一切的历史情境下,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并不是以男性为标准,而是以是否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为标准的,因为在国家的视野里只有已经获得了解放和平等的(男女)建设者,而没有抽象的男性标准。强调和激励妇女走出家庭,为国家建设做贡献,成为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传统延续至今。
实际上,这一时期被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是维护传统性别关系和角色定型的政策,也都体现出对社会性别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改造始终是从属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五好”活动,在1957年全国民主妇联召开的城市妇女工作会议上被纠偏,认为在“五好”宣传中存在未能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解释“五好”,导致在“五好”活动中出现要求家庭妇女“服侍丈夫,作旧式贤妻良母”的偏差,指出要正确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务劳动的意义,使家庭妇女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自觉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新型家庭妇女”,而不是成为男子附属品的旧时代的家庭妇女。指出贯彻“五好”不仅仅是妇女的事,也是关系到整个家庭男女共同利益的事,因此男女要一起发动。此外,受到女性主义批评、被认为是将妇女的角色定位于家庭的“两勤”方针,其目的也同样是服从于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的。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两勤”方针的完整表述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这里,“勤俭持家”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并成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曾亲自指导“两勤”方针制定的邓小平明确表示,“男同志也要勤俭持家”,“要向男同志宣传”,指出勤俭持家是家庭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必须依靠全家男女老少一齐努力。1958年1月,全国妇联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能将“勤俭持家”片面理解为动员妇女搞家务,“两勤”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迅速发展”。[5]351—354
三、主要结论
对20世纪50年代重要的妇女历史事件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看清国家对传统性别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社会主义性别关系的认识,以及身处其中的妇女的处境、感受和对自身主体身份的认同。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国家对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改造始终与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传统性别文化和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改造,是阶级革命和民主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期,对社会性别关系的构建则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内容。性别文化由此成为中国革命文化以及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20世纪50年代对社会性别关系的改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以改变男尊女卑的性别文化和不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为目标,在国家强力推行和妇女的支持参与下,初步构建了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文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家对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改造实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改造,构建的是社会主义的性别关系,即将男女两性改造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同志,男女两性不再是利益不同的两个群体,性别分工也由此被遮蔽。用社会属性作为判断家务劳动性质和妇女解放标志的结果有二:一是成为“去性别化”的认识基础;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高于一切的背景下,在国家的性别话语中,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并不是以男性为标准的,而是以是否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为标准。
第三,20世纪50年代的性别关系改造始终是以国家为主导,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大力倡导全力推行。对社会性别关系、性别文化的改造和建构不仅始终服从于国家的需要,而且在方式上也沿袭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启发觉悟、群众运动等方式,体现出很强的国家意志和政治色彩。
第四,“被运动起来”的妇女参与了这一变革过程,并逐步成为促进变革、谋求男女平等的重要力量。国家对妇女的尊重,赢得了妇女对新政权的高度认同。妇女被纳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规模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之中,逐步实现着自身主体身份的建构,改变着传统性别文化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并使之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五,这一时期对性别文化和性别关系的变革伴随着理论的探索,妇女运动领袖和全国民主妇联身处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这一时期的中国妇女运动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指导,同时又试图结合中国妇女发展的实际,突破经典作家的历史局限,做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阐释。但是,由于受到党内“左”倾思想和急于建成先进工业国家的强烈愿望的影响,加之,对改变社会主义时期性别不平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做出的理论判断过于简单或有失偏颇,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妇女解放理论探索的艰辛和曲折。
第六,在大力号召妇女“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在劳动贡献中求平等”的思想主导下,出现了忽视男女两性差异的“去性别化”倾向,进而也相对忽视了要在促进妇女为社会主义做贡献的热潮中,有意识地维护妇女的特殊利益,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20世纪50年代的贡献话语一直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所沿用,为共和国的妇女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1]顾秀莲.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卷)[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2]章蕴.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A].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献[C].北京:中国妇女杂志社,1958.
[3]马文治.职业妇女可以回家从事家务劳动吗?[J].中国妇女,1957,(3).
[4]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的讲话.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编,全国职工家属代表会议主要文件[G].北京:工人出版社,1957.
[5]全国妇联关于1958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的通报[A].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编,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1949—1983):第2册[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