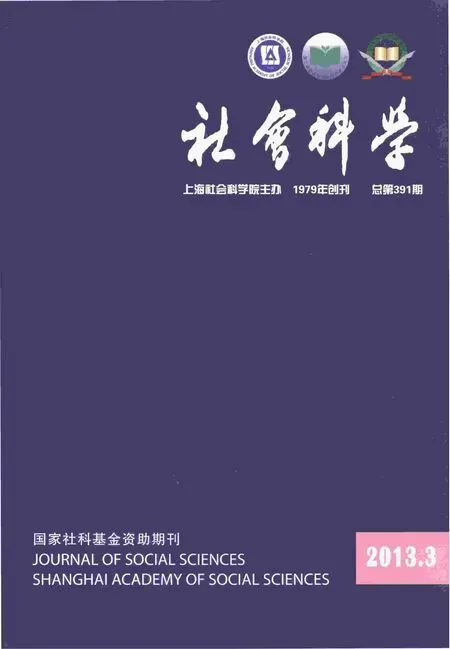“具体的形上学”之构建——杨国荣哲学思想初探
王论跃
在阅读201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国荣教授的《具体的形上学》三书(《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的同时,我再次通读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11册《杨国荣著作集》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杨国荣教授的文集《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等论著,在阅读时,我每每为杨教授所涉领域之广泛、讨论之深入所震惊。在当今中外哲学界,对哲学的各个领域以及相关命题如此融会贯通的哲学家并不多见。具体的形上学不仅是杨国荣先生对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各种形而上学的扬弃,也是其三十年哲学沉思的重大理论突破。鉴于具体的形上学在杨国荣先生的整个哲学构思中的特殊意义,所以不能将之等同于其哲学研究的其他阶段性成果或个案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概述,具体的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其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的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①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载《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这一高度浓缩的概括包含了多层哲学含义。我们在这里只强调两点:首先,具体的形上学是对形上与形下、道与器之间的沟通,是对超念的玄学与现象主义偏向的双重克服;其次,具体的形上学既是哲学的问题,也是哲学史的问题,是中西哲学一个世纪多以来对话、互动中的理论选择。具体的形上学作为杨国荣先生的哲学思考的既然状态 (已济)与动态过程 (未济),具有相当的兼容性与可完善性。下面,我从杨国荣先生哲学研究的历程来阐述具体的形上学与他的整个哲学构思之间的连贯性,并就具体的形上学的可能引发的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只要我们沿着杨国荣先生的哲学研究的轨迹,便不难发现作为他的哲学研究逻辑发展的具体的形上学这一提法虽然晚出,但是具体的形上学的思路却一直贯穿着他的哲学思考。在这里我们以“成己与成物”这一议题为例来说明这种一贯性。
早在《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1990年)一书中,杨国荣先生已经在征引王阳明弟子黄绾的《明道编》卷五中的一段:“《大学》之道,‘成己’、‘成物’而已。‘成己’者,‘明德’、‘亲民’之事也;‘成物’者,‘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也;‘成己’所以‘成物’,合内外而一之也。其用功之要,只在‘致知在格物’一句。”引用之后,杨国荣先生分析道:
成己即理想人格的自我培养,成物则指凭借主体的力量以裁成万物。以致知格物为成己成物之要,也就是强调德性的自我培养与主体对外部对象的作用,都必须以“知道”(则)为基础。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解决主体的能动作用于必然之道 (理)之关系的一种尝试:成己与成物分别从主体自身和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上肯定了主体的能动性,而以致知格物为要,则实质上将这种能动作用置于必然之道 (则)的规范之下,后者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扬弃了泰州学派离开必然之道而片面强调自我决定自我与自我决定非我 (造命由我)的意志主义观点。①杨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杨国荣著作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页。
黄绾在《明道编》中基本上是用《中庸》来解释《大学》的,因为《中庸》第二十五章中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者自道也。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②关于《中庸》中“诚”的概念的讨论,参见吴怡《中庸诚的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1年版)以及陈赟的文章《中庸之道为什么必须以诚为基础》,载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编《思想与文化》第七辑,2007年,第135-175页。杨国荣先生本人的《〈中庸〉释义》附录于其所著《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41页。“诚”在成己与成物上的展开,便是伦理与知识的维度。对此种意义的“诚”的探讨便进入道德哲学与认识论的视域。顺便指出,这种由己及人的儒家伦理与法国已故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由人及己的理路正好相反。黄绾在《明道编》中对其师王阳明的思想有所扬弃。一方面,他强调《大学》的“诚意”,这一点基本上是顺着王阳明的思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格物致知”作为功夫的关键作用,对轻视功夫的意志主义具有纠偏的作用。可以说,“诚”的概念在《大学》《中庸》《孟子》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此概念正是连接此三书的重要纽带。我们可以来看《孟子·离娄章句上》第12条中所引的孟子的话:“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众所周知,“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通书》基本上是围绕着“诚”的概念而展开。其开篇就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③《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3页。。从《中庸》到《通书》,“诚”体也从物的存在偏向人的存在。周敦颐一方面用《太极图说》构建宇宙、天道本体,另一方面用《通书》通过诚体来构建人极。周敦颐还用《周易·系辞》的资源来进一步阐述他对“诚”的理解:“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精故明,神应故妙,几微故幽。诚、神、几,曰圣人。”①《周敦颐集》,中华局书1990年版,第17-18页。“诚”“神”“几”成为表达圣人精神境界 (体)、感通应变 (用)的不同特征,然而其本、其体仍是“诚”。
杨国荣先生在《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中已经通过对阳明心学以及阳明后学的哲学史梳理,注意到成己与成物这一问题的范式意义。不过,这里的分析侧重成己的主体能动性这一层面以及相关的制约,尚未从意义理论上考察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也还没有将它们与诚体放在一起研究。随着对《大学》的“诚意”尤其是对《中庸》的进一步研究,杨国荣先生对成己与成物问题的思考不断地深化。
几年之后,杨国荣先生在《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1997年)一书中,在考察王阳明的“意”的概念时,指出“王阳明将存在的追问与意义世界联系起来,在人自身的存在过程中澄明世界的意义,从而避免对超念本体的过多承诺,并表现出统一本体论与价值论、伦理学的趋向”②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华东师大版《杨国荣著作集》2009年版,第118页。。王阳明“统一本体论与价值论、伦理学的趋向”可以视作杨国荣先生本人统一、整合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的具体的形上学的雏形。
在《具体的形上学》第三册《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中,杨国荣先生对于成己成物的意义向度作了多方面的考察,对虚无主义与权威主义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
以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认识人自身与改变人自身为指向,成己与成物内在地展开为一个寻求意义的过程。如果说,在理解-认知层面与目的-价值之维对意义的双重承诺使成己成物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那么,对虚无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克服与扬弃,则意味着确认这一过程的价值创造性质,也赋予意义世界的建构已走向自由之境的历史内涵。③杨国荣:《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除了意义、价值层面的关怀,杨国荣先生还从本体论角度来论证成己成物的含义,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说的:“作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在’世方式,成己与成物可以视为人的基本存在形态:当人作为存在的改变者而内在于这个世界时,成己和成物便开始进入其存在境域。正是这种存在的处境,使人区别于其他的对象。从赞天地之化育,到成就自我,现实世界的生成和人自身的完成,都伴随着人对存在的改变。可以说,离开了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人本身便失去了现实的品格,从而难以真实地‘在’世。”④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载《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这种对诚体所包含的成己成物,认识自己与改造世界的意义诠释与某些海德格尔专家对他提出的“此在”(Dasein)概念的解释有相通之处。法国哲学家、伊斯兰哲学专家Henri Corbin(1903—1978)在20世纪30年代将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重要术语Dasein(être-là)翻译成法文réalité humaine(人的实在性),并翻译解释 “Das Dasein ist sein Da”为 “la réalité humaine réalise,effectue une présence-réelle”(人的实在性实现、履行真正的在场)。他解释道:“这种在场,这一Da,就是‘存在 [在]世中’。然而,这一论点的本体论意义意味着‘在世’丝毫不表征容纳其存在的庇护地。相反,‘存在’在这里表征的是使得‘在世’现象得以可能的原始条件。”⑤Henri Corbin,《Avant-propos》(引言),in Martin Heidegger,Questions I et II(问题1、2 集),Paris,Gallimard,1968,p.15.我不知道法国汉学家、哲学家于连 (François Jullien)在将《中庸》翻译成法文时将“诚”译成authenticité réalisante(反过来可以直译为:能够实现的真诚)是否曾经受到这种译法与解释的影响⑥关于于连的《中庸》翻译,可以参看 François Jullien(trad.),Zhongyong.La régulation à usage ordinaire,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1993.。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抽象形态趋向于离器言道、“后形而上学”的内在特点在于离道言器,那么,“具体的形上学”则表现为对以上思维进路的双重超越。这正如杨国荣先生自己说的那样:“与不同领域的知识首先涉及特定对象不同,哲学以求其‘通’为其内在指向。哲学层面中的求其‘通’,既指超越知识对存在的分离,回归存在的统一性、整体性、具体性,也指把握存在的视域、方式之间的统一。通过再现存在的统一性和具体性、联结把握存在的不同视域和方式,形而上学的具体形态或‘具体的形上学’同时也体现了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深沉内涵。”①杨国荣:《具体的形上学·引言》,《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对智慧之思的追求,是哲学的元问题。在这一点上,作为清华学派的主要传承者之一,杨国荣先生自觉地继承了冯契先生的哲学遗产。冯契将智慧认作知识的转化与飞跃,同时强调:“不能把知识与智慧割裂开来,飞跃不是割裂。”②冯契:《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0页。杨国荣先生自己这样评论其师求“通”的努力:“以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价值界为主干,冯契展开了其智慧说中的天道理论。这种考察无疑具有本体论意义,但它又不同于思辨的本体论:它的目的并不是构造一个形而上的宇宙模式或世界图景,而是以认识世界为主线,阐明如何在实践的基础上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从而化本然界为事实界;通过把握事实界所提供的可能以创造价值,在自然的人化与理想的实现中不断达到人的自由。冯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谈天道 (自然的秩序),并把这一过程与通过价值创造而走向自由联系起来,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统一,这一研究路向无疑有其独到之处。”③杨国荣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2页。如果我们使用冯友兰先生的“照着讲”“接着讲”的两分说法,杨国荣先生的“具体的形上学”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冯契先生的广义认识论或者智慧说。具体地说,杨国荣先生对冯契先生的若干表述或者提法作了更为严密的处理。比如,冯契先生在谈到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时,认为“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这也就是功夫与本体的统一”④冯契:《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杨国荣先生在分析了功夫与本体在中国哲学,尤其在王阳明、黄宗羲等人论述中的含义之后,表示“将本体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等同于中国哲学中的功夫与本体的统一,似乎不甚妥切”⑤杨国荣:《论冯契的广义认识论》,载杨国荣主编《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具体的形上学出发点是对哲学本身由“道”流为“技”、由智慧之思走向技术性的知识,由此导致的哲学的知识化与智慧的遗忘进行的批判。应该指出的是,哲学本身由“道”流为“技”也不乏正面的效果。如果没有这种流变,很难想象一些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产生。众所周知,西方近代以来不少优秀的哲学家转向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并成为这些学科的一流学者,又同时为这些学科提供新的方法论。直至20世纪60年代,法国著名现象学家德桑蒂(Jean Toussain Desanti,1914—2002)还要求其学生们“立足实证科学”。曾是他的学生的原法国人文高师校长奥鲁 (Sylvain Auroux)教授因此在法国创立了语言学理论认识论。道与术不可须臾离也,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也是具体的形上学所主张的。
具体的形上学关心人的真实的存在,关心此在,关心人与世界的互动,但是对于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修炼,也即修身的层面相对来说言之不详。而部分现代哲学家对此给予相当的重视,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铎 (Pierre Hadot,1922—2010)。Hadot对蒙田推崇备至,认为正是蒙田让他感觉到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话语”。真正的智慧,哲学追求的目标,常常是溢出言语的。他指出:“哲学话语应该从生活方式的图景来理解。哲学话语是生活方式的手段与表达。哲学应该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哲学话语精密相联。”他还说:“哲学只是智慧的预备练习。”⑥Pierre Hadot,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什么是古典哲学?),Paris,Gallimard,1995,p.19.
古典哲学以一种或者另一种方式承认自从柏拉图的《会饮篇》开始,哲学家不是智者。同时,古典哲学不把自身视作一种纯粹的话语,一种智慧出现的时候才止住的话语。它既是话语又是生活方式,两者不可分割;话语以及生活方式以智慧为指向,却从未达到智慧。但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的话语确实是止于某些经验的门槛。这些经验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一种前兆。①Pierre Hadot,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antique(什么是古典哲学?),Paris,Gallimard,1995,p.20.
对Hadot而言,哲学话语与生活方式不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不是理论与实践。哲学话语直接具有实践功能,因为它对于听众或者读者能够产生影响。客观而言,对于这种将哲学视作生活方式的态度,具体的形上学已经给予一定的回应。《道论》第八章《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在分析了日常生活的有限性与终极关怀的无限性之后,从《中庸》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找出解决两者之间对峙的经典资源:“‘极高明’意味着走向作为终极存在的道,‘道 (导)中庸’则表明这一过程即完成于日常的实践过程。在这里,终极之道与人的日常存在表现出互补的向度:日常存在及其实践 (道中庸),赋予终极之道以现实的品格;终极之道则从行而上的层面给日常存在提供了超越自身的目标与方向。”②杨国荣:《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进一步讲,具体的形上学正是这种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之间的统一。杨国荣先生一再强调:“对‘形上之道’的追问与对经验世界、生活世界的关注并非彼此排斥,无论是哲学的研究,抑或哲学史的考察,都不应当忽视这一点。”③杨国荣:《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6页。
海德格尔在《什么是形而上学?》一书的导论《回归形而上学的基础》中说:“只要形而上学仅是不断地表征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它就无法立足于对存在本身的思考。哲学并不集聚到其基础上。因为形而上学之故,哲学不断地抛弃其基础。然而哲学又无法逾越其基础。”④Martin Heidegger,《Qu’est-ce que la métaphysique?》,in Questions I,II,p.25.出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海德格尔建立了指向“存在”而非“存在者”的基础本体论。尽管西方学者对海德格尔有种种批评⑤汉学家中对海德格尔进行过激烈批评的有毕来德 (Jean-François Billeter)。他在《驳于连》(Contre François Jullien)一书中,说他“完全无视于历史并将哲学家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见中译本《驳于连》(周丹颖译),高雄:无镜文化,2011年,第105页。,但中国哲学家始终对他予以相当的关注与同情。这大概跟本体论的困扰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以来不少哲学家以及哲学思潮都对形而上学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要么存而不论,要么漠然视之。但是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哲学成为中国大学的学科,中国的主流哲学家一直为本体论问题所困惑。冯友兰、金岳霖、牟宗三、冯契等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去构建本体论。他们的起点不同,有的从知识论或者认识论入手,有的从道德形而上入手,还有的,如成中英,则以《周易》哲学为“内源”发展出本体诠释学。就连认为“如何活”应该先于“为什么活”(道德等等)的李泽厚也提“历史本体论”“情本体”。不过李泽厚也认为:“哲学不是思辨的认识论或本体论,也不是语言治疗的技艺,而是在这个人生-世界中的‘以实事程实功’的自我建立。但这建立并不是康德的道德理性,而是包容量度更广的情感本体。”⑥李泽厚:《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页。在与李泽厚的对话中,杨国荣先生把“如何活”与“为什么活”分成两个层面来讨论,他认为从本体论讲,人“活着”先于对“如何活”与“为什么活”的思考,而从价值论的角度讲,“为何活”的问题逻辑地先于“如何活”的问题⑦杨国荣:《问题与视域——与李泽厚的哲学对话》,《认识与价值》附录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
从金岳霖到冯契,再从冯契到杨国荣,从本体论入手到认识论,再从广义认识论融入本体论,又从广义认识论到具体形上学,清华学派的哲学脉路得到了继承与发展。相对来说,形而上学包含了比本体论更广泛的内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哲学家的智慧探索的历程。
杨国荣先生的具体形上学内容广博,触及本体论、道德哲学以及意义理论等重大哲学分支,关涉古今中外哲学与哲学史中的最根本的命题与问题。我这里只是从其哲学沉思的连贯性以及具体的形上学与生活哲学的可能关系作了初步探讨,至于其他专题性的讨论,有待对《具体的形上学》三书的进一步阅读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