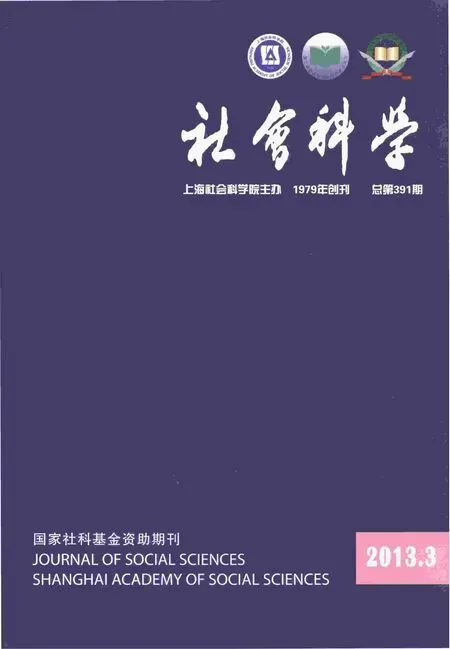“Shoah”的词源、内涵及其普及化——一项语义社会学的考察
艾仁贵
一、指称“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各种词汇
对于几千年屡遭迫害的犹太民族而言,其中最为苦难、最为惨痛的一章即是在二战期间遭遇的“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从广义上说,其时间跨度为1933—1945年,从希特勒上台开始,此为纳粹一系列暴力反犹活动的开端;从狭义而言,其时间跨度为1941—1945年,从提出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开始,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灭绝行动真正走向组织化、系统化。如何称呼与定义这场“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实际上,早在二战期间就有指称这一行动的不同词汇,分别来自纳粹、犹太世界及非犹太世界等阵营;而在犹太世界中,宗教与世俗力量对其的称谓也各自不同。为正本清源、厘清名实,本文拟对犹太世界指称这场大灾难的专门术语——“Shoah”(,意为“浩劫”,应译作“纳粹屠犹”)进行语义社会学的考究,以期探知这场空前大灾难概念的社会化进程及其与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的互动关系。除“Shoah”以外,学术界指称“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词汇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最后解决”(Final Solution)
“Final Solution”是一个纳粹术语,与之对应的德语词汇为“Endlösung” (含“斩尽杀绝”之意);该词最初来自纳粹的称呼,全称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 (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①François Furet,Unanswered Questions:Nazi Germany and the Genocide of the Jews,New York:Schocken Books,1989,p.182.。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制定从肉体上消灭欧洲所有犹太人的计划,通过实施这个灭绝性方案,旨在一劳永逸地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Judenfrage/the Jewish Question)①长期以来,德国社会内部滋生的反犹传统将犹太人的存在视为威胁德意志民族生存及健康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将之定义为“犹太人问题”。。当前学界对于“最后解决”被提出的年代尚有分歧,但根据学者格尔纳奇的研究,这一想法是由希特勒在1941年12月12日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随后德国军官及高层在1942年1月20日于柏林召开的万湖会议 (Wannsee Conference)上对这一计划的实施进行了系统的讨论,海因里希·希姆莱被指定为该计划的总负责人②Christian Gerlach,“The Wannsee Conference,the Fate of German Jews,and Hitler’s Decision in Principle to Exterminate All European Jews”,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70(Dec.,1998),p.790.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在1942年2月26日写给友人的信件中使用了这个表达形式——“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后来成为证实该计划存在的重要依据。。总之,该词体现出纳粹反犹的空前残酷性,通过对犹太人发动种族战争的形式以使困扰已久的犹太人问题永远不复存在。
出于国际道义以及实施效果的考虑,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对其灭绝犹太人的行动高度保密而几乎不为外人所知;直到战后对纳粹分子进行的纽伦堡审判才使有关“最后解决”的详细计划及实施情况为世人所知。战后初期纳粹德国史研究的最突出代表——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谈及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时多次使用了“最后解决”:“海德里希给陆军总司令部送去了一份关于‘清除’工作的初步方案。第一步工作是把犹太人全都赶到城市里去,因为在城市里比较容易把他们一网打尽加以消灭。他说,‘最后解决’需要隔一个时期才能实施,而且必须‘严守秘密’。但是所有看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将领都明白,所谓‘最后解决’就是斩尽杀绝。不出两年之内,当这项方案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最后解决’就成了德国高级官员之间提到战争期间纳粹这一惨绝人寰的滔天罪行的代号。”③William L.Shir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60,p.662;中文版参见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董乐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916页。随后普通大众也接受了这个称呼,并成为战后初期英美学界指称“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常用名词。
(二)“毁灭”(Hurban)
然而,“Hurban”并不代表犹太历史连续性的终结,相反它是对某个时期流放生活的审判与清算;因此极端正统派人士坚信它更是对犹太信仰的考验,凡信守与上帝契约者将会得到拯救:尤其当犹太人濒临集体性死亡的边缘之际,仁慈的上帝将以“大能的手”施行干预以实现对子民的救赎 (Geulah),历史上出埃及的壮丽神迹将再度重现⑧Gershon Greenberg,“Redemption after Holocaust According to Mahane Israel:Lubavitch 1940-1945”,Modern Judaism,Vol.12,No.1(Feb.,1992),pp.61-62.。为了牢记灾难,二战期间许多犹太教正统派的机构开展了所谓“毁灭研究”(Hurban Research);1946年又在德国创办意第绪语不定期刊物《最近的毁灭之后》(Fun letztn Hurban),主要用来记载这场大灾难见证者的证词①Philip Friedman,“The European Jewish Research on the Recent Jewish Catastrophe in 1939-1945”,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Vol.18(1948-1949),pp.189-192.。1947年,马克斯·考夫曼拉比推出畅销书《拉脱维亚犹太人的毁灭》(Churbn Lettland)②Max Kaufman,Churbn Lettland,Die Vernichtung der Juden Lettlands,Munich:Self-published,1947.,主要描述二战期间纳粹对于拉脱维亚犹太人的毁灭性打击,该书使“Hurban”一词与“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尽管“Shoah”一词在后来取代“Hurban”获得主导性的地位,但由于后者独特的神学内涵而仍为极端正统派频繁使用。
(三)“集体迫害”(Pogrom)
“Pogrom”一词最初来自俄语“погрóм”,主要指俄国政府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迫害、杀戮等行为,该词通常为东欧犹太人使用。其主要特征是政府发动、群众参与的有组织反犹攻击行为,《犹太百科全书》对该词进行了界定:“集体迫害在俄语中特指一场伴随有毁灭、掠夺、谋杀与强暴的攻击性行为,是由人口中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进行的恶行。……作为一个国际性词汇,‘集体迫害’一词在许多语言中被用来特别指称伴随有抢劫杀戮犹太人的攻击性行为。”③Yehuda Slutsky,“Pogroms”,in Fred Skolnik & Michael Berenbaum,eds.,Encyclopaedia Judaica,Second Edition,Vol.16,Jerusalem:Keter Publishing House Ltd.,2007,p.279.1938年11月9日由党卫军一手炮制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通常被视为纳粹集体迫害的代表④例如研究“水晶之夜”的代表作—— 《水晶之夜:1938年的集体迫害》,参见Kurt Pätzold&Irene Runge,Kristallnacht:Zum Pogrom 1938,Köln:Pahl-Rugenstein,1988。,而经常与“pogrom”连在一起使用—— “Pogromnacht”。随着反犹暴力的不断升级,该词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展,约翰·克里尔指出,“到20世纪,‘pogrom’一词在英语中已经成为指称一切直接针对犹太人的集体暴力之通用词汇”⑤John Klier,Russians,Jews,and the Pogroms of 1881-1882,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58.。
战后初期,有些西方媒体使用“pogrom”一词来形容这场大灾难,在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中,集体迫害就被用来形容“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在许多场合,(美国首席律师罗伯特·H.杰克逊)与其他起诉人使用‘pogrom’一词来形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⑥Lawrence Douglas,“The Shrunken Head of Buchenwald:Icons of Atrocity at Nuremberg”,in B.Zelizer,ed.,Visual Culture and the Holocaust,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01,p.286.汉娜·阿伦特在1963年的《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强调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是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集体迫害:“迄今为止所有参与者都没有获得关于奥斯维辛真正恐怖的清楚理解,它与以往所有暴行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它在控方与法官看来似乎并不是犹太历史上最为恐怖的集体迫害 (pogrom)。”⑦Hannah Arendt,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First edition in 1963,New York:Penguin,1994,p.267.总体来看,与其他指称纳粹屠犹的词汇相比,“pogrom”的程度要轻一些,而没有体现出这场灭绝暴行的空前规模与惨烈程度。
(四)“大屠杀”(Holocaust)
“Holocaust”一词最初源自《希伯来圣经》中的“olah”(意为供奉)⑧Jon Petrie,“The Secular Word HOLOCAUST:Scholarly Myths,History,and 20thCentury Meanings”,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Vol.2,No.1(2000),p.31;Zev Garber & Bruce Zuckerman,“Why do We Call the Holocaust‘The Holocaust’?An Inquiry into the Psychology of Labels”,Modern Judaism,Vol.9,No.2(1989),p.199.,后来七十士译本将之转译为希腊语 “òλóκαυστοç/holókaustos”,“hólos”本意为全部、“kaustós”本意为焚烧,因此合起来意为“献祭所用的全部祭品”⑨用“Holocaust”来指称惨遭纳粹屠戮的六百万犹太人,遭到一些犹太学者的质疑。沃尔特·拉克强调以该词来指称纳粹灭绝暴行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它暗示着六百万犹太遇难者即是献给上帝的“焚烧的祭品”:“纳粹的目的并非进行这种形式的献祭,犹太人的地位也并非那种仪式性受害者。”参见 Richard Evans,In Hitler’s Shadow,New York:Pantheon,1989,p.142。。 “Holocaust”的正确译法为“大屠杀”,它不但指代在“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中丧生的六百万犹太人,而且还包括同样死于纳粹迫害的大约五百万非犹太遇难者;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对其有一番详细的定义:“大屠杀 (Holocaust)特指20世纪历史上的一场种族灭绝事件。这一事件是1933—1945年间由纳粹德国及其合作者操纵的、由国家主持的、有计划地迫害与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行动。犹太人是主要的牺牲品——600万人被杀害,吉普赛人、有生理缺陷者和波兰人也因种族或民族的原因而被列为毁灭与致死的目标。另有数百万人,包括同性恋、耶和华见证会信徒、苏联战俘和持不同政见者等,也在纳粹暴政之下遭受了严酷的迫害并被致死。”①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Teaching about the Holocaust:A Resource Book for Educators,Washington,DC:Center for Advanced Holocaust Studies,2001,p.3.
一般认为,美国犹太历史学家鲁弗斯·利尔斯在1949年首次将该词与纳粹屠犹联系起来②Rufus Learsi,Israel: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Cleveland & New York: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49,p.645.;但如科尔曼注意到的:“在1949年,英语中的‘Holocaust’并不具有今天 (1972年)的内涵。学者与作家们普遍使用‘持久的集体迫害’(permanent pogrom)……或‘最近的劫难’(recent catastrophe)、或‘灾难’(disaster)、或‘这场灾难’(the disaster)。”③Gerd Korman,“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History Writing”,Societas,Vol.2(1972),p.256.著名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1961年出版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被认为是揭开战后大屠杀研究序幕的经典之作,而在该书中并无一处使用“Holocaust”一词④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London:W.H.Allen,1961.。但就在同年于以色列进行的埃希曼审判成为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有学者这样强调这场审判的重要意义:“这是一场有关‘Shoah’的审判,它也是将六百万欧洲犹太人屠杀的意识带给本土以色列与更广范围世界的青年在自我意识上的尝试。”⑤Tim Cole,Selling the Holocaust:From Auschwitz to Schindler,New York:Routledge,1999,p.7.埃希曼审判直接导致了大屠杀意识的上升,这一词汇也获得了广泛的认同,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被人们用来作为专指这场灭绝暴行的英文名词:“到1967年,‘Holocaust’由于其巨大而惊人的回响,已经成为犹太人讨论与认同的核心词汇。”⑥Paul Breines,Tough Jews:Political Fantasies and the Moral Dilemma of American Jewry,New York:Basic Books,1992,p.71.诺拉·列文的《大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就是突出代表,参见Nora Levin,The Holocaust: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ry,1933-1945,New York:T.Y.Crowell,1968。此后, “Holocaust”成为希伯来语“Shoah”的英文对应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
二、《希伯来圣经》中的“Shoah”
事实上,“Shoah”一词并非20世纪的发明,早在《希伯来圣经》中就已被使用;它总共出现12次,通常指代一场恐惧可怕的与不可预料的个体或集体灾难。它往往与上帝的报复和惩罚联系在一起,以战争或天灾的形式体现出来,以作为对人悖逆行为的应有惩罚。而且它的发生是一种突如其来、无法预料的结果,从而给个人或群体带来巨大的震惊恐慌;由于人们完全无法预见灾难所带来的结果,因而一旦发生,受害者便陷入惶恐无措、进退失据的境地。通过对《希伯来圣经》中“Shoah”一词用法的探讨,可以发现它在后来被用于指称“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若干痕迹。就具体的经文篇章内容而言,其用法及侧重各有不同:
首先,“Shoah”强调了灾难的降临及其突然性、破坏性,该词的首要性质即是一场降临到人身上的大灾难。在《以赛亚书》中,它指代末日审判时对行不义之人的惩罚:“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⑦《以赛亚书》10:3。;在《诗篇》中,被用于大卫对仇敌的诅咒:“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⑧《诗篇》35:8。。这种大灾难不同于一般的恶性事件,因而它的降临通常带来毁灭性的严重后果:“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⑨《以赛亚书》47:11。;“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10]《箴言》3:25。。而且更重要的是,“灾祸”、“毁灭”这些词经常与“忽然”连在一起使用,以此强调灾难降临的突如其来与不可预测。
其次,“Shoah”指代灾难降临的独特方式,它通常以“暴风”的隐喻形式体现出来,这也与其突如其来的特征相吻合。在《箴言》中,它用在因自然或恶行而招致惩罚的个体身上:“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①《箴言》1:27。在《以西结书》中,这种惩罚对象扩展到全体以色列人,以色列的敌人歌革作为雅卫的工具将对以色列人的悖逆行为给予突然的打击:“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许多国的民必如暴风上来,如密云遮盖地面。”②《以西结书》38:9。由此可见,以“暴风”作为比喻重在强调灾难降临的迅猛异常以及带来的巨大心理震撼。
第三,“Shoah”还被用来形容末日来临前的萧条景象,而这种状况正是对悖逆上帝者的应有惩罚。在《西番雅书》中,该词指代末日来临前的恐怖异象,上帝将毁灭以色列人中的有罪者:“雅卫的大日临近……那日,是忿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③《西番雅书》1:14-15。在《约伯记》中,它被用来描绘没有生机的贫瘠之地,而罪与罚仍是其中心主题: “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④《约伯记》30:3。;“使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⑤《约伯记》38:27。。
最后,“Shoah”直接指代灾难导致的恐怖场景,即面临灾难的最高顶点——死亡。约伯在向上帝申诉恶人对其的致命攻击时说:“他们来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⑥《约伯记》30:14。在《诗篇》中,该词被用来指代仇敌对大卫的攻击以及大卫对仇敌的诅咒:“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⑦《诗篇》35:17。;“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⑧《诗篇》63:9-10。。在此,敌人的攻击是致命的,它不同于一般性的仇恨憎恶,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灭绝行为。
三、“Shoah”一词的现代运用与广泛普及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知,“Shoah”在神学内涵上要比“Hurban”逊色不少:前者几乎从来没有与圣殿毁灭联系在一起,而在犹太传统中经常被用来指称灾难的词汇是“Hurban”。圣经时代以后, “Shoah”已很少为犹太人所使用,更无需说用来指称灾难以及与之类似的概念。自1933年希特勒上台推行疯狂的反犹暴行伊始,许多犹太人就已对当前面临的这场空前大灾难进行了分析和探讨⑨Philip Friedman,“The European Jewish Research on the Recent Jewish Catastrophe in 1939-1945”,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for Jewish Research,Vol.18(1948-1949),pp.179-211.;当时为流散地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经常用来指称此次大灾难的主要词汇仍是“Hurban”,这仍然是在传统的框架中理解最近发生的这场大灾难。但是,随着灾难规模的发展与主导力量的改变,对于这场灾难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转变。更重要的是,由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最后解决”计划一直处于高度保密状态,犹太人对于这场灾难的空前规模以及恐怖程度的真正认识,要到战争结束后才能完全理解;而这种局限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这场灾难的认知及其概念的演变。
在纳粹开始入侵波兰、大举迫害犹太人的1939年,“Shoah”一词已开始被人们用来描述当前的艰难处境。同年在巴尔干建立的援助波兰犹太难民的犹太代办处便在一般意义上使用了该词:“波兰人与那些居住在当地的犹太人正遭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 (Shoah)。波兰已经被希特勒的德国摧毁,而其残余部分则为苏联所瓜分。”①Dalia Ofer,“Linguistic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Palestine and Israel,1942-53”,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31,No 3(July,1996),p.570.在此,“Shoah”不仅指犹太人的流离失所同时也指波兰人的惨痛遭遇。
1940年,一本题为《波兰犹太人的浩劫》(The Shoah of Polish Jewry)的论文集在巴勒斯坦出版,其中包括许多曾在波兰居住而于战争爆发后离开者的证词与回忆文章②Orna Kenan,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Israeli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1945-1961,New York:Peter Lang,2003,p.7.;其中的一位作者、华沙犹太委员会的领袖阿波林埃勒·哈特格拉斯 (Appolinaire Hartglass)根据自己的多年经历及亲身观察,在前言中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这场战争持续许多年,纳粹通过对波兰人与犹太人的系统灭绝将使波兰变成犹太民族的坟墓③Dalia Ofer,“Linguistic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Palestine and Israel,1942-53”,p.569.。由此可知,“Shoah”一词已被用来指代纳粹正在进行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行为;由于该词的使用者主要是波兰犹太人,故而也将波兰人包括在这一概念之内。
到1942年,该词也为巴勒斯坦的一些犹太作家与诗人所用,它更多的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恐惧心理与绝望情绪;著名诗人扫罗·切尔尼克夫斯基 (Saul Tchernichowsky)用它来表达极度恐惧的处境以及犹太人在战后将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与政治命运④Dalia Ofer,“Linguistic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Palestine and Israel,1942-53”,p.571.。尽管在当时的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还没有人将“Shoah”理解为整个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也尚未设想由于纳粹屠杀机器而致使欧洲没有犹太人的情形;但“Shoah”一词已被用来指称当前纳粹迫害欧洲犹太人的行动表明,人们力图用一个明确的词汇来描绘一种不可忍受的状况,一些犹太人已经逐渐意识到当前的灾难不同于此前的一切灾难。
面对纳粹反犹暴行,当时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主要反应并非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积极的营救行动,而是呼吁人们参加驻巴勒斯坦英军中的犹太部队。这种对欧洲犹太人命运状况的漠不关心与有限理解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Hurban”而非“Shoah”占据着当时公众话语的主导地位⑤Idit Gi,l“The Shoah in Israeli Collective Memory:Changes in Meanings and Protagonists”,Modern Judaism,Vol.32,No.1(Feb.,2012),p.78.。时人普遍认为,发生在20世纪的“Shoah”是犹太历史上遭受的反犹主义迫害的延续;因而,把它与1492年西班牙大驱逐、1881年沙俄集体迫害等历史上的大灾难放在一起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世界尚不知道等待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将会是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1943年,随着纳粹集中营以及华沙隔都起义的消息传至巴勒斯坦,有关纳粹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情况逐渐清晰起来,这促使人们对屠杀重要性的理解不断加深,其直接结果就是“Shoah”的使用逐渐普遍起来。
到战争临近结束之时,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意识到,纳粹几乎成功地达到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邪恶目的,它与此前一切反犹暴行的不同也变得更加显著起来,由此人们更加倾向于使用“Shoah”以区别于此前的所有灾难。
但只有到战争结束、真相大白后,犹太人才真正了解纳粹灭绝犹太人的全盘计划。战争结束后由盟国进行的纽伦堡审判使许多不为人知的纳粹反犹暴行公诸于世,特别是“最后解决”计划的揭露更是使世人首次了解到纳粹毁灭欧洲犹太人的真正企图,从而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于这场大灾难的概念认知。到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纳粹制定了系统而完整的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政策,而这直接促使人们对屠杀的理解上升到一个崭新的层次。因此,1946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点,“Shoah”一词由此开始与所有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正式联系起来。同年,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有人提议建立“Yad Vashem”(亚德·瓦谢姆)①在希伯来语中,“yad”(memorial/hand)字面上意为手指,通常象征着一座纪念碑;“shem”(name)意为名字。“yad vashem”作为一个词组最初出现在《以赛亚书》,意在强调给予与上帝联合、信守契约的人记念及名号以示永存不忘:“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 (人)……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记念、有名号(yad vashem/a memorial and a name),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56:4—5)的机构以纪念被纳粹灭绝的几百万欧洲犹太人,由此将指代这一事件的概念使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②建立纪念遇难欧洲犹太人机构的想法最初由莫迪凯·舍纳哈比在1942年提出,参见Orna Kenan,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Israeli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locaust,p.43。。1947年7月13—14日,希伯来大学在耶路撒冷举办了首届世界犹太研究会议 (WCJS),此次规模空前的学术会议将主题定为“对我们时代的浩劫与英雄主义的研究”(Research on the Shoah and Heroism in Our Time),表示要研究最近在欧洲大地发生的“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Shoah uGvurah),从而在“Shoah”一词的推广过程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自此之后不少学者在论著中提及有关欧洲犹太人的毁灭时经常使用“Shoah”一词来称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正在进行一场争取建国的艰苦努力,而武装斗争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这种政治现状投射到学术研究之上,即是对于“Gvurah” (即英雄主义)一词的高度凸显。这次会议多次将“Shoah”与“Gvurah”连在一起使用,实际目的在于强调二战期间犹太人从事的反抗活动,以为当前犹太人的斗争树立榜样。
“Shoah”首次进入以色列官方视线之中是在1951年4月,当时以色列公众围绕为遇难欧洲犹太同胞设立纪念日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4月12日,议会正式决定将尼散月27日作为“纳粹屠犹与隔都起义纪念日” (Yom ha-Shoah u-Mered ha-Geta’ot/The Shoah and Ghetto Uprising Remembrance Day)③James E.Young,“When a Day Remembers:A Performative History of Yom ha-Shoah”,History & Memory,Vol.2,No.2(Winter,1990),p.60.。这个日期的确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纪念华沙隔都起义,意在凸显二战期间的犹太抵抗活动,将之提高到与纳粹灭绝行为同等的地位;由于以色列建国初期对流散犹太人的消极态度,这个节日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具体开展④Roni Stauber,The Holocaust in Israeli Public Debate in the 1950s:Ideology and Memory,trans.Elizabeth Yuval;London:Vallentine Mitchell,2007,p.33.。但它的重要后果是,“Shoah”作为指称“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专有名词首次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⑤1959年4月7日,以色列议会又通过法案将之更名为“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日”(Yom ha-Shoah veha-Gvurah/The Shoah and Heroism Remembrance Day)。。
然而,使“Shoah”成为指代“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的法定专有名词是1953年8月19日以色列议会颁布的“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纪念法” (Yad Vashem,rashut ha-zikaron la-Shoah vela-Gvurah/The Law of Remembrance of the Shoah and Heroism),以此为标志获得了最终的合法与正统地位。这项法律规定成立名为“亚德·瓦谢姆”的纳粹屠犹殉道者与英雄纪念机构,赋予它建造一座国家纪念工程,搜集相关证据并“向世人提供教训”;同时决定为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设立纪念日,以便“为其英雄与遇难者提供一个整体性记忆”⑥Jackie Feldman,“Between Yad Vashem and Mt.Herzl:Changing Inscriptions of Sacrifice on Jerusalem’s‘Mountain of Memory’”,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Vol.80,No.3(Fall,2007),p.1152.。在此,“Shoah”作为指称这场大灾难的专有名词正式升格为国家法律,随后凭借国家权力渗透到各个角落,获得了无可质疑的合法地位,从而将创伤记忆的国家化、政治化推向顶点⑦实际上,使“Shoah”一词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事件是1985年克洛德·兰兹曼根据同名剧本改编而来的电影《浩劫》(Shoah),公映后迅速取得巨大成功。参见Shoshana Felman,“Film as Witness:Claude Lanzmann’s Shoah”,in Geffrey H.Hartman,ed.,Holocaust Remembrance:The Shapes of Memory,Oxford:Basil Blackwell,1994,pp.90-103。。
四、英雄主义的道德内涵与创伤记忆的国家化
研究“Shoah”一词现代意义的学者发现,该词在巴勒斯坦犹太社团政治与思想论述中的出现,既与1939年之前德国犹太人的命运也与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其他犹太人的处境密切相关①Dalia Ofer,“Linguistic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in Palestine and Israel,1942-53”,p.569.。“Shoah”一词的现代使用不仅体现了犹太人在其所有历史经验中对此次灾难的不同理解,而且反映了犹太人在记忆这次空前大浩劫上所付的巨大努力,以使之区别于此前的一切灾难;此外,与《希伯来圣经》相比,该词在其现代使用过程中,仍然保留了难以理解的突如其来与恐怖震惊的传统意义,而罪恶与惩罚的神学概念已经不复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巴勒斯坦犹太社团的世俗领导反对这种神学解释,而且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愿接受对该词的世俗化理解②实际上,有些极端正统派人士一直拒绝使用“Shoah”,而坚持使用“Hurban”来指称这场大灾难。伊扎克·胡特纳拉比即是典型代表:“‘Shoah’一词是否可以接受?答案是显然不。就像英语中的‘Holocaust’一样,‘Shoah’一词在希伯来语中意味着一场孤立的灾难,与此前及此后的所有事物完全无关,就如同一场地震或海啸。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径完全不同于托拉对犹太历史的看法;欧洲犹太人的毁灭 (Hurban)是我们历史中的必要部分……我们面临着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创建者的错误,他们觉得有必要因为它的比例与范围而为欧洲犹太人的毁灭寻找一个新的名词。”参见 Yitzchak Hutner,“‘Holocaust’—A Study of the Term and the Epoch It’s Meant to Describe”,The Jewish Observer,trans.and ed.Chaim Feuerman & Yaakov Feitman,(Oct.,1977),pp.8-9。。该词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广泛普及与官方化的过程表明,“纳粹灭绝犹太人行动”不仅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死亡、大屈辱、大劫难,而且还反映出这场大灾难对于犹太人的影响及其如何被内在化及概念化的特点;实际上,“Shoah”作为一种政治化的修辞策略,在借助权力实施教化、控制之目的的同时,本身也成为被权力规训、驯化的对象。
“Shoah uGvurah”的连用代表着一个新概念的产生,这个词组为纳粹屠犹带来的空前灾难意识深入公众观念发挥了重要作用。透过这个词组,不仅体现了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种族反犹动机,而且暗示着犹太人对此灭绝行为的回应、努力及纪念;如果说“Shoah”代表着困境与悲剧本身,而“Gvurah”则表达了对这一危机的应对与反抗。约瑟夫·耶鲁沙尔米指出,“集体记忆”概念的希伯来语形式—— “Zakhor”,蕴含着犹太传统对于灾难性或破坏性历史事件的典型回应模式,即通过记忆来克制创伤、恢复秩序③Yosef Hayim Yerushalmi,Zakhor:Jewish History and Jewish Memory,Seattle &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2,p.99;Saul Friedlander,“Trauma,Transference and‘Working through’i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Shoah’”,History & Memory,Vol.4,No.1(Spring-Summer,1992),p.42.;哈西德派创始人贝施特也曾不止一次地告诫:救赎的秘密在于记忆,而遗忘必然导致流放。实际上,纳粹屠犹与英雄主义的结合进一步扩充了“Shoah”的概念,使之不仅指代来自纳粹的恐怖行径,而且包括犹太人对其的思考与回应;换言之,它蕴含着抵抗行为,更准确地说,它可以被视为对缺乏犹太抵抗运动的反击,从而对许多流散犹太人提出了积极的道德要求与奉献意识。
“Shoah”的现代使用还反映出建国前后以色列社会对于流散地的排斥。长期以来,犹太复国主义极力推崇反抗异族压迫、从事武装斗争的犹太战士,奉行“否定流散地”(Negation of the Diaspora)的观念,认为大流散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屈辱史,对此著名学者萨洛·巴龙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描述—— “犹太史上的流泪概念”(Lachrymose Conception of Jewish History)④有关这个概念的详细内容,参见 Salo Baron,“Newer Emphases in Jewish History”,in idem,History and Jewish Historians,Philadelphia: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1964,p.96.。在这种武装反抗的英雄主义主流话语下,土生土长的“萨布拉”对数百万欧洲犹太人“像羔羊一样走进屠场”的软弱举动表示困惑不解,认为他们是犹太人的耻辱;另一方面,高度赞扬纳粹屠犹期间的武装反抗并将之与流散犹太人区别对待:“游击战士与隔都反抗者因而从‘纳粹屠犹’中脱离开来,以作为在流散地与现代以色列之间搭起的一座象征之桥。与马萨达及特尔哈伊的守卫者一道,他们成为以色列英雄般过去的一部分。与之相反,纳粹屠犹的其他经历被降格为流散时期并与‘他者’相连,被称作是屈辱的流散犹太人。”⑤Yael Zerubavel,“The Death of Memory and the Memory of Death:Masada and the Holocaust as Historical Metaphors”,Representations,No.45(Winter,1994),p.80.
更重要的是,“Shoah”的广泛普及与以色列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相互促进、互为表里。纳粹屠犹与以色列建国在时间序列上的靠近,使得“从浩劫到重生”(Me-shoah le-tekumah)在建国前后的主流话语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①Dalia Ofer,“The Strength of Remembrance:Commemorating the Holocaust During the First Decade of Israel”,Jewish Social Studies,Vol.6,No.2(Winter,2000),pp.38-40.,这个连用扎根于“灾难与救赎”的犹太传统主题,从而表达出大灾难后犹太人获得奇迹般拯救的思想。可以说,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重要时期,词语推广与认同建构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一方面,“Shoah”的话语凭借国家权力强制渗透到以色列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而成为以色列人集体认同的核心要素—— “奠基神话”(founding myth),在此创伤记忆国家化过程中获得了无比的神圣地位;同时,以色列国通过对创伤记忆的控制、管理、运用,特别是建立亚德·瓦谢姆纪念馆为国家记忆场所、确立纳粹屠犹纪念日为国家法定节日,通过将纳粹屠犹遇难者内在化为以色列人,从而在世界犹太人中间获取对于“Shoah”话语的主导权。正如奥默尔·巴尔托夫指出的:“(以色列官方一再宣称)如果在纳粹屠犹之前存在一个犹太国家,种族灭绝将不会发生;既然种族灭绝已经发生,那么就必须要有一个犹太国家。正如这个国家可以追溯至纳粹屠犹一样,纳粹屠犹同样也属于这个国家:几百万受害者都是潜在的以色列人……更为甚者:所有以色列人都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潜在受害者。”②Omer Bartov,Murder in Our Midst:The Holocaust,Industrial Killing,and Representat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