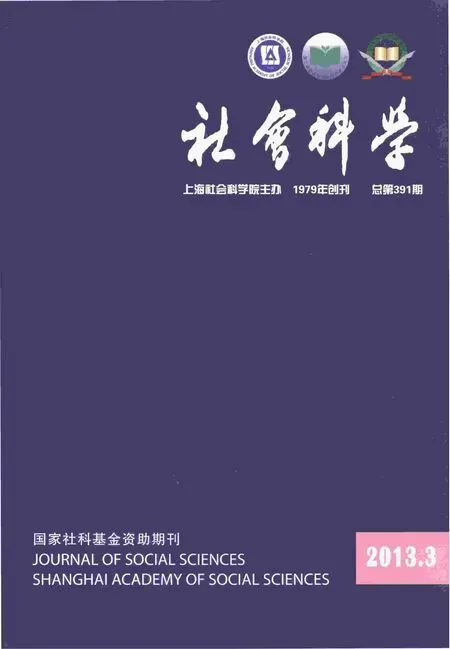东西交汇下的晚清冒险小说与世界秩序*
李艳丽
晚清被称为中国小说史上最为繁荣的时代,谴责小说、政治小说、写情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女英雄小说……每一种类型都可以找出它之所以流行的理由,譬如针砭时弊、提高文学的地位、文学救国、自由婚恋意识的觉醒、倡导新女性,等等,这使得处于古今变动、中西交汇的转换期的晚清小说显得异彩纷呈。
然而,晚清小说中还有一种“冒险小说”,却不为人知。此名称常常出现于晚清小说题目的旁边①或称“角书”。此种标记不见于古代中国小说,追索起来,似乎是从梁启超引进政治小说、创办《新小说》开始的。梁氏与日本渊源深厚,这种标示大约也是受了日本的影响。。冒险小说之所以给人隔膜感,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国家情势与“冒险小说”不相匹配——对外,受西方列强欺凌,国人正奋起“救国”“保种”;对内,则以科学启蒙为要事,而更重要的原因似乎是,传统社会崇尚文治、以文为美,这与具有冒险精神的勇武,即“蛮”“力”,似乎也是相对立的。阿英著名的《晚清小说史》中甚至连“末流”中也没有列入冒险小说。可是,1903—1907年间的确出现了很多种冒险小说,先有翻译后有创作。
晚清翻译小说来源驳杂,根据笔者的调查,晚清所译冒险小说主要来自日本和欧美,前者可以以“殖民冒险”的军事科幻物语概括,后者则体现“科幻冒险”的特征。那么,这其中的交集是否仅仅局限于“冒险”?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隔海遥望的西方,跨越了“海洋”,将“近代”的种子撒播在了晚清的土地上。以《鲁滨孙飘流记》为代表的西方小说、以押川春浪的海洋军事小说为代表的日本小说自不必说,纵是非洲开拓、澳洲殖民的小说也都是跨海的冒险。受了这些影响的晚清,在自创小说中也体现出了“海洋”的特征。
一“冒险小说”的含义辨析
(一)何谓“冒险小说”?
在阿英《晚清小说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都没有关于冒险小说的叙述,中国古代小说中似乎也没有这一类别,更无专门定义。
从字面上来看,“冒险”含有对未知领域进行开拓的意思。从贬义上来说,“冒险”是思考欠成熟的“鲁莽”行为,类似“赌博”。从褒义上来说,“冒险”具有创新、异想天开之意,可与“科幻”(科学)相联系。但是,如何定义晚清冒险小说,还需要仔细甄别。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很多鬼怪妖精的故事,体现了丰富的想像力;古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士也具有闲云野鹤、放浪不羁的特点,这些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冒险”有一些契合之处,但并不等同。
(二)商务印书馆的划分
1903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刊印《说部丛书》。在四集系列初集100种中,有一分类为“冒险小说”,计有13种作品。根据小说情节,笔者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勇闯险境类:《小仙源》(瑞士·戈特尔芬美兰女史著,商务印书馆译,1905)①Johann David Wyss,Der Schweizerische Robinson.1812-27.、《鲁滨孙漂流记》(英·笛福著,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蛮陬奋迹记》(英·特来生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1906)、《金银岛》(英·司的反生著,商务印书馆译,1904)②即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森,他撰写了大量散文、游记、随笔、小说等。该作品于1883年出版,发表后被誉为儿童冒险故事的最佳作品,广为流传。、《雾中人》(美·哈葛德著,林纾、曾宗巩合译,1906)③Henry Rider Haggard,The people of the mist.1894.、《旧金山》(美·诺阿布罗克士著,金石、褚嘉猷合译,1906)。
·科幻旅行类:《世界一周》(日·渡边氏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1907)、《环游月球》(法·焦奴士威尔士著,商务印书馆译,1904)。
·殖民拓荒类:《秘密电光艇》(日·押川春浪著,金石、褚嘉猷合译,1906)、《澳洲历险记》(日·樱井彦一郎著,金石、褚嘉猷合译,1906)④Lady Broome(ed.),Harry Treverton.1889。樱井彦一郎译《殖民少年》,(日本)文武堂、博文馆1901年版。、《鲁滨孙漂流续记》(英·笛福著,林纾、曾宗巩合译,1906)、《斐洲烟水愁城录》 (英·哈葛德著,林纾、曾宗巩合译,1905)⑤Henry Rider Harrgard,Allan Quatemain.1887。、《复国轶闻》(英·波士俾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1907)⑥Guy Newell Boothby,A sallor’s bride.、《冰天渔乐记》(英·经司顿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1908)、 《梦游二十一世纪》 (荷兰·达爱斯克洛提斯著,杨德森译,1903)⑦Dr.Pesud Dioscorides,Annonno 2065.,Een Blik in de Toekomst.1865。杨德森依据英译本Dr.Alex.V.W.Bikkers转译。。
商务印书馆在刊行小说之前,一般都会在晚清著名报刊《申报》上做广告。有了这些宣传,想必冒险小说已经受到了广泛阅读。上面的这十三种作品的差异也显而易见,而且,晚清译介的冒险小说并不局限于此。那么,这些不同来源不同风格的作品,何以都被归类为“冒险小说”?
1902年,《新小说》刊登的启示称“冒险小说”是“如《鲁滨逊漂流记》之流,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⑧梁启超:《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十四号1902年。。1905年,小说林社刊登的征文启示称“冒险小说”是“伟大国民,冒险精神,鲁滨孙欤?伋朴顿欤?”⑨小说林社:《车中美人》之《谨告小说林社最新之趣意》,小说林社1905年版。《小说林》把小说细致具体地划分为历史小说、地理小说、滑稽小说等12类。
《新小说》和《小说林》是晚清有名的小说杂志,可以说他们的选题选材就是近代小说的风向标。二者不约而同选择的“鲁滨孙”当然是冒险小说的突出主题。那么,“鲁滨孙”在西方是如何被解释的?它是否能够涵盖“冒险小说”?
(三)西方:航海 +科幻
关于“冒险小说”,牛津词典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及剑桥词典 (Cambridge Dictionaries)中都没有专门的解释。牛津词典对《鲁滨孙漂流记》也未作详细解释,仅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英国第一部小说。《金银岛》在牛津词典中被解释为“孩子们的探险故事”。哈葛德被解释为“一个写作刺激的冒险小说的英国作家”。至于鼎鼎大名的法国作家凡尔纳,基本可以界定为“科幻小说之父”,但词条中没有收录。参照上述商务印书馆的出版情况,笔者将晚清引进的西方冒险小说定义为“科幻游历冒险小说”。
关于凡尔纳一类“科幻小说”的主题,先行研究充分,此处不再赘言。“游历冒险小说”在欧洲的影响深远,其发源可以追溯到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不过,早先的流浪汉小说是以底层流浪汉 (类似于地痞无赖之流)如何在社会中谋生为主要题材的,到19世纪末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研究者认为,“文艺复兴至18世纪间欧洲小说的创作中大多将游历冒险人物作为主人公,这里面既有文艺复兴后人们对自我的发现、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的背景,也有中国三大发明传入欧洲后对航海、印刷和军事技术的巨大促进。地理探险的重大突破,开辟出广阔的海外市场。新世界的发现与追求财富的欲望成为这一时期的时代特征”①亢西民:《欧洲游历冒险小说简论》,《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可见,是航海技术的发明催生了冒险小说,然而,仅仅局限于此的话,冒险小说只能流于海外新大陆的发现一类,也无法满足冒险家的野心。于是,军事技术的发达加速了冒险小说的发展,也加剧了世界各国对权益的争夺。
《鲁滨孙漂流记》是冒险开拓小说的典范。结合其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冒险小说”来看,“新时代的代表为主人公的冒险探求活动”成为晚清冒险小说的重要主题。广为人知的林译“哈葛德冒险与神怪小说”就是一例②郝岚:《林纾对哈葛德冒险与神怪小说的解读》,《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哈葛德 (1856—1925),被认为是历史和传奇小说的多产作家,以写非洲故事得名。在中国,哈氏作品被认为神怪诡异,具有比较浓厚的冒险精神、个人英雄色彩。虽然在林译小说中哈氏的作品为最多,但无论是针对哈氏或是林纾,这些作品得到的评价都不高。前者被视为二三流的作家,后者被认为翻译了香艳作品而有失稳重。长期以来,晚清冒险小说湮没无闻的原因或许可以从这种评价中寻得端倪。有趣的是,日本研究者称哈氏为“幻想小说”③[日]武田雅哉、林久之:《中国科学幻想文学馆》(上册),(日本)大修馆书店2001年版,第66页。。在晚清,他与凡尔纳被统归于冒险小说。
(四)日本:航海 +军事
作为晚清冒险小说的一个重要分支,来自日本的那部分冒险小说又显示出另一种特色,即具有较浓厚的军事色彩。
押川春浪 (1876—1914)是晚清小说翻译者偏爱的一个作家。在日本,他的作品被称为“军事科学小说”“武侠小说”。包括《海底军舰》在内,他连续发表了《武侠日本》《新造军舰》《武侠军队》《新日本岛》《东洋武侠团》六部作品,构成系列军舰物语。
《海底军舰》描绘了一个名为“柳川龙太郎”的旅行家经历的一连串冒险活动。龙太郎乘坐“弦月丸”从意大利归国途中,在印度洋上遭遇了海盗船的袭击,“弦月丸”沉没。龙太郎漂流到一个叫做“朝日岛”的孤岛,在那里遇到了正在建造海底战舰的樱木海军大佐一行。于是,龙太郎参与了“自动冒险铁车”的制造。三年后,海底战舰完成,却遭遇了大风暴,导致作为战舰动力的药液泄露,急需到印度Colombo调取。于是,龙太郎跟武村下士乘坐气球前往。途中遇怪鸟袭击落入大海后,被偶然路过的巡洋舰“日之出”救下。险象环生,船员们最终在朝日岛上建立了“武侠”团体。
押川春浪在明治乃至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时期都深受读者的欢迎,而这一热潮的出现自然与当时的国情密不可分。日本处于岛国位置,国土资源并不丰厚,自古以来深受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即便在江户锁国时代,也依旧开放了长崎港口,吸收中国及荷兰等外国文化。明治开化后,日本迅速实现了近代化,经济及军事实力急剧增长。及至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的两场胜利,更刺激了日本向海外开拓的雄心。
押川春浪的这六部作品都被晚清引进,深受译者徐念慈的推崇。徐念慈说,日本国民具有武侠的气概、英雄的志气,而日本与中国的“文野之别,不容讳言”①觉我:《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九期1908年版,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页:“日本蕞尔三岛,其国民咸以武侠自命,英雄自期,故博文馆发行之押川春浪各书,若《海底军舰》,则二十二版,若《武侠之日本》,则十九版,若《新造军舰》(即本报所译之《新舞台》三)、《新日本岛等》,一书之出,争先快睹,不匝年而重版十余次矣。以少我于十倍之民族,其销书之数,千百倍于我如是,我国民之程度,文野之别,不容讳言矣”。(福泽谕吉等人就将甲午战争称为“文野的战争”),并在自己创作的小说中也贯彻了武士道精神②铁:《铁瓮烬余》,《小说林》第十二期1908年版,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356页。。不过被日本人称为武侠的押川作品,在《空中飞艇》的译者“海天独啸子”看来却是科学小说③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明权社1903年版,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06页:“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第107页:“是书为日本押川春浪君所著,以高尚之理想,科学之观察,二者合而成之”。。这也体现了晚清小说的多重性格。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澳洲历险记》的作者樱井彦一郎 (樱井鸥村,1872—1929),他是日本著名的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教育家和实业家。1901年,时年29岁的樱井创刊了《英学新报》,出版了《世界冒险谭》系列翻译小说。其中,他翻译的《二勇少年》《澳洲历险记》《朽木舟》《航海少年》都被晚清引进。1908年,樱井将新渡户稻造 (1862—1933)的“Bushido,the soul of Japan”翻译为《武士道》出版。这与押川的“武侠”精神可以说是相辅相成。樱井鸥村的胞弟樱井忠温,是一个陆军少尉,曾参战旅顺战役。他负重伤归国之后,以此为经验创作了《肉弹》,获得高度评价,甚至因此受到明治天皇的接待, 《肉弹》被翻译成十几国语言④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有详细论述。董炳月:《“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1909年黄郛翻译为《旅顺实战记》。
(五)晚清接受“冒险小说”的基盘——航海 +科技
通过上述整理,晚清冒险小说与中国古代神怪小说、侠义小说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首先,神怪小说的发达与传统民间故事的联系较大,包含了民俗上的认同,也有一种对超自然“迷信”的心灵契合。另一方面,侠义小说中的“英雄”并不是积极地去开拓新天地的个人主义形象,而多是被挤出社会秩序中的边缘化了的人物。在某些程度上,与西方早先的“流浪汉小说”具有相似之处。
即便如此,晚清已经具备了接受冒险小说的底盘,出现了冒险小说的“嚆矢”。
李汝珍《镜花缘》(1818),内容丰富。其中有一个主题正是海洋冒险。人们乘坐一种名为“飞车”的机器在空中飞行,离地约达10丈,顺风的时候日行万里。这可以说是滑翔机的雏形。
俞万春《荡寇志》(1853?)中的梁山泊招聘了一个西洋人军师,制造了许多高科技兵器,如奔雷车、沉螺舟 (类似潜水艇)。作者曾跟随父亲在广东生活,在那里接触了西方文化,后来还撰写了《火器论》《骑射论》等武器史著作。
张小山《年大将军平西传》 (1899),是以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的事件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其中,也有一个专门开发新式武器的西洋人“南国泰”,设计了“升天球” (飞翔机)、“地行船”(类似于穿山甲的地底战车)。
王韬《淞隐漫录》(1884年起《点石斋画报》连载,1886年单行本)中有很多以海洋为背景的故事。如《海外美人》(新式船只、整容术)、《仙人岛》、《海底奇观》、《海外壮游》。其时凡尔纳等小说尚未进入中国。
著名的康有为《大同书》(1913年、1919年陆续刊出)是未来人类史的计划。
这些作品固然延续了中国古代的要素,而同时又融合了西方的近代科技,是晚清正式引进西方科幻小说之前的本土先锋。众所周知,晚清翻译小说十分发达,不过,热衷翻译的契机并不是文学,而是出于文学救国的目的。陈平原说:“对域外小说既没有积极介绍,也没有强烈反对,只是默然置之——这种对域外小说的冷淡,到戊戌变法前后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转折的契机主要还不是文学,而是政治。”①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的起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因此,政治小说首先被看中,其次是符合晚清国势的“科学”与“民主”主题的科学小说、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就是凭借了科学性及勇武的特质被挑中。
首先,从冒险小说的题目中清楚可见“军舰”“未来”“世界”及“海”等关键词。其次,翻译的时期多集中于1903—1907年,这是中国在甲午战败后,亟亟向西方及邻国日本吸收军事技术与科学知识的时期,同时穿插了日俄战争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晚清虽力图保持中立,但作为两国交战的阵地无法置之开外。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以徐念慈为代表的小说家所翻译的“武侠军事”题材的冒险小说逐渐形成热潮。
由此,再次审视前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冒险小说。
《小仙源》:1906年1月28日《申报》刊载广告“上海商务印书馆又有小说六种出版”。称:“此书叙一瑞士国人洛苹生,携其妻子航海触礁,舟人皆乘小艇逃生。洛全家在坏舟之中,万分危险。忽因风涛所泊,得见新地。洛生挈妻携子,相率登岸,寄居荒岛,以田猎渔樵为生。观其经营缔造,足为独立自治者植一标影。后其子孙蔓延,遂成海外一新世界。与《鲁滨孙漂流记》同一用意,而取径各殊。欧人好为此种小说,亦足见其强盛之有自来矣。”
《世界一周》:1907年8月22日《申报》刊载“上海商务印书馆续出最新六种小说”广告。称:“是书叙葡萄牙人麦折仑以冒险性质,誓必环游地球,开辟殖民地。为西班牙王所信用,率其徒分乘五舟,放大西洋而南。数数濒危绝食而无退志,搜索群岛土人,为之演说基督教。乃末至麻喇甲,竟毙于土蛮之手。其徒耶斯比继之,乃克偿其未了之志。至今南美洲麦哲伦峡,几千百年尤虎虎有生气。阅之令人作乘风破浪想也。”
《澳洲历险记》:1906年6月25日《申报》刊载“上海商务印书馆最新小说六种出版”广告。称:“是书显礼以一十六龄童子抱殖民志,远迹澳洲,历种种危险劳苦,几濒于死,卒能坚忍激昂,于困厄中增长智识。”
《鲁滨孙漂流续记》:1906年7月16日《申报》刊载“上海商务印书馆续出最新小说五种”广告。称:“书叙鲁滨孙返国后第二次复出航海,重蒞前岛,询知西班牙人督众与生番鏖战,获男妇凡数倍。又舟行抵马达加斯岛,舟人因挑少妇启衅,袭击土人,焚毁村舍等事。摹写战时情状,均极生动酣烈,有声有色。其后兼叙鲁滨孙游历至我国,采风纪俗,语含讽刺,虽多失实,亦未始不可借为针砭。”
《蛮陬奋迹记》,讲述一青年从印度前往英国的途中,所乘之船遭遇风暴触礁,漂流至南非的一个荒岛。于是在此黑人族群的岛山开始了生活。
《鲁滨孙漂流记》《金银岛》《秘密电光艇》与海洋的关系自不必说。其他作品,即便没有大肆渲染海上历险,也都是跨海越洋后的非洲拓荒、澳洲殖民的冒险。可见,“海洋”是冒险小说的重要关键词。作为航海技术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的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大约在公元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由海路传入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开洲际航海创举。其后,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发现了新大陆;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达·迦马 (Vasco da Gama)横渡印度洋;1519—1522年,麦哲伦 (Fern o de Magalh es)实现了环球航行。这些航海技术的发达,促进了地理学研究,推动了科技进步。
晚清翻译小说种类众多,作品数量多达5000种①[日]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出版1997年版。其中收入翻译作品4974种。,目前尚不能一一区别内容属性。笔者根据上述分析,对晚清冒险小说定义为:以航海技术为基本要素,配以现代科学知识,对自然界的不可思议的现象进行描述的;或者添加社会意义、凸显国民性及人类史思考的作品,如科幻冒险、殖民冒险、军事冒险等。
二“冒险小说”中的世界秩序:东方 (晚清、日本)与西方
“冒险小说”的主人公具有智慧勇敢的共同点。然而,由于日本和西方国家所处的历史境遇不同,这些冒险小说也呈现出不同的主题。这体现了20世纪初日本和西方的国家情势,也反映了包括晚清在内的世界秩序。
(一)日本:岛国的海外扩张
在翻译的冒险小说中,来自日本的作品数量占有绝对优势。这固然体现出晚清为寻求西方文化与技术而选择近邻的客观性,但纵观晚清翻译的日本小说,除了大名鼎鼎的“政治小说”外,冒险小说也是很突出的。这印证了明治日本迅速实现近代化、意欲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暴发户”身份。
押川春浪是武士阶层出身,体质孱弱而神经敏感,他的作品往往渗透出武侠的气味。其父是日本基督教界的元老,以“武士道化的基督教”志向创建了仙台东北学院。因为父亲与大隈重信关系交好,明治28年,押川春浪进入东京专门学校英文科,后入政治法律科。在东北学院时代,他与岩野泡鸣同窗,嗜好外国冒险小说。当时日本文坛的主流是自然主义文学,表现出暴露人性与社会的丑陋阴暗的特点。对此,押川春浪认为这样的文学会使国民堕落,误害青年,是对国家具有极大危害性的潮流。因此,他想通过翻译大仲马、雨果等作家的作品来与之抗衡。
大学时他创作的处女作《海岛冒险奇谭海底军舰》经亲戚樱井鸥村介绍给儿童文学家岩谷小波,并被推荐发表。在该书的前言中,作者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他请了五个海军军人为此书题字、作序,并请海军少佐进行校阅。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以来,具有富国强兵色彩的军人精神充斥着日本社会。加之,日俄开战即在眼前,押川春浪自由豪放的作品深受国民欢迎。后来,在太平洋战争末期 (昭和19年)石书房出版了春浪选集的第一版,印数多达一万部。作为斗志昂扬的爱国小说,押川的作品再次获得了读者的欢迎。
《武侠日本》表现了日本与俄国对抗的意识,作者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给予了同情。书中的主人公说:“所谓武侠,就是面对自由、独立、人权的压制者,不屈不挠的对抗精神。是打倒不法压制者,拥护弱者权力的精神。那些为了苟且私欲而侵犯他国他人权利的都是武侠的敌人。”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很多日本人为了国家的利益,出于所谓的“爱国心”而“不得不”做了一些违反正义的事情。至于押川的案例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②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比较法制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朝和贯一就提出,需要有反省力的真正的爱国心。他在1909年出版了《日本的祸机》一书,批判那些支持日本政府侵略满洲的狂热分子,督促国民的反省。。
(二)西方:鲁滨孙指向中国
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晚清有三种译本:1898年沈祖芬译《绝岛漂流记》(《鲁滨孙漂流记》与《鲁滨孙漂流续记》的节译本);1902年12月—1903年10月《大陆报》连载的秦力山译《鲁滨孙漂流记》(未完,但关于中国游记尚完整)③详见崔东文《翻译国民性:以晚清〈鲁滨孙漂流续记〉中译本为例》,《中国翻译》2010年第5期。;1905年林纾、曾宗巩合译《鲁滨孙漂流记》,1906年合译《鲁滨孙漂流续记》。
据说沈祖芬之所以翻译这部作品,是被作品中的进取精神所感动,《译者志》称:“在西书中久已脍炙人口,莫不家置一编。 (中略)乃就英文译出,用以激励少年”①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9页。。其胞兄称译者“欲借以药吾国人”②[英]狄福著,沈祖芬译:《绝岛飘流记》,高凤谦:《序》,开明书店1902年版。。1902年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的该书的第一部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做序:“此书以觉醒吾四万万之众。”宋教仁在1906年阅读后认为鲁滨孙的“冒险性及忍耐性均可为顽懦者之药石”③宋教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正如早先鲁迅在《月界旅行》的“弁言”中阐释了凡尔纳“实以其尚武之精神,写此希望之进化者也”④周树人:《<月界旅行>辨言》,日本东京进化社1903年版,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67页。;梁启超在1903年作《新民说》,专门写了一节《论尚武》,1904年发表《中国之武士道》;蔡元培在1912年作《对新教育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当时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尚武的精神来改变文弱不堪的中华。
不过,中国对鲁滨孙的关心并不止于荒岛求生的勇敢精神。在《鲁滨孙飘流续记》中,鲁滨孙游历至中国,他批评中国经济衰退、军备落后、人民贫苦、傲慢愚蠢。但是,作为作者的笛福本人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他的批判是来自于西方的普遍论调。尽管沈、秦、林三种译本都带着译者自身的价值判断而所有增减与改写,但是译者均有意将原著中的中国人形象展示给读者,这正应合了晚清“国民性批判”的思潮。林纾说:“此书在一千六百七十五年时所言,中国情事历历如绘,余译此愤极,至欲碎裂其书,掷去笔砚矣。乃又固告余曰:‘先生勿怒,正不妨一一译之,令我同胞知所愧耻,努力于自强,以雪其耻。’余闻言,气始少静,故续竟其书。”⑤[英]达孚著,林纾、曾宗巩译:《鲁滨孙飘流续记》(下册),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56页。并且林纾对鲁滨孙的行为并非褒赏,而认为是“鼠窃之尤”⑥林纾:《雾中人·叙》,商务印书馆1906年版,转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185页。。同时,他认为哈葛德的蛮荒志异作品是以鲁滨孙为蓝本的,这种殖民主义的先锋欺凌中国,而中国人却无力抵抗。他希望翻译出来可以让读者奋起,尚武自强。强者、英雄精神的呼吁,以改造国民的惰性、奴性和中庸之气⑦详见郝岚《林纾对哈葛德冒险与神怪小说的解读》,《东方论坛》2004年第1期。。林纾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雾中人》的序中:“西人以得宝之故,一无所惧。”⑧林纾:《<雾中人>叙》。他认为,西方人为了获得宝玉可以不畏艰难勇探非洲,那么地大物博、风调雨顺的中国势必成为西人的眼中之物,所以他要翻译此书以提醒国人。
1719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在1905年传入晚清,其中对于中国的认识虽然有时间的差距但并无实质性的错误。因此,具有勇武精神的漂流记与批评国民性的续记,成为此期冒险小说的重要代表。
(三)东西格局:科学崩溃与黄祸论
凡尔纳一类的科幻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新式交通工具,追求太空探索;押川春浪类的军事冒险小说中也设计了很多高科技的军舰、武器,上天入地,实现了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许多新设想。
但是,这些科幻发明的发展终极,却并不是美好的愿景。试看1902年梁启超翻译的《世界末日记》⑨载《新小说》第一号。根据德富芦花的译本转译,原作为法国Flammarion,The last days of the earth.1891.德富芦花译:《世界の末日》,载《国民之友》第119号、120号,1891年。,1903年杨德森翻译的 《梦游二十一世纪》[10]杨珈统校阅:《梦游二十一世纪》,《绣像小说》第1~4期连载,1903年。根据1874年上条信次译《開化進歩後世夢物語》转译,原作是ディオスコリデス 《紀元二○七一年——未来の瞥見》。,1905年徐念慈翻译的《暗黑星》[11]根据黑岩泪香的译本转译,原作是美国Newcomb,The end of the world.1903.黑岩泪香译:《暗黑星》, 《万朝报》1904.5.6—5.25连载。,1906年包天笑发表的《世界末日记》,都体现了人类灭亡、地球毁灭的残酷景况。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正值经济大萧条、宗教信仰发生危机、进化论的科学处于崩溃的边缘①参见李艳丽《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一方面是对世界毁灭的绝望,另一方面表现出西方对东方 (亚洲)的上升趋势所产生的巨大恐惧—— “黄祸论”。这在晚清的自创小说中也有相当的呼应。
例如,李伯元编译的《冰山雪海》(1906),讲述了2399年的中国,当时地球气候异常,急剧寒冷化。抱着殖民希望,人们为开辟新天地而起航。从北极到南极,终于安置下来。9年后美洲大陆的犹太人和非洲人逃离出来,危难之际遇到在已在南极安身的中国人而获救。碧荷馆主人《黄金世界》 (1907),讲述华工的悲惨生活与境遇,描写了美国反华工运动。他在《新纪元》(1908)中描绘了1999年黄色人种与白人的决战。可以看出受到《未来之世界》《世界末日记》的很多影响。肝若《飞行之怪物》(1908),讲述了1999年从加拿大出港的巡洋舰在太平洋上遇到一怪物。怪物袭击世界大都市,给人们造成了巨大恐慌。结果,从怪物上落下一样东西——支那的鼻烟壶。于是世界各城市向中国索赔,并在中国铺设外国铁路。虽然是一篇没有结束的小说,但已清晰地反映出“黄祸论”的背景。陆士谔《新野叟曝言》(1909),讲述了未来的清朝实现了人口控制—— “计划生产”、农业技术改革,建立起空想社会主义。此时,欧洲已为中国所支配。大清帝国意图征服全世界,开始木星殖民计划。许指严《电世界》 (1909),讲述了2010年电化的世界。拿破仑十世想要征服世界,灭绝黄色人种,遂率空中舰队而来。此时,中国的人口寿命延长至120岁,人口众多而策划海底殖民。而日本因遭遇大地震,被迫海底移民。
作为老大帝国的中国,人口众多而具有经济、军事潜力,在上述自创小说中体现出积极向外开拓的宏图。而新兴崛起的日本,则在《空中飞艇》《新舞台》《千年后之世界》《银山女王》《白云塔》《秘密电光艇》《大魔窟》《月界旅行》《星界想游记》《未来战国志》《新社会》《北极探险记》《大地球未来记》《地中秘》中,体现出其“大东亚计划”的嚣张气焰。
研究者②本节主要观点参考罗福惠《“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08年第5期。认为,黄祸论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西方人士用以向同种示警,对日本和中国进行诬蔑、丑诋并寻衅的核心话语之一。19世纪后半期,当西方人在东亚大力扩张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阻碍。一个是崛起的日本,对西方造成了威胁;另一个是拥有古老的儒学文明的中国,人口众多,开始了近代化工业与军事。这样的人口可以作为充足的工业劳动力,也能够成为军事补充力,并且中国人向海外移民,势必对西方构成威胁。
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西方在东亚推进殖民扩张的时候,其内部正处于各种忧患焦虑的状态。1853年法国的人种学家Joseph Arthur Comte de Gobineau发表了著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竭力论证白色人种的优越性。这其实是在1848年欧洲革命后,人们的悲观情绪——担忧欧洲文明的没落和白种人的衰退——的体现。于是,在这样的东亚崛起与欧洲没落的强烈对比的形态中,在德皇威廉二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的阴谋下(1895年春夏),黄祸论的影响逐渐扩大。1898年英国的M.P.Shiel发表了“THE YELLOW DANGER”,描绘了日本人和中国人等亚洲人攻入欧洲,表现出对亚洲征服世界的恐慌。
与此同时,与中国同处于亚洲的日本,在签订《马关条约》的前后,出现了一种“中国人种威胁论”,如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中有一节写“中国人种侵略世界”。这与明治以后日本脱亚入欧、刻意与中国 (后进国)区别开来的论调一致。
(四)东亚:晚清冒险小说输给了日本小说
晚清引进冒险小说已在甲午战争之后,距离日本出现冒险小说有15年左右的时间差。接受冒险小说的初衷,自然是出于时势之需,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士”的责任与抱负接受了含有科学及尚武意味的冒险小说。另外这一外来文学模式与中国古代神话、侠义小说也有契合点。尽管《镜花缘》《西游记》《荡寇志》等古代小说与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冒险差距还很大。
虽然冒险小说的创作在晚清出现了不少,但是在后来的鸳鸯蝴蝶派之类的通俗小说潮流中,在五四新文学潮流中,它都没有发达起来。个中原因也许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一是缺乏创作的客观能力。林语堂说,外国人评价中国人在文字上具有唯美主义,但在语言符号上非常缺乏抽象思维,“中国人的思想总是停留在有形世界的外围。这使得中国人能对事实更有感受,而这又是经验与智慧的基础”①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6、98页。。中国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这是因为中国人缺乏分析性的思维,而喜欢抽象名词。“在中国人的心灵中,科学方法不能得到发展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科学方法除了要求分析性思维之外,总是免不了要有一些枯燥的工作要做。而中国人则相信自己的庸见与洞察力的闪光。推理的方法在应用到人际关系 (中国人最感兴趣的东西)时,常常导致一种愚蠢的结论。”②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6、98页。“逻辑从来也没有被发展成为一种科学。”③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6、98页。虽然林氏的评论有片面性,但是总体而言,由于文化、习俗及教育上的差异,亚洲人 (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不强。这一点在现当代文学创作中都有所反映。
二是将冒险小说视为驱除生活乏味的趣物的看法。钱钟书可以算作这样一个例子,虽然晚清读者的详细情况难以确定。他说:“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四十年前,在我故乡的那个县城里,小孩子既无野兽片电影可看,又无动物园可逛,只能见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儿把戏或者牵一头疥骆驼卖药。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我只能向冒险小说里去追寻。”④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也就是说,他们真是将“小说”作为乐趣来看的。这与日本人将“冒险小说”作为民族奋发的力量、青少年意志培养的源泉的看法截然不同。
正如明治的知识分子将甲午战争称为“文野的战争”一样,明治冒险小说是“文明国”梦想下诞生的产物。随着明治维新的近代化成功,日本积极争取国际地位,谋求与西方的条约修正。与此同时,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如对尼采的译介,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法国文学 (如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也很深。其实,以押川春浪为代表的海外雄飞物语的发达也可以说是政治小说的衍生——在国会召开之前的内部自由民权运动,在国会召开之后转为对外的海外殖民冒险意愿,体现出国力发达后的日本想要加入资本主义秩序的欲望。
受甲午战争胜利的刺激,日本民众的自觉意识受到极大鼓舞。同时,由于“三国干涉”及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谋求、国内经济困境等原因,日本对俄国做好了战争准备。所以《海底军舰》出现后,便一举获得了血气方刚的青少年读者的狂热支持,推动了日本少年小说的潮流。
小 结
小说界革命兴起后,最先舶来的政治小说及其催生物谴责小说,不仅在晚清风靡一时,向来也倍受研究者的关注。冒险小说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具有浓厚的趣味性;但精英知识分子更注重其中隐含的政治意义。不过,即便处于国家危亡之际,晚清的冒险小说创作依旧充满着建设新中华的希望,意图实现无国界无人种差异的大同世界。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站在2002年的时间点上描绘2062年的中国。为庆祝维新50周年,国人相聚上海,举行盛大的博览会。不仅有工商业展品,各种学问、宗教也都汇聚一堂。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博士争相讨论,俨然是一个大同世界。蔡元培的短篇小说《新年梦》(1904)描述全球铺设了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实现了语言统一,普及了一种表音的容易记忆的文字。“国家”“国际法”“世界联合军”等名词都成为历史,人类不再互相竞争,而是成立了“胜自然会”,通过发展科技来克服不利的自然条件,从而使人类更容易掌控世界。
这些作品表现了中国对日本人和非洲人的友好情绪。中国人开拓新行星、开拓新地域的“殖民”,并非强势对弱势民族的欺压、征服,而类似移民、移居。
日本的情况显然不同。甲午战争后、日俄战争前,日本国内主要有“南进论”和“北进论”两种大陆扩张论调,即南下台湾岛,北上朝鲜和中国。这些对外政策极大地促发了国民心膨胀,使得冒险小说、军事小说层出不穷。这些作品中的“殖民”企图最终演变为事实。
以“海洋”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东西方冒险小说,在跨越了海洋的边际相遇时,呈现出的并非文学的较量,而是文明的对抗。它反映了西方对处于上升趋势的东方的恐惧,形成了以“黄祸论”为背景的对峙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