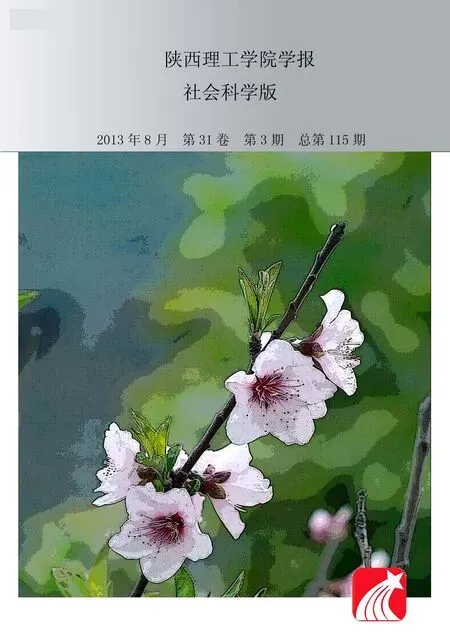宋江形象的矛盾及其文化阐释
陈 檄 焌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英雄传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以宏大叙事的方式,描述了北宋末年梁山泊义军聚义以及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小说以传奇手法塑造了众豪放不羁、多敢作敢为的好汉形象,他们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深受读者喜爱。但是,对梁山义军的领袖宋江,历来却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笔者以为,宋江形象是多元文化交融的产物,要想真正理解这一形象,必须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做具体的剖析,必须将他放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
一
对于宋江的评价,影响最大的是明末思想家李贽和清初著名小说批评家金圣叹,两人先后对《水浒传》做了评点,但对宋江的看法却截然相反。李贽在《水浒》评点中高度评价了宋江,认为宋江是“忠义”之人,对他投降朝廷、接受招安的行为也大加赞扬,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1]192金圣叹则持相反态度,在一百单八人中将宋江定为“下下”[2]2,认为“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他在评点梁山英雄时说道:
宋江盗魁也,……自吾观之,宋江之罪之浮于群盗也,吟反诗为小,而放晁盖为大。何则?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2]193
他把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一概视为权诈虚伪、笼络人心,是朝廷的乱臣逆子。
现代研究者对宋江的评价也有千差万别。有人称宋江是农民起义雄才大略的领袖;也有人说他是地主阶级野心家,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封建皇权的卫道士,赵宋王朝的忠实走狗、刽子手。[3]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与评论家的立场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宋江形象本身就充满了矛盾。大体来看,宋江形象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王法的态度上,他知法、守法,但又不断地犯法。宋江在小说第十八回首次亮相,他当时的身份是郓城县押司,职位虽卑,却有较强的功名思想。他忠君守法,但在“朝廷奸臣当道,馋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的社会现实下,为了遭遇风险时不连累家庭,就预先在家中佛堂下挖了藏身的地窖,以备不虞,并“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4]283。在得知晁盖劫取生辰纲一事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晁盖是我心腹兄弟,他如今犯了弥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将休了。”[4]227于是用心周全,“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私放了晁盖。这是宋江重义气、轻法度的一大表现。
其次,在对落草的态度上,自己迟疑不决,但却不时拉他人甚至逼他人上梁山。宋江对朝廷始终抱有幻想,也一直下不了与统治阶层决裂的决心,醉心“功名”的宋江宁愿浪迹江湖,吃尽流寓之苦,也不愿上梁山落草。如在小说第三十六回,宋江刺配途中被梁山好汉请上梁山,晁盖劝他留在山上共聚大义,宋江却道:“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4]472此时,封建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使宋江没有顾忌兄弟义气而站在朝廷的对立面。但在众好汉劫了江州法场后,他走投无路,才不得不“逼上梁山”。此后为了自己的梁山事业,他费尽心机,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为了逼呼延灼、关胜等上梁山,他不断打出招安的旗号;为了招纳卢俊义,更是派人在其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致使卢俊义蒙冤陷狱,不得不落草。
第三,在对朝廷尽“忠”方面,也常常是言行不符。宋江从小接受儒家文化教育,“忠君”思想极为浓厚,他的人生理想就是为国家出力,通过自己的奋斗,“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他认为私放晁盖、怒杀阎婆惜都是大逆不道之举,因此诚心服罪,以待重新做人。但在醉酒之时却在浔阳楼上题了“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诗句,酒后吐真言,他的“凌云志”竟是如黄巢一般率兵造反,这与他一再标榜的“忠君”大相径庭。在上梁山后,宋江一掌权立刻就把“聚义厅”改名为“忠义堂”;排座次后,宋江更是不放过一切机会表达归顺朝廷的意愿:“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4]985但是,为了达到招安的目的,他又不断和朝廷作战,屡次打败前来围剿的官军,给国家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第四,在与晁盖的关系上,行为也有可疑之处。宋江做了梁山首领后,与众兄弟“哥弟相称,不分贵贱,患难相助,同生共死”,正因这“义”的凝聚力,众人才与他“生死相随,誓不相舍”,梁山义军才能紧密团结,从而取得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攻城夺县、惩恶扬善的辉煌战果。但是,对于自己曾舍命相救的晁盖,宋江所为颇令人生疑。他以“山寨之主”为由,屡次阻拦晁盖下山,如第五十一回写柴进落难,晁盖欲“亲自去走一遭”,宋江拦住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可便轻动?”随后主动请缨,“情愿替哥哥下山”。金圣叹于此批道:“写宋江自到山寨,便软禁晁盖,不许转动,而又每以好语遮饰之,权诈可畏如画。”[2]603第五十七回救孔明、第五十八回救史进,宋江的理由都是“哥哥山寨之主,未可轻动,原只兄弟代哥哥去”。于是,他屡次出征,不断招降纳叛,发展自己的势力,种种表现,确有架空晁盖之嫌。
综上所述,小说中的宋江的确充满了矛盾,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自然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也就是人们对宋江做出不同评价的原因。那么,宋江形象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多的矛盾?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将宋江形象放在他产生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
二
胡适曾经说过,“《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十二世纪初年)到明中叶(十五世纪末年)这四百年‘梁山泊故事’的结晶”[5]9。宋江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从历史人物到小说中的文学形象,有一个较为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的来看,宋江形象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史家笔下的“盗寇”、“剧贼”。
宋江是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关于这次起义,《东都事略》、《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等史书中都有一些零星记载。宋代王偁的《东都事略》中最早记载了宋江之事,《徽宗本纪》中写道:
“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宗与方腊战于清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1]2
关于宋江事迹具体化的记叙也出现在同书的另外两篇人物传中。《侯蒙传》中写道: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陈制贼计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1]3
这里提到“其才必过人”,并对宋江起义的规模、声势和应对策略做了记述。另外,《张叔夜传》中也有这样一段话:
会剧贼宋江剽掠至海,趋海岸,劫巨舰十数。叔夜募死士千人,距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使战。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合,即焚其舟。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1]3
这段文字,对宋江到海州后的遭遇及结局做了比较清楚的交代。这三段文字也见于《宋史》,文字略有不同。总的来看,史书中对宋江起义一事记载不详,宋江本人的事迹也比较模糊,但不管是野史还是正史,宋江最初都是被当做“盗寇”、“剧贼”来记述的。
史书中对宋江思想性格的叙述更少。元人陈泰在《所安遗集补遗·江南曲序》中提到,“宋之为人,勇悍狂侠”[1]54,这是关于宋江性格最直接的描述。
第二阶段,民间文学创作中的“及时雨”。
宋江事迹在南宋时期就逐渐受到人们关注。宋末遗民龚开在《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说:“宋江之事见于街头巷尾,……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1]21这说明宋江故事的影响范围之大,受欢迎程度之高。他肯定宋江“识性超卓,有过人者”[1]21,但仍称他是“与之盗名而不辞”的“盗贼”。
在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中,宋江故事也成了热门话题。《大宋宣和遗事》一书记述了北宋衰亡到南宋南迁临安前后的史事,书中有七节涉及宋江起义,比较详细地写了宋江私放晁盖、秘受刘唐金钗、怒杀阎婆惜、题反诗、遇九天玄女、带领兄弟三十六人上梁山、被招安、受命征方腊的全过程。书中的宋江性情粗犷、蛮横凶残,带着浓厚的“强盗气”,如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宋江等犯京西、河北等州,劫掠子女玉帛,杀人甚众。[1]41
是时宴会已散,(宋江等)各人统率强人,略州劫县,放火杀人,攻夺淮扬、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余县,劫掠子女玉帛。掳掠甚众。[1]47
宋江虽仍是“劫掠子女玉帛”、“放火杀人”的“寇”,形象单薄,但性格中多了“勇悍狂侠”的成分,并带上了较强的伦理道德色彩。宋江私放晁盖、送董平等人投奔梁山,这是“义士”的行为;告假归省,照顾父亲直至病愈,传递出了感动人心的“孝”。在落草之后,玄女娘娘赠的天书里明确提到要“广行忠义,殄灭奸邪”[6]47,宋江等人最终也接受招安,归顺朝廷,受了封赏,“忠君”思想成为宋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还产生了一批“水浒”题材的杂剧,宋江开始作为独立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形象特征也逐渐鲜明。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等记载,元末明初产生的水浒戏有三十余本,全本流传至今的有六种。在水浒戏中,宋江不再是杀人放火的强盗,在他身上“忠义”特征已经体现得较为明显,有胆有识,治军严明,与官兵作对,为民除害。如在《黑旋风双献功》、《大小夫妻还牢末》、《黑旋风负荆》、《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同乐院燕青博鱼》等剧中,明确提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每一部均让宋江首先出场。“五部剧五个作者……五个人俱都接受了一个规定了的宋江。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宋江众望所归的领袖形象已经在人们心中扎根了。”[6]127在《黑旋风双献功》和《大小夫妻还牢末》中,宋江有了“及时雨”的绰号,他自称“我平日度量宽宏,但有不得已的英雄好汉见了我,便助他些钱物,因此天下人都叫我做及时雨宋公明”。在《黑旋风负荆》中,他惩治流氓泼皮;在《还牢末》、《争报恩》中出现了“只杀贪官滥吏”等。这些杂剧增加了宋江侠义品质的描写,受众好汉和百姓拥戴的起义英雄、豪杰侠士形象呼之欲出。
第三阶段,文人的加工成书。
从南宋直至元末明初,宋江的故事大致沿着两条线索在社会上流传:一是以南宋以来的史志、文集、笔记为代表的史家和文人的历史记载;一是以《大宋宣和遗事》和元杂剧为代表的民间传说和文人创作。这些都为《水浒传》的最后形成做了准备。元末明初,施耐庵总其成,把经过了一代代加工、演义的水浒故事编纂成了长篇小说《水浒传》,最终完成了宋江形象的塑造。在塑造宋江形象时,作者广泛吸收了正史、民间传说以及杂剧、讲史话本中的有关内容,同时还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体现了鲜明的道德观念和爱憎态度,因此,这一形象带有各种文化的印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来自不同层面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它们有时能够彼此吸收、融合,有时又互相冲突,很难完整而又和谐地统一于某一文学形象身上。”[7]不同文化的冲突加上作者在艺术分寸把握上的失度,使小说中的宋江形象出现了许多矛盾。
三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小说处在雅、俗两种文化的结合部。很多作品都有一个在民间流传、定型的过程,因而作品中既有士人文化的因子,又有俗众文化的成分。宋江是水泊梁山的灵魂,《水浒传》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首先取材于历史上起义首领宋江的史事和南宋以降的相关传说,这决定了宋江身为盗魁、统领群雄的基本身份及特征;其次,在具体表现这一人物名重江湖的领袖气质及行事时,又深受侠义文化的影响,并在他身上隐括了“义侠”的特征;同时,在写定过程中又融入了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信条和价值理想。大量异质思想的混融,使小说中的宋江形象显得十分复杂。在这个矛盾而复杂的人物形象身上,作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并集中大量笔墨从多层面、多角度来塑造这一心目中的英雄形象。总的来看,作者在塑造宋江形象时主要做了两项工作:
第一,突出了宋江的义气和人格魅力。在宋江出场时,作者便赞道:“年及三旬,有养济万人之度量;身躯六尺,怀扫除四海之心机。志气轩昂,胸襟秀丽。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4]225-226接着又加上一段宋江“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4]225-226的总体评价,定下了对宋江这一人物热烈赞颂的基调。而后,全书从多个侧面展开了叙述:通过他的赈助贫苦,写他的心性善良,富有同情心,与书中周通、李忠、王英一班打家劫舍的强人拉开了距离;通过他的私放晁盖,写他过人的义气,突出了他最为江湖好汉看重的品质;在第二十三回中又借叙述他与柴进对待武松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了他性格中一种持久的魅力,以及与出身下层的好汉之间天然的亲和力,这又与同样颇有江湖声望的柴进拉开了距离;江州法场获救后智取无为军一节,则写出他的领袖群伦及智谋,与鲁智深这种纯粹的江湖豪侠显示出层次的不同;至于写他反复言说待到异日招安赴边庭一刀一枪博个功名,则是为了展示他的胸襟眼光超越了李逵辈乃至晁盖。此外,书中还通过江湖中各色强人闻宋江之名莫不望风而拜,通过柴进这种前朝皇室后裔对宋江的格外礼敬,通过秦明、黄信等远离宋江家乡的军官得知对手是宋江时立刻改容相向,通过一系列类似情节的反复渲染,写出了宋江强烈的个人魅力和巨大的号召力。正是由于这些全方位、多角度的刻画,作品给读者留下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印象:只有以宋江为核心,梁山大寨才能形成巨大的凝聚力,才能吸纳各方好汉,使梁山事业兴旺发达。
第二,强化了宋江对朝廷的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模式是“伦理-政治”型文化,它产生的社会基础是带有宗法性质的君主专制制度。随着专制政治的不断强化,在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为专制政治服务的理论体系,其中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理论,他把“君”摆到了绝对统治地位,强调对君无条件的服从,于是,“忠”就成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和道德品质的最高标准。这种伦理观念经过一再强化,成了中国文化观念的核心,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士人,都难免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张锦池先生在《“忠义之烈”的艺术典型》一文中指出:“宋江的形象早在南宋水浒故事中便被赋予忠义思想的色彩。宋江形象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其忠义思想被不断深化的过程,而忠于宋室的观念则越来越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8]215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施耐庵在塑造宋江形象时就进一步强化了忠,这从梁山前后三位寨主的设置上就能看出端倪:第一任寨主王伦,不忠不义,与好汉们格格不入,因此只能被好汉们毫不留情地除去;第二任寨主晁盖,重义但不讲忠,这不符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理想,只好将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则完全不同,他对朋友义,但同时也对朝廷忠,这才是作者理想中的义军领袖。宋江“自幼曾攻经史”,这使他与一般的血性江湖汉子自然地形成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在“长成亦有权谋”,即虑事周密、富有谋略,另一方面,传统的经史教育使他将追求青史留名视为终极理想。面对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宋江同情和支持晁盖为首的义军,对梁山兄弟仗义相待。但宋江从小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忠君报国”的正统观念在他思想中根深蒂固,因此,在他看来,造反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的。他祈求“博得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所以既反贪官污吏,又不想真正推翻封建统治,“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走上招安之路,可以说是宋江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激烈的反叛也好,屈辱的招安也好,最终都要指向这一目标,因此书中的宋江最终死得那样凄凉,却也那样坦然,成为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个”。
“忠”和“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忠”要求下对上的无条件服从,它是制约上下关系尤其是君臣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义”则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真诚,它是制约朋友关系、兄弟关系的一种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时代的道德理想,二者是互相补充、难以分割的统一体。但随着“义”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二者之间也常常发生矛盾。一般来说,“义”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统治者标榜的“义”,它和“忠”连在一起,常被称为“春秋大义”;二是民间推崇的知恩必报、哥们义气,也被称为“小义”。在《水浒传》中,“义”和“忠”、“小义”和“大义”处于对立的两极,对晁盖等造反者讲“义”,往往就是对朝廷的不忠,作者要把这两种美德都集中在宋江身上,势必会发生极为严峻的冲突,并由此导致了宋江自身性格的分裂。如研究者所说,宋江“作为小说的第一个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义主导下曲折发展”[9]40;“宋江一生似乎总处在自我‘矛盾’的纠缠中。他的行为看似出于自为的选择,而实则身不由己,常常陷入两难的困境之中而无力自拔。”[10]203宋江自身就是一个“忠”“义”扭曲的矛盾体。
要之,宋江的传奇故事从北宋末年开始流传到元末明初基本定型,历经数百年,而宋江这一文学形象也因此融入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理想、人生价值和各个阶层的审美情感,带有多个阶层的特征以及不同时代的思想倾向与道德标准。从历史人物到文学典型,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各种文化都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作者在创作时对来自不同层面的文化都有所吸收,同时也注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不同质的文化的融合、冲突,使宋江形象充满了矛盾,但也增加了其文化内涵,因而具有更持久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朱一玄.水浒传资料汇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2]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
[3]纪德君.百年风云:宋江形象争论的回顾与启示[J].明清小说研究,2005(3).
[4]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5]胡适.《水浒传》考证[M]//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1979.
[6]陈松柏.《水浒传》的成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7]雷勇.关羽形象的塑造及其文化矛盾[J].襄樊学院学报,2009(3).
[8]张锦池.“忠义之烈”的艺术典型——论宋江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发展[M]//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0]冯文楼.四大奇书的文本文化学阐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