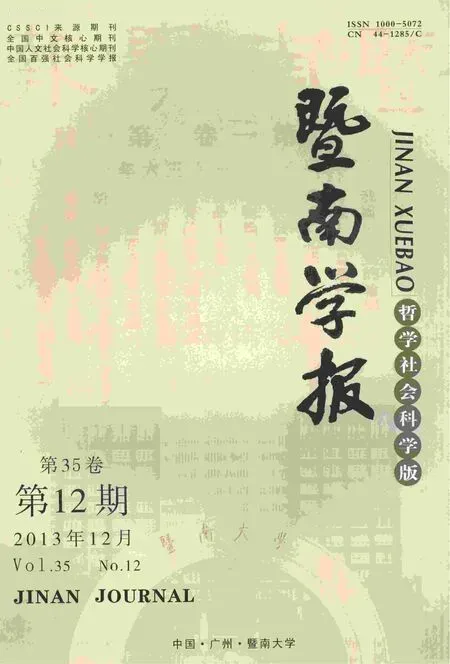论跨国破产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
邓瑾
(广州医科大学法学系,广东 广州510182)
跨国破产,特别是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法律适用是解决跨国破产问题最棘手、最薄弱的环节。这些破产案件经常都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同时开始,因为各国都希望将破产债务人的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著名的欧洲食品公司案(Eurofood)、英吉利海峡隧道案(Eurotunnel),马克斯韦尔集团案(Maxwell Group)、安然公司(Enron)和道康宁(Dow Coming)公司案就是很好的例证。根据跨国破产的传统理论,在处理这些案件时,会运用“属地主义”的方法或者“the grab rule”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就使各国对自己能够掌握的资产根据本国的破产法进行分配。而跨国破产学界所推崇的“普遍主义”方法则希望跨国破产程序仅在债务人的母国(home country)进行,那么唯一的破产法院将通过清算或重组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对债权人进行分配。
目前,在跨国破产实践中完全采用“普遍主义”方法是不可行的。支持“普遍主义”方法的国家也只能尽可能地使跨国破产案件在全球范围的管理和破产财产的分配上达到一致的结果。要想达到这样的结果,除了需要有统一的管辖权依据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跨国破产问题的解决上有详尽而完备的法律选择规则。目前,在国际上,也只有《欧盟理事会关于破产程序的第1346/2000号条例》(European Union:Council Regulation No.1346/2000 of 29 May 2000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以下简称《欧盟破产条例》)规定了较为详尽、全面的法律适用规则。本文将结合《欧盟破产条例》的有关法律适用规则和跨国破产实践,对跨国破产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进行讨论。
一、明确区分非破产法与破产法的适用
在跨国企业集团破产案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明确区分破产法和非破产法的适用。在争议的解决过程中,这两类法律选择都可能会用到。例如,一个由合同产生的索赔是破产债务中的一部分,债权人声称其债权应优先分配。但实际上,合同的效力、合同的损害赔偿等相关问题都是由非破产法来调整的,因此在法律适用上应遵循一般的法律适用规则,即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在确定了合同的法律适用,明确了合同的有效性及其赔偿数额以后,才涉及破产法的适用,最终确定破产分配顺序等问题。在近几年的跨国破产实践中,这个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一)非破产法适用与破产法适用的区分
在任何有争议的跨国破产案件中,法院都必须通过法律选择确定应适用的准据法,从而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正确,并且对破产财产进行分配。在跨国破产案件的法律选择过程中,法院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根据非破产法,破产请求权的有效性以及索赔金额的多少。第二,根据破产法,确定该请求权是否具有优先性,以及在破产财产的分配中顺序如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在法律适用上是有区别的。通常情况下,第一个问题适用非破产法,第二个问题则适用破产法。在单一法制体系国家中,法院只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即可,而在美国这种联邦制国家中,第一个问题可能由当地州法律来调整,第二个问题则由联邦破产法来规制。在跨国破产案件的解决上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用一国的法律来确定请求权的合法性,而用另一国的法律来确定优先权和清偿的顺序。对于采用“属地主义”方法解决跨国破产问题的国家在第二个问题上就会直接适用本国的破产法,而无论第一个问题的适用情况如何。而采用“普遍主义”方法的国家则有可能适用外国破产法来解决第二个问题。
可以举一个清晰明了的例子对这个问题进行说明。一个人在债务人破产之前遭到了非法侵害,这个非法侵害的索赔就只能由非破产法来调整,也就是说这个请求权在一般的诉讼中是可以得到满足的。但是,如果在破产程序中进行索赔,请求权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就取决于适用于破产程序的法律,该法律确立的优先权规则如何,财产的分配顺序如何等等。如果一个法律体系中的破产法规定了给予其他类型的请求权如税收、员工工资予优先权,非法侵害的索赔可能一无所获。但是,如果破产法规定了对人身损害优先赔付,那么非法侵害的索赔就有可能得到全额的赔偿。跨国破产案件将会更加复杂,因为索赔或财产的权益所适用的法律与破产程序所适用的法律往往是不同国家的法律。因此,法院在处理跨国破产案件时应明确区分哪个国家的法律适用于索赔的范围和财产权益,哪个国家的破产法适用于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对于索赔或财产权益主张的法律适用,法院可以考虑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原则等联结因素,而对于破产财产的分配以及受破产法调整的其他事项,则应将债务人在全球的事务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适用中关注主要营业中心所在地、主要财产所在地、大多数债务人的住所地、经济利益中心地等联结因素。
(二)典型案例剖析——乐奥与豪斯顿诉斯托宁顿案
下面通过乐奥与豪斯顿诉斯托宁顿案(Lermout&Hauspie Speech Products N.V.v.Stonington Partners,Inc.)来阐述实践中非破产法与破产法适用的情形。
1.案情简述
乐奥是一家在比利时成立的公司,在其破产的前一年就已经和美国的两家公司合并,结果导致在破产时超过一半的资产位于美国。此次并购是通过股票的转让实现的,在股票的转让中公司对其财务状况进行了虚假陈述。当会计问题被揭露时,公司的股票崩盘,在同一天,债权人分别向美国和比利时都提出了破产申请。本案的关键是,美国和比利时的破产法对是否给受欺诈的索赔人予优先权存在着冲突。斯托宁顿公司认为他们在接受其股票时受到了债务人的欺诈,受到了实质性损害。在美国破产法中,这种索赔权在破产财产分配顺序中次于无担保的债权,因此,在破产程序中将一无所获。而在比利时的破产法中,这种索赔权与其他无担保的债权一样,没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但在优先债权受偿以后,将能够按比例受偿。因此,受欺诈的股票索赔权在美国破产法中无法受偿,而在比利时的破产法中将会得到部分受偿。相应地,其他无担保的债权人在比利时破产法下的受偿金额会相应地减少。事实上,破产人的大部分资产都在美国法院的控制之下。
美国破产法院认为,美国破产法中的这种受偿规则应该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斯托宁顿公司的索赔,并且应该禁止比利时法院重新对该问题进行审理。这种认识在上诉时得到了地区法院的肯定。美国破产法院对该问题的认识正是基于法律选择规则,认为对于股票欺诈索赔的破产分配顺序问题应受美国破产法调整。然而在上诉中,第三巡回法院将案件发回重申。上诉法院认为,破产法院对法律选择的分析是完全错误的,需要重新考虑。
债务人在这时候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提出了一个清算方案,在美国和比利时破产程序分配财产。但这个清算方案将大部分资产分配给美国的破产程序,仅留下小部分给比利时,这使得比利时甚至无法偿付具有优先权的债权。与比利时的破产管理人进行协商后,债务人对该计划进行了修订,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比利时优先债权的支付,但仍将大部分资产的分配放在美国。破产法院支持了这个清偿计划,并在法律适用上认为在美国的破产程序应适用美国的分配规则,回避了原先所宣称的美国的分配规则应适用在全球范围内的破产程序。因此,破产法院认为,斯托宁顿公司因股票欺诈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在美国的破产程序中是无法得到偿付的。但破产法院同时强调,任何索赔人同时可以在比利时求偿,但没有优先权的债权请求权将会一无所获。地区法院对破产法院批准清算方案的做法也表示了认可。斯托宁顿公司也没有再进一步上诉。
美国破产法院实际上是运用了“修正的普遍主义”方法来解决跨国破产的法律适用问题。“修正的普遍主义”方法要求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每个国家的破产法时,在破产法允许以及实际情况可能的环境下,尽可能地接近一种普遍性的结果。根据乐奥公司所提出的清算方案进行破产清算与仅仅根据破产申请时破产财产所在地的法律解决跨国破产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是典型的用“属地主义”的方法,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在公司会计问题被揭露之前,财产可能已经被转移。在这个全球化动态的世界中,贷款人、投资者,或客户都很难预知公司的主要资产在特定的时间位于何处。从这个层面上看,“属地主义”的法律适用方法是不适当的。
2.非破产法适用与破产法适用之分析
在乐奥案中,因股票欺诈的索赔应该受非破产法的调整,而对于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则由破产法来制约。在美国,对于欺诈这种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应采用“重力中心”理论或“侵权行为地”理论,从而确定在美国应适用的准据法。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以及优先权问题应该适用哪个国家的破产法?对于采用“属地主义”方法解决跨国破产问题的国家和法院来说,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法院只需要适用自己国家的破产法来分配其所控制的破产财产。而对于采用“普遍主义”方法、“修正的普遍主义”方法的国家和法院来说,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要想对债务人的财产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一分配,并且尽可能达到一致的结果,法院在法律适用中就必须认真考虑应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来处理统一分配问题。如果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地、主要营业中心所在地、主要资产所在地都在同一地点,该地点所在的国家的破产法应适用于破产案件,但这种情况较为少见。在大多数跨国破产案件中,债务人的破产财产都分散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地或主要营业中心所在地的国家的破产法是应适用的法律。但是,如果债务人的主要利益中心地与主要财产所在地不在同一管辖区域内,答案就没那么确定了。乐奥公司一案正好也是这样的情形,公司破产前由于合并大部分的资产已经转移到了美国,使债务人的主要营业中心所在地和主要资产所在地分离。
在乐奥公司案中的法律选择问题上,这些因素都没有发生作用。实际上,破产法院和地区法院都将重点放在了侵权行为地与当事人在合并协议的法律选择上。而这些又与根据非破产法所确定的股票欺诈行为以及索赔数额有很大的联系。如果美国和比利时法律在欺诈侵权以及索赔数额计算问题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就会成为问题的关键。然而,对于由破产法调整的破产财产的分配顺序则与欺诈索赔的事项毫无关系。要根据属地主义原则适用法院地法,将能够控制的资产在当地进行分配;还是为了达到跨国破产的目标,根据普遍主义原则选择单一的法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统一适用,管辖法院必须作出选择。美国破产法在跨国破产问题上采纳的是“修正的普遍主义”原则,采用单一法律的方式更为合适。像乐奥这种类型的公司,在世界各地从事着兼并,公司主要资产所在地可能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大多数债权人和有关的利益主体很自然会想到乐奥公司是一个在比利时法律管制下的全球公司,它的管理和经济交易主要在比利时进行。因此,应适用的法律是比利时法。
二、法律适用的立法趋势——法院地法与例外情形相结合
“法院地法”在跨国破产的法律适用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在“法院地法”的认识上,国内外的学者、法官长期存在着一些错误认识,影响了跨国破产的法律适用。
(一)有关跨国破产中“法院地法”的错误观念
首先,部分学者将跨国破产问题看作是程序性的,这导致在法律适用上直接适用法院地法。在跨境破产案件中实质上不存在什么法律选择问题,破产救济是具有程序性质的救济,根据“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在程序和形式方面适用法院地法具有方便、经济和必然性等特点。而实际上,破产法是集程序法与实体法于一身的综合性法律部门,跨国破产问题既有程序性问题,也有实体性问题,一概适用法院地法不利于跨国破产案件的解决,更不利于跨国破产、跨国企业集团破产的统一化。一般来说,管辖破产案件的法院都会适用法院地法(lex fori)来处理破产的相关问题。这是由于破产一直被认为是程序性问题,破产事项适用法院地法因而被广为接受。另外,有学者认为,法院地法的适用也避免了为确定准据法而另行诉讼,节省了破产的时间和费用。只要法院地的破产法在整个破产案件中得到适用,就避免了对不同的债权人适用不同的法律,既增加了确定性,又减少了诉讼的成本和风险。
其次,法院没有运用法律选择方法来解决跨国破产中出现的法律冲突。美国巴克斯鲍姆(Hannah L.Buxbaum)教授在《反思国际破产:对法律选择规则与理论作用的忽视》一文中提到:跨境破产法律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法律冲突的过程,是一个法律选择问题,即应当如何选择适用于整个跨境破产程序或者其中某一方面问题的法律。然而,有趣的是,跨国破产法一直没有以传统冲突法的思维模式区分析跨境破产的法律选择问题,通常是从普遍主义和属地主义理论出发讨论跨国破产的选择问题。在普遍主义之下,将统一适用一个法律;在属地主义之下,每个国家将适用自己本国的法律。美国修正普遍主义的代表,即原《美国破产法》第304条也没有包含法律选择规范。美国学者库尔森(Rechard E.Coulson)认为,在美国,法律选择规则在解决跨国破产案件的法律冲突问题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绝大多数法院在适用《美国破产法》第304条第3款决定是否给予外国破产程序予承认和救济的同时,也就决定了是否允许适用外国破产法处理美国债权人的分配。也就是说,它排除了法律选择规则在确定破产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最后,在跨国破产问题上,没有正确区分法院选择和法律选择,以法院选择代替法律选择。法院选择指的是应由哪个法院来审理特定的破产案件;而法律选择是解决法院在审理跨国破产案件时应当适用哪个国家法律的问题。而在实践中,由于受到将跨国破产问题认定为程序性问题的错误观念影响,或者仅仅从属地方法来解决跨国破产问题,很容易导致以法院选择取代法律选择的后果。法律选择是普遍主义方法实际上所要求达到的结果,即对所有的债权人按照同一法律原则进行破产财产的分配。从此意义上讲,在对普遍主义的贯彻方面,法院选择是一种形式上的体现,而法律选择则是一种实际上的要求。在跨国破产的法律制度中,债务人“主要利益中心地”是核心概念。目前,此概念已经成为法院选择(choice-of-forum),而不是法律选择(choice-of-law rule)的标准,但它对实现法院选择和法律选择的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主要利益中心地”确定跨国破产案件的管辖权后,当法院适用“法院地法”时,实际上就是在适用“主要利益中心地”的法律。事实上,一国法院在受理了跨国破产案件以后,通常也会适用法院地法,特别是在有关程序性问题的事项上。这既保护了本国当事人的利益,也体现了一国的司法主权。
(二)法院地法为主,例外情形为辅的立法模式
由于跨国破产的特殊性,一般的法律适用规则并不能直接在该领域适用。对于跨国企业集团破产案件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整个破产案件适用一个破产法律,在一个破产法院进行,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破产方式。这种法律适用会使得一国的国内破产法效力及于债务人资产存在的地方。另外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则是适用启动破产程序国的法律,也就是法院地法。在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法律适用中,有一个妥协:作为一般原则,启动破产程序的法院适用法院地法,而在特定事项的法律适用中规定例外情形。这种做法在目前的跨国破产中已被广为接受[。
在目前跨国破产的国际性文件中,要属《欧盟破产条例》在法律适用上的规定最为详尽、具体,而且《欧盟破产条例》在欧盟25个成员国有自动执行的效力,应该可以称作是适用范围最大、运用最广的跨国破产的国际性文件了。《欧盟破产条例》的法律适用条款规定在第4条至第15条。第4条是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第5至第15条则是特殊例外的条款。
《欧盟破产条例》第4条确立了“法院地法”的适用。它规定,破产程序及其效力所适用的法律是启动破产程序成员国的法律。该条款再次肯定了这一广为接受的法律适用规则:破产法院地法(lex concursus)。破产法院地法在破产程序的效力,破产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以及破产程序的开始、进行和结束的条件都予以适用。为了更加明确和清楚,《欧盟破产条例》第4条第2款的第1项到第13项列出了13种适用破产法院地法的特殊事项,他们分别是:(1)债务人的破产能力;(2)破产财产的构成以及对在破产程序开始后债务人取得或接受移交的资产的处分;(3)债务人和破产管理人的权力;(4)抵销权行使的条件;(5)债务人作为合同一方当事人时,破产程序对合同的效力;(6)破产程序对个别债权人提起的诉讼程序的影响,未决诉讼除外;(7)在破产程序开始之后针对债务人的财产提出的权利请求以及对该请求的处理;(8)关于债权的申报、审查和确认的规则;(9)关于债务人财产变现所得收益的分配、债权清偿顺序以及在破产程序开始后通过物权或抵销权获得部分清偿的债权人权利的规则;(10)破产程序终结的条件和效力,特别是通过和解终结破产程序的情况;(11)破产程序终结后债权人的权利;(12)因破产程序而产生的成本和费用的负担;(13)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法律行为的无效、可撤销或者无执行效力的规则。这里列举的13个具体事项不仅包括跨国破产的程序性问题,也包括直接关系到债权人利益的实体性问题,如破产财产的构成、债权的清偿顺序等等。
除了上述法院地法的适用外,在特定的实体法领域仍然有其特定的法律适用规则。而《欧盟破产条例》第4条第1款规定,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适用于破产程序的法律及其效力都适用启动破产程序的成员国法律。这里所称的“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指的就是《欧盟破产规则》第5条至第15条这11个条款,他们也提供了在某些具体案件中确定法律适用规则的不同方法。例如,破产程序对获得或利用不动产的合同的效力专由不动产所在地成员国法律确定。破产程序对支付或结算系统或金融市场的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效力应专由该系统或市场所适用的成员国法律确定。破产程序对于债务人在不动产、船舶、航空器等应在公开登记部门登记的财产的效力应由该登记机关所在国法律确定。
《欧盟破产条例》所采用的“以法院地法为主,以其他例外情形为辅”的立法模式是目前跨国破产法律适用的立法趋势,它反映了属地主义与普遍主义在法律适用上的博弈,也是跨国破产法律适用在立法上的成功典范。
三、意思自治原则在跨国企业集团破产中的发展
意思自治是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并在侵权等其他领域不断发展。在跨国破产领域,它指的是破产法律实体有权在清算或重组问题上选择其适用的破产法。但公司实体对破产法的选择应明确规定在公司的章程中,在没有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允许变更。一个公司如果选择了甲国的破产法作为准据法,就不能同时选择乙国法院对其管辖,因为在跨国破产领域,管辖法院在很多方面都适用法院地法,法律选择和法院选择的不一致容易引起更大的冲突。其他国家理所当然应该尊重公司实体的选择,但当公司债务人的选择不合理或不公正,与当地公共秩序相悖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破产程序或裁决。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论发展
美国学者拉斯穆森(Rasmussen)就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他曾经在文章中列举了公司在成立时可以作出的有关破产的5种选择。拉斯穆森认为,意思自治原则鼓励公司选择效率最高的破产法,使公司资产价值最大化,将更多的资产分配给债权人。将意思自治原则运用到跨国破产的法律适用中是有好处的。首先,公司在破产之前已经确定了破产应适用的法律,这就使跨国破产具有了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其次,在破产前确定了准据法避免了“挑选法院”情形的发生。
荷兰学者弗兰肯(Franken)也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她认为这种自由选择的制度可以使事前的确定性与事后利益最大化有效结合起来,并且能够更好地协调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破产的相关制度。
德国学者伊德穆勒(Eidenmueller)在其文章中还提及了四种类型的选择:一是准据法的选择(free choice of the applicable law);二是破产准据法的选择(free choice of the applicable insolvency law);三是破产法院的选择(free choice of the bankruptcy forum);四是破产法院与公司准据法的选择(free choice of the bankruptcy foru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mpany law applicable to a company)。伊德穆勒认为,法院选择与法律选择相结合的方式是最适合的。
在跨国破产的法律适用中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也受到了很多批评。首先,它可能会使受“强制的”法律适用体系保护的有关利益方失去了保护,例如:对基于侵权或其他非合同义务所提出的索赔;其次,债务人所作出的法律选择并不是选择一个最高效的破产制度,而是选择一个对其最有利的法律。而这样的选择对债权人来说是有失公允的。此外,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还可能会使应受担保权益保护的债权人受到影响。最重要的是,这种自由选择并没有真正反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它实质上是债务人单方面所作出的选择。债务人所作出的选择也不可能充分考虑到第三方的利益。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实践运用
在现今跨国破产体系下,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完全采用意思自治原则是不现实的。它的发展目前主要体现在“跨国破产协议”(cross-border protocols)中。从跨国破产协议面世至今20多年来,它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跨国破产所涉及的法院和当事方建立起了一个沟通与合作的桥梁,为在不同管辖区域开始的平行破产程序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便利。一般来说,跨国破产协议并不是预先解决在破产程序中可能出现的实质性法律纠纷,而是在纠纷或冲突发生之前对跨国破产进行协调管理。一旦破产案件发生,法院可以批准跨国破产协议,适用相关条款解决法律适用以及破产程序等有关问题。
近年来,跨国破产协议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使用的较多,如今也逐渐被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所接受。为了能够深入论述跨国破产协议在跨国企业集团破产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得不谈及著名的麦斯威尔案(Maxwell Communication Case)。
在美国法院和英国法院之间运用跨国破产协议最成功的案例就是麦斯威尔通讯公司案。1991年12月16日,麦斯威尔通讯公司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向美国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一天以后,英国高等法院法官根据英国法指定了联合管理人。美国法院法官蒂娜(Tina Brozman)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04条指定了审查人(examiner),而审查人的工作就是要协调《美国破产法》第11章的程序和英国程序,以维护麦斯威尔债权人、股东的权利。两个法院都授权审查人和管理人进行跨国破产协议的签订工作。协议书要求审查人和共同管理人在采取任何行动(如出售或抵押资产,提出重整计划等)之前必须进行协商。
霍夫曼法官(Justice Hoffman)这样评论麦斯威尔案件:
英国和美国法院在麦斯威尔案件中体现了高度的国际合作以及两国在破产法领域的协调。尽管两国的破产法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双方仍就有关问题达成了协议。麦斯威尔的分配方案正式建立在破产协议之上,避免了两国复杂的破产实体和程序上的冲突问题,使破产财产能够实现债权利益的最大化……
跨国破产协议在麦斯威尔案中所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成功地促使美国法院和英国法院进行合作,协调了平行破产程序,并最终解决了破产分配问题。
四、对我国涉外破产法律适用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涉外破产法律适用的立法现状
由于我国在跨国破产领域一直采取的是属地主义的方法,在涉外破产的立法上相对滞后。对跨国企业集团的破产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作为民法草案的第9编,在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时,第24条是有关破产的法律适用的。它规定:破产,适用破产人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律或者破产财产所在地法律。破产财产的评估,适用破产财产所在地法律。破产清算,适用作出破产宣告的法院所在地法律。该条直接采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关于破产法律适用的立法建议。但是由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已经删除了有关的条款。
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条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从以上条款可以看出,在其他法律对涉外破产的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与涉外破产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目前,由于我国在涉外破产的法律适用上没有作出其他的具体规定,“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就成了涉外破产法律适用的唯一依据。
(二)对我国涉外破产法律适用的借鉴意义
首先,正确区分非破产法与破产法的适用。在跨国破产案件的法律选择过程中,法院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根据非破产法,破产请求权的有效性以及索赔的金额的多少。第二,根据破产法,确定该请求权是否具有优先性,以及在破产财产的分配中顺序如何。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是不可混淆的。对有关财产权益纠纷的非破产法的适用,根据我国已有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进行法律适用,平等地对待国内外的当事人。而对于破产法应如何适用的问题,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的立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条所提及的“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似乎成了适用的依据。但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目前我国涉外破产的法律适用依据是不合适的。“最密切联系原则”体现的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方法,平等地对待各国的破产法。这虽然是涉外破产法律适用最希望达到的目标,但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属地主义或修正的属地主义的方法,不可能真正在涉外破产中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很可能就会想尽各种方法寻找连接点,最终将最密切联系地认定为在我国,从而适用法院地法。这种情形不利于我国涉外破产的发展,对国内国外的债权人也是不公平的。
其次,在涉外破产法律适用的立法上,可以参考《欧盟破产条例》的方式,以“法院地法”为一般规则,在特定事项的法律适用中规定例外情形。这需要在我国的单行法或司法解释中进行补充规定。这种立法既符合跨国破产法律适用的立法趋势,也有利于保护本国债权人的利益。在具体的法律选择中,对于跨国企业集团破产案件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整个破产案件适用一个破产法律,在一个破产法院进行,这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破产方式。这种法律适用会使得一国的国内破产法效力及于债务人资产存在的地方。另外一种法律适用方法则是适用启动破产程序国的法律,也就是法院地法。在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法律适用中,有一个妥协:作为一般原则,启动破产程序的法院适用法院地法,而在特定事项的法律适用中规定例外情形。这种做法在目前的跨国破产中已被广为接受。《欧盟破产条例》在目前跨国破产的国际性文件中,其法律适用的规定最为详尽、具体。第4条是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确立了“法院地法”的适用规则;第5至第15条则是特殊例外的条款。由于在现阶段要想统一各国破产法和相关破产程序是不切实际的,只能作为一个长远的目标和奋斗的方向。而《欧盟破产条例》的这种立法方式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
最后,注重破产协议在跨国破产合作中的作用与发展,研究跨国破产协议在我国适用的可能性。目前,最常见的跨国破产合作是通过“跨国破产协议”来实现的。笔者认为,对跨国破产协议适用的情形不应该有太多的限制,只要有利于跨国破产的合作,不损害我国债权人利益,都可以用。《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破产合作实务指南》(UNCITRAL Practice Guide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Cooperation)指出,跨国破产协议虽然是个案性的,但在某些情形下被认为更适合使用协议来解决跨国破产问题。跨国破产协议是对多个跨国破产程序进行管理的有效工具,以促进跨国破产程序为目标的国际项目或多或少都提及了跨国破产协议。例如:国际律师协会破产委员会(The Insolvency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在1995年以国际私法为基础,拟定了一项《跨国破产协约》(Cross-Border Insolvency Concordat),制定了协助谈判跨国破产协议的原则;欧洲破产协会制定的《联系与合作准则》建议使用跨国破产协议作为实现合作的最佳方式;2000年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在其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跨国破产的工作中,制定了《跨国破产案件法院对法院联系的适用准则》(Guidelines Applicable to Court-to-Court Communications in Cross-Border Cases),准则中提到应在联合审理情况下使用跨国破产协议。《欧盟跨国破产协调与合作指南(草案)》(European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Guidelines,draft)是由荷兰莱顿大学法学院鲍勃韦瑟尔斯(Bob Wessels)教授和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法学院米希尔威格斯(Miguel Virgós)教授草拟并在2006年9月公布的,它是有关跨国破产协议的法律文件。我国应加强在跨国破产协议的研究,分析其他国家的立法与实践,时机成熟时推行跨国破产协议在涉外破产合作中的运用。
[1]Simona Di Sano.COMI:the sun around which cross-border insolvency proceedings revolve:Part 2[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and Regulation,volume 24,issue 3,2009.
[2]Andrew T.Guzman.International Bankruptcy:In Defense of Universalism[J].98 MICH.L.REV,2177,2179,2181(2000);Jay Lawrence Westbrook.A Global Solution to Multinational Default[J].98 MICH.L.REV,2276(2000);Lynn M.LoPucki.Coope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A Post-Universalist Approach[J].84 CORNELL L.REV,696(1999);Frederick Tung.Fear Of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Bankruptcy[J].33 GEO.WASH.INT'L L.REV,555(2001).
[3]Hannah Buxbaum.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The Neglected Choice-of-Law Rules and Theory[J].36 STANFORD J.INT'L L,23,2000.
[4]American Law Institute.Transnational Insolvency Project.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in Transnational Insolvency Cases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M].American Law Institute,2003.
[5]Bruce Leonard(Editor-in-Chief).Norto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J].Thomson Reuters business,2010.
[6]Jay Lawrence Westbrook.Universalism and Choice of Law[J].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Vol.23,Issue 3,2005.
[7]Jay Lawrence Westbrook.A Global Solution to Multinational Default[J].98 MICH.L.REV,2000.
[8]Russell J.Weintraub.Commentary on the Conflict of Laws[M].4th ed.2000.
[9]黄进.《国际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J.L.Westbrook.Locating the Eye of the Financial Storm[J].Brook.J.Int’l L,2007.
[11]P.K.Rasmussen.Resolving Transnational Insolvencies Through Private Ordering[J].98.Mich.L.Rev,2000.
[12]Hannah L.Buxbaum.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The Neglected Role of Choice-of-Law Rules and Theory[J].STAN.J.INT’L,2000.
[13]Rechard E.Coulson.Choice of Law In United States Cross-Border Insolvency[J].DENV J.INT’L&POL’Y,Vol.32,2004.
[14]石静遐.《跨国破产的法律问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15]Jay Lawrence Westbrook.Theory and Pragmatism in Global Insolvencies:Choice of Law and Forum[J].American Bankruptcy Law Journal,1991.
[16]Irit Mevorach.Insolvency with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Group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7]Bob Wessels,Bruce A.Markell,Jason J.Kilborn.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Bankruptcy and Insolvency Matter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18]Robert K.Rasmussen.Debtor’s Choice:A Menu Approach to Corporate Bankruptcy[J].71 Tex.L.Rev.51(1992);Robert K.Rasmussen.A New Approach to Transnational Insolvencies[J].19 Mich.J.Int’l L.1(1999);Robert K.Rasmussen.Resolving Transnational Insolvencies through Private Ordering[J].98 Mich.L.Rev.2252(2000).
[19]Robert K.Rasmussen.The Problem of Corporate Groups,A Comment on Professor Ziegel[J].7 Fordham J.Corp.&Fin.L,2002.
[20]Alan Schwartz.A Contract Theory Approach to Business Bankruptcy[J].107 Yale L.J,1807(1998);Lynn M.LoPucki.A Reply to Alan Schwartz's“A Contract Theory Approach to Business Bankruptcy”[J].109 Yale L.J,317(1999);Robert K.Rasmussen.Where Are All the Transnational Bankruptcies?The Puzzling Case for Universalism[J].32 Brook.J.Int’l L,983(2007).
[21]Safa M.Franken.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Bankruptcy Law:A Review[J].11 European L.J,2005.
[22]Horst Eidenmueller.Free Choice in International Company Law in Europe[J].6 Eur.Bus.Org.L.Rev,2005.
[23]Jay Lawrence Westbrook.A Global Solution to Multinational Default[J].98 Mich.L.Rev,2000.
[24]Muir Watt.Choice of Law in Integrated and Interconnected Markets:A Matter of Political Economy[J].Ius Commune Lectures on European Private Law No.7,2003;Safa M.Franken.Three Principle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Bankruptcy Law:A Review[J].11 European L.J,92(2005);Elizabeth Warren&Jay Lawrence Westbrook.Contracting Out of Bankruptcy:An Empirical Intervention[J].118 Harv.L.Rev,1198(2005).
[25]Paul H Zumbro.Cross-border Insolvencies and International Protocols-an imperfect but effective tool[J].Business Law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2004.
[26]Norto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M].West,2010 edition.
[27]季立刚,解正山.美国跨国破产立法的最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