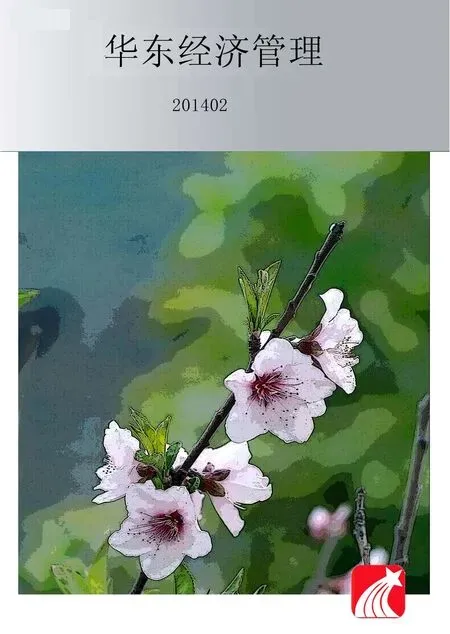服务型政府下的街头官僚问责制研究
——街头官僚绩效测量体系的构建
颜海娜,丁 元
(1.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 公共行政学系,加州 富尔顿 92831)
服务型政府下的街头官僚问责制研究
——街头官僚绩效测量体系的构建
颜海娜1,丁 元2
(1.华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2.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 公共行政学系,加州 富尔顿 92831)
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以广州市工商局A分局为样本,参考平衡计分卡模型及关键绩效指标法,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绩效测量体系的构建,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利用绩效管理工具,以及让包括基层执法人员在内的所有内部利益攸关者参与绩效指标的构建来落实对街头官僚的问责,进而推动政府的治理转型。
街头官僚;问责;服务型政府;绩效测量
一、引 言
2003年,叶娟丽、马骏在《武汉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的论文[1],首次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街头官僚理论。在这之后,尽管我国学者也做了不懈探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中国街头官僚研究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而仅有的研究又大多停留在以李普斯基为代表的西方街头官僚理论的介绍,鲜有将街头官僚放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背景下进行实证性的探讨,这与中国街头官僚的庞大数量及其影响力是非常不相称的。
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以广州市工商局A分局为样本,通过对基层行政执法人员绩效测量体系的构建来探讨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利用绩效管理工具来落实对街头官僚的问责,进而推动政府的治理转型。
二、街头官僚的问责制研究
(一)街头官僚的角色及自由裁量权
1977年,美国学者李普斯基首次提出了“街头官僚”的概念[2],开创了街头官僚的研究,由此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注。李普斯基把“街头官僚”定义为“那些在工作过程中直接与公众进行互动,并且在执行工作过程中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公务员”[3]。在我国,基层公务员和执法人员,例如行政服务大厅窗口的工作人员、派出所的片警、工商局的段管员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街头官僚。街头官僚处于政府管理的第一线,他们直接与民众打交道,他们决定了公共服务的好坏,因为公共政策最终能否得到切实有效地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于政策执行末梢的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挂羊头,卖狗肉”等政策执行偏差行为,有相当一部分原因出自作为执行者的街头官僚上,人们所诟病的“好经被坏和尚念歪了”中的“坏和尚”指的往往也是街头官僚。因此,街头官僚的工作态度、业务素质、专业技能以及服务水平等决定了公共服务以及政府工作效率的高低。
事实上,街头官僚不仅在执行公共政策,他们同时也在制定公共政策,其政策制定角色是建立在他们“相对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相对于组织权威的自主权”上[3]。由于街头官僚的工作环境充满了挑战、风险及不确定性,很难对其工作进行程序化规定,并且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经常面临着如何解释法规与政策的问题,因此赋予街头官僚必要的管理弹性以及自由裁量权是必需的。此外,在很多情况下,官僚机构的资源在满足顾客需求上总是不充足的,因而街头官僚需要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决定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优先满足哪些顾客的需求,进而实现机构所赋予的任务[3]。自由裁量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街头官僚提供依靠专业判断和工作情境特殊知识灵活处理及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便利;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及服务对象的非自愿性,自由裁量权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3]。因此,如果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街头官僚有可能随意地对待顾客,或者漠视顾客的需求,甚至是滥用职权及侵害公民权益。
关于中国的街头官僚有多大的自主性这个问题,学术界有截然不同的观点。“自上而下”(top-down)的观点认为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自主性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由高层领导制定的执行框架与制度强化了组织纪律,对街头官僚的行为有相当程度的约束,使得他们最多也只能略微地调整政策执行的手段,但无法拒绝或选择性执行政策[4]。“自下而上”(bottom-up)的观点则认为,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权是比较大的,上级对基层政策执行者的控制手段有限,并且执行者拥有许多的“抵制资本”,他们可以在执行过程中改变政策的实质[5]。如果把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的自主性问题放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地方政府自主性空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自下而上”的观点似乎更具有解释力。伴随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及持续性的行政改革,传统的单一的中央高度集权模式逐步转向多元化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并存的新格局,地方政府逐渐成为拥有独立的财力和财权,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公共事务管理主体[6],其权限及行为选择空间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相对地也为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提供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然而,我们不能为了夸大街头官僚的自主性而忽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因为任何政策的“制度结构,可得资源,以及可进入的执行场域极可能都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其实质性地影响着政策执行结果”,并且“所有执行者的行动可能都要落到中央所框定的政策范围内”[7]。欧博文和李连江在对中国乡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上述两种分析途径都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农村的基层官僚对有些政策执行得很成功,对另一些政策则执行得很不理想;换句话说,他们有时扮演恪守原则的代理人,有时却变成回避上级意志的投机者[8]。这意味着在探讨中国情景下的街头官僚问责制时,我们不能仅仅注重组织目标和正式的规章制度,还必须考虑到基层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对政策执行过程和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街头官僚的问责困境
传统的命令与控制模式强调限制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强化组织的规章制度来加强对其行为和工作过程的监督和控制,进而落实街头官僚的问责制。然而,政策目标的冲突与不确定性,以及政治与行政问题的不可分性,使得削减街头官僚的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难以践行;加上管理者与街头官僚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街头官僚能比较容易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避免问责,并以问责的名义来规避和摆脱这些控制他们的努力”[3]。并且,过于强调管理控制也有可能破坏公共服务的质量,因为在落实问责制的名义下,对街头官僚提供公共服务或执行公共政策的具体行为进行过多的干涉,虽然可以引导街头官僚更好地遵循机构的政策,但也有可能挫伤他们的公共服务动机(如“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作为命令与控制模式的替代,新公共管理的量化评估模式,摒弃了控制的管理策略,在赋予街头官僚必需的自由裁量权前提下,试图通过绩效评估体系对街头官僚的工作产出与结果进行考核,从而实现对其的问责。然而,一味地追求量化的绩效措施可能会妨碍公共服务的质量,导致他们专注于那些可被测量的工作,漠视其他不容易被量化的任务[8],进而诱发他们的“选择性执行”甚至是弄虚作假的行为[3]。
此外,上述策略虽然在表面上加大了政府强化问责制的努力,但它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隐藏因素——街头官僚本身对其工作过程和环境的认知。因此,要对街头官僚进行有效的问责,我们不能仅仅依靠传统公共行政下的命令与控制模式,或是新公共管理所追求的量化评估模式,而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那些一线的政策执行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以及他们实际操作的方式,并试图理解街头官僚的世界,和他们所需面对的管理目标、顾客要求以及官僚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9]。目前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在构建基层人员绩效考核体系的时候,通常是以管理阶层立场为主,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绩效考核被作为规范和约束街头官僚,以体现管理者行政意图和政策偏好一种常见的问责手段。然而,在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体系下,管理者大多数时候只是站在组织与科层的角度来思考,而忽视了基层官僚所面临的复杂工作环境、相对匮乏的执行资源以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鉴于这一思路,本文从街头官僚的角度,着重于设计一套针对广州市工商局基层执法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用于落实对街头官僚的问责,进而推动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三、案例分析——街头官僚绩效测量体系的构建
(一)研究样本背景介绍
近年来,广州市政府采取了很多举措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管理方式,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其中,为了改变传统的“以罚代管”、“命令强制”的模式,广州市政府以工商局为试点,推行“公共服务型市场监管执法机关”的建设,要求工商局融服务于监管之中,在履行监管职责、规范监管流程的同时,更好地为工商业户和消费者服务。作为基层工商执法人员的段管员分布在A分局下辖的8个工商所内,他们处于工商局管理的最末梢,是典型的“街头官僚”,其主要职责是“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上级工商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职责和时限,或根据网格特点、监管重点及工作计划,对相关市场主体实施的巡查监管工作”,例如检查市场主体是否有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者无照经营的行为。按照广州市网格化服务监管的要求,段管员除了要履行基本的监管职能之外,还承担了一定的服务职能,如“依法为网格内的经济组织和群众提供服务”、“调解消费纠纷”等。段管员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服务型政府的政策主要依靠基层公务员来落实。工商服务监管的绝大部分职责,都需要通过处于第一线的段管员才得以具体落实。另一方面,由于直接面对监管与服务对象,段管员执法的素质、能力、作风等都代表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由于执法环境的复杂性、任务的庞杂以及专业性的要求,段管员在其工作过程中拥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根据威尔逊的观点[8],工商部门属于典型的“应付型组织”——工作付出和成果都不易被观察到。其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一般不容易观察,例如每个段管员在其责任“网格”内是如何开展巡查工作的、具体巡查了多少个经济业户、有没有认真按照要求来巡查等,分局的管理者是无法进行实时观察的,一般通过要求段管员在巡查之后把巡查监管记录输入信息系统的办法来进行监控。至于段管员在巡查过程中是否“走过场”或虚报,信息系统是无法识别的。由于信息在管理者与段管员之间是严重不对称的,段管员可以发展出一套“机制”以应付管理者的控制,例如他们在保留工作记录时总是会有意识地防备以后的审查[3];在绩效目标的驱动下,他们会倾向于“刮脂”[10],即专注于那些容易处理以及让他们的绩效评估结果看上去更好的工作;一些段管员甚至会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权力寻租,以谋取个人的不正当利益。而管理者通常较难以掌握段管员工作的细节,也不大清楚他们是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是否有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情况发生,因而也就难以对段管员进行有效的问责。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绩效测量指标体系的设立,引导基层执法人员转变他们执法方式和行为,以提升监管效能及服务水平,进而推动广州市政府的治理转型。
(二)从街头官僚角度设计的绩效测量体系
与大多数政府部门一样,A分局以往在构建基层执法人员绩效测量体系的时候,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具体的考核项目、指标、方式以及结果的应用等,都是由分局领导和职能科室的负责人来决定,而作为重要利益攸关者的段管员通常被排除在体系设计之外。例如,在2008年的段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中,上级领导设置了“罚没收入入库额”、“限塑率”、“无照整治率”、“食品‘三无’产品抽查率”等段管员难以控制的结果性导向指标。因而,一方面,异化的绩效目标诱导了段管员的“选择性执法”行为(选择那些执法成本低、有助于完成上级指标的任务,而对那些吃力不讨好、对完成上级指标贡献不大的任务则采取消极应付甚至阳奉阴违的态度),或“一线弃权”行为(逃避一些容易导致冲突或纠纷的任务)。另一方面,绩效考核的最终结果无法真正反映段管员的实际工作表现,出现了“干得越多扣分越多”、“得分高而绩效不高”的绩效悖论。
在探索性研究阶段对段管员的深度访谈中,我们发现段管员对现有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普遍抱有一种不满情绪。有的段管员抱怨说,“考核目标与实际工作脱节……目标订得比天高,而工作需要我们基层人员一点一点做出来的”;有的段管员认为已有的考核“对段管员太求全责备了,有的时候即使段管员很尽职尽责地去干,但一些外在的不可控因素会大大降低段管员的绩效,如无照问题”;还有的段管员对现有的管理体制颇为不满,认为绩效考核变成了上级管理者往下卸责的一种工具,“分局的管理格局是‘两头尖,中间大’,领导层和基层工商所为两头,而处于中间的业务科室的权力太大,一味地把责任往工商所身上推…基层工商所和段管员太苦,工作压力太大,权责严重不对等”。
如前所述,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体系经常忽视基层执法人员所面临的环境及其挑战,容易导致考核与基层的实际工作内容相脱节,并且过于强调执法行为的权力色彩,相对忽视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以及顾客的需求。在以往的工商执法实践中,执法者的权力意识和执法行为的权力色彩比较浓厚,经常依靠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执法手段,对有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行政相对人动辄进行罚款或者没收,这种“强制性行政可能会因为相对人或相关人的有意或无意的抵制而减损行政效能”[11]。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府执法方式的变革,其具体表现是:淡化执法者的权力意识,强化行政相对人的各种程序性权利,加强强制性权力在行使过程中的合理性,并且更多地使用行政提醒、辅导、建议以及规劝等柔性的执法手段。例如,在无证照整治中,段管员以往的做法是通过行政强制手段直接取缔。执法方式变革后,段管员会根据无证照的不同情形分别进行相应的行政辅导。对于“正在筹建没有经营行为”的无证照情形,段管员会查明经营者、出租方联系方式、经营项目等情况,然后向当事人发出温馨提示,提醒当事人办理证照,并将有关资料存档,进行跟踪指导。
2010年6月,为了落实广州市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策要求,广州市工商局下发了《关于网格化服务监管考评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分局“进一步完善网格化服务监管工作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以“指导基层工商所及工作人员不断提高服务监管水平,实现监管与服务的有机统一”。因此,如何基于网格化服务监管背景,落实市工商局的文件精神,设计一套针对段管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是分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然而,市工商局的文件中对于段管员如何落实服务监管的职责规定得非常笼统,只是把“为网格内的经济组织和群众提供服务的情况”规定为考评段管员的内容,而在考核指标的设计中,如何把考评内容转化为具体的考核指标,是分局管理者面对的一个难题。在监管过程中到底哪些环节需要段管员提供相应的服务?哪些服务性指标对于落实网格化服务监管职能更加重要?考虑到段管员直接面对工商业户和消费者,更能够知道他们的服务需求,分局的领导层决定改变以往的自上而下构建绩效考核体系的做法,在新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中把作为重要利益攸关者的段管员纳入进来,重视段管员的话语权以及发挥他们的专业知识在指标设计中的作用。
为了提高考核指标体系的效度和信度,广州市政府引入了独立第三方机制。在工商局的委托下,我们首先进行前期的探索性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10年7月5日到7月16日),我们针对A分局的管理层,即其主要领导(包括局长、分管绩效考核的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各业务科室的负责人(包括科长、副科长等)进行了深度访谈;第二个阶段(从2010年7月16日到7月27日),我们根据监管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监管对象的类型,从分局中抽取了3个代表不同监管难易程度的工商所,深入访谈了这3个工商所的所长、副所长以及所有的段管员,从街头官僚的角度来了解他们对分局现有绩效考核制度的看法,以及对构建新的段管员绩效考核体系的具体想法;第三个阶段(从2010 年7月至9月),课题组成员分别到两个工商所,对段管员日常工作的具体过程进行参与式观察。在探索性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参考计分卡模型(在下面一节详细讨论)设计了《广州市工商局A分局绩效考核制度及考核指标体系咨询问卷》,于2011年2月至3月,对分局全体工作人员进行了结构性访谈①。访谈对象囊括了分局领导、中层管理者以及基层执法人员,共计133人,其中两人拒绝接受访谈,有效访谈率为99.2%。在131个有效访谈中,分局领导、中层管理者以及基层执法人员的比例分别为6.9%、42%以及51.1%(见表1)。

表1 接受访谈的样本特征
(三)构建街头官僚绩效测量体系的框架
为了更有效地设计一套针对段管员的绩效测量体系,我们参考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简称BSC)模型来帮助A分局构建段管员绩效测量体系的框架。平衡计分卡最初是由卡普兰和诺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私人部门而设计的绩效测量工具。他们指出,仅仅考虑财务维度对于测量绩效以及管理组织是不够的,高层管理需要考虑不同维度和有关信息,例如质量、市场、顾客、供应方、竞争以及技术等,以帮助组织决策和战略规划[12]。换言之,管理者需要同时考虑财务和其他三个非财务的维度,包括顾客、内部流程、学习与进步,才能从不同的视角更全面地审视组织绩效。
BSC作为绩效及战略管理工具,已经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的公共部门中有所应用。此外,BSC也在医疗卫生、城市垃圾管理以及非营利组织等领域中得到了采用[13]。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BSC提出了一个适用于公共部门测量多元目标和利益攸关者绩效的多维度观点[14];BSC能够把组织高层的战略目标落实为基层员工的个人目标,并“在笼统的使命和战略目标与具体的工作行动之间搭建一座桥梁”[12];BSC能帮助公共部门设计绩效测量指标,并把绩效指标集中在最关键和可管理的事情上[15];此外,BSC可以被用于作为对外部利益攸关者沟通的工具,为决策者以及纳税人提供更多的信息,以改进公共部门绩效及强化对其的问责[16]。鉴于这些研究结果,为了落实街头官僚的问责制,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我们必须从一个多维度的、顾客的角度来思考段管员绩效测量体系的构建问题,并且要跟组织的战略目标—建立服务型政府—紧密地结合起来。
根据卡普兰和诺顿的BSC模型,我们为分局构建的绩效测量框架具有如下特点(见图1):保留了初始模型的四个主要维度,明确工商部门的“远景战略”是打造“公共服务型市场监管执法机关”;把“顾客”维度放在模型的最顶端以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工商局所服务的“顾客”群体包括工商业户和消费者;将“财务”维度改为“落实监管职责”,因为财务结果并不代表公共部门组织的“底线”,对于基层执法人员而言,落实监管职责才是他们最基本的工作要求;把“内部流程”维度改为“规范监管流程”,工商部门作为典型的行政执法机关,对于行政业务流程的标准化、程序化以及规范化有更加严格的要求。在巡查监管的过程,段管员必须按照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严格执行执法程序;“学习与成长”维度改为“提高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

图1 A工商分局绩效测量框架
(四)街头官僚绩效测量指标的设定
如前所述,我们参考BSC模型构建段管员绩效测量体系的框架,并确定了组织的战略目标。接下来,我们采用关键绩效指标法(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来设计段管员的绩效考核指标。KPI是以组织目标和岗位描述为基础,通过将组织的目标层层分解,结合岗位职能落实到组织成员的绩效指标。它的核心观念是组织中80%的绩效可通过20%的关键指标来把握和引领,因此,每个组织应集中全力找出那些能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最关键绩效指标。
A工商分局构建的绩效测量框架确定了该组织的四个基本目标─融服务于监管之中,提高工商业户和消费者的满意度;落实网格化服务监管职责,完成监管工作任务;完善和优化监管流程,规范执法人员的监管行为;提高执法人员的监管能力和服务水平。在确定四个目标之后,我们接着对这些目标进行层层分解,结合段管员的岗位职责确定个人目标,并采取KPI法首先析出段管员的一级指标(见表2)。表二显示,段管员的岗位职责共为八项,其中,第一、第二、第八项职责属于段管员“监管能力”的内容;第三和第五项职责属于“服务监管”的内容;第四项职责中有属于“监管业务”的内容(考核具体的监管业务开展情况),也有属于“监管基础工作”(考核段管员在开展巡查监管的时候是否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规定来做)的内容;第六和第七项职责属于考核“监管业务”的内容。
对应分局的四个主要目标,我们从段管员的关键职责中析出四个一级指标(见表2),分别为“服务监管”、“监管业务”、“监管基础工作”以及“监管能力”。由于段管员所面临的监管环境具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例如辖区内经济业户的数量、类型及分布的聚集程度,临时性、突发性任务的多少,消费者投诉的数量,以及监管工作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程度都可能影响到其绩效考核的结果。为了设计出来的考核指标体系与段管员的实际工作情况更加吻合,我们在上述四个一级指标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个“监管环境维度”。

表2 段管员绩效测量体系中的一级指标
在确定段管员的四个一级指标之后,接着需要考虑的是影响他们职责的关键成功因素是什么,然后根据关键成功因素设计12个二级指标(见表3)。在“服务监管”中,其关键成功因素为“工商业户和消费者对段管员服务的满意程度”,因此可以相应析出“服务工商业户”和“服务消费者”两个二级指标;在“监管业务”中,其关键成功因素为“段管员落实市场监管(包括无证照监管)、食品安全监管、商标广告合同监管以及经济检查职责的程度”,因此可以相应析出“市场监管”、 “食品安全监管”、“商标广告合同监管”以及“经济检查”四个二级指标;在“监管基础工作”中,其关键成功因素是“段管员在巡查前期、具体实施以及后期整理三个阶段是否按照ISO的工作流程及时规范地开展工作”,因此可以相应析出“巡查前期”、“具体实施”以及“后期整理”三个二级指标;在“监管能力”中,其关键成功因素是“段管员监管业务知识和监管技能的掌握程度”,因此可以相应析出“监管业务知识”和“监管技能”两个二级指标。
为了进一步设定段管员的三级绩效指标,我们根据探索性研究阶段对分局主要业务科室的负责人、三个工商所的所长和副所长及其段管员深度访谈所搜集的资料,从不同角度深入挖掘影响段管员绩效的多种因素,然后在参考A分局工商所以及其他工商分局段管员绩效考核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初步为段管员设定了80个三级绩效指标,具体见表3。
段管员绩效测量指标初步设计出来后(表3中的三级指标),传统的做法是从分局领导和职能科室的角度来筛选最终适用于段管员的绩效考核指标,很少把作为被考核者的段管员纳入考核指标构建的过程当中。有别于以往的做法,我们对A分局全体工作人员(包含67位段管员)进行结构化访谈,并采取李克特量表的方式来测量所有三级指标对他们的重要性(“非常重要=5”、“比较重要=4”、“一般=3”、“不太重要=2”、“不重要=1”)。通过访谈收集的数据和因子分析法(在下面一节详细讨论),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包括基层执法人员在内的分局所有利益攸关者对绩效指标的观点,以建立一个更具有可操作性,更能强化街头官僚问责制的绩效测量体系。

表3 段管员绩效测量指标的初步设定

续表3

续表3
(五)街头官僚绩效测量指标的因子分析结果
如前所述,初步设计出来的绩效测量体系共有80个指标,为了有效地识别哪些是最重要的关键考核指标并对其效度进行验证,我们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帮助提取相关性最高的指标。因子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工具,它通过研究众多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探求观测数据中的基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隐性变量来表示基本的数据结构,最终达到浓缩数据的目的[17]。简而言之,因子分析就是研究如何在牺牲最小信息的情况下把众多的观测变量浓缩为少数几个因子。例如,在表3中涉及“服务工商业户”的指标有高达15个,这15个指标(变量)之间可能是高度相关的,它们所反映的信息可能是高度重合的。通过因子分析我们能找到较少的几个因子来反映数据本质特征,如此,可帮助我们找出能反映“服务工商业户”领域中最重要的关键指标。由于本文的篇幅所限,下面将以“服务工商业户”为例,报告因子分析的结果。
首先,我们运用KMO样本测度法(Kaiser-Meyer-Olkin Measures of Sampling Adequacy)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法(Barlett Test of Sphericity)对指标相关性及模型适用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KMO样本测定值为0.857,因此,我们初步设定的“服务工商业户”的三级指标可用于因子分析;同时,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值为867.822,自由度为105,显著性概率为0.000,显示指标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适用于因子分析。接着,我们采取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分析法求初始公因子特征值(Eigenvalue)、方差贡献率(%of Variance)和累计方差贡献率(Cumulative%)(见表4)。第一主成分F1是四个因子当中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它在指导行业协会、商会,落实帮扶计划,提供经济信息,定期访问工商业户,听取经济业户的要求和建议,积极落实分局和工商所指定的各项服务工商业户措施,经营风险防范提醒上有较大的负载,因此命名为“沟通及提供信息服务因子”;第二主成分F2是四个因子当中次重要的影响因子,它在宣传工商管理法律法规、积极引导办照、宣传年检、验照规定和要求上有较大的负载,因此命名为“宣传因子”;第三主成分F3在开展企业诚信建设活动,推荐培育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积极指导推荐企业参加为省、市著名商标的申请认定,及时处理合同纠纷调解上有较大负载,因此命名为“商标和合同服务”因子;第四主成分在对正在筹建但没有经营行为经济业户,归档有关资料,进行跟踪指导,提醒许可证过期或失效,督促经济业户进行年检、验照上有较大的负载,因此命名为“证照服务”因子。经过因子分析后,我们可从“服务工商业户”15个三级指标中提取出4个最能反映其变量之间关系的因子,并用它们作为最终关键指标来测量段管员在这方面的绩效。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从所有80个三级指标中提取出25个因子,这25个因子平均能解释总量变异的70%。

表4 “服务工商业户”的因子分析结果

续表4
但是,我们不能把因子分析作为唯一的提取指标的方法。除了用因子分析提取的25个关键指标之外,我们还结合所搜集的政府资料、深度访谈的数据,以及对段管员的巡查监管行为进行的参与式观察来提取和筛选关键指标,最终选择了33个关键指标(见表5)。我们的基本思路是,对于能够考核段管员结果的工作事项,尽可能设定结果型指标,如亮照率、持照率、户外广告登记率等;对于不能够考核段管员结果的事项,退而求其次,设定行为型指标,如规范填写各种巡查规范性文件和表格、责令限期年检和验照等;对于既不能测量段管员的工作结果,也不能考核他们行为的事项,设定能力型指标,如工商业务知识和管理系统的操作能力等。

表5 段管员关键绩效指标的最终提取结果

续表5
四、结 论
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绩效测量被很多西方国家当作一个主要的政策工具以强化政府的问责。在这个效应的影响下,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热衷于利用绩效考核来落实对政府官员的问责。然而,面对这一个趋势,我们不禁要问,绩效考核真的有助于落实对官僚的问责,进而提高政府的绩效吗?“问责→绩效”是否被许多学者及政府官员奉为“圭臬”而变成一个不受挑战的命题[18]?因而,学者们有必要对问责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地探索。基于这个观点,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法,以广州市工商局为例,参考卡普兰和诺顿的BSC模型,结合公共部门的特点和背景,通过结构化访谈搜集的数据设计一套绩效测量体系,来落实对街头官僚的问责制,以推进广州市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第一,可以通过街头官僚绩效测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将服务型政府从符号行政转化为真正的行政实践。目前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与此同时,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研究也成为这几年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热点。然而,鲜有研究从实证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把服务型政府的治理理念转化为对地方政府街头官僚的具体问责。服务型政府到底在地方如何落实,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落实,这对于实践工作者而言可能是一个挑战,正如广州市工商局A分局所面临的如何把服务的元素融入段管员的监管工作中的问题一样。对于研究者而言,仅仅停留在对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总结上是不够的。如何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把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落实到政府的治理实践中,如何在绩效测量体系的设计中充分地考虑到街头官僚在政策执行中的自由裁量权以及问责问题,如何结合公共部门的背景和特点把私人部门先进的绩效管理工具运用到公共部门中去,学者们应该对此有更加深入的思考以及应该在指导实践上更有所作为。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参考BSC模型构建了一个绩效测量体系的框架,从战略管理的角度确定了组织绩效的四个维度,然后把这四个维度的绩效目标层层分解为段管员的具体考核目标,并在这基础上设计出段管员的三级绩效考核指标,并采用李克特量表的方式通过结构化访谈收集关于这些考核指标的重要性信息,最后采取因子分析法把影响段管员绩效的最关键指标提取出来。当然,由于公共部门组织运作的范围非常广,而且目标、活动、产出等的多样性以及难以量化,要构建一套简洁易行的、能够涵盖所有主要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标非常困难,这对于广州市工商局A分局而言也不例外。在段管员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考虑到执法机关的特点以及段管员执法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监管环境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程序性和行为性指标上,而非产出和结果性指标。
第二,在我国政治文化背景和制度框架下,通过绩效目标的价值导向以及绩效指标体系的构建可以将街头官僚的问责落到实处。如本文所述,转型期中国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街头官僚有关,因为街头官僚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大任务就是必须改变政府的责任指向,将原来纯粹向上的负责机制转变为多向负责机制。政府不再只对上级负责,更重要的是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这样的制度的安排下,政府及公务员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与服务态度,成为服务型政府的近期目标”[19]。因而,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来落实街头官僚的问责制,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中国政府及学者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方国家,官僚的问责机制是多元的,既有科层问责(强调效率,要求服从组织)和法律问责(强调法治,要求遵从法律),又有专业问责(强调专业知识,要求遵从个人判断、专业知识以及专门技术)和政治问责(强调回应性,要求对民选官员、顾客群体以及一般公众等的回应)[20]。西方国家政府的问责机制是建立在深入人心的问责文化、发达的公民社会以及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等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的行政问责主要依靠议会、法院、社会组织及公民等外部问责,而不是仅在行政部门的内部问责。然而,在非民主的政治文化中,“问责可能只是形式上存在,并且缺乏一个精心设计的多元化问责框架”[21]。中国这些年在官员问责的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官员问责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但由于公民社会不发达、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疲软、问责的制度设计不够完善等一系列的原因,使得我国目前对官员的问责主要还是以科层问责为主,现有的官员问责机制绝大多数是以上级党政部门为主[22]。总体而言,我国“问责的监督主体也自上而下递减弱化,上级党政部门监督力度最大,人大、人民法院等实体监督难以发挥其职能,民主党派、公众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状态”[23]。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制度框架下落实街头官僚的问责制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学者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在这个案例中,广州市工商局A分局在落实段管员监管职责,规范其监管行为(强化科层问责)的同时,通过服务性指标的设计来引导段管员更好地服务工商业户和消费者,从而间接地促进段管员的政治问责,是地方政府在不突破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对如何强化街头官僚问责的一个值得鼓励的尝试。
第三,应该重视街头官僚在构建绩效测量指标体系中的话语权问题。由于街头官僚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所处的特定工作场域,仅仅依靠传统公共行政的命令控制模式或新公共管理的量化评估模式都无法对街头官僚进行有效问责。因此,我们要试图理解街头官僚的世界,要增强街头官僚在构建绩效测量指标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也是行政管理实践中贯彻群众路线的表现。街头官僚,作为地方政府中的“基层人民”,是对外管理中政府与人民衔接的“中间型人民群体”,他们的意见是一个绩效评价体系具有“观赏价值”还是具有“实践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与大多数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不同,A分局在段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过程中,让包括基层执法人员在内的所有内部利益攸关者参与绩效指标的构建,这一方面体现了对作为被考核者的段管员的话语权的尊重,重视街头官僚的专业知识、专门技术、执法经验以及个人判断在指标构建中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段管员的一种专业问责;另一方面,使得所构建的绩效指标体系更可能得到街头官僚的认同与支持,减少组织监控的成本。
遗憾的是,A分局在构建绩效测量体系的时候,没有把组织外部利益攸关者(如工商户和消费者)纳进来,而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意见对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至关重要。本研究只着眼于街头官僚绩效测量体系的设计,广州市工商部门构建的这一套绩效测量体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落实对基层执法人员的问责制,它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遇到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是什么,还有待于未来的进一步实证检验。此外,基于中国的情景,通过什么样的制度设计,把组织外部利益攸关者纳进街头官僚绩效测量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也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
注释:
① A分局在编人员共179人,访谈期间在岗的有133人。
② 根据企业遵守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及违法情节轻重等情况,将企业相应分为守信(A类)、警示(B类)、失信(C类)、严重失信(D类)四个信用类别。工商部门对于不同信用类别的企业分别采取企业信用分类监管。
[1]叶娟丽,马骏.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6(5):612-618.
[2]Lipsky M.Toward a Theory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C]// Hawley W,Lipsky M.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Urban Pol⁃itic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77.
[3]Lipsky M.Street-Level Bureaucracy:Dilemmas of the Indi⁃ 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10.
[4]Harding H.Organizing China[M].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350-351.
[5]O’Brien K J,Li L.Selective Policy Imp 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J].Comparative Politics,1999:31(2):167-186.
[6]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及其行为逻辑——基于地方政府自主性的视角[J].浙江大学学报,2007,37 (6):25-35.
[7]Matland R E.Synthe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The Ambiguity-Conflict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J].Journa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 Research&Theory. 1995,5(2):145-174.
[8]Wilson J Q.Bureaucracy:What Government Agencies Do and Why They Do it?[M].New York:Basic Books,1989.
[9]Brodkin E Z.Accountability in Street-level Organizations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8,31 (3):317-336.
[10]Thiel S V,Leeuw F L.The Performance Paradox in the Public Sector[J].Public Performance&Management Re⁃view,2002,25(3):267-281.
[11]肖金明.论政府执法方式及其变革[J].行政法学研究,2004(4):9-16.
[12]Kaplan R S,Norton D P.The Balanced Scorecard-Measures that Drive Performance[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2,70(1):71-79.
[13]Sharma B,Gadenne D.Balanced Scorecard Implementation in a Local GovernmentAuthority:Issues and Challenges[J].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2011,70(2):167-184.
[14]Nothcott D,Taulapapa T D.Using the Balanced Scorecard to Manage Performance i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Is⁃sues and Challenge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2012,25(3):166-191.
[15]Chan Y L.Performance Measurement and Adoption of Bal⁃anced Scorecards-A Survey of Municipal Governments in the USA and Canad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2004,17(3):204-221.
[16]Griffiths J.Balanced Scorecard Use in New Zeal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Crown Entities[J].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2003,62(4):70-79.
[17]Kim J,Mueller CW.Introduction to Factor Analysis-What It is and How to Do It[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78.
[18]Dubnick M.Accountability and the Promises of Perfor⁃mance:in Search of the Mechanisms[J].Public Adminis⁃tration Performance&Management Review,2005,28(3):376-417.
[19]沈荣华,沈志荣.服务型政府论要[J].行政法学研究,2008(4):78-83.
[20]Romzek B S.Dynamic of Public Sector Accountability in an Era of Reform[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 inistra⁃tive Sciences,2000,66(1):211-44.
[21]Smith T S.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ureaucratic Ac⁃countability[J].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1991,13(1):93-104.
[22]宋涛.中国官员问责发展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8,276(1):12-16.
[23]齐秀强,李冰水.官员问责制度化:现实困境与制度设计—对“问责风暴”的深层思考[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56(2):9-12.
[责任编辑:欧世平]
Holding Street-levelBureaucrats Accountableunder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Building a PerformanceM easurement System for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YAN Hai-na1,DING Yuan2
(1.Schoolof Politics&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2.Departmentof Public Adm inistration,California StateUniversity,Fullerton,Fullerton 92831,US)
Using the case analysismethod and taking a Bureau A of Guangzhou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for Industry and Commerce as a sample,the paper shows how to design a performancemeasurement system for the street-level code enforce⁃ment officers.It also explores how do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use different performancemanagement tools like the Bal⁃anced Scorecard model and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and incorporatemajor stakeholders including code enforcement offi⁃cers into its designing process for creating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o hold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ccountable to the needs of citizens,thu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street-level bureaucrats;accountability;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performancemeasurement
F062.6
A
1007-5097(2014)02-0127-10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4.02.025
2013-08-07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青年项目(GD10YZZ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630261)
颜海娜(1977-),女,广东茂名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府组织与绩效管理;
丁 元(1959-),男,美籍华裔,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政府绩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