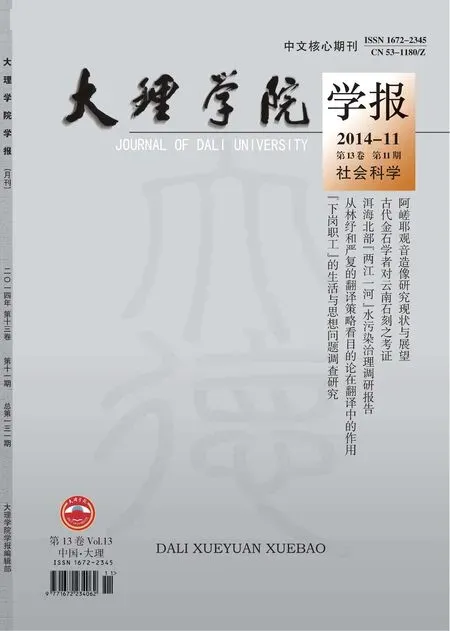阿嵯耶观音造像研究现状与展望
张成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阿嵯耶观音造像研究现状与展望
张成
(大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
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非常独特的一类佛教造像,其研究存在起步晚,过分倚重于一些期刊、图书、图片等文献及有限的实物资料,轻视基础资料的全面收集和整理,研究方法过于单一且缺乏创新与突破的问题。运用考古学、民族学、美术史学、文献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协同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展开跨学科、跨区域的宏观性、整合性研究,不仅是解决该项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走出困境并有所突破的有效途径,亦是对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研究在理念、方法上的思考与创新。
南诏大理;阿嵯耶观音;造像;跨学科、跨区域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教造像中,有一类造型独特、风格始终如一的观音形象。其造型特征为:宽肩、细腰、上身赤裸,下着裙裳,身材颀长纤细,头戴高大精美的化佛头饰。其姿势或立或坐,均以扁平挺直、正面严格对称为特征,与身体曲屈圆润、婀娜多姿的汉地、藏地观音之造型大不相同。学界把这种大理独有的观音形象,称之为阿嵯耶观音,美其名曰“云南福星”(见图1〔1〕)。
一、研究史略
阿嵯耶观音自20世纪20年代发现以来,其发现、认识与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70年代(发现和认识期)
1925年大理地震时,从千寻塔的塔顶部震落下

图1 阿嵯耶观音铜鎏金立像(正面、侧面、背面图)
来一些文物,包括塔模1件和鎏金阿嵯耶观音像7件在内的文物,全部流失海外。1942年,德国传教士鲍格蓝重金雇人攀上千寻塔顶,盗取阿嵯耶观音像2件,解放时被遣送回国时缴获,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由于这些文物大都流失海外,并未引起大陆学界的注意。而最早研究和推崇这种观音造像的是美国Helen B.Chapin。1944年,Chapin博士对美国博物馆以及其他个人收藏的这类观音造像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为这些观音造像皆为云南制造,并把收藏于美国圣地福尼亚的一件有铭观音造像称为“云南福星”(见图1)。她对这类造像的来源抱有极大兴趣,并留给后来研究者一个饶有兴趣的研究课题,即关于这类观音造像来源的探讨:“这些观音造像接近于十二世纪观音像的标本,在蒙氏统治的那些日子之前,帕拉或室利佛逝的观音像模式可能为云南的雕塑家们利用。这些观音像是依照库普达(Gupta)时代的印度原型呢?还是仿造唐代中国的雕像呢?亦或是一种兼有中国、印度特点的综合类型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后来的研究者,希望他们中间有人能解决这些问题”〔2〕。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霖灿先生读了Chapin博士的论文之后,对这类观音造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1967年刊行的《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一书中,专门就圣地安哥艺术馆所藏观音像,即Chapin博士所称“云南福星”之铭文进行了考证。对于此类观音造像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在以往的学者们每每把这种观音铜像,归之于印度或缅甸系统,也有列之入中南半岛的系统内的,如今大家都因研究而逐渐知道,这是南诏大理民族最崇拜的一尊神祇,首先我们得向云南这个系统内去考虑他的位置,然而才能旁及其他”〔3〕60。在《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一书中,还首次全彩版公布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胜温梵像卷》、日本京都有邻馆的《南诏图传》,为此类观音造像的研究提供了绘画、文字方面的珍贵资料。此外,1951年,大陆学者宋伯胤先生《剑川石窟》〔4〕一书的出版,亦为阿嵯耶观音造像的研究提供了石刻类的资料。1978年,在对三塔进行全面维修时,又在千寻塔顶部发现了大批文物,出土观音造像80余件,其中有1件珍贵的阿嵯耶观音〔5〕。
整体而言,本阶段是阿嵯耶观音造像逐步发现和认识的时期,雕塑、绘画、文字方面的资料逐步公布,但相关讨论还未上升到研究的高度,仅限于国外、中国台湾的少数学者对这些资料的著文介绍及一些初步的讨论,尚未引起大陆学界的关注。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20世纪末(积蓄期)
继李霖灿之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李玉珉对《张胜温梵像卷》中的观音造型发文讨论,提出“大理观音相关的真身观音(阿嵯耶观音)在造型上,是以爪哇作品为依据,其中又渗入了中南半岛的一些特征,而其源远流长,印度帕巴拉及美术就是真身观音的造型基础。故仅从真身观音的图像看来,大理与印度、中南半岛应有深厚的文化渊源”〔6〕。这一时期,泰国、美国、日本等国学者对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地区的观音造像还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如泰国学者Nandana Chutiwongs对东南亚地区的观音造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7〕;美国学者Daviol Snellgrove对佛教造像从印度的兴起、发展,再向亚洲传播的过程进行详细的论述。其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观点,即观音像通过东南亚传到云南〔8〕;美国学者Angela.F.Howard认为阿嵯耶观音造像受缅甸、泰国、越南观音造像的影响,称其为“西南边疆的混血艺术”〔9〕。此外,日本学者镰田茂雄也认为南诏的佛教艺术与泰国、印度尼西亚半岛的佛教艺术有关。
相比国外和台湾学者,大陆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多集中于对《南诏图传》《张胜温梵像卷》的考释。云南的一些学者多从当地的历史文献、民族文化、本土信仰等方面对阿嵯耶观音进行讨论。其中,尤以李东红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经历了从“梵像观音—阿嵯耶观音—观音老爹”的演变历程,是佛教密宗不断民族化和地方化的结果〔10〕。
纵观本阶段的研究,国外和台湾的学者多把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南亚的观音造像加以比较,以期找出二者之间的联系。而国内的学者更倾向于从云南本土探索其源与流的问题。
第三阶段:21世纪~现在(蓄势待发期)
进入21世纪初,随着“剑川石钟山石窟”和“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剑川、大理的召开,使得南诏大理的佛教艺术、历史文化广受关注。学术界各领域、各方向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日本学者今井浄円以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观音像为例,对南诏大理国的观音造像进行了讨论〔11〕。这一时期,除了一些散见的期刊论文外,还有一些硕士、博士论文对阿嵯耶观音造像进行了专门研究。傅云仙以图像学的方法,对南诏大理的阿嵯耶观音、东南亚及印度的观音造型进行了比较研究〔12〕。朴城军以《南诏图传》《张胜温梵像卷》和剑川石窟等为资料,对阿嵯耶观音的造像以美术史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13〕。此外,杨斯斐还对造成阿嵯耶观音与南亚、东南亚以及汉地观音在造型上异同、以及产生这种异同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讨论〔14〕。
总的来看,本阶段的研究在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发现、认识期和第二阶段的积蓄期之后,进入一个讨论更为活跃和集中的阶段,出现了阿嵯耶研究向系统化、专项化发展的趋向。
二、现状述评
从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发展史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起步晚,轻视基础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从美国Chapin博士发文讨论阿嵯耶观音开始,至今不过70多年的时间,研究的起步较晚。而大陆的研究更晚,距今不过20多年。国外、台湾学者的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多从东南亚、南亚佛教交流的视角,探讨南诏大理阿嵯耶观音的来源。这种跨区域的研究思路值得我们学习。近年,大陆的一些青年学者对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南亚观音造像进行了图像学的比较研究。然而,所用资料大多转引于一些期刊或图书,没有对实物的亲自考察,没有考古学严谨的线图,仅靠一些模糊不清的图片或含混不清的说明文字,去揣测、想象,其结论很难令人信服。
笔者认为,当前所面临的紧要问题,不是通过为数不多的几张图片的比较去印证自己或别人先入为主的推论,而是应该首先完成与云南地区与阿嵯耶有关的全部资料(包括雕刻、绘画、文字等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这项最为基础的工作。在此之上,再将目标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云南以外包括西藏、四川、东南亚、南亚等相关区域。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再结合云南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才可能找到阿嵯耶观音的来源。
正如李霖灿先生指出那样:“以往的学者们每每把这种观音铜像,归之于印度或缅甸系统,也有列之入中南半岛的系统内的,如今大家都因研究而逐渐知道,这是南诏大理民族最崇拜的一尊神祇,首先我们得向云南这个系统内去考虑他的位置,然而才能旁及其他”〔3〕60。目前所见这类与东南亚、南亚观音造像的比较研究,很容易流于为了证明某个结论而去千方百计地寻找证据的怪圈。我们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从资料的全面收集做起,再去进行比较和分析。其结果,可能进一步以第一手的实证资料(实物资料、文献资料)证实学界历来对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南亚观音造像间渊源关系的认识,亦有可能会推翻这一固有认识,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二)研究方法单一,缺乏跨学科、跨区域的宏观性、整合性研究
综观各阶段海内外研究成果,以美术史论、文献史学方法为主。正如李霖灿先生所言:“史学家对南诏及大理国的研究十分注意……只是一向因受了资料的限制,一直是在唐书宋史或南诏野史一类的故纸堆中钻研,却缺少当时的第一手资料来相印证,因而其成就并不十分令人满意”〔3〕1。
针对这种现状他又极具前瞻性地指出:“所以近来的趋势,是注意到了考古学上的田野发掘和民族学上的实地调查各项资料,意思是想找出当时的人证物证,请他们来现身说法,来和现存的纸面史料印证,以求解决那一些久疑不决觗觸纷纭的各项问题,这项办法显然是高明正确得多了。当时的资料,可以被埋藏于地下,也可以留传与民间,因之用考古及人类学的方法,自然可望有良好的收获,但是我们每每忽略了另一个所在,那就是博物馆中的艺术珍藏”〔3〕1-2。
李霖灿先生的这些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利用考古学、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去发现和搜集一手资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资料整理和分类时,可以发挥考古学类型学、地层学的优势,对这些资料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分期和分区,从而明确各类型在时间、地域上的变迁规律。在此基础之上,再结合美术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全面的研究。
近年来,跨区域研究成为一个热点。上述第二、第三阶段的研究,虽然亦有跨区域研究的一些尝试,但大多受Chapin博士等人的观点影响,以少量的代表性的资料去印证阿嵯耶观音与东南亚、南亚的关系。如上所述,姑且不论其结论的对错,这种先入为主、为了证明而证明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三、研究展望
基于目前有关阿嵯耶观音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采用跨学科、跨区域的研究方法,是走出这一课题研究的困境,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嵯耶观音造像为考察的切入点,逐步将对象扩大至云南及其周边地区的观音造像资料,进而将对象范围(以佛教遗迹、出土文物及藏品为主,包括立体雕塑类和平面绘画类题材)延伸至东南亚、南亚地区。在全面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考古学、民族学、美术史学、文献史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协同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跨学科研究,是该课题研究的发展趋势,也是该研究获得新突破的有效举措。
阿嵯耶观音造像作为佛教传播之载体,必须将其置身于佛教传播与变迁这一宏观视野下去考察。不局限于地域、学科界线的跨学科、跨区域研究,是今后阿嵯耶观音、乃至东南亚、南亚地区观音造像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同时,跨学科、跨区域研究的理念与方法,亦适用于南诏大理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正如李霖灿先生所言:“他日历史学家广辑群书,考古家挥动锄头,民族学家展开调查,益之以更多的南诏大理遗物自博物馆剖析发现出来,那南诏大理研究的前途是充满了光辉的”〔3〕3。
〔1〕李昆声.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249.
〔2〕HELENB Chapin.云南的观音像〔M〕//查尔斯·巴克斯.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林超民,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301.
〔3〕李霖灿.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67.
〔4〕宋伯胤.剑川石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8.
〔5〕李朝真,张锡禄.大理古塔〔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59.
〔6〕李玉珉.张胜温“梵像卷”之观音研究〔M〕//刘崇鈜,石璋如等.东吴大学中国艺术史集刊:第十五卷.台北:东吴大学,1987:228-264.
〔7〕NANDANA Chutiwongs.The Iconography of Avalokitesvara in Mainland South Asia〔D〕.Leiden:Rijksuniversiteit Groningen,1984.
〔8〕 DAVIOL Snellgrove.The image of The Buddha〔M〕. UNESCO,1980:125.
〔9〕ANGELA Falco Howard.南诏国的鎏金铜观音:西南边疆的混血艺术〔J〕.秋石,译.云南文物,1991(29):132.
〔10〕李东红.大理地区男性观音造像的演变:兼论佛教密宗的白族化过程〔J〕.思想战线,1992(12):58-63.
〔11〕今井浄円.マンダラの諸相と文化〔M〕//頼富本宏博士還暦記念論文集:2.京都:法蔵館,2005.
〔12〕傅云仙.阿嵯耶观音造像研究〔D〕.南京:南京艺术学院,2005.
〔13〕朴城军.南诏大理国观音造像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8.
〔14〕杨斯斐.云南剑川石窟神像艺术的地方特性及其成因试探〔D〕.上海:复旦大学,2010.
(责任编辑 张 成)
Current Research and Future Prospect of the Study of the Sculpture of Acarya Avalokitesvara
ZHANG Cheng
(Dali University,Dali,Yunnan 671003,China)
Acarya Avalokitesvara is a very special sort of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he Nanzhao Dali Kingdom period.The study of Acarya Avalokitesvara started late and emphasized too much on the journals,books,pictures and other documents and limited materials.The study neglected the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basic data and the its research method was too simple and lacked innovation and breakthrough.The combin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ethnological,historical and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ing method,and the cooperation of experts in different fields with conducting multi-disciplinary and cross-regional study are the keys to the facing problems and the effective breakthrough of current predicament,and are also the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of the idea and method of the study of Nanzhao Dali's history and culture.
Nanzhao and Dali;Acarya Avalokitesvara;sculpture;inter-discipline;cross-region
K879
A
1672-2345(2014)11-0001-04
10.3969/j.issn.1672-2345.2014.11.001
2014-10-06
张成,编辑,博士,主要从事美术考古、佛教考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