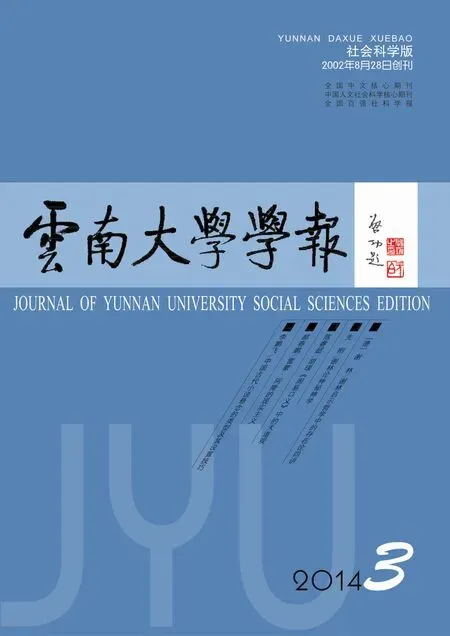胡瑗《周易口义》中的天道观
陈睿超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胡瑗的《周易口义》作为义理易学发展史上从“说以老庄”的玄学易向“阐明儒理”的宋易之转变过程的关键点,[1](P50)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一·易类一》云:“《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也……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起其论端。”不仅在解易体例方面对孔颖达的《周易注疏》多有超越与创新,在哲学思想方面也与《周易注疏》构成了紧密的对话关系。胡瑗的很多基本观念都承自孔疏,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又有自己的创见。这些创见的总体特征,一方面是以儒家之实理对峙玄学之虚无,另一方面是以儒家倡导的有为对峙老庄之学的无为。实际上,根据朱伯崑先生的研究,孔疏自身的思想倾向,即是企图调和汉易与玄学派的观点,“力图扬弃王弼派贵无贱有的思想”,“标志着从汉易向宋易的过渡”。[2](P362)因此,在哲学思想方面,《口义》与其说是对《注疏》的反动,毋宁说是对《注疏》自身思想倾向的推进。而这种推进非常显著地体现在胡瑗易学解释中呈现出的对“天道”的理解中。通过对天道观中玄学虚无之说的摒弃,胡瑗实际上建立了天道对人间秩序的奠基性关联,从根本上说这仍是其“阐明儒理”的思想意图的体现。
一、气与道
胡瑗理解的世界,总体说来,是气的世界。自天地未分之前,至万物已成之后,皆是一气之运化。《口义·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注云:
天地之判,混元廓开,而万物之情皆生于其间。[3](卷十一P352)
天地分判之前所谓“混元”,实则是无分别的元气。《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注云:
“太极”者,是天地未判,混元未分之时,故曰“太极”。言太极既分阴阳之气,轻而清者为天,重而浊者为地。是太极既分,遂生为天地,谓之两仪。[3](卷十一P408)
以太极为元气,两仪为天地阴阳之气,皆袭孔疏之说。[4](卷十一P466)孔疏的理解源自汉易,说到底即“太极”是气、是“有”,这显然与韩康伯《系辞注》“有必始于无,故太极生两仪”[4](P466)这样“本体之无”式的解读不同。胡瑗取孔疏而不取韩注,正是其推进《注疏》以有易无的思想倾向的明证。
太极混元之气分为阴阳,阴阳二气又聚为天地,于是,万物都在天地阴阳的作用下产生。《系辞上》“刚柔相摩,八卦相荡”注云:
夫天本在上,地本在下。及夫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阳极则变而为阴,阴极则反而为阳,阳刚而阴柔,阴消而阳伏,刚柔互相切摩,更相变化,然后万物之理得矣。[3](卷十一P354)
“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阴阳之气相交,这是《周易口义》论万物生成的基本模式。万物皆由阴阳的消长变化而来,人亦不例外。《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注云:
人受阴阳之精气萃之于身……得精气之多者则为神,得精气之少者则为魄。……及其死也,体魄降于地,骨肉毙于下,精神散之于天则为神,体魄散之于下则为鬼,是天地之精气萃聚于人身则为精神体魄矣。[3](卷十一P367)
此段注文后面引用了《左传》与《礼记》,可见胡瑗承袭了先秦以来对人的鬼、神、魂、魄的朴素认识,皆将之解释为阴阳之气的变化形态。胡瑗在《谦·彖传》注中说:“鬼神者,天地之用也。”[3](卷三P114)把鬼神看作天地阴阳之气的作用。这种排斥神秘色彩的理性态度,可谓是张载“鬼神者,二气之良能”这一重要哲学观念的先声。
产生了万物与人的阴阳二气,其消长变化的背后,自有“道”在。《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注云:
夫天以刚阳之气居于上而生物,地以柔阴之气在于下而承天。在于天者,则为日月星辰之象。在于地者,则为草木山川之形。是天地之道,生成之理,自然而然也。[3](卷十一P354)
天阳生物,地阴成物,这种有条不紊的运作形式,源自“天地之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注云:
言天之道始于无形而终于有形,皆由道之所生。道者,人可以为之法,由而通之谓之道。[3](卷十一P416)
这里所说的“道”即“天之道”。气之混元未分的“无形”状态与万物已成的“有形”状态,皆由“天之道”所贯穿。这里需要注意,胡瑗说“皆由道之所生”而非“皆道之所生”,表明“道”不是气之外的、自身产生万物的本体,而是气从无形至于有形的整个变化过程的最终根据(“由”)。“由而通之谓之道”的定义,也表明“道”是万物所“由”,即其生成与存在的根据。
“天地之道”的具体内容,首先是“生成万物”这一原则。《系辞上》“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注云:“使天下之物无不遂其性者,天地之道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注云:“道者,自然而生也”,[3](卷十一P355)*“道者,自然而生也”承自孔疏。[4](P447)皆言此产生与成就万物的原则。这一原则亦被称为“天地之心”。《复·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注云:
天地以生成为心,故常任阳以生成万物。今复卦一阳之生潜于地中,虽未发见,然生物之心于此可得而见也。[3](卷五)(P157)
生成万物之“心”在生成作用显明之前即已透露出来,可见生成是天地所遵循的最根本的原则。我们知道,王弼注“天地之心”为“天地以本为心”,“寂然至无,是其本也”;孔颖达则疏之为“静为其本”,“静之为本,自然而有”。[4](卷五P362-363)孔疏虽然用“自然”消解了王注的“本体之无”,但仍然受到玄学派以静为贵倾向的影响。胡瑗则直接将“天地之心”与“天地之道”等同,皆释为生成的原则,而生成本身即是充满生命力的活动,这无疑是更纯正的儒家生活态度关照下的义理阐发。
“天地之道”根本上是生成的原则,而此生成是持久、广大的。《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注云:
夫天地之大德者,惟是阴阳二气上下相交,生成万物,周而复始,无有限极,故其德常大。若生之不常,运之有极,则所生之道不广也。[3](卷十二P424)
“天地之大德”即是“所生之道”,是指导天地运动的原则,其恒久不息,正成就了其广大。
天地持久的生成,又让人无从察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系辞上》“易则易知”注:“天之道,寂然不见其用,杳然不知其为”;“阴阳不测之谓神”注:“生成之道周而复始,极而复生,不言而信,不疾而行,以至变化之理,及究其生育之形,不可得而知也。”[3](卷十一P356,376)胡瑗这里理解的“天地之道”似乎保留了某种不可知的神秘色彩,在后文对“形”与“用”的讨论中,我们将对此加以更具体的分析。
将上述内容总结起来,则“天地之道”即是一种持久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生成原则。胡瑗在《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注中,也对“道”做了总括性的描述:
道者,自然之谓也,以数言之,则谓之一;以体言之,则谓之无;以开物通务言之,则谓之通;以微妙不测言之,则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言之,则谓之易;总五常言之,则谓之道也。[3](卷十一P371)
这一概述基本包括了我们以上总结的“天地之道”的内容,而它实则仍是因袭孔疏。《注疏》此句注云:
一谓无也,无阴无阳,乃谓之道。一得为无者,无是虚无,虚无是太虚,不可分别,唯一而已,故以一为无也。……自然而有阴阳,自然无所营为,此则道之谓也,故以言之为道。以数言之谓之一,以体言之谓之无,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以应机变化谓之易。总而言之,皆虚无之谓也。[4](卷十P453)
朱伯崑先生认为,孔疏所谓“一,无,道,神,易,都是虚无即自然无为的不同称号”,将韩康伯注中本体意义上的“道”转变为“自然”的一种称谓。[2](P376)胡瑗的“道者,自然之谓也”正承袭了这一观念,又进一步排除了“虚无”这样明显带有玄学色彩的词语。而仍保留的“以体言之,则谓之无”的说法,根据土田健次郎的分析,意为“就形体而言,是无形的”,[5](P110)可见并无“本体之无”的含义。这可说是更彻底地推进了孔疏对王弼派易学思想的扬弃。此外,“总五常言之,则谓之道也”这一描述是胡瑗的创见,“五常”当是指与乾之“元亨利贞”四德相配的仁义礼智信,天道本身蕴涵着人世伦理秩序的基础,这正体现了胡瑗通过阐说天道为儒家人世秩序奠基的用意。
从以上的比较中不难发现,胡瑗在《口义》中对“气”与“道”的论述与《注疏》有别,但似乎都未完全跳出其藩篱。那么,从本质上划定胡瑗“天道观”自身特色的观念究竟何在呢?我们认为,就在于对天道、人事之差别的认识。《系辞上》“崇高莫大乎富贵”注云:
天地之道,但能生成万物,不能生成天下之人。是故君子有大才大德,凡居崇髙极盛之位,代天理物,能以仁义敎化,生成天下之人。[3](卷十一P410)
天地之道虽然广大持久地支配气的运行,以生成天下之物,但作为万物之一的人是特殊的,不能完全依赖天地之道得以成就,而必须以自己的努力成就自身。因此,人世中的为政者(“君子”)必须承担起“代天理物”,即辅助天地完成人自身之成就的责任。《复·彖传》注云:
然天地以生成为心,未尝有忧之之心,但任其自然而已,故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是虽有凶荒、水旱、饥馑,而未尝忧而治之也。若圣贤有天地生成之心,又有忧万物之意,是以其功或过于天地,故《系辞》曰:“鼔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但圣人无天地之权耳,使其有天地之权,则凶荒水旱之类无得而致也。[3](卷五P157)
“无忧”与“有忧”,正是天道与人世的本质差别。天道之生成皆是自然,即使偶尔发生“凶荒水旱”也是其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天道对此是无所谓担当的。而圣人君子面对人世的苦难却必须有所忧恤、有所担当,带领百姓去成就美好的生活。胡瑗对天道、人事的分判,固然是“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这一中国古老思想的发展,但是,在胡瑗所处的以“忧”之精神趋向及在此趋向下的士大夫政治主体性觉醒为标志的北宋时代,[6](P1-4)一个重要的观念得以觉解,那就是:人之所以为贵,就在于他具有“忧”的精神,自觉的担当的意识,他能够以主体性的担当所转化出的巨大精神力量超越现状而成就自身、成就他人、成就天下。就这点而言,圣人君子“其功或过于天地”——这可说是对人自身之价值的最高肯定。胡瑗最后感叹“但圣人无天地之权耳”,若圣人有天地那样广大的权能,能够忧恤、治理世间万物,那么,天地间任何灾难就都不会发生了。这可以说是在北宋的时代背景下奏响了儒家之宏伟政治理想的最强音。
二、形与用
《口义·系辞上》“与天地相似故不违”注云:“推其本原,大易之道,皆圣人穷神尽性而作也,上则准拟于天地,下则包言于人物。”[3](卷十一P368)天道虽与人事有别,但却是人世秩序的根本源泉,易道即是圣人法天之作。但是,天地之道本身毕竟是“形而上”的、抽象的东西,对天道的效法,必须落实在人所能感知到的“形而下”的层面。在胡瑗这里,“道”所衍生的形下层面的概念,便是“形”与“用”。《系辞上》“形乃谓之器”注云:
言天地之道,生成不已,故万物始有其形。形之不已,乃可成其器用。[3](卷十一P408)
《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注云:
言天之道始于无形而生于有形……浩然而不局于器用。
言天始于无形而生于有形,故形于下者则为其器。器者,则为有形之用,但可止一而用之也。故在形之外者谓之道,在形之内者谓之器也。[3](卷十一P416)
很明显,“道、形、用”三个概念的层次是递降的。“道”是无形的根本原则,“形”是气凝聚产生的形态,而“用”则是成形后具有的功用。这里所说的“形”与“用”皆就天地间产生的具体器物而言,具体事物的功用只在于特定方面,而“道”作为生成原则是广大周遍的,故“不局于器用”。
除具体器物外,胡瑗认为天地也自有其“形”与“用”,这就涉及人之“法天”究竟是“法形”还是“法用”的问题。在《乾·卦名》注中,胡瑗对两者进行了详细的分疏:
既象天,其不名天而名乾者,盖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夫天之形,望之其色苍然。南枢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枢出地上三十六度,状如倚杵,此天之形也。言其用,则一昼夜之间,凡行九十余万里。夫人之一呼一吸,谓之一息,一息之间天行已八十余里。人之一昼一夜,有万三千六百余息。是故一昼一夜,而天行九十余万里,则天之健用可知。自古及今,未尝有毫厘之过,亦未尝有毫厘之不及,盖乾以至健至正而然也。故圣人于此垂教,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所以名乾而不名天也。[3](卷一P13)
这里胡瑗主要解决的是《乾》卦何以象天而名“乾”的问题,而其归旨在于“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关于天之形的描述取法浑天说;而天之用,则通过具体的天文学计算凸显其至健不息的特征。按“天”与“乾”的区分,最早是由王弼做出的。《注疏》之《乾·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王弼注云:
天也者,形之名也;健也者,用形者也。夫形也者,物之累也。有天之形而能永保无亏,为物之首,统之者岂非至健哉
从字面上看,胡瑗与王注区别不大,但两者实有本质的不同。王弼以“健”即“乾”为“用形者”、“统之者”,即统御天之形体、使其发挥作用的东西,是将“乾”解释为一种形而上的抽象原则,可说是其“执一统众”的无为思想倾向的产物。而胡瑗释“乾”为“天之用”,则并非形而上的原则,而是由天之形体产生的现实具体的作用。那么,胡瑗为何强调人必须效法天的这种实然的作用呢?前引注文之后,胡瑗接着讲道:
天之形,象人之体魄也;天之用,象人之精神也。……故为君、为臣、为父、为子、为兄、为弟、为夫、为妇,以至于为士农工商,莫不本于乾乾不息,然后皆得其所成立也。《左氏》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皆言人当法天之健用也,故曰乾。[3](卷一P13-14)*“莫不本于乾乾不息”,原文误在第一个“乾”字后断句,兹改正。
可见,人必须法天之用,因为形体本身是静止的、无生命的,而人之为人就在于他是有生命的、有精神作用的。人若是法其形,就失去了其生命的活力。因此,人应当效法天体运行不息的活动,去过充满生命活力的、奋发有为的、乾乾不息的生活,这才是儒家观念下君臣百姓皆得成立的理想共同体的生活所应具有的生活态度。胡瑗对“乾”的解释,以“天之用”这一活生生的运动代替王弼的“用形者”这一抽象原则化的解释,正是其易学以儒家之有为对峙玄学之无为思想倾向的范例。
前述《乾·卦名》注中“法天之用”主要指效法天之运行之刚健不息,除此之外,“法天之用”还有其他内容。《系辞上》“圣德大业至矣哉”注云:“圣人法天之用,广生成之道”,紧接着“富有之谓大业”注云:“圣人法天之行事”,“日新之谓圣德”注云:“圣人法此天地之道”,[3](卷十一P374-375)可见这里的“法天地之道”就是“法天之用”、“法天之行事”;“天之用”的具体内容则是“广生成之道”,“法天之用”即效法其产生、成就万物的功用。天地生成万物的功用,可说是作为生成原则的“天地之道”的实现状态,人对它的效法,便有“代天理物”、承担起成己成人之责任的意涵。
但是,“广生成之道”意义上的“法天之用”,似有其矛盾处。《系辞上》“显诸仁,藏诸用”注云:
夫天地之道,乾刚坤柔,日临月照,春生夏长,秋杀冬藏,使万物绵绵而不绝者,天地生成之仁也,然不知天地生成之用也。[3](卷十一P373)
人本应效法他能够感知与理解的东西,这里却说“天地生成之用”是不可知的,那人又如何效法呢?实际上,这里所说的“仁”是天地生成之功用的结果,“用”则专指生成之功用的作用过程。人们只能见到万物“春生夏长,秋杀冬藏”这一结果,知道天地生成之用是存在的,却看不到天地究竟通过怎样的过程实现了这一功用,故曰“显诸仁,藏诸用”。这里便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整体理解的问题。包括胡瑗在内的持理性观念的古代思想家认为,一方面天地是向人敞开的,天象地形中给出的自然秩序,其生成万物的活动,都是人类建立自身生活世界之秩序的借资;另一方面,天地又是自身遮蔽着的,其作用的过程排斥人类理性的介入,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承认天地有遮蔽着的一面,以其为不可知故存而不论,这样既保持了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排除了各种怪力乱神式的非理性解读的可能。因此,胡瑗在“天道观”中“天地生成之用不可知”的观念,并非是神秘主义,反而是真正理性的态度。
不仅如此,圣人对天道之生成的效法,同样具有“不可知”的特点。《系辞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注云:
天下之人既皆得其利,是圣人妙用如神,而人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3](卷十一P408)
“天下之人既皆得其利”是圣人教化之功用的结果,这是可知的,但如天地之生成一样,其功用之“所以然”即具体过程,却是不可知的。圣人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之中实现美好生活,这是中国古代思想所共享的效法天地的理想治理方式。
总而言之,胡瑗理解下的“法天”即是“法天之用”,一方面效法天刚健不息的运动而成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效法天生成万物的功用而成“代天理物”的承担精神,以及“妙用如神”的理想政治形态。虽然“道、形、用”三者中“用”处于最低的层次,但恰恰是对“用”的效法中才有儒家所倡导的人的生命力的呈现与主体性的发扬。
三、理与分
《周易口义》在对人之“法天”的讨论中,前述“形”与“用”的区分涉及的是“如何法”的问题,而“法天”之具体内容则是以“理”这一概念表述的。我们知道,“理”的本义是“治玉”,*《说文》卷一玉部:“理,治玉也。”亦有“纹理”之义,而治玉必然要依据可为人所见的、玉石中客观本有的纹路来进行。因此,“理”这一后来构成宋明理学之思想体系核心的概念,可概括为在天地万物中客观呈现出的可为人所接受、理解和遵循的东西。但胡瑗所说的“理”,与自二程以降所发展出的这一概念的成熟形态所具有的内涵,仍有着重要区别。《口义·系辞上》“唯深也”注:“夫人之深,未有其理,未有其形,而又天下之心,亿兆其心……”;“唯几也”注:“几者,是有理而未形之谓也。”[3](卷十一P402-403)*对“几”的解释是因袭孔疏之说,《乾·文言》“知至至之,可与几也”,孔疏释为“几者,去无入有,有理而未形之时”。[4](卷一P305)这里涉及“理”与“形”的关系问题。“理”虽然可以在事物仅露端倪、没有完全成形之前,即“几”的状态中显现;但当事物(引文中特指人心中的念头)还完全不存在时,即“深”的状态中,其“理”也是没有的。显然,胡瑗所讲的都是具体事物的“理”,二程那里具有绝对先在性与普遍性的“理”,在胡瑗的思想中是找不到的。
《口义》中对天道的论述涉及的“理”,其具体含义有三。首先是指“道”,即事物活动所遵循的规则。如《系辞上》“变化见矣”注言:“天地之道,生成之理”;“乐天知命故不忧”注言:“性命之理,死生之道”;“阴阳之义配日月”注言:“大易之道,变通之理。”[3](卷十一P354,369,378)这几例都是“道”、“理”对言,“理”皆指生成、死生、变通等活动所遵循的“道”,即规则。
其次是指“性”,即事物的性质。《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以象其物宜”注云:“言圣人推测天下之幽赜,以拟度万事之理……使皆各得其宜,各顺其性”;“天下之能事毕矣”注言:“天地之性,万物之理。”[3](卷十一P380,399)这里都是“理”与“性”对举,“万物之理”就是“万物之性”的意思。
以上两种含义都是“理”的常见用法。但《口义》中的“理”还有一种较特别的含义,即指“分”。《履·卦辞》注言:“上下之分定,尊卑之理别”;“法象莫大乎天地”注言:“高者有其分,下者有其理。”[3](卷三P90,409)这里皆“理”、“分”对称,且都与上下、尊卑、高低之秩序相关,这里的“理”即是本分的意思。
按“理”训为“分”,古已有之。《礼记·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云:“伦,犹类也;理,犹分也。”但欲获知胡瑗思想中“理”与“分”之关联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分析“分”的含义。《系辞上》“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注云:
夫天地卑高既定,则人事万物之情皆在其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贵贱高卑之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皆有其分位矣。[3](卷十一P353)
“分位”一词表明,本分即指人在共同体生活中应处的位置。而“分位”本身又是“天地卑高既定”的结果,即是天地给予出来的。又《乾·彖辞》注释“礼乐刑政”之“礼”云:
圣人制礼以定之,使上下有分,尊卑有序。[3](卷一P15)
这里“分”与“序”对举,皆由“礼”定,表明共同体生活的礼制秩序的建立,就在于每个人都得到其适当的位置。可见,“分”与人世的礼制秩序是紧密相关的。《系辞上》“继之者善也”注云:
夫天地之道,阴阳之功,生成万物,千变万化,以盈满于天地之间,使高者得其髙之分,卑者得其卑之理,圣人得天地之全性,继天地生成之功,以仁爱天下之物,以义宜天下之众,使居上者不陵于下,在下者不过其分,是圣人继天养物之功,以为善行也。[3](卷十一P371-372)
如前所述,“理”是指天地给予出来的,可为人所接受、理解和遵循的东西。而“理”具有“分”的含义,便表明一种高下井然的秩序包含在这些可理解和遵循的东西之中,为人世之上下尊卑奠基。圣人“代天理物”,即是以天地高卑之理分为依据,建立“上不凌下,下不过分”的人间礼制秩序。因此,人世秩序的来源既非人的纯粹主观创造,也非神秘不可知之物,而就在于天地所给予人的可知的“理”中。在这里,尽管缺乏更具体的论证,胡瑗还是为儒家的人世秩序找到了极为明晰与牢靠的基石,这是“理”与“分”之关联的意义所在。
“分”就其本义来说是指界限;而本分,即人在共同体中应处的位置,也是一种对人的限制。但是,胡瑗并不认为“分”是外界强加的、已然不可变更的限制。《坤·文言》“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注言:“此所以尽为臣、为子之分”,[3](卷一P46)这里的“分”非现成,而是需要去“尽”,即有待于去成就的。“分”的存在并未抹杀人的主体性,相反,自身本分的成就必然需要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即是说,人应当依靠自己的努力找到并成就自己在共同体生活中应处的位置。
如果说在胡瑗的易学思想中,“天地之道”与“法天之用”的观念尚含有不可知的成分,那么,“理”的观念则完全是可为人所理解和遵循的。“理”所具有的“分”的含义,可以说是胡瑗为儒家的共同体生活方式寻找天道根基之努力的最终落脚点,即将人世秩序奠定在人可理解的天道的基础之上。
四、小结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不难发现,胡瑗在《周易口义》中对天道的阐释的根本目的在于破除《周易注疏》中不切实际的玄学倾向,通过天道为儒家倡导的现实生活中的伦理价值与政治秩序奠基。这种奠基是二重性的:对“道”、“理”等概念的讨论表明,从天地的角度看,人世秩序不是人为妄造的,而是由天地以人可理解的方式给予出来的;而对“形”与“用”、“理”与“分”的讨论则表明,从人的角度看,天地呈现出的秩序不是现成的,人必须以一种乾乾不息、奋发有为的生活态度,发挥主动性,依靠自身的努力去实现秩序的建构,找到自己应处的分位。尽管胡瑗的天道观所“阐明”的“儒理”仍是初步的、粗疏的,但他的思考方式以及所使用的“道”、“气”、“理”、“分”等哲学话语,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之后的宋代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3][宋]胡瑗.周易口义[A].儒藏精华编(第三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孔颖达.周易注疏[A].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册)[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日]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M].朱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杨立华.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