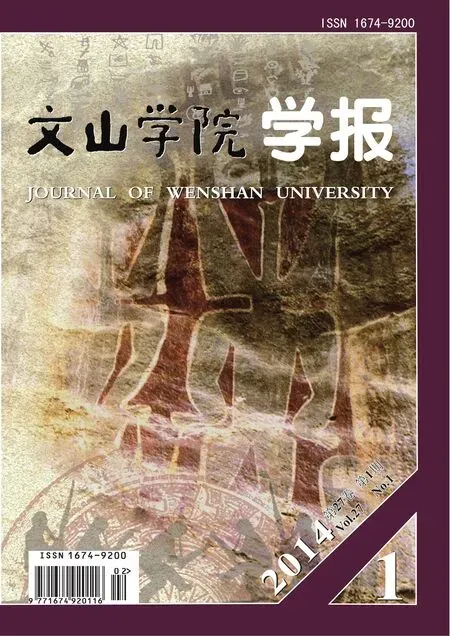谈五场壮剧《彩虹》音乐的艺术探索
——云南壮剧音乐初探(之十四)
许六军
(文山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00)
谈五场壮剧《彩虹》音乐的艺术探索
——云南壮剧音乐初探(之十四)
许六军
(文山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00)
五场壮剧《彩虹》音乐在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中获得成功,主要在于音乐设计者在创作中不断探索和大胆创新。该剧的音乐在融入民歌、变化板式、运用衬词、特色乐器、伴唱帮腔等几个方面进行了不断的艺术探索,使该剧音乐更具民族特色,更加成熟。
壮剧《彩虹》;艺术探索;民歌;板式;衬词;特色乐器;伴唱帮腔
五场壮剧《彩虹》是根据流传在壮族地区的叙事长诗《幽骚》(原名《逃婚调》)改编而成,讲述一对壮族青年为反抗土司的压迫,逃到远方成为夫妻的故事。《彩虹》一经登上舞台就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2013年7月参加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荣获银奖,该剧音乐获优秀音乐奖(本届会演音乐类只设“优秀音乐奖”)。应该说《彩虹》获银奖与该剧音乐的成功不无关系。
该剧音乐的成功并获奖,在于音乐设计者大胆地进行艺术探索。那么,该剧音乐的艺术探索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探索一:融入民歌,民族色彩更加鲜亮
云南壮剧音乐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融合型的〔乖嗨咧腔调〕〔依嗬嗨腔调〕〔沙戏腔调〕和〔壮剧皮黄〕,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壮族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本土型的〔哎依呀腔调〕〔哎的呶腔调〕和〔乐西戏调〕。这两种类型的7种腔调使云南壮剧形成了多声腔少数民族剧种。
“戏剧音乐来源于民歌、曲艺、歌舞、器乐等多种音乐成分……”[1]718这是所有戏曲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共性特征,云南壮剧也不例外。在云南壮剧音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壮剧的各种腔调始终都是在不断地以各种不同形式与壮族民歌进行互渗和融合,实际上就是一种探索和创新的过程,换句话说,壮剧音乐浓郁的壮族风格是壮剧音乐与壮族民歌不断互渗和融合的必然。
云南壮剧音乐虽然有7个腔调,但在民间土戏班的演出中,每个戏班只唱一种腔调,互不混杂,演唱哪种腔调就是哪种戏班,如富宁县洞波乡芭莱土戏班就只唱〔哎依呀腔调〕,不唱其他腔调,它就是“哎依呀戏班”,其他戏班亦然。不同腔调的戏班的每一次演出都是壮剧音乐与壮族民歌互渗和融合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演出中用一段时间(或演出前、或演出中、或演出后)进行民歌对唱,这种对唱与当时表演的剧目内容无关,是有意识地拉动观众与演员之间的互动、活跃舞台气氛、吸引观众参与的一种有效方式,很受群众欢迎;另一种方式是直接将当地流行的民歌曲调与剧目紧密联系,突出了壮剧音乐的壮族民歌风格。《彩虹》音乐采用了第二种方式。
在《彩虹》音乐中,成功地采用了以下几支民歌曲调:
一支是【吩打劳】(壮语曲调名),汉语曲调名是【大河调】,流传范围很广,分为【剥隘吩打劳】和【阿用吩打劳】两种,《彩虹》用的是【阿用吩打劳】。第一场,在富宁县壮族地区一年一度隆重盛大的传统节日陇端街上,壮族男女青年穿上盛装、打起花伞、背着花包、带上五色花糯饭等食品和定情礼物,唱着【吩打劳】来赶陇端街。此时,【吩打劳】由远及近,由独唱到齐唱,歌声此起彼伏,青年们用山歌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爱意。他们唱着山歌,一对对、一拨拨地来到陇端街,舞台上呈现的正是现实生活中隆重的陇端街的热闹景象。舞台上演唱的【阿用吩打劳】旋律优美、清纯温润、秀丽流畅、脉脉含情,此时倾听【阿用吩打劳】仿佛置身于壮乡的田园风光之中去感受壮族男女青年热恋时情真意切的纯真爱情。原生的壮族民俗和优美的壮族民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
第二支是【吩呃哎】(壮语曲调名),汉语曲调名是【归朝山歌】,因起源于归朝地区而得名。这是一种流行范围很广,很受壮族群众欢迎的壮族民歌,广泛流行在富宁县境内所有壮族村寨。
【吩呃哎】优美动听、端庄流畅,演唱时真假嗓频繁交替,真嗓浑厚淳朴,假嗓嘹亮高亢,节奏不规整,有很强的随意性。大量的各种装饰音和不同的演唱方法使【吩呃哎】别有情趣,既可优美流畅、古朴端庄,又可高亢激越、振奋激昂,也能空灵高远、舒畅豪放。演唱【吩呃哎】的最高境界是真假嗓转换和换气时不露痕迹,低音沉静而回味无穷,高音穿透力强且沁人肺腑,演唱难度很大,具有好听难唱的特点。民间有很多演唱【吩呃哎】的高手,剧中演唱【吩呃哎】的歌手与民间歌手相比不分高下,难分伯仲。
这支曲调在《彩虹》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剧中出现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二场。剧中主人公沐郎和朵比是一对壮族男女青年,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成了恋人。但在一次陇端街中,美丽善良的朵比被荒淫无耻的土司看中,用号字黑绸号下朵比,这就意味着七天后朵比就要成为土司娘娘。沐郎和朵比决意逃到远方去成家,但又不忍留下朵比的阿妈,阿妈劝二人赶快离开,不然就难脱魔爪,无奈之下沐郎和朵比依依不舍、悲痛欲绝地与阿妈分别。此时,曾被土司号下成为土司娘娘又被土司抛弃的阿花出现。在追光下,阿花清唱【吩呃哎】,悲凉凄惨,孤苦无靠,预示若朵比被号成为土司娘娘,今天阿花的悲剧就是明天朵比的下场。低沉哀怨的【吩呃哎】令人悲伤,催人泪下。此时的【吩呃哎】实为第二场的点睛之笔,令观众久久回味,难以释怀。
第二次是在第五场,土司强迫朵比为妻,朵比誓死不从,土司以沐郎和朵比私奔乱伦、违反土规为名,将二人残酷毒打,最后焚为灰烬。在熊熊烈火中,阿花又出现在舞台上,此时除了熊熊烈火的声音,一切归于寂静,阿花在烈火声中再次唱起【吩呃哎】。先是阿花清唱,哀怨忧愁、低沉凄婉,接着众女青年齐唱,沉吟伤感,呼号激越,再后来是男声近关系转调,在更高的音上与众女合唱,空灵高远,豪放激荡,此起彼伏,似呼唤呐喊、似团结反抗、似追求向往,似黑夜惊雷划破夜空。同时,众姐妹摘下象征封建枷锁的号字黑绸抛到台下,寓意砸碎身上的封建枷锁,追思沐郎和朵比,共同追求幸福的生活。最后,在【吩呃哎】的歌声里,沐郎和朵比在狂风暴雨中化为彩虹,成为了理想与吉祥的象征。这次出现的【吩呃哎】把本剧推向高潮,精确地揭示了壮族人民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的深刻主题。
第三支是【吩央】(壮语曲调名),汉语曲调名是【郎恒山歌】,因产生并主要流行在富宁县田蓬镇的郎恒地区而得名,是壮族侬支系的布央人演唱的曲调,几乎在富宁县壮族地区都有流行。这支曲调音域宽阔,旋律优美亮丽、清新明快、高亢悠远、节奏鲜明,有很长的拖腔。由于旋律优美,此曲易学易唱易传,演唱时给人一种呼唤、呐喊、舒畅、赞颂、唯美的心理感受,极具震撼力。在壮族地区,大凡娶亲嫁女、红事喜事、会亲访友、谈情说爱都要用对唱【吩央】的方式来进行。在《彩虹》第三场,管家率家丁和侍女前往朵比家送彩礼接朵比上轿,姆比(朵比之母)谎称朵比已被河神接走,土司不悦,命家丁将姆比丢下河淹死,此时阿花穿着嫁妆头顶红帕冒充朵比欲乘土司不备刺杀土司报仇雪恨,土司以为真是朵比,要把“朵比”接走,“朵比”提出按照壮乡礼俗要与土司对歌,土司无奈只好答应。此时“朵比”和土司对唱【吩央】,“朵比”用“高起”的唱法,清新亮丽、高亢悠远,土司管家和家丁们用“低起”的唱法,滑稽可笑,再现了壮家青年男女对歌择偶的习俗和情景。精彩的无伴奏原生态男女对唱,令观众目不暇接,为《彩虹》音乐的成功增色不少。
类似的民歌融入方法还有第三场姆比唱的【吩龙安】(壮语曲调名),汉语曲调名是【龙安山歌】,给人以凄婉、悲凉、哀怨和无奈的听觉感受。
融入民歌还有一种方式,即根据唱词和角色的情绪变化、舞台气氛的变化或故事情节激化,没有用原生态的民歌而是用民歌的旋律作为音乐素材重新设计音乐。如第一场陇端街上青年男女的舞蹈音乐就是用【吩央】【吩打劳】的旋律作为素材重新设计的,众青年表演手巾舞、花伞舞、棒棒舞、铜鼓舞时欢快热烈、喜庆红火,而绣球舞则含情脉脉、情意绵绵。在陇端街上,土司管家和家丁与众青年舞蹈时,用【阿用吩打劳】作为音乐素材设计舞蹈音乐。众青年表演时表现压抑、悲愤、憎恨、无奈的情绪,土司管家和家丁表演时滑稽可笑、狂妄放肆,很好地渲染了舞台气氛。再如第三场,管家率家丁侍女抬轿和聘礼去接朵比上轿的舞蹈是用【哼央细】(壮语曲调名,汉语曲调名是【天保山歌】)的音乐素材设计而成的抬轿舞蹈音乐,描绘了管家和家丁侍女“汗珠落地摔八瓣,唢呐声声泪千行”的凄苦命运和“只要主子他高兴,我也乐得做陪郎”的虚荣卑微身世和无奈心情,很好地刻划了土司府中底层土民的苦难悲惨的人物形象。
用这两种方法融入了大量的民歌,使《彩虹》音乐呈现出多彩的壮乡风情和浓郁的壮族风格,是《彩虹》音乐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探索二:变化板式,戏曲韵味更加浓郁
以往新编剧目的音乐是想向板腔体的音乐体式作更多的尝试,而《彩虹》则是想在既有曲牌体和民族歌剧的特征又有板腔体的韵味上去作新的探索。
例如第一场,土司用号字黑绸号下朵比,此时朵比犹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众青年也预感到朵比即将大难临头,此时音乐设计者将“毒蛇闯进了池塘要驱散鸳鸯,饿虎闯进了寨子要叼走羔羊,钢刀插在胸口上,心在流血泪似汪洋”设计了一段【垛板】,一字一音,字字铿锵,节奏鲜明,句式短促紧凑,表现了朵比和众青年呐喊、控诉和抗争的强烈心声,使《彩虹》的戏曲韵味更加浓郁。再如第五场,沐郎朵比在外乡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由于思念母亲,双双返乡探望,不料中了土司设下的圈套,被土司严刑拷打,遍体鳞伤。面对酷刑,二人宁死不屈,演唱了“众父老,众乡亲,别流泪,别呻吟……”的唱段,唱段在原板和快板间两次转换。唱段质朴流畅,唱原板时悲壮冤屈、催人泪下;唱快板时坚定不屈、悲愤激昂。唱段不长,却抒发了沐郎和朵比心中的冤屈和愤怒、坚韧和不屈,使《彩虹》音乐的板式更加丰富,韵味更加浓郁。
探索三:运用衬词,壮剧唱腔更具特点
云南壮剧的衬词丰富多彩,共有8类30种,来源于壮族民歌。各种不同类型的衬词使壮剧唱腔具有十分突出的民族特点。《彩虹》也发挥了这个优势,在唱腔中大量运用衬词。一是在演唱原生态民歌时衬词不变,味道更浓,如“首句型起腔性衬词”、“字间填充性衬词”、“前后呼应性衬词”、“句中感叹性衬词”、“气氛渲染性衬词”、“衬字型收腔性衬词”、“呼应型称谓性衬词”等等。衬词的恰当使用使该剧的唱腔更具民族特点。二是把有实际词义的汉语直译为壮语来作为衬词。如第五场,沐郎朵比被严刑拷打,二人疼痛难忍、奄奄一息,互相宽慰,设计者把汉语的“苦命罗苦命罗”翻译成壮语“赫目莱罗赫目莱罗”作为“句前感叹性衬词”。这种衬词十分特别,民族特点就更加鲜明。
探索四:特色乐器,增强壮剧音乐色彩
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班的演出会使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而自制的不少特色乐器。在《彩虹》中也把这些特色乐器运用到音乐演奏中来进行尝试和探索:
胭诺玛:壮语乐器名,汉语名“马骨胡”,云南壮剧主奏乐器。琴筒用马腿骨做成,蒙蛇皮,琴杆用楠木或老金竹制作,顶雕马头,琴轴用麂角或楠木制作,张二弦,用普通马尾弓。音色圆润亮丽,清纯悠远,有浓郁的壮族特点。《彩虹》音乐中,不管是群众舞蹈场面还是沐郎朵比柔情似水、含情脉脉的情景,胭诺玛的演奏都能很好地渲染当时的舞台气氛和角色的内心活动。
哦比:壮语乐器名,汉语也以此为名,云南壮剧吹管乐器之一,用上好竹子制作,开七孔,顶置竹制簧片,音色优美圆润、浑厚低沉、凄婉哀怨、古朴苍凉。《彩虹》音乐里,在“序”中幼年时的沐郎朵比吟诵儿歌嬉戏时就用哦比独奏作背景音乐,剧场效果很好;在第五场,沐郎朵比被土司严刑拷打奄奄一息时共同回忆儿时无忧无虑、天真活泼、嬉戏玩耍、吟诵儿歌的情景的对白时,也是用哦比独奏背景音乐。第五场和“序”前后呼应,凄美的音色引导观众去追忆沐郎朵比儿时的情景,反观长大后的艰辛和疾苦、磨难和屈辱,如泣如诉、悲凉凄苦,深深地打动了观众。
恩啯果:壮语乐器名,汉语名“竹筒鼓”,云南壮剧打击乐之一。这是壮族民间用来驱赶牲畜或传递信息的生活用具,在《彩虹》中用作乐器。它用大竹做成,中间开一长槽,置于支架上,用竹键击打发声,音色洪亮沉稳、粗犷豪放、古朴沧桑,在打击乐中起到烘托情绪、渲染舞台气氛和指挥击乐的作用。在第五场中,沐郎朵比惨遭土司严刑拷打,誓死不屈,土司无计可施下令兵丁用大火把沐郎朵比烧成灰烬,兵丁手持火把舞蹈时的音乐就加入“恩啯果”,阴森恐怖的音乐令观众窒息,舞台效果极佳。
使用了壮剧的特色乐器,凸显了壮剧音乐的民族色彩,这也是《彩虹》音乐获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探索五:伴唱帮腔,烘托戏剧的矛盾冲突
高腔是中国戏曲音乐的主要声腔之一。高腔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帮腔”,帮腔对“描写环境,渲染舞台气氛;加强怀念、悲伤、怨恨、谴责或欢乐、喜悦的情绪,揭示剧中人的内心活动等,能收到感人的艺术效果”。[1]721很多地方戏曲剧种和少数民族剧种也借鉴“帮腔”这种演唱方式来丰富本剧种的音乐风格和增强戏剧效果。
云南壮剧民间土戏班的演出很少见到在音乐中运用伴唱帮腔的演唱形式。而在《彩虹》音乐中,音乐设计者进行了大胆的探索,运用伴唱帮腔的演唱形式来刻划人物形象、渲染舞台气氛、烘托戏剧矛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是主题歌《啊,彩虹》,在“序”、第四场、第五场中出现,同是主题歌,分别在三个地方出现,前后呼应,一脉相承但作用不同、意义不同、效果则很明显。二是在第一场的陇端街上,众青年的舞蹈场面也用伴唱烘托喧闹、热烈、红火、喜庆的舞台效果。三是第一场陇端街上,荒淫无耻的土司用号字黑绸号下美丽善良的朵比,此时幕后伴唱【垛板】,把沐郎朵比和众青年悲伤、愤怒、呼号、呐喊、抗争的舞台情绪渲染得淋漓尽致。四是第二场,七天后朵比将成为土司娘娘,面对即将降临的悲剧,沐郎和朵比决定逃到远方去成家。当逃到阴森恐怖的深山莽林时,二人筋疲力尽,饥寒来袭,此时女声幕后伴唱“月黑夜莽林间,山风阵阵冷阴阴,脸贴脸心贴心,暖流遍全身”,柔绵温情、优美流畅的旋律和情真意切的伴唱把沐郎朵比相互关心体贴、恩爱有加、情深意浓的深厚感情渲染得深刻感人,该唱段也因此而在观众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
《彩虹》音乐中还有在唱腔中采用唱前帮、句中帮、重句帮等帮腔形式,为渲染人物情绪和戏剧冲突增色不少,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彩虹》音乐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艺术探索以外,还有其他音乐形式的探索,如器乐曲牌的探索、击乐鼓点的探索、旋律发展手法的探索、和声配器的探索、唱腔中壮语汉语互渗和融合的探索等等,这些探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是《彩虹》成功并获奖的重要因素。可以预想,云南壮剧将会在无数创作者不断尝试、不断探索、大胆创新的不懈努力下,在祖国的戏曲百花园里大放异彩,光彩耀人。
[1]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音乐舞蹈》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A Study on Artistic Exploration of the Music in the Five Scenes of Zhuang Drama Rainbow: The 14th Study of Zhuang Drama Music
XU Liu-jun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The music in the five scenes of Zhuang drama Rainbow gets ahead at the Third China MinoritiesDrama Festival for designer’s continuously exploration and bold innovation. The music focuses on continuous artisticexplorat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folk songs, changing rhythm, practicing auxiliary words, special instruments andvocal accompaniment etc. Continuous artistic exploration will make Zhuang drama music more ethnic and the dramawill be more mature.
Zhuang drama Rainbow; artistic exploration; folk songs; rhythm; auxiliary words; specialinstruments; vocal accompaniment
J825.74
A
1674-9200(2014)01-0001-04
(责任编辑 王光斌)
2013-11-21
许六军(1948-),男,壮族,云南富宁人,主要从事云南壮剧音乐的创作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