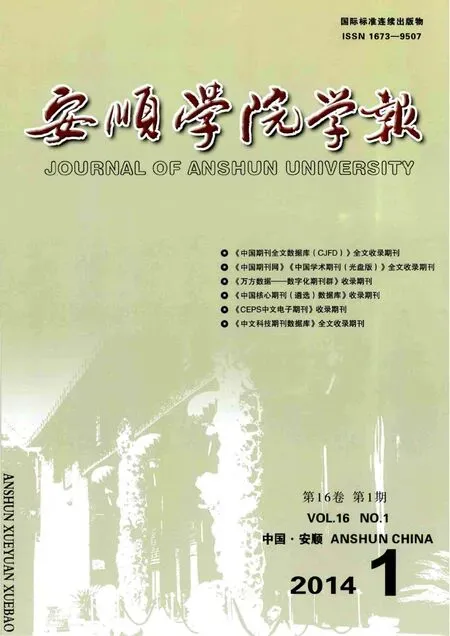《张生煮海》与 《柳毅传》的形象特征
姜 楠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张生煮海》与 《柳毅传》的形象特征
姜 楠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元代李好古所作的 《沙门岛张生煮海》是演绎于唐传奇 《柳毅传》的一部作品,并在后世享有盛名。文章试从其中主要人物龙女和儒生两个形象入手,探究元戏曲对唐传奇的改编特点,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时代特色。
《柳毅传》;《张生煮海》;龙女;儒生。
《柳毅传》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品,后世的戏曲作家多喜爱以此为母体进行改编创作。在元代,尚仲贤将柳毅与龙女的故事以戏剧的文学形式展现,成为名作 《柳毅传书》,同时还有李好古的 《沙门岛张生煮海》,后世简称为《张生煮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赋予了故事不同的时代意义,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现存的 《张生煮海》主要有两个版本,一是孟称舜 《柳枝集》本,另一个是臧晋叔《元曲选》本。孟称舜 《柳枝集》第三折的情节是仙姑毛女听到张生诉说后,将银锅、金钱和铁勺赠与张生煮海,令海水沸腾,阆苑仙母此时正在龙宫赴宴,受龙王所托前去劝化张生并为之做媒。臧晋叔 《元曲选》本中将阆苑仙母替换为石佛寺长老。两个版本除这一情节和个别曲子不同外,其余大致相同。由于 《元曲选》本流布更广,本书将此版本作为研究对象。《张生煮海》讲述的是书生张羽和龙女琼莲之间的爱情故事,可以说是一出人神相恋的神话剧。虽然基本沿着龙女报恩和柳毅传书的母题发展而来,但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已大不相同。
一、形象特征
《柳毅传》的作者并没有介绍龙女的名姓,《张生煮海》中的龙女闺字琼莲,同时唐传奇的柳毅在李好古笔下改名为张羽。名姓的改变仅仅只是外在,更主要的是人物性格的内在改变。
1、喜剧化的豪放女
唐传奇龙女的出场便是一个悲剧女性形象,她自述“父母配嫁泾川次子”。古代对女儿的称谓是 “在室女”,这也是对与父母兄弟共同生活的未出嫁的女子的统称。在强大父权制的束缚下,这些 “在室女”不可能拥有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婚姻嫁娶只能是 “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甚至她们的人身自由权都要由 “家事统于一尊”的父亲来掌控。虽然唐代社会比较开明,但婚姻自由自主仍不被世人所接受,他们同样认同封建社会传统的婚姻价值体系,即:“不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1]在这一体系中,“在室女”的婚姻大事常常沦为苟活性命、追逐名利的工具。出身名门的女性,成为政治联姻的工具;出身贫寒的姑娘,变成偿还债务的抵押品。在婚姻选择的过程中,她们所看到和得到的只是为了家族所进行的利益交换。
这一切也同样发生在龙女的身上。关系她一生幸福的婚姻是由父母控制的,我们甚至可以猜想,洞庭君将女儿嫁与泾川次子的目的并非单纯地为了女儿的幸福,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在龙女与泾川小龙的结合中,“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2]虽然她最后勇敢地站起来抗衡,奋力一搏,争取自己的幸福,甚至表达出即使赔上性命也无怨无悔绝不退缩的决心,但已经奠定了其作为悲剧女性形象的基础。
不仅婚姻选择的不自主令人悲悯,婚后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婚姻是古代女性所生活的全部世界,夫君的好恶决定着龙女生活的幸福与否。龙女向柳毅哭诉道:“夫婿乐逸,为婢仆所惑,日以厌薄”,而在 “从一而终”道德观的压制下,龙女没有权利选择离婚,只能 “诉于舅姑”,但公婆的态度是:“爱其子,不能御”,龙女也因为 “迨诉频切”而 “得罪舅姑”。可见龙女嫁到泾川龙王家之后就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丈夫贪恋女色无法自拔,公婆溺爱儿子不能主持正义。最终,龙女沦落到 “牧羊於道畔”,即便受到如此虐待,她也没办法逃离婚姻的牢笼,挽救自己,只能托柳毅传信给自己的父母,让娘家人解救自己。龙女嫁到泾河,更像是被卖给了夫家,她受到的只是与日俱增的厌恶和虐待,成为一场政治婚姻的牺牲品,她的悲剧呈现出女性对抗丈夫时的单薄无力。虽贵为龙国公主,却和广大被厌弃的女性一样,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李好古的 《张生煮海》中,与悲戚的唐传奇龙女截然不同,琼莲出场,是 “与梅香翠荷今晚闲游海上,去散心咱”[3],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让人在梦幻的场景中感受到一个龙宫公主闲适自在的生活。在观赏海上景色时,龙女将龙宫与人间做了一番比较:“觑了那人间凤阙,怎比我水国龙宫;清湛湛、洞天福地任逍遥,碧悠悠、那愁他浴凫飞雁争喧哄。”如此闲情逸致,与 《柳毅传》中龙女形象的悲剧意蕴完全相反。琼莲可以自由出入龙宫,只需要由侍女陪同即可。而唐代龙女在夫君公婆的不平等对待下,我们可以猜想她若出龙宫是多么困难。走出龙宫,琼莲轻松愉悦地欣赏美景,和侍女玩乐,而唐代龙女则是在道畔牧羊,接受风雨无情的摧残。一个喜,一个悲,两个龙女出场时不同的状态将唐代 《柳毅传》与元代 《张生煮海》定位为不同的基调。
这种改变体现了元代社会的变迁。元代是由蒙古族统治的朝代,蒙古族的经济生活方式与汉族有很大不同。做为迁移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妇女不可能和汉族妇女一样足不出户,她们必须和外界有一定的交流。美国人鲁不鲁克在13世纪曾来到蒙古,他写道:“妇女们的义务是:赶车,将帐幕装车和卸车挤牛奶,酿造奶油和格鲁特,鞣制和缝制毛皮 (她们用牛筋制成的线来缝制)。她们把筋劈成很多条的线,然后把这些线拧成一根长线。她们也缝制短袜和其他长袍。……妇女们也制作毛毡并覆盖帐幕。男人和妇女都照管绵羊和山羊。有时候是男人。有时候则是妇女挤羊奶。”[4]马可波罗在游记中也写道:“所有买卖和丈夫及家庭里所需要的东西皆是妇女做的。”[5]直至在男性为主要角色的战争中,也有女性的身影:“年轻姑娘们和妇女们骑马并在马背上飞跑,同男人们一样敏捷,我们甚至看见她们携带着弓和箭。男人们和妇女们都能忍受长途骑马,他们的马蹬很短;……她们也赶车和修理车子,装载骆驼驮的东西。她们从事所有卜作,是非常迅速和精力充沛的,所有的妇女都穿裤子,有些妇女也能象男人一样射箭。”[6]所以这些表明,在元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和社会生活,甚至男性霸权的政治生活中也有女子的参与。由于蒙古女性从事着最为繁重的工作,所以她们的家庭地位或是社会地位都非常之高。蒙古部落首领妻子的地位尤为崇高,按照蒙古传统,如果部族领袖先行离世,他的遗孀可以暂为主政,直到新的领导人即位。
上层社会女性地位的崇高必然直接影响到在其统治下的普通百姓,在当时的商品贸易发达的地区,虽然妇女工作仍以家庭劳动为主,但也开始参与商贸活动,在这些商贸活动中,展现了女性的经济才能:“浙西风俗太薄者,有妇女自理生计,直欲与夫相抗,谓之私,乃各设掌事之人,不相统属,以致升堂入室,渐为不养之事,或其夫与亲戚乡邻往复馈之,而妻亦如之,谓之梯己。……今渐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羽以成风。”[7]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汉族妇女也同蒙族妇女一样由于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得到了与丈夫平起平坐的权利。在元代,无论是蒙古族还是汉族,抑或是其它少数民族女性的地位都较之其它朝代有很大提高。
其次,元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龙女琼莲表现出少有的自信,这在唐代龙女的形象中是没有体现的。琼莲评价自己的容貌时说:“风飘仙袂绛绡红,则我这云鬟高挽金钗重,蛾眉轻展花钿动;袖儿笼,指十葱,裙儿簌,鞋半弓。”[3]在这段描绘中,我们体会到的是琼莲对自己美貌的充分自信和欣赏。唐代的龙女虽然也有着漂亮的容貌,但她却不敢妄自评价,只是借柳毅的眼睛,我们看到她的“殊色”,在被解救回宫后,仍然是借柳毅的双眼观察到龙女的美丽本色:“自然蛾眉,明珰满身,绡縠参差”。在龙女告诉柳毅真实身份时,评价自己的夫君为:“无重色之心”,可见龙女的容貌实为非凡,但却从未将此作为自己婚姻幸福的筹码。琼莲对婚姻的价值观则略有不同,正因为知道自己 “容貌端的非凡也”,在水国龙宫里拥有无虞生活的琼莲才会有这样的烦恼:“似俺这闺情深远,直恁般好信难通。”对自身容貌的认可,加上琼莲一心认为长相标志的人儿必须有一段好姻缘,才能配得上这非凡的容貌,而龙宫里 “无非是蛟虬参从,还有那鼋将军,鳖相公,鱼夫人,虾爱宠,鼍先锋,龟老翁”,这些长相怪异的角色又怎能被美丽的龙国公主相中呢,因此琼莲才会有 “好信难通”的烦恼。这时,风流倜傥的书生张羽出现了,他带给孤单寂寞的龙女琼莲的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不仅容貌非凡,琼莲还是一位才女。张生的琴声将龙女吸引,还未与张生谋面,琼莲就从悠扬的韵律中感受到张生的才情和心性:“端的心聪,那更神工。悲若鸣鸿,切若寒蛩,娇比花容,雄似雷轰,真乃是消磨了闲愁万种。这秀才一事精,百事通。我蹑足潜踪,他换羽移宫;抵多少盼女词媚涪翁,似良宵一枕游仙梦。因此上偷窥方丈,非是我不守房栊。”[3]未见其人,却能先感受弹奏者在音乐中所表露的情感,并理解得十分到位,可见元杂剧中的琼莲不仅是美丽的,更是具有才情和智慧的。对琼莲的刻画,作者力求完美,她不仅要知书达理、温柔贤淑,而且也要秀外慧中,能够精通琴棋书画。所以,《张生煮海》中的琼莲,外貌上是艳丽动人的美女,内在气质上是精通音律的聪明才女,这种才貌双全的形象,完全不同于唐传奇中对才情没有任何刻画,仅仅是长相 “殊色”的龙女,这种改变反映了元代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和宽松的社会环境。
最后,敢于对爱情大胆直接的追求也是唐代龙女和琼莲的主要区别。《柳毅传》中龙女与柳毅的结姻最开始是由钱塘君做媒,钱塘君为侄女与柳毅牵红线之前是否征求过她的意见,询问过她真实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龙女对自身爱情的诉求在作者的眼中是无足轻重的,并不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内容,故将此段省略。之后龙女为柳毅生下一子,重述前缘时解释道:“衔君之恩,誓心求报”。龙女最终和柳毅成为夫妇,但我们只能从龙女的表达中感到她对柳毅之情以报恩为主,即使有因为义士搭救而萌动于心中的爱情,龙女也未能宣之于口。
《张生煮海》中的琼莲无意听到张生的琴声,便激发出心中涌动的情思:“莫不是汉相如作客临邛,也待要动文君,曲奏求凰凤;不由咱不引起情浓。”[3]在张生询问龙女可否嫁与自己时,龙女更是大胆直白:“我见秀才聪明智慧,丰标俊雅,一心愿与你为妻子。”[3]二人成婚后,龙王向女儿问询为何与书生张羽初次见面就许下婚约,龙女回答说:“他待觅莺俦燕侣,我正愁凤只鸾孤;因此上,要识贤愚,别辨亲疏;端的个和意同心,早遂了似水如鱼。”[3]从细微处我们感受到琼莲作为元代女性,她冲破封建礼教的阻碍,具有强烈的婚姻自主意识,龙女的身上闪耀着人性解放的自由光辉,她开始主动掌握自己的婚姻大事,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爱和婚姻,自由选择她理想中的伴侣,为了婚姻理想不懈斗争。前文中提到,元代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她们的社会地位也逐步提高,在元代,认为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劣势有一定程度的弱化,女性开始掌握对爱的选择权。因此,元杂剧中的女性往往大胆主动。正如幺书仪先生所持观点:“在元人爱情剧中,女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在反抗外力的阻挠、在争取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8]琼莲身为公主,属于上层社会的贵族小姐,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基础,她对人间景色的评价也体现了其在锦衣玉食的生活中所体会的优越感,她还应该受过封建道德体系的教育,为儒家思想所熏陶,因此,琼莲更渴望追求爱情和婚姻的理想,必然对伦理和封建婚姻制度加以反抗,以达到爱的解放。
2、儒生:充满智慧的凡夫
张羽与柳毅同为书生,但作者刻画的重点却不同。
张生自报家门时描述自己是:“自幼颇学诗书,争耐功名未遂”[3],“颇”在 《辞海》中的释义为 “很、相当”,一个 “颇”字,可以表达出张生将自己定位在了 “才子”的行列。在石佛寺住下后,张生又描绘住所为:“僧家清雅,又无闲人聒噪,堪可攻书”[3],虽然功名未成,但这段描绘让我们看到了张羽乃是一个喜好读书的儒雅之士。当天色已晚,四下无人,张生散心的方式则是抚琴,更体现了他不同凡俗的生活旨趣。优美的旋律将出海游玩的琼莲深深吸引,琼莲评价张生的琴声是:“恰便似颤巍巍金菊秋风动,香馥馥丹桂秋风送,响珊珊翠竹秋风弄。”[3]张羽在音乐上是才华横溢的,不仅深谙音律的琼莲对他有如此高的评价,就连随行不懂音乐的丫鬟也觉得他的琴声 “悠悠扬扬,入耳可听”,“果然弹得好也”,这无疑直接肯定了张羽的音乐才能。前文曾论述过才貌双全的龙女形象,《张生煮海》中不仅对女主人公要求如此,对男主人公的要求亦如是,不仅应当精通诸子百家、诗书文章,还要通晓音律歌舞。琼莲见到张生的样貌时,大呼 “好一个秀才也”,同样,张生不仅有 “才”,也拥有姣好的容貌,同龙女一样也是才貌双全。
但是,琼莲的怦然心动首先是听到张生的琴声,也就是首先被他的 “才情”所吸引,之后才看到张生的容颜,此时,“才情”已经成为对男主人公的突出要求。《柳毅传》中介绍柳毅为:“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之后就没有了对柳毅才华的刻画,读者对柳毅更多的印象则是 “义”的体现。柳毅身上,“才情”仅仅是一种点缀,至于对其容貌的描写更是没有丝毫涉及。
正如本文所述,元代统治者来自于草原,他们精骑善射,以武力征服天下,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重视武略,而轻视文化教育。因此,元代统治者轻视儒生,对从隋唐以来兴起的科举制度也避而不谈,元代的实际统治时间为163年,其中只有45年举行过科举考试,录取率又极低,可见通过此途径选拔官吏的数量是微乎其微。在这为数不多的科考中,为维护蒙古民族利益,蒙古人和色目人还拥有特权。因此,和中国历代王朝相比,科举在元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使得当时社会中文人的地位下降,科举的减少甚至停开,也阻塞了文人儒生进入仕途的门径。
但由于历代文人都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形成了积极人世的心态。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兼济天下”是他们无法割舍的人生终极理想,中国古代文人穷尽毕生精力,都是在探寻达到终极理想的途径。元代的现实生活告诉文人仕进无门,但那积极入世的思想却依然存在于他们内心深处。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异成为一种落寞的矛盾心理长久存在于元代文人心中。所以,尚仲贤笔下的柳毅一脱古代儒生入世的藩篱,将科举看作可有可无的东西。李好古亦如是,将科举视为无物,但与尚仲贤不同的是,李好古仍不能彻底摆脱儒生的理想追求,于是将其异化为 “才情”嫁接在张羽和琼莲的形象特质上。
其次,张羽同元代其他才子佳人戏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有对爱情直接大胆的追求。他和琼莲相见后,主动相问,并询问龙女的名讳,当按照礼节介绍自己时,又顺带提及 “并无妻室”,看似无意之语,细细品味,我们能感受到当张羽被琼莲的美貌和才华所打动,胸中荡漾起的澎湃激情,这也为后来张羽的求婚打下伏笔:“小娘子不弃小生贫寒,肯与小生为妻么?”[3]得到琼莲的应允后,又迫不及待地催促道:“既蒙小娘子俯允,只不如今夜便成就了,何等有趣;着小生几时等到八月十五也!”[3]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不可耐要与琼莲成就好姻缘的尘世俗人。接着,张生又向龙女索要定亲信物,生怕口说无凭而误了好事。龙女离去后,手拿琼莲留下的鲛绡帕,张生却仍不放心:“我看此女妖娆艳冶,绝世无双。他说着我海岸边寻他,我也等不到中秋”[3]。元杂剧人物形象对风月情事的大肆追求已经不同于唐代,纵观 《柳毅传》全文,无一字表达柳毅对龙女的爱慕之情,和对自己婚姻的期许。李好古则将张羽对情爱的追求大肆渲染,细心刻画。虽然 《柳毅传》中也描绘了柳毅和龙女的结合,但这无关乎风月之事,只是李朝威为了娱乐而体现出了文人骨子里的浪漫虚荣,其中甚至带着夸耀的闲情逸致。在元朝,如前所述,文人失去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他们逃不出早已设定好的社会角色,因为儒家思想已根深蒂固,却又无法面对现实的宿命,他们被排挤于社会边缘,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们悲愤、抑郁,却无奈。于是,他们在才子佳人的戏剧表演中寻求慰藉,用才子对风月的追求来麻醉自己,以求得暂时的精神解脱。
最后,总是混迹于勾栏瓦舍的封建文人们难免会受市井习气的影响。体现在张生的性格上就是对财富毫无遮拦的追求。唐传奇中的柳毅最终也得到了财富,“赠遗珍宝,怪不可述”,从龙宫出来,“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凭借这些财富,柳毅成为淮右富族,“百未发一,财以盈兆”。虽然龙王将这些珍宝赠送给柳毅时,文中并未描写柳毅像拒绝与龙女成婚那样决绝,但也未写到柳 毅对财富的直接索取,可见唐传奇中所体现的对财富的追求是隐性的。而张羽对财富的追求从隐性变为显性,当他与琼莲互传情愫后,张生竟问:“小生做贵宅女婿,就做了富贵之郎,不知可有人服侍么?”[3]二人分别时,他又说:“有如此富贵,小生愿意往。”与龙女不多的几句交谈中,就两次提到了富贵,这在唐代儒生看来是多么不堪,但这点却并没有影响到张生的形象,而是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真实。由于失去了仕进的机会,不能直接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地位低下,加上生活窘迫,使得元代文人日益边缘化。同样是由于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放下儒生的架子,走出理想国,逐步融入到那个他们曾经鄙夷的阶层中去,成为混迹于勾栏瓦肆的文化承载者。和唐传奇一样,张羽最终在功名路上止步不前,回了瑶池,成为神仙,情感价值虽已凌驾于功名之上,但还得考虑吃穿用度。这正体现了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文人们和市民阶层在价值观上的相互影响,更是由于李好古自身生存的需要而最终放下了高雅文人的心态。
[1]刘宏章校注·论语·孟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4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4.
[3]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78-195.
[4]耿开、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不鲁克东行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8.
[5]冯承钧译·马可波罗游记[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62.
[6](意)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著·出使蒙古纪[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18.
[7](元)孔齐·静斋至正直记·(卷二)[M].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社,1972:浙西风俗卷.
[8]幺书仪·元人杂剧和元代社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1.
The Image Characteristics——“Zhang Sheng Zhu Hai”and“Liu Yi Zhuan”
Jiang Nan
(Tongling Vocatinoal Technology College,Tongling 244000,Anhui,China)
“Sha Me DaoZhang Sheng Zhu Hai”written by Li Hao in Yuan is one of the deductive works of the Tang Dynasty Legend in“Liu Yi Zhuan”.And it is highly acclaimed in a guide to the afterlife.The author starts with two characteristics--Long Nüand Ru Sheng,and tries to explore the adapt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ama of the Yuan Dynasty o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reflected in it.
“Liu Yi Zhuan”;“Zhang Sheng Zhu Hai”;Long Nü;Ru Sheng
颜建华)
I207.04
A
1673-9507(2014)01-0011-03
2013-12-10
姜楠 (1982.05~),女,山东烟台人,铜陵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