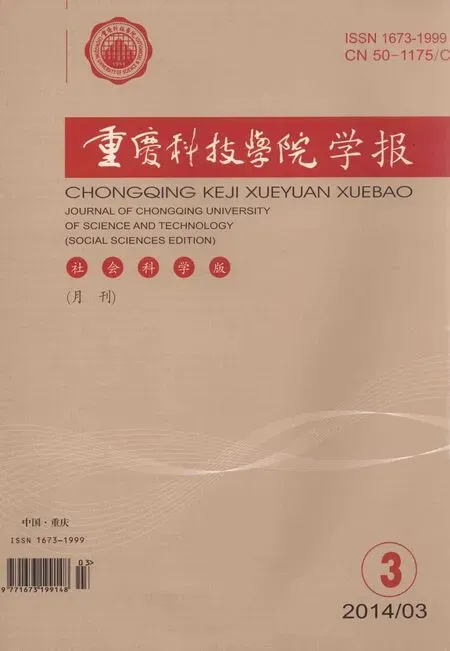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新型盗窃行为视角
孙大勇,张恒志
盗窃罪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犯罪,与民众的财产利益密切相关,成为各国刑法规制的重点。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通说采用的是“控制说”,与此相对的观点是“失控说”。在一般情况下,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之时,也就是行为人非法控制财物之时。在这种情况下,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是统一的。然而,司法实践中我们会发现盗窃罪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形:被害人已经遭受了财产损失,而行为人却由于意外因素的介入并没有实际控制或者取得财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通说的观点,该行为构成盗窃罪未遂;但是,如果按照失控说或损失说,其行为则构成盗窃罪既遂。在司法实务中,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才定罪处罚。因此,盗窃罪既遂标准的确定,关系到罪与非罪的界分问题。
一、盗窃罪既遂标准的理论纷争
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由于各国对盗窃罪构成要件的界定不同,理论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八种学说:接触说、转移说、隐匿说(或藏匿说)、失控说、损失说、控制说、取得说、失控+控制说等[1]。前三种学说主要是德日刑法学的观点,在我国关于盗窃罪既遂标准的争论主要在后五种学说中。
后五种学说虽然名义上是五种学说,但实际上就是控制说和失控说这两种学说的争论。从词源学意义上来说,取得和控制的含义是相通的,某人取得了某物也就是实际上控制了某物,二者的法律性质是等同的。因此,正如有学者所言,“控制说”和“取得说”,实际上是异曲同工,两者都是同一理论,只是称谓不同而已[2]。同理,某人失去了对某物的控制,也就意味着遭受了财产损失,这时的法律评价应当是等同的。因此,“失控说”与 “损失说”并无二致。另外,当一个人控制了某物,必定意味着另一个人已经失去了对该物的控制,因此,“失控+控制说”实际上就是“控制说”的翻版。在此分析基础上,重点探讨“失控说”、“控制说”两种学说。
(一)失控说
该说主张以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即以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支配权为界限。这是一种站在被害人立场的观点。凡是财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因犯罪分子的窃取行为,丧失了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就是盗窃罪的既遂;凡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财物并没有脱离所有人或者保管人的实际控制的,则为盗窃罪的未遂。
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盗窃未遂。”根据该司法解释,关于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应当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财物的实际损失(即“损失说”)进行判断。然而,这一规定在 1998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并没有再次出现,因此,“损失说”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虽然“失控说”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但理论界支持该说的学者还大有人在。
(二)控制说
该说主张以财物是否实际被行为人非法占有作为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即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所窃取的财物作为盗窃罪的既未遂的分水岭。这是一种站在行为人立场的观点。在盗窃过程中,如果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所窃取的财物的,就是盗窃罪既遂;反之则是盗窃罪未遂。这是当前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主流观点。
2003年11月,《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谈到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时指出:“贪污罪是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职务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显然,现阶段我国的司法实务部门是赞同“控制说”的,毕竟审判权掌握在法院手中。
二、失控说之提倡
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占有了某项财物,也就表明被害人失去了对该财物的控制。因此,无论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实现,还是从保护被害人利益的立场考察,“控制说”并无不妥之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被害人因行为人的窃取行为而丧失对财物的控制,而行为人又没有实际取得该财物时,应如何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例如,扒手在集市窃取正在行走路人的祖传玉佩时,因学艺不精,割断玉佩挂绳时玉佩没有掉入手中,而是顺势滚入桥下河流内。在此情况下,路人遭受到了切实的财产损失,而扒手并没有实际控制该玉佩。根据“控制说”,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在主观上并未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也未实现实际控制财物的结果。因此,其窃取行为只是处于一种未遂状态。这种忽视了被害人因交付财产而使其财产利益遭受完全侵害的事实的观点值得商榷。
首先,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在同一窃取行为下,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与行为人能否实际控制财产在法益侵害性上是等值的。在犯罪成立的基础上区分既遂与否,其实质是区分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法益的侵害程度,从而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通常认为,在同种犯罪中,法益侵害性等值的行为应当处于同一个犯罪形态。因此,在盗窃罪中,只要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窃取行为遭受了财产损失,无论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产,对于被害人来说,其财产损失是相同的,不因行为人最终能否实际控制财产而有所减损。其实,“财产所有权遭到侵害,意味着行为使财物的控制范围实际发生了转移,而行为人是否获取了所有权的权益则是将来发生的事情”[3]。刑法的任务之一是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既然财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失去了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就说明其合法权益已经遭受了实际侵害,其财产损失已经发生,危害结果也已经产生。至于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该财产或者如何处置该财产,这已经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是否受到侵犯无关[4]。
其次,犯罪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与既遂相区别的基本标志,而目的犯中的目的能否实现,不影响犯罪既遂的成立。一般认为,犯罪未得逞是指没有发生行为人所希望或者放任的行为性质所决定的危害结果。行为人所希望、放任的结果应当限定于实行行为的性质本身所能导致的结果(即行为的逻辑结果),不包括没有实现目的犯中的目的的情况。在行为的逻辑结果已经发展完毕的情况下,犯罪就已经得逞。
盗窃罪的行为逻辑是:行为人实施窃取行为——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正如张明楷教授所言:“非法占有的目的并不是盗窃罪主观方面要件的要素,而是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是超出了主观构成要件要素范围的一种心理态度。这种超过要素不要求有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只要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即可[5]。”也就是说,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实现不是行为的必然逻辑结果,不影响犯罪是否得逞的认定。因此,只要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窃取行为而遭受财产损失,盗窃罪即可以认定为既遂。
最后,以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符合《刑法分则》对盗窃罪的罪状描述。一般认为,我国的《刑法分则》是以犯罪既遂形态为立法模式的。因此,按照《刑法分则》对盗窃罪的规定,诈骗罪既遂有五种表现形式:窃取行为+数额较大、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在窃取公私财物行为下:其一,作为定罪要素之一的“数额较大”是以犯罪对象的价值大小而不是以行为人违法所得数额多少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而犯罪对象的价值就是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其二,作为定罪要素之一的 “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分别是以行为人盗窃的次数、场所、携带的犯罪工具、场所+指向的犯罪对象作为定罪量刑标准的,而与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财物无关。由此看来,以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即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是完全符合立法规定的。
因此,盗窃罪应当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既遂标准(即“失控说”),而不宜以行为人实际控制财物作为既遂标准(即“控制说”)。 当然,所谓“实际控制”,并非指财物一定在行为人手里,而是说行为人能够在事实上支配、处理该项财物[6]。
三、以失控说评析新型盗窃行为的既遂标准
在此,我们已经确立了以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然而,所应注意的是,在认定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时,必须根据财物的性质、形状、体积大小、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状态、行为人的窃取样态等进行判断[7]。因此,拟以《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行为为例,对盗窃罪的既遂标准进行进一步分析,以廓清“失控说”的实际内涵,为司法的统一适用提供借鉴。
(一)入户盗窃既遂的认定
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供他人家庭生活、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盗窃的行为。以常理来判断,户内的财物应当推定为属于房屋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其对于财物有事实上的控制权。入户盗窃应当以行为人把财物转移到户外作为认定盗窃罪既遂的标准。如果行为人把财物转移到了户外,就表明财物已经脱离了房屋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的控制,盗窃罪成立既遂。如何认定户内,应当按照房主个人所能控制的范围为界。如果是楼房或没有院子的平房,户内与户外应当以房门作为户内外的界分线;如果是是带有院子的平房、别墅或楼房,所谓户外应该是指院子的围墙之外。如果行为人实施盗窃时并未走出院门即被发现并被擒拿,则应当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人窃取体积很小的财物(如戒指、项链)时如何认定盗窃罪既遂。只要行为人处在户内这一特定场所,即使财物已被其实际控制,但由于户的性质所限,房主仍对该财物具有控制的可能性,这时的财物处于双重控制下,其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应由行为人的后续行为而定,而不应当一律认定为盗窃罪既遂。如果行为人在户内主动放弃对财物的非法占有而放回原处或者很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其行为构成犯罪中止;如果行为人只是把财物暂时藏匿在房主很难发现的地方,以待寻找有利时机取走,其行为构成犯罪既遂;如果行为人窃取财物后被房主及时发现而要回,其行为构成犯罪未遂。
(二)携带凶器盗窃既遂的认定
携带凶器盗窃是指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盗窃;或者为了实施违法犯罪携带其他足以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器械的盗窃的行为。立法者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目的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一般盗窃行为更为严重。行为人携带凶器盗窃会使其人身危险性更大,更容易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从而方便犯罪分子实施盗窃行为。携带凶器盗窃不但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也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形成潜在的威胁。但是携带凶器盗窃侵害的法益只能是被害人的财产权,而不包括其生命健康权。如果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造成了侵害,这时的携带凶器盗窃行为已经转化为抢劫罪,超出了盗窃罪的评价范围。因此,那种认为携带凶器盗窃是行为犯,行为人着手就既遂的观点是不恰当的。笔者认为,携带凶器盗窃与一般盗窃行为没有质的差别,只是行为人在犯罪工具上下了一番功夫,使其盗窃行为更容易得手。携带凶器盗窃仍然是盗窃罪的一种,既遂的标准仍然需要行为人使财物脱离被害人的控制范围。
(三)扒窃既遂的认定
扒窃是指在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扒窃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场合(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针对特定对象(随身携带的财物)的盗窃行为。按照失控说的原理,行为人只要将财物从被害人身上或者身边拿走,使得财物脱离被害人对其的实际控制就应当认定为扒窃行为的既遂,如果并未使得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实际控制即认定为未遂。生活中常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扒手行窃时被人发现而仓皇逃窜,随之被人擒获。在这种立即发现、立即追赶的情况下,无论扒手有没有从被害人身上或者身边拿走财物,只要扒手当场被抓住,被害人就没有丧失对财物的实际控制,扒窃就应当认定为未遂。
[1]高铭暄.新中国刑法研究综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640-643.
[2]王礼仁.盗窃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77.
[3]姜先良.论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A].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13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58.
[4]王志祥.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新论[J].中国检察官,2007(3).
[5]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31.
[6]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198-199.
[7]张明楷.刑法学:第 4 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887.
——兼论“二维码偷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