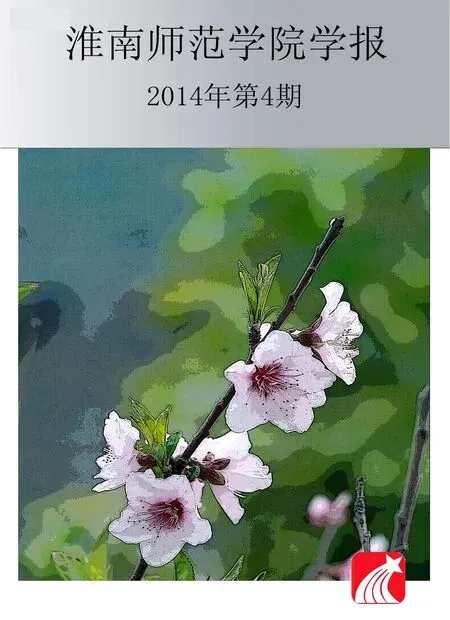中国近代教育与国民性研究的缘起、发展与启示
郭瑞迎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中国近代教育与国民性研究的缘起、发展与启示
郭瑞迎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对早期文献进行分析发现,国民性与民族性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而与社会性、人性相区分。近代教育与国民性研究的缘起主要受到教育与国民性的传统联系、内忧外患的夹击以及他国的影响等因素的推动。早期文献主要是从本国单一比较、多国比较以及他者立场三种角度对中国国民性特征展开讨论,并提出用教育改造国民性的具体措施。主要启示有:国民性是事实也是臆想;改造国民性不等于改造人性;教育对国民性改造作用是有限度的。
近代;教育;国民性;人性
国民性,一个跨世纪的话题,在20世纪,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如此憎恨自己国家的国民性,并迫不及待地要通过教育对其进行改造。那么上世纪早期该问题是如何产生并得到探讨,是为本文主要论述的问题。
一、教育与国民性研究的缘起
(一)教育与国民性的传统联系
《大学》的开篇之句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且诸如“夫治国莫先于开民智,利民生,以成民性,前者为教,后者为育”这样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们相信“一国文野兴替,教育恒左右之。今吾人欲重新估定国民性,当注意乎教育,惟教育视野,步骤鲜明,务本培根。”①《国民性与小学教育》,《湖南教育》1928年第4期。另一方面,当时“我国教育上的弱点,暴露太多,在量的方面,国家向漠视国民教育,机会不能均等,在质的方面,教育内容失之空虚,与实际隔离太远”,这样的教育与民族复兴的理想背道而驰,“欲挽救我民族之危机,自非从教育上亟行改造不可”。②《改造民族性与发展历史文化教育》,《建国月刊》1933年第9卷第4期。因而可见,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实情况的分析上来讲,都表明在我国用教育来型塑国民性决不是偶然。
(二)内忧外患的夹击
外部列强的不断入侵,内部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是国民性改造兴起的根本原因。在技术救国、经济救国、政治救国等努力均告败后,国人开始从自身找原因。立国必先立人,无论是经济制度改革,政治制度改革,或者思想观念的革新,都要靠“立人”来完成,故而,进行国民性改造成了当时的第一要务、而对国人进行思想启蒙,唤起民众精神上的觉醒,教育的作用当仁不让。特别是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了空前的威胁,教育界人喜欢谈民族复兴的教育,③邱椿:《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前途》1933年第1卷第7期。.“复兴民族精神必先提倡乡土教育”、“用教育来振起我们的民族精神”、“音乐教育与民族精神”等都被提上日程。
(三)他国的启发
诸多遭遇,都是中华民族近五千年来未曾遇过的,国人在寻求出路的同时,也在找着与自己有着相似之处的“盟友”,希望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产生共鸣并有所借鉴。因此,日本、法国、以及在战后迅速复兴的德国,都成为国人与之比较的对象。用镜秋的一句话来讲,即“世界各国对于爱国教育,都是积极的提倡着,以培养他们国民爱国爱族的观念。所以,我们也应当竭力鼓吹的呵!”①镜秋:《用教育来振起我们的民族精神》,《广播周报》1935年第31期。中国人从他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认为其他各国之所以能够生存于现世界,都是赖于他们各有其特殊优良的国民性。由此类推,中国亦可,用教育改造国民性则顺理成章。
二、先期关于教育与国民性的研究
(一)关于国民性概念本身的研究
“国民性”一词,英文为nationalcharacter,是源自欧洲,途经日本,再到中国的“舶来品”。在我国近代的期刊文献中,对“国民性”一词的探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国民性与民族性
经发现,同一时代的作者在谈论同一对象的时候,有的使用民族性这一概念,有的则使用国民性这个概念,均没有对二者作严格区分,国民性就是民族性。
一部分学者使用民族性这一概念进行论述。1933年邱椿认为所谓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对于其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所表现之特殊的“模型反应”。一个民族的模型反应,就民族的内部说是共通的,对外族是特殊的。它不是先天的,而是获得的;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动的。它的形成与改变,由于遗传,环境,教育三大因素。②邱椿:《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前途》1933年第1卷第7期。之后,王政、庄泽宣与陈学恂也采用民族性这个概念,认为民族性是由种族遗传、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交感互映的产物。③王政:《书评:中国教育史与中国民族性》,《是非公论》1936年第17期;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图书季刊》1939年第1卷第4期。1940年陈科美在研究教育与民族性关系的时候,则进一步将民族特性分为根本的特性和附属的特性。④陈科美:《教育与民族性》,《福建教育》1940年第1卷第2期。
另一部分学者采用国民性这一概念。1914年玄中认为,“所谓国民性焉,国民性者,因一国之风俗、地理、历史之特点以造成者也,山国之民多深毅力,海国之民多活泼,寒国之民多局促,热国之民多轻浮,专制之民多墨守,民治国民多踔厲,国家者,因其国特别之国民性所造成,并因保存此国民性而发挥广大,以振起其立国之真精神,然后其国乃得永存在而不敝。”⑤玄中:《国民性论》,《民国》1914年第1卷第1期。1926年邹敬芳也认为,一国的国民性的基础,是筑在国家的地理环境,国民固有的遗传,历史的因果,以及哲学的思潮上面的。这与上文相关学者对于民族性的界定基本是一致的。
第三种情况是将国民性与民族性概念同时混用。如1931年冯庸大学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一民族的生活状态,即可表现其民族的优劣,故一民族的一切活动,都是表现其民族的元气,元气旺盛的民族是进展的,是创造的,是革新的,是进而政府其他一切的。故一国国民性的优劣,与其国的强大关系至大,是不得不注意的。”⑥《今日中国的国民性》,《冯庸大学月刊》1931年第2期。1939年许昌业翻译的日本学者水野梅晓的文章中标题是“关于中国的国民性”,但是内容却以汉民族为主要对象进行论述。1941吴贻芳在论述国民性的时候说到,“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能够生存于现世界,都是赖于他们各有其特殊优良的国民性。”
(2)国民性与社会性(社会思想)
鉴于“社会”这个概念也是一个舶来品,所以在早期论述国民性与社会性的关系中,对于这两者关系的探讨不多。在笔者的查找范围内,仅发现两篇与之相关的简要论述。一则是邹敬芳认为一国的国民性,是先形成于国家的,民族的,因袭的地盘上面,然后渐次向社会的,个人的,进化的方面发达的。前面的普通都叫他做国民精神,或国民思想,后面的普通都叫他做社会思想。二是在1937年一篇译作中,作者七理重惠认为,“中国的国民性,常被中国的社会性所包涵,国民性的特异的,独特的,遂致埋没于社会性中,缺乏表露于外面……那么,我们要明白中国的国民性自应先从社会性开始。”⑦[日]七理重惠:《中国的国民性(特译稿)》,陈兆蓝节译,《周报》1937年第1卷第3期。但是,该译文中对中国人“富于顺应性”的社会性进行论述的方式,也是从地理环境、人的环境角度进行的,与其他关于国民性与民族性论述的方式基本相同。可见当时对于这两者的认识还不够清晰,也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
(3)国民性与人性
关于人性,中国自古就有“性善论”、“性恶论”、“性不善不恶论”等说法,因此,在国民性与人性的比较上,观念比较清晰。1914年玄中在《国民性论》中明确指出了人性与国民性的不同之处,认为,“有人类之公性,有国民之特性,博爱平等自由,人类之公性也。所谓国民性焉,国民性者,因一国之风俗、地理、历史之特点以造成者也。”1934年罗廷光分析了英法德美意俄的国民性与教育制度的关系时也指出,自从民众教育推行后,人类的固有特性已经改变了很多,因此,国民性一词亦不可滥用。
(二)中国国民性的特征
(1)国人眼中的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可谓是最早的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论述。他认为国民性即“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国民性中有正面积极的方面,也有负面消极的方面,后者即劣根性,而“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梁启超所总结的国人的劣根性有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以及无动等六点。同时,他在《新民论》里又举出华族所最欠缺的十个方面:即公德心、国家思想、冒险精神、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进步精神、自尊心、合群力、生产能力、毅力等。
庄泽宣和陈学恂则将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限于“停滞的社会”的现象归结为中国的民族性,认为中国民族理想对于宇宙观念乐天安命,尊重现世,故产生自然放任与迷信,而缺乏宗教信仰,对于人生,重视伦常道德,以家族为中心,“推己及人”为出发,“中庸调和”为原则,“克己复礼”以自省,其结果重视家族观念而轻于社会意识,对于事物能守淳朴生活,力求知足常乐之生活理想,于是缺乏科学发明能力。①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图书季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邱椿在总结梁启超、日本渡边秀芳,美人亨丁顿关于中国国民性讨论的基础上指出,华族最显著而亟应改造的民族性还有三种,一是自私自利,因为自私自利,所以缺乏合作与组织能力,缺乏国家思想,所以日本敢大规模蚕食中国领土;二是文弱,即体格瘦削,精神萎靡,意志薄弱的意思,因为性格文弱,所以厌恶一切正义的战争,而迷恋奴隶的和平,所以懒惰喜静,所以缺乏毅力;三是虚伪,所谓虚,即不切实际,所谓伪,即好说假话,空虚确是华族一种显著的民族性。②邱椿:《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前途》1933年第1卷第7期。
曾克熙是从当时准备战争的角度谈及中国的国民性,认为准备战争最重要的有物质的和心理的两方面。在心理学方面,第一点,我们的国民性是散沙的,个人的,游离的,乃至于时常互相摩擦冲突;第二点,我们必须是建设的,积极的,前进的,而不可固步自封,消极的,保守的;第三点,我们必须是踏实的,从根底起认真努力,我们不可再轻浮、表面,敷衍了。③曾克熙:《由太平洋战争说到中国国民性》,《改进》1942年第5卷第12期。
以上均是侧重于从反面特征关注国民性,而从优缺点两方面审视国民性的也有。如陈科美将民族性分为根本特性和附属特性,中华民族的根本特性,一方面是非常坚强的,一方面是比较消极的。中华民族的附属特性,第一是容忍性,第二是保守性,第三是中和性,第四是现实性。④陈科美:《教育与民族性》,《福建教育》1940年第1卷第2期。冯庸大学月刊上的一篇将我国国民的优劣点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论述:优点有:1.好和平;2.无阶级的观念;3.善忍耐;4.能勤俭;5.能服从;6.人心宽大;7.大同主义;8.唯物主义;缺点则是:1.不知礼仪谦让;2.不知亲切爱人;3.不知研究独创;4.诈欺不真实;5.偏私不正义;6.虚伪倖进不进取;7.荒怠浪漫;8.醉梦不觉;9.缺少公益道德的精神;10.缺少合作互助的精神;11.缺少竞争追求真理的精神;12.社会制裁力的薄弱;13.国家观念的薄弱。⑤《今日中国的国民性》,《冯庸大学月刊》1931年第2期。
玄中则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国民性,他将中国“向来之国民性”与“今日之变相”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向来之国民性的特质表现为:1.正道公义;2.崇尚清议性;3.富于侠义之性;4.团结性;5.高尚性;6.淡泊性。而在今天,那些以往的那些国民性特质已经渐失,名存实亡,变成了:1.举世相竟于势利之途;2.权力之所在,即道德之所在;3.趋于势利,习为吝鄙,以负义为能事,以无信为当然,依强以凌弱,克人以自肥;4.苟有利于己者,虽自残同类可也,苟势高于我者,虽谓他人父可也,苟于其一身有大益得厚;5.以依赖为第二之天性;6.志行猥琐,目光如豆,所争不出货利之外,所虑不越市井之间;7.骄奢淫逸,挥霍无度。①玄中:《国民性论》,《民国》1914年第1卷第1期。
(2)多国比较中的中国国民性
比较出真知,在与他国的比较中清晰自己的国民性,也是早期国民性研究的一个特点。多者比较,有同有异,无论是相同还是相异,都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自己。
宋以衡从观察世界经济会议上各国的表现着眼,采取以小见大的方式窥探各国的国民性。②宋以衡:《从世界经济会议观察各国国民性》,《中华周报》1933年第88期。他从美国人低减关税,但又有一定的限度的主张上,看出美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粗放的国民性,以及那种勇往直前,具有坚强有力的生活意志的品性。法国则由于带着浓厚的传统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再加上国民大多是农民、信奉加特力教派,性情质朴而勤勉,重视现实秩序,所以在会议上完全表现了他们的顽固,偏狭,现实,坚强的性质。而德人坚忍的性格,强烈的义务意识,在愤慨激昂中,在应然失望中,也是格外光芒万丈的。至于英国,他认为在此次会议中则完全表现出了老奸巨猾的行径,他把国家看作最大多数最大物质的寄托机关,而国策总是倾于物质利益最大的方向,他对于利害的打算非常敏感,而利益的主张又绝不肯露骨,那种虚伪的绅士面子,与斯文的绅士态度,英国是独擅胜场的。
邹敬芳从整体视野出发,分别论述了各国国民性的特点之后(如表1),将中国与其他各国进行差异对比,认为中国人和英国人相比,在傲慢自尊、功利、权利、责任思想方面差得远,但是进取的、调和的上面是相同的;和法国人相比,创意理想的念头、社会的正义思想缺乏,艺术的、浪漫的更差得远,但是直觉的、情绪的、感受的、空想的特征和法国差不多;和德国人相比,哲学的、批判的方面差远了,但是服从的、抑制的、统一的特征差不多。因而他认为,中国国民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一齐感受、调和、和统一世界的文化和思想。③罗廷光:《英法德美意俄的国民性与教育》,《教育杂志》1934年第24卷第4期。

表1 邹敬芳关于各国国民性的论述
罗廷光则是从国民性与教育制度的关系视角出发,指出国与国之间教育制度的差别绝不是因为教育理论的歧义,而是由各国的国民性所决定的。他所总结的各国教育制度与国民性的对比论述如下(表2)。

表2 罗廷光关于各国国民性的论述
通过以上各国情形的对比后,罗廷光得出结论:由于环境的不同,任何一国教育制度决不可贸然移植于他国。但这并不是说,各国教育,必须个个保持独立,彼此不生关系。只是强调:一是教育理论和实施的发展,很难得到普遍的应用;二是教育学者应根本认清所研究国家的文化背景,即与教育有关的背景。教育史上那些将西方教育制度整套移植到东方的失败例子,已成了共见的事实。教育上的成功是由于个性的适应,那么国家教育制度的成功是由于国民性的适应。
(3)他者眼中的中国国民性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荣辱”。外人眼中的国人形象,就像一面镜子,使国人可以更加清醒的看见自己。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素质》是西方关于中国民族性格最早的著作,对后世影响极深。明恩溥根据自己在中国传教22年的经历和观察而得出结论,书中概括论述了中国人的26条持质,包括重面子、节俭、勤劳、守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天性误解、拐弯抹角、柔顺固执、心智混乱、麻木不仁、轻蔑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因循守旧、漠视舒适方便、有活力、忍耐、知足常乐、孝行当先、仁慈行善、缺乏同情、共担责任和尊重律法、互相猜疑、言而无信、多神泛神无神等。书中描述的基本色调是贬多于褒,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难免有偏颇之词。
1920年英国人罗素来中国讲学,对中国人性格气质的形成和独特的生活观念等作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驳斥西方人所宣扬的西方民族“优等”,中华民族“劣等”的言说,十分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伟力,以及无以伦比的民族凝聚力。在他看来,中西方人的差异根源于各自文明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办事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等。但是,罗素相信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使双方都能获益,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质,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日本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国民性是什么样的呢?下面从《中国国民性论》一书中的三篇文章进行对比分析。这三篇文章都完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者们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学识出发,以丰富的在华生活经验和扎实的汉学功底,在介绍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同时,深入剖析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民族心理。内山完造认为中日两国人民不同的大部分原因是由各自国家的环境造成的,他总结出的中国人特征有:重同乡、富于人情味的买卖、尊重生存权、节俭、相互扶持、大家族制度、因人定价、埋头于实际生活等。渡边秀芳则总结出中国人所具有的八种民族性,即重天命、重孝道、文弱、实利性、保守、趣味性、矛盾性。原惣兵卫认为当时的中国充满着许多因袭的固陋性,是与近代精神绝不相容的,他所总结的中国国民性特征有:天命观,非科学性的演绎的逻辑,归纳逻辑的缺乏与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与变态心理,大家族制,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与保守性,面子等。更进一步,他认为由于中国缺乏国家观念,违背条约与不守条约是家常便饭;中国人利用口舌欺诈来迁延外交;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转嫁责任的天才;中国民族的性质是贪婪的,因而中日的外交也复杂困难。
综上可见,“他者”因国别、身份、视角、观念的不同,而产生了对中国国民性不同的判断,有正面积极的内容,也有消极的内容;有的是依照自己的看法而对中国人进行定性,有的则是只凭研究文章而了解的中国人形象,有的是生活中真实的中国人形象。有时即使面对同一中国人的特性,不同的作者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尽管这些描述都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框架基础上,缺乏严格的概念界定,并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描述对于我们认识自身不失为一种参考。
(三)需要何种教育以改造中国的民族性
在教育对国民性的作用上,大家纷纷献策。根据不同的立足点和视角,大致观点有以下几种。
庄泽宣认为,教育为民族生活遗传与改良之工具,教育对民族性之功能仅止于消极的逐渐改良,而不能达于积极的根本改造,国人过去对于教育救国之失望,盖由于重视教育“万能之说”,而未认清其力量与使命也。因之我国今后教育采取之方针:一在思想方面应注意“人本的教育”;二在设施方面应注重“人才的选拔”。①庄泽宣,陈学恂:《民族性与教育》,《图书季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有的主要谈小学教育对国民性的作用。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小学教育当养成自信之国民性。为此要做到训育学生,寓罚于赏,以及教学当以本能为体,书本为用;二是小学教育当养成进取之国民性,对于学生之长要因势导之,同时实行分组比赛以促进取;三是小学教育当养成乐群之国民性,小学教育应组织并奖励学生团体;四是小学教育当养成博爱之国民性,要做到残酷之行不入学生之目,残酷之言不入于耳,促进学生间之互相劝勉。同时,这四点是相辅相成的,惟自信而后进取,进取之后必乐群,乐群而后可言博爱。②《国民性与小学教育》,《湖南教育》1928年第4期。
有的根据教育部九月整理全国教育的说明,即“中国民族复兴,必有待于教育者有二:一为养成国民之民族观念,一为回复国民之民族自信力”,而提出教育上的三点相应措施:(甲)课程上注重本国历史文化教育以改造民族性;(乙)注重本国历史教学培养正当的国家观念;(丙)养成不虚伪不夸大专尚实际的历史精神。①《改造民族性与发展历史文化教育》,《建国月刊》1933年第9卷第4期。
有的根据现代社会的需求,针对中国目前情形所表现出来的偏于安土重迁的保守性和自私自利的独存性,而提出中国教育改造的中心在如何发展民族性中的进取性和互助性。发展进取的体力需要注意儿童的养护事宜,要对青年进行严格的童子军训练和军事训练,培养进取精神须注意胆识的培养和劳苦的锻炼。互助的观念和习惯的养成则需要从培养协作的、纪律的、牺牲的、以及民族的观念和习惯着手。②陈科美:《中国教育改造与中华民族性》,《中华教育界》1934年第21卷第7期。
有的从人的身心素质培养出发,认为我国的民族性必须全部改造,方法主要是优生、优育、和优化。用教育的力量传播优生知识并将其化为信仰,重视儿童特质的改善,以及心灵上坚韧性、创造性、诚毅性、社会性的扩充和改善。③陈科美:《教育与民族性》,《福建教育》1940年第1卷第2期。
还有的则通过回顾民国前后的教育思潮,认为民国以后的一切教育思潮,多重文字宣传,而忽视实验结果;多重理论探讨,而漠视实际行动,多重欧美新制的移植,而不顾国内客观的条件。最大的毛病在各种教育运动缺乏联络与统一性,大家都忘却国家教育的总目标与中华民族的运命。因而,作者主张现在中国教育的出路应该“回到二张的政策”,即中国近三十年来中国一切教育思潮的两位创动者,最伟大的“教育政治家”——张之洞和张百熙那样,用教育作为改造中华民族性的工具。因此,为达到这个目标,作者认为中国教育至少应有三个改革:首先,为铲除自私的根性起见,今后的教育应是“国家本位”的教育,而不是以往“家庭本位”的教育;其次,为铲除文弱的根性起见,今后的教育应是“军事化”的教育,不是过去“女性化”的教育;再次,为铲除虚伪的劣根性起见,今后的教育应是“生产化”的教育,而不是过去贵族化的教育。同时,作者对每一个改革的具体措施,从教育行政、学校行政、课程、教学法、课外活动、以及训育等方面都给予了细致的指导,并且认为,只有这种教育才能铲除华族虚伪的劣根性,只有国家化军事化生产化的教育,才能复兴中华民族。④邱椿:《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前途》1933年第1卷第7期。
为了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从宏观层面的学校制度、文化到微观层面的课程、教法、课外活动,从儿童的身体训练到儿童心灵上的改善,从回顾民国前的教育思潮到展望现代社会的需求等方面,学者们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这是教育史上浓重的一笔,为今日之教育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三、启示
(一)国民性:是臆想也是事实
国民性问题是个跨世纪的话题,自晚清至今一百多年间,国民性情结一直萦绕在国人的脑中,忽明忽暗,挥散不去。关于国民性的讨论至今仍是倍受瞩目和争议,周宁、摩罗等学者力图论证中国国民性是一个西来的殖民话语,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一种想象的建构,之后又被国人认同的一种思维模式。无论是哪一种关于国民性特征的概括都无法说服他人,因为其所总结出的中国人的特征的适用范围又有多大?若有一个人不适,岂不是证伪了此国民性特征?究竟国民性是真实,还是幻象?
其实,针对传教士斯密士关于中国国民性的言说,邱椿早在1933年就批评道,“现有的关于中华民族性的资料,多无科学价值。外国旅行家的记载,传教师的叙述,因观察欠精细,胸怀成见或别有作用,当然不甚可靠。”⑤邱椿:《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前途》1933年第1卷第7期。书丹在1941年也谈到,“一个生活习惯根本不同的外国人在中国住上很短的期间,便来乱谈中国人的特性,真是等于盲人说象,因此流于肤浅错误以至自相矛盾而不自知,是不可以不辩。”⑥书丹:《盲人说象的中国民族性谈》,《世界文化》1941年第3卷第1-2辑。可见,谈论国民性,就像举起一面镜子照自己,在镜子里的可以是真实的形象,也可以是经过粉饰的形象,无论是国人自己还是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准确总结出中国人的形象,也不可能用一些词或者描述概括全部中国人这个整体。因此,众多对于国民性的论述,有事实,也有臆断。面对同一个中国,既然我们无法企及真实的中国国民性,那么从多个角度去窥探,至少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于真实。
早期学者们对于国民性的讨论功不可没,然而现在我国的国情较之以前已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也应与时俱进,而不是不喑时事地大肆夸张宣传,或随意否定贬斥。在理论上走入极端,或在心理上不敢直面事实,两者都不可取。为此,我们要在早期国民性批判的基础上取精华,去糟粕,对国民性进行理性的判断,摆脱那些只是对于国民性表象特征的描述,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本质。对国民性的批判保持向外批判和向内自省的两个维度,以保证批判的有效性和价值。另外,批判也不等于全否,批判的最终目的是重构,因而对于国民性更应多提倡良性的、有建设性的批评,而不是将其摧毁成无数的碎片和废墟。将一切人类正面价值都赋予一个民族的性格,这当然很好,却没有多大意义。只有正视这种负面性,才是一个民族所应当有的反思能力的体现。
(二)改造国民性不等于改造人性
国民性与民族性是涵义相近的概念,即一国民众共同的性格特质,是在一国或民族特殊的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独有的特性,是国家之间相互区分的标志。而人性是人之为人的特有属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总和。人只要存在就必然具有这些特性,如孟子的“食色性也”等。因此,全人类有相通的、普遍的人性,正如休谟所说的那样,“人类在一切时间和地方都是十分相仿的,所以历史在这个特殊方面(人性方面)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新奇的事情。历史的主要功用只在于给我们发现出人性中恒常的普遍的原则来”。①姜国柱,朱葵菊:《中国人性论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0页。在一定程度上,国民性可以被看做是人性的特殊化,国民性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改变而产生变化。
那国民性有无优劣之分?其实这样的一种问法的背后隐含着二元对立的前提,即将西方与中国国民性置于一种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对立中。当我们从文化视角对国民性进行的解释,演变成了一种天生的“素质决定论”或者“人种决定论”的时候,这会引起更多的误解。正像罗廷光所言的那样,“凡谓为国民根性者本无优劣可言,正犹如个人气质难有冷热浮沈之别,而不得评以善恶也。”②余箴:《国民性与教育》,《教育杂志》1912年第5卷第3期。他还以我国国民“实用”的特征举例,一方面“实用”可以让我们远离空想和玄谈,养成勤勉、俭朴的好习惯,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限于因袭性而不求其所以然,让我们变得急功近利而限于极端利己主义。因此,所谓国民性优与劣的转换就在一念之间,取决于论述者的立场和态度。他还强调,“否则人们每喜冒昧下笼统的断语,强分国家的种类,这国和那国的不同,像是天生成功两样。致使国际间发生种种误会,多少悲剧,即从此时产生出来!”③罗廷光:《英法德美意俄的国民性与教育》,《教育杂志》1934年第24卷第4期。所以,强分国民性的优劣,将改造国民性上升为改造人性,这都不可取,对于国民性的审视都应还原到本土的语境中进行。
任何一国的国民性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对于中国国民性要有一个基本的认可和信任,即人类所具有的普世价值,中国人也有,而人性中的阴暗面,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国民性批判不仅是中国人应做的事情,而且是各国人都该做的事情。改造国民性也不是根治人性之恶,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君子,这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君子国的故事”已经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国民性不是与生俱来、完美无缺的东西,受后天文化环境因素影响较大,因而对于中国国民性我们不能贬低,因为这是我们自我进取的源泉之一,同时也不能天真的认为改造国民性成功就一切万事大吉。
(三)教育对国民性的改造是有限度的
现在人们一谈及国民性与教育问题,很容易就能列出很多条举措,希望通过教育的作用养成良好之国民,但是,愿望与现实之间是永远存在一定的距离。国民性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对国民性的改造也注定多是精神层面的改革,而精神作用的发挥还需要制度力量的强大支撑,因而,国民性的成功改造需要整个社会的力量,教育之于国民性的改造,只是其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不能像当年荆有麟所认为的那样,以为“国民性不改革,无论什么事也作不出来”。①荆有麟:《改革国民性与救国》,《京报副刊》1925年第356期。在我国重视社会文化建设的今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都要抓,单靠任何一方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更何谈促进中国的发展。
换言之,教育必须首先顺应国民性的自然,然后才能对其进行引导和改正。教育者的作用就在于“必反省其国民性而导之于有益之方向,譬诸个人气质,不能由教育而变化,然察其气质所偏而利用之,则教育所有事也。”②余箴:《国民性与教育》,《教育杂志》1912年第5卷第3期。1933年邱椿就谈到,“能影响民族性的原素极多,如气候,物产,自然环境,经济制度,交通方法,人口密度,社会制度,民族血统,文化等,教育不过许多原素中之一。假若要改造中华民族性,应努力改革上述种种原素,教育的革新不过是改造民族性的许多工具之一。教育不是万能的,教育的功能当然为其他原素所限制。”③邱椿:《教育与中华民族性之改造》,《前途》1933年第1卷第7期。
因而,教育只是改造国民性的众多途径中的一种,不可夸大教育的作用,否则会走向“教育万能论”,但也不能忽视教育的作用,而陷入极端的“教育无用论”。我们应该在这两者中保持平衡,“要使国民自觉到将来的目标和民心的祈向,同时须要断行教育方针的变革,政治组织的改革,法律制度的革新,经济制度的改造这几椿大事。”④邹敬芳:《东西国民性及其社会思想》,《东方杂志》1926年第23卷第11期。我们应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制度的整体改进中,充分发挥教育对国民性引领和指导的积极作用,促进我国国民性不断的优良改进。然后在此基础上,来建设新文化和新思想,这确是我们国民的使命。
总之,改造国民性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单从教育着手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社会各方的齐心协力;改造国民性也不可一蹴而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改造国民性也不应仅仅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更应深入到实际层面,从一点一滴做起,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The origin,develop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research on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
GUO Ruiyi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early literature,we have discovered that national character ismisused with nationality to some extent,but distinguished from sociality and human nature.Research on modern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 resulted from mainly the traditional link between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haracter,the combination of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invasion,and the influence of other countries.The early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through single comparison, multinational comparison,and the standpoint of other countries,and proposed concrete measures on how to transform national character by education.The main implications are:national character is both a fact and a fantasy;trans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 is not equal to transforming human nature;education is lim ited in transforming national character.
modern;education;national character;human nature
G529
A
1009-9530(2014)04-0115-08
2014-02-28
郭瑞迎(1987-),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