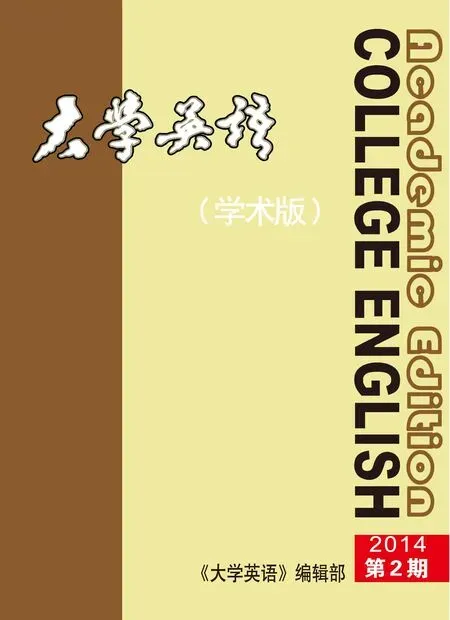《四次会见》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王银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四次会见》是亨利·詹姆斯早期的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1877年11月的《斯格里伯纳月刊》,1879年与《戴茜·米勒》和《一个国际故事》一起以《〈戴茜·米勒:一份研究〉和其他故事》为名,由麦克米伦公司在英国出版。1909年收入詹姆斯晚年重新修订的纽约版全集。
小说讲述了来自新英格兰乡间北维罗纳的一名乡村女教师卡罗琳·斯宾塞小姐对欧洲文化倾慕而最终未能善终的故事。身为乡村教师,斯宾塞小姐具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因而对作为美国文学母国的欧洲充满了神圣的向往。她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到欧洲作一次深度旅游。乡村教师的菲薄收入使她的梦想不易实现,但经过长时间的省吃俭用,她终于攒够了一次旅行所需的费用,开始了她的朝圣之旅。在法国港口小镇勒阿弗尔登陆之后,她遇到了前来接待的以学习艺术为名已在欧洲逗留很长时间的堂兄。堂兄编了一个贫穷小子和贵族小姐的悲惨爱情故事骗过了斯宾塞小姐,激起她的同情心,使得她心甘情愿地奉上她所有的旅费,只在欧洲呆了仅仅十三个小时之后,就启程返回了美国。后来,又在家乡供养了在欧洲无法生存的她堂兄的妻子,一位假冒伯爵夫人的法国女人,再也无力再次完成自己前往欧洲的梦想,不久郁郁而终。
这部小说是詹姆斯早期众多国际主题小说中的一部。詹姆斯研究专家帕沃尔斯认为是“詹姆斯最早最巧妙的国际题材小说之一,是描述被剥夺痛苦的完美之作”(Powers1979:39)。我国学者王跃洪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小说描述的是“年轻美国的‘天真’与古老欧洲‘世故’的冲突”(王跃洪2001:86)。斯宾塞小姐的悲剧在表面看来是因为她涉世不深、过于纯真,未能识破她表兄和假冒法国伯爵夫人的狡诈把戏所导致的,而事实上是一种文化霸权,是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时的失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本文拟采用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来解读斯宾塞小姐的悲剧原因,以及由此取得的相关启示。
后殖民主义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的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朱立元2010:414)。赛义德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自觉与成熟,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则进一步拓展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阐释了文化控制与知识权力的关系。赛义德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指出了文化不对等的原因,是因为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进行单向的输出与同化,通过权力话语,对弱势文化群体的文化身份和历史进行建构,使弱势文化成为失语和沉默的“他者”,由于无法体现和表述自己的主体性和文化意识,弱势文化只好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强势文化,成为文化上的被殖民者。二是指明了消除文化误读的正读是要超越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朱立元2010:417)。本文主要根据赛义德的这两个观点来分析斯宾塞的悲剧以及由此获得的启示。
一、悲剧的原因:弱势文化的失语
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逢南北战争之后社会政治经济的剧变时期。南北战争的本质是“工业和农业之争”。北方的胜利标志着延续两百多年的农业美国的分崩离析,工业美国则在废墟上蒸蒸日上。铁路的快速铺设,人口的迅速流动,使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阶层都产生了剧变。工业资本主义信奉简单的个人主义,对利益的追逐冲击着美国传统的清教道德观和价值观。这是是马克·吐温称之为“镀金时代”的年代,表面的物质繁荣无法隐藏内在的丑陋与空虚。
在政治上已独立一百余年,在经济上已有飞速发展的美国,在文化审美上却依然欠缺。詹姆斯在《霍桑传》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来描绘美国当时的文化欠缺:“没有君主,没有宫廷,没有个人忠诚,没有贵族,没有教学,没有牧师,没有军队,没有外交部,没有乡绅,没有宫殿,没有城堡,没有庄园,没有古老的乡间宅地,没有牧师住所,没有茅草屋顶的村舍,没有长满常春藤的废墟,没有大教堂,没有修道院,没有小型的诺曼底式教堂;没有名牌大学,没有公立学校),没有牛津,没有伊顿公学,没有哈罗公学,没有文学,没有小说,没有博物馆,没有美景,没有政治团体,没有娱乐阶层,没有埃普索姆的跑马场,也没有埃斯考特赛马场!”(James1909:43)当时的美国,除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中心,如费城、波士顿等有一些美国本土的杂志报纸外,民众阅读的大部分文学艺术作品都来自于英国。 “表面上,文字只是写作的文字,好像看不到社会政治控制,其实,它与欲望和权力有着很深的联系”(朱立元2001:422)。文学艺术作品的内涵的从来都与社会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文化输出的良好载体。在政治经济上已独立的美国,在精神文化上依然接受并仰赖于原来宗主国的文化。那个时代的欧洲,尚未经历战争的摧残,正处于最后的黄金时期,散发着数千年文明积淀下的浪漫气息。前往欧洲朝圣,成为那个年代受过教育的美国人的必修课(Zabel1979:486)。朝圣者们试图在文化起源的旧世界里,寻找灵感和启示,而新大陆的新富阶层们则纷纷携家带眷前往欧洲游历,将之看成是攀附高雅文化的镀金之旅。因此,相对于具有审美厚度的欧洲文化,当时尚未形成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美国文化是弱势文化,而欧洲文化是强势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卡罗琳·斯宾塞这样一个被强势文化同化并失语的典型例子。
卡罗琳·斯宾塞是新英格兰的一位乡村教师。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她也大量地阅读,但她阅读的多是欧洲的书籍与作品。比如她不仅阅读拜伦,也阅读欧洲历史,欧洲旅游指南,游记以及等等其他的东西,因此她了解欧洲的很多事情。(James1979:47)作为欧洲强势文化输出载体的这些书籍作品,改变了斯宾塞的价值观,让她觉得她从小身处的新英格兰乡间浓郁的刻板严肃的清教氛围是死气沉沉的,而开始认同迷恋书中描绘的欧洲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在她周围的同伴们只对有人物的照片感兴趣时,只有她对纯粹的风景照展现浓郁的兴趣。前往欧洲一游变成她的梦想。她的朋友评价如果她不能出海远航至欧洲,她会发疯的。(James1979:46)乡村教师微薄的收入,使得她的梦想实现不易,但她以坚忍的毅力,省吃俭用终于在数年后攒够了前往欧洲的旅费。在前往欧洲的汽船上,与大部分晕船躺在床上的女性不同,她坚持坐在甲板上,注目远方,因为梦想即将实现而精力旺盛。
斯宾塞对欧洲文化的迷恋,对本土生活的不耐,使得她不能分辨欧洲这个强势文化中良莠不齐的两面。在登陆欧洲,异域的风情挟带恶意扑面而来时,她发不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只能束手就擒。她是在勒阿弗尔登陆的。这个只是充当旅游中转站的港口小镇,在她看来已是如诗如画之处,路边小咖啡馆的咖啡也比北维罗纳美味。当她的堂兄抛出能被有经验者一眼识破的骗局,理所当然地拿走她所有的旅费,并大饱口腹之欲时,虽然她自己梦想的失落让她痛苦不堪,但她却未兴起一丁点反抗和拒绝的念头,因为“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旧世界的浪漫史!”(James1979:61)这样一对因门第遭到迫害的恋人向她求助,使得她也成为了这样一个书中故事的一部分,参与感使得她心甘情愿地奉送了自己的积蓄,在踏上欧洲的土地仅仅13个小时之后,就启程返回了美国,并终生未能重返。
五年以后当斯宾塞的堂兄去世,她那位假冒伯爵夫人,事实上可能是落魄厨娘和美发师老婆的法国堂嫂,远赴新英格兰,受她供养,并以不善体力劳动为由,视斯宾塞为她的侍女。虽然斯宾塞痛苦万分,抑郁不乐,却认为这样一位经受苦难的“高贵人物”,虽然给她的生活带来了重担,却至少也让她可以日日看到属于欧洲的一些东西。就像伯爵夫人那位没有头脑的学生,新英格兰乡绅米斯特先生一样,仰望着这来自欧洲“高雅文明”的代表。
二、悲剧的启示:强弱文化的交流对话
因为面对强势文化的失语,使得斯宾塞无法分辨好坏善恶,盲从一切来自欧洲的文化而导致了自己的悲剧。这样一个悲剧给我们的启示并不仅仅是坚持对强势文化的批判,建立若弱势文化的自我认同,而是要避免非此即彼的另一种极端。赛义德认为理想的文化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并生,交流对话的文化状态(朱立元2001:417)。这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文化观与詹姆斯本人的世界主义观点类似。詹姆斯认为要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必须要经历足够多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直到有一天发现,不管是哪种文化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这才标志着你已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
小说中的叙述者“我”来自纽约,在欧洲旅居多年。在切实欣赏欧洲文明灿烂的一面,并推荐斯宾塞一定前往欧洲的同时,也能迅速辨别古老文明中阴暗诡诈的那一面。在第二次在勒阿弗尔的小咖啡馆偶遇斯宾塞时,一听斯宾塞的堂兄拿了她的旅行支票前往兑换时,立刻明白了事情的不妙。他试图阻止却未能成功。在斯宾塞的院子里一看到那位伯爵夫人,他就认出了她的真实身份,而囿于对斯宾塞小姐的恻隐之心,并未道破实情。同时,“我”也能发现被斯宾塞无视的美国文化的优劣两面。固然地处新英格兰腹地的北维罗纳冬日寒冷,积雪及膝,小镇建筑风格怪异,但斯宾塞建了木棚,还有两只咯咯叫的母鸡的小院子,虽然简朴却可爱,“褪色的印花棉布,古老的金属雕版画,以浸润过的秋日落叶为框,流溢出一种动人的典雅。”(James1979:68)
这样两种文化交融和对话的理想,詹姆斯在斯宾塞身上做了隐喻。斯宾塞被描绘为欧洲文化的仰慕者,她的发型类似她从未亲眼目睹的希腊女性半身像的发型。(James1979:42)但小说叙述者“我”在描绘对斯宾塞的印象时,将她比喻为“一支茎秆细长,色彩柔和的清教之花”(James1979:51)。叙述者的姐夫则点评斯宾塞是一位“亲切的扬基小妇人”(James1979:50)。斯宾塞身上有着深刻典型的清教烙印。她的受骗主要在于对欧洲文化的失语,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清教守望相助的道德因素在起作用。这样一支清教之花,当她处于对欧洲光彩灿烂的文明的热切向往中时,虽然两次见面间隔了三年,她却“一如既往的端庄美丽”。而在相隔五年后的最后一次见面,日日与代表欧洲文明丑恶一面的假冒伯爵夫人相处之后,斯宾塞却看上去像 “老了十岁”(James 1979:68)。可以说,当代表美国文化优秀一面的道德与代表欧洲文明光明一面的审美相遇时,使斯宾塞荣光焕发,而当与丑陋相对时,则极速衰老。因此,詹姆斯通过斯宾塞的悲剧给出的启示是两种文化优良面的交流和对话才是有益于文化的整体发展的。
三、结语
詹姆斯在一百多年前描绘的强弱式文化相遇,弱势文化失语造成的悲剧以及由此带来的启示,在今天这个文化多元交融的时代,依然不无启发意义。建立本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同时不忘自省,并能对他文化明辨是非,才能降低文化冲击,提高对多元文化的适应性。
James, H. (1909). Hawthorne [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Powers, H. L. (1979). Editor’s Note to Three Tales. In D. Morton Zabel (ed.) The Portable Henry James [M]. Kingsport:Kingsport Press.
Zabel, D. M. (ed.) (1979). The Portable Henry James [M]. Kingsport: Kingsport Press.
王跃洪(2001).情景·人物·结构——评亨利·詹姆斯的《四次会见》[J].外语教学(4)。
朱立元主编(2010).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