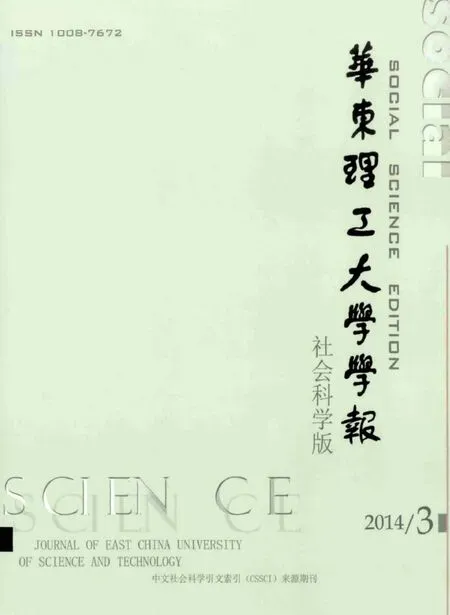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能力的一项历史分析
——以陕甘宁政权建设为研究个案
李 冉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上海 200433)
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是2012年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首次指出的,十八大报告又做了强调。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作为一种政党品质,它伴行了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是党历经危难并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即是说,在学理层面尚需对这个新话题做出更为清晰的理论阐释,在历史层面不乏有党自我革新的史实印证。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通过对历史实践的个案分析,为当下的理论研究提供些许支撑,这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问题意识。基于此,本文以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为研究个案,对中国共产党从中体现出来的自我革新能力做个历史分析,以期对当下的执政党自我革新提供一些历史经验上的启示。
引言:研究个案的选取依据及其时限界定
列宁曾经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自我革新能力较为突出地体现在政权建设方面。在近二十个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是唯一经历过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的根据地,边区的政权形态最为丰富也最为典型。因此,有理由把陕甘宁政权建设作为研读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能力的一个经典案例。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其政权建设能力就在逐步累积。①比如,1925年中国共产党在西北成立了第一个基层组织--西安特支,这标志着党的政权创建正式开始;1927年12月广州起义中组建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广州革命政府;1928年5月共产党人策动渭华起义,建立了第一个地方性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到了陕甘宁边区,党的政权建设能力得到了集中锻炼与释放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意愿来看,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其他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根据地建设的“样板”,因而把边区政权首先建设好,就构成了中央高度重视边区建设的主观动因。从历史基础来说,边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的组织比较健全,政权建设的经验比较丰富。从地理位置上说,边区横跨西北三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东南部),地形复杂,适于集中建设政权。从时局上说,边区政府最早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从而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建设环境。,为1949年全国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历练③章开沅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对比。他指出,辛亥革命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的新政权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夭折了,这固然有客观的和主观的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革命党在匆忙执政之前并未做好起码的执政准备。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并建立新政权之前,就有了极为充分而全面的准备。这种准备就包括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所积累的能力、经验与人才储备。参见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序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毛泽东就曾指出:“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可以说,陕甘宁边区堪称党局部政权建设的示范区、新中国政权建设的试验田。在这块试验田中,中国共产党关于政权建设的试验是最为复杂也是最为成功的: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不仅在各自时期引领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而且对接平稳过渡有序。此外,作为“革命的根本问题”,边区政权建设也反映了党在应对时政大局方面的自我革新能力,比如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关系处理,国共两党基于战争形势的分合策略,支援战争与改善民生之间的政策倾斜,战争动员与阶级关系的适时调整,等等。总之,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沿革,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方面的自我革新能力,也体现了在应对时局方面的自我革新能力,这正是本文选择边区政权建设为研究个案的依据所在。
此外,为了对研究对象有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本文还需对“陕甘宁边区”的时限加以界定。在学术研究中,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时限主要有三种理解。其一,广义时限。有学者认为,陕甘宁边区“泛指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几个历史时期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⑤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政权建设史》前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这是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做出的历史划分。在广义理解中,陕甘宁边区的历史跨越最长,从1928年5月西北渭华起义中创建的西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到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撤销。这样算来,陕甘宁边区“经历了二十二年的漫长岁月”⑥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其二,中义时限。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陕甘宁边区就是指1937年2月西北根据地改制⑦193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正式着手西北根据地改制为陕甘宁边区的工作,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9月6日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通令,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后统称为陕甘宁特区政府”。1938年春天边区政府下令,又将陕甘宁特区恢复为陕甘宁边区。到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被撤销的十三年,这是从政权建制的角度来划断的。其三,狭义时限,指的是与统战区相对的陕甘宁边区,这种理解是从陕甘宁边区的管辖范围来说的。从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到1940年9月完全统一政制与政令,狭义上的陕甘宁边区历时3年。⑧经过1937年2月至9月国共两党的多次谈判,国民政府终于承认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合法性,并直属南京中央政府。但是,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明确陕甘宁边区的管辖范围。如此一来,在边区的十几个县中,就出现了两种政权的局面:一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即狭义上的陕甘宁边区),另一种是由国民政府陕甘宁三省委派的地方政权(即边区内的统一战线区)。这两个政权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及其利益。“这种双重政权局面的存在,不仅使边区在行政上的不统一,而且造成政令上的不一致。”(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直到1940年9月,中共中央才以“边区化”为手段将统一战线区彻底改造成为“新区”,自此以后,陕甘宁边区的政制与政令才得到了完全的统一。
对于陕甘宁边区的时限问题,本文采用中义时限,并略做调整。原因是,广义时限涉及的内容繁多,它适合著作的选题,而在一篇文章中难以把问题讲得简洁明晰。狭义时限虽然更具有学理性,但若拘泥于此又难以把“自我革新”这个颇具宏观色彩的题目讲清楚。中义时限虽然有着明确的历史时段与研究对象,但是从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这之间有个明显的过渡时段,因而问题也就有延伸性。基于此,本文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研究时段从1937年2月上溯至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提出了全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由此开启了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过渡的战略大幕。简言之,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35年12月至1950年1月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
一、建设模范政权:自我革新的主观动力
一个政党是否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这固然是个实践问题,但是首先还是要看这个政党是否有自我革新的主观意愿,一个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政党自然也就谈不上自我革新。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一个崇高追求,这种使命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不断自我革新的主观动因。
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改制伊始,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就明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被问到“边区的意义和作用”时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这种制度要全国采用,……所以我们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来看的人也不少,青年学生尤多,除了少数人说这种制度不好之外,大多数人都说是好的,这是可以引以为幸的事。”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159页。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指出:“边区在全中国说来,是个政治上先进的地区。……边区实在是一个模范的抗日根据地。”③林伯渠:《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1938年10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在全国起模范与推动的作用。”1940年3月4日,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上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1944年12月林伯渠又指出,边区政府要“建设出一个很好的地方,协同整个中国解放区,为全中国人民作出榜样”⑤同③,第459页。。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还提出了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自治省区”的口号,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作为建设“模范自治省区”的基本法则。纵观陕甘宁边区政治文献以及中共领袖的论述,要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政权的观点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所限笔者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所谓“模范”必是基于比较。边区时期,党对模范政权的定位,是基于两个层面上的比较。进而说,边区政权的模范价值是在两个层面上体现出来的。第一,对于其他根据地和解放区而言,边区政权应该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模范。任弼时曾经指出:“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说来,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⑥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对于边区在所有根据地中的“领袖地位”与模范作用,毛泽东甚至用“英国伦敦”⑦1942年9月,李维汉即将调任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府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在枣园谈话时指出:“罗迈(即李维汉,笔者注),延安好比英国的伦敦。”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中写道:“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伦敦是英国的首都,它的政策影响着英国的众多的殖民地。我们当时也有很多根据地,根据地当然不是殖民地,但需要一个‘首都’作为政策中心,则是一样的。毛泽东是要求陕甘宁边区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页。的类比加以强调。第二,对于国统区乃至全国而言,边区应该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模范。对此任弼时又指出:“陕甘宁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就是说,边区每一个政策的实施,国内外的人士,国民党,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都可以把它看成为我党中央的设施,并根据它来判断我党的动态……边区的每一进步政策,不仅可以使大后方的人民‘心响(此处应为“向”,笔者注)往之’,而且也未尝不可提供我们的友党参考。”①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由上观之,中国共产党通过赋予陕甘宁政权模范与榜样的价值定位,形成了革故鼎新、追求进步的政权意识。这种政权意识既是自我革新政党品质形成的动因,也是政党自我革新能力在观念上的一种体现。
二、服务革命事业:自我革新的方向驾驭
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始终有个鲜明的指向,那就是服务于革命大局。这就把党的自我革新与中国革命的规律结合起来了,以革命的方向校正自我革新的方向,确保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不会偏离历史航道,不会成为“自我折腾”式的革新。
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政权很重要,它是革命的核心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问题的基本立场。第二,革命的特点与进程往往决定着政权建设的特点与进程,对于革命与政权之间的这种“决定关系”,中共在边区政权建设过程中把握地十分准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陕甘宁政权建设反映了中国革命“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③斯大林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对这个观点,毛泽东完全赞同,并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做了强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的规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这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由此说,武装斗争的成败决定着政权建设的成败④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3页。),政权建设要在根本上服务于武装斗争的开展。这也决定了边区政权建设的两个特点。首先,边区的政权建设要围绕着军队建设而展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该有强大的军队。”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中国革命的成功要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军队建设也就成为了边区政权建设的核心工作。从工农红军到八路军再到人民解放军,这三支革命军队的锻造始终贯穿着边区政权建设的主线。其次,边区的政权建设还要围绕武装斗争的保障而展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和目的是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在革命战斗年代,政权建设必须围绕革命战争而进行,为着争取尽可能的物质条件,去保障革命军队的给养和供给,实现革命战争的胜利。”⑥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1页。边区的土地改革是这个目的,边区的经济发展是这个目的,边区的民主建设亦是这个目的⑦比如,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在阐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指出:“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这一切(即民主制度的实行,笔者注)都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第159页。,这也就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二,陕甘宁政权建设反映了中国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规律。从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再到人民民主政权,陕甘宁边区是各根据地中唯一完整经历过这三种政权形态的根据地。尤其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面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完成了向人民民主政权的转变。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边区政权从老区边区政权发展到西北大区政权,从农村政权发展到城市政权,这个过程全面地反映了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早在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就曾指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共产党对边区政权建设的筹划与整个中国革命道路的演进逻辑是一致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武装夺取政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与中国革命特有的道路相适应的,也是一个政权建设的独特发展模式,这就是……由小块到大片,由农村到城市,由地方到全国的政权发展道路”。②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政权建设史》前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权建设中的自我革新始终是以政党承载的使命为参照的。以正确的历史方向为坐标,党的自我革新才能发挥“正能量”,倘若没有正确方向的引领,政党的自我革新就未必是好事了。
三、注重改善民生:自我革新的民意基础
自古以来,当政者的自我革新不胜枚举,而脱离民众支持最终沦为当政者一厢情愿式的自我革新也是屡见不鲜。如何将当政者的自我革新与民众的支持结合起来,这是改革者需要理顺的大事件。进一步来说,当政者的自我革新能否为民众所接受,这往往取决于民众能否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那些罔顾民众利益的“自我革新”,要么是当政者孤芳自赏,要么是当政者欺世盗名,是终究要被民众所抛弃的。易劳逸教授在研究了1937-1949年的国民党后指出,国民党被打败的真正原因是“背弃了民生主义”④[美]易劳逸:《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王建朗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相反,“边区是实施三民主义最为彻底的地方”⑤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的题词,《陕甘宁边区实录》扉页,解放出版社1939年版。转引自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大力改善民生,先是在苏维埃政权中实行“扶助农工”的政策,后又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⑥当然这里的“三民主义”不是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改造过的三民主义,而是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边区生活的改善极大地增进了人民对共产党政权的拥护和支持。在边区的三种政权形态中,抗日民主政权时间最长,民生建设也最为典型,笔者就以抗日民主政权为例来谈谈边区的民生建设。
1937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标志着苏维埃政权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这次会议上,党作出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并对新形势下的民生工作做了定调,“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⑦《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页。这个定调大体上反映了整个抗日民主政权时期党对民生工作的基本态度,即边区的民生工作还是为着战争而服务的。⑧对此,有人认为,这种民生观是功利的,但毛泽东却认为,我们就是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同时,这种“功利”也成为了党认真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推动力,从战争成败与民族危亡的高度强调民生建设,这是边区民生得到极大改善的政治原因。如此以来,民生工作便有了两个看似矛盾的价值指向,一是修养民力改善民生,二是保障供给服务战争。如何在两者之间实现有机平衡,这是诠释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分屯田的机会,那么,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页。这段论述大体反映了边区时期休养民力与供给战争侧重点的变化轨迹,同时也说明,一九四三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改善民生的策略做出了重要调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边区来自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压力明显减少。同时,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阻断了日军与边区的直接接触,并成为保卫边区的屏障。由此,陕甘宁边区获得了难得而短暂的军事安宁,边区政府抓住有利时机休养民力。②比如,减少农民缴纳公粮数量,取消苛捐杂税,以保证农民对已得土地的利益,“1937年至1940年,边区每人公粮负担平均1升多,负担最多的也不超过七升。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42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轻税率。”梁星亮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1页。但是,到了1940年至1942年,边区的战事又骤然加重,休养民力不得不转向服务战争③比如,1941年征缴公粮(即农业税)二十万担,是1940年九万担的两倍多,民众的生活负担显著增加。对此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页。,边区群众的生活陷入困境④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并引发了民意的不满,甚至出现了“雷公打死毛泽东”⑤参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404页。的怨恨情绪。至此,可以看出,战争对民力的消耗是惨烈的,甚至能引发民意的反弹,在休养民力与服务战争之间做二元转化的模式能否真的俘获民意,这是需要反思的。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高度警觉,并在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进行了反思。毛泽东认为,1941年至1942年“虽然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不是极端的困难。”“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那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困难。”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1页。在这里,毛泽东对未来战争之于民力的消耗做出了准确的预判,这也意味着,休养民生寄希望于战事改善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以服务战争为指向的民生改善还需要做出调整。而对这个问题,当时党内还缺乏清醒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对于这个极端的困难,“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⑦直到1942年整风,尤其是在194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这个问题才被全党所重视起来。自此以后,也就是进入毛泽东所说的“第三阶段”,因着政策的调整,改善民生与服务战争相互掣肘的局面才得到了根本改善。
第一,以先予后取的方法,妥善处理战争供给与休养民力的关系。毛泽东在招待边区劳功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⑧同上,第933页。。笔者将这种思路概括为“先予后取”,它有三个基本点,一是把主要精力用于休养民力,二是战争供给的问题会迎刃而解①1943年毛泽东又一次指出:“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三是从国共两党作风的高度唤起全党对这个问题的重视。②对此,毛泽东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4页。
第二,精兵简政,以减少军队与政府消耗的方式摊薄民力负担。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和以往相比,这是边区政府减少自身消耗摊薄民力负担的一个新思路,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③同上,第881页。对于精兵简政之于摊薄民力负担的意义,毛泽东指出:“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④同上,第895页。经过三次精兵精简,1943年延安县动员民力28000多个,大大低于1942年的60000多个,1944年节约粮食15000石。⑤刘景范:《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2页。
第三,军民兼顾,以公私两利的方式辅助民力休养。1942年12月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页。在这里,毛泽东对战争供给的认识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除了以往主要依靠民力供给以外,中央已经对自我供给加以重视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军民兼顾、公私两利来解决“物质困难”的新思想逐渐成型。毛泽东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指出:“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⑦同上,第894-895页。这个思路正确处理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优化了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良性互动,有力地推动了“物质困难”的解决。
第四,减租减息,以少取放活的方法休养民力。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要解决物质的困难,终究还是要靠民力,“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2页。为了调动民众的大生产的积极性,边区政府于1942年冬至1943年春实行了减租减息。首先“清算”1939年减租条例公布以来到1942年未执行减租而多交了的租额;然后根据“清算”结果,确定应退租的数量,并由地主将多收租子如数退给佃户;最后租佃双方,进行“换约”,实行保佃,这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又保障了佃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显著提高。同时,边区又发动了“大生产运动”,放活边区的商业贸易,这些措施都极大地休养了民力、改善了民生。
四、广施民主政治:自我革新的动力支持
陈毅曾经指出:“激荡全中国的民主运动的浪潮,其发源地就是陕甘宁边区。”⑩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7页。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实施的民主建设,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为党的自我革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支持。
第一,民主政治为党的自我革新提供了合法性支持。“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早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⑪苏维埃政权实行苏维埃民主制,工农第一次成为民主的主体,并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为了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把国体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开放了民主,为向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奠定了基础。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
⑪ 梁星亮等主编:《陕甘宁边区史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3页。中全会电》中对边区的民主建设作出了郑重承诺:“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①《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8页。,此后以“三三制”为民主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逐步建立起来,边区的民主建设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抗战胜利前夕,抗日民主政权向人民民主政权的转变被提上议事日程。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情况和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页。。1945年9月边区第三次民主选举正式启动,并将边区参议会改为边区人民代表会,随后老区改选各级政权和新区建立各级政权时,均实行了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从苏维埃政权的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到抗日民主政权的参议会制度,再到人民民主政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边区的民主形式日趋完善,民众的民主权利得到了有效保障,这与封建政权的专制与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形成了鲜明对比,以至一位外国人这样评价:“现在中国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的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的中心,在延安。”③《解放日报》1943年9月30日。转引自李忠全、王振中:《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简述》,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94页。在边区的民主建设中,民众的政治主体地位被确立起来,这激发了民众对于党自我革新的合法性认同,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描述的:“华池有个地主感激地说:‘37年选举,咱们没有选举权,现在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看得起咱们了,又给咱们选举权,咱今后一定要选好人。”④林伯渠:《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所主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4页。
第二,民主政治为党的自我革新提供了智力支持。毛泽东曾经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在与党外人士的民主合作中,党的自我革新获得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比如边区的“精兵简政”。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边区参议员民主人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对此,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⑥同上,第1004页。毛泽东不仅把精兵简政作为克服物质困难的一项根本政策,而且把它作为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基本政策。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把精兵简政作为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最切要”十大政策之一,且名列第二,仅次于“对敌斗争”。随着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发表,李鼎铭这位延安时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闻名党内外,开明绅士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建议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成功典范。
第三,民主监督为党的自我革新提供了纠偏能力。在延安,毛泽东提出了以民主这条新路打破历代统治者兴衰周期率的著名论断,强调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才不会人亡政息。民主监督能为党的自我革新提供一种纠偏的机制。首先,民主监督能防范党和政府工作上的懈怠,正如谢觉哉所指出:“防止官僚主义有效的药剂是发动人民自下而上地批评、监督、控告以至要求罢免(对上级人员)或直接实行罢免(对乡村人员)。”⑦《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0页。其次,民主监督有利于政治廉洁。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公职人员管理制度,比如,《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等,并接受群众的民主监督。林伯渠就曾在边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⑧林伯渠:《林主席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四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63页。再次,民主监督与协商对党的自我革新具有补充与纠正功能。在民主协商方面,既有我们熟悉的“三三制”,也有“非党民主人士座谈会”这一边区民主政治的新形式①参见宋金寿、李忠全主编:《陕甘宁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9-250页。,党的革新政策在民主协商的平台上得以检验、补充甚至是纠正。
余论:自我革新能力的生成要件及其当代启示
自我革新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政党品格,自我革新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政党软实力。九十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每逢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关口都能化险为夷顺利转型,与这种品格及能力是大有相关的。
从陕甘宁政权的历史经验来看,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生成大体需要如下几个条件。其一,存在着强烈的外部刺激,这往往表现为社会的大转型与大动荡,一般社会变迁下还谈不上“革新”。其二,面对强烈的外部刺激,政党凭借“内生性能力”做出应急性反应。无力做出应急性反应也就无所谓“革新”,没有“内生性能力”亦谈不上“自我”革新。其三,政党的应急性反应能够驾驭并最终引领时局的变化,不能引领时代变革甚至落后于时代需求的“自我革新”只能制造更大的政治困局。以上三个环节可以概括为“刺激-应对-超越”,这三个环节的有效轮转是政党自我革新能力得以发挥的关键。
当前,国情世情的变化以及由此对中国共产党构成的“外部刺激”不可不谓之不大,正如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②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中国共产党要在新形势下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就需要在“应对”与“超越”这两个环节上做出努力。在这方面,陕甘宁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为当下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其一,全党上下要凝聚共识,形成追求先进性的政党意识。其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事业的大局,以此来寻找并校正政党自我革新的大方向。其三,通过切实有效的民生改善,为党的自我革新夯实坚实的民意基础。其四,进一步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为党的自我革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