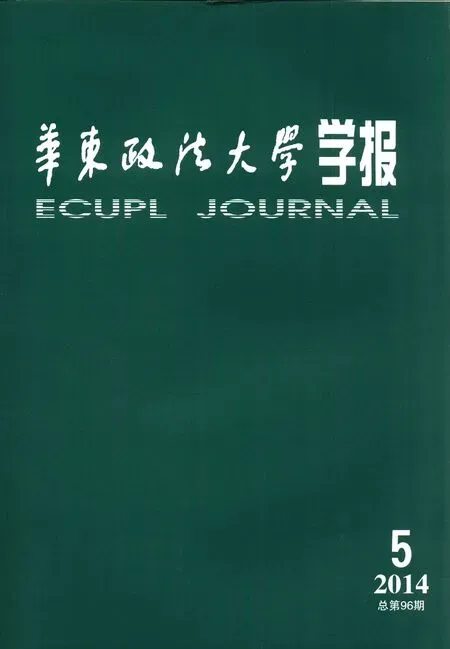何为意思表示?
[德]耶尔格·诺伊尔 著 纪海龙 译
本文主要探讨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除意思表示的外部构成要件,本文也探讨了意思表示之能力上的基本要件、意图上的基本要件和实质上的基本要件。
一、导言
“意思表示”概念,是私法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按照一般性的语言用法,“意思表示”这个词非常笼统地表达了表示人想对生活关系发生影响的意图(“从今天开始我要戒烟了”或“我想和朋友们去看电影”等等)。而该词在法学上的语言用法具有特殊性,其含义比一般性的语言用法更窄,即法学上的意思表示服务于对法律关系的塑造。〔1〕有关意思表示的概念史,详见Schermaier,in:Schmoeckel/Rückert/Zimmermann,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zum BGB,2003,§§116–124 Rdnr.2;Werba,Die Willenserklärung ohne Willen,2005,S.14ff.m.w.Nachw。
意思表示对于表示人而言,是以私人自治方式参与法律交往的媒介;从而,意思表示应同时适于被其他法律主体所了解。〔2〕参见 Bydlinski,JZ 1975,1;Larenz,Allg.Teil,7.Aufl.(1989),S.335。这个双重功能在“意思—表示”这个复合词中得以明显体现;不过也在意思和表示不相一致时,提出了何者具有优先性的问题。就此问题,在《德国民法典》生效之前,就已经燃起了所谓“意思说”和“表示说”之间的著名争论。意思说认为意思表示的正当性基础完全在于意思;而另一端的极端观点即“表示说”仅仅对表示赋予了重要性。〔3〕对于此理论争议详见 Kramer,Grundfragen der vertraglichen Einigung,1972,S.119ff.;Vogenauer,in:Schmoeckel/Rückert/Zimmermann,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zum BGB,2003,§§133,157 Rdnr.34ff.m.umf.Nachw。在《德国民法典》已经对意思瑕疵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具体规定,从而这些规定对相互分歧的理论都予以证伪的意义上,上述意思说和表示说之间的教义学争论已然过时。〔4〕对于法学理论的可谬性详见Canaris,JZ 1993,377(385ff.)。并且,在法律规定层面已经有明确答案的范围内,纯粹的原则性论据——即一方认为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更为重要,另一方认为信赖保护和交易保护更为重要——也已然无关紧要。
从而,下文在可能的范围内,将从现行法(lex lata)中得出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不过,此种方法显然也带来了另一个具有类似结构的问题。由于《德国民法典》中的规范作为集体之自决的表达,也追求其被受众理解和遵行的目的,从而在此立法文件的语境内,也会出现意思和表示存在分歧的问题。
故而,在法律层面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争议,即法律解释学中的“客观说”和“主观说”。〔5〕对此仅需参见 Larenz/Canaris,Methodenlehre,3.Aufl.(1995),S.149ff.;Neuner,Die Rechtsfindung contra legem,2.Aufl.(2005),S.111ff.m.umf.Nachw。虽然人们从这个关于法律概念的争论中,也能够转而得出有助于认识意思表示之意义和目的的结论;不过在此,法学上的理解受制于前理解以及“解释学循环”〔6〕“解释学循环”或“解释学螺旋”这个图景表达的是:只有理解者带着“前理解”或“先见”来触及文本时,他才能将文本表达出来。换言之,只有当他一同进入到理解视域内时,他才能够对他曾将何者预见为“临时”的结果,进行有效的论证;参见Arthur Kaufmann,Rechtsphilosophie,2.Aufl.(1997),S.46 m.w.Nachw。的不可避免性,需引起特别的注意。
二、意思表示的要件
从意思表示这个概念的词语构成上,就可以区分出作为意思表示之构成因素的意思和表示。与此相关,意思表示常常被划分为一个“主观的”和一个“客观的”构成要件。〔7〕例如 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Vorb.§ 116 Rdnr.1;Köhler,Allg.Teil,30.Aufl.(2006),§6 Rdnrn.2f.;Leipold,BGB I,4.Aufl.(2007),Rdnrn.14,17。不过,表示通常并非是向不特定人(ad incertas personas),而是向特定表示对象作出的,从而表示亦应从表示对象的特定角度进行解释。就此而言,“主观的”和“客观的”构成要件这种表述,是具有误导性的。〔8〕对此亦可参见 Jahr,JuS 1989,249(251f.)。
所以更为恰当的是,把意思表示的构成要件区分为“内部的”要件和“外部的”要件。〔9〕相同作法例如 Bork,Allg.Teil,2.Aufl.(2006),Rdnrn.567,578。不过即便这个区分也是相对的,因为意思和表示相互间部分地关联。
(一)意思表示的外部要件
意思表示的外部要件由外部表示所构成,而外部表示则必须通过解释来确定。
1.表示
作为必要条件,意思表示要求无论如何要有某个东西被表示出来。无表示,则意思只是纯粹的内心想法而不具有现实中的形成力,也不能在主体间被理解领会。
(1)表示的方式。表示可以被明示或默示地作出。〔10〕《德国民法典》只是在例外的情形中才要求明示的意思表示,参见《德国民法典》第244条第1款、第700条第2款、第1059a条第1款第1项。此取决于意思是直接从表示中得出,抑或只是间接地表现出来(如通过上出租车和讲出目的地而默示地订立一个运输合同)。〔11〕即便所谓的意思实现(例如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51条、第959条),也可被理解为默示的意思表示;参见Repgen,AcP 200(2000),533(548ff.);Kramer,in:MünchKomm-BGB,5.Aufl.(2006),Vorb.§116 Rdnr.26;Singer,Selbstbestimmung u.Verkehrsschutz im Recht der Willenserklärung,1995,S.161ff;其他观点见 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24 Rdnrn.21ff.m.w.Nachw。与此相反,沉默原则上不具有表示的意义。虽然在例外情况下,沉默可以是有意义的(beredt)沉默,例如在当事人间就此有所约定时;不过对于沉默作为意思表示要存在特别的依据。〔12〕与“有意义的”沉默相区别的是法律“规定的”沉默(例如基于《德国民法典》第416条第2款、第516条第2款)。后者涉及的是对意思表示的拟制;对此整个问题详见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28 Rdnrn.66ff.;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 § 116 –144 Rdnrn.60ff.m.umf.Nachw。
(2)表示的目的。在法律意义上对意思表示的特别要求是,在任何情况下意思表示在外部都必须指向某种法律后果的发生。〔13〕对此只需参见 Medicus,Allg.Teil,9.Aufl.(2006),Rdnr.175;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 §116–144 Rdnr.1 m.w.Nachw。只有在满足此条件的情况下,表示者才进行了自决地形塑法律关系的选择。从而,人们将此称为“显露(!)法律拘束意思”〔14〕参见 BGHZ 97,372(377f.)=NJW 1986,2043=JuS 1988,602(Fehnemann);Köhler,Allg.Teil,30.Aufl.(2006),§6 Rdnr.2。的要求。而被表示的法律拘束意思在多大程度上确实主观地存在,涉及的则是意思表示的“内部”要件。〔15〕对此详见下文二(二)。尤其在仅仅是准法律行为(例如设置额外期间)的场合,在纯粹社会交往性承诺(如请客吃饭)的情形,或在纯粹的事实性通知(“我们曾承担保证……”〔16〕这构成了关于作出保证决定这个事实的解释 (BGHZ 91,324=NJW 1984,2279=JuS 1986,440[Brehmer])durch Canaris,NJW 1984,2281。)时,意思表示的“外部”要件并不存在。
2.解释
意思表示的“外部”要件需要通过意思表示解释来确定。进行意思表示解释时,不仅要探求是否的确存在意思表示,还要探求该意思表示的具体意义。〔17〕参见 Larenz,Die Methode d.Auslegung d.Rechtsgeschäfts,1930,S.82f.;Kellmann,JuS 1971,609。而由于对意思表示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的回答,无法脱离其表达的内容,从而就此而言,探求意思表示的存在和探求意思表示的具体意义,这两者实属一体的过程。例如人们不能在没有探求出表示之具体内容的情况下,把银行的某个文件解释为意思表示(保证的表示)。
通常,对意义的探求始于语义学上的解释,以此来试图发现书面或口头体现出来的词语或符号的意义。在此,一般性的词语用法通常具有决定性。特别的词语用法(如《德国民法典》第854条第1款意义下的“占有”(Besitz)),原则上只能在精通法律的合同当事人间或在特定交往圈子中(如在商人间),才能得以承认。〔18〕参见 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 §133 Rdnr.14;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28 Rdnr.34;主张偏离一般语言用法之人,对此负有举证责任,参见Stathopoulos,in:Festschr.f.Larenz,1973,S.357ff.(365f.)。
按照《学说汇纂》中的一处著名段落,在词语“意思明白无歧义”的情况下,不得再对事实上的真意进行探究,〔19〕Paul.D.32,25,1:“当词语不存在歧义时,不应再探究意思问题(Cum in verbis nulla ambiguitas est,non debet admitti voluntatis quaestio)”;对此详见Zimmermann,The Law of Obligations– Roman Foundations of the Civilian Tradition,1990,S.622ff。此点在今天尚存在于所谓的含义清楚规则(plain meaning rule)和行为清楚原理(Acte-clair-Doktrin)中。〔20〕具体参见 Lüderitz,Auslegung v.Rechtsgeschäften,1966,S.65ff.;Meder,Missverstehen u.Verstehen,2004,S.13f.,17ff.,234ff.m.w.Nachw。然而,这个观点过于僵化,因为对词语是否“明白无歧义”的确定,也只能借由解释进行。另外,纯粹的文义解释也忽略了当事人的意思,从而在法律上亦被《德国民法典》第133条和第155条所否定。只是在要求文本形式(Schriftform)的场合,才可能存在文义的拘束力;不过这一点也是由相关形式要求的目的所决定的,所以应将此点与解释结果的获取进行区分。〔21〕参见 Wieser,JZ 1985,407(408);Staudinger/Singer,BGB,2004,§133 Rdnr.30 m.w.Nachw。从而,最终具有决定性的是目的(telos)。和在法律解释时一样,目的可主观或客观地被探求。只有在穷尽所有解释规则后还是存在多义性(例如预定“两个房间带三张床”〔22〕该例来自于 Larenz,Allg.Teil,7.Aufl.(1989),S.337,340。)时,表示才可被认定为无效。〔23〕参见 Staudinger/Singer,BGB,2004,§133 Rdnrn.19,23;Medicus,Allg.Teil,9.Aufl.(2006),Rdnr.759。
(1)主观—目的性解释的优先性。按照主观—目的性解释,表示人进行表示时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具有决定意义。与此相应,《德国民法典》第133条要求,“探求真实意思而不应拘束于表达的字面意义。”主观—目的性解释首先在无须受领的意思表示情形下具有优先性,因为(也只是在此范围内)此时不存在对交易和第三人信赖的保护问题。〔24〕对此只需参见Staudinger/Singer,BGB,2004,§133 Rdnrn.6,15;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28 Rdnr。此主要的适用情形是单方遗嘱。只有在对特定人群(如在悬赏广告情形)进行(无须受领的)表示时,才应例外地照顾第三人可能作出的理解。〔25〕参见 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105 Rdnr.2;Staudinger/Knothe,BGB,2004,§105 Rdnr.12;Schmitt,in:MünchKomm-BGB,5.Aufl.(2006),§105 Rdnr.39。
另外,即便在须受领的意思表示情形,在接受方事实上理解了表示人的真实意图时,主观—目的性解释也具有决定意义。此时无论表示的通常语言含义为何,发生效力的是表示人的真正意图。因为此时沟通是成功的,且自我决定原则没有被交易保护或信赖保护所压倒。例如订阅人订阅杂志时将《法学教育》误订为《法学》,在只是存在一个就《法学教育》杂志的供应合同情形,杂志社应该明白订阅人指的就是《法学教育》。〔26〕AG Wedding,NJW 1990,1797;Staudinger/Singer,BGB,2004,§119 Rdnr.39.在此意义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条第1款也规定:“在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被另一方当事人知悉或不可能不被另一方当事人知悉时,该方当事人的”表示“应按照其意思去解释。”
就像表示人会犯错一样,表示的接受人在其承诺表示中,也可能会进行“错误”表达。此时“错误的表示无害”(falsa demonstratio on nocet)原则也适用。但对此应区分两种情形。如果双方当事人都具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思,而双方只是错误地选择了一个用词,则实际的意图发生效力(例如,就鲸鱼肉达成合意,可实际的用词“Haakjöringsköd”在挪威语中的意思是鲨鱼肉)〔27〕RGZ 99,147;对此详见 Cordes,Jura 1991,352。。与此相反,如果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受法律约束的意思,则此时存在《德国民法典》第117条第1款规定的虚伪行为。在此,即便在外在要件层面上,也不存在意思表示。〔28〕参见 Larenz,Allg.Teil,7.Aufl.(1989),S.366;Staudinger/Singer,BGB,2004,§117 Rdnr.1 m.w.Nachw。从而,在外部表示只是关涉双方当事人的语言运用而不涉及外部第三人的理解方式的限度内,主观因素也会影响意思表示的外在要件。
(2)客观—目的性解释的优先性。如果表示接受人没能了解到表示人的真实意图,则客观上外部表示具有优先意义。然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57条,对外部表示的解释应遵循“诚实信用并顾及交易习惯”,而不应仅仅限于“字面意义”。例如,如果在互联网网页上用粗体字显示“免费下载”,尽管用小号字体补充了“0900...0.49欧元每分钟”,那么点击“是,继续”也不构成意思表示。此处缺少的并非只是所谓的“表示意识”,〔29〕持此见解者参见AG München,MMR 2006,184。而是缺少意思表示的外部构成要件,因为此时一个善意的表示接受者只会把点击行为理解为继续无偿使用的意思。另外一个例子是明显无行为能力之人(如一个小孩)表达出的法效意思。在此种情形,在外部构成要件层面上就已然并非意思表示。
(二)意思表示的内部要件
如果被表示出来的法律拘束意思(Rechtsbindungswille)和真实意图相吻合,则此时该行为便是总体上成功地以私人自治方式参与法律交往的无瑕疵行为。对于此种“最终的”、〔30〕Kramer,Grundfragen der vertraglichen Einigung,1972,S.147f.;Kramer,in:MünchKomm-BGB,5.Aufl.(2006),Vorb.§ 116 Rdnr.18a.“完整类型的”〔31〕Sandrock,RabelsZ 34(1970),375(376).意思表示,无需特别地予以归责(Zurechnung),**** 德语Zurechnung一词一般译为“归责”,英译一般为attribution,偶尔被译为accounting(参见Hans Kelsen,Essays in Legal and Moral Philosophy,translated by Peter Heath,1973,pp.154-164)。但需说明的是,此时“归责”中的“责”,应做非常广义的理解,其笼统指为某行为或某事负责(Verantwortung;Responsibility)。Zurechnung指将某行为或某事的法律后果归到某人头上,从这个角度讲该人为此行为或此事负责。此时的“责”包括但不限于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等作为义务违反之后果的民事法律责任(Haftung;Liability),也包括将某种不利益(如善意取得中原所有权人丧失所有权)归到某人头上,也包括(如在本文中)外部表示体现出的法律效果被归到表示人头上;等等。“归责”理论是法学上的重大课题。凯尔森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因果关系,在法学内与自然科学中因果关系相对应的便是“归责”(参见本注解中所引Kelsen书),也即是将某行为或事件的法律后果归到某人头上。本文将Zurechnung一词虽统一译为“归责”,但其上述具体含义,应予明辨。——译者。因为内部的意思形成被忠于原样地在外部表示了出来。因此,教义学上的争议集中于如下前置的问题,即在何种条件下自治的决定得以可能,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与事实上意思相偏离的表示,应被规范性地予以归责。如果人们忽略新生物学对意志自由观念的根本性怀疑,〔32〕尤其参见 Roth,Aus Sicht d.Gehirns,2003;相反的批判观点参见 Wolff,JZ 2006,925 m.w.Nachw。那么本质上在三个因素上可能会出现问题:能力、意图和自由。
1.能力上的要件
外部表示事实可被归责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表达出来的意思应是基于理性而形成。
(1)行为能力(Geschäftsfähigkeit)。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1款,无行为能力人所为的意思表示无效。对此存在特别规定:即适用于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德国民法典》第105a条之规定;适用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德国民法典》第107条及以下诸条;适用于被监护人的《德国民法典》第1903条的同意保留。虽然《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1款所规定之完全无效的法律效果,有时被诟病为不具有合比例性,〔33〕参见 Canaris,JZ 1987,993(996ff.);相反的观点参见Staudinger/Knothe,BGB,2004,§105 Rdnrn.7f.m.w.Nachw。但此争议在本文中关系不大。即便是相应提出的效力待定(从而有被追认之可能)的缓和替代方案,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也是,自我形塑法律关系的前提条件是自由意思决定的形成能力。
与此相应的后果是,无(完全)行为能力人也不承担那些基于缔约过失责任或《德国民法典》第122条所保护之落空的信赖的附属性损害赔偿责任。〔34〕可能的责任知识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2款结合《德国刑法典》第263条和《德国民法典》第826条的侵权责任,前提是该责任没有被《德国民法典》第827、828条所排除;参见 Schmitt,in:MünchKomm-BGB,5.Aufl.(2006),§106 Rdnrn.17ff.;Staudinger/Knothe,BGB,2004,Vorb.§ § 104–115 Rdnr.28 m.w.Nachw。法律交往的安全性和便宜性要求单纯的法律明确规定以及要求明确的年龄界限,从而(限于“具有难度之”法律行为情形的)“相对无行为能力”这种中间类型,尤其应予拒绝。〔35〕参见 BGH,NJW 1970,1680(1681);Bork,Allg.Teil,2.Aufl.(2006),Rdnr.984;Köhler,Allg.Teil,30.Aufl.(2006),§10 Rdnr.4。
(2)行动能力(Handlungsfähigkeit)。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如果某意思表示是在无意识的状态或临时性精神障碍时作出的,则此意思表示无效。
(2.1)对《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解释。例如在醉酒或吸毒后,便存在《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意义上的临时性精神障碍。例如在梦游、癫痫或被催眠时即存在意识障碍。〔36〕参见 Staudinger/Knothe,BGB,2004,§105 Rdnrn.12f.m.w.Nachw。不过根据通说,《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并不涵盖完全无意识的情形(昏厥),因为此时由于欠缺行为意思(Handlungswille),意思表示这个事实本身根本就不成立。〔37〕参见 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105 Rdnr.2;Staudinger/Knothe,BGB,2004,§105 Rdnr.12;Schmitt,in:MünchKomm-BGB,5.Aufl.(2006),§105 Rdnr.39。
通说的这个观点不能让人信服。它既不符合《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文义,也不符合该款的目的。很明显,给第三人造成存在法律行为表示之印象的“点击鼠标”动作,是由于无意识地碰到了电脑导致,还是由于癫痫导致,不应造成不同后果。在这两种情形中,从价值评价的角度看,表示者对其行为都没有控制力,亦即并未处于能够理性地形成意志的状态。与无行为能力的特别情形相比,此处的表示者缺乏从事受意志支配之行动的能力。该行动能力在直接强制(vis absoluta)时也同样不存在,从而对此情形《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应予类推适用。
另外,在法律行为重新实施的情形,也能体现出在意识障碍和无意识之间进行区分的不妥当。如果只是在无行为能力或精神活动障碍情形,可以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41条对无效的法律行为进行认许,而在无意识或直接强制的情形,却由于“在构成要件上就根本不存在法律行为”〔38〕按照 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141 Rdnr.3中的观点,在满足此条件时,《德国民法典》第141条的规则不得适用。而不允许对之进行认许,这显得太具有概念法学意味,与利益状态相违。
(2.2)行为意思(Handlungswille)的学说。根据绝对通说,意思表示的要件之一为行为意思,亦即的确进行作为或有意识地不作为的意思。〔39〕参见 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24 Rdnr.3ff.;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Vorb.§ 116 Rdnr.16;Flume,Allg.Teil II,4.Aufl.(1992),S.46;Ahrens,JZ 1984,986;Köhler,Allg.Teil,30.Aufl.(2006),§7 Rdnr.4 m.w.Nachw.;a.A.Schermaier,in:Schmoeckel/Rückert/Zimmermann,Historisch-kritischer Komm.zum BGB,2003,§§116–124 Rdnr.14;Brehmer,JuS 1986,440(443);Kellmann,JuS 1971,609(612ff.)。缺少行为意思,则只是存在一个意思表示的表象而已。
在教义学上存在多个理由拒绝行为意思的学说。其不仅偏离《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中的法律规则,在行为的归责和表示内容的归责之间也没有做出足够的区分。对于行为的归责,重要的并非“意欲”,而是“能够”。因为即便某行为并没有被意欲,也可能要对该行为负责。〔40〕亦可参见 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 § 116–144 Rdnr.27。例如某人无意地打碎花瓶或无意地踩了刹车踏板,都存在侵权法上的行为。〔41〕参见 Larenz/Canaris,SchuldR II/2,13.Aufl.(1994),§75 II 1a(S.361)。并且,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第2种情形,即便是误写或误说的情形,也存在可归责于表示人的意思表示,尽管表示人并不愿意做出该具体行为。〔42〕参见 Werba,Die Willenserklärung ohne Willen,2005,S.71f.,84ff。虽然以上所述并不排斥某意思表示外部要件的归责取决于特定意图上的要件,即进行沟通以及参与法律交往的意图。〔43〕详见下文二、(二)、2。但行为意思对此却并非适当的规范性标准。
从行为意思中,也即从实施某行为的意图中,人们不能够推出意思表示形式的沟通行为的存在。在拍卖时是否基于“行为意思”驱赶某个讨厌的蚊子,这对于法律行为上的关系是否成立,不具有意义。一方面,举手这个被意欲的“肌肉动作”并不追求沟通上的目的;另一方面,极度个人化的行为目的并不适合作为法律上的区分标准。驱赶昆虫的意图,与一般性的动物保护观念类似,是不具有相关性的内心想法。对于潜在责任具有决定性的首要要件,限于作为表示创造者的举手者是否具有归责能力。相反,无论在意思表示的内部要件抑或外部要件上,行为意思都不具有意义。〔44〕相反,Stephan Lorenz,Der Schutz vor d.unerwünschten Vertrag,1997,S.214ff.甚至主张在内外要件上都要考虑行为意思。
基于《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的反对解释,对于行为的归责,充分且必要的仅仅是造成外部表示事实之时的行动能力。如果睡眠者或无意识之人造成了意思表示的表象,那么这对该人不发生法律行为上的负担,因为该人根本就“对此无能为力”。〔45〕亦可参见 Hepting,in:Festschr.600 Jahre Universität Köln,1988,S.209ff.(221)。应与行为的可归责性加以区别的,是表示意义的可归责性,即表示人对其所表示者在多大范围内负责。〔46〕对于行为与表示意义之间的区分,亦可参见 Larenz,Die Methode d.Auslegung d.Rechtsgeschäfts,1930,S.34。而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却需要先在能力方面探究,是否行动的私主体的确具有自由地形成意思的能力。
(2.3)损害赔偿责任。缺乏行动能力时,尽管意思表示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05条第2款归于无效,但可能基于《德国民法典》第280条第1款、第241条第2款和第311条第2款发生缔约过失责任。〔47〕亦可参见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116–144 Rdnr.50;Kramer,in:MünchKomm-BGB,5.Aufl.,(2006),Vorb.§ 116 Rdnr.8 Fußn.22。某人在极度疲劳状态进入拍卖场,并且也知道自己睡着时可能会发生反射行动,那么他应对违反相应的注意义务负责。
2.意图上的(intentional)要件
外部表示(即显露出来的法律拘束意思)的归责,可出于多种原因而存在问题:首先会由于表示人根本就不想表示任何东西;其次会由于表示人虽然想表示点什么,但并无法律行为上的意图;最后会由于表示人打算实现的法律效果不同于表示出之法律效果。
(1)沟通意思(Kommunikationswille)。即便某人通过其行为导致了意思表示的外部构成,他也可能缺少向第三人显露任何事情的意思。例如某人在拍卖场举手只是要驱赶苍蝇或想挠挠脑袋,即是如此。
此亦存在于所谓的脱手意思表示情形,即表示人做成了临时性的、尚待考虑的意思表示草稿,可是由于表示者自己或某第三人(如秘书或同屋)的疏忽而与其他信件一起被寄出。对于此等情形可将之称为缺乏“沟通意思”。
(1.1)原则上排除履行责任。法律对缺乏沟通意思的后果作出了极其明确且具有典范性的规定。〔48〕对此亦可参见 Neuner,JuS 2007,401(410f.)。一个明确的规定存在于《德国民法典》第794条第1款中。按此规定,即便不记名债券“并非基于其意思而进入交易中”,其发行人也应承担义务。此种对积极利益承担责任的做法,亦存在于汇票法中,其前提是针对善意后手取得人被引起了(veranlasst)存在有效汇票义务的权利外观(《德国汇票法》第16、17条)。不过这些规定只是作为被严格限定的特别规定,它们是为了保障有价证券流通性。〔49〕只需参见 Staudinger/Marburger,BGB,2004,§794 Rdnr.1。另外,这些法律规定并没有建立法律行为上的义务,它们的基础是法定的权利外观责任,〔50〕只需参见 Palandt/Sprau,BGB,66.Aufl.(2007),§793 Rdnr.8;Hueck/Canaris,Recht d.Wertpapiere,12.Aufl.(1986),§3 II(S.33ff.)。而这只是体现了对第三人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对这些有价证券法上特别规定的反对解释显示,在一般民法中缺少沟通意思时并不存在履行责任。“意思表示必须是基于表示者之意思而达致另一方”,这被历史上的立法者直接认定为是“不言而喻的”。〔51〕Mot.I,S.157.即便现代的立法者也认同此观点,并以电脑上的“发送命令”非基于表示者之意思而被激活为例。〔52〕BT-Dr 14/4987,S.11.
对此,另一个规范文本上的确认是《德国民法典》第172条第1款。按此规定,对于代理授权证书内容的归责,要求该证书被“交出”(Aushändigung)。另外,《德国民法典》第130条第2款也表明,表示人在发出意思表示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对于意思表示的效力不发生影响。基于对此的反对解释:如果某意思表示的草稿是在具有行为能为时完成,但嗣后在无行为能力时被发出的,此时不存在意思表示。〔53〕将表示草稿带入交往中,其实并不需要特别的行动能力。理论上,甚至自然力也可造成脱手的事实(例如草稿被风吹走)。只是书面文件的起草必须要可归责地被作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表示的可归责性加以确定。某保证表示的作出人如果在其完全失去知觉后交出该表示的,亦同。〔54〕此例来自Köhler,Allg.Teil,30.Aufl.(2006),§6 Rdnr.12(但该作者不恰当地从欠缺行为意思出发)。从而,具有决定性的是,在表示进入交往中时,表示人是否存在(可被推测出的)沟通意思。
相反的观点认为,沟通意思缺乏时,也存在(可撤销的)意思表示。〔55〕参见 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130 Rdnr.4;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 26 Rdnr.7 m.w.Nachw。此观点在法律中找不到依据,并且也模糊了自决和他决之间的区分。〔56〕亦可参见 BGH,NJW-RR 2003,384;Leipold,BGB I,4.Aufl.(2007),§12 Rdnr.8;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 § 116–144 Rdnr.49;Lorenz,Der Schutz vor d.unerwünschten Vertrag,1997,S.220。在结果上,该观点使得某个顶多只是过失地造成意思表示之外部构成的人,可能为积极利益负责,这一点也不具有合比例性。除去尤其在有价证券法领域中存在的保护交易安全优先的情形,只有在承担责任者自己在追求法律行为上的好处时,让他承担履行责任才具有适当性。
(1.2)损害赔偿责任。至于承担消极利益责任,这里的问题是,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80条第1款、第241条第2款和第311条第2款(德国新债法下缔约过失责任的请求权基础——译者)存在以过错为要件的责任,抑或类推《德国民法典》第122条存在不以过错为要件的责任。在表示人通过其行为(例如起草了意思表示的草稿)有意地导致了发生信赖损害的危险时,基于立法者的规制意图,〔57〕参见 BT-Dr 14/4987,S.11。会存在加重的责任。〔58〕参见 Canaris,JZ 1976,132(134);Singer,Selbstbestimmung u.Verkehrsschutz im Recht der Willenserklärung,1995,S.197;其他观点见 Bork,Allg.Teil,2.Aufl.(2006),Rdnr.615 m.w.Nachw。
(2)参与意思(Partizipationswille)。争议极大的是,除了一般性的沟通意思,意思表示的内部构成还在多大程度上以其他因素为要件。对此存在着各种观点,从主张具体效果意思的必要性,到要求存在表示意识或存在表示过失,直到主张完全放弃其他额外标准。
(2.1)效果意思说(Lehre vom Geschäftswillen)。所谓的效果意思,指向的是使得特定的法律后果发生效力。因此,人们也将之称为“法效意思”(Rechsfolgewille)(指向的是发生非常具体的法律效果)。〔59〕参见 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 § 116 – 144 Rdnr.29;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24 Rdnr.9;然而对此的用语并不统一;其他一些人将“法效意思”一词理解为一般性地导致任何某一种法律效果的意思。此种“法律效果意思”便等同于“法律拘束意思”(Rechtsbindungswille)了;参见Köhler,Allg.Teil,30.Aufl.(2006),§6 Rdnr.2以及参见下文脚注[66]处。如果表示人向外部表示出了非其主观所愿的某个内容,即该人意欲他样的“法律行为”或根本就不意欲任何“法律行为”,那么该人便缺乏效果意思。
按照少数说,效果意思属于意思表示的构成性要件。〔60〕较新的文献尤其参见 Singer,Selbstbestimmung u.Verkehrsschutz im Recht der Willenserklärung,1995,S.45ff;ders.,JZ 1989,1030(1031ff.);Lobinger,Rechtsgeschäftliche Verpflichtung und autonome Bindung,1999,S.89ff。例如,表示人说错或写错时,不存在意思表示,而只是在《德国民法典》第121条中的撤销期限经过后,基于信赖和交易保护而发生他决性(heteronom)的拘束力。〔61〕参见 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 § 116–144 Rdnrn.21ff。按此观点,意思表示的效力根据在于意思上的自我决定,而(尤其是)信赖和交易保护原则只是构成法定的、也即他决性的责任的基础。
在效力来源理论上进行严格区分的优点在于方法上的高度透明,但其却难以和现行法吻合,并且在法理学上也无法“立足”。例如在立法层面上,在规范文本没有正确体现立法的规制意图时,也存在与有缺陷之意思表达相类似的问题。〔62〕对此详见 Neuner,Die Rechtsfindung contra legem,2.Aufl.(2005),S.114f。在发生此种偏离的场合,将“有缺陷”立法行为的效力完全归诸强制和他决,同样显得颇为怪异。毋宁是,具有决定性的是自决思想,该思想必然地涵括了对失败的自决形式承担责任。〔63〕亦可参见 Flume,in:Festschr.zum 100-jährigen Bestehen d.DJT I,1960,S.135ff.(159f.);Kramer,in:MünchKomm-BGB,5.Aufl.,2006,Vorb.§ 116 Rdnr.39 m.w.Nachw。因此,即便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19条及以下条文规定的现行撤销体系,表示相对方先天地对表示的信赖,也是得到保护的。〔64〕亦可参见 Lorenz,Der Schutz vor d.unerwünschten Vertrag,1997,S.223;Werba,Die Willenserklärung ohne Willen,2005,S.50ff。只是在起初有效的意思表示被依期有效地撤销后,信赖保护才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2条而被限于消极利益。
(2.2)表示意识说(Lehre vom Erklärungsbewusstsein)。所谓表示意识在文献中的定义并不统一。有些学者将“表示意识”和“表示意思”(Erklärungswille)概念等同。〔65〕例如 Eisenhardt,JZ 1986,875(879);Leipold,BGB I,4.Aufl.(2007),§10 Rdnr.19;Brox/Walker,Allg.Teil,30.Aufl.(2006),Rdnr.85。不过表示意思只是体现出了进行某种表示(沟通)的不特定意思,而非对私法关系之确定和形成发挥作用的具体意图。在此意义上,此种说法太过宽泛和笼统。另一些学者将“表示意识”理解为一般性的“法效意思”,〔66〕Köhler,Allg.Teil,30.Aufl.(2006),§6 Rdnr.3.即表示人“意图将公布的表示行为作为一个意思表示”。〔67〕Lorenz,Der Schutz vor d.unerwünschten Vertrag,1997,S.216.这个定义又失之过窄。其原因是,如果某人向第三人显露出法律拘束意思,即便他主观上根本就不想被拘束,他也算是已经参与到法律交往中了。例如,某人在互联网拍卖中将起价有意订得很低,尽管他想在价格高过一定界限时才卖,该拘束意思的缺乏也无关要旨。〔68〕参见 BGHZ 149,129(136)=NJW 2002,363=JuS 2002,219(Lettl);Kramer,in:MünchKomm-BGB,5.Aufl.,(2006),§116 Rdnr.5。对此,自决地、无瑕疵地表示出法律拘束意思即已足够。〔69〕亦可参见 Canaris,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t.PrivatR,1971,S.419ff。谁若想让第三人基于有意表达出来的负担性表示而在法律上受拘束,必然不得自己将自己所为表示的拘束力停止掉。此种不带有法律拘束意思的意思表示应归责于表示人,〔70〕其他观点见 Lobinger,Rechtsgeschäftliche Verpflichtung und autonome Bindung,1999,S.132f.;Eisenhardt,JZ 1986,875(879);Singer,BGB,2004,S.203ff.,该作者对于心意保留情形,基于法律效果意思的缺乏而否认了法律行为上的拘束力,而转而选择了一种信赖理论上的进路。因为他想让第三人负担义务,他自己也就应被如此对待。否认此种归责,将导致私人自治的理念自相矛盾。因为在有疑问时,任何人都只愿意让别人负担义务,从而该潜在的心意保留会最终使得任何的履行责任都变为他决的。正是因此,《德国民法典》第116条第1款明文规定,表示人暗地保留,并不意欲被表示出的,意思表示并不因此无效。〔71〕相反,在表示接受人知悉保留的情况下,《德国民法典》第116条第2句所规定的无效可基于错误表示无害真意原则在外部构成层面上就得到了解释。
从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表示意识”进行较宽泛的表述。按此,存在“的确参与法律行为交往,并基于自己行为以某种方式作出在法律行为上具有相关性的表示”的意思即已足够。〔72〕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24 Rdnr.6.按照此恰当的描述,具有决定性的方面在于参与法律行为交往的意思;从而,与权利外观责任不同,在此并非只是存在某个“意识”,而是在追寻某个特定意图。表示人不仅仅是有意地进入充满风险的私法交往层面,而是意欲对法律关系发挥形成和改变的作用。他作为私法主体积极地行事,追求法律行为上的好处。因此,人们最好将之称为“参与意思”或“参加意思”,而不是将之仅仅称为“表示意识”。
(2.3)缺乏参与意思的法律后果。缺少参与意思的经典例子,如“特里尔葡萄酒拍卖案”(为打招呼而举手),错误以为是贺卡而签字但其实签的是订单,以及本意作为事实通知但却误解性地进行了表述(“保证案”〔73〕对此亦可参见上文脚注[16]处,那里指出了对是否存在意思表示外部要件的怀疑。)。在使用互联网场合也可以想见,某人客观地发出了承诺表示,但主观上只是想获取无拘束力的信息。
(2.3.1)与缺乏沟通意思的相似性。关于缺少参与意思(或曰“表示意识”)案件的处理,学术上的讨论受主观说影响很大。此说强调了自决原则,并主张对此采用《德国民法典》第118条规定之戏谑行为无效的当然推理。相反的观点为客观说。客观说突出信赖和交易保护原则,力倡对《德国民法典》第119条第1款的类推适用。〔74〕详细的论述见 Werba,Die Willenserklärung ohne Willen,2005,S.28ff.;Werner/Neureither,22 Probleme aus d.BGB Allg.Teil,7.Aufl.(2005),S.22ff.;Grigoleit/Herresthal,Allg.Teil,2006,Rdnr.373 m.w.Nachw。
与争论到底是类推《德国民法典》第118条还是类推第119条第1款相比,在方法论上更有说服力的是,将这些情形与法律状态相对明确的“脱手”意思表示进行评价上的对比。〔75〕对此 类 比 亦 可 参 见 Staudinger/Singer,BGB,2004,Vorb.§ § 116 – 144Rdnr.49;Lobinger,Rechtsgeschäftliche Verpflichtung und autonome Bindung,1999,S.229ff.m.w.Nachw。在“脱手”意思表示情形,草稿作者至少具有潜在的法律拘束意思和参与意思;而在缺乏所谓“表示意识”的情形,却完全不存在法律拘束意思和参与意思。尽管如此,尽管与缺乏“表示意识”不同,草稿作者暂时根本不想作出任何表示,但互联网使用者是由于“网上冲浪”时误点(此时“表示人”根本不具有潜在的参与意思,即不具有表示意识——译者)还是由于搞混了“关闭”按钮(作者应指此时“表示人”完成了草稿,想关闭窗口却错误点击了发送键,从而为“脱手的”意思表示——译者)而激活了意思表示的“发送命令”,这对于某表示的法律拘束力而言,并不构成具有决定意义的区别。这两种情形,都缺少参与法律交往的决定性意图,即缺少交换契约中的“双方性”(do ut des)观念。在这两种情形中,认定法律行为上的义务都同样地不恰当和不合比例,因为表示人这方面根本就未追求任何第三人在法律行为上的义务,从而顶多只是为因此引起的损害针对第三人负责。
总而言之,缺乏参与意思和缺乏沟通意思在目的论上应等同视之。某人在拍卖会上举手是为了赶苍蝇还是请烦人的邻座离开(赶苍蝇中缺乏沟通意思,因为此时并非想和别人沟通;请人离开时存在沟通意思,即请对方离开,但缺乏参与意思,即不想拍卖——译者),很明显不应有所区别。典型地如《德国民法典》第794条、《德国汇票法》第16、17条中有价证券法上的特别规定以及《德国民法典》第130条第2款和第172条第1款所展示的,〔76〕参见上文二、(二)、2、(1)、(1.1)。在这两种情形都不存在意思表示。
(2.3.2)表示过失说(Erklärungsfahrlässigkeit)。尤其是司法实践倾向于支持一种介于(意思表示)可撤销性(相应地对是否撤销具有选择权)和不存在(从而也就不必顾及《德国民法典第》第121条规定的期限)之间的看似折中的解决方案。也即是,司法实践“在表示人尽到交往中注意就能够认识并避免其表达……被理解为意思表示时”,〔77〕BGHZ 91,324(324,330)=NJW 1984,2279=JuS 1986,440(Brehmer);109,171(177)=NJW 1990,454;149,129(136)=NJW 2002,363=JuS 2002,219(Lettl);亦可进一步参见 Bydlinski,JZ 1975,1(5);Gudian,AcP 169(1969),232(234ff.);Kramer,in:MünchKomm-BGB,5.Aufl.(2006),§119 Rdnr.99 m.w.Nachw。认定意思表示的存在。然而,这个所谓表示过失的要求并非“黄金中道观”(goldene Mitte),因为在法律中不存在任何此种区分标准的指示。现行法中并不存在“过失的意思表示”这个范畴。〔78〕亦可参见 Singer,BGB,2004,S.174(作为“主观”说的支持者),以及Lorenz,Der Schutz vor d.unerwünschten Vertrag,1997,S.218(作为“客观”说的支持者)。过错只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80条第1款、第241条第2款和第311条第2款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的必要条件;过错并不能表明某人是否私人自治地参加到了法律交往中。
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将表示无过错地发给了一个错误的收件人(该人将表示转给正确的收件人)的情形,与司法上的做法不同,应认定此时在事实构成上存在意思表示。〔79〕不同观点见BGH,NJW 1979,2032(2033),其将可归责性取决于表示人是否能够考虑到以及是否的确考虑到了转交的可能。在此,表示人公布出了必要的法律行为上的参加意思;尤其是发件人自己在文件正文中抑或在地址上书写错误,并不应被区别对待。同样,当传达人篡改了其传递的表示时,也应认定存在意思表示。这里表示人在参加法律交往时有意地采用了辅助人员,从而也应承担由此造成的行为失检风险。〔80〕参见 Marburger,AcP 173(1973),137(143ff.);Staudinger/Singer,BGB,2004,§120 Rdnr.3;Lobinger,Rechtsgeschäftliche Verpflichtung und autonome Bindung,1999,S.232ff.;其他观点见 Palandt/Heinrichs,BGB,66.Aufl.(2007),§120 Rdnr.4;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36 Rdnr.18 m.w.Nachw。
(2.3.3)损害赔偿责任。就信赖损害而言,这里的问题是该损害只是按照缔约过失原则来赔偿,还是应类推《德国民法典》第122条中的无过错责任。一以贯之,这里也应与“脱手”意思表示情形同样处理:〔81〕参见上文二、(二)、2、(1)、(1.2)。只是在(表示人)增加了风险和对风险可控的情形,无过错的责任才属正当。〔82〕深入的探讨参见 Singer,BGB,2004,S.194ff。但此条件在如作出“陈述性的”表示时(如“保证案”〔83〕BGHZ 91,324=NJW 1984,2279=JuS 1986,440(Brehmer);对此亦可参见上文脚注[16]处。)得到满足,但在事先未曾预料进行旧书拍卖的大厅中举手的情形,却非如此。
3.实质的条件
为了保护群体利益,为了维护法伦理上的最低标准,以及尤其为了保护行为人自己,法律可以否认某法律行为的效力。在此,保护行为自由构成一个重点。对行为自由的保护既展现了自由维度也展现了社会性维度。〔84〕对此亦可参见 Neuner,PrivatR u.Sozialstaat,1998,S.237ff。在社会性方面涉及的是保障对于参与私法交往所必需的实质基本条件。与公民的自由一样,私法自治也并非是不取决于任何条件,而是尤其以充分的知悉和认识状态为前提;该状态使得例如对合同对象、合同对手或未来发展风险的评估成为可能。自由方面则涉及针对外部的、由第三人造成的侵害提供保护。不当胁迫或许可以作为此种外部侵扰的直观例子。在不当胁迫的情形,自我决定虽然在形式上得到了保障,因为被胁迫者是从本身未受破坏的空间出发作出的判断,但此时实质上的决定自由在事实上已经被抹去。在对意思形成过程可能发生潜在侵扰的背景下,便提出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也就是,在何种法律事实上的条件被满足时,通过私人自治方式形成决定才的确可能。
(1)学术上的讨论。一种少数说认为,有效的意思表示不仅以形式上的基本条件为前提,也取决于“法律行为决定自由”意义上的事实—经济上的充分行动可能性。〔85〕参见 Wolf,Rechtsgeschäft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 u.vertraglicher Interessenausgleich,1970,S.101ff.,180;Kramer,Die“Krise”d.liberalen Vertragsdenkens,1974,S.58f。只有在这些另外的实质性条件得到满足时,各个私法行动者才处于可以自决地对正当利益协调发挥作用的状态。从而,要求对意思表示概念进行构成要件上的扩张,对其加入对形成自由决定所必要的、法律事实上的情事。〔86〕参见 Wolf,Rechtsgeschäft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 u.vertraglicher Interessenausgleich,1970,S.123ff。
的确,各个私法主体的自由只能存在于各自的社会背景下,且不具备实质的基本条件其自由便会丧失意义。从此角度看,上述观点具有一定道理。即便作为基础性法益的人类尊严,也并非仅仅会被国家或私人所侵犯,而是也会受到贫困、无知识和无机会的破坏。然而,笼统地——即仅仅以导向于与事无涉之利益的方式〔87〕参见 Wolf,Rechtsgeschäftliche Entscheidungsfreiheit u.vertraglicher Interessenausgleich,1970,S.167ff.,180。——把实质决定自由放入意思表示的要件中,这并非正确的做法。在方法上,该作法导致各种不同原则模糊地混杂在一起,在法律实践中会严重影响法的安定性;其尤其和不同的法定保护体系无法吻合。〔88〕亦可参见 Fastrich,Richterliche Inhaltskontrolle im PrivatR,1992,S.39ff.,215f.;Singer,BGB,2004,S.18ff.;Lorenz,Der Schutz vor d.unerwünschten Vertrag,1997,S.231ff。
(2)法定的保护体系。法律上对实质决定自由的保护建基于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的思想上。原则上,干涉只是偶尔的,且应符合比例原则。〔89〕对此亦可参见 Enderlein,Rechtspaternalismus u.VertragsR,1996,S.237ff。
带有警示功能的形式要求(例如《德国民法典》第311b条第1款、第518条第1款)和教导义务(例如《德国公证法》第17条)可算作对私人自治最轻微的干涉。为了弥补信息上的缺乏,可直接将(潜在)合同对手牵扯进来。如,此种信息义务在《德国民法中信息义务规定》(BGB-InfoV)中被详细规定。它们部分地服务于对其他保护工具的说明,尤其是关于撤回权的存在(例如《德国民法典》第312条第2款、第355条第2款)。撤回权应被用于对抗例如特定情形下对优势地位的利用(如对于上门销售交易按照《德国民法典》第312条第1款)或与合同标的有关的风险(如对消费信贷合同按照《德国民法典》第495条第1款)。亦存在其他的选项,如撤销的可能,例如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23条在胁迫或欺诈情形的撤销。〔90〕除此之外,按照通说,亦存在基于《德国民法典》第280条第1款、第241条第2款和第311条第2款中的缔约过失原则废止合同的可能性;详见 BGHZ 165,363=NJW 2006,845;Looschelders,SchuldR Allg.Teil,4.Aufl.(2006),Rdnrn.193ff.;Lorenz,Der Schutz vor d.unerwünschten Vertrag,1997,S.387ff.m.w。Nachw.;除此之外,在满足特定条件时,也存在基于《德国民法典》第313条的交易基础落空的可能;对此详见Larenz/Wolf,Allg.Teil,9.Aufl.(2004),§38 Rdnrn.1ff.;Singer,Selbstbestimmung u.Verkehrsschutz im Recht der Willenserklärung,S.222ff.m.w.Nachw。
最后,法律规定的无效导致了对私人自治最严重的干涉。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的基本理念,只有在被暴利侵犯者主观上的决定条件受到限制(例如基于无经验),暴利行为者利用了此情况,并且在客观上给付和对待给付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合比例时,才产生无效的后果。联邦宪法法院却超越了此限制性的做法,对实质的决定自由予以了更多的关照。如果某合同对手事实上单方面决定了合同内容(尤其是在保证合同、婚姻合同和保险合同情形),则应“防止对于(另一方)合同当事人而言,其自决被颠倒为他决”。〔91〕BVerfGE 114,1(34)=NJW 2005,2363=JuS 2005,1026(Sachs);114,73(90)=NJW 2005,2376;103,89(101)=NJW 2001,957=FPR 2001,137;89,214(232)=NJW 1994,36.
除此之外,也存在法律规定的无效。在此,尤其涉及的是对未来事态发展进行评估的意思形成过程中的瑕疵和危险,从而最终也部分地保护了人类尊严这个核心。对此,值得提及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29条的流质约定禁止、按照《德国民法典》第311b条第2款关于未来财产之合同的无效以及根据《德国器官、组织移植法》第17条第1款结合《德国民法典》第134条对器官交易的禁止。
总而言之,很明显,立法者只是在特定情形,并且是按照一个分层次的体系,对私人自治进行了干涉。从而,把对实质决定自由的一般性考虑作为意思表示的生效条件,无法立足。此亦适用于把合同正义作为实质性的功能原则引入自决原则的教义学观点,〔92〕例如参见 Zweigert,in:Festschr.f.Rheinstein II,1969,S.493ff.(501)。或主张至少在“特定伦理正义”的意义上实现合同机制之“正确性保障”的观点。〔93〕尤其参见 Schmidt-Rimpler,AcP 147(1941),130(132ff.,149ff.);ders.,in:Festschr.f.Raiser,1974,S.3ff.(4ff.)。这些主张使得合同自由只是拥有下位的意义,使得合同自由取决于“合同正义”如何被具体地定义。就此而言,它们颇有问题。毋宁是,合同自由作为受到宪法保障的独立的防御权,恰恰不应受制于任何一般性的“正确性保留”,而只应受制于阻抗不公平结果的、好像作为“消极”过滤器的那些限制。〔94〕详见 Canaris,in:Festschr.f.Lerche,1993,S.873ff.(882ff.);Neuner,PrivatR u.Sozialstaat,1998,S.222f。只要私法主体遵守了包括基本权利和人权基础框架在内的法秩序,便不存在法院干涉和进行结果控制的缘由。
三、结语
如果从表示的善意接受人角度看,表示体现出了法律拘束意思,那么意思表示的外部要件便得到满足。一个少数观点将“意思表示”的概念只是限于此定义,从而对表示人的主观方面未加以顾及。〔95〕参见脚注39结尾处援引的文献。这种界定导致了“无意思的意思表示”,从而显得不甚妥当。尽管不得不承认,《德国民法典》第105条不太准确地规定了无行为能力人的“意思表示”为“无效”。把“无效的意思表示”亦理解为“意思表示”,这种定义弱化了自我决定这个实质要素。〔96〕亦可参见 Bartholomeyczik,Festschr.f.Ficker,1967,S.51ff.(70f.)。特别是,这样使得意思表示和其他创设义务的事实构成(尤其和权利外观责任)之间的术语界分被消除了。不过,关于概念正确性的争论并不具有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毋宁是法律中所确定的评价;因为正是基于该等评价,法律行为上的负担才事实上得以产生。
在主观方面,行为意思、表示意识和效果意思的传统三分法,并不能充分体现具有决定性的事实标准。行为意思这个要求,根本就是多余,因为此处涉及的只是行动能力的能力方面,而并非行为的目的性。所谓的行为意思更非“具有前构成要件属性的”先天性条件。毋宁是,行为的可归责性在《德国民法典》第104条及以下条文中已得到了完全的规制。
应该与行为的可归责性进行区别的是表示意义(Erklärungssinn)的可归责性。如果人们进行此种区分,则所谓发出意思(Abgabewille)问题明显无法在《德国民法典》第105条中找到匹配者,而是该问题应落入缺少“沟通意思”这个范畴。基于对《德国民法典》第794条、《德国汇票法》第16、17条这些有价证券法特别规定的反对解释,以及按照《德国民法典》第130条第2款和第172条第1款中一般规定所确立的准则,存在沟通意思原则上应为意思表示的必要条件。同时,也基于这些规定,可得出“参与意思”这个进一步的要求。至于“表示意识”这个传统的概念,由于并非单纯的意识,而是参加法律行为交往的意思构成使人负担义务的决定性标准,从而“表示意识”概念并不恰当。另外,在此之外的效果意思也非必要。
结果是,意思表示并非纯粹的“对意愿进行的表示”(Wollenserklärung),也并非纯粹的“不带有意思的表示”(Erklärung ohne Willen)。毋宁是,意思表示的意义最好应被理解为效力性表示(Geltungserklärung):“对于意思表示按照其意义究竟何指的恰当表达,也即对表示意义的恰当表达应为如下:‘应如此发生效力’,或‘这样就对了’(‘Ita jus esto!’)。”〔97〕Larenz,Die Methode d.Auslegung d.Rechtsgeschäfts,1930,S.44f.;另外亦可参见Canaris,Die Vertrauenshaftung im dt.PrivatR,1971,S.418ff.;Stathopoulos,in:Festschr.f.Larenz,1973,S.357ff.(358ff.);对此的批判尤其见Bydlinski,Privatautonomie u.objektive Grundlagen des verpflichtenden Rechtsgeschäfts,1967,S.3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