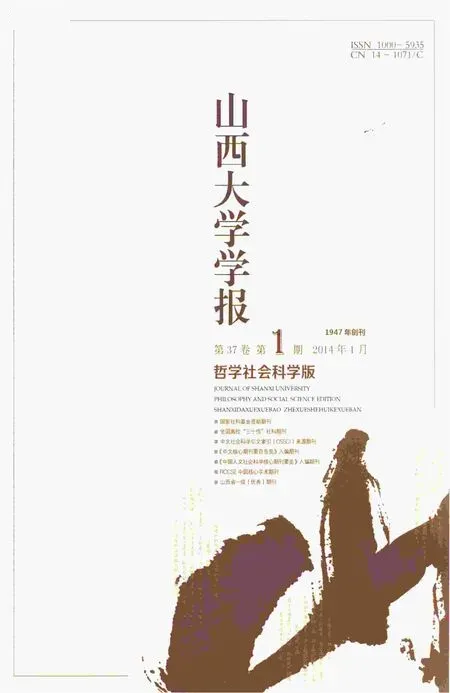试论令德堂书院在近代化转型中的艰难蜕变
张 莉
(太原理工大学人文素质研究与教育中心,山西太原030024)
令德堂书院创办于光绪八年(1882)。在晚清学制改革中,经历了三次艰难蜕变。“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上谕,各地书院改建新式学堂,民间祠庙之不在“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改为学堂,各地学堂广为编译西学书籍,以为肄业。[1]108时任晋抚胡聘之奏准将令德堂改为山西省省会学堂,按京师大学堂章程,实行中西并课。[2]15清末“新政”,再下兴学诏。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清廷颁谕,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为大学堂、府改设中学堂、县改设小学堂。晋抚岑春煊在令德堂基础上,合并晋阳书院,筹办山西大学堂。此时,为办理山西“教案善后事宜”,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拟在太原创办中西大学堂。后经磋商,将二者合并为山西大学堂中、西二斋。中学专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基本是令德堂的继续。1904年,提学使宝熙对大学堂中斋再次进行整顿,将高等科分为一二两类。第一类以文为主,第二类以理为主,增设了外文、数学、理化、博物、体、音、美等新课程。[2]15至此,“中斋的落后与西斋的进步由矛盾而统一了”[3]3。令德堂书院作为晚清山西教育改制的范例,在山西近代教育转型中可圈可点。
一 令德堂书院的创建
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抚晋,在山西省城太原创办了一所新式书院——令德堂书院。
(一)张之洞创建令德堂书院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重要的奠基人”。[2]14光绪七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四月(1882.1.3 -1884.5.22)任山西巡抚。
下车伊始,眼前的境况令张之洞怵目惊心。众所周知,光绪三四年(1877-1878)间,华北地区经历了一场特大旱灾,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连年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生灵涂炭,史称“丁戊奇荒”。山西尤为重中之重,时任晋抚曾国荃在奏文中称“大祲奇灾,古所未见”。[4]730
当时,李提摩太正在山西传教、赈灾,曾提出以工代赈、修建铁路、开发矿产、创办大学等建议,因大荒过后百废待兴,暂被搁置。张之洞接任后,特聘李担任洋顾问,又请他筹建洋务局,以实现这些建议。[5]1393-1394但令张意想不到的,是山西隳败的政局及颓靡的民风。他在写给朝廷的《整饬治理折》中描述:“历年以来,晋省公私困穷,几乎无以自立。物力穷匮,人才艰难,上司政出多门,属吏愍不畏法,民习颓惰以蹙其生,士气衰微而废其学,军律日即荡驰,吏胥敢于为奸。”①原注:王树柟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楚学精庐藏版1937年版,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第4卷,第530页。转引自《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张之洞抚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13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为扭转风气,培养兴办洋务所需各类人才,令德堂书院的创办便提上议事日程。
(二)《令德堂章程》及其主要内容
“令德”二字,最早见于《诗经》。《诗·大雅·假乐》载:“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意即歌颂周成王受人爱戴的高尚品德。书院以此命名,意涵不言自明。光绪八年(1882),在太原府署之北原明代晋藩王府宝贤堂②宝贤堂亦称志道堂、虚益堂,是明代晋藩王府书院。因刻书有功,嘉靖八年(1529),皇帝亲笔御书,赐名养德书院。旧址上,创办令德堂书院。至光绪十年,院舍建成,订定章程,聘请大儒王轩为山长,张于铸、杨笃、杨深秀为协理,作为一所培养新式人才的书院就此诞生。③关于令德堂的创办时间,学界有三种说法:光绪八年(1882)、光绪九年和光绪十年。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杨深秀传》中说“光绪八年,张公之洞巡抚山西,创令德堂”,主张光绪八年说。《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之《张之洞抚晋》也说:“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设立令德堂,‘选通省高材生肄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张文襄公年谱》第2卷,第67页)同书《杨深秀在山西》又说:“1883,令德堂书院创建于省城,正式开办在1884年5月。”2012年9月28日,山西省实验中学举行60周年校庆暨纪念令德堂书院创办130周年庆典活动,采光绪八年说。但《晋政辑要》卷二十三《礼制·学校六》有明确记载:“查光绪十年(1884)四月巡抚张札行冀宁道照得本部院并立令德堂,以为考课诸生经史古学之所。”准确讲,令德堂书院正式建立是在光绪十年(1884)。
《令德堂章程》共六条四十二目,大凡“延请主讲,编立功课,修缮杂支,如何筹款、动用,应用书籍如何购置、藏庋,课卷、日记如何定式、刊印,以及监院教谕如何责成稽查,兼差、分校如何责成教督,驻院高才如何体察勤惰,书役、斋夫、巡更、杂役如何添设约束”等,皆建章立制,使“略备夫规模,庶各得有准则”,“以期历久可行”。其创建旨趣,使“翩翩群彦,济济同堂,朝而考,夕而究,自强不息,极儒生稽古之功;日有课,月有程,久道化成副。”④以上引文均见《晋政辑要》卷二十三《礼制·学校六》。
令德堂书院的教学内容,仍以经史、考据、辞章为主,但增加了自主选学的部分。如《章程》规定:“诸生所习,或经或史,或《文选》,或《皇朝经世文编》,各择其性之所近而肄业之。”强调学生的读书兴趣和个人爱好。又如:“每日午至晚阅书,凡《说文》、《史记》、《汉书》、《通鉴》、《文选》、《古文辞》、《三通序》、《日知录》、《困学记》⑤《困学记》当指明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潜邱札记》,均可随意观看,但务看首尾。”给予学生自主选学机会,且以研习明清学人笔记为主,丰富了学习内容,开阔了学术视野,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学以致用的精神。
与之相应,在教学方法上,令德堂改变了以往死记硬背的模式,鼓励学生多做读书札记,勤写心得体会,常与教师沟通交流,以发挥潜质,启迪心智。如《晋政辑要礼制·学校六》规定:“诸生各立札记一本,每日将所得及所疑各条,书明原委,送协讲处加批……其有须面为剖析者,协讲亲身接见。”注重学思结合,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关于书院所用各种教材及参考书目,《晋政辑要》也有明确规定:“本院应需书籍,由浚文书局刊刻。暨由各省购到书籍内,每种由监院官承领一部,藏庋于院,以便诸生阅看。”浚文书局,由巡抚曾国荃于清光绪五年(1879)创办,是当时全省唯一一所官刻机构。令德堂所用教参,除由此刊刻外,还从省外大量购进各种西学书籍,既满足师生渴求新知的需要,也引导和促进了新思想、新学说的引进与传播。
对于学生的日常管理,令德堂也有严格规定,如“诸生如逢一、六考校日,未经告假无故不到者,每次记大过一次。记三大过者,扣除膏火银一两”;“诸生如有早眠宴起、出不请假、夜出归迟、喧哗讕语、听戏醉酒、秽弃字纸、冠履不整之类,有一于此者,均记一过,六过扣膏火银一两”等,以改革旧习,培养良好社会风尚。书院还实行较为开放的制度,准许晋阳、崇修二书院的肄业生来院听课,“有愿随课者,由监院另造名册,准其一体应课”,促进了士子间的交流。
总之,张之洞创建的令德堂书院,给一向闭塞的山西吹进了西学东渐的新风,也开启了山西新式教育的先河。书院既讲儒家经传,也讲新学西政;精研格致算学,讲求实事求是;提倡士子潜心治学,反对唯科举是务,对开启民智,传播西学,培养近代早期科技人才,尤其为近代山西新式教育的启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 令德堂书院的第一次改制
书院改学堂是晚清教育改制的重大事件。令德堂书院作为省城唯一的新式书院,自然成为改制的试点。胡聘之抚晋,拉开了晋省书院改学堂的序幕。
(一)胡聘之改令德堂为山西省省会学堂
胡聘之(1841-1912),字靳生,湖北天门人。光绪十七年至二十五年(1891-1899),先后出任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对山西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颇有知悉。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1896),针对山西书院存在的种种弊端,晋抚胡聘之和学政钱骏祥上《请变通书院章程折》,直击书院制度的痼疾:
查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2]15
奏折一语中的,代表了当时朝野上下普遍的诉求。在其看来,书院教学内容乏善可陈,“空谈讲学”、“溺志词章”、“专摹帖括”,“无裨实用”。久而久之,士子们便养成“注意膏奖”,追名逐利;“志趣卑陋”,唯科举是务的不良习气。
有鉴于此,他提出有较强针对性的四项改制措施:(1)裁汰书院学生名额;(2)修订原有书院章程;(3)改革课程设置;(4)另立水师、武备、船炮、器械及工技制造等类学堂。[2]15这道奏折后经光绪帝批准施行,成为晚清学制变革的滥觞。
晚清政治变革是书院改学堂的外部诱因。甲午战败,民族危机日趋深重,康有为等发起的“公车上书”,拉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废科举、兴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派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提议改旧书院为新学堂。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就曾上《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在京师及省府州县设立学堂,京师设大学堂,辅授西学,他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善也”,把矛头直指禁锢人才的科举制度。晚清正式改书院为学堂的举措,是在戊戌变法时期。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光绪帝颁“定国是诏”,“百日维新”开始。五月二十三日,颁《改书院为学校上谕》:
谕内阁即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至于学校等级,自应以省会之大书院为高等学堂,郡城之书院为中等学堂,州县之书院为小学堂。其地方自行捐办之义学、社学等,亦令一律中西兼习,并奖励绅民办学。
民间祠庙之不再祀典者,由地方官晓谕居民,以广造就,一律改为学堂。[1]108
据此谕,胡聘之奏准以令德堂为试点,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这次山西实行学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其一,改令德堂书院名称为山西省省会学堂;其二,改书院院长为总教习;其三,聘请1-2位精于西学的副教习,按京师大学堂章程,实行中西并课。同时,拟增设经济日课,令学生在政治时务、农功物产、地理兵事、天算博艺等四门中任选一门,以培养“明体达用”的“通才”。对那些“才能超越,新法通明,兼达时务”的学生,“咨送总理衙门考试,以备器使”;对学有心得、算法通晓者,派赴府属各书院传习知识,予以推广。看来,胡聘之等人对这次改制寄寓了厚望。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戊戌六君子”血溅菜市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落下大幕,清廷随即“下诏废各省学校”,拟议中的“山西省省会学堂”,又匆匆改回令德堂旧制。
(二)屠仁守致力于令德堂教学改革
之所以选择以令德堂为改制试点,还与书院最后一任院长、新式学堂第一任总教习屠仁守的努力密不可分。
屠仁守(1836-1904),字静夫,号梅君,湖北孝感人。他学识渊博,且中西兼通,被梁启超誉为“海内士大夫之巨子”。曾主讲于令德堂书院,后出任院长。光绪二十二年,曾代晋抚胡聘之草拟《奏陈变通书院章程疏》,提出“革书院旧习,凡辞章、考据不急而无用者,悉弃弗治”,主张开设天文、地舆、农务、兵事等一切有用之学;还主张广购外国书籍,使学生吸收外来文化,及时了解中外形势。
屠仁守思想开明,治学有方,使令德堂在各方面皆有明显进步。首先,教学效果良好,学生人数不断增加。时人曾论及:“令德堂诸生肄业者,初仅三十人,后广为五十人,续增为七十人,其后通省人才多出于此。”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一日,清廷下令褒奖:“以教士有方,赏山西令德书院院长、已革御史屠仁守五品卿衔。”对其教育理念与教学实践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其次,改旧书院为新学堂,为其后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的创办,培养了师资力量,准备了教学条件。山西大学堂中斋总理谷如墉,教习田应璜、张友桐、董化时等,都是令德堂早年的毕业生。再次,中西学并重,为近代山西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时人赞誉“通省人才多出于此”,或有过誉之嫌,但此时肄业于令德堂的学生,在其后山西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领域,成绩卓荦者不乏其人。
尽管这次改制似昙花一现,但风气已开,便在全省上下形成热潮,史称民间私立者尚纷纷,亦由民智已开,“不可抑遏矣”。[6]胡聘之、屠仁守改书院为学堂,为晚清山西教育改制增添了一抹新绿,为晋省社会转型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近代知识背景的新式人才,大大加速了晋省教育近代化的步伐。
三 令德堂书院的第二次改制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深渊,民族危机更趋深重。在义和团运动中,由于广大人民对外国传教士极端仇恨,加之时任山西巡抚毓贤执行了慈禧太后杀绝洋人的密电,山西教案尤为严重。为办理山西“教案善后事宜”,清廷急邀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赴并解决教案问题。
(一)李提摩太拟建中西大学堂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 -1919),英国基督教新教浸礼会传教士。字菩岳,威尔斯人。1866年由英国来到中国,在山东青州一带传教。1877年“丁戊奇荒”时,应上海洋人赈灾会之约,来山西赈灾、传教,曾在太原建立起浸礼会教堂、耶稣医院、小学和孤儿院等作为传教基地。维新运动期间,曾以“西学”占有者和“中国之友”的身份,参加维新派成立的“强学会”,聘请梁启超为其私人秘书,对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献计献策。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二十六日,李提摩太由上海到北京,向李鸿章面交《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提出:“共罚全省银五十七万两,每年交银五万两,以十年为期。但此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民知识,设立学堂,教育有用之学,使官绅庶子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①原载《光绪朝东华录》卷169,第4719页。转引自《山西大学百年纪事(1902-2002)》,山西大学纪事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页。李鸿章立即表示同意,把开办大学堂、延聘教授、安排课程、管理经费诸事交李提摩太全权负责。
按此章程,将在山西省城太原开办一所中西大学堂,以十年为期,期满交由当地政府自行管理。至于其他应办具体事宜,则交李提摩太前往山西与巡抚及地方士绅商议办理。因晋抚岑春煊对办学问题持异议,未与定议。后经反复磋商,至十月,方议定创办中西大学堂章程八条。
(二)岑春煊创建山西大学堂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因率部勤王有功,授陕西巡抚,不久调任山西巡抚。时逢“新政”,兴办学堂便成为其施政的重中之重。
在中外势力博弈中,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清廷再下兴学诏:“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州县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②原载《光绪朝东华录》卷169,第4719页。转引自《山西大学百年纪事(1902-2002)》,第2页。同时,明令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废除武试。此即是所谓的清末“新政”。
此时,令德堂校舍被天主教教士安怀珍、刘博弟等强占为临时教堂,书院被迫停办。根据清政府所下诏书,岑春煊奏准在原令德堂基础上,合并晋阳书院,创办山西大学堂,以文瀛湖南乡试贡院(今太原市儿童公园内)为临时校址,接受令德堂及晋阳书院学生复学,筹备开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准备正式开办山西大学堂,岑春煊委任山西候补道姚文栋为首任督办,谷如墉为总理,高燮曾为总教习,教务长、提调、管理员以及教习等,都已落实到位。同时将《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行办章程》奏折上报朝廷,待核准后施行。有关筹经费、建学舍、选生徒、订课程、议选举、司礼法等等,一一建章立制,为山西大学堂的开办,做好了充足准备。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公历5月8日),光绪帝朱批:“选举一条,著管学大臣议奏,余著照所拟办理。”③原载《清实录·德宗实录》卷498,第7页。转引自《山西大学百年纪事(1902-2002)》,第8页。山西大学堂正式开办并开学上课。
(三)山西大学堂设立中、西二斋
此间,李提摩太从上海“迭次催促,函电往返”,岑春煊即派洋务局候补知县周之骧赴沪与李商谈开办大学堂事宜。十月,周之骧代表山西当局、李提摩太代表耶稣教山西各教会在《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上签字,并在原拟合同上加入“此中西大学堂与晋省大学堂一样看待”。
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公历4月30日),李提摩太等一行抵达太原后,发现山西大学堂已正式筹办,便建议将山西大学堂与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同年五月初二,以山西官绅代表沈敦和、谷如墉为一方,以李提摩太、敦崇礼为另一方,正式签订《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原在上海签订的《晋省开办中西大学堂合同八条》即行废止。
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如是记述:
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一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一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千方百计反对建立实施西式教育的大学。……考虑到在同一所城市里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我与巡抚岑春煊进行了交涉,把两者合并为一所帝国大学。[7]290
根据新合同:将中西大学堂改名为西学专斋,归入山西奏设的山西大学堂,作为中国国家学堂,教授西学,由西人主持。原山西大学堂改为中学专斋,教授中学,由华人主持。至此,山西大学堂正式成立。
山西大学堂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中西合璧的典范,其办学理念、教学内容、管理制度等,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也是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集中体现。她的创立,是我国省立新式大学的开始,不仅开创了山西教育的新纪元,而且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2]20
四 山西大学堂中斋的再次改制
新成立的山西大学堂中斋,沿用令德堂旧制,不论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与传统书院无二致。未设大学专门分科,只设高等科。课程也只有经、史、政、艺四科。学生仍重经史考据,主要钻研十三经、前四史、诸子著作、《古文辞类纂》、《东莱博义》等,爱好算学者很少。光绪三十年(1904),新任提学使宝熙对山西大学堂中斋再次进行整顿。
(一)宝熙整顿中学专斋
宝熙(1871-1930),字瑞臣,号沉盦,满洲正蓝旗,河北宛平(今北京)人。历任编修、侍读、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总理禁烟事务大臣等职。光绪三十年出任山西提学使。
1902年和1903年,清廷又先后拟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后者亦称“癸卯学制”,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并在全国推行。根据该学制,大学教育共分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三级,设立在省会的大学堂,至少需设置三科才能成立。[2]21
按照“癸卯学制”要求,1904年2月,宝熙对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进行整顿。主要措施如下:第一,奏设监督,聘请其门生——湖北人杨熊祥充任;第二,取消总理职位,将总教习和副总教习改称教务长,提调改称庶务长,学舍监督改称斋务长;第三,根据新学制,对中斋的学科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较大改革,将高等科分为一、二两类,第一类以文为主,第二类以理为主,课程增设英文、日文、法文、俄文等四国外文;又增加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还增加了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又增加了图画、音乐和体操等许多新学科,对旧课程除保留经学外,其他科目都一律取消,尽量与西斋趋于一致。第四,除聘请了两名日本教习小金龟次郎、刚田外,又聘请了杨培根(英文教员,上海广学会毕业)、吴渭滨(法文教员,京汉铁路翻译)、傅岳棻(西史教员)等17名新教习,分别担任各科教师。另聘巡抚卫队长为体操教员,发给学生操衣、布靴和头巾等。同时规定,每星期上24节课,上下午各两节,星期日休息。服装也与西斋统一,即蓝洋缎操衣、操裤、皂布、操靴等。[8]19
至此,山西大学堂中西二斋才基本趋于一致。两斋并存,又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的实质。
(二)主要成就
经宝熙整顿后,大学堂中斋不论在教学管理,还是在教学质量上皆取得长足进步。光绪三十年五月,中斋选送首批30名官费生赴日留学。次年五月,又派出第二批官费留日生30名。在日期间,留学生学习刻苦,思想进步,创办报刊,积极宣传革命,多数加入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的骨干,也为山西辛亥起义的成功蓄积了力量。与此同时,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亦多有自备资金请求留学者”,[3]使避居一隅的内陆省份山西,成为清末北方留学大军的基地。本年八月,侯家巷新校址落成,全体教职员及学生迁入同一校区,两斋学生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尤其是中斋学生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往鄙视西斋学生的风气也一扫而尽。中斋学生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3]8
五 结语
西学的引进,打破了传统书院知识传承和知识建构的秩序,使书院的知识体系和知识传统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使过去相对游离于现实社会生活的书院,在知识结构上更趋“世俗化”,在知识传递上更趋“普及化”,这就为书院的废止埋下了伏笔。因此,书院自身在蜕变过程中,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下,一次次发生蜕变,使其一无容身之地。
晚清政府颁布的一系列学制,旨在顺时应变,提倡新学以求富求强,汇通中西以挽救传统。随着维新思想的深入和西学的传播,一些书院为求生存,不得不在教学内容上进行亦步亦趋的改革,在保留传统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同时,适时增加一些新学、西学知识,使中西渐渐融合。这一历程,反映了书院的进步发展,[9]92也表明书院在时代大潮裹挟下,不得不迈开近代化转型的艰难步履。
令德堂书院的艰难转型,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缩影,也是山西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写照。从创始之日起,就高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旗帜,明确以经史、考据、词章为教学内容,又以培养新式人才,发展“西学”为旨趣,充分体现了晚清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质。正是这种特殊身份,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山西教育近代化改制的试点。不论是戊戌变法期间胡聘之改书院为学堂,还是清末“新政”时岑春煊创建中西合璧的山西大学堂,直至宝熙对中斋再次进行整顿,前后历经了20年的时间,最终成就了其作为清末三所国立大学之一的地位。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重拾记忆碎片,解构令德堂书院在山西教育近代化转型中的蜕变历程,对于深入研究山西近代教育史、中国近代教育史,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诚如学者所论:“由书院转变而来的山西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如山西书院为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一样,为山西社会培养了一大批近代新型人才,成为近代化社会文明的中心,有力地推动了山西社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4]760薪火相传,任重道远。
[1]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十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赵立法.山西高等教育简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3]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精选[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86.
[4]侯伍杰,主编.山西历代纪事本末[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7][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M].李宪堂,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8]山西大学纪事编纂委员会.山西大学百年纪事(1902-2002)[M].北京:中华书局,2002.
[9]王欣欣.山西书院[M].太原:三晋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