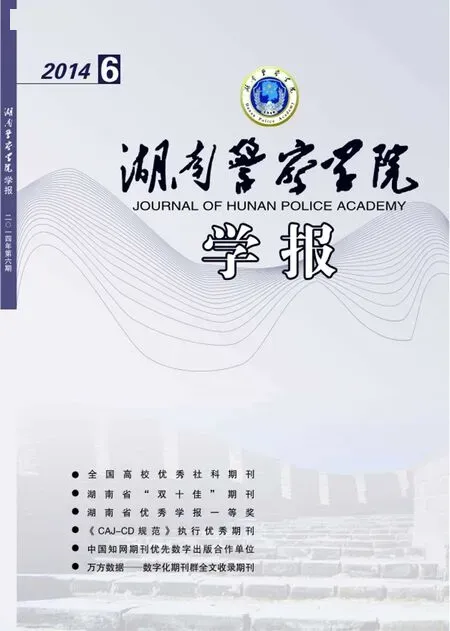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刘振华,蒋荣清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长沙 410138)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刘振华,蒋荣清
(湖南警察学院,湖南长沙410138)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传统调解制度长期发展的产物,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在国际上享有“东方一枝花”的美誉。但是,随着我国国情的发展变化和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不断出现,目前人民调解制度存在适用范围不够明确、法律效力不强、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和经费严重短缺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人民调解制度需科学界定其适用范围,进一步增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创新人民调解工作机制,多措并举解决人民调解经费和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以此促进人民调解制度价值和功能的实现。
人民调解;价值;适用范围;效力;队伍;经费;机制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主法律制度,是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1]。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积极化解社会矛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发展,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一枝花”。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多元和复杂,人民调解制度在新形势下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日趋凸显。因此,完善和创新人民调解制度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分析
价值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项制度能够得以长期存在与发展,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的调解制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它以法律法规、政策为依据,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促使矛盾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达成协议,节约了诉讼成本,推动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一)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其基本目标。它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以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为依据,注重“情、理、法”的有机结合,在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及时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实现定纷止争的社会效果。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已成为了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82万余个人民调解组织中的422.9万余名人民调解员扎根基层,贴近群众,大力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2013年全国广大人民调解组织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87.7万余件,化解纠纷943.9万件,防止因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4.9万余件,防止群体性上访9.9万余件,防止群体性械斗2.3万余件[2]。
(二)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社会效益
当前我国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途径有诉讼和非诉讼两种。诉讼在我国常被视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一种高度专业化、高成本的行为。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增多和公民对“诉讼万能”的迷信,上法庭讨说法成为了一种时尚,从而大量矛盾纠纷进入法院,使法院的诉讼案件数量呈几何递增。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和审结案件数量首次突破1,000万件,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已达1,220.4万件。可以说,中国已经开始步入“诉讼爆炸”的时代[3]。“诉讼爆炸时代”一方面造成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需花费大量财力、物力和精力,另一方面人民法院面对诸多案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需要审理,审判质量无形之中会下降,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或者群体性事件就会不断增加。非诉讼是当事人不通过诉讼形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它包含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和仲裁等多种形式。人民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积极疏导矛盾纠纷,防止矛盾纠纷扩大升级,减少矛盾纠纷进入法院,节约了诉讼成本;同时人民调解制度具有覆盖面广、形式多样、程序灵活、执行容易等特点,且无需当事人交纳任何费用,最大限度满足了社会和人们的现实需要,能让我国有限司法资源去解决重大的疑难案件,实现了司法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三)促进了和谐理念的发展
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植根于我国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当中,是一项以和谐为最高理想和目标的法律制度。我国古代的调解有“居间”、“和解”和“调停”等多种提法,也有乡治调解、宗族调解和民间调解等多种形式,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都贯彻着传统的“和谐”精神和教化原则。和谐体现在社会关系方面,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无诉,认为诉讼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和影响人际关系的极端方式。正如古人所云:“与宗族讼,则伤宗族之恩;与乡党讼,则损乡党之谊,幸而获胜,所损己多”[4]。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一旦出现矛盾纠纷坚持调解,反对诉讼,把社会和谐作为解决一切纷争的出发点。同样,在当今中国,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坚持平等自愿原则,充分运用法律法规、政策和伦理道德,采取规劝疏导、说服教育、协商和解等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既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又减少诉讼对抗造成群众人际关系的破裂,实现和谐共处的目的。因此,无论是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还是当今的人民调解制度,“和为贵”贯彻于这种制度的始终,促进了我国和谐理念的发展。
(四)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治国方略。但是,有些人一提到依法治国,就片面地认为法治社会只有依靠诉讼才能实现,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解决机制作为法治的对立物而怀疑或排斥。殊不知,法治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多元化的行为模式和谐共存的社会,必然要求提供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5]。因此,包括人民调解在内的非诉讼解决机制也是法治社会应有之义。首先,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项民主法律制度,《人民调解法》、《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对人民调解制度进行了规范,说明人民调解制度是在法律规范之内;其次,人民调解工作主要依据《婚姻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它是依法依规进行的,同时在人民调解过程中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处理当事人的矛盾纠纷,它也成为了法律法规宣传的重要形式;最后,我国法治建设中纠纷解决方式是多样的,它不仅包括通过诉讼形式,而且也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在内的非诉讼途径,只有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调处体系,才能达到社会矛盾纠纷能够准确、有效的化解。因此,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并不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旧衣服”,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催化剂”。
二、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多元和复杂,同时纯粹法治主义思潮对社会主流意识的误导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无论是立法上还是实务工作中都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模糊
目前,我国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在《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被界定为调解“民间纠纷”。何谓“民间纠纷”?它本身就十分笼统和模糊,理论界对“民间纠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常常被人们理解为发生在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纠纷。因此,许多学者把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公民之间因邻里、家庭、继承等基本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纠纷,当事人仅限于公民之间,内容局限于家庭、邻里等基本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已经明显扩大,内容也不仅是限于家庭、邻里等基本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实践中早就将因征地拆迁、医疗保险、移民补偿等新型矛盾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围之内,在北京、上海等地甚至将轻微刑事案件也纳入人民调解的范围,并且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社会效果。由此可见,我国在立法上将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界定为“民间纠纷”,造成人民调解适用范围不科学和不明确,使一些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在实践中能否适用人民调解带来争议。
(二)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不强
我国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不强,一直是制约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的瓶颈。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对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既然是民事合同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觉遵守,自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其法律效力不强。虽然2010年我国《人民调解法》规定了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明确了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在此基础上,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和2013年1月正式实施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对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进行了规范,标志着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勿庸置疑,这些规定在解决人民调解协议效力问题上是我国法制的一大进步。但是,这些规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不高的问题,一方面这些规定依然未能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本身以执行力;另一方面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人民法院应当对已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双方当事人”和“共同提出”这显然提高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门槛和条件,同时也给双方当事人留下反悔的空间,影响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也没有规定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审查程序的可操作性明显不足,造成人民法院对协议的审查也持观望的态度,在实践中使用率不高,影响了调解协议的效力。
(三)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未形成,队伍整体素质较低
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日趋凸显,作为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无论是组织建设还是队伍建设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兴行业场所不断涌现,这些新企事业单位、集贸市场、工业园区等领域和环保、医疗卫生等行业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还比较薄弱,有些新兴行业场所中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还存在着“断层”和“空档”现象,人民调解组织覆盖社会的网络尚未形成,造成一些新型社会矛盾纠纷无处可调。
长期以来,我国人民调解组织也一直在积极探索提高队伍整体素质的方法和路径,队伍的整体素质比以前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我国人民调解队伍还是存在队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以及法律知识欠缺等问题,制约了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据湖南省某区的统计数据来看,50岁以上的占27.6%,40-50岁之间的占47.7%,30-40岁之间的占20.6%,30岁以下的占3.9%;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8%,高中学历的占49%,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的占41.8%[6]。这种人民调解队伍的结构难以适应当前社会的新变化,面对复杂的新型的社会矛盾纠纷时不能做到依法调解、有效调解,阻碍了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人民调解工作经费难以保障和落实
虽然我国人民调解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应当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和办公条件。但是,法律规范中使用的是“必要”的工作经费支持,“必要”的本身就是模糊概念,不同的人对必要性有着不同的认识,造成人民调解工作经费支持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乡村财政十分紧张,根本无法保障人民调解经费,一些县级地方政府即使在当地财政预算中列入了人民调解经费,但是在具体执行中并没有严格按照财政预算予以拨付,造成一些人民调解委员会尤其是农村地区人民调解委员会没有固定、专门的办公场地,办公设施缺乏,调解工作经费短缺。据有关资料显示,湖南省某市2011年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平均每个司法所一年只有2,940元,平均每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一年只有205.7元,平均每个调解员一年只有4.6元[6]。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挫伤了调解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不利于吸收高素质的人才参加到人民调解工作中来,使人民调解工作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
(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协调
多元化的矛盾必然要求多元化、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必然要求内在的协调统一[7]。面对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纠纷,我国逐步形成了以诉讼为圆心,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为要素的多元化、多层次同心圆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这样的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基本上各自为战,在人民调解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对三种调解的受案范围和彼此如何衔接进行规定,未能实现有效的“三调联动”。同时,“人民调解也未能与诉讼实现有效衔接,有些法院在国家法律法规未建立相应制度的情况下,强制将某些矛盾纠纷案件实行调解前置程序,即使当事人未表示调解的意愿,在开庭之前也必须进行调解,这样既没有充分尊重当事人对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权,也对当事人的诉权造成了一定的侵害”[5]。
三、完善和创新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路径
人民调解制度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途径,成为了一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民调解制度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在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需对人民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效力和经费保障等问题予以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调解制度的功能。
(一)扩大和明确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
人民调解在当前社会复杂多变、各种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扩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成为必然。对于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为改变当前人民调解制度适用范围规定模糊的现状,建议采取概括式加列举式的模式来确定比较适宜。首先,在立法中应使用概括性文字来描述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同时扩展适用人民调解的主体范围,不仅仅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还应拓展到法人与法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有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这种概括式的规定,扩大了适用人民调解的主体范围,防止人民调解因主体的因素而被排除适用。其次,这种概括性的规定可能导致人民调解内容过于宽泛而在实践中难以把握,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社区调解和日本的《民间调解法》的做法,根据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实践对一些常见的民事纠纷采取列举性规定,将传统的涉及邻里、家庭、继承等常见、多发的民间纠纷,以及医疗保险、移民补偿、征地拆迁等新型社会纠纷罗列在“民间纠纷”之内。这种概括式加列举式的模式,既扩大了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又使人民调解的适用范围明确具体、便于操作。
(二)增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
增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促使人民调解协议的有效履行,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功能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增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就必须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一定的强制执行力。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一定的强制执行力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解决:一是降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条件。对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条件应降低,规定调解协议只要一方当事人提出司法确认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审查确认后即具有强制执行力。二是调整人民调解协议异议期的规定。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异议期为30日内,这是一种刚性规定。笔者认为,将人民调解协议的刚性规定转变为弹性规定,即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认申请,该日期适用诉讼时效延长、中断事由的规定。这样对人民调解协议异议期的调整,增强了协议的效力,有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履行义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强化人民调解的组织和队伍建设
1.强化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和网络建设。规范化建设是组织得以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队伍素质的重要措施。为推进我国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笔者认为,我国应在部分省市先行试点,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统一的《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建设标准》,各级地方政府、村(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单位等应按照规范化建设标准的要求,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队伍、业务、制度、经费和标牌标识等规范化建设;为及时妥善处理新型社会矛盾纠纷,地方政府应按照司法部的相关要求,加大新型行业场所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减少化解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的“空档”,形成覆盖全社会的人民调解网络。
与此同时,向社会借力,推动市场化、社会化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由于人民调解具有民间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因此,我国人民调解工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人民调解需求大、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设立一些类似于上海“李琴工作室”的市场化人民调解组织。必要时政府可以采取政府出资向市场购买人民调解服务的方式,及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同时,地方政府应重视社会力量在消除矛盾和解决纠纷中的重要性,成立人民调解协会,向社会借力,吸纳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大学院校师生、退休法官和检察官以及律师参与人民调解工作,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社会化方向发展。
2.建立人民调解员职业准入制度。为适应新时期我国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应将人民调解员作为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专业人员,按照地域、行业的不同要求,分类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员职业准入机制,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员应具备的条件以及只有通过人民调解员资格考试合格才能持证上岗,以此推动人民调解员队伍向职业化、专业化方向发展。据有关资料显示,河南省加快专职调解员队伍建设步伐,改变专职人民调解员配备不平衡状态,力争全省每个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配备5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每个乡镇(街道)配备2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至少配备1名专职人民调解员[8]。
3.建立人民调解员培训和等级评定制度。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是提高其素质和业务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提升人民调解队伍的整体素质,各级地方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制定人民调解员培训规划,加强人民调解员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人民调解的基本知识、调解技能和专项技能培训等方面;培训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经验交流、现场观摩、法庭旁听和专题讲座等。通过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提高人民调解员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技能,以适应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
为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可借鉴江苏、辽宁等地的做法,将人民调解员划分为调解员、助理调解师、调解师、高级调解师等四个等级,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等级评定主要依据人民调解员的政治思想、职业道德、学历、能力、工作业绩和遵纪守法等指标,确定每个指标的分值和权重,每年年底由县级司法机关组织,采取异地考核或者集中考核的方式对专职人民调解员进行一次考核,连续三年评比中获得优秀的人民调解员,除给予物质奖励以外,还应晋升一个等级。通过人民调解员的等级评定制度,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其专业水平。
(四)多措并举解决人民调解经费
经费保障是人民调解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和提高人民调解员工作积极性的基础。我国人民调解制度要健康长期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制度的经费保障问题,进一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多措并举解决人民调解经费。一是将人民调解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地方政府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司法部的规定要求,规范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开支范围、保障办法和经费管理;进一步细化《人民调解法》中经费保障的规定,以制度化的方式规定人民调解的财政预算,明确居(村)民委员会、企(事)业单位的支持范围。对于纳入了财政预算的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确保人民调解经费到位。二是建立人民调解“以奖代补”制度。为调动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在保障人民调解员的工资和购买相关保险基础上,建立调解案件“以奖代补”制度。三是设立“人民调解基金”。通过各种媒介加大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通过政府牵头发动社会力量筹集资金,设立“人民调解基金”,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财力支持。
(五)完善“大调解”的工作体系
2003年发源于江苏省南通市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中央领导称为“新形势下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新的伟大创举”,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大调解”工作体系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负责,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大调解新格局[9]。“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核心就是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做到“三调联动”,形成“三调”工作有效衔接,达到共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目的[10]。
1.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衔接。一般而言,治安、劳动等行政纠纷主要由行政机关组织行政调解来解决,人民调解则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由此可见,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不同,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存在诸多行政违法案件带来一些民事纠纷,如交通事故、工伤事故中的经济赔偿纠纷等。因此,将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有机结合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一是拓展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行政机关解决纠纷专业性、综合性等特有优势,依托行政机关的资源,在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的相关行政部门内设立人民调解组织,如在公安派出所、交警中队内设立人民调解室,及时化解发生在行政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矛盾纠纷。二是建立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的程序对接。一些矛盾纠纷虽然属于行政机关管辖的范围,但是由于行政机关工作任务繁杂,对一些行政调解的纠纷显得心有余力不足,因此,行政机关对于一些适合人民调解的纠纷,在进入行政调解前,应告知当事人可通过人民调解组织调处;人民调解组织也应加强协助行政调解的执行和善后工作,及时与行政机关沟通交流有关情报信息,防止矛盾纠纷的反复[11]。
2.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当前法院工作的重要原则,为贯彻调解优先的原则,《人民调解法》规定了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衔接制度。一是建立诉前调解机制。诉前调解是在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之前,由人民法院将纠纷引入调解程序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诉前调解既可以是法院邀请人民调解组织对相关适合人民调解的纠纷进行调解,也可在法院由调解经验丰富的法官和人民调解员组成专门调解组织,负责诉前调解。二是建立诉中委托调解机制。诉中委托调解是在案件审理中,对于部分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委托特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纠纷进行调解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诉中委托调解是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的一种新形式,它有利于解决矛盾纠纷,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1]彭芙蓉,冯学智.反思与重构:人民调解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5.
[2]周斌.去年人民调解组织化解纠纷943.9万起[N].法制日报,2014-02-28.
[3]解读“诉讼爆炸”的几个法社会学公式[EB/OL]http://www. chinalawedu.com/new/201211/qinyinjing2012111618150938907095. shtml.
[4]刘艳芳.论我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继承与改造——兼论现代人民调解制度的重构[D].合肥: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5.
[5]秦志斌.对人民调解制度重构的思考[EB/OL]http://wenku.baidu. com/link?url=jEPQGOQ7qrYLyRF_c6WXqS0qKtfbk2eOcLpctP WAdx2vVWRNd7xpnwg-FCEw96ACjOu94GguJ8uw_dB03c7aNm XLM4A9xyil2VpS1ZbtrIy.
[6]肖艳辉.湖南省人民调解工作的调查报告[EB/OL].http:// 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ZHN201301004.htm.
[7]孙青平,吴传毅.人民调解制度的现实困境及完善[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6).
[8]赵蕾.我省探索实行人民调解员分级管理[N].河南法制报,2014-03-18.
[9]张蓬,周望.人民调解的典型“模式”及其完善[N].法制日报,2013-06-26.
[10]杜建华,叶翔.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及其化解[J].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4,(3):100.
[11]陈光,梁俊菊,刘筱童.论转型时期民间纠纷的特点及解决机制[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6).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LIUZhen-hua,JIANGRong-qing
(Hunan Police Academy,Changsha,410138,Hunan)
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is a product from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our traditional mediation system and the first threshold of resolving social conflicts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which is dubbed the name“A unique flower in the east”internationally.Presently,however,with the changing of our country's content and the surging of new social conflicts,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displays some critical problems,such as uncertainty of application scope,impotency in the force of law,the relatively low quality of mediation team,and the shortage of funds,etc.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 our country,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needs to define its application scope scientifically,strengthen its law force, innovate its working mechanism,solve the problem of funds shortage with various measures,and construct the“great coordination”working system to realize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people’s mediation system.
people’s mediation,value,application scope,force,team,funds,mechanism
D631.4
A
2095-1140(2014)06-0031-07
2014-07-15
教育部201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多发型群体性事件预防与处置研究”(12YJC630165);湖南省2011年度社科基金课题“‘法制湖南’建设中我省社会矛盾纠纷‘本土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11YBB159)和2014年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法治湖南’建设中我省社会矛盾纠纷化解长效机制研究”(14C0416)
刘振华(1969-),男,湖南涟源人,湖南警察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治安管理和群体性事件研究;蒋荣清(1985-),男,湖南永州人,湖南警察学院治安系讲师,主要从事危险物品管理和安全防范技术研究。
(责任编辑:王道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