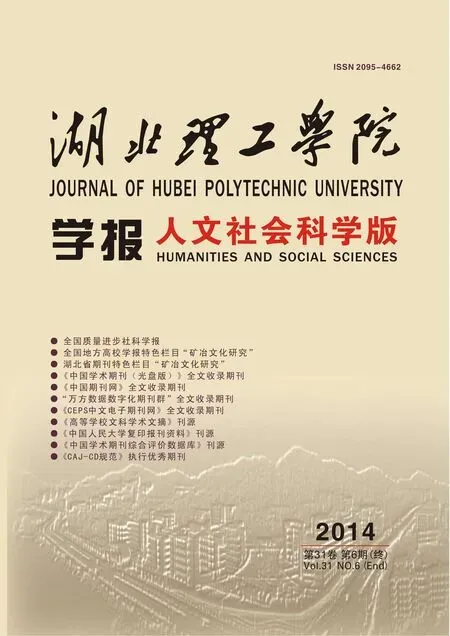康德:二律背反的破除与幸福的达成
刘 玲
(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1)
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纯粹理性批判》是对知性、悟性、科学、物质世界的探讨,《判断力批判》则是对情性的探讨,而《实践理性批判》乃是对意志、道德以及人的目的和自由的探讨,是关于人的终极问题或其实也是现实问题的论述。应该说,《实践理性批判》在三大批判中最具有实践意义,也是理解起来最有难度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要解决人如何幸福,怎样才能达至幸福的问题,也就是回答“我能做什么”的问题。而关于“我能做什么”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张扬,也是对人的权利即获取幸福的肯定。他首先分析了人获取幸福在理论上的可能性,然后分析了在客观上的必须性,以及在获取之后得以回报的保障性。在分析每一个问题的时候,康德一点点抽丝剥茧,扫清每一个问题所可能面对的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上的重重障碍,把每一个细小的问题都处理得干干净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康德主要是对感觉主义以及神秘主义的不足予以批判,也是他自认为的对西方哲学、宗教问题的一次反思和清算。虽然他最终将问题的前设和后撑都归于宗教,但在他看来,或许他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毋庸置疑,在思辨的道路上,康德和近代西方以前的哲学家相比,他所做的工作的严谨性、细致性、体系性是前无古人的。
康德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先发现命题,然后找出所发现命题中的矛盾之处,最后对矛盾之处予以二元辩证式的自我击破,然后提出实现某一目标的可行性办法。实践理性批判是目的论,研究的是人的目的,人的目的最终就是达到幸福,幸福地生活。在到达幸福旨归的路上,同样有多重二律背反,康德都一一化解了,最终(至少)在理论上到达了幸福的目标。应该说,《实践理性批判》所要探讨的就是如何幸福、怎样幸福的问题。实践理性所要阐述的就是人的道德实践活动所应该以及怎么做的事情,它既不是纯粹理性的思辨律,也不是判断力的想象律,他最终要在现实的地面研究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研究人最切身以及现实的问题。要研究人的现实问题,实际是研究人为什么要,以及如何理性地、有尊严地、有幸福感地活着的问题。康德作为一代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不遗余力、呕心沥血地探讨人作为类存在的意义,他没有瞎唱高调,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解决了我们在追求幸福、德行时所遇到的困惑以及问题。而对于幸福的探讨,恰恰也是我们当前生活实践中,亦或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对道德及其实践的细致而微、精准且用力的一种诉求。因此,康德虽然在此书中,或多或少在有些地方也表现出理想与实践的矛盾,也流露出某种无奈,以至于后来不得不以艺术的、审美的方式化解之而写作了《判断力批判》,把幸福推向了虚无缥缈,但《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诤诤之心以及“人是目的”的价值与意义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小觑的,甚至可以说,康德将此作为人类生活的信条,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在实践意义上申明了人的地位和价值、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在此,我们将沿着康德的思维一步步体察他是如何看待以及破解幸福道路上的二律背反的。
一、感觉与理性的二律背反
康德一直致力于消除感觉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弊端。感觉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一切从感觉出发,一切以感觉作为好恶的出发点,相信感觉、经验是求得真理的基础。感觉主义极具个体性,所以无法具有实践效用的普遍性,且很情绪化,不稳定,随时随地变化。对于道德而言,个体性的道德观显然不能作为一种出发点,好恶的漂移性更是有害。理性主义葆有理性,在道德实践中,理性主义者告知人们“应当如此”,但理性主义者并没有从本心出发,这同样也是违背个性的。康德希望道德律令应该既是从本心出发,又从理性出发,感性与理性交织在一起,合并在一起。人是目的,一件事情怎么去做,为什么要去做,都要以人的真实性、此在性为本。凡是以前者为本,以感觉欲望为本的,“都是依靠经验,而不能提供法则实践的。”[1]6从经验出发,既不可能带有纯粹理性,更不可能将一己之好变成普遍原则。那么,从所谓的理性出发,从德行出发呢,是不是更好一点呢?“但是建立在这些原理上的实践规矩永远不能普遍(有效),因为欲望官能的这个动机原是依靠在那永远不能假设为时时处处都指向同一对象的苦乐之上的。”[1]11同样如此,从德行出发获取的依然是快乐或不快乐的效果,要让理性成为一条普遍的律令,那又是一件复杂的工程,而理性主义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相反地,他们最终仍然借助了快乐或不快乐的原则作为向导,也就最终与前者殊途同归,沦为一样的效用。就是说,即使不介入感官,在实践上,理性主义也难以做到时时处处具有全方位妥帖的普遍性。应该说,后者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快感主义,这正是最浅表的也是康德所要破解的魔咒。同时,破解这样的魔咒也显示了纯粹理性的重要性。康德之所以一直在强调纯粹,在第一部著作前加注纯粹理性批判,在第二部著作前加注纯粹,而且在第三部著作的引论部分不惜篇幅重申加注纯粹的意义,其目的在于,他要斩断前人在研究问题时的不严谨,而且,之所以加注纯粹二字,在于强调抛开一切感性与个体理性的前结构,绝对不混为一谈来干干净净探讨实践道德的问题。或者,换句话说,他要将人看作一个理性的类存在,这个存在不为任何世间万象所左右、所摇摆,不以任何条件为转移,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这人应该像星空那样,一直在那里,不突兀、不造作、不矫情、不干涉。这里的纯粹,也在于说明,美德、德行或伦理实践是一个灵性的类存在区别于其它类存在的最重要的能力。如果人没有德行,没有美德,那么就跟兽类无异。
作为一个进化了几千年的类存在,本来或理应具备悟性、纯粹理性,也就是在认识论上,脑海里与生俱来就具备了判断能力,好坏善恶的能力,这是人的知性、悟性或纯粹理性本有的能力,或者叫做先验理性。康德批判了休谟的“白板说”。一谈到先验论我们并不能直接将其看作唯心论,在康德看来,先验即为“就有”,这既防止了懒惰者为自己寻找托词和借口的机会,也杜绝了一切野蛮主义、享乐主义的口号。康德的目的就是启蒙,所谓启蒙,是指将那种被历史尘埃所蒙蔽的东西重新唤醒、重新揭开。人的一生应该就是一个不断完善自我、不断完善德行的过程,而且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要把它当作本来就应当如此的作为。倘若在理性或悟性上认识到人有道德实践能力而不去实行,这算不上什么,但倘若认识到人有能力去实践却又以此行为能获取什么作为目的,那也不行。因此,所谓纯粹,就是表明实践理性在存在层面即认识论上是如此,在实践论上也理应如此,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是只就人这个个体、这个生物本身而言的。以此考量,就会发现感觉主义实际是感觉快乐至上的功利主义,虽然只是一己私利,但会导致人以自我为中心,而无法成为类中心。如果从理性主义出发,虽然表面上看似做到了“应当如此,也去做”,但摒弃了个人感受的作为是做作的、虚假的,也是非人道或非人性的,即便不是如此,大约理性有更强的目的,实则也是一种更为有力度的或者更为有害的实用主义。如果说,前者的危害还是一己私利,那么后者就是一种野心;前者是小害,后者则是大害。“那就仿佛在形而上学中班门弄斧的一个不学无术之人……”[1]9比如,一个没有多少知识、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他的生活不会影响到其它人,顶多就是自己享受没有文化的快乐或苦恼。但是一个有文化、高智商的人,他在理性、知性、悟性上知道知识之于他的重要性,并且也知道知识运用不当会犯罪,但他却恰恰运用知识为自己获取功名,甚至为犯罪所用,这就有害于群体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做的人,他的范围仅在自体内;而一个知道是什么,且知道怎么做,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利,并且可以既获取名,也可获取利的食利主义者,表面看来他也做了事情,但这种事情背后的目的不纯,表面看来也没什么错,也的确做出了贡献,就像中国当前的学术垃圾制造者一样,但这是一种伪道德、伪德行。因此,一言以蔽之,康德的纯粹,实际就是老子《道德经》里所强调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信与美的关系的辨析,是一种神与物游、两忘、坐忘的状态和思想。
由此,我们将进一步引出另一个二律背反,即古希腊罗马哲学派别中的二律背反,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主义,这个不妨看作是对感觉与理性二律背反的一个细节的注解。
二、伊壁鸠鲁和斯多葛主义之悖论
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都是探讨人如何活着,人活着的目的,怎样活着才会幸福的希腊化时期哲学流派,两种流派都认为人们按照他们流派的想法生活就能达成幸福。伊壁鸠鲁认为,人活着是受苦的,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痛苦与快乐在于个体的感觉,精神的痛苦与否大于肉体的痛苦与否,因此,一个人的德行很重要,德行是达于意义的途径。伊壁鸠鲁学派的本意大体也不是说追求享乐,在希腊化时期,他们其实是寻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享乐主义者。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伊壁鸠鲁的学说留下了很多弊端,后世的伊壁鸠鲁学说沦为享乐主义的说辞。这也是因为,伊壁鸠鲁学派从感觉出发,以感觉的快乐或痛苦为要旨,这就自然地留下了理论的漏洞,虽然他们也强调德行,但在时间的累积中,快感、感觉置换了德行。用精神的愉悦痛苦作为尺度,原是为了控制贪于肉体的享乐而导致的个体性,但伊壁鸠鲁的精神性尺度虽以知识的认知做保证,但最终难以成为强有力的普世性的依据,在实践上难以成为普世性的、或可操作性的条例,最终也就不了了之。作为人道主义者的康德,在探讨幸福问题时,当然首先从个体感觉出发,但并没有一味沦为个体感觉的享受,这是康德在批判以往哲学时,极力避开的。无论伊壁鸠鲁学派的初衷如何,即使它看起来并不是只要感觉、要精神,但最终没有达到经验与精神的完美统一,所以也就最终沦为了近似于后来的经验主义或感觉主义了,康德自然要去除这类观念的悖论之处。
斯多葛学派在人们看来似乎比伊壁鸠鲁高级,因为它的出发点在于伦理,在于精神,而且看起来优于前者,是高雅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斯多葛学派在认识论上和伊壁鸠鲁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实践论。在实践论上,斯多葛主张,个体小理性和宇宙大理性是统一的,人应该按照宇宙大理性生活,合于规律而达成自己的目的,要有德性的生活、理性地生活,但他们也指出以此未必带来幸福。伊壁鸠鲁以自我为出发点,我快乐我存在;斯多葛学派以他人为出发点。前者难以成为普遍性原则,而后者无形之中又忽略了个人的幸福。
两方来看,在原则上二者相差不多,从实际上虽有差异,但每一方的长处恰恰是另一方的短处,而这两者最致命的伤害,在于对待幸福的问题上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可供操作以及有保障性的实现途径,最终都只能不了了之。或者如伊壁鸠鲁一样只有目的,不讲手段,只是达到了个人的快乐,无法达到大爱和至善。“在德行方面,我们如果同伊壁鸠鲁一样只让德行所带来的快乐来决定意志,那么我们后来就不应怨他把这种快乐与最粗俗的感官快乐混为一谈了。”[1]9或者如斯多葛一样又不顾个人的感受,以大的目标为目标,最终也因为失去了现实根基而难以成功。虽然斯多葛是从理性出发,但他们的的理性的法度在哪儿?理性能否不以快乐或痛苦作为衡量的标准?理性对意志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些问题,显然在斯多葛主义那里是无法厘清的。因此,康德认为,“只有当理性自己就可以决定意志(而不为好恶所役)时,它才是那受感性所决定的欲望官能隶属于其下的一个真正高级欲望官能,而且它与后者确有差异,甚至还有种类上的差异,因而感性冲动只要稍微掺杂其间,就会摧毁它的力量和优越性……”[1]10显然,斯多葛学派没有就理性、实践法则的决定性功能予以说明,因此由于不确定与游离的规定性而最终和伊壁鸠鲁殊途同归。
上述两种流派应该都属于“福乐主义”。“福乐主义的伦理观把暂世福乐看成是人生和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有逸乐和幸福本身是好的、善的东西,那些招致痛苦与不幸的就是坏的、恶的,那么伦理上正确的东西就是那些有用的、能帮人实现暂世福乐与成功目标的东西。”[2]74康德实践理性的宗旨在于既不以个人享乐为能事,也不以空有的德行为至上。前者不具有普遍性,而后者又罔顾个人的幸福。因此,要达成最终的至善,就要消除这两者中最基本的二律背反。
三、本有与做作的二律背反
在处理了前面的历史中理论上的二律背反后,康德需要在现实的生活中解决个体实践中的二律背反。在个体实践中,我们的行为受制于我们的心理,我们的心理反作用于我们的实践。
一个人要善,必得发自内心,而且没有反思性,且不能具有反思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做了善事之后,也不能耿耿于怀、斤斤计较、不停反思。柏拉图在论正义的时候,说起正义有三种,一种是正义,一种是不正义,一种是“看起来”正义的所谓正义[3]314-317。看起来正义的人,做事情时他也愿意做正义的事情,但是他在权衡利弊,或者在做了之后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正义之人,是行正义之事。表面上看,这样的人做事的确是中规中矩,正义的,但并没有发自本心,而是在考量了于人于己无害的情况下做了这些事,他本身也希望得到别人好的评价。康德认为,这种情况由于不是发自本心,也未必快乐,而且也并不是自律,而是他律。康德所要求的是从自我出发,不是考虑到福利、利益才去做。与第二点相呼应的,是指有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在做了某件事后也并没有什么害处,康德也认为不妥。他认为即便是看起来是无害的,但实际上也是有私心的。另外一种相反的做法就是热衷于谋求利益,比如大张旗鼓地、狂热地做正义之事,就是我们所说的作秀,因为从中他能得到荣誉的快乐,这既有本有的情况也有做作的情况,我们平时所讲的会来事,会做人就是如此,但你又找不出他的破绽,他所做之事的效果也是好的,看起来也是正义之事。但在康德看来,这样的行为就是做作,因为它指向利益。做正义之事,既不自知,也不想自知,且自己幸福快乐,这才是至善的本义。如果一条准则只是适应于个人,且在做的时候很清楚它所带来的利益或好处,那这样的正义就不是美德了。
我的理解是,康德在此要表明的是,人的美德正如苏格拉底所说,是教不来学不来的,如果能教能学的就不叫美德,不叫德行。既然如此,康德这里所说的,应该是一颗赤子之心,就像郭明义做善事,不是从某个方面着手,也不是考虑做了之后的效果,而是觉得人应该那样做,恰如中国文化中”不以善小而不为”的做法。就如父母对子女之爱,出于本心,是最自然、最本能也最没有任何私心的作为。换个角度来说,正义或美德是不可分析的,真正意义上的正义或美德或者善是自在之物。虽然善或美德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但这些东西又似乎是先验的,就是说,作为类存在的人应该具备那样的素质,然后在实践中得以显示出来才是完美的善或美德。而作为类存在的善一定要是一条普遍法则,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法则,它是不能思量的。一思量总是从利益出发,从利益出发与感觉主义是一致的。而本有的善是指没有任何反思、任何思量,没有利益计较,没有感觉经验,甚至在善事之后也没有任何感觉的一种行为。康德作为人道主义思想家,既反对任何非利己的作为,也反对任何只是专门利己的行为,即使在对于集体行为是有益时,但不合人类普遍的原则也是他所排斥的,康德所要求的善行既要从个人出发,是个体的行为,又应是所有存在者的行为。
四、手段与目的的二律背反
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善的实施过程中,有时会存在着手段与目的的二律背反。有时手段是不道德的,但目的是纯良的。康德举了个例子,有个人,很会做事,既为人精明、巧于牟利、勤勉不息、善用机会,又深明生活雅趣,又不奢侈浪费,人际交往也很高雅,似乎在表面看来是个十全十美的人。但在手段上,他却毫无顾忌,中饱私囊,且能做到不被人发现。康德认为,如果一个人做事果真如此,那就是疯了,根本就不可能。但其实并不是不可能,在生活中,还是存在这类现象。比如为善,有些人做慈善,他的确做了慈善,但他做慈善的钱却是他在另一个行业以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得来的,那么这样的慈善最终让人难以接受。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即手段并不会危害他人,但却伤害或牺牲了自己,比如卧冰求鱼等中国古文化中所崇尚的孝子的行为,就不能成为普遍可效仿的手段,所有伤身害命的手段,即使它显示的是良好的目的,这样的手段也不足取,不可要。第三种情况,是“舍小家为大家”的行为,即舍弃自家的利益,为了大家的利益,这种行为康德也不认同。第四种情况,是虽然目的不好,但手段却是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与愿违,比如家长疼爱小孩,各方面都很好,但最终的结果却使得小孩生活能力很低,成年后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手段与目的的二律背反,在生活中总会出现,我们既不能要不顾手段的所谓效果、目的,也不能要只顾手段而不管目的的方式。康德认为美德或人类的完美既要高尚的手段,也要完善的目的,在行使自己权利的过程中,既要爱自己,也要爱他人,所做的事情,既要符合自己的利益,也要符合他人的利益。或者说,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找准平衡点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在局部利益方面是能达到手段与目的的齐一,但我们认为康德所说的手段和目的应该是普世主义的二者的统一,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基督教意义上来说,行善事的目的是达于上帝,与上帝齐一,在上帝的关怀下求得灵魂和肉体的救赎,手段是在现世,是个人的自律表现、个人的善行善言,这一点我认为清教主义较为接近或符合康德的意愿。清教主义者在职业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积累下财富后又重新造福于社会,以实际的行为(手段)完成对上帝(目的)的信仰,而且在这一手段与目的的交合关系中,主体应该是幸福快乐的,就是说这样做了,而且乐在其中,这样就可以达到完善。这样,就既符合感性的需要,又符合理性的精神。但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清教徒。近代社会以来,人的欲望的膨胀与发展导致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人类的野蛮与灾难沉重打击了内心的信仰,不要说清教徒了,成为一个正常的人都成问题,那么,从人类发展的长远来看,手段与目的二律背反的解除是一项长期的事情。
五、德行与幸福的二律背反以及悬设
如果我们既能在理论上破除二律背反,又能够在实践中实现善举,那么还有什么是障碍呢?康德认为,人不仅要有能力,达意愿地做德行的完善者,也要有资本享受美德带来的幸福,不仅现世要有幸福,而且来世也会幸福。然而,关于幸福的达成却又是一个纠结在二律背反中的现实难题。
早在柏拉图那里,他就看见了德行与幸福之间的悖论性关系,而这悖论性关系就是冰冷的现实。在当时的讨论者们看来,有德行的人未必幸福,而没有德行的人未必不幸福。这其实就是社会现实的必然。在康德那里,他没有再纠缠这个问题,他认为人应该,而且配享受德行所带来的幸福,但他也认识到,这些在现世是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为了解决这样的悖论,他悬设了三个概念,第一是自由,第二是灵魂不朽,第三是上帝。悬设了自由,在于表明人有驾驭自己行为的能力,人有自主的判断力,意愿、行为是统一的;悬设了灵魂不朽,说明今生未完成的永生都可以不断完善;悬设上帝的作用跟柏拉图一样,说明我们可以保证德行的完善者能有享有幸福的承诺和保障。其实,严格讲来,自由并不是一种悬设,因为自由本身就是人所具备的能力。但真正的自由是指不受任何“经验、情欲、利害关系、效果有无等条件的制约”的自由。所以所谓自由,就是先验的、发自内心的一种绝对命令,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是由于我们必须假设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的自由。”[1]128所谓绝对命令就是无任何条件地、不沾染任何因素的一种直言判断。自由虽然是直言判断,但有自由,就表明并不忽视经验,也有纯粹思辨理性的依据,就是说,在行与思上都畅通无阻,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后,保证了人追求幸福的先天性,幸福本身也是自由的一个方面。但幸福并不是一个常量和定量,就是说,幸福的达成却是受制于各种因素的,于是必须得给幸福一个保证,那就是灵魂不朽(亦即人的不朽)和上帝才能保证幸福的达成。而灵魂不朽和上帝的存在在康德这里也是一个直言判断,德行加幸福才是至善。“‘追求幸福’必然是每一个有理性而却有限的存在物的欲望,因而也是必然会决定他的欲望的一个原理。”[1]10上帝的存在保证了美德与幸福的神圣性和威严性,也就是说,二者任何一方都不是随随便便、可有可无的,只有德行与幸福结合在一起,才是至善。具体来讲,德行是至善的条件,幸福是人的需要,人既能完善德行,又能享受幸福,也配享受幸福,才是至善和圆满。“努力修德与合理祈福原非两相差异而是完全同一的行为。”[1]106至高无上的圆满乃是一种神圣性,可是任何一个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是无法达到神圣性的,“但是意志和道德法则的圆满契合就是所谓的神圣性,而这乃是感性世界中任何有理性的存在着在其生存期间的任何刹那多不能达到的一种圆满境界”[1]118。因为上帝在彼岸,不在此岸。“可是它只能在趋向那个圆满契合的无止境的进步中才能被发现……”[1]118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能是无止境地趋向于那个圆满的境界,而不可能达成那个境界,而且这种趋向的条件在于“灵魂不朽”。康德在此悬设灵魂不朽避免了隐含的悖论,即避免了理论的自大与宗教的狂热,亦即很理性地告知人们总是有个界限在那儿,那个界限不是盲目地叫嚣或陷入宗教迷狂就能达到的虚假的圆满,这也是需要我们坚决制止的。
总而言之,自由说明了人有能力也应该去追求道德的完善;灵魂不朽,表明人总是会达成道德的完善;上帝的存在说明人在完善自我以后有资格有条件去享受幸福。至此,所有的二律背反都处理殆尽,也就在理论和实践上达到至善和幸福。
六、余思:悖论“解决”之后的现实意义
至此,我们可以认为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因为有了那三个悬设,或者更主要是灵魂不朽和上帝这两个假设。当然,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否定这两个悬设,但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今天,我们人类依然为许多现实问题所困扰。有些谜团一样的事故、事件无法最终为我们带来答案,有些事情并不以我们的人力所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且不管悬设本身所悬设的对象其真伪性如何,我们只要知道,悬设保证了一种戒尺,或一种界限的存在,它要昭示我们的是: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应该敬畏那些我们人力无法达到的领域。
[1]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关文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白舍客.基督宗教伦理学:第一卷[M].静也,常宏,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二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