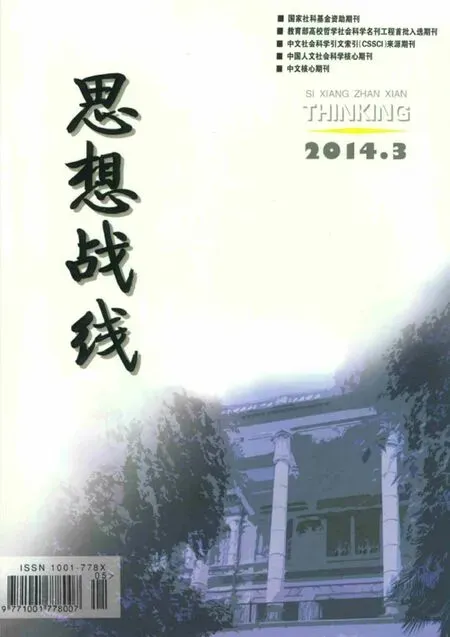权力的诞生是否天然?
——对皮埃尔·克拉斯特权力概念的研究
许轶冰,[法]波第·于贝尔
20世纪60年代初,受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和阿尔弗雷德·梅特劳(Alfred Métraux,1902~1963)等人的影响,法国学者皮埃尔·克拉斯特(Pierre Clastres,1934~1977)将其研究领域从哲学转到了人类学,开始对南美洲中部巴拉圭境内属印第安人的瓜拉奇人(Guaraki)的部落进行实地考察。1974年,他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研究员;1977年,他成为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第五部研究主任。
虽然皮埃尔·克拉斯特早年就因车祸去世,然而他在西方学界至今仍享有盛名。这主要得益于他所提出的社会不需要国家,即国家与社会并非不可分割的理论。这一理论建立在他对国家是社会最终成就的进化论观点的批判基础之上。根据皮埃尔·克拉斯特的理解,权力的存在是所有社会的共识,但是人们仍然希望个体的自主性能够在社会上得到保证,因此,社会实际上是由众多抵制专制权力的权力构成,而国家是通过以法为基础的等级制度被建立在那些依靠自然调节体系已然不能发展的社会中。比如,根据皮埃尔·克拉斯特的观察,中美洲人数众多的社会不同于非洲亚马逊的那些人数较少的社会:前者有国家,后者只有酋长制(chefferies)部落;而酋长制的社会结构不允许部落的头领将其威信转化为权力。因此,这后一种社会实际上是自愿拥有非国家结构(la structure non-étatique),而不是由于它们的文明或政治体系尚未进化到具有国家结构的结果。皮埃尔·克拉斯特还认为,部落间的战争也是一种自然消减人口的方法,这亦妨碍了国家结构的出现。虽然皮埃尔·克拉斯特的无国家社会理论如今已经成为现代西方人类学经典,但是国内学界对其人其论仍旧鲜有认知:国内既无其著述的中译本,也无对其理论深入细致的梳理研究。本文不揣冒昧,将尝试考察皮氏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权力”,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权力的概念
(一)原始社会与权力
西方的人类学家,尤其是欧洲的人类学家对于部落的研究总是充满兴趣。他们往往认为,通过对人类社会从原始简单向理性复杂进化过程的了解,人们就能更好地认识当下社会并对未来社会作出预测,即“经程—前景(parcours-perspective)”逻辑。他们中的一些人重点研究了非洲的“原始社会”,即人类学通常定义的,以亲族关系为基础,人口较少,经济生活采用平均主义,社会秩序依靠家长和传统来维持的社会组织类型。这或许是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毗邻,或许是由于研究内容上的契合。可无论怎样,正如非洲历史学家基-泽博(J.Ki-Zerbo)所言:
人们相信一些人类学家的做法,认为借助对古代集体性,如国家、无政府的社会等的分类就可以对当前社会进行预言。然而,如果将此种做法放到非洲,即要对整个非洲社会进行归类的话,那么归类的结果将是不可穷尽的,因为非洲的每个社会都与其他的社会不同,如此的分类只会造成武断和受限定的结果。不存在两种状况的同一或不同事物在细节上的完全相似。[注]Joseph KI-ZERBO,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frique,Ouvrage collectif,éd., Paris:Présence africaine / Edicef / Unesco,1996,p.175.
皮埃尔·克拉斯特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这样的归类实际上是用方法的惯例取代了思想的进取,与认识或研究本身无关。归类掩盖了现实的内在复杂性。这种对于归类的批评其实也是对当时流行的理性主义方法论,即对“通过分解、分析和分类,将一切纳入某个可供解释的范畴”[注]许轶冰:《米歇尔·马费索利和他的后现代性》,《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的做法的批评。稍后不久,在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首先提出了“后现代性”的概念之后,这样的批评就成为创建新的方法论,即不再强调纯粹理性,而是强调理性与非理性结合的思想的重要参考。比如,研究后现代性的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就曾在其《部落时代(LeTempsdestribus)》(1988)一书中多次引用类似这样的批评意见。
皮埃尔·克拉斯特主要考察的是南美洲的原始社会,尤其是印第安图皮-拉瓜尼人(Tupi-Guarani)的部落文化。该文化的典型性表现为其酋长制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深入观察,皮埃尔·克拉斯特提出了权力的问题。长久以来,在各种共同体,如部落之中,总是多数的人服从少数的头领,因此服从似乎就成了人们最熟悉、最擅长,也是最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行为,人们亦就误以为人本身具有服从的天然需要。或换言之,权力是天然的。皮埃尔·克拉斯特对此提出了质疑,而这样的质疑在当时亦受到人种学对于政治空间中权力研究的影响。当时的人种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非洲、三美洲、[注]指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亚等地区的古老社会(les sociétés antiques),他们对于“古老”的定义主要基于两个条件:书写的缺乏(l’absence d’écriture)和以生存为导向的经济(une économie de subsistance)。
(二)权力的类型学
许多人类学家会根据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地位对原始文化进行程度高下的类型学区分;也就是说,政治权力越集中、权力结构越清晰、权层关系越紧密,该社会的文化水平也就越高。然而,政治权力可以接近于零,这是因为在一些以基本生存为导向,生活条件受到限制的封闭的小社会中,人类群体已经超越政治权力。由此,权力的实现实际上涉及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命令—服从(commandement-obéissance)”。
一般的观点认为,有国家的社会不同于没有集中权力的社会:
没有集中权力的社会无视社会阶级的划分和职业的区分,它们被迫接受简单的生存性经济。这种经济让它们付出了重大努力,却没有让它们从社会条件的束缚中获得法律。为了生存,它们必须忍受这些条件的束缚,既不能去修改,也不能去选择。简言之,相对被认为是已经达成目标,即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其余的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都将是缺乏和失败的社会。[注]Michel Alliot,Le droit et le Eervice Public au Miroir de l’anthropologie,Paris:Edition Karthala,2003,p.197.
然而,从经济和权力本质两个角度,马歇尔·萨林斯[注]美国人类学家,主要研究斐济和夏威夷住民。(Marshall Sahlins)和皮埃尔·克拉斯特推翻了这种带有种族中心主义倾向的观念,“他们不仅证实了这种观念的错误,并且指出这样的错误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原始社会的认识及态度”。[注]Michel Alliot,Le droit et le Eervice Public au Miroir de l’anthropologie,Paris:Edition Karthala,2003,p.197.
首先,是权力与统治之间的关系。
很早以前,马克斯·韦伯就将势力,即权力[注]韦伯的“puissance(势力)”指的就是“pouvoir(权力)”;我国学界亦将韦伯的“puissance”直接译为“权力”。与统治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81页。而统治,“应该叫做在一个可以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或者: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因此,不是任何形式的对别人实施‘权力’和‘影响’的机会”。[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8页。这也就意味着,权力实际上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之上,而统治“在具体的情况下,可能建立在服从的极为不同的动机之上:从模糊的习以为常,直至纯粹目的合乎理性的考虑”。[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8页。另外,统治必须以权力关系被纳入合法的范围内为前提;也就是说,统治实际上是通过人们对它的忍受(subir)才被接受(accepter)。那么,人们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产生哪怕是“最小量”的服从意愿?人们又怎样能够自愿地同意服从他人或其他的一些人?
根据韦伯,人们具有4种服从原因:(1)基于习俗——因袭社会势力的自然表现;(2)基于情绪动机——对待认知内容的特殊态度;(3)基于物质利害关系——使起积极变化的因素;(4)基于思想动机——对于目标是否合乎理性的预期。[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8页。韦伯认为,基于习俗和物质利害关系是现实中最常见和最重要的原因,然而“习俗或利害关系,如同结合的纯粹情绪的动机或纯粹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一样,不可能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的基础”。[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39页。于是,为了获得统治或权力的稳定性,人们就产生出对于合法性的信任要求。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统治实际上表现的是一种建立在人群之中的信仰关系。
其次,是权力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在尼采生前未能完成的《希腊人的国家》(L’ÉtatchezlesGrecs,1872)中,这位伟大的哲学家认为,国家具有两种略显悖论的用处:(1)国家能以好的方式促进个体的社会化,建造城市,成就可能;(2)国家能够孵化和保护各种“天才(génie)”。[注]Rogério Miranda de Almeida, Nietzsche et le Paradoxe,Strasbourg: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1999,p.34.对此,巴西学者罗基里奥·德·阿尔梅达(Rogério Miranda de Almeida)评论到:“这些都表明了国家的必要性;倘若没有国家,大自然将无法通过社会的策略获得天才们释放出的光亮。”[注]Rogério Miranda de Almeida, Nietzsche et le Paradoxe,Strasbourg: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Strasbourg,1999,p.34.而国家,既是权力的代表,也是暴力的象征。
实际上,无论是韦伯、尼采,还是当代的人类学家,他们都认为权力的存在和真实在于暴力,暴力因而成了权力不可或缺的谓语。比如,在一篇名为《政治作为一种职业》(PolitikalsBeruf)的论文中,韦伯认为,国家权力“拥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地位”。[注]Daniel Warner,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Boulder: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1,p.9.然而,在皮埃尔·克拉斯特看来,倘若以这样的认识作为类型学的考察标准,那么美洲新世界,尤其是中美洲的部落就只能被看做是“前政治的场域(le champ pré-politique)”了,因为此种类型的社会都是政治权力为零的社会。或,换言之,“权力—暴力”的共识在中美洲的无国家社会中不具意义。根据他本人的观察和其他学者们的描述,皮埃尔·克拉斯特指出,如果出现了一些对于印第安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事情,他们的思想就会自动给出一个条理或者要求遵守一种秩序;除非是特殊情况,如战争,一般情况下,不会有暴力的发生。
(三) 另一种分类
人类学家曾对人类社会进行过各种以类型学为基础的考察研究。类型学,是一项特殊过程,从经验上获得可校检的单位,即类型,从而作为之后的研究基础。如前所述,欧洲的人类学家尤其研究了非洲的部落,然而英国人研究的非洲社会类型可能适用于黑色大陆,却不一定能够适用于美洲大陆,因为在北美的易洛魁人(Iroquois)的酋长和非洲最小游牧部落的头领之间尽管没有本质的区别,社会本身却不完全相同。当学者们考察这些古老社会时,他们发现这些社会共同、也是重要的特征是:人们不是在生活(vivre),而是在生存(survivre);换言之,由于技术和文化的缺乏,这些社会无法生产多余,它们的存在因此就成了一场与饥饿所进行的无休止战争。通过对这些不同社会的类型学分析,皮埃尔·克拉斯特给出了自己的划分,他认为:(1)社会可以被分为两种类型:权力社会和无权力社会;然而,政治权力是普遍存在且内在于社会的,它的实现亦可分为两种类型:强制权力和非强制权力。(2)作为强制的政治权力不是真正的权力类型,它只是一种特殊情况,只有在某些相应的文化领域,它才会有具体的表现。(3)即使在政治体制缺席的社会,政治也在场,权力的问题由此被提出:不是在煽动重视不可能存在缺席的虚假意义上,而是在某种事物的确存在于缺席之中的意义上。[注]Pierre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2003,pp.20~21.因此,皮埃尔·克拉斯特进一步认为,这样的政治人类学实际上是广泛性而非地域性的研究,应当注意的重大问题有两个:(1)什么是政治权力?或换言之,什么是社会?(2)非强制权力如何或为什么能够过渡到强制的政治权力?或换言之,什么是历史?[注]Pierre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2003,p.22.
二、政治的组织
(一) 原始社会的二选一
问题回到政治权力。事实上,皮埃尔·克拉斯特在两种不同的见解中完成了他对原始社会政治权力的认识:第一种见解认为,相对实际存在的政治组织形式,原始社会缺乏政治权力。这是因为组织机构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在执行方面的显明和有效性,它的缺乏会导致社会对政治权力运行本身的排斥。因此,这样的社会往往会被认作是停滞在某历史阶段的前政治社会或无政府主义社会 ;第二种见解认为,少数的原始社会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无政府主义,人类社会的先进政治形式,即政治体制已经开始在这些社会中生根发芽。然而,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观察到,早先的权力缺乏亦已转变为权力过剩,政治权力开始走向了专制主义或者暴政。简言之,根据皮埃尔·克拉斯特,原始社会的政治权力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要么体制的缺乏带来无政府主义,要么体制的过度带来专制主义或者暴政;而且,所有的原始社会都处于这样的二选一的状况中。
(二)头领角色及其特征
继而,是头领。不管是第一批抵达美洲的巴西探险家们,还是随后而至的人种志学者们,他们都注意到了印第安人头领几乎不具任何权威的显著特点。政治功能在这些部落群体中没有太多明显的表现,只是在较为细致的方面,部落成员之间才会有所区分。事实上,在多数印第安人的社会之中,社会阶层与权力的缺乏正是其社会政治组织的重要特征。有些社会甚至没有酋长制。比如,印第安希瓦罗人(jivaro)的语言中没有表示头领的词汇。由此,没有实现手段的权力是什么?由于不具权威,头领又该如何定义?基于进化论的认识传统,人们迅速地意识到在这些社会之中,有些事情、情况等,应当归因为社会的特质;那么,是否只是因为这些社会没有办法,或没有智力去发明那些诸如现代社会的可靠政治形式呢?通过对于印第安人世界中社会运行的观察,皮埃尔·克拉斯特总结出了印第安人酋长制头领的3个基本特征:(1)头领是投身创造和平的人,也是族众事务的调解人,军权和民权的常规性分离证明了这一点;(2)头领在财富方面必须是慷慨的,他不能拒绝部落群众对他的无休止索要;(3)作为头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必须是一个好的演说者。[注]Pierre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2003,p.27.
首先,头领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酋长制头领的常规工作是计划经济行为和组织群体仪式,但是头领没有决定权,他不能强制性地开展工作。若是不能与部落群众的意愿相联系,他的工作就会遭到社会的抵制。因此,头领必须深入部落去了解群众的想法和需要。他只是部落的代言人,仅有建议权。然而,当部落内部发生影响和平的中断或危机时,权力干涉会被唤醒;与此同时,拒绝或反对的意见也会出现,而此时的头领将无法克服他所需要面对的情况。
其次,头领的数量可以不只一个。酋长制的头领通常会由两个不同的人来担任:一个作为战争时期的头领,一个作为和平时期的头领。这也就意味着,部落社会有时会存在两种权力:军事权力和民事权力。战争时期,头领掌握重大权力,有时甚至是对全体士兵的绝对权力。当和平回归后,战时的头领将失去所有的权力。因此,强制权力类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如全体成员需要面对外部威胁时才会被集体(社会)所接受。普通权力,即民事权力,建立在一致意见的基础之上,而非强制。因而,此种权力具有深刻的和平性质,其职能也是和平的。和平时期的头领负责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保护部落成员间的和睦相处。他应当缓息纷争、协调差异。他不能运用强制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他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按他的要求做事。即使他想这么做,他的想法也不会被集体所接受。他惟一可以使用的就是他作为头领的威望(le prestige),而威望亦主要来自于他平日的公正和他合理的语言表述。简言之,与其说和平时期的头领像是能够判断对错的法官,还不如说他更像是寻求和解的事务调停人。
第三,头领的慷慨是其应尽的义务。酋长制的头领是慷慨的,慷慨是头领应尽的义务;或换言之,慷慨似是对头领的奴役。人种学家们的笔记中重点记录了南美洲原始社会里头领们的付出与给予。事实上,这样的现象始终存在,我们甚至可以把这看做是印第安人从他们的酋长那里进行的无休止掠夺,而他们的酋长必须顺应这种掠夺行为的正当性或者说是法则。换言之,部落头领必须为其部落成员提供“礼物”,如果他尝试限制这样的行为,他将失去所有的威望。“头领是一个慷慨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必须给那些向他提出要求的人所有他们想要的东西(Francis Huxley,1991)。”[注]Pierre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2003,p.28.因此,慷慨实际上是作为头领的基本要求,吝啬与权力在印第安人的世界中不能相容。为了判别新头领的声望大小,印第安人首先考虑的就是他够不够慷慨。
第四,除了义务以外,头领也有一定的专属权力,如多配偶制。几乎所有的原始社会都会承认和接受酋长的多配偶制,[注]这里的多配偶制主要是指一夫多妻。并将此作为头领的专属权力。然而,类似这样的专属权力也会适用于元老会成员。元老会,通常是由本部落的杰出头领,如战争头领、宗教头领等组成。酋长服从元老会的所有决定。元老会有权通过会议选举新的头领。换言之,元老会本质上就是部落头领们的集合,原本专属酋长的一些权力在此被共享。另外,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当多配偶制不只局限于头领之时,那么它必然会建立在某种文化的规定性上,如特权阶层、奴隶制度、掠夺战争,等等。这时,由于一夫多妻不再是独享的特权,后一种社会,即多配偶制不限于头领的社会,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比其他的社会更加民主,然而其悖论在于这种规定性本身规划了相应的层级。
最后,头领必须是一个好的演说者。“头领不是因为演说才是头领,而是因为是头领才演说。”[注]Pierre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2003,p.37.依附于群体的头领应当传递信息,作为方法而非强制的语言更容易得到群体的理解。头领的演说不必非要聆听,因为群体不必非要对此回应。头领的演说通常只是为了唤醒传统的原则,即那些可以成为事实的东西。不存在头领通过演说来要求群体的情况。不管怎样,所有的决定必须征得群体的同意。因此,头领的演说以某种孤独尝试“唤醒诗意的语言以使字词比意义更有价值”。[注]Pierre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aris:Les Editions de Minuit,2003,p.42.
(三)无国家社会
由此,权力的关键在于它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程度。无国家社会模式可以接纳那些在最初的观察中似是矛盾的事物。比如,只有威望的头领。但是权力的确是这些社会本身所意愿拥有的东西。事实上,现实的发生犹如这些社会在用直觉的方法实现了原本是强制权力的社会基本规则。因此,对于皮埃尔·克拉斯特而言,不具国家可能的原始社会才是无国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看不到国王,却找得到头领;然而,社会的头领并不是国家的头领。这样的头领不具权威,没有强制权力,没有办法向群众下达命令。为了完成作为社会事务调解人的使命,这样的头领所能采用的手段只有语言。简言之,头领的空间不是权力的处地。头领的主要职责在于平息发生在个人、家庭、家族之间的冲突。头领依靠其威望重建秩序和协调关系。没有无国家的原始社会容忍其头领走向专制。
此外,皮埃尔·克拉斯特还观察到,原始人世界中的大众、部落、社会等,都能被划分成局部群体(en groupes locaux)。相对由其构建、未被划分的整体而言,这些群体非常重视保护自身的自主性。比如,在战争时期,即使这些群体与其相邻部落或是同胞组成了临时的联盟,群体本身的自主性也不会发生改变。这种部落性总体雾化(l’atomisation de l’univers tribal)的结构方式不仅是一种能够阻止社会进行整体构建的有效方法——整体构建被群体构建代替;也是一种能够防止国家结构涌现的自然策略——国家从本质上讲是统一者。
三、结 语
皮埃尔·克拉斯特对于权力的认识与以往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普遍认识并不相同。他认为政治权力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人类社会,多数的原始社会都会对权力及其形式有自主、自发的选择。因此,权力的诞生并非天然,它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创建。这不仅让我们对于传统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于现代国家权力有了新的反思和反省。比如,对于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讨论:历史表明,国家权力在保障民众利益的同时亦带来无数的恶行,对于它的合法性讨论实际上是在分析它被社会所容许和接纳的理由。以往,与此相关的讨论主要聚焦于由国家政权引起的政治权力关系方面,而皮埃尔·克拉斯特的无国家社会理论则强调了回归国家权力本身的重要性。这亦为现代政治学的“社会的自组织(l’auto-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根据目前人类学的考察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被皮埃尔·克拉斯特所关注的原始社会类型亦存在于除非洲、美洲之外的其他大陆。比如,被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历史学家威廉姆·冯·米德尔[注]参见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vol.6,2002,p.20.(Willem Van Schendel)和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注]参见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James C. Scott)等人所重视的亚洲佐米亚(Zomia)高地。在这块两千多年前开始形成,西起印度东北部,东至越南北部,包括中国云贵高原部分地区在内的狭长区域里,居住约有1亿不愿接受国家统治,继而选择避居或隐居的人们。这些人以平等(égalité)、自主(autonomie)和移动(mobilité)为核心建立了高地社会的价值体系,该体系独立于我们有国家的现代社会体系。在佐米亚高地,人们放弃了文字记录,社会只有容易被篡改的口述历史。而这也只是该地区的社会为绕开国家统治和避开政治权力所采取的技术性策略之一。但是由于目前电信、网络、交通业的日益发达,该地区的平静秩序开始遭到破坏,原本被认为是不会来临的国家权力也已具有了僭越的可能性。而对此类型地区,即对当前原始社会地区的各种考察成果,包括不同人文学科的考察成就,都证实了皮埃尔·克拉斯特先前有关原始社会权力研究的结论。
然而,皮埃尔·克拉斯特并没有解释国家是如何产生的。或许是由于侵略战争,或许是由于特殊机遇,或许由于宗教影响,等等。不管怎样,皮埃尔·克拉斯特的政治人类学始终对立于传统的进化论科学。比如,美国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认为,人类是从低级发展阶段开始,通过知识经验的漫长积累,才逐步由落后社会走向先进社会的。其间包括了蒙昧阶段(la sauvagerie)、野蛮阶段(la barabarie)、文明阶段(la civilisation)三阶段。[注]Lewis Henry Morgan,Ancient Society,Tucson: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2003(1887),pp.9~13.对于皮埃尔·克拉斯特来讲,由于原始社会抵制国家;或换言之,由于原始社会是自愿拒绝文明的,比如原始人坚持缺乏文字,坚持以生存为导向的经济,等等,因而“落后—先进”的社会发展走向并不具有必然性,这样的分类本身亦会因此失去其意义。
另外,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对无国家社会类型进行过研究。比如,法国社会学家让·威廉姆·拉皮埃尔(Jean William Lapierre)认为,虽然无国家社会类型的核心也包括了政治维度,然而国家不是被人类社会所惟一承认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权力在社会运行中所具权威性的大小,在其《无国家生存》(VivresansEtat,1977)一书中,拉皮埃尔将社会的政治组织状况划分为9个等级,[注]Jean William Lapierre,Vivre sans Etat?Essai sur le Pouvoir Politique et l’innovation Sociale,Paris:Le Seuil,1977,pp.75~76.即政治权力单薄、模糊,社会没有调停机制的等级1和等级2;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开始出现,然而只是具有裁判员或中间人功能的等级3和等级4;特殊的政治权力开始出现,权力不再分散,承担一定政治任务的头领开始出现的等级5和等级6;政治权力被划分,其中开始出现个人主义倾向的等级7;制度化的政治权力开始出现,制度被写入长期性的规定中,且这些规定通过其支持网络,如封建制国家等被执行的等级8;政治权力制度化完成,或换言之,通过等级制度或其他一些特殊行政手段,政治权力被执行的等级9。这也就意味着,根据拉皮埃尔的分类,社会政治组织只有到了等级8或9以上,国家才有可能出现。拉皮埃尔以反问的方式对国家的出现作出了说明:
我们是否可以避免无国家?难道不是为了生存,一些社会才最终策略性地建立了国家?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如何能够通过逃避或被动屈从来抵抗有国家社会的侵略?[注]Jean William Lapierre,Vivre sans Etat?Essai sur le Pouvoir Politique et l’innovation Sociale,Paris:Le Seuil,1977,p.357.
他还谈道,在殖民者离开被殖民的原始社会后,是被统治过的原始人主动提出了建立国家的要求,等等。通过以上介绍,我们不难发现,拉皮埃尔的政治组织分类是对皮埃尔·克拉斯特的权力研究的补充。实际上,拉皮埃尔也正是受到皮埃尔·克拉斯特的影响才从社会学角度开始对无政府国家类型进行考察的。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皮埃尔·克拉斯特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他为之后的学者们在政治权力的多种形式、社会组织的多样类型、社会进化的多项选择方面提供了客观的认识和积极的思路,还在于他的研究从最大程度上消减了人们对于不同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或多或少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而这后一点,不仅代表了皮埃尔·克拉斯特本人学术研究的先进性,也代表了现代人类学思想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