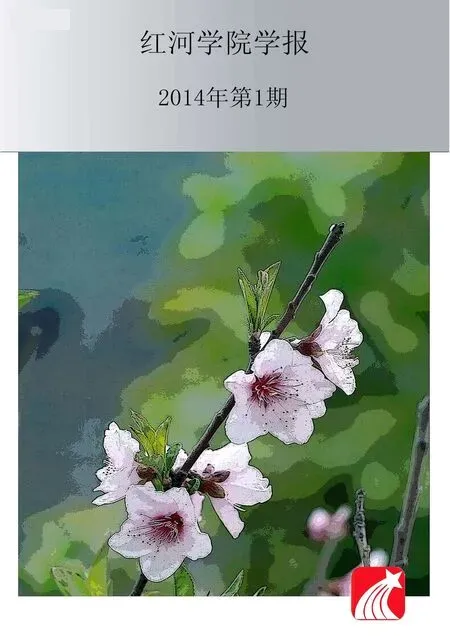中世纪英国教会对黑死病的反应及应对措施
刘 黎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云南曲靖 655011)
黑死病作为一场大瘟疫,对欧洲社会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体现在它对欧洲人生命的严重威胁,它具有死亡率高、传染性强的特点,加之中世纪医疗水平的落后,此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是无药可医的。黑死病带来的毁灭性破坏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产生了连锁反应,所经之处哀鸿遍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食品匮乏,物价飞涨,道德败坏,家庭破裂,教会崩溃,政府瘫痪,完全就是一副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景象,对中世纪英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震撼。
教会在中世纪是欧洲最大的社会势力,它主宰着整个欧洲的社会意识形态。黑死病给欧洲这个最大的封建势力沉重的打击,当然英国也不能幸免。黑死病在1348年至1350年间席卷了英国,面对这场危机,英国教会作出了种种的应对措施,保证了英国社会的基本稳定,尽管效果不够理想,而且有很大的局限性。
一 英国教会对黑死病的反应
中世纪是基督教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它控制着社会意识形态,对任何事物的解释以教会神学为标准,因而中世纪普遍存在着无知,因此人们对黑死病的普遍认识是:一种从来都没有见过和听说过的传染性疾病,它来无影去无踪。对于黑死病的来源及病因,整个社会都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你斟酌一下:教会凭借其是上帝在人间代理者的角色给黑死病所做的解释在当时无疑是“当仁不让”的占了权威的主导地位。
在中世纪,当时的医学理论的标准是教会监管下的神学标准,病人的死亡被归因于罪孽,而瘟疫则是因为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因此黑死病的成因被归因于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即“天谴说”,认为黑死病的出现和传播是由于人类的罪孽所引起的。“神职人员和浸润在宗教情感中的广大民众,相信这是上帝愤怒后对人类的惩罚。”[1]英国最早对黑死病作出解释的是威廉·苏支大主教,他认为黑死病“显然是由于人类的罪孽引起的,因为他们享受美好的时光,却忘了上帝的恩赐”[2],因此上帝才降下灾难以惩罚人类。面对瘟疫,教会告诉人们“瘟疫是上帝的行动,是人类的罪恶引起了上帝的震怒,他以此来惩罚人类的罪恶和警告人们悔改和走上行善的道路。”[3]“在教会看来,瘟疫是人类自身罪孽招致的惩罚,社会道德的堕落则是上帝发怒的主要原因”。[4]2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教会对黑死病的病因及大量人口的死亡解释为因为人类的罪孽而导致上帝发怒,而致上帝降罪人间。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教会对黑死病的解释在具体的原因上却没有说清楚,对黑死病的病因只是做出了原则性的解释——社会道德的堕落,然而究竟是社会道德在哪些方面的堕落?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导致上帝降罪人间?到底是什么行为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为什么有的地方儿童死亡的特别多?为什么这场瘟疫会如此遍布?为什么教士本身都无法幸免?诸如此类的问题教会并没有能力向人们解释清楚。因而下级教会在解释黑死病病因时就有了很大可自由发挥的空间。有的人认为跟天象有关,有的认为是人们的道德出了问题,有的人认为是因为人们的淫荡引起的。关于具体的原因五花八门,但是却都没有超出“天谴说”的范畴。教会向人们解释了一种普遍认知的神学原则,但是由于黑死病的突如其来,整个社会陷入悲痛、恐慌和动荡之中,这种笼统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能宽慰那些正为黑死病的恐惧所煎熬的人们,因此教会对黑死病的解释也普遍的为人们所接受,教会提出的从根源上寻求黑死病病因的“天谴说”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和防治依据。
二 基于“天谴说”教会对黑死病的应对措施
(一)借上帝之言抚慰民心
黑死病在英国流行期间,面对死亡,教会告诉人们,瘟疫是上帝的行动,是人类的罪恶引起了上帝的震怒,他以此来惩罚人类的罪恶和警告人们悔改和走上行善的道路。《坎特伯雷副主教致伦敦主教的信》(A letter from the Prior of Canterbury to the bishop of London)中说:“上帝经常让瘟疫、悲惨的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灾难降临,借此来恐吓和折磨人们,让人们驱赶走自己的罪恶。”[5]所以扭转这场瘟疫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向上帝求助,教会教导人们以忏悔和祈祷的方式来应对黑死病,认为摆脱瘟疫的最佳方式只有祈求上帝的原谅。因此,在黑死病肆虐期间向上帝忏悔的宗教仪式就变得重要起来,贯穿于教会应对黑死病的始终。教会努力让人们相信忏悔和祈祷就能得到上帝的解救。“人们要祈祷并唱赞美诗,要忏悔、朝圣和积极地向教会奉献”。[2]教皇亲自为驱逐黑死病而设计了弥撒,并通过红衣大主教向英国全境推行。为此教会在黑死病期间制定了驱逐黑死病的计划和行动方案,而且具体到教堂,这种行动方案细致,并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如规定“要组织僧侣和民众低头、赤脚、禁食,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忏悔他们的罪孽,他们在走动时尽量的多念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2]这种类似的规定英国在黑死病期间还有很多,如在约克镇,大主教苏支就规定在每周的周三和周五都要举行虔诚的游行和祈祷,并且为了减轻瘟疫,每天作弥撒时都要朗诵特别的经文。在坎特伯雷教省,在温彻斯特主教区都有这种类似的规定。
教会对黑死病的应对措施基于“天谴说”,但是“天谴说”只是一种原则性的认识,由于对瘟疫流行原因的误解,这些措施对于控制瘟疫来说毫无成效,并且还因人群的集中游行以及类似的活动而使瘟疫更加肆虐。教会的忏悔措施所起到的作用仅仅在于安慰人心和稳定秩序。
黑死病引起大量人口死亡,如“1348年,总计1800人的小村子日夫里死亡750人;在威斯敏斯特皇家法庭,死亡记录从25人一下子跳到700多人”[6],恐慌充斥于每个民众的内心和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秩序混乱不堪,而又无药可以抑制黑死病,面对这种情况,稳定、抚慰民心成为首要大事,也是唯一有效的选择。
对于在中世纪英国全民信教的时代,这样的措施是有极大的意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黑死病所带来的对社会的冲击,更重要的是这对人们普遍的恐慌心理是一种极大地安慰,其对社会安抚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无可置疑的。
(二)“死亡援助”——保住生者在人间的生存信念
教会严格要求各级教士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在中世纪英国几乎全民信教,因此教徒在临终前的圣事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英国教会要求各级教士坚守自己的岗位,特别要做好死者临终前的圣事。基督徒在临终前圣事:聆听忏悔、领圣体、涂油仪式是很重要的,在基督教的教义里人是带着罪孽来到人世的,因此人的一生要不断的向上帝赎罪,教徒在临终时的圣事仪式是洗脱其在人世罪孽的重要仪式。而“信徒们最大的不安,便是没有举行教会的圣事就死去,而主持圣事是教职人员的职责”。[4]8黑死病的流行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这种临终的圣事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仪式对恢复心理平稳和维系社会平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7]教会要求教职人员坚守自己的岗位对于已经死去人的意义我们没必要去深究,但是这对于全民信教的英国来说就十分重要了,这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剂非常好的稳定剂。教会的这一举措,对于安抚人们内心的恐惧起了较好的作用,使社会的动荡得到一定的稳定。再者,瘟疫流行期间,教会组织的祈祷和忏悔是应对黑死病的主要措施,这些工作具体下来就必须要大量的教职人员来完成,因而教会要求教职人员坚守自己的岗位对于这些措施的贯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务实的增补教职人员
黑死病引起大量教士的死亡,因为教职人员与患病者接触的频率很高。教会迅速地采取各种措施补充教士的不足,以维持教会的正常运转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面对这种情况,教会重新任命了许多新的教士,以应对教职人员缺额的状况。“为了填补教职空缺,教皇任命了大批教士。”[8]“由于1349年大量教职人员死于瘟疫之后,各地教会紧急补充新教职来应付人员短缺危机”。[9]贝特曼大主教在剑桥大学建立了神学院来批量生产教士。后来许多在瘟疫期间失去妻子的男子也加入了神职。甚至有的文盲也加入了神职人员的行列。这样就明显带来一个问题,这些新的教职人员的神学和文化修养就大打折扣。本来在中世纪教职人员的任选需要经过层层的考察。但是在大危机下,补充的教职人员的素质却无从考虑。“在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补充的情况下,教会只好把那些不够资格,甚至根本不适合当教士的人招纳进自己的队伍。新的教士队伍中很多是文盲,有的即使识字也无法理解经卷中的内容,更多的人则没有任何经验,甚至为了填充严重的空缺,教会连原来任命教士的规定也放弃了”。[3]本来教徒的临终圣事是很神圣的,必须要相关的神职人员来完成。但是在黑死病期间,由于教会人员损失太大,因而在某些地方教徒的临终圣事问题上,在教会的允许下世俗人员甚至是妇女也可以为教徒完成临终圣事。在黑死病期间加入教会的人员虽在素质上大打折扣,更有甚者连世俗的人员也参与了教职人员的工作,但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法,这无可厚非。由此也可窥视教会在应对黑死病时对其政策调整的力度之大。
(四)实行物质与精神集为一体的“特赦”之法
在瘟疫期间教会的另一个做法是宣布特赦,即规定一定的时间段为特赦期,在特赦期内,健康的人也可以向上帝忏悔,只要他是诚心的忏悔,即使是在他染病后没有进行临终的圣事他也可以得到上帝的原谅。“只要他足够真诚,那么在此有效期内他即使没有忏悔而死去,也可以获得谅解。”[10]在黑死病期间英国不论是大至教省,还是小到具体的教堂都对特赦期做了规定,这些特赦期的时间在一个月至六个月不等,多数在三个月。
(五)最切实际的行动——开辟墓地
黑死病带来大量人口死亡,需要大量墓地安葬死者,这方面教会所作的努力与它对黑死病的解释和祈祷相比较,显得更有意义。在中世纪几乎是全民信教,按教会的说法,人在死后的某一天将会复活,因而一个人死后应该将他埋葬在被祝圣过的地方。在这一点上,“教会在对墓地的开辟和选择上具有决定权”。[10]面对大量的人口死亡,突然间原有的墓地不足以容纳如此多的尸体,死者的埋葬问题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因此英国教会不得不扩大墓区的面积,开辟了大量墓地。如在温彻斯特,当地的大主教就下令扩大教区的墓地的面积,并开辟了一些新的墓地。在伦敦,教士约翰·考瑞劝说阿尔孟特的圣三一教堂的主持尼古拉斯出售一块空地作为墓地。约克大主教发送了许多特许状,允许教省区各主教去开辟墓地并为之祝圣。在伍斯特教区,布伦斯托德主教就要求他的下属在圣奥斯沃德救济所开辟新的墓地,作为应急之用。在伦敦,教会在政府和王室的支持下开辟了新的墓地。“在伦敦开辟公墓的过程中,政府积极加以支持,爱德华三世后来还为西多会的修士修建圣慈玛利亚修道院。”[4]93
三 结论
中世纪是基督教最赋辉煌和荣耀的时代,“君权神授”,让世俗政权甘愿为其做马前卒,这在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达到了顶峰。教会控制着当时欧洲庄园式封建社会的多数物质资源,最重要的是她在欧洲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拥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此时的英国亦如此。在黑死病降临不列颠之际,教会无疑完全暴露再其面前,首当其冲。
在中世纪包括医疗在内的科学水平和物质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面对如此猛烈凶恶的大瘟疫,教会更多的是发挥精神方面的作用——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与支撑,这一点也是宗教的本质功能,在法国尚蒂伊.孔代博物馆里有这样一幅画——《贝里公爵的美好时光》——画上描述了冒着黑死病的危险,教皇在罗马亲自领着一支教士队伍做祈祷,这在前面的叙述上很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教会在力所能及的进行救助。教会其外还充分发挥其手中掌握的诸多资源,以一种世俗式的姿态积极的同黑死病做斗争,如同英王政府合作,开辟墓地;教会的修道院还积极收养孤儿和无家可归的民众。
综上所述,教会在面对危机时采取了其力所能及的措施,基本上维持了英国社会的稳定。如果教会在黑死病期间其运作难以维持的话,黑死病期间的社会救助和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将无从谈起。
[1]张绪山.十四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2):59.
[2]李成化.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J].中国社会科学学,2007,(3):191—193,196.
[3]赵立行.1348年黑死病与理性意识的觉醒[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2):40,42,44,45.
[4]李化成.黑死病期间英国的社会救助与整治[M]//候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第四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5]刘美君.转变了的灾难:黑死病社会文化影响初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增刊,11-14.
[6][法]罗伯特.福西耶.剑桥插图中世纪史(1250—1520年)[M].郭方,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43.
[7]李晓光.黑死病与14-15世纪欧洲社会历史的变迁[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6:38.
[8]崔敏.试论并以对欧洲中世纪社会进程的影响[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2:21.
[9]李成化.黑死病与英国人口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03:29.
[10]李成化.论黑死病期间的英国教会[J].安徽史学.2008,(1):7.
——新修订《湖北省宗教事务条例》解读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