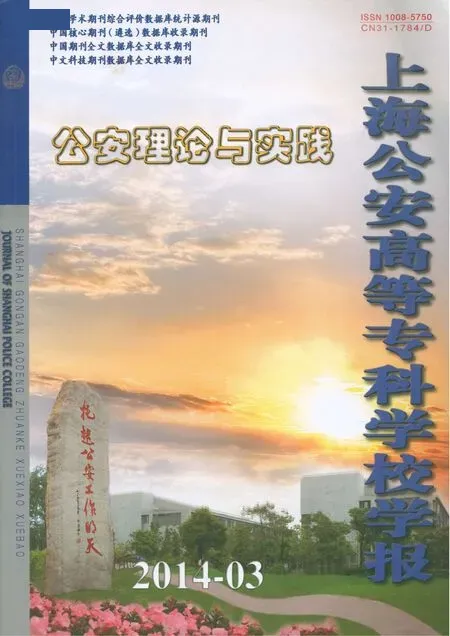关于扒窃型盗窃罪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解析
石 魏,白崇伟,孙沙沙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 100007;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北京 102100)
关于扒窃型盗窃罪司法实践疑难问题解析
石 魏,白崇伟,孙沙沙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 100007;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北京 102100)
扒窃型盗窃罪于2011年得到《刑法修正案(八)》认可,是司法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争议和疑难之处,造成了定罪量刑认定的困惑。从扒窃型盗窃罪的定性入手,对“公共场所”对扒窃型盗窃罪成立的作用、“不得重复评价”原则在扒窃后转化型抢劫罪之认定中的适用、法院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又自动投案的行为认定等六方面疑难问题加以解析,有利于司法实践。
扒窃;盗窃罪;转化型抢劫;司法实践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工具日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公交优先”的战略下,各地公共交通设施不断完善,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里程也大幅增长,但伴随而来的是各类扒窃案件日益多发,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同时也增加了法院的受案数量。对此,《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罪的一种加以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截至2013年5月1日,扒窃入刑已满两年,此类案件在审理中仍存在诸多争议和疑问。因此,本文立足司法实践,以维护公众合法权益、提高审判质效为出发点,探析扒窃类案件的疑难问题,以期为稳定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
一、扒窃型盗窃罪的定性及入罪:行为犯还是结果犯?是否一律入罪?
犯罪既遂包括行为犯和结果犯。行为犯的既遂标准为法定犯罪行为的完成,不要求造成物质性的和有形的犯罪结果,即只要行为实施到一定程度,即为既遂;结果犯的既遂不仅要具备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
从法条文义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将盗窃罪分为普通形态的盗窃罪和特殊形态的盗窃罪。普通形态的盗窃罪客观方面要求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犯罪结果要求达到数额较大,属于典型的结果犯。特殊形态的盗窃罪与普通形态盗窃罪并列,但其没有数额的限制,只要实施了“多次、入户、携带凶器、扒窃”四种行为之一,即构成盗窃罪既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并非是对扒窃行为犯罪数额的限制,而是盗窃罪法定刑的升格条件;“扒窃”以“顿号”与“多次盗窃”并列,说明刑法对扒窃行为入罪并无次数方面的限制;“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并列,说明对扒窃入罪的方式也无特别规定。综上,扒窃入刑惩治的是扒窃行为本身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且危害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故立法将其规定为行为犯,既无数额要求,也无次数、方式要求。
从刑法保护的权益来看,扒窃型盗窃罪作为行为犯可以更好地保护公众合法权益。扒窃严重危害了公众财产权、人身权,破坏了社会公共秩序,如果加以结果限制,会造成部分犯罪分子游离于刑法之外。现实中,大部分扒窃数额并不大,以北京某区为例,自2011年扒窃入刑,截至2012年12月20日,法院共审结公交扒窃型盗窃案件442起,其中窃取数额1000元以下的占64%,100元以下的占5%。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盗窃数额在2000元以上的方构成盗窃罪。如果将扒窃作为结果犯加以数额限制,则多数公交扒窃行为将得不到惩治,但此类扒窃分子又大多具有前科劣迹,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险性较严重,如此无疑纵容了此类行为的发生。因此,从更好地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扒窃定性为行为犯更佳,司法实践也秉持此种观点。
从刑法体现的立法价值来看,将扒窃定性为行为犯体现了刑法应对风险社会的价值。多年来,我国刑法强调结果无价值论,侧重客观,[1]但《刑法修正案(八)》作了重大突破,规制一些犯罪时开始重视行为无价值理论,侧重考量行为本身体现出的人身危险性。尤其是针对我国面临的风险社会状况,刑事立法对某些严重危害群众身体健康以及财产安全的犯罪在立法价值方面作了重大突破,可以说,《刑法修正案(八)》最能体现刑事立法应对风险社会的宗旨,[2]扒窃入刑即是此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刑事立法将其认定为行为犯,侧重的是行为惩治。
与此同时,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非所有扒窃行为都科以盗窃罪进行定罪处罚。对于符合《刑法》第十三条规定的行为,应以出罪处理,对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如初犯、偶犯、犯罪时已满16周岁但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具有自首、立功表现的行为人,全部退赃、退赔的,协助抓获其他被告人的,也不应以盗窃罪定罪论处。
二、“公共场所”的认定:是否应作为扒窃型盗窃罪本质特征之一?
简而言之,“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自由活动、具有开放性的场所,应作为扒窃行为本质特征之一。
其一,区别于其他三种特殊形态的盗窃。扒窃作为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并列的犯罪行为,具有相似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限于公共场所,则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将大大降低,远远低于一般盗窃罪的条件。公共场所的高流动性、高密集性以及人员的陌生性,给扒窃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地点发生扒窃事件,不仅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还会对公众的安全感带来严重的损害,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再加上在公共场所实施的扒窃,窃取过程比较短暂,每一次窃取的数额可能不太大,但由于扒窃分子多是惯犯,常年进行扒窃,况且扒窃分子窃取的多是钱财、手机和各种购物卡,钞票、购物卡具有大众性、难以区分性,扒窃分子在被抓获时,要么把财物丢弃,使得证据难以收集,要么拒不承认身上的财物是偷盗而来的,从而使公共场所的安全存在更大的隐患。为了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保障公众在公共场所的合法权益,在司法实践中无疑也应该将公共场所作为扒窃行为的本质特征之一,从而加强在此区域的管理和整治,提升公众对此的信任感。
其二,区别于普通形态的盗窃。排除“公共场所”,会造成盗窃类型的混同,如扒窃型盗窃罪与普通形态盗窃罪,两者的客观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重合,对两者的区分就在于是否具备公共场所这一特征,而且两者的入罪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通形态盗窃罪要求盗窃的数额达到2000元以上,而扒窃型盗窃罪对数额则没有要求,如果不把公共场所作为其本质特征,则会混淆普通形态盗窃罪与扒窃型盗窃罪之间的界限,导致严重的罪刑失衡。
其三,区别于一般违法行为。从刑法的谦抑性及最后性的属性来看,对扒窃型盗窃罪进行恰当的限制,也是充分发挥刑法的保障法作用的具体体现。刑法作为国家控制社会、应对犯罪的最后手段,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足以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时才予以适用。[4]将扒窃型盗窃罪限制在公共场所,可以将一般的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排除在刑法之外,既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刑法效用,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也可更好地实现刑法与行政法之间的衔接和贯通,便于发挥法律的合力作用。
三、扒窃对象及范围认定:是否仅限于随身携带财物?
“随身携带”是指在从事日常活动的住宅或者居室以外,将某种物品带在身上或者置于身边附近,将其置于现实的支配之下的行为。[5]对其范围应作广义上的理解,不仅包括被害人随身携带在身上的财物,也包括在被害人的身边控制范围之内、可以随时支配的财物。
笔者以为,扒窃对象应限于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扒窃行为之所以成为一类特殊的盗窃行为,就在于其窃取的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因与人身紧密相关,会显著加重民众对社会治安以及自身人身安全的担忧,从而使其重于一般的盗窃行为。[6]
我院毕业生很多就业于中小型民办跨境电商企业,有些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设自己的英文网站,学生经常要撰写公司英文简介、产品介绍等建站信息。所以我们建立业务关系模块中增加了公司介绍、产品介绍的案例。在案例的选择上,注重了案例的真实性,选取相关公司的真实英文网站。学生一方面要广泛浏览国际知名品牌的英文网站,另一方面要关注中国中小企业的英文网站。我们选择了一些中小企业的英文网站上的公司介绍作为原始版(original version),并提供了改进版(edited version)给学生讨论分析。
其次,由于扒窃分子侵犯的财物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其窃取行为可能被被害人知晓,进而采取暴力行为,侵害到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同时,由于扒窃分子在窃取的过程中要与被害人的身体进行接触,还同时可能会侵犯公众的隐私权,扒窃分子的主观恶性更大,亦需加大对公众的保护力度。
最后,扒窃分子对财物的控制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即行为人将财物从被害人处转移于己处并随时可以支配。因此,扒窃行为在切实侵害财产权、人身权的同时,还会造成公众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对社会产生不信任感。
四、扒窃型盗窃罪的罪数认定:一罪还是数罪?
扒窃型盗窃罪的被告人在实施扒窃过程中或之后,经常还会实施后续行为或属于延伸行为的其他行为。对此,应构成一罪还是数罪?本文认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扒窃型盗窃与普通形态盗窃客观行为重合时的罪数认定
被告人在公共场所进行扒窃,窃取他人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时,该客观行为既满足普通形态盗窃罪的入罪标准,也满足扒窃型盗窃罪的成立条件,但对同一情节不能重复评价,否则会严重导致罪刑失衡,对同一行为作双重评价。因此,对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财物达到“数额较大”的行为应独立评价。由于无论是扒窃型盗窃罪还是普通形态的盗窃罪都是盗窃罪范畴,属于实质上的一罪,所以,应以盗窃罪一罪论处,盗窃数额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二)被告人随机实施扒窃行为,窃取他人票据后又冒用他人的汇票、本票或者支票骗取财物的罪数认定
1. 罪与非罪之认定。如上述,扒窃型盗窃罪为行为犯,并无犯罪数额要求,故被告人实施完扒窃他人票据的行为后,即构成盗窃罪既遂,无论其后续行为是否利用票据进行诈骗。而票据诈骗罪是结果犯,只有在发生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的犯罪结果,达到一定数额时,才构成犯罪既遂,因此,诈骗数额对于是否构成票据诈骗罪具有决定作用。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利用金融票据进行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票据诈骗罪;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单位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①参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第五条。故5000元是个人构成票据诈骗罪的入罪标准。综上,在被告人扒窃他人票据后又利用其诈骗,获取财物不超过5000元的,不构成票据诈骗罪,应以盗窃罪一罪对其定罪处罚,利用票据诈骗的行为应作为量刑情节加以考虑。
2. 一罪与数罪之认定。被告人随机扒窃他人票据后又利用票据实施诈骗,获取财物超过5000元时,构成盗窃罪和票据诈骗罪,应数罪并罚,因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侵犯了两种不同的客体。一方面,被告人的扒窃行为侵犯了被害人财产权,应以盗窃罪惩处。另一方面,被告人随后实施的票据诈骗行为是一种新的、具体的实行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对金融票据的管理秩序以及他人的财产所有权。票据诈骗罪的客体与盗窃罪的客体不存在包容关系,也不属于能包含盗窃行为与其他行为的同一犯罪的复杂客体,故应以盗窃罪和票据诈骗罪数罪并罚。
五、公交扒窃转化型抢劫罪量刑之认定:基本量刑幅度还是加重量刑幅度?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而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是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之一。因此,被告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扒窃过程中或既遂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即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对此并无疑问。问题是如何确定量刑幅度,在基本刑的幅度内量刑,还是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加重刑幅度内量刑。存在分歧的症结在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扒窃这一盗窃罪的定罪情节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实施抢劫这一抢劫罪的量刑情节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和重合性。对此,立法从不同角度作了规定和评价,也引发了定罪量刑的困惑,即两者只能择一认定还是可以并存,能否重复评价“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这一情节。
刑法理论的不得重复评价原则认为,在定罪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具体事实情况,在量刑时就不能再作为处刑轻重和是否处刑的根据。简言之,同一情节不能既作为此罪的认定条件,还作为彼罪的认定条件,也不能既作为定罪的条件,还作为量刑的条件。因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这一情节已经作为先前盗窃罪的成立要件加以认定和评价,不宜也不应在后续的转化型抢劫罪的量刑情节中再次评价。具体来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进行扒窃转化为抢劫后,对其量刑已经上升了一个档次,即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抢劫罪定罪,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如果再次适用《刑法》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加重情节量刑,则量刑幅度又再次上升一个档次,达到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幅度,如此,会造成一个行为因两次评价在量刑中上升两个档次,明显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六、自首的认定:取保候审中脱逃后又自动投案的认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六十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逮捕的条件是:(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刑罚;(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阻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大部分扒窃因数额较少、情节简单而不符合逮捕条件。根据北京市委政法委规定,对不符合逮捕条件而适用拘留强制措施的,适用轻刑快审程序,即公检法必须在一个月内将案件审结。但是,司法实践中,30天的刑事拘留期限届满时,判决还未生效,此时,就需对被告人变更为取保候审,但易发生脱逃。对于在法院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再主动归案的情况,本文认为不能认定为自首。
首先,其不符合一般自首的条件。一般自首需要满足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两个条件。所谓自动投案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还未对其进行讯问、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出于本人意愿将自己置于有关机关或者个人的控制之下,自动说明其有自愿性和主动性,可以自由选择,也就是其是在公安机关未对其采取措施前的一种选择权。扒窃型案件是公安机关主动侦破的案件,被告人是一种被动的归案,只是由于具备某些情节而被采取了取保候审,因此,成立自首的自愿性前提由于其已被公安机关抓获而丧失,在法院办理取保的时段,侦查机关已经进行了讯问、采取了强制措施,进入了审理阶段,行为人也不可能再回溯到侦查阶段,因而,不符合一般自首的条件。
其次,其不符合特别自首条件。特别自首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而实际上在审理阶段对其取保,其脱逃,已经违背了如实供述的本质,而且,所投之“案”应为司法机关未掌握的案件,但在审判阶段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水落石出,另外取保候审并不因为行为人的脱逃而失去法律效力,案件仍在处理过程中,不满足投案的条件。
此外,从自首的本质来看,也不应该将此脱逃后又主动归案行为认定为自首。设立自首的目的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机关的办案效率,扫清案件侦破过程中的障碍,脱逃既浪费了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成本,而且还违反了取保候审行为人的法定义务,如果将其认定为特别自首,会导致严重的不公,试想没有脱逃的依法定罪量刑,脱逃的反而以特别自首认定,量刑时从轻、减轻处罚,这严重违背了罪刑相称原则。
但是,行为人取保后脱逃又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则可以认定为特殊自首。因为这一方面反映了其有悔过自新的表现,另一方面也节约了司法成本,因而,对有特殊自首情节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扒窃型盗窃罪发生频率之高、追责难度之大、影响危害之广已不容小觑,其存在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是一大隐患。正确界定扒窃的内涵,对于在实践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准确把握,化解争议,方可更好地惩治犯罪,保障人权,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在公共场所的安全感和信任感。
[1]肖中华,孙利国.“扒窃”犯罪成立要素的合理界定[J].政治与法律,2012,(9).
[2]高铭暄.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正当性理论研究[J].法学论坛,2011,(4).
[3]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7.
[4]曲新久.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89.
[5]张明楷.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7:280.
[6]陈家林.论刑法中的扒窃[J]].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4).
[7]阴建峰.刑法的迷失与匡正[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
[8]高铭暄,马克昌.中国刑法解释[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赵秉志.《刑法修正案(八)》宏观问题探讨[J].法治研究,2011,(5).
[10]李齐广.论《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认定[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2,(5).
[11]张明楷.盗窃罪的新课题[J].政治与法律,2011,(8).
[12]阴建峰.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J].河南社会科学,2011,(2).
[13]卢建平.风险社会的刑事政策与刑法[J].法学论坛,2011,(4).
[14]陈家林.论刑法中的扒窃[J].法律科学,2011,(4).
[15]许光.试析“扒窃”入罪的条件与司法认定[J].江南大学学报,2011,(6).
The Analysis of Diff cult Larceny Problems such as Pocket-picking in Judicial Practice
Shi Wei, Bai Chongwei, Sun Shasha
(The People’s Court of Dong 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7, China; the People’s Court of Yan Qing County, Beijing 102100, China)
The larceny such as pocket-picking was conf rmed by the Eighth Amendment of Criminal Law in 2011, which is an example of justice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many controversies and confusion, which causes problems of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The writer analyzes and explain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nature of pocket-picking, establishment of pocket-picking in public places, suitability of the principle of “Not repeated judgment” to the conviction of criminals who commit pocket-picking which, however, is transformed into robbery and who skip bail but turn themselves in to the police later. The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are conducive to judicial practices.
Pocket-picking; Larceny; Transformed Robbery; Judicial Practice
D915.3
B
1008-5750(2014)03-0050-(05)
10.13643/j.cnki.issn1008-5750.2014.03.009
2014-02-25 责任编辑:陈 汇
石魏,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区域刑法;白崇伟,男,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法官;孙沙沙,女,北京市延庆县人民法院法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