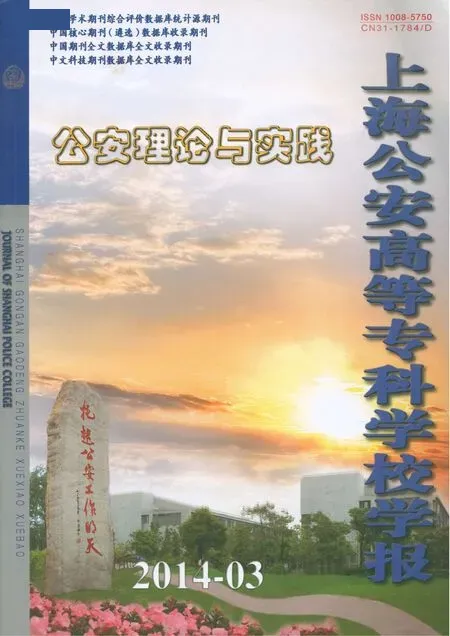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构建
姜 利,张庆立,钱金钗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030;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1620)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构建
姜 利,张庆立,钱金钗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030;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 上海 201620)
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具体追偿制度缺位等诸多问题。一般而言,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仅指向加害方追偿。目前,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建构具有立法、理论和实践上的依据,具体应包括发现、追偿、处置、救济四种机制。为实现该制度的长效化,除追偿资金外,还可以探索将追缴的犯罪所得及收益、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监管场所在押人员的劳动创收等全部或者部分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以拓宽其资金来源渠道。
检察机关;被害人;刑事救助;追偿制度
自2009 年中央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会签《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八部委意见》)以来,全国各地检察机关都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①仅从检察工作的角度看,刑事被害人救助不同于刑事救助,前者仅指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救助,而后者在实践中,除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外,部分地方还扩大了救助的范围,包括因被追究刑事责任生活陷入困难的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家属、因被打击报复陷入生活困难的举报人、证人和鉴定人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数据看,《八部委意见》发布后,全国各地检察院都加紧落实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从2009年3月至2010年8月,累计已有866人获得了刑事被害人救助,救助金额达1177万元。[1]仅广东省检察机关自2008 年试点以来到2012年,就已救助190 人,金额达307.04 万元,且2012年救助140 人,发放救助金132.6 万元。[2]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以来,上海市检察机关共救助刑事被害人331人,发放救助金198万元。可以说,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实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刑事被害人的人文关怀,也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要求,实践中对于安抚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情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从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实践中这一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就在于具体追偿制度的缺位。这一问题直接涉及救助资金的来源、救助标准的确定、救助范围的界定、救助对象的界定等问题,②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普遍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存在资金来源单一、救助标准过低、救助范围狭窄、救助对象不足等问题,归根结底,这些问题都与救助的资金不足有关。可以说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亟待研究、探索。
一、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概念辨析
《八部委意见》在第四条“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基本要求”第四款“救助决定、资金的发放”第四项中规定,“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获得救助后,如果被告人或其他赔偿义务人有能力履行民事赔偿义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向其追偿”。上海市八部门制定的《上海市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也作了相同的表述。上述规定即刑事救助被害人追偿制度的法律依据所在,但是,由于该规定中对追偿对象的表述采用了“其”这一指示代词,造成了实践中具体应当向谁追偿理解不一。为了进一步澄清具体追偿的对象,2010年3月,《上海市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获得救助后,如果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有能力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向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追偿”。另外,《上海市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十一条还规定,“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当事人通过隐瞒事实、伪造证明文件等方式骗取救助资金的,应当要求返还,并批评教育。拒不返还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可见,对于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骗取救助款的,检察机关一经发现也应当依法要求返还。由于汉语中的“偿”即“归还”的意思,因此,尽管条文中没有用“追偿”来表述,但这种要求返还的行为也可以称为“追偿”。
从上述内容看,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概念应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追偿制度既包括对被不起诉人、其他赔偿义务人等加害方的追偿,也包括对骗取救助款的刑事被害人、近亲属等被害方的追偿;而狭义上的追偿,仅指对被不起诉人和其他赔偿义务人等加害方的追偿。其实,无论对加害方还是被害方的追偿,在追偿程序的设置上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同时,考虑到尽管各地的做法纷繁复杂,但研究仍应力求以《八部委意见》的意见为依据,①实践中,按照《八部委的意见》,部分地方检察机关除对不起诉案件中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开展了刑事救助外,对提起公诉案件中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也进行了救助,这确实需要在各地方追偿制度设计中予以考虑。然而,为了照顾追偿制度设计的普适性,考虑到《八部委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和各地探索实践的共性,本文研究的追偿制度将以不起诉案件中对加害方的追偿为限。而且追偿制度本身的构建也需要遵循循序渐进,先试点后扩大的思路。因此,为求研究上的集中性、适用上的统一性,建议将其概念界定为:人民检察院在对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依法开展刑事救助后,发现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有能力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应依法向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要求返还已经向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支付的救助款及其孳息的相关规定的总和。这一概念有以下几个要素:一是检察机关的追偿必须在已经对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开展刑事救助后。在刑事救助前,发现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有能力履行赔偿民事赔偿义务的,应当通知被害人,由其依法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通过当事人和解解决。二是只能向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主张。尽管检察机关刑事救助的对象是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救助款也发给了刑事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但由于刑事被害人救助性质的“替偿性”特征,②域外被害人补偿制度具有目的的公益性、责任的替偿性、数额的补充性以及受偿主体的特定性。诚然,该制度与我国目前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还存在诸多差别,但就实践看,我国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已经是目前与域外被害人补偿制度最相类似的一项制度,而且也有学者主张将其改造为中国版的被害人补偿制度。[3]追偿的对象只能是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三是追偿款的数额既包括了救助款,也应包括救助款所生孳息。因为犯罪行为是造成被害人或其近亲属人身伤害的直接原因,本着责任自负的原则,应当由加害人负责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国家的救助应当是代位性质的,这就要求救助款必须追偿,而这种代为救助不应该造成代位人的损失,因此,救助款的应得利息也应当计算在追偿额之内。四是这种追偿制度不仅包括追偿的程序设计,即追偿主体、追偿数额、追偿对象、追偿方式等,也应当包括追偿的发现制度,即对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经济能力的动态跟踪评估制度,以及追偿款的最终处理制度和异议救济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尽管目前有关规范性文件对于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作了规定,但是该制度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就在于对该制度理论根据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实践中,有些人在对国家赔偿、国家补偿和被害人救助的概念进行区别后指出,相关刑事补偿机构在完成补偿后,不得向犯罪人追偿。因为与国家刑事赔偿不同,国家刑事补偿并非源自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4]国家刑事补偿不是“国家替代刑事犯罪人及其他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主体,为弥补刑事被害人及其他权利主体遭受的民事权益损失所为之‘赔偿’”。[5]也有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实施救助之后,救助机关享有对加害人或其他赔偿义务人的追偿权”。[6]对此,我们认为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建立应当是有其理论依据的,具体如下:
1. 刑法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双重职能的必然要求。有犯罪必有惩罚,只有对犯罪行为进行追偿,才能使犯罪行为人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从而增加其犯罪的成本,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另外,追偿还有益于丰富被害人救助资金的来源,为更好地保护被害人权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追偿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实践中“变相鼓励无经济能力的犯罪嫌疑人多犯罪和犯重罪”的不合理现象。
2. 民事侵权行为因果关系和归责原则的根本要求。犯罪是严重的侵权行为,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从侵权行为的一般角度讲,被害人的损害是由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与犯罪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应当由犯罪行为人承担侵权赔偿的责任。在国家救助以后进行追偿,正是体现了侵权归责的一般要求。
3. 刑事救助制度中国家责任代偿属性的本质要求。根据通说,刑事救助制度的理论依据在于国家责任。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解释,国家与公民之间达成契约,公民让度部分权利给国家以保护个人自由,国家则有义务维护公民的安全,但犯罪行为的发生使公民的安全受到侵害,国家应当承担责任。而国家承担责任的形式是后置性、代位性的,必须在没有其他救助途径的前提下才能承担,而且一旦犯罪人恢复了赔偿能力,还应当有权予以追偿。
实践中,有些人反对追偿,其理由主要在于:一是被害人救助不同于国家赔偿,因此不能参照国家赔偿中的追偿规定开展追偿;二是刑事被害方救助体现的是国家在契约中的违约责任,是国家本身的责任,而不是代他人承担的责任。应当承认,国家赔偿与刑事被害人救助确实存在区别,但仅仅因为二者不同就认定被害人救助不能追偿,理由并不充分。另外,国家对刑事被害方的救助确实体现了国家责任,但这种国家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后置性的,只有在穷尽其他方式仍然不能恢复犯罪以前的被害方状态时,国家才有义务承担责任,而且为了保证国家这种责任承担方式的良性运作和高标准运作,国家在承担了相应责任后,也应赋予国家向恢复经济赔偿能力的犯罪方追偿的权利。按照反对者的逻辑,如果不允许国家追偿,一方面有可能放纵犯罪,另一方面对提高救助标准、扩大救助范围等未来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发展也无益处。
三、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具体构建
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程序是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制度的关键和核心,要实现追回救助款的目的,必须建构一套合理可行且与其他相关制度相契合的科学程序。具体如下:
1. 发现机制,即对被不起诉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经济能力的动态跟踪评估机制。一是建立定期报告和走访制度。对已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的案件中的被不起诉人和其他赔偿义务人,在救助的同时,应当通过书面方式告知其每年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个人经济能力的情况,检察机关控申部门还应当指定专人对该报告进行审核,并实地走访了解,对于被不起诉人和其他赔偿义务人系外地人的,可以委托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居住地检察机关控申部门负责走访了解,核实个人经济能力情况。二是依托现有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平台,完善平台界面,将被害人救助工作作为平台日常录入项目,并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方式,建立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保险监督管理部门、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等行政部门的信息交流机制,实现信息共享。三是建立信息公开和线索举报奖励制度。对于已经开展刑事被害人赔偿的案件要及时通过检察网站、公示栏、社区检察室或警务室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尤其是向被不起诉人及赔偿义务人所在社区公示追偿信息,并对举报其恢复经济能力经查证属实且已成功追偿的案件,按照追偿款的一定比例或者按照固定数额,给予举报人物质奖励。
2. 追偿机制,即人民检察院要求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返还救助款及其孳息的具体方式。一是建议规定人民检察院经调查核实,认为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已恢复经济赔偿能力的,应当及时向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发送要求其主动归还救助款及其孳息的书面通知。经通知,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主动归还的,追偿结束。二是建议规定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在收到追偿的通知后,有能力归还而拒不归还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要求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在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诉讼能力不足的情况下,还可以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在胜诉后,通过当事人自愿履行或者法院强制执行,依法扣除追偿款,其他款项交被害人或其近亲属处分。三是考虑到刑事被害人救助也是刑事诉讼的延续,且刑事追偿对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化解至关重要,可以考虑对有能力归还而拒不归还的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实施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方式,直接实现追偿。但是,由于上述手段在理论上属于侦查行为,因此,这些手段的采取必须坚持审慎、谦仰和比例的原则,对其使用可以进行明确的范围限制,作为紧急情况下或特殊情况下的追偿措施加以使用。
3. 处置机制,即人民检察院对已经追回的救助款及其孳息应当如何处理。有些人认为救助资金可以纳入本级政府预算,由财政部门负责管理,专款专用,也可以成立被害人救助基金,委托专门机构进行管理。[7]参照上述模式,实践中就追回的救助款及其孳息的处置具体也有两种做法:一是将其重新纳入财政,因为救助款本身是从财政中列支的,按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原则,应当重新交还财政。二是设立被害人救助专项基金,将其纳入该基金运作,从而实现专款专用。在前者中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重新交还财政,财政入账必须要设明确的收入进项项目,但目前检察机关由于不收取诉讼费,因此,财政系统中未设该进项项目,不好入账。另一方面,根据规定,部分地方被害人救助款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两级分比例负担的,在将救助款与孳息交还财政时,具体交还哪级财政,如需按比例交还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具体应如何操作也是一个问题。对此,建议采取第二种方式为宜,但考虑到该资金与社会上普遍称的“基金”存在区别,并不参与市场化运作,因此应将其名称修改为“设立被害人救助专项资金账户”,同时明确该账户由财政部门管理。按照现行的救助审批和资金发放体制,人民检察院负责初审、政法委负责审批、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人民检察院负责资金交付,在财政之外专门设立由财政部门管理的被害人救助专项资金账户符合文件的要求。同时,对检察机关而言,也遵循了“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资金使用原则,还可以避免资金管理与具体执法主体合一的角色混同问题。
4. 救济机制,即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检察院追偿行为有异议的解决办法。在刑事被害人救助追偿的过程中,由于实践的复杂性,人民检察院作出追偿的决定、确定追偿的具体数额以及采取的具体追偿方式,尤其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拍卖、变卖等方法追偿的,都直接涉及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的财产权利,部分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涉及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的权利,正所谓“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有必要设置权利遭受侵害的救济机制,也可以称为异议的处理机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规定,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参照这一规定关于被害人异议的处理程序,并考虑到有效发挥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功能,建议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检察院的追偿异议处理机制确定为: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人民检察院的追偿决定、追偿数额、追偿方式等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人民检察院的书面通知后七日内向作出追偿决定的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请求,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维持原决定的,被不起诉人或其赔偿义务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可在接到维持原决定的书面通知后七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再申诉。由此,通过设立两级申诉的方式为被追偿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设置一定的权利保障机制。
四、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的来源拓展展望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在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推行以及社会矛盾凸显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该制度的设立对于恢复被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防止被害人二次受害、实现案件当事人息诉罢访、预防被害人危害社会都具有重要作用,也体现了我们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司法温情,同时,对于树立司法权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也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如何确保这样好的制度能够进一步规范化、持续化和长效化应值得我们深思,而要做到规范化、持续化和长效化,就离不开充足的资金保障,这是比较实际的问题。
实践中,尽管《八部委意见》规定救助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划拨、社会及个人捐助,但从实践来看绝大部分是财政划拨,社会及个人捐助的资金极少。这种单一的资金来源渠道,显然不利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①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主要是拓宽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标准、增加救助的对象等,但这些良好的改革措施都需要充足的资金加以保障,而完全依靠政策财政划拨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其结果要么无法实现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的初衷,要么将增加财政的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地方检察机关甚至向全院干警摊派或者变相摊派,要求全院检察干警捐助。②据调研,某地检察机关救助专项基金共31.5万元,其中30万元来自财政拨款,1.5万元来自干警捐助。在目前,检察人员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无疑将使被害人救助这项好的制度在实践中受到部分人的消极抵制。
如上所述,为进一步拓展社会救助资金的来源渠道,除将追偿的资金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账户外,根据部分人的建议,还可以探索将追缴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对犯罪行为的罚金和没收的财产、监狱等监管场所在押人员的劳动创收等全部或者部分直接纳入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8]其原因在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言,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的侵害,由在追诉犯罪中国家收缴的犯罪收益予以弥补,既符合宏观上的责任自负原则,也体现了国家的这部分收入源于犯罪又用于平复犯罪的资金使用原则,应当是可行的。③实践中,目前上述资金中除监狱在押人员的劳动所得外,其余资金也是上缴国库的,但这种先上缴后下拨的方式,既浪费了行政资源,也降低了救助工作的效率。
[1]刘克梅.期待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完善[N].人民代表报,2012-02-16.
[2]李娜.刑事救助消解伤害如杯水车薪[N].法制日报,2013-05-13.
[3][5]陈彬.由救助走向补偿——论刑事被害人救济路径的选择[J].中国法学,2009,(2).
[4]李海滢.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未来走向[J].齐鲁学刊,2012,(2).
[6][7]宋英辉.特困刑事被害人救助实证研究[J].现代法学,2011,(5).
[8]代春波,姚嘉伟.检察机关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实证考察[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10).
The Establishment of Mechanisms of Aiding and Compensating Crime Victims in Prosecution Agencies
Jiang Li, Zhang Qingli, Qian Jincha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Song Jiang People’s Procuratorate, Shanghai 201620, China)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echanism of aiding crime victims, certain progress has been made, but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the mechanism of retrieving damag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echanism of retrieving damages for crime victims in prosecution agencies refers to retrieving damages from the victimizers. Nowadays, the formation of the mechanisms of aiding and compensating victims is based on legi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More exactly, it should consist of four mechanisms of discovery, retrieving, disposing and aid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ifelong effectives of the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o retrieving aiding funds, exploration can be made by retrieving prof ts of the crime, using f nes, and conf scating property and some or all income which is earned by criminals when they labor in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so as to widen the source of aiding funds.
Prosecution Agency; Victim; Criminal Aid; the Mechanism of Retrieving Damages
D916.3
B
1008-5750(2014)03-0069-(05)
10.13643/j.cnki.issn1008-5750.2014.03.013
2014-04-10 责任编辑:陈 汇
姜利(1973- ),女,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张庆立(1983- ),男,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钱金钗(1982- ),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