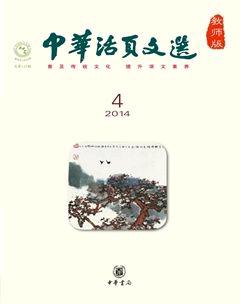和中学老师谈鲁迅作品教学(三)
钱理群
本文是本次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主要谈鲁迅作品的教学方式和对师生的影响。
“怎么教”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以语文的方式学习鲁迅,走进鲁迅”。这里有一个容易忽视,却至关重要的认识问题:鲁迅作品教学不同于我们通常说的鲁迅作品鉴赏,它是一个语文教育中的教学活动,因此,它必须遵循语文教学的一般规律,这里说的“以语文的方式学习鲁迅”,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自然涉及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等根本性的问题,这里无法展开来说。只能简单地说说和今天讨论有关的我的认识。我比较赞同福州著名的特级教师陈日亮先生的“文心”之说:语文课既要教学生“为文”,同时又要“育心”,而“文”与“心”是融为一体的,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如何理解“文”与“心”的融合?又有两句话:一是“文从心出”,从来没有无心之文,过去那种脱离了作者心灵世界(思想、情感、生命体验),从中抽出“知识”体系的教学法,是违背“文从心出”的基本常识的。但还有一句话:“心在文里”,从来没有无文之心,或文外之心,最近几年一些人脱离文字表达,抽出所谓“人文精神”而任意发挥的教学法,也同样违背了基本常识。我们现在就是要回到常识,从“文”和“心”的契合上把握课文。
以这样的“语文的方式读鲁迅”,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具体地分析和把握鲁迅每一篇作品“文”和“心”的契合点。每一篇都有不同的契合点,这是最要下工夫的,这个“点”抓准了,整个教学就“拎”起来了。
这样讲或许有些抽象,那么,我们也举几个例子。
我常常说,鲁迅的作品里往往有些“神来之笔”,这是作者创造力出人意料,甚至出乎自己预料的突然爆发,我们读和讲鲁迅作品就要抓住这些神来之笔。比如《阿长与〈山海经〉》最后一句:“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魂灵!”就把整篇文章的情绪推向高潮,把文章的意境也推到新的高度。我们的讲课就可以抓住这一点,引导学生把阅读课文的重心放在体会“我”对长妈妈的情感这一个中心点上,细心感悟和体会这种感情的发展、酝酿过程:开始在“厌恶”中蕴含着爱(要引导学生体味贬义词的背后的爱意),后来因长妈妈买来了心爱的《山海经》,而顿时觉得长妈妈高大起来(要引导学生辨析:鲁迅为什么要用“伟大”“神力”“敬意”这类的大词),最后才引发了这一声高呼——初中学生未必能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但却完全可以通过朗读,在情感上受到一定的震动,就够了。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神来之笔出现在文章中间的过渡段:“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我的”蟋蟀、覆盆子、木莲,而且还是“们”!中间还突然冒出了德语:这真是太特别了!从来没有人这么写过,鲁迅自己也就用了这么一次,这是不可重复的灵感。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抓住,引导学生体会:童年的“我”和大自然中的动植物亲密无间的感情,可能失去百草园这个乐园的沮丧,以及对未知的三味书屋的恐惧,以至情急之中讲出了外语单词。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句神来之笔是全文的一个纲,纲举而目张,我们的阅读和教学不妨以此为出发点,引发阅读的好奇心:为什么“我”要对蟋蟀们以朋友相称,这么舍不得离开百草园?“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去三味书屋?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到底有什么?对于“我”,分别意味着什么?在读完、学完全篇以后,还要回到这里来体会其更深的内在意义和韵味,并联系学生的现实生活:今天我们有自己的“百草园”吗?我们的学校和“三味书屋”比较,有什么异同?这就是“会文章之意,而及学生之心”了。
这样的文和心的契合点,是因文而异的。比如《孔乙己》,我在教学中找到的“点”,就是其“叙述人称”的选择。在学生熟悉故事基本情节以后,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由谁来讲孔乙己的故事?可以由孔乙己自己讲,也可以由酒店掌柜或酒客来讲,但鲁迅却选择了“我”,一个酒店的小伙计来讲,这是为什么?接着又引导学生细读“孔乙己被丁举人吊起来打”的故事,提醒学生注意,鲁迅没有正面叙述这个悲惨的故事,而是通过“我”怎样听酒客和掌柜如何议论这件事,侧面讲出来的。由此而点明:鲁迅最关心的,或者说他最感痛心的,不只是孔乙己受拷打的不幸,更是周围的人对他的痛苦的冷漠态度,以及孔乙己这样的自命高人一等的读书人却在人们眼里毫无地位的尴尬。因此选择小伙计这样的酒店里的旁观者讲故事,就最能表达鲁迅的这个发现和意图。在学生有了这样的基本感悟以后,又引导学生注意小说中“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这句概括语,再去细读“孔乙己和我的对话”以及“孔乙己的最后”这两个场景,来加深对孔乙己悲剧命运的认识。可以看出,整个教学过程,是一个“由怎么写到写什么,再由写什么回到怎么写”的过程,正是在两者之间往返中,学生逐渐进入了鲁迅所描述的情境之中,体味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以及鲁迅的情感。最后,还是回到“怎么写”上面来,要求学生改换叙述者(改成孔乙己自己,或掌柜或酒客)重新叙述孔乙己的故事。通过这样的参与式的重写,鲁迅的文本(他怎样写和写什么)就融入学生的写作生活里了。
鲁迅曾经引用惠列赛耶夫的话说过:“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因此,他认为,研究作家怎样改文章,“这确实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我因此向老师们推荐朱正先生的《跟鲁迅学改文章》这本书(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该书收集了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课文的原稿和改定稿,并有具体解说和分析。我这里要说的是,鲁迅的少数文本是在不同的时间写了两次的,如语文课本选入的《风筝》,在1919年所写的《自言自语》里就有一篇《我的兄弟》(收《鲁迅全集》第8卷),写的是同一个题材,同一件事,写法要简略得多。类似的情况还有《自言自语》里的《我的父亲》和收入《朝花夕拾》里的《五猖会》,以及《自言自语》里的《火和冰》和《野草》里的《死火》,都是一文二作。因此,讲《风筝》,完全可以和《我的兄弟》对照起来读,看鲁迅怎样把一个相对单薄的文本,扩展成一个十分丰富的文本,看他从中增添了什么,又怎样增添,这不但会加深学生对《风筝》怎么写、写什么的理解,而且也向学生提供了一个如何扩展、修改自己的文章的范例。我曾写有文章,作对比阅读,可参考。
关于“怎么教”,我的第三条建议是:鲁迅作品教学要删繁就简,要有所讲,有所不讲,不必“讲深讲透”。其理由有三。
其一,鲁迅作品作为民族原创性、源泉性的经典,是要读一辈子的。同一篇文章,在不同的年龄、生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时代、社会环境下,都会读出不同的意味和意思。这是一个说不尽的鲁迅,他的作品是常读常新的。因此,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读鲁迅作品是有不同的要求的。中学阶段,学生还处于学习成长的时期,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知识储备,就决定了他们对鲁迅的阅读与理解,只能是初步的(当然,不排斥个别的学生可以达到相当的深度)。在中学阶段的鲁迅作品教学的任务,只有“播下种子”,就是说,要让学生亲近鲁迅,被鲁迅所吸引,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需要鲁迅,把鲁迅作为自己汉语家园和精神家园的重要源泉,并大体知道鲁迅有哪些作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认清门牌号码”),为以后读鲁迅打下基础,这就达到目的了。绝不能期待、要求第一次读鲁迅作品就读深读透、全部弄懂,似懂非懂才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学生读鲁迅作品印象不好,不愿意读,那也很正常,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又会回过头来读鲁迅作品。有的学生以后再也不读,也属正常,鲁迅毕竟不是唯一的。
其二,鲁迅的文本,自有其复杂性和丰富性,是复杂与单纯,深刻和平常,荒凉和温暖的奇妙结合。即使选入教材,我们认为比较适合学生阅读的鲁迅作品,也有许多随手拈来的对现实某些人和事、某种文化现象的批评,借题发挥的议论,典故,引文,还有许多有很大寓意性的文字,这都形成了他的文本的丰富性,对成年读者来说,读这样的摇曳多姿的文字,自然是极大的享受。但对阅历和知识都不够的中学生,就会形成阅读的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在教学中对鲁迅文本作某种处理,即有所讲,有所不讲。对学生必须懂的,就要大讲特讲,有些难点,也要采取一些教学手段,帮助学生理解;但有些学生不懂、也不要求懂的文字,就可以不讲,把问题留在那里,让学生在以后的阅读里解决。也就是说,在中学语文中的鲁迅作品教学,要将鲁迅文本相对单纯化,当然,这是保存了一定丰富性的单纯。
其三,不能把老师自己懂的东西,全部教给学生。有经验的教师,既要从鲁迅的文本的实际出发,又要结合教材的要求,以及学生的接受情况,确定本课文教学的具体目的和要求:哪些是必须让学生懂的,就要牢牢把握,认真讲清楚、讲充分;哪些是不必要求学生懂的,就可以少讲,甚至不讲。这就是“删繁就简”,有所不讲,才有所讲。总体来说,语文教学,特别是鲁迅作品的教学,应该是丰富的;但具体到某一篇课文、每一堂课,教学目的要相对单纯,教学内容、方法则可以、应该丰富多彩。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在有所讲中,还要区分:哪些是要求全体学生都掌握的;哪些则是只有少数理解力比较强的学生能够懂的。我是主张在面对全体学生的前提下,也要顾及在学习(特别是鲁迅作品学习)上有较高要求的学生,这些学生在班级学习里往往有影响,不可忽视。因此,我在讲鲁迅时,在照顾大多数学生的理解水平,以调动全体学生的积极性的同时,也适当讲一些对中学生来说,稍微深一点的在大学里才讲的内容,对鲁迅有特殊兴趣的学生自然大受启发,其他学生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也感觉到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和境界的存在。回到刚才所说“有所讲,有所不讲”的问题上,我觉得关键是要在“吃透教材(鲁迅作品),吃透教学大纲和教材,吃透学生”这“三吃透”上下工夫。这三吃透,原本是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当语文教师时提出的要求,我觉得今天也还不失其意义。
关于“怎么教”,最后还要谈一个还没有引起广泛重视,但却很重要的新的教育课题:“如何运用网络新技术进行包括鲁迅作品教学在内的语文教育”。网络在中国城市里的迅速普及,是这些年影响深远的变化和发展,它同时也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包括语文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许多人都更关注挑战的方面,而且多从消极方面去围堵,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注意到,有些语文老师已经开始从积极方面把网络技术的出现,看作是解决语文教育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新机遇,作了大胆的试验,他们的试验又往往从鲁迅作品教学入手,这本身就很有意思。我曾经为北师大附中邓虹老师的试验写了一篇长文,收在我的《语文教育新论》里,这里仅说一点大意。她在讲鲁迅的《药》时,自觉地运用了网络技术,试图把网络的“虚拟课堂”和教室的“实体课堂”结合起来,分成三个教学阶段。首先是网络的“预习”:要求学生利用网络技术收集有关鲁迅《药》的信息;然后根据自己读了《药》以后的最初感受、认识在网上交流。这样,就由原来的学生个人关在家里预习,变成了全班同学在网上的相互争论和启发,老师也借此机会了解了学生的初步接受情况,便于有的放矢地设计自己的教案。而且学生因为有了争论,产生了许多问题,迫不及待地要在课堂上讨论。这样,“课堂实体教学”里,老师和学生都取得了主动权,学生带着问题学习,老师则有针对性地讲解:将学生在网络预习中发表的好意见加以展开和升华,对认识上的不足以至误读予以纠正与引导,教学重点与难点的把握都比较准确,符合学生实际,就较好地营造了一个“作者、学生、老师良性互动”的教学氛围。最有创造性的,是第三个教学环节的设置:再回到网络写网上作文,题目是“和鲁迅一起写《药》”,要求学生选择一个特定的叙述视角,根据鲁迅文本提供的材料,重新写一篇《药》。于是,有的学生就选择“路灯”的视角,写他看到的故事;有的写康大叔的故事;有的把小说侧面描写的夏瑜改成正面讲述;有的专门写小说里红、黑、白颜色的变幻,等等。这样的作文,改变了过去“学生写、老师看”的作文模式,同时发表在网上,供老师和全班同学欣赏和评论,这就自然引发了良性的竞争:谁都希望写出最有创意的文章,最后甚至带有游戏的意味。但也正是这样的符合青少年年龄特征的竞争性、游戏性的写作,迫使学生反复阅读、消化鲁迅的原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进行再创作。这既是语文教育、鲁迅作品教学的创新,又是对学生使用网络的一个正面引导。当然,这样的试验才开始,问题也不少,但其提供的教学前景,还是令人鼓舞的。
我的这一篇演讲,实在太长了。最后还要说一点,中学的鲁迅作品教学不仅学生受益,而且也是教师提升自己的人文精神、语文素养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一位学生曾对我所上的鲁迅课作了这样的概括:“这门课,是一个鲁迅和我们,老师和我们,自己和自己对话的过程。”这确实是一门在与鲁迅对话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共同成长的课。还有一位学生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正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需要更大气,更深刻的思想激发。”说得真好!鲁迅对我们的中学生和老师,最大的作用,就是他的作品使我们变得大气和深刻:这是人的精神的大气、深刻,也是教学境界的大气与深刻。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教育、大学教育和中小学教育,今天的语文教育,太需要大气和深刻了。
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选自《经典阅读与语文教学》,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