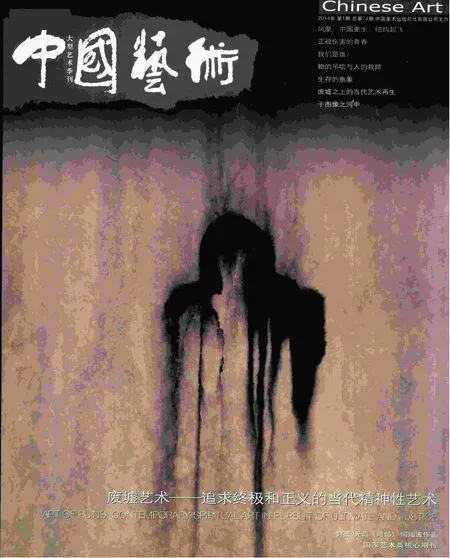于图像之河中——赫尔加·麦斯特对话比亚特·斯特鲁利
王文婷/译
(注:由于篇幅限制,采访内容有部分删节)
编者按:摄影艺术家比亚特·斯特鲁利1957年出生于瑞士小城阿尔特杜夫(Altdorf),曾在罗马、巴黎和纽约生活与创作,现主要工作、生活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和布鲁塞尔。赫尔加·麦斯特与艺术家在布鲁塞尔见面并进行了对话。正是在布鲁塞尔,艺术家创作了作品“世界图像”系列,展示了一些对镜头浑然不觉的人们。这次对话从艺术家的生平、习画经历进入,进而谈到设备、技术,最后进入时间、记忆与生活的哲学层面,由远及近地展现了这位摄影艺术家的创作思路及艺术思考。《艺术论坛》杂志总第214期(2012年3—4月)刊发了此次对话,本期“域外传真”将二人的对话翻译成中文,以飨读者。

图1 比亚特·斯特鲁利在布鲁塞尔的工作室中 2011年 摄影者:Helga Meister
赫尔加·麦斯特(以下简称H):我们从你的履历开始聊吧。你是瑞士人,1957年生,生于阿尔特杜夫,请问此为何地?
比亚特·斯特鲁力(以下简称B):在瑞士中部,就是威廉·泰尔(译注:瑞士自由斗士W ilhelm Tell)中用弓箭射中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的地方。
H:你来自怎样的家庭?你的父母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吗?
B:没有,我来自一个普通的瑞士中产阶级家庭。不过我只有在很小的时候住在阿尔特杜夫,之后就搬到苏黎世附近。最近我在老家阿尔特杜夫为当地一家艺术疗愈中心做了一个公共艺术项目,用透明的大幅儿童肖像装点这家艺术疗愈中心的窗户。在创作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才得以和童年时期的家乡风景重逢。
H:你在1977年进入苏黎世和巴塞尔的美术学校上学,但前后只上了三年。你当时学的是什么?

图3 Retiro Bs As 亚克力盒子上有色印刷 150cmx200cm 2011年 比亚特·斯特鲁利Beat Streuli

图4 曼哈顿09 广告版数码印刷 150cmx225cm 2009年 比亚特·斯特鲁利?Beat Streuli
B:我先在苏黎世美术学校读自由艺术预科,主要学习绘画——这是当时在瑞士德语区学习艺术的唯一选择。我的老师是弗兰茨·费迪尔(Franz Fedier),一位抽象画家,他的绘画从没有形体发展到有清晰明确的形状和色域。
H:这种形状清晰的抽象艺术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B:对我来说美国的极少主义艺术更有影响力。我当时仔细研究了唐·贾德(Don Judd)和索尔·勒维特(Sol Lew itt)的雕塑。对我而言,关于载体与表面、边框与实体的基本问题更加重要。
H:边框和你的作品有什么关系?
B:我们必须随时记住,照片也是一个实体,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平面的雕塑,因此内部和外部的边界是清晰可辨的。
H:也就是说,在你转向摄影之前,先把20世纪的前卫艺术学习了一遍?
B:是的,对我来说经典前卫艺术的终点就是美国的极少主义艺术,比如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的白色方形。在此以后,年轻艺术家已经不能再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了。在此背景下,我认为摄影就是开拓新道路的理想工具。摄影的历史与前卫艺术史不同,它是平行于前卫艺术发展史的另一条线索,艺术家从中能学到另一套东西。
H:你当时是怎么作画的,都画了些什么作品?
B:我学习了素描、水彩和拼贴,此外还用现成品进行创作。比如格哈德·梅尔茨(Gerhard Merz)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当我上学的时候,他的综合材料和字牌作品正好在苏黎世展出。他的纯粹主义构图在当时令我耳目一新。当我感到在瑞士已经无法继续深入地学习艺术时,我就到柏林艺术学院(HdK)访学,并开始了一段四处漂流的岁月。
H:你是怎样受到人们注意的?
B:那时在瑞士的各大艺术展览馆里有所谓的“圣诞大展”,每个人都可以送自己的作品去参展。我在让-克里斯多夫·安曼(Jean-Christophe Amm ann)任馆长的巴塞尔艺术展览馆参加了圣诞大展,此后他就开始资助我的艺术。我在他那儿展出的是一组黑白照片拼贴,由字迹、碎片和一些具象元素构成。我在艺术博物馆的第一次展出是在1986年的阿尔高尔艺术博物馆(Argauer Kunstmuseum),当时的馆长是比亚特·维斯莫尔(Beat Wismer),他现在任职于杜塞尔多夫的艺术殿堂博物馆(M useum Kunstpalast)。
H:但今天你的艺术履历是从30岁才开始的,当时你在巴黎、罗马和纽约居住和创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B:当时我想继续探索国外的生活,也想继续待在大城市。我30岁时在一笔画室赞助金的资助下来到巴黎和罗马,有机会在那儿作丰富的摄影探索。之后我出版了关于罗马和巴黎的摄影集,其中有很多建筑元素,也有电影式的——公路电影风格的图像。这本摄影集帮助我获得了纽约P.S.1的赞助金。
H:我读到,你15岁时得到一部相机,17岁得到一部长距镜头。是这样的吗?
B:是的,我有一间小小的暗房,摄影是我青少年时期的爱好。
H:长距镜头的原理是用望远镜片把远处的物体放大,从而达到视觉上拉近距离的效果。它的焦深很浅,只有当试图锐化主要对象时才会使用这种镜头。你为什么对长距镜头产生兴趣?
B:对我来说,比起将远处的物体拉近而言,长距镜头焦深很浅的特质更有意思,它使得画面的背景变得非常模糊。这种视觉效果更贴近于人类的肉眼和大脑功能,因为它们总是立刻把不重要的事物忽略不见。人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人们与之对话的对面之人的脸上,因此透过中等长距镜头的观看模式更贴近于人类的目光。

图5 比亚特·斯特鲁利2009年的灯箱装置《La Voie publique》是根特市圣彼得站永久装置的一部分Beat Streuli
H:当你用长距镜头创作时,你和对象之间明显有很多的空间。你是否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制造某种“软性”的效果?这样的图像和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的人物肖像所具有的那种锐利的质感显然不同。
B:对我而言,对现实进行可触可感的重现一直很重要。极度的锐化,即人们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每一处细节,是有悖于我的这一目标的。观众不会因此而获得对外部真实的锐利观看,而是正好相反。这样的画面仿佛在眼前树立了某种过于光滑的表面,观者很难透过它看到真正的外部世界。我们肉眼所见的真实并不像照相写实主义所表现的那样。肉眼的观看永远存在某种介于清晰、不清晰和运动之间的区域,正因如此才使观看具有了感官的愉悦。这样所见的真实才显得那么近,那么具有触感。
H:你的照片诱使我走进图像里,也包括走进图像所展示的内容里。
B:我想要在摄影中达到一种开放性,通过这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在我的作品里。同时,我也不希望对观者的视线作过多的引导。
H:现在你是用相机还是摄像机创作?
B:我从很早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相机之余也使用摄像机创作。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有趣的时间点:因为相机和摄像机越来越成为一体,所以人们可以用相机拍出同样好的视频。这对于摄影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虽然看起来这不过是技术上的一个小进步。自此以来,我的作品就处于运动画面和静态画面之间的交接点上,而二者也因此变得更加彼此接近。由此产生的是一种全新的视觉思维方式。
H:你会使用视频中的截屏吗?
B:视频截屏的表现力还是远远逊于照片,它的图像质量不足以达到我的目标。但话说回来,视频图像比从前更接近于照片,因为它是用同一台相机、同样的传感元件拍摄同样的对象。从所有的图像参数——色相、景深等等来看,它都非常接近照相出来的图像,所以我就可以实现图像和影片的无缝融合。除此之外,我可以在一两秒钟之内用一台相机拍出十张连续画面,从中选出我认为最优的。但我估计,再过两年人们就可以直接用摄像模式拍摄这样的连续影像,并从数百张静态高清画面中挑出最好的。这样,一张张静态的图像又将重新融入时间的河流,这简直太神奇了!至于到那个时候,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摄影是否还作为一种取像技术继续存在,我是不知道的。而这对未来的视觉语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实在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

H:这样的发展和你的创作是相对立的,你一直在捕捉动态的瞬间。
B:我从来不认为作为技术媒介的摄影或者录像截屏是个问题。我从来就可以使用一切合适的工具,只要它能帮助我转化和再现真实。
H:你的照片序列有一种音乐的韵律感。运动的瞬间,停止和前进。这种时间性总是默默地发生。时间的运转、运动过程的放慢对你来说重要吗?
B:节奏是一种基本的东西,它为一件作品提供了结构性的基调,与人类的感知体系形成平行和共振。我常常在创作中使用慢动作,不过它始终只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而已。它是为了更好地用视觉方式呈现流动性的东西。话说回来,的确有这样一个问题:当人们把一部影片无限放慢时,它最终会不会变成照片?
H:何谓定格,它算是一幅单独的图画,一张照片吗?
B:我们可以把照片视作时间的停留,或者对时间的截取。这是两种不同的视角。对时间本身的认识也可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也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人们通过时间从开头走到结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认为,人们是静止的,而时间从人的身边呼啸而过,好像一列火车那样。有趣的是,照片在我们的视觉世界里总是具有一种极大的精确性,尽管随着多媒体科技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时间性的记录工具可以供我们选择。
H: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
B:如果照片足够好,它就可以包含拍照这一刻之前与之后的信息,以及许多其他信息。它是感官图像,也就是有灵的图像,或者适合于我们记忆生成的图像。也就是说,它将许多个瞬间和许多种角度融汇凝结成一个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显示出一个情境或一个人的整体面貌。在这点上,照片和电影相比而言更加集中、更加有效果。此外就和绘画一样,照片也能使创作者的视点得到具象化的呈现。有一些照片因此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图标,或成为某种图腾,这就远远超越“凝固的瞬间”这一意义了。

H:在谈论你现在的作品之前,我还是想先了解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回头看来,你好像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似的。但现实几乎不可能这样发展。你没有受过系统的摄影教育,也不属于所谓的“贝切尔的门生”(译注:即“新客观摄影”发起者、摄影艺术家贝切尔夫妇——Be rnd & Hilla Becher——在20世纪末培养的一批摄影艺术家)。正因如此你能够发展出自己独特的东西。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去杜塞尔多夫的?
B:20世纪80年代末。但我当然不认为自己是所谓杜塞尔多夫“学派”的成员。换言之,杜塞尔多夫也不只是贝切尔师生的天下。2009年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的杜塞尔多夫摄影展就展示了这一区域摄影作品的多样化。
H:人们可以分辨出你照片的地域性吗?生活在纽约、哥本哈根和塔拉戈纳的人们在照片上分别是怎样的?
B:在哥本哈根和塔拉戈纳我都拍过学校的课堂,拍过青少年。如果要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我会说丹麦的孩子都金发,面色苍白;塔拉戈纳的孩子则皮肤黝黑,具有南部民族的魅力。但这显然太肤浅了。事实上我觉得不同地域的人们的共同点更有意思。在布鲁塞尔,我想用镜头关注这儿的摩洛哥—非洲人聚居区,而当我拍摄他们时,我的目光将和我在拍摄苏黎世的银行家时别无二致。
H:你不会真的要拍苏黎世的银行家吧?你的作品里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还有许多女孩子。
B: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开始关注相对年轻的族群。在大城市的市中心,人口构成总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而我拍摄的就是我四周所见。在过去十年中,我的作品越来越关注不同的生活片段——时不时地也会在我作品里出现银行家的生活片段……就像拉里·克拉克(译注:Larry Clarke,因拍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年人放纵生活而出名的美国摄影家)说过的那样,我为之着迷的并非青春,而是社会。
H:在你位于杜塞尔多夫储蓄银行玻璃立面上的作品中,那些人物肖像的形象和你今天的作品完全不同。
B:我在20世纪90年代尝试过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即不再抓拍,而是先和路人攀谈,再请求对方允许我为他们拍照。我当时想要更多地认识这些面孔,而这是偶然路过的抓拍无法达到的。此外,为银行大楼立面而作的项目无论如何也必须征求拍摄对象的同意才可以。所以人们在观看这些照片时,有时候会感觉到这种不一样的情景。
H:你当时有刻意和托马斯·鲁夫的学生肖像区别开来吗?
B:不,当然没有,这从一开始就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托马斯·鲁夫的学生肖像系列很棒,因为它们虽然被一丝不苟地导演和策划,但与此同时它们所展示的情景又非常具有即时感。我从来没有要和“贝切尔的门生”们刻意划清界限的意思。相反,我和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点。此外,像杰夫·沃尔(Jeff W all) 或君特·弗尔格(Guenter Foerg)等“贝切尔的门生”的早期作品在当时是有重要影响力的。
H:你是如何被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圈接受的?
B:20世纪90年代初一切都很酷。如果你不是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学生,而想作为一个保守的瑞士人而被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圈接纳,那确实会有点难度。不过这终于还是发生了。
H:人们喜欢将街头摄影和偷窥癖这一概念联系起来,也就是在对某人的观察中产生的快感,尽管这种观看是在一定距离之外的。你对此怎么看?
B:我的作品显然和一般意义的偷窥癖毫无关系。至于我照片中出现的年轻女性,我想是马蒂斯在被问及他为什么人到老年还为漂亮女孩所吸引时曾经回答道,就算时光流逝也无法阻止人们欣赏夕阳之美。可惜在我们这个很容易陷入新保守主义的世界里,这样的观点偶尔还是被批判的。

H:你的摄影作品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片段性,亦即从一个运动过程中截取某个完美的瞬间。你是如何确定片段的?
B:当画家描绘一个情景时,他自己设计一切。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都按照画家的构思组合起来。而当人用镜头面对未经设计的真实世界时,会发现真实总是抗拒成为艺术家设想的样子。画家用画笔建构或修改的东西,摄影师要通过对现实的筛选获得。第一步是从大量材料中精确地择取可用之材,而或许还有第二步即通过截取画面的某个部分。但我极少使用第二步,就像我极少使用后期修图一样。
H:关于肖像权,当你拍摄某位不知道自己被拍的人物时,法律上是怎么处理的?当人们不期然看到他们自己出现在你的作品中时会作何反应?
B:在我的作品里认出自己的人不少。但以我的经验来看,这些人大多联想到的是在电视剧里以路人身份偶然出境并因此“出名五分钟”的情况,所以对此的反应多半是觉得有趣或者好奇,而不会立刻想到肖像权的事。毕竟人的脸受之父母,而不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肖像权其实是种奇特的想法。不过考虑到一张照片可能被用于政治宣传或商业广告,肖像权的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
H:你在拍完某人以后也不会问那人要拍摄许可?
B: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拍的人有数千名,如果要完成这个动作,我得雇佣一大群助理来帮我确认照片里的人是谁。
H:街头生活总是有某种平庸感,或者说某种不言而喻的感觉。你对这种直接的、在某种条件下显得平庸无奇的现实有何看法?
B:有很多摄影师都有意将平庸作为平庸本身来呈现,这不是很有趣。如果我只是拍摄一处毫无内容的街角,而且也按照其毫无内容的本相呈现出来,那在我看来就不是足够的。为什么马奈描绘福烈斯—贝热尔酒吧的女孩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品?不是因为画中有酒吧,也不是因为它特别漂亮,而是画家对镜子的巧妙处理带有某种艺术理念。但使它真正成为标志性的伟大作品的原因,是极其微妙难说的。正是平庸的综合体中多出来的这一点点微妙之处,才能流传永世、感动观者。
H:你能想象你的艺术中没有人吗?
B:不能。
H:在关于你作品的文章中常常提到,你从人群中抽出某些个体。但我现在和你在布鲁塞尔,从窗户看出去根本没有能供你“抽出个体”的大批人群。
B:我的摄影作品里很少出现人群,主要是个体或数个人,其背景也多半不是人群。大量人群更多出现在我的影像作品里。
H:在你的作品中,形式要素常常很重要。当我在苏黎世看到你拍摄的一位身处充满装饰的金属大门前的女孩,她的倒影出现在玻璃窗上时,我发现画面本身就制造了一种电影场景的瞬间。这种取景是怎么产生的?
B:人群的移动是迅速的。我会快速拍摄连续画面,再从中选择最好的,这个过程混合了有意的构图和完全的意外。微小的叙事性是苏黎世展出的作品的特别要素,比如另一幅照片中的男子正看着前幅照片里的女孩,或者同一张钱币在另一幅照片里从一只手换到了另一只手中。
H:关于光线:你的照片通过对自然光的运用获得了活力,这种光线常常会改变事物的结构。你会在创作中使用闪光灯吗?
B:不会,闪光灯属于极少数我从未尝试过的东西。
H:时间和时间性总是指向一个结束。而你对时间的诠释是更加积极的,并不只有线性的指向。
B:罗兰·巴特说过,一张照片展示的是确定发生过的——同时也是确定已经逝去的。这一表述非常精彩,也是对这一命题的最佳表述。不过我在作品中并不会想到过去,我并非作为宏大的人类历程的记录者而创作我的作品的。
H:最后的问题:你也曾经以时尚摄影和政治选举宣传海报为例,说明非语言交流的不言而喻性以及其类型的不同性是并存的?
B:这些视觉世界,当然也包括电影,是对我最初的影响。当我刚开始街头摄影时,看到街上有奥利维欧·托斯贾尼(O liv ie ro Toscani)为贝纳通拍摄的巨幅商业广告,它们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它们的美和智慧并不逊色于纯艺术,但它们发生在公共空间,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