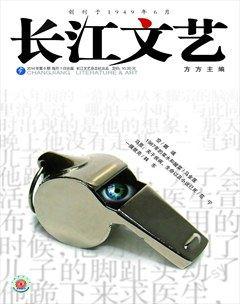跳出印刷文明,重新思考“文学性”
邵燕君
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对麦克卢汉半个世纪前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理论终于有了切身的体会。麦克卢汉提醒我们跳出哺育我们长大的印刷文明的局限,以人类文明整体发展的“大局观”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麦克卢汉看来,任何媒介都不外乎人的感觉和感官的扩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视觉能力的延伸,广播是人的听觉能力的延伸,电视则是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能力的综合延伸。他认为在机械时代,人类已经完成了一切身体功能的延伸,进入到电子时代,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得以延伸。所谓“媒介即讯息”指的是,“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塑造历史和社会的隐蔽力量。媒介和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的感官能力由“统合”—“分化”—“再统合”的历史。拼音文字发明之前,部落人感觉器官的使用是均衡的。拼音文字的发明打破了部落人眼、耳、口、鼻、舌、身的平衡,突出了眼睛的视觉。从古希腊荷马开始的文字时代在人类社会持续了约两千年,而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出现才最终结束了部落文化,保证了视觉偏见的首要地位,进一步加重了感官使用失衡的程度。以电报发明预示的电子革命的来临,尤其是电视和网络多媒体的出现,则恢复了人的感官使用比例的平衡,使眼、耳、口、鼻、舌、身重新均衡使用,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重新统合化。电子时代由于人的感觉器官重新统合化,人们比分割化的过去更多地使用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尽管是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然而它又是综合的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方式之一,然而它又是单一的思维方式。在更深广的意义上,形象思维包括了逻辑思维。麦克卢汉对电子革命可能带来的“地球村”的乌托邦想象是以前文字时代为蓝本的。在他看来,以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为基本判断标准,人类社会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前文字时代/部落时代、古登堡时代、电子时代。我们以往认为的“文明时代”在他这里恰恰是“文明陷落的时代”,是两个伟大的“有机文明”之间的插曲。
今天看来,麦克卢汉半个世纪之前的预言虽不免过于理想乐观,但对于我们思考互联网时代的文艺生态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仍是超前的。在这一理论视野的观照下,很多艺术“原理”、文学“常识”要被颠覆,因为这些“原理”、“常识”都是建立在以文字为中心的印刷文明的价值体系和审美经验上的。
首先,我们必须要重新认识的是,文字的艺术是“转译”的艺术,是“视觉偏见”、“文字统治”的显现。印刷文明解决了跨时空传输的问题,但封闭了所有感官,只留下视觉,而人们目力所见的并非形象而是文字。这就需要一群受过专门训练的作家和读者系统地“转译”和解读——作家们在一个时空孤独地编码,读者在另一个时空孤独地解码——其中“误读”的必然性甚至成就了“接受美学”这样一门学科。这种超越时空的“编码—解码”过程,使文学艺术具有了某种神秘性、永恒性和专业性。即使是最低等级的大众读者也必须识文断字,具备一定的在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之间转换的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与作家共享某种文学传统。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类的主导艺术形式是发乎“肉声”的诗歌和成于“肉身”的戏剧,印刷术发明之后才转变为可阅读的小说。印刷文明极大丰富了人类的艺术资源,也使“文字统治”成为可能。
我们今天很多“艺术的法则”都是建立在印刷文明体系下的“视觉偏见”、“文字统治”的基础上的。
比如,文学创作中常被视为极高境界的“通感”,要求作家精准地选择描写对象和细节,抓住通感的触发点,令“各司其职”的五官“兼差”、“越职”,尽可能地把感观全部调动起来{2}。今天看来,这种登峰造极的技艺恰恰出于“文字艺术”的迫不得已。多媒体时代不需要触类旁通,而是五官齐开,全身心卷入,甚至是“实在界”和“虚拟界”的难以区分。在这个意义上,“通感”的技艺就如残障人士的特长,虽非常人之所及,也是常人不必学习的。
再如“言简意赅”、“惜墨如金”等美学原则,也和纸媒时代物质的有限性直接相关。在数码时代,不再有字数版面限制,长短不再是篇幅问题而是时间问题,而时间长短取决于受众的需要。当粉丝们需要一部他们喜欢的作品长期陪伴时,总是希望它尽量地长,甚至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注水”。精简含蓄的美学原则也与理性主义压抑克制的心理模式深切相关,读者习惯于在有节制的放纵中深切体味,在对有限文本的反复咀嚼中充分调动想象力以达到进一步满足。而电子时代同时是消费时代,快感原则至上,人们需要大量地、直接地、充分地被满足。在网络写作中,任何“留白空缺”、“冰山一角”都会被视为“挖坑不填”的“不道德”行为,受众的想象力不再用于“创造性理解”,而是通过与作者及时互动等方式直接参与创作进程,或者干脆自己写“同人”。
印刷时代的写作对作品完整性和完满性的追求也与先创作再出版的生产方式相关,而在创作者和接受者不再被隔绝的口头文学时代和电子写作时代,创作往往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完成、完善,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为例,《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积累型”作品,有数百年的“集体创作”历史,而它们之所以在明朝中叶集中被文人整理成书,正是印刷业发展和市民社会成熟的结果。图书业的进一步发展催生了《金瓶梅》《红楼梦》这样的由文人独立创作完成的小说,而直到清末,中国古典小说都保持着“章回体”,保持着“客官”“且听下回分解”等口头文学的遗风。中国小说写作真正进入“印刷时代”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现代白话小说才是彻底遵循印刷文明模式的写作。而网络文学兴起后,“新文学”传统基本被绕过去,网络写手们直承中国古典小说写作传统,向“四大名著”致敬的小说和相关同人写作持续不断。这不仅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亲缘性,也出于生产机制上的相通性。试想,如果《红楼梦》的写作是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进行,“增删五次”可能是在“更文”的过程中完成的,也可能是完结后的再修改,而曹雪芹的“高参”将不仅是脂砚斋这样几个身边的朋友,而是一个“粉丝团”,自然,这应该是一个相当高端、小众精英的“粉丝团”。如果这样,曹雪芹可能不致穷困潦倒,但《红楼梦》也未必能达到如此完美精致的境界。在孤独中反复打磨以求完美精致,一朝付梓,洛阳纸贵——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与印刷出版机制相连的创作心理。正如“文字转译”的迫不得已成就了“通感”的艺术,印刷出版机制的限制也成就了经典作品的完整性和完美性。但与对作品完整性和完美性的追求相连的对不朽的追求,则是一种带有基督教神学色彩的现代主义信仰。“背对读者”“为后世写作”则更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神话,在前现代和后现代,人们重视的是作品在当下流行,代代流传是不期然的结果。印刷文明的终结,也是“作者神话”的终结。
跳出印刷文明的局限,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文学性”的问题。并不是说人类在印刷文明时代形成的一切关于文学的标准和审美习惯都要被废弃,而是要如麦克卢汉所言引入“新的尺度”。必须把“新的尺度” 带来的“感官比例和平衡”的变化引入对文化的判断标准之中。对于移动互联网时代文艺形态的想象,我们不能延续任何一种“网络移民”的路径,而是要考察网络新生——来自前文字时代的“文学性”必然穿越印刷时代,以“网络性”的形态重新生长出来。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抱有任何既有的观念来界定、评价网络时代的文学,而且必须接受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在网络时代,作为“文字的艺术”的文学将不再居于文艺的核心位置。鉴于互联网的媒介性质,未来的主导文艺形式很可能是电子游戏;而文学,除了作为一种小众流行的高雅传统外,主要将以“游戏文本”的形态存在,其“文学性”必须在“新尺度”下重新建立。
总之,身处媒介革命的千年之变,我们不能固守任何“本质性”的观念,或许只能以“精灵”这样的抽象意象来理解“文学性”。它既不绑定于某种媒介,也不绑定于某种形式,更不绑定于某种标准。“内容一经媒介即发生相应变化”应该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的另一种重要含义。
注:
{1}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增订评注本),何道宽译,第20页,译林出版社2011年。
{2}最早全面阐述这一概念的是钱锺书(《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发表了论文《通感》),从心理学角度入手,认为“按逻辑思维,五官各有所司,不兼差也不越职”,但“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诸如此类,在普通语言里经常出现”。 钱锺书:《七缀集》,第63页、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