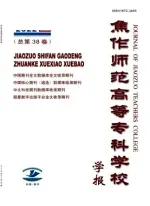“失败主义”是否成立:试述一则中国托派研究史料的争论
杨 强
(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8)
在中国托派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少争议,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托派是否在解放战争中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失败主义”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争议双方的分歧在于对一则史料的认定。
一、分歧的由来
唐宝林先生于1994年8月在台北出版了《中国托派史》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托派历史的著作。该书在第六章第二节叙述渡江战役后中国托派的应对时,使用了“对中共实行失败主义”的标题。这个观点所依据的材料是《叛逆者》第1期刊登的《内战问题的总结》一文。文章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保护富农的政策,渡江后的解放战争已经“变质”,“由领导农民转变为抛弃农民,转变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共产党已由“农民党”变为“资产阶级党”,“军队则由农民军变成资产阶级雇佣军。现在内战在中共方面,不再是一个农民运动,而是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的战争,内战由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战争,变成资产阶级的争夺战。它在客观上的进步性消失了,成为一个反动的战争。由于内战性质的转变,我们的态度也转变,不再保护内战,应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不过应该注意在中共方面实行失败主义,并不是促使国民党胜利”。[1]310对于这个《叛逆者》的杂志,作者在书中称是上海解放后“多数派”①在是否应该对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实行“失败主义”的问题上,中国托派内部出现了分歧,随后分成两派,反对实行“失败主义”的一方面成为“多数派”,以彭述之、刘家良为代表,另一方组成“少数派”,以郑超麟、王凡西为代表。后来两派各自建党,分别称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和“国际主义工人党”。潜伏组织的地下反共油印刊物,从1949年11月至1950年4月,共有6期。
《中国托派史》出版后,唐宝林先生写信给托派老人王凡西,认为这本书中的立场观点他们可能不会同意,但可以展开讨论,而如果其中一些材料存在错误,则希望他们及时指出,以备重印时改正。总的来说,信中的态度十分诚恳。与此同时,他还向托派另一位重要成员郑超麟寄去了一本。
1994年11月间,郑超麟收到此书,他克服严重的白内障带来的阅读上的不便,重点阅读了第五、六两章,并写下一篇题为《批评唐宝林所著<中国托派史>》的文章。他认为,“从第五章看来,唐宝林的这本《中国托派史》就是康生和王明从莫斯科带回中国来的‘反托运动’的余波”[2]359。他还在文中指出了多处认为与史实不符的地方,而“对中共实行失败主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处。
关于“对中共实行失败主义”这个说法,郑超麟一开始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胡说。然而看到《叛逆者》的这段材料后,他感到颇为意外。他不相信托派会有这样的观点,因此对这个根据表示怀疑。“我认为这些话仍然不能作为根据,我想,所谓多数派的中央决不会写出这样的话。写这种话的人,自己也不懂得什么是‘失败主义’。这话本身又是不通的,即不合逻辑的。总之,这话不能代表整个托派的意见。”[2]363
二、一番调查
然而,毕竟这个材料就摆在那里,《中国托派史》的附录中甚至还有《叛逆者》的影印图片,上面赫然印着象征着托派的图标。这则材料在托派老人中间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对此该做何解释呢?是谁发布了这样的观点,他和中国托派又有何关系?为了弄清这些疑问,托派成员就此材料展开了调查。
对于这个调查,另一位托派老人刘平梅在以马怀士为笔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托派》的小册子中披露了一些细节。按照《中国托派史》所指,《叛逆者》是由“多数派”的潜伏组织所办,而“多数派”在上海解放前夕确实成立了留守组织,名为“江浙临时委员会”,它代替迁离大陆的中央组织领导各地支部。因此,如果内容属实,该刊物则应该是“江浙临时委员会”所办。于是,托派成员间开始询问所有在世的曾担任上海地区“多数派”领导职务的成员:“1.有没有出版过《叛逆者》这个刊物;2.有没有见过这个刊物;3.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刊物。”[3]78然而,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听过、见过,更没有出版过这个刊物。于是刘平梅得出结论:“唐宝林说《叛逆者》是多数派(中国革命共产党)所出版的刊物,是唐宝林想象出来的。”[3]78
在调查中,不仅没有人知道这个刊物,而且得到的另一些信息也证明其可能并不“存在”。
“多数派”曾办有一个油印刊物,名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这个刊物在上海解放后继续出版。1949年10月中旬,上海的“江浙临时委员会”被公安机关破获,相关人员被捕,在保证不再进行托派活动的情况下,他们很快被释放。出狱后大部分人离开上海去了香港。自此,“江浙临时委员会”停止了活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停刊,也没有再办其它刊物。按照《中国托派史》记载,《叛逆者》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4月,共出版6期。因而从时间上推断,此刊物不可能是“多数派”所办。而是否为“少数派”所办呢?作为“少数派”主要成员之一的郑超麟十分肯定地认为《叛逆者》并非“少数派”刊物。
如此一来,似乎这个《叛逆者》与中国托派并无关系。因而也不能用以论证托派在解放战争中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失败主义”的政策。
三、对材料的追认
2005年,刘平梅在香港出版了《中国托派党史》,这是托派成员自己撰写的历史,用作者的话说是针对《中国托派史》而作[4]。就在这部书中,对《叛逆者》出现了一个新的说法。书中记载,在“少数派”于1949年正式建党时,也同时成立了团组织,取名为“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温州都设有组织。而其中的温州青年团在1949年11月15日出版《叛逆者》,其第1期发表《内战的总结》一文,提出在中国内战中实行“失败主义”的口号。
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托派》书中否认的观点相比,《中国托派党史》不仅承认了这个刊物以及相关文章的存在,还披露了更多细节。这显然表明作者获得了有关《叛逆者》的新信息。然而信息从何而来,作者并未交待。不过这或许并不影响这一信息的可靠性,因为在一本一定程度为中国托派辩护的书里追认一个不太情愿看到的观点,这本身或已说明了问题。
对于这个新信息的来源,由2006年在中国托派问题上的另一个争论给出了答案。
2006年4月,《往事》第13期发表唐宝林《中国托派概述》一文,以《中国托派史》一书的内容为基础对中国托派进行了简要的概述。在论述托派对内战的态度时,再次使用了《叛逆者》所载《内战问题的总结》一文的观点。随后不久,曾是中国托派后期成员的黄公演,在4月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主办的《陈独秀与革命史研究通讯》第20期上,发表《评唐宝林的“中国托派概述”》一文,在几个问题上指责唐文中的观点。随后,5月份,唐宝林回应此文,写下《不要以今天的认识否认托派的历史事实——答黄公演先生》一文。就在这3篇文章之中,有关《叛逆者》的史实终得“浮出水面”。
早在2001年5月在温州召开的第6次“陈独秀研究会”上,有人针对《中国托派史》史实问题提问时,就曾涉及到《叛逆者》这个油印刊物。提问者有些不解,既然托派的“少数派”和“多数派”都不曾知晓这个刊物,为何不做出相应的修改。而参加了此次会议的黄公演,给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答案。即这个刊物确实存在,也确实和托派有关。然而“多数派”和“少数派”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也是正常的,因为《叛逆者》是温州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内部刊物。这个刊物不仅托派两派都没听过,连温州团组织的周边人员也不知晓。而黄公演之所以对此非常清楚,正是因为他曾是这个刊物的编辑和刻印者。
在此会议之后,到了2004年,刘平梅以马怀士的名字在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主办的“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上发表了先前出版的小册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见到其中关于《叛逆者》的说法后,黄公演又在该网站上发表了书面说明进一步澄清。如此一来可以推断,2005年出版的《中国托派党史》一书对于《叛逆者》的新阐述,应直接源自于此。
至此,《叛逆者》的“身世”已经清楚。它并非《中国托派史》中所述为“多数派”的潜伏组织所办,也非托派老人们认为的与中国托派无关。
四、仍然存在的争议
《叛逆者》的存在已经证实,而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这对于《中国托派史》所述托派对中共的内战持“失败主义”态度的观点是否会产生影响?如果有,那将是何种影响?
这或许本不应该成为问题,既然确有这个杂志,其中确有《内战问题的总结》这篇文章,也确实提出了对解放战争中的中共一方持“失败主义”的观点。那如郑超麟、刘平梅等托派老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否定似乎也就不能成立,而《中国托派史》的叙述也就没有问题。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仍然存在。
首先,对中共持“失败主义”的观点能否代表中国托派的主张,仍存在争议。早在1995年郑超麟在《中国托派史》的书评中就认为,这个观点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托派的意见。在2001年的“陈独秀研究会”上,黄公演在说明了《叛逆者》的情况之后,同样质疑这个观点的代表性。在他看来,一方面,知道这个观点的人非常少。另一方面,此观点只属于个人意见。按照托派传统的民主原则,党、团员有权利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个人意见,而《内战问题的总结》正是这样的文章。对文中的观点,托派团组织中央并没有表示赞同,做出相应地决议。在这种情况下,黄公演认为唐宝林抓住这个与“多数派”和“少数派”无关的个人意见不放,以此来论证中国托派对中共持“失败主义”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托派成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质疑,唐宝林有正面的回应。在看到郑超麟的书评后,他写下《就<中国托派史>致郑超麟及其托派朋友们的公开信》,在代表性的问题上,他认为,这个逻辑本身存在问题,中国托派从成立到1952年在大陆被取缔,其内部就一直存在分歧,不仅分有各派,就连同一派内部意见也经常不能统一。如果“‘不能代表整个托派的意见’的材料不能用,那么,中国托派就没有历史可写,因为它从来没有过能‘代表整个托派的意见’”[5]313。对于托派的这种情况,他在写作时多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对各派的意见分别加以叙述。而之所以使用《叛逆者》的这段材料,“因为它毕竟是托派历史上出现过的一种带有典型意义的事情”[5]313。而在2006年回应黄公演的文章中,唐宝林也是认为这则材料具有典型意义,才加以使用。
如何看待这样的争议呢,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代表性问题。在意见多样,不能够统一的情况之下,想找到一则能代表全体托派的材料确实不易。当研究的开展需要依赖大量具有局部代表性的材料时,对它们的具体分析必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同的材料在其代表性上存在着程度的不同,像托派这样成员有权在内部发出不同声音的党派,其派别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必然要比成员的个人意见更具有代表性。回到《叛逆者》的这则材料,笔者认为,从郑超麟、刘平梅等人四处打听无果的经历,和当事人黄公演的说法等这两个方面,可以判定《内战问题的总结》这篇文章属于个人意见,其代表性着实有限。而这份材料是否具有典型性呢?文章所述“失败主义”指的是在渡江战役之后作者对中共所持的态度。而此时“多数派”和“少数派”对内战、对中共都持什么态度呢?“多数派”方面,从1949年4月18日“多数派”中央发出《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封公开信》中号召中共党员起来纠正中央领导层存在的“致命错误”[6],到6月从香港向大陆成员发出指示,提出支持共军追击国民党,支持其进步措施,批评其错误措施等内容[7]336,都可以判断其主张与“失败主义”还有很大距离。而“少数派”方面,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时仓促召开的建党大会,虽然做出了《关于党纲的决议》,但只是确定了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立场,对时政问题并非每一个都有确定的立场[8]265。而对于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由于文本丢失,其作者王凡西也记不起来其中的内容。但从他和郑超麟事后对“失败主义”的惊讶态度上,或可推断这个文本并未包含“失败主义”的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将《内战问题的总结》中的个人意见归于“少数派”或者“多数派”,都似有不妥。
[1]唐宝林.中国托派史[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2]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下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
[3]马怀士.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托派[M].香港: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会,2003.
[4]刘平梅.我的回忆[EB/OL].[2013-10-21]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iupingmei/marxist.org - chinese - LauPing-Mui-2006.htm.
[5]唐宝林.求真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6]致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封公开信[EB/OL].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 - international/china/mia-chinese-fi- 19490418.htm.
[7]刘平梅.中国托派党史[M].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
[8]王凡西.双山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