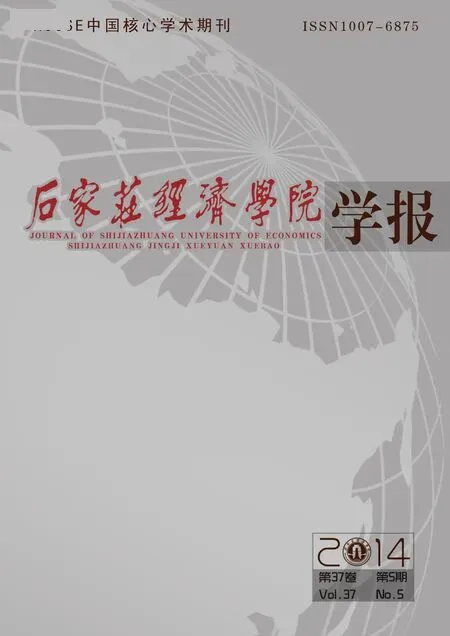保障性住房政策演变下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研究
——以德国、美国为例
郭 平
(云南大学 发展研究院,云南 650091)
一、引言
任何一个经历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都必将经历住房短缺问题,为满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各国政府都将实行保障性的住房政策。较早开始解决住房问题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发现难以依靠市场来填补住房需求与供给的鸿沟,其保障性住房政策经历了由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建设到以公平、效率为目的的市场化住房保障体系的演变。而其住房租赁市场也从最初分割的二元结构缓慢趋向统一。根据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住房租赁市场在住房保障体系的演变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成熟的统一的住房租赁市场才能更好解决了无力购房者的住房需求,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了高效的多层次的福利保障[1]。掌握保障性住房政策演变下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解决在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将为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借鉴。
二、保障性住房政策演变与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现今世界各国的住房保障政策呈现以上四种形式,主要涉及产权与使用权,实物保障与货币保障的选择。产权性质的保障房类似与我国提出的“经适房”与“限价房”。中低收入者往往没有购房能力,政府提出的经适房的价格并不能为大多中低收入者所接受,反而为政府寻租提供了空间,使之成为中高收入者的福利。限价房更是扰乱了正常市场,妨碍价格机制形成低效率。所以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都是从“使用权+实物保障”的模式开始,通过政府出资的形式兴建大量住房来解决,它快速有效地缓和了急需解决的住房供需矛盾,但随着公共住房存量的扩大,大量公共住房带来了财政支出危机,其对私人住房租赁市场的冲击日益明显,政府干预造成的对私人市场的挤出效应显现出来,政府开始转向“使用权+货币保障”的模式[2](见图1)。货币保障相对实物保证而言,避免了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同时也遵循了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使得住房需求者有更多的自主权。

图1 四类住房保障方式的优劣
保障性住房政策经历了从产权模式到使用权模式,从实物保障到货币保障的演变。住房租赁市场也随着政策的演变从分割的二元结构市场向统一市场的目标进行发展。我们先将租赁住房分为成本型租赁部类与营利型租赁部类[3]。成本型租赁部类包括政府提供的低价的公共住房和获得政府补贴以成本价格提供租金的私人出租房(一般有一定的补贴年限,年限结束后不受租金管制)。营利型租赁部类指完全以市场定价的私人出租房,在这类出租房中还存在着一类接受租房券的私人出租房,租房券是政府发放给中低收入者的货币补贴。这一类住房虽然以市场定价,却发挥了保障性的作用。保障性住房租赁体系由成本定价的私人出租房、成本定价的公共住房与市场定价接受租房券的私人出租房三类组成(见图2)。

图2 住房租赁体系的组成
保障性住房政策演变的第一阶段,是大量住房需求急需得到满足的阶段。政府一般都会直接兴建大量的公共住房来增加住房存量,而货币补贴的保障形式并不能满足这一点。所以住房租赁市场中只存在公共住房与未接受政府补贴的私人出租房。政府主导的公共住房与私人出租房形成分割的二元结构市场。由于公共住房对市场的冲击和其本身的维护成本颇高,为保护私人住房出租者利益和减轻财务负担,政府不得不对公共住房采取严格的管制。这样公共住房的发展受到限制,财政投入也渐渐减少。公共住房的衰弱,使得二元结构的租赁市场开始向相互连通的租赁市场转变,一方面政府会将一部分公共住房私有化,另一方面一部分私人出租房将以直接接受政府补贴或者接受租客的租房券的形式来担当保障性出租房的角色,填补公共住房退出而留下的缺口。
随着政府的保障房由实物保障变为货币保障,住房租赁市场进入第二个阶段。成本型租赁部类与营利型租赁部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获得政府补贴以成本价格提供租金的私人出租房与以市场价格定价却接受租房券的私人出租房加入了进来。第二阶段是成本型租赁部类成长以及成熟化的过程。所谓成熟化过程(the process of maturation),指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单位已建住房的未偿债务与单位新建、翻新、购买住房的平均新生债务的比值越来越小,两者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通胀引起的建筑成本上升[4]。成熟化的结果将形成大量低负债的成本型住房组成的成熟的租赁市场。在此阶段中,实行合理租金管制,着力发展协调成本型租赁部类与营利型租赁部类之间竞争关系的国家将较快形成成熟的租赁市场。租金管制压低了营利型租赁的盈利空间,使两种部类的盈利水平达到一致,这样市场的逐利性就不会在成本型租赁的萌芽期将其淘汰。政府对成本型租赁的保护将促使它走向成熟。
如果政府在成本型租赁部类尚未成熟阶段奉行自由经济,以营利型租赁部类发展为主导,那么大量的成本型租赁住房将难以培养。即使存在着接受租房券的私人出租房来发挥保障性作用,但按市场实际价格定价的市场规则也会使租房券的补贴份额反应到新的市场价格中去,从而使租房券失去效力。同时每年以市场价格百分比进行调整的租房券补贴将随价格上涨而上涨,使得政府负担越来越重。由于没有足够的成本型租赁部类满足需求,又鉴于租房券推升的高额房租,许多中低收入者被迫进入购房市场,这些对经济敏感的中低收入者加剧了住房市场的价格波动,损害了中低收入者的利益。所以政府必须先建立稳定成熟的租赁市场,再慢慢放开租金管制,才能稳定价格,对中低收入者提供保障。在完成成本型租赁部类成熟化过程后,成本型租赁与营利型租赁的竞争对整个租赁市场的租金价格起到下拉的作用,市场再不会是营利型租赁占主导地位。这样在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的第三阶段将形成多元化的协调统一的竞争性租赁市场,政府补贴也会渐渐退出。大量低负债的成熟的出租房拉低了住房租赁市场的价格,中低收入者的需求得到极大满足。住房租赁市场的演进路径见图3。

图3 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演变下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三、案例分析
(一) 德国保障性住房政策下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德国的公共住房兴起于1847年,当时德国工业开始迅速的发展,城市化进程进入加速阶段,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许多企业开始兴建员工住房。德国保障性住房大规模的兴建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住房严重短缺,人口从东德向西德迁移,更加剧了住房的紧张,德国政府通过政府出资,由非营利组织建造的方法,建设福利性公共住房780万套,占同期新建住房总数的49%,成功缓解了战后住房的供需矛盾。人们的住房需求得到很好的满足,1960年至1982年期间住房数量增长了62%,住房质量也得到改善,1982年的住房中有66%的已经配备了浴室与中央空调。德国住房存量中出租房的比例一直较高,这一点为中低收入者提供了保障。随着公共住房存量的扩大,德国经历了公共住房衰弱的阶段,沉重的财政负担,以及日益加剧的边缘化效应,使得二元化的住房市场难以为继,1950年—1988年期间每年德国兴建公共住房建设数量急剧下降,减少了近87%[5]。
德国开始进入二元化住房市场向单一型市场的过渡的第二阶段,政府选择不再参与公共住房建设,住房供给完全由市场决定,原有低租金的公共住房,一部分转为市场租赁房,一部分出售给住户,目前仅剩余150万套左右,约占市场租赁住房的8%。德国也开始转向租赁市场的货币补贴政策,但与完全市场化的竞争不同,德国为保护成本型租赁的发展,采取了独特的租金管理制度,向非营利性型的房东以及营利性的房东均发放公共补贴,所有新建住房房东均可获得25年补贴,但受到补贴的房租应在年限内保持租金在回收成本的水平。政府在住房使用寿命25年之后停止补贴,取消租金管制。成本型租赁住房在政府补贴的支持下日益成熟,住房存量规模不断扩大,起到了对中低收入者生活保障的作用。为了时刻监督房屋租赁市场的租金价差,政府还对整个租赁市场进行租金控制,将租金增长控制在超出当地房租水平20%以内。德国大多数城市都确定了一种“镜子租金”的价目表,各地方政府负责按市场水平确定适当的房租标准。未接受政府补贴的房东可以参照“镜子租金”水平的增长来提高房租。由于政府控制了房租价格浮动,稳定了住房租赁市场,防止了成本型租赁与营利型租赁之间的租金差价危机[6]。这样成本型的住房租赁即非营利性型出租房与以成本价格提供的营利性出租房的存量逐渐增大,在其达到补贴年限摆脱成本定价的限制后,进入较为宽松的第二层级的租金浮动管制体系。由于长期受到政府的补贴,这一类住房的成本已经得到回收,又可以发挥自身的成本优势,与新建的营利型出租房形成竞争机制,产生压低市场租金的作用。到2007年德国住房租赁市场中成本型出租房已经占出租房存量的26%,在某些地区还达到50%,形成了存量很大的一类低租金住房。随着这类住房成熟化水平的提高,成本型租赁与营利型租赁的租金差价控制在一定水平,德国房价指数也一致趋于稳定(见图4)。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大量负债率较低的旧房达到补贴年限摆脱租金管制,与新的高负债,成熟化较低的出租房展开竞争,拉低了市场的价格,另一方面,新建的住房乐于接受政府的补贴来填补成本型租赁住房的存量。随着住房存量的上升,新建住房的减少,政府对于租房补贴的支出将越来越少。虽然德国住房租赁市场并未完全摆脱租金管制,但随着其成本型租赁的成熟化,租金趋于稳定,中低收入者住房需求得以满足,租金管制已渐渐放开,德国住房租赁市场已开始向第三阶段缓慢过渡。

图4 2000年—2012年德国房价指数
资料来源:德国统计局网站 https://www.destatis.de,以2010年房屋价格指数=100。
(二)美国保障性住房政策下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美国设立了公共住房项目,由联邦政府出资修建,其设计是由联邦政府支付建设成本,而由租户负责支付平时的运营支出,公共住房的实施进行的非常缓慢,经历了二战后很多项目用于对城市的住房修复,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建设,并于1994年达到顶峰140万个单位,随后大部分的资源用于对现有公共住房的维护与更新。由于美国的住房市场是以营利型住房租赁部类占主导的,采取自由竞争的机制,而大量公共住房的出现将干扰正常的住房价格。为防止公共住房干扰住房交易市场,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公共住房准入标准。于是被严格控制的公共住房与自由放任的私人住房市场,形成了两者分割的二元结构。住房租赁市场进入发展的第一阶段,市场中封闭的成本型租赁用于保护中低收入,另一部分则实行市场机制。但是公共住房难以解决与营利型住房租赁市场之间问题,一方面因为国家为避免公共住房出现增长和吸引更多住户的危险,必须对其加以限制,这导致国家出于保护市场的目的对公共住房实行更严苛的资格审核制度。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不断推进,受惠面积的不断扩大,公共住房运营费用大大提升,已经超过的租户的实际收入,加之私人租赁市场对公共住房的涨价压力,公共住房的运营模式受到挑战,各地住房管理机构不得不提高租金,或者停止住房的维护。公共住房的成本优势丧失,居住环境日益恶劣。1993年到2004年期间,公共住房总数下降了12.3%[7]。针对以上问题保障性住房政策开始倾向对私人出租房的供需双方提供货币补贴,这推动住房租赁市场进入第二阶段。公共住房因毫无吸引力的房租以及恶劣的环境渐渐衰弱,二元分割的住房租赁市场被打破,有相互联通的趋势,公共住房开始被私有化处理,新的货币补贴形式如租房券的发行,使得营利性型租赁也能服务于中低收入者。租房券这一类对于住房需求方的补贴政策,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资助项目,它较之低收入住房补贴更加的灵活,使得租户能够自由选择合适的居住区。该券可以用来支付当地允许的最高房租超过住户税前收入的30%的部分[8]。
在第二阶段里,美国并没有将培育成本型租赁部类看作主要任务,而是希望通过租房券这样的货币补贴形式来缓解中低收入者的租房需求,但是在一个未成熟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实行营利型租赁为主导的市场化机制,无疑只能是推高租金价格,使得政府的补贴负担越来越越重。像第8条款新建与修缮这样的政府按市价与出租者收入的30%进行差价补贴的项目,也因为不断高涨的租金而变得难以承受,政府最终把补贴合同的期限从20年削减到5年,最终再次减为1年。2001年—2010年期间,低收入住房需求不断上升,但低收入者可负担租金的住房单元数量却下降,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见图5)。随着中低收入者在租赁市场越来越被边缘化,高昂的租金迫使他们想要购买自己的住房,美国住房自有率从1940年的43.6%上升到2010年的66.85%,这种处于临界状态的购房者对于经济波动的敏感程度非常大,他们只是勉强能承担高昂房价或是通过次级贷款获得资金,整个住房市场开始受到这种畸形的需求的影响,出现大幅波动(见图6)。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的这几年,美国住房租赁市场开始受到重视,美国只有致力于成本型租赁的培育才能真正摆脱住房市场不稳定的噩梦。
四、结论与启示
德国、美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案例表明促使成本型租赁部类的成熟化是完善住房租赁市场的关键,而合理的租金管制是较好的政策选择。

图5 低收入租房者的需求与可支付的租赁住房的供给缺口
资料来源:JCHS tabulations of US Census Bureau,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s.

图6 1992年—2012年美国三个典型城市的房屋价格变动率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住房金融机构网站 http://www.fhfa.gov
从建设保障性住房租赁市场的演变过程来看,公共住房是建设前期的共同选择,它也具有快速扩充住房存量的优势。但随着公共住房的衰弱,使用货币补贴的保障政策开始取代政府直接投资政策。这时合理的租金管制能有效地抑制营利型租赁部类与成本型租赁部类的租金差价危机,而如美国一样完全市场化的住房租赁市场将导致成本型租赁部类的边缘化。德国正是凭借合理的租金管制体系,培育了大量的成熟化的出租房,成功抑制了房价的波动,真正的保障了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而我国正处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初期,应该开始重视使用权性质的保障房建设,重视租赁市场的发展与完善,停止经适房的供应,转向公共住房即公租房的建设。目前我国住房租赁市场还处在第一阶段,二元结构的租赁市场逐渐形成,但公共住房的存量还很低,对自由市场的影响还不大。现阶段,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巨大的住房供需缺口,在短时间内增加住房的供应还离不开实物保障。在公共住房形成一定规模,城市化放缓的情况下,政府应该结合货币保障的方式,采取货币补贴的形式,将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向第二阶段引导,这样有利于缓和将来会出现的公共住房对自由市场的冲击。政府在利用货币补贴的方式培育一批成本型的租赁房,扩大住房租赁市场存量的同时,也应对其采取适当的租金管制,保障租赁市场的稳定性,这样成本型租赁才能在适当的环境中成熟,当成本型租赁在住房租赁市场中发展到一定规模后,低收入者的基本住房需求才能得以满足,这时缓缓放开租金管制,将有利于形成稳定统一的住房租赁市场。
参考文献:
〔1〕 施继元,李涛,李婧骅.国外住房租赁管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软科学,2013(1):31-36.
〔2〕 天则经济研究所.建立我国住房保障制度的政策研究[R] .北京: 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 24-29.
〔3〕 KEMENY JIM.The significance of Swedish rental policy:cost renting command economy versus the social marke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HousingStudies,1993(3):3-5.
〔4〕 KEMENY JIM.FromPublicHousingtotheSocialMarket:Rentalpolicystrategiesincomparativeperspective[M].Routledge,Chapman & Hall,Incorporated,1995:34-36.
〔5〕 余南平.欧洲社会模式——以欧洲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为视角[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8-83.
〔6〕 姚玲珍,张小勇.德国公共租赁住宅体系的剖析与借鉴[J].消费经济,2009(3): 67-68.
〔7〕 ALEX F SCHWARTZ.HousingpolicyintheUnitedStates[M].Routledge,Chapman & Hall,Incorporated,2004:45-48.
〔8〕 曾辉,虞晓芬.国外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模式的演变及启示——以英国、美国、新加坡三国为例[J].中国房地产,2013(2):2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