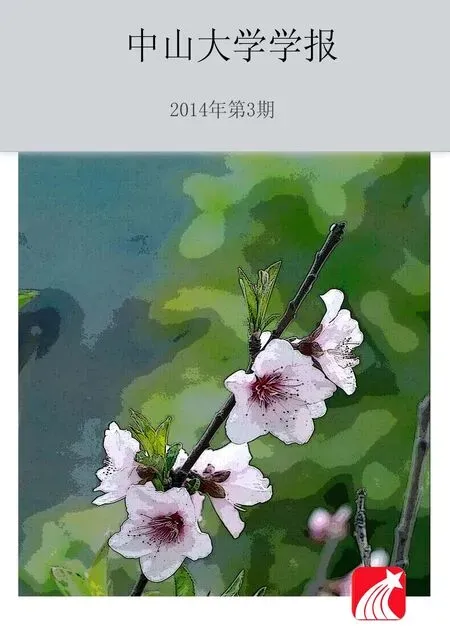论《尚书》非“照写口语”
陈 桐 生
《尚书》的难读是人所共知的。早在战国初年,十六岁的孔子之孙子思到宋国游学,宋大夫乐朔就对子思抱怨《尚书》“故作难知之辞”①旧题孔鲋:《孔丛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2—23页。,年轻气盛的子思不去正面解答《尚书》语言为何难知,反而当面讽刺乐朔是“委巷之人”(棚户区居民)。乐朔无辜受辱,率众围攻子思,幸有宋君出面,才救下子思一命。子思的命虽然保下来了,但乐朔提出的《尚书》为何“故作难知之辞”的问题,当时无人能够解答,此后历两千多年仍然没有合理的答案。尽管历代经师耗尽了脑力,但仍然没有人敢说完全读懂了《尚书》二十八篇文章②本文所论限于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不包括《伪古文尚书》,也不含清华简《尚书》。。连近代博学如王国维者也声称:“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③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载氏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页。《尚书》语言为什么如此难懂呢?鲁迅、刘大杰对此有一个解释:《尚书》的难懂是由于用当时口语写成的,这些口语随着时代变迁而走向僵化,所以原本浅易的商周口语成了后人的语言难题。刘大杰在谈到《尚书·商书》难懂时说:“难懂的原因,不是太文言,而是太白话。因为用的大都是当时的口语,时间过久了,后代读起来就难懂了。鲁迅说:‘《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以作为照写口语的证据。’(《门外文谈》)。”在谈到《尚书·周书》时,刘大杰又说:“《周诰》佶屈聱牙,不容易懂,其实并非此中有奥妙的道理,也并非作者的文章特别高深;原因是《周诰》中的文辞,全是用当时的口语记录的文告和讲演。记录以后,一直没有什么变动,于是那种言语渐渐随时代而僵化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19、68页。商周口语方言究竟是什么样的语言,由于古代没有录音设备,所以谁也说不清这个问题。一方面人们无法了解商周口语的情形,另一方面《尚书》语言又确实佶屈聱牙,再加上鲁迅地位特殊,刘大杰是著名文学史专家,其他人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于是《尚书》“照写口语”的说法就成为现当代学术界流行的观点。

尽管《尚书》留下了若干口语方言的印记,但从总体上说,这些口语方言在《尚书》语言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绝不能说《尚书》完全是“照写口语”,《尚书》语言艰深问题绝不是“太白话”或“照写口语”那样简单。下面让我们逐层对此剖析。
第一,从时间来看,人类语言是与时俱进的,无论是口语方言还是书面语,都处于持续的变化发展之中,不可能处于凝固、静止状态。《尚书》有虞、夏、商、周四个部分,其中《虞书》、《夏书》应该是出于商周史官的追记,《商书·汤誓》为《尚书》中最早的文章,故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最晚的是《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前后历时近千年。虽然《尚书》中也有几篇语言相对浅易的篇章*《尚书》之中,语言最浅易的是《金縢》,《禹贡》、《洪范》、《无逸》语言也相对容易。,而且商周两朝文诰各有深浅不一的情形*以《商书》为例,《盘庚》语言最难,《微子》次之,其他三篇稍微容易一些。,但从总体上说,商周绝大多数文章语言风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周诰”的语言难度不会比“殷盘”更小。以“誓”这一文体为例,《汤誓》是公元前16世纪商汤伐桀的誓词,《牧誓》是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的誓词,《费誓》是西周初年鲁侯伯禽征伐淮夷、徐戎的誓词,《秦誓》作于公元前627年,记载秦穆公袭郑失败之后的谈话。四篇誓词相隔近千年,记录者如果是“照写口语”,这四篇文章语言肯定会体现不同时代的差异。而在事实上,我们将这四篇誓词对照阅读,却看不出多少语言风貌的时代变化。
第二,从空间上看,商朝的活动中心在今天的河南,而周朝自称为西土之人,他们的活动中心是在今天的陕西。虞、夏虽为传说中的王朝,但后代史官既然根据传说追记虞、夏帝王言论事迹,他们应该顾及虞、夏语言的地域特色。尧、舜的中心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天山西的南部,夏朝的中心活动区域大约在今天河南登封一带。《尚书》二十八篇文章所涉及的空间地域大约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一带。地域差异是口语方言一大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隔一座山或隔一条河,人们就会说不同的方言,如果《尚书》果真是“照写口语”,那么虞、夏、商、周四书语言肯定存在很大的地域区别。但这种方言口语的地域区别并未在《尚书》中反映出来。如果《尚书》真的是记录虞、夏、商、周方言口语,那么让山西方言学者研究《虞书》语言,让河南方言学者研究《夏书》和《商书》语言,让陕西方言学者去研究《周书》语言,让山东方言学者去研究《费誓》语言,他们应该具有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应该能够揭示出某些《尚书》方言口语的奥秘。但事实上两千多年来,陕西、河南、山西、山东方言学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写出一部揭示《尚书》口语方言奥秘的学术著作。
第三,同一历史人物的诰辞语言在不同文章中深浅不一,这是“照写口语”观点强有力的反证。同一历史人物在不同文章中的诰辞语言应该在句式、用词难易等方面保持一致,因为一个人的方言口语在形成之后是很难改变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最明显的例子是《周书》。《周书》收录了西周初年大政治家周公十二篇诰辞:《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君奭》、《多方》、《立政》。在这十二篇诰辞中,语言最浅显的是《金縢》,其次是《无逸》,剩下的十篇诰辞语言都非常晦涩古奥。这十二篇诰辞都是出于周公一人之口,周公的口语方言在定型之后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是“照写口语”,那么周公诰辞的语言难易程度应该是均等的,使用的语汇也会有规律可循,可是《周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同出周公之口的十二篇诰辞,其语言难易程度真有天壤之别!让我们分别摘录《金縢》和《大诰》的一段文字,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两者之间的语言差异: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337,346、347页。(《金縢》)
肆予冲人永思艰,曰:呜呼!允蠢鳏寡,哀哉!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义尔邦君,越尔多士、尹士御事,绥予曰:“无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宁考图功。”②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337,346、347页。(《大诰》)
《金縢》语言明白如话,几乎比《国语》、《左传》还要容易,不用借助注释就可以读懂*有人说,《金縢》、《无逸》语言的浅易是由于后代经师在传习过程中将其改过来的。这个说法有一定合理性,经师在传习过程中擅自改变个别文字,这是经典传播过程中的常有现象。但它远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因为《尚书》所有文章都经过后代经师传习,每篇文章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改动,经师改字的现象并不是单纯出现在《金縢》、《无逸》等少数篇章之中。。《大诰》这一节除了“呜呼”、“鳏寡”、“哀哉”几个词汇可以理解以外,其他句子如果不查阅专门的训诂书籍,读者简直如读天书。为什么同出周公一人之口,却会出现语言难易不一的情形?难道周公在不同场合用不同的方言口语说话吗?对此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它们出自不同的记录者——史官之手。史官语言文化素养包括掌握典诰文体的水平造诣、运用语言的能力,文化素养高深的史官会选择难度高的词汇,而文化素养低的史官则倾向于选择浅易的词汇。史官本人也有不同的文字风格,有的史官倾向于选择典雅高深的词汇,有的史官则爱好平易的语言。《金縢》语言平易,这是因为它的记录者受殷商典诰文风影响不深,对典诰这一文体素养不够,不擅长运用殷商以来形成的典诰语言,只能运用西周初年的普通书面语——一种在当时民众生活口语基础之上提炼的书面语言。而《大诰》语言之所以深奥,乃是因为它的记录者应该是一个谙熟殷商典诰公文语言的史官,这位老辣的刀笔吏其实对周公的口语进行了艰深化改造,用殷商形成的典诰语言来改写周公的口语,他能够把周公鲜活的口语诰辞写成与《盘庚》一样的古奥语言。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周公的“口语”,而是记录者的文字素养,是史官将口语改写为书面语的能力。从现存《尚书》来看,商周史官们语言文化素养差异是很大的*西周初年史官的语言文化素养究竟有多深,对此我们只要读一下《周书·洛诰》就知道了,这是《尚书》二十八篇中唯一留下记录者名字的文章,它的记录者是史逸(佚),他是由商奔周的史官,对殷商典诰文体造诣尤深,应该代表了商周之际史官较高的语言文化水平。不过,并不是每一个西周史官都能达到史逸的文字水平。。于是,文字素养深厚的史官笔下的文章晦涩深奥,而文字根基浅薄的史官自然只能用当时普通的书面语言从事记录。
第四,《尚书》语言高度浓缩精炼,与口语方言详尽易懂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同。《尚书》的某些言论因其过于精炼而导致理解困难。如《盘庚上》“起信险肤”*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229,228,244,237,244页。,这四个字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起信”,意为“兴造言论”;第二层意思是“险肤”,意为“进行险恶的传播”。史官将这两层意思浓缩为“起信险肤”四个字,用词是如此的古老,又省去了“险肤”的谓语,由此造成理解的障碍。为了追求精炼效果,史官往往不惜将几句话浓缩为一句话。如《盘庚上》“无傲从康”③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229,228,244,237,244页。,今人将四个字不加停顿一气读下,读后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无傲从康”绝不会是盘庚当年发表诰诫时的原话,盘庚说的应该是“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放纵,不要贪图安逸”这一类的口语,史官本应该写成“无傲,无从,无康”,但他省略了后两个“无”,仅抓住了“傲”、“从”、“康”几个关键字眼,使“无傲,无从,无康”缩减成为“无傲从康”。今人可以运用顿号来表明这是三层意思,写成“无傲、从、康”,但是在文不加点的古代,这样浓缩的句子确实难懂。同样的例子又见于《盘庚下》“予其懋简相尔”④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229,228,244,237,244页。,“懋”意为“勉励”,“简”意为“挑选”,“相”意为“视才而用”。这一句译为现代汉语就是:“我将会勉励你们,从你们当中挑选人才,视你们的才能而加以任用。”“懋”、“简”、“相”,本为三层意思,却被记录者浓缩为一句。又如《盘庚中》“予迓续乃命于天”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229,228,244,237,244页。,“迓”意为“迎接”,“续”意为“延续”,“乃命”是指那些听盘庚训诫的民众的生命。此句扩展开来就是:我要把你们的生命从天帝那里迎接回来,让你们的生命延续下去。这两层意思,本应该写成“予迓乃命于天,予续乃命于天”。负责记录的史官将两句话浓缩为一句,此句因此变成难句。再如《盘庚下》“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229,228,244,237,244页。,从汉代郑玄到宋代蔡沈《书集传》,都未能把此句讲清楚,直到近人戴钧衡《书传补商》,才算把这一句话意思讲通。“鞠”意为“养育”,“谋”意为“谋划”,“保”意为“安居”,“叙”意为“任用”,“钦”意为“尊敬”。这一句意思是说,凡是那些能够养育民众以及为民众安居谋划的人,我都会任用他们,尊敬他们。记录者用了九个字概括盘庚这么多的意思,给后人造成很大的理解困难。《周书》在语言浓缩精炼方面不逊于《商书》。例如《梓材》“肆亦见厥君事戕人宥”,据孙诒让《尚书骈枝》的解释,“肆”是语气词,“事”意为任用,“戕人”是指戕害他人者,“宥”意为“宽宥其罪”。此句意谓:“臣下看到君主任用戕害人者,且宽宥其罪。”记录者将两句话凝炼为一句话,第二句简化为一个“宥”字。又如《酒诰》“引养、引恬”,《释诂》:“引,长也。”养,养育。《说文解字》:“恬,安也。”“引养、引恬”,译为白话就是:“养育人民,安定人民。”史官将这两层意思浓缩成四个字,令人不知所云。再如《多士》“上帝引逸”,据俞樾《群经平议》的解释,此句意思是说:“上帝不会放纵人们逸乐,如果有人逸乐,上帝就会让他收敛,不让他犯大错。”如此丰富的意思,却只用“上帝引逸”四个字表达,真是惜墨如金。从这些例句来看,《尚书》记录者对谈话者口语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浓缩提炼,这种高度浓缩提炼的表达方式与口语明显不同*《尚书》语言高度浓缩凝炼,可能与记录者速记方法有关,记录的速度总是无法赶上说话的速度,于是记录者只能快速捕捉几个关键词语,整理成文诰之后,又未能将速记文稿还原为谈话原貌,于是出现缩减字句的现象。。
第五,口语的特点之一,是对同一事物往往用某一个相对固定的词语来表达,如称“我”的人不会换称“俺”或“咱”,而在《尚书》之中,往往同一个意思,记录者会选用不同词语加以表达。例如,在《汤誓》中,第一人称就用了五个不同的词语,如“台小子”(“非台小子”)、“我”(“我后不恤我众”)、“朕”(“今朕必往”)、“予”(“予其大赉汝”)、“予一人”(“尔尚辅予一人”)。《汤誓》中的第二人称,交替运用“汝”和“尔”字,如“今汝其曰”、“尔无不信”*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尚书》中的“不”,很多情况下写作“弗”,如“弗知”、“弗告”、“弗靖”、“弗率”、“弗念”、“弗济”、“弗或”、“弗出”等等,“弗”的书面语色彩显然要比“不”更浓一些。记录者有时将“不”与“罔”对用,“罔”的书面语意味比“弗”更为浓厚,如《盘庚上》:“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上句用“不”,下句用“罔”,所表达的其实是同一意思。《尚书》中还可以举出很多词异而意同的例子,如《盘庚上》载“猷黜乃心”、“汝克黜乃心”,“猷黜”与“克黜”是意思相同;“罔有逸言”、“其发有逸口”,“逸言”与“逸口”都是指过失的言论;“格汝众”、“则惟尔众自作弗靖”,“汝众”意即“尔众”;“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尔祖其从与享之”,“乃祖”与“尔祖”意义相同;“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尔”和“乃”都是第二人称领格②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又如《盘庚中》有“高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与汝罪疾”、“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③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崇降”与“丕降”都是指“重重地降下”,它们与《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④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中的“毒降”意义相近。在对先王的称呼上,《盘庚上》称“先王”、“先神后”,《盘庚中》称“前后”、“古后”,名称不同,所指则一。以上诸例说明,商周史官在记录君王讲话时,有意识地运用不同词汇表达同一意思而造成生涩化,避免用语的雷同,这应该是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努力。
第六,《尚书》中很多词汇和语句又见于商周铜器铭文以及《诗经》等文献之中。商周铭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这是一种高度书面化的文体。《诗经》中的《商颂》、《周颂》、《大雅》为庙堂文献,语言高贵典雅,是典型的书面用语。《小雅》以书面语居多,有时也会运用口语。《国风》则因为要“观风”而有意保留口语化。《尚书》与铭文、《诗经》雅颂共用某些语汇,说明《尚书》不是“照写口语”。这种情况首先体现在成语之上,王国维指出:“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载氏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第40页。认为这是导致《尚书》难懂的原因之一。王国维列举了《尚书》中运用成语的若干例子,诸如“陟降(又作‘陟恪’、‘登假’、‘登遐’、‘昭登’)”、“作求”、“由哲(又作‘迪哲’)”、“迪知”、“厥若”等等。继王国维之后,杨树达、杨筠如、刘节、 屈万里 、姜昆武、于省吾、刘起釪等人又相继发掘出《尚书》中一大批商周成语,诸如“罔知”、“致告(指告)”、“勿亵”、“承保(又作‘应保’、‘膺保’、‘容保’、‘怀保’)”、“在上”、“爽德”、“协比(又作‘洽比’)”、“小大”、“将食”、“初基(又作‘肇其’、‘启其’)”、“祗威(又作‘祗畏’)”、“显民”、“保乂(又作‘俾乂’)”、“要囚”、“速由(又作‘率由’、‘率从’)”、“敬忌”、“丕则”、“经德”、“昧旦(又作‘昧爽’)”、“昏弃(又作‘泯弃’、‘蔑弃’)”、“诞以”、“丕显”、“冒闻”、“迪屡”、“弘孝(又作‘追孝’)”、 “监兹”、“王人”、“新造”、“庸释”、“敷心”、“敬德”、“丕时(又作‘丕承’)”、“灵承”、“训德”、“万姓”、“答扬(又作‘对扬’)”、“奸宄”、“降格”、“厎绩”、“敷佑(又作‘普有’、‘匍有’)”、“棐忱”等等。这些成语以双音节居多,在当时或前后文献中出现两次或者两次以上,它们不仅见于《尚书》,也见于其他文献。在文字尚未统一的商周时代,同一成语可能会以通假字、假借字等形式出现。除了成语之外,《尚书》中还有很多语汇又见于商周铭文、《诗经》及其他先秦文献。兹举数例。《金縢》:“敷佑四方。”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秦公钟》:“匍有四方。”*马承源:《商用青铜器铭文选》(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6页。《墙盘》:“匍有上下。”*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4,316,316,174,316页。“匍有”意为“抚有”,这是周人的习惯用语。《无逸》:“治民祗惧,不敢荒宁。”⑨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毛公鼎》:“女(汝)母(毋)敢妄(荒)宁。”⑩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4,316,316,174,316页。“荒宁”意为“荒废怠惰”。《文侯之命》:“闵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诗经·周颂·闵予小子》:“闵予小子,遭家不造。”*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1344,730、737页。《毛公鼎》:“余小子湛于囏(艰)。”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4,316,316,174,316页。“闵予小子”是周王慨叹自痛之词,与“惧余小子”意义相近。《多士》:“旻天大降丧于殷。”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189—194,223—234,235—241,263,334,430,557,422页。《诗经·小雅·雨无正》和《小旻》中均有“旻天疾威”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1344,730、737页。的诗句。《师询簋》:“今昊天(疾)畏(威)降丧。”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4,316,316,174,316页。《毛公鼎》:“(旻)天疾畏。”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4,316,316,174,316页。“旻天”是指仁慈的上天。“降丧”意为“降下丧亡”。《费誓》:“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多友鼎》:“用严()(狁)放(方)(兴)。”*马承源:《先秦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83,228,224,215,166页。“并兴”、“方兴”意义相近,都是指并起作乱。《大诰》:“弼我丕丕基。”《立政》:“以并受此丕丕基。”《盠方彝》:“天子不叚(遐)不(丕)其(基)。”③马承源:《先秦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83,228,224,215,166页。“丕丕基”意为“伟大的基业”,是西周典诰公文中的常见用语。《盠方彝》“不其”就是“丕基”或“丕丕基”。《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有王虽小,元子哉!”④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此处“元子”指嫡子。《番匊生壶》:“番匊生铸賸壶,用賸(媵)氒元子。”⑤马承源:《先秦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83,228,224,215,166页。此处“元子”指长女。《召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曶壶盖铭》:“永令多福。”⑦马承源:《先秦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83,228,224,215,166页。商周铭文的“命”多写作“令”,“永令”即“永命”,意为“受天长命”。《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⑧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文人”是周代美称,商周铭文中多用“前文人”称呼前人祖宗,如《昊生鼎》:“用喜侃前文人。”⑨马承源:《先秦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83,228,224,215,166页。《君奭》:“在让,后人于丕时。”⑩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诗经·大雅·文王》:“帝命不时。”*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957,966,576,1421,1046,740,1222页。王国维指出,“不时”、“丕时”当是同一成语*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载氏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第45,42页。。“不”即“丕”,或释为无义语气词,或释为“大”。“时”者,是也。“丕时”为意动词,意为“伟大而正确”。《君奭》:“天难谌,乃其坠命。”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诗经·大雅·大明》:“天难忱斯,不易维王。”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957,966,576,1421,1046,740,1222页。“天难谌”即“天难忱”,意谓天不可信,这是西周初年上层统治阶级对上天的新认识。《君奭》:“我则鸣鸟不闻。”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957,966,576,1421,1046,740,1222页。《伐木》以鸟鸣求友比喻求得友声,周公以“鸣鸟不闻”喻自己听不到诤言。《君奭》:“丕冒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诗经·鲁颂·閟宫》:“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莫不率从,鲁侯之功。”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957,966,576,1421,1046,740,1222页。“海隅”意即“海邦”,“罔不”意同“莫不”,“率俾”与“率从”意义相近。《康诰》:“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诗经·大雅·下武》:“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957,966,576,1421,1046,740,1222页。“求”是“仇”的假借字,“作求”意为作匹、作配。“《康诰》言与殷先王之德能安治民者为仇匹,《大雅》言与先世之有德者为仇匹,故同用此语。”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载氏著,彭林整理:《观堂集林(外二种)》,第45,42页。《洪范》:“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诗经·小雅·小旻》:“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或哲或谋,或肃或艾。”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957,966,576,1421,1046,740,1222页。这两处都提出“圣”、“哲”、“谋”、“肃”、“艾”概念,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洪范》:“无虐茕独而畏高明。”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诗经·大雅·烝民》:“不侮矜寡,不畏强御。”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第957,966,576,1421,1046,740,1222页。“无虐茕独”意思与“不侮矜寡”相通。以上诸例表明,《尚书》与商周铭文、《诗经》雅颂的语言词汇有着相通之处,没有人说商周铭文“照写口语”,也没有人说《诗经》雅颂“照写口语”,为什么偏偏认定《尚书》“照写口语”呢?
第七,《尚书》语言究竟是“照写口语”,还是一种仿古文字,还可以与同时代其他文献的语言进行比较。在同一时代,“照写口语”的作品语言应该比当时书面语言更容易理解。下面将两篇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一篇是《周书·秦誓》,这是公元前627年的作品;另一篇是《国语·周语中》中的“王孙满观秦师”,是公元前627年东周史官的记言散文。
嗟!我士,听无哗。予誓告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惟古之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谝言,俾君子易辞,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562,394、396,402,558,449,440,447,449,370,303,308,569—572页。(《周书·秦誓》)
二十四年,秦师将袭郑,过周北门。左右皆免胄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观之,言于王曰:“秦师必有谪。”王曰:“何故?”对曰:“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秦师无谪,是道废也。”是行也,秦师还,晋人败诸崤,获其三帅丙、术、视。*《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0—61页。(《国语·周语中》)
两者比较,《秦誓》语言的难度显然要远超《国语》。如果《秦誓》是“照写口语”,那就等于说公元前627年的口语比《国语》的书面语还要艰深得多,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为什么“照写口语”的《秦誓》语言变得僵化而让人看不懂了,运用书面语的《国语》反而没有僵化?如果说虞、夏、商和西周初年的口语因年代久远而僵化,那么像《秦誓》这样年代较晚的作品语言是不应该走向僵化的,为什么《秦誓》的语言也那样艰深呢?实际情况是,《秦誓》并非“照写口语”,它们所使用的是一种属于前代的仿古语言。《秦誓》语言是如此,《尚书》其他篇章的语言也是如此。
第八,《尚书》语言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这就是西周铭文。商代铭文篇幅简短,与《尚书》语言可比性不大,西周铭文比殷商铭文要长,特别是到西周中后期,百字以上的铭文大量涌现。铭文中载有很多周王诰辞和册命之辞,其语言难度及格式与《周书》相当,可以看做是铸在西周青铜器上的“尚书”,而且是没有经过传习者改动的原汁原味的“尚书”。西周铭文中的诰命文章在用语、格式、文体上都与《周书》相通。《大诰》、《康诰》、《酒诰》记载周王诰辞,第一次用“王若曰”,以下各段用“王曰”,这种格式与《大盂鼎》等铭文所载周王诰辞形式相同。《召诰》、《洛诰》、《立政》等篇礼仪称扬辞“拜手稽首”,广泛见于西周铭文,一般写作“拜手旨页首”、“拜首旨页首”、“拜旨页首”。《大盂鼎》、《小盂鼎》、《矢鼎》等都是以“惟王几祀”置于铭文之末,《洛诰》也是以“惟七年”置于末尾。《大盂鼎》、《师酉簋》、《班簋》、《师虎簋》等记载册命的铭文,其中表彰功德、册命赏赐、勉励期望等内容,都可以与《文侯之命》相互印证。西周铭文语句也可以与《周书》互证,如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其上铸有周王诰辞:“昔才(在)尔考公氏克远(弼)玟王,肆玟王受兹□□(大命)。隹珷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辞(乂)民。’”*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第20页。按“隹”应为“惟”。铭文大意是说:“从前你的父亲能够辅弼文王,文王受此大命,武王消灭殷商,于是敬告于天说,我居于天下中央,从这里来治理人民。”这一节文字不仅证明了《尚书·洛诰》、《逸周书·度邑》内容的真实性,在语意上也与《洛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第415页。等语相近。西周铭文从侧面表明,当时应用性公文的语言是书面化、程式化而不是口语化,铭文如此,《尚书》也是如此。
《尚书》语言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上古语言,它经历了创造—定型—模仿—凝固的过程。我国的信史是从殷商开始算起的,因此我们暂把《尚书》这种公文语言的成型定于殷商早期。在文字没有发明之前,商王政令应该是通过口头传播;而在文字发明之后,史官们运用当时有限的文字,将商王夹杂方言的口语尽快记录下来,尽可能地将口语转换为当时的书面语,使口头的政令文诰变成简帛文献。早期殷商文诰就是这样诞生的。一种文体在形成之后,就会获得相对的稳定性,并对后人产生一种长期的示范作用。商周史官都是世袭,后人会忠实地恪守先人的文字技法,因此当早期典诰作品问世以后,这些作品就作为一种用语典范在史官家族内部世代传习。早期典诰作品的佶屈、稚嫩、朴拙、艰涩、古奥、不准确等特点,都被后世史官作为一种神圣范式刻意加以模仿,由此最终凝固、定型为《尚书》晦涩古奥的语言系统。周革殷命,虽然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但在公文语言方面却一直沿袭殷商语言。要揭开《尚书》语言之谜,需要将《尚书》语言放在商周语言发展大背景之下,做艰苦、缜密的论证工作,而绝不是一句简单的“照写口语”就可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