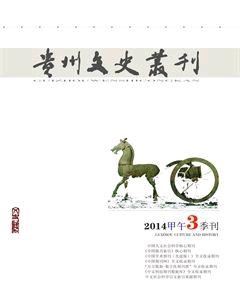马阮关系考略
李晓
上
明末一段历史,错综复杂,多少年来聚讼纷纭,一直是史学界甚至文化界的一个热点。由于战火兵燹,史籍焚毁殆尽,种种原始依据荡然无存。待到世事稍定,清代官修明史,主事者既秉统治者意旨而妄加取舍,且据个人与党社好恶而随意涂抹。致使相关史实模糊,谬说盛行。如《明史·本纪》至二十四卷《庄烈帝》为止,以崇祯身亡、清兵入京作为明朝终结,而不承认南明弘光及其后隆武、永历等南明诸帝。在《奸臣传》中,却录入担任要职主要在弘光朝的马士英传记。更为荒谬的是,传中将马士英阮大铖二人交错而写,造成两人关系非同寻常的印象。作为正史,不仅不加考证和辨识地采用大量言无实据、似是而非的传言,而且为世间言南明者必称“马阮误国”提供了依据。且不说马阮二人在弘光一朝政事中所持政见、所起作用皆有众多待辨之处,单只马阮二人关系而言,即有诸多疑点待析。
封建社会,官员之间私密关系,依时空为序,无外亲戚、同乡、同门(师生、同学)、同年(弟子座师)、同僚(同事、同朝为官)、同志(意气相投,政见一致)诸种。马阮之间,非亲非眷,即使族亲姻亲之类宽泛概念的亲戚关系也扯不上。一为黔人,一为皖籍,自然也不是同乡。乡试中举,阮于万历三十一年安徽乡试中举,马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贵州乡试中举,两者互不搭界,即非同门。
姚大荣先生曾言:“士英与大铖早年、中年无可合之实迹,史称其‘相结甚欢,谅因会榜同年,他无所见也。”其实,马阮二人即使“会榜同年”,亦难有“相接”可能。马阮二人都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同在京师参加会试,而且两人且皆顺利中式,所以是同年,有可能互相知晓。但是,马士英于会试前一年(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中举。按明朝考试制度,乡试为八月“秋闱”,而会试为三月“春闱”。两者之间仅隔大约半年时间。而当时的交通情况,贵阳至北京,如果加上置办行装的时间,应该超过一个月。马士英虽然赴京参加会试,却因年纪小(中举时“甫弱冠”,二十岁),被家族寄予厚望,是由父亲亲自送到京城去进行适应性考试的。在京备考时间有限,且有严父督学,应少有交朋识友的余暇;又因乡里不同,难得交流互动平台,两人难有交往。会试之后,马士英一举上榜,考取“贡士”。其父马明卿“恐其少不任吏,与俱归,读书讲求身世之事,以老其才。”也就是说他虽然通过了会试,但家里还是把他叫回家复读,三年后才又重新赴京参加殿试。这样,丙辰会试之后,阮大铖作为即将上殿面试者,与要返乡读书的马士英,更难有交游的时间和机会。所以,姚大荣先生推测马阮二人“‘相结甚欢,谅因会榜同年”也是难以成立的。
会试之后三年,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年),马士英参加殿试(补殿)中二甲十九名进士。过后实授南京户部主事,长期在南京任职,启、祯间先后出任严州、河南、大同知府,阳和道副使等地方官职,直至崇祯五年出任宣府巡抚,不数月得罪镇守太监王坤遭劾罢官。而阮大铖自丙辰(1616年)中进士后,授行人(官名,专司捧节奉使,曾出使凉州、福建等地),一直在京任职,崇祯元年,在光禄寺卿的位置上被御史弹劾罢官。两人仕宦历程,一在朝廷,一在地方,没有共事的经历。
综上所述,在马士英崇祯五年罢官居宁之前,马阮二人之间,无论从已知种种记载,还是二人各自行踪轨迹来看,即使不是素昧平生,也并无实际交往。二人交往,应当是从两人皆被罢官且移居南京之后。两人既系会试同年,又同遭罢官,境遇相同,且皆有才名,有若干共同爱好,一旦接触,很快就建立比较友好的关系。这在阮大铖的《咏怀堂诗集》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
阮大铖罢官归乡后,自称“惟日读书作诗,以此为生活耳。无刻不诗,无日不诗。”黄山书社于2006年在“安徽古籍丛书”中收录出版了《咏怀堂诗集》,其中收集了迄今所见的阮大铖所有诗作,包括崇祯八年刻印的《咏怀堂诗》四卷,《咏怀堂诗外集》甲乙两卷;后来的《咏怀堂丙子诗》上下两卷,《咏怀堂戊寅诗》卷下一卷,《咏怀堂辛巳诗》上下两卷,共十一卷。计一千一百四十八题,约两千首。其中接近百分之七八十的篇目为酬应唱和之作,从中可窥其与当时各方人士交往关系,亦可证与马士英交游关系。
崇祯八年刻印的《咏怀堂诗》四卷共三百九十二题,诗按文体排列,多数未列创作时间,然当多为罢官(崇祯元年)后作。再有研究者认为“当系同时所刻”的《咏怀堂诗外集》两卷共二百九十七题,未按文体排列,亦未见明显时间标记。可能是阮大铖先整理选编诗作刻为《咏怀堂诗》,后又对选下来的作品敝帚自珍,不舍丢弃,补刻为《外集》。这两部诗集占阮氏现存诗作约百分之六十,收录阮在崇祯八年(1635)以前的诗作。在《咏怀堂诗》中有三首直接同马士英有关:
(4)《同越佥宪卓凡马中丞瑶草夜酌》
(5)《再同卓凡集瑶草水亭》
(6)《同越卓凡饮马瑶草水亭闻寇警感赋》。
三首诗都记载是“同越卓凡”一起。越卓凡即马士英的亲戚越其杰,在《咏怀堂诗》中另有三首直接同越其杰有关,算是间接同马士英有关:
(1)《春夜同叶以冲越卓凡先生集卓车械园》
(2)《过卓凡北窗下偶成》
(3)《越卓凡出天界同宿月下赋》。
诗前面的序号是该诗在集中出现的顺序。从这六首诗,我们感觉得到:这段时间(崇祯八年以前)1、阮大铖先同越其杰相识相交,又才在越的引荐陪同之下与马士英交往。(同越交往的三首皆排序在前);2、无论是阮同马的交往,还是同越的交往,都有一个关系逐渐亲密的过程(同越先尊称“先生”,同马先尊称“中丞”,同马交往的第一首诗对越其杰还称“佥宪”官衔);3、阮大铖同越、马的交往都是文人之间的宴避聚会。由此可见,在马罢官居宁(崇祯五年)之前,马阮之间并无直接交往,关系也比较生疏。崇祯五年马罢官居宁以后,阮大铖先与马士英的亲戚越其杰交往,过后又经越介绍,得以同马士英结交,且关系逐渐加深。
在《咏怀堂诗外集》之后,阮大铖就采取按年编集的方式,编了《咏怀堂丙子诗》卷上、卷下,《咏怀堂戊寅诗》卷下(当有“卷上”,未发现),《咏怀堂辛巳诗》卷上、卷下,是否有《丁丑诗》或其他年份诗,只能存疑。从《咏怀堂丙子诗》中就明显感觉得到马阮关系日趋紧密。《丙子诗》不分体裁,当是依写作时间为序,上下两卷共一百九十五题中,有直接同马关联的四题:
(1)《雨中同马中丞瑶草、吴元起宗白循元登牛首夜集》
(2)《与马瑶草同宿范华阳居瑶草述其逝姬有感》
(3)《寿马瑶草年伯母六十》
(4)《连同瑶草、子占、班王、吉甫、次鲁、子卿登雨花琢錬诸胜》,从诗题中,就感觉得到,马阮关系已经进入比较友好的程度,以至于连比较私密的个人感情话题(述其逝姬)也坦诚交谈。马士英为母亲贺寿祝寿这样比较私密的聚会,也邀请了阮大铖参加,而且两人之间也叙了同年。《丙子诗》编好刻印时,马士英还直接为之写了序言。
在《戊寅诗》卷下一百零九题中,也有四首同马士英直接关系:
(1)《初度感怀呈萧大行伯玉、黄给谏水帘、马中丞瑶草、葛参军震甫》
(2)《山夜有怀马中丞瑶草》
(3)《同瑶草中丞夜赋》
(4)《除夜述怀寄瑶草》。
诗题中,我们见到,马阮之间关系已经到了真正好友的程度(不见面也要怀想)。令人觉得奇怪的是,到了《辛巳诗》,也就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时候,上下两卷共一百八十题诗作中,居然一首同马士英有关的都见不到。当然,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形势严峻,也许忧心国事的马士英已经无心继续文友之间游山玩水诗酒应酬的生活。而就在第二年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马士英就复出担起“总督庐凤军务”的担子,率军与张献忠厮杀去了。
通过《咏怀堂诗集》,我们对马阮关系在崇祯十五年(马士英复出)之前的状况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两人之间是在崇祯五年马士英罢官居宁之后,(应该是崇祯七年)开始交往,很快就建立了比较密切和友好的关系。这一点《明史·马士英传》的说法比较吻合,“坐遣戍,寻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但是,这种密切和友好应该只是相同境遇的下台官员和意趣相投的文人之间的友好,交往也是文人之间的寻幽访胜、诗酒雅集,而没有明显的政治同盟或其他利益关系。
中
通过阮大铖的诗作,我们对从崇祯五年马士英罢官居宁,到崇祯十五年马士英复出总督庐凤军务这十年间的马阮关系,已经有所认识。从阮大铖的诗作中,也可以见到,他交游广泛,酬唱应和牵涉当时人物多达数百,包括史可法、文震孟、钱谦益、冯梦龙、张岱等名人。所以,从阮的诗作只能说明马士英是他广泛交往的文友之一,固然关系较好,但只是文人往来,而不能说成政治的同盟。让马士英同阮大铖的交往蒙上令人怀疑的阴影,让人把他与阮大铖连为一体的,是广为传说的阮大铖为马士英复出所起的作用。
《明史·奸臣传》写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光斗以失五城逮治,礼部右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这一说法,在晚明各种官私记载中,无论私家名作《烈皇小识》文秉、《鹿樵纪闻》吴梅村、《三垣笔记》李清、《崇祯朝野记》李逊之、《明季北略》计六奇等等,还是被认可为官方记录的《崇祯实录》《崇祯长编》等,细节虽略有不同,而阮大铖助马士英复出这一基本说法却是共同的。即使对马士英评价较为客观的夏允彝《幸存录》也持此说。也就是说,马士英因阮大铖而得以复出,已成各家公认的定论。我们把马士英平生事迹排列,就发现正是从这一说法起始,马士英被人们视作同阮大铖有特殊关系,进而导致“马阮”并称,并把阮大铖的各种言行归罪于马士英。
然而,细读相关史料,却能够感觉到,这个众口一辞的说法存在明显问题。
首先:马士英复出是怎么决定的?周延儒在其中实际起了什么作用?第二:阮周之间的密约为何众所皆知?
《明史》记马士英复出,只是一句话“礼部右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凤等处军务。”同前面所记阮大铖托周延儒的事接在一起,似乎就是周延儒主持起用了马士英。然而按照明代诸帝的情况,如果是万历那样,几十年不上朝理政,主持朝政的首辅是可以决定一方总督的任用的;如果是天启那样的皇帝,专心于自己的个性爱好(做木匠),他信任委托的人(魏忠贤),也可以决定高级官员的任免。对于在魏忠贤阴影下,战战兢兢登上皇位的崇祯帝来说,督抚这样的省部级大员,他是不可能让其它任何人作主的。夏允彝的《幸存录》就说:“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窃用。”马士英的起用,不是一句“延儒从中主之”这样简单。
文秉的《烈皇小识》记载:“士英先为王坤所纠遣戍,至是会推凤阳总督,士英列名其中。上怒甚,日:‘会推大典,辄以废弃窜名其问,冢臣欺蔽殊甚。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奏日:‘冢臣岂敢蔽,实以马士英曾历边疆,颇有才略,禁锢可惜。今止开列,候皇上裁夺。惟是冢臣不先奏明,诚为有罪。上怒稍霁,曰:‘马士英既说他有边才,即著他去。遂起升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凤等处军务。”
把文秉的记录同《明史》合在一起看,就清清楚楚。在高光斗被逮后,朝廷要进行“会推”,也就是够资格的大臣集中开会,推荐接任的官员。会推中,是礼部右侍郎(云南人)王锡衮提名,使马士英进入了备选名单(“士英列名其中”)。拿到报送的庐凤总督候选名单,崇祯帝看到马士英的名字还很生气,是徐石麒为马士英作辩解,使崇祯转怒为喜,在若干候选人中定下了马士英。
文秉是文震孟的侄子,本人也是党社成员,参与了《留都防乱公揭》署名。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这段记载中崇祯多疑善变,喜怒无常,置事随意,视任事之臣如草芥,的确是他的性格。而对马士英复出起了关键作用的是两个人,直接提名推荐马士英的礼部右侍郎王锡衮,还有说服皇帝的刑部右侍郎徐石麒。如果说王锡衮是因为同马士英是同乡(明代云南贵州曾为一体),而对马有所了解的话,徐石麒这个东林党骨干成员就同马士英没有什么直接的个人关系了。这两个人都是比较坚持原则的清流,即使以比较挑剔的标准衡量,也属于传统的正人君子范围。两人对马士英,一个推荐在前,一个辩说在后。可见马士英的复出,正如夏允彝中所说:“马士英素以才望称。”主要还是由于自身的才名、在朝中的人望。周延儒所起的作用仅只是在“会推”时,对王锡衮的提名投了赞成票,过后又将包括马士英在内的一份多人候选名单报给了皇帝,除此之外并没有起其他作用,根本说不上“从中主之”,阮大铖的操作更是无从谈起。
这儿,不禁要对《明史》的编修者表示佩服。古人曾有“刀笔”之说,意思是用笔也可以伤人。《明史》的编纂者精心制造了一个假象,把“延儒从中主之”者六个字直接置于阮大铖以金钱助周延儒的传说之后,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让人以为马士英复出就是因为阮大铖的运作,从而影响了马士英的名声达数百年。
否认马士英重新起用是周延儒(阮大铖)的作用,并不是说阮大铖关说的事完全无中生有。问题在于:阮大铖向周延儒行贿,这无论在周还是在阮,都不是光彩的事。两人之间不传六耳的“四知”密约,为何会炒得沸沸扬扬,天下皆知呢?
这个源头,很有可能就在阮大铖本人。
按中国历来的官场风气,被废官员除有重罪无望起复者,一般为求复出,都要多树声气,广结人缘,互相游说鼓吹。马士英与阮大铖既是同年,又处境相似,交往密切,在适当的人如周延儒之流面前和适当的时间,互相说几句好话是可能的。而马士英复出总督庐凤军务之后,不负众望,率领黄得功和刘良佐的部队,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逼使威慑留都的张献忠调头而去,南京转危为安,一时声名卓著,众望所归。(笔者另有专文考证)阮大铖就有意将自己为马士英说过几句好话的事有意夸大,到处宣扬。这样做一是攀附,二是炫耀,第三可能还有向复社示威的意思,暗寓江南的安定是间接出自他阮胡子。
笔者说很有可能出自阮大铖本人,并不是凭空臆想。《留都防乱公揭》说“大铖于大臣之被罪获释者,辄攘为己功,至於巡方之有荐劾,提学之有升黜,无不以为线索在己,呼吸立应。”由此来看,阮大铖在马士英复出之事上夸口炫耀的可能性极大。而且官私各家记载,对此不靠谱的传说均记而不疑,当有确切可信来源。所谓“确切可信来源”,只能来自于当事双方。而周阮之间,周延儒于此等事,回避否认尚且不及,更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抹黑。唯一可能,也就是出自阮大铖自己的宣扬。
由于马士英自福王登基,同一度还能合作的东林复社诸人渐行渐远,分道扬镳,又力主重新起用阮大铖,后来为筹措经费更是激怒江南世家豪族。南都从官场士林到民间商界,仇马形成风气。东林复社党社成员出于种种原因,乐于将这明显贬低马士英的传说到处宣扬,再经众人之口辗转流传,就似乎真的成了事实。从此马阮并提,甚至连马士英辛苦征战建立的种种功绩,也不再被人们提及,几乎被抹杀殆尽了。
下
福王登基之后,马士英不顾朝中众位大臣的反对,坚持推荐起用阮大铖。同前述阮大铖助马复出的传说互相呼应,似乎形成了马阮勾结的完整环节。
对于阮助马复出的说法之谬,前文已作辨析。而对于马士英推荐阮大铖,则应当依据南都政治形势、人际关系、施政态势方方面面细加辨析。略而言之:马士英因军方态度而改变拥立立场,(顾诚先生据《过江七事》考定)被一些东林党人认为有意出卖,加之若干人事、政务与东林一派不合,从而导致众多施政主张遭到把持南都官场的东林复社党人种种抵制。作为已身居关键高位的首辅,马士英亟需打破这种被动局面,需要物色非复社东林一派的人选入朝“掺沙子”,这样的情况下,才名远扬,且与己曾诗酒唱和、关系亲密的文友阮大铖,自然要成为马士英极力推荐入朝任职的对象。
同时,马的本意并不是要与朝中占主要势力的复社东林党社成员截然对立,而是看到了如后世所说的“民族矛盾大于阶级(党派)矛盾”的局面,希望打破党社的壁垒,广用人才。故而李清《三垣笔记》日:“马辅士英初亦有意为君子,实廷臣激之走险。当其出刘入阮时,赋诗曰:“苏蕙才名千古绝,阳台歌舞世无多。若使同房不相妒,也应快杀窦连波。”盖以若兰喻刘,阳台喻阮也。”
当然,待到阮大铖一旦真的复出,坐稳了官位,“一阔脸就变”,甩开马士英,另行其事,不顾马的劝阻,大兴冤狱,迫害东林党人。在马是识人不明,而于阮本身则是人品的问题了。
总之,马士英同阮大铖,两人在特定处境之下,结成了诗酒雅集的友好关系。后来,阮大铖助马士英复出的传说被渲染传播,而马又不肯在施政时迁就复社东林党人,造成“被对立”的局面,马阮这种关系就被方方面面有意夸大,也就造成了陈援庵先生感叹的“马、阮并称,诚士英之不幸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可为士英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