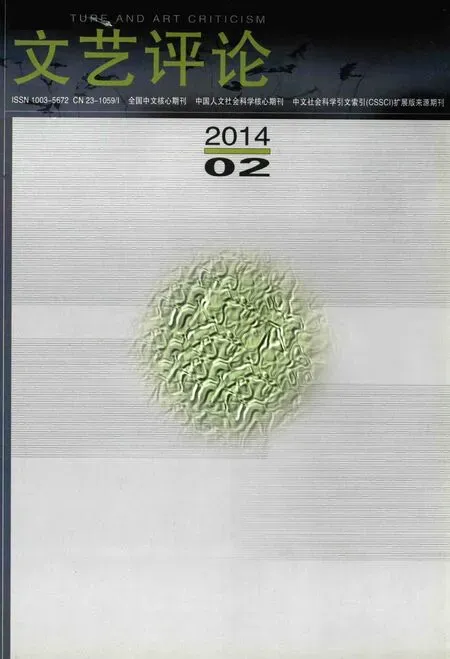“沉郁顿挫”:杜甫“当时体”追求的体现
王艳军
“当时体”①是杜甫诗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杜甫对于初唐四杰等前人及其诗歌创作批评中的一个诗学概念。目前的学术界,大都聚焦于杜甫诗论的总体内涵、思想渊源、地位影响,但对于杜甫诗论中的“当时体”的美学内涵阐释不够。“沉郁顿挫”是人们对杜甫诗歌风格的最主要概括,笔者拟通过“沉郁顿挫”、“当时体”内涵的比较、阐释,进一步探讨杜甫诗论的内涵及对杜甫诗歌的作用。
一
对于杜甫的诗论思想,学者多关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三首诗作,尤以《戏为六绝句》着力最多。就《戏为六绝句》思想的诠释,学者们各自引述,言之成文,论及语义、思想、形式等方面,然就《戏为六绝句》中“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等具体内容又颇多疑虑和争议。又如“当时体”,这是杜甫在此诗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学者们很少提及,既是涉及到也是杂糅到《戏为六绝句》整体诗论思想中,很少单独论述,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创作实践来看,杜甫入蜀前后的古体并非多用律句,从《戏为六绝句》本身来讲,“当时体”并非仅属于艺术表现形式的范畴,而是杜甫将思想、内容、形式、风格合而为一所产生的一个诗学概念,是指诗人创作中所具有的体现时代特征并融合诗人艺术特色的一种艺术取向。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第二首提出了“当时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二)
从诗句来看,杨炯、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诗文为什么是“当时体”,当时轻薄为文者所哂笑的是什么,杜甫并没有明说。“当时体”如何解释,浦起龙《读杜心解》仅提出“宜于一时成体之文”②,仇兆鳌《杜诗详注》提出“四公之文,当时杰出”③,都没有详加注释,但可以肯定的是杜甫认为四杰“当时体”之作是“不废江河万古流”。
仅从这一首诗而言,“当时体”确实很难理解,《戏为六绝句》是一脉贯穿的六首诗作,再看其他五首: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其一)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其三)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蓝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其四)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做后尘。(其五)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其六)
对于《戏为六绝句》的创作,清人浦起龙指出“后生轻薄,附远而谩近。盖远者论定既久,不敢置喙。至于近人,则哆口诋呵,以高自誇诩剽窃古人影响,博其谈资。究其古人所谓师承派别之源流,茫乎未有闻也。少陵痛焉,而作是诗”④。由此可以看出,在这六首诗中,诗人杜甫举近代诗人庾信、四杰以立案,“附远而谩近”的轻薄后生毫无忌惮的“嗤点”,使前贤生畏惧之心,杜甫是为庾信、四杰等前辈诗人叫屈,提出了“当时体”的观点和主张。
庾信、四杰是唐前和唐初的重要诗人,庾信由南入北后的诗文“老愈成格,其笔势则凌云超俗,其才思则纵横出奇”⑤,诗风文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四杰未脱六朝习气,然“宫体诗在卢骆手中是从宫廷移到币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到江山塞漠……五言八句的真正唐音是从他们开始的”⑥,杜甫以“当时体”论之,“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⑦,换言之,杜甫驳斥那些轻薄后生,以“当时体”来评价庾信、四杰的地位和价值,再结合诗作中的“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鲸鱼碧海”、“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等表述,可以看出“当时体”并非执于一端,而是涉及思想宗旨、创作倾向、语言词句、表达规范、形式技巧等多方面的内容,“亲风雅”和“老更成”着力于思想追求,“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着力于创作倾向,而“老更成”和“凌云健笔”则是诗歌艺术风格上的体现,庾信和四杰的时代、思想不同于杜甫,创作的体例和规范也不同于杜甫,杜甫认为他们的作品将这多方面综合到了一起,他们的作品才形成了时代性和历史性,也才能“江河万古流”。杜甫能够以“当时体”概论他们的作品,体现了杜甫审视文学的历史眼光和发展理念,因此,“当时体”作为一个诗学概念,我们可以看出从诗论的角度以及对前人的态度,杜甫同样站在了唐诗发展的时代高度和历史高峰。
二
“当时体”是杜甫的艺术追求,“沉郁顿挫”是杜甫诗风的概括,不论从唐诗发展还是杜甫自身的诗歌创作来看,“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是杜甫“当时体”创作追求的体现。
“沉郁顿挫”出自杜甫《进〈雕赋〉表》一文:“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及也”。在此文中,杜甫将自己的作品与杨雄之作都看作是“沉郁顿挫”之文。至此,后世学者多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甫诗歌的基本风格,但对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却说法不一。
在这当前各大高校最通行的三个版本的文学史教材中,对于“沉郁顿挫”都是强调“特征性”、“最主要”,而且将“沉郁”和“顿挫”分而言之,基本可以概括为“沉郁是思想博大精深,内容厚重丰满,感情深沉郁勃;顿挫是诗句意思的频频逆转以及形成的回旋、激荡的文势”⑧。如游国恩等先生认为“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时代环境的急剧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⑨。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家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曲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⑩。而袁行霈先生认为“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⑪。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本人并没有解释“沉郁顿挫”的含义。后世学者在论及“沉郁顿挫”时,大多着眼于“沉郁顿挫”的内涵、特征,很少涉及《雕赋》本身,更没有涉及杜甫对诗歌功能的认识,也就是杜甫的诗论思想。应该看到杜甫认为《雕赋》具有沉郁顿挫的风格,并以此进献给皇帝,再参照刘歆在《与扬雄书从取方言》中所说的“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大致也可以推断出“沉郁顿挫”绝非仅指“沉郁”或“顿挫”某一方面,而是更加侧重于二者的结合所形成的一种诗歌风貌。我们把“当时体”与“沉郁顿挫”结合起来来看,尽管《进〈雕赋〉表》和《戏为六绝句》两篇作品的创作时间相差了10年,但它们的内涵、义理却是一致的,“当时体”的艺术追求下所形成的诗风正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的形成条件恰恰是“当时体”在思想倾向、创作技巧、艺术形式三方面的要求,二者相互阐释又相互补充,兼综互系,在杜甫的诗歌体系中,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诗歌理论。
三
“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是杜甫“当时体”创作追求的体现,前提是杜甫思想的深邃和老成。提出“沉郁顿挫”的《进<雕赋>表》创作于天宝九载(750年),提出“当时体”的《戏为六绝句》创作于上元二年(761年),相差10年,这10年是大唐王朝巨变的10年,也是杜甫尝尽人生艰辛并思想深入转化的十年。天宝年间杜甫困居长安,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往奉先,至德元载自鄜州奔行在、陷贼中而羁押长安,至德二载脱贼谒上凤翔,乾元元年六月出为华州司功,乾元二年七月辞官往秦州、十月奔同谷、十二月远赴成都,上元元年卜居浣花溪畔,终于暂时栖居于草堂。这10年之中,杜甫既感受到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困居长安的屈辱,也经历了“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入门闻嚎啕,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人生大难,也饱受了“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⑫生活困顿之苦,更是备尝了乾元年间“一岁四行役”、“三年饥走荒山道”(《发同谷县》)的流离的艰辛。这10之间,《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羌村》、《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寓同谷县作歌七首》、《秦中杂诗二十首》写出了安史乱后政治的多难和民生的多艰,也写出了诗人在战乱中颠沛流离的悲痛。10年之间,尽管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忠君、爱国、忧民的思想始终如一,但乾元二年的华州辞官则意味着杜甫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草堂生活中,诗人杜甫面对“昼引老妻乘画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的朴实宁静的江村生活,也流露出了以前少有的“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水槛遣心二首》)的闲适之感,这一类诗作也就成为杜甫“风云变幻忧患重重的诗史里,有如暴风雨中暂时的晴霁,重峦叠嶂中的一缕清溪”⑬,风格、题材迥异于其他时期,但这绝不是草堂时期杜甫的主要思想。杜甫虽然欣赏和自足于暂时的生活状态,对理想的坚守和对政治的关注仍是杜甫思想的主调,杜甫欣赏却不能完全融入到当下所处的生活之中,这就是造成杜甫痛苦的渊薮。“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两首》),这才是杜甫心中挥之不去的真正隐痛。
也正因此,杜甫由“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联想到“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由“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联想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草堂时期的杜甫有过矛盾和困惑,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与那个动乱的时代相结合,才更加彰显出杜甫对国家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才更加令人感觉真实可信,沉郁苍凉、闲适自得、悲愤伤感交杂在一起,少了早期的锋芒毕露,更多以理智和深沉,才形成了沉郁顿挫的情感内涵。此期的杜甫“当兵戈骚扰流离之际,道路颠顿冻饿之余,其忠君一念,炯然不忘,故其发而为诗也,多伤时悼乱痛切危苦之词”⑭,同时,“杜甫开创了诗歌写意的风气,不仅在感事述怀中频繁穿插对时政的意见,还写了一定数量以陈述意见为主的诗作”⑮。
《进〈雕赋〉表》杜甫提出了“沉郁顿挫”,还仅仅是对自己作品风格的大致勾勒,至于如何形成“沉郁顿挫”杜甫并没有详细的解说。而这10年之间时代的巨变以及诗人生活思想的变迁,促使诗人杜甫在创作中践行这种诗风,当然这种践行并不是诗人有意为之,而是时代巨变之中诗人自身的一种调整,一种自觉,而且践行这种诗风的过程充满了艰难和痛苦。创作《进〈雕赋〉表》10之后,杜甫又在《戏为六绝句》中提出了“当时体”,这是杜甫对10年之间诗歌创作实践的思考,是对自己10之间用独具时代特色的诗歌形式反映的时代、生活、精神的诗歌风格的理论升华,是杜甫自己对逐渐形成的“沉郁顿挫”诗风的理论阐释。
四
“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是杜甫“当时体”创作追求的体现,基础是杜甫创作实践的努力和积淀。杜甫提出了“沉郁顿挫”,却没有解释“沉郁顿挫”的内涵和特征,而其形成又经过了长期的积累、酝酿、融合、提炼的过程。“当时体”作为杜甫的诗歌美学主张,在“亲风雅”的思想倾向、“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创作技巧、“凌云健笔”、“老更成”的形式规范三方面的要求,恰恰是“沉郁顿挫”诗风形成的必然要素,因此“当时体”和“沉郁顿挫”在创作实践上是一致的。
“风雅”是传统的儒家诗学主张,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崇高理想的杜甫,“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宗武生日》)和“缘情慰飘荡”(《偶题》)的精神,使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挠弱,情不忘君”⑯,杜甫“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⑰,诗作中呈现出“上感九庙焚,下忧万民疮”(《壮游》)、“百年从万事,故国耿难忘”(《遣闷》)忠君爱国、忧民伤时的情怀,“亲风雅”是杜甫一生诗歌创作的情感依托。
在创作实践中,杜甫把“亲风雅”这种精神和情怀与“比兴”的手法结合起来。就《雕赋》本身而言,杜甫以雕自喻,希求引荐,却“有悲壮之音,无乞怜之态”⑱,作品对小人尸位禄餐而君子困厄远遁的现象进行批判,就像仇兆鳌所说的“雕鹗飞而乌枭匿形,犹正人用而佥壬屏迹。陈力窃位,明刺当时素餐尸位之流”⑲,作品以比兴的手法寄以讽喻,情感意蕴深沉而又曲折委婉。再如杜甫读到元结《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两首诗时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士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⑳,在这段小序中,杜甫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来高度评价元结“道州忧黎庶”的情怀以及对“盗贼未息,知民疾苦”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再如草堂时期的创作的《恶树》、《病柏》、《病橘》、《枯棕》、《枯楠》一组咏物五律,比兴中表达作者对时事的关注。而《江头五咏》等五律组诗借比兴手法表达杜甫“时而自防,时而自惜,时而自悔,时而自宽,时而自警”㉑的情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作品中不仅对时事的关注多借助比兴手法,更重要的是强调作品要能够发扬美刺比兴的精神,使诗歌直面现实,对统治者和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有所批判又含蓄婉转,不失温柔敦厚。“比兴体制”和“微婉顿挫之词”的结合,从诗歌功用角度来看,这是一代诗人面对巨变的时代,对于朝廷、对社会、对民生强烈期盼而希望诗歌发挥价值的要求;从杜甫自身创作实践来看,二者结合就是“亲风雅”的必然要求,更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形成的基础。
同时,杜甫在创作形式和技巧规范方面也与“亲风雅”的创作思想倾向相适应。在创作形式上首先要“别裁伪体”,还要“转益多师”,最后形成“老更成”“凌云健笔”的风貌。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对四杰、庾信以及屈宋的态度,也就是杜甫对待六朝以及前人诗歌的态度。对于六朝诗歌,初唐存在着不同的态度。沈宋、上官仪等人继承了六朝诗歌音韵和谐、辞藻华美、对偶工整的特点,而陈子昂、李白等人则从恢复风雅的角度对六朝持以批评态度,并力倡复古。杜甫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对于齐梁偏执形式、背离风骚传统的倾向予以批评,也就是“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既认识到了前代诗歌的不足,对前代诗歌的特点和成就,也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主张“转益多师”,兼收并蓄。如对庾信,早年杜甫认为“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在此期间则提出“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论诗戏为六绝句》其一),夔州期间更是认为“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之一)。“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这两句诗,从诗句内涵上讲,“凌云健笔意纵横”是对前一句“老更成”的详细阐述,形象而具体。而这些也恰恰符合杜甫安史乱后诗作中的情思沉郁、笔力苍健的风格。庾信由南入北之后,将追求声律、句法、用典等南朝诗歌创作技法与个人身世离乱之感相结合,“子山身坠殊方,恨恨如忘,忽忽自失。生平歌咏,要皆激楚之音,悲凉之调。……汇彼多方,河汉汪洋,云霞蒸荡,大气所举,浮动毫端。”㉒。庾信后期诗歌所形成的这种“老成”境界,其实也正是杜甫安史乱后诗歌创作中所努力追求的。正是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使杜甫在创作实践中不自觉地学习并借鉴了庾信入北后的诗歌境界,这也正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形成的重要原因。
再如对屈、宋。杜甫与屈、宋“萧条异代不同时”,一部杜诗,其中直接提及屈、宋的有18首之多,杜甫对于屈、宋的评价,不仅仅是其艺术风格的赞同,还有就是情感上的共鸣。“迟迟恋屈宋,渺渺卧荆衡”(《送覃二判官》),“曾闻宋玉宅,每欲到荆州”(《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官重赠》),“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奉汉中王手札》),杜甫对于屈、宋遭遇的悲悯和同情,也是对自己际遇的自悼。杜甫推尊屈、宋,是站在艺术自觉的立场上,不仅肯定其艺术表现,提出要“窃攀屈宋”,而且认为“亦吾师”,将自己人生的不平、追求、情怀借对屈宋的肯定而表达出来,就像仇兆鳌指出的“扬宋玉者,亦所以自扬也”㉓,“怀庾信、宋玉,以斯文为己任也”㉔。正是对屈、宋在艺术表现和思想情怀上的融合,使杜甫的诗作体现出了“当时体”的时代特色。草堂时期,蜀中清秀的山水与野郭江村的情趣,使杜甫对于齐梁诗歌的“清新”特质有了更深的认识,并加以借鉴,展现了“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吊钩。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江村》)的暂享安逸时闲适自得的情趣,但“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至后》)的现实,是诗人杜甫更多的表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奉赠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恋阕丹心破,沾衣皓首啼”(《散愁二首》)、“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恨别》)、“兵戈与人事,回首一悲哀”(《遣愁》)、“故国犹兵马,他乡亦鼓鼙”(《出郭》)的忧虑、愤懑和悲凉。在这波澜起伏、开合顿挫的境界中呈现出的那位“江边老人”(《释闷》)、“天边老人”(《天边行》),与屈原、宋玉、庾信等怀有一样的孤寂和凄凉,这样的诗作,就像郭绍虞先生所说的“杜老诗风,能兼清新、老成二者”㉕,所形成的自然也是“沉郁顿挫”的诗风。
要之,“沉郁顿挫”是对杜甫诗歌风貌的概括,是杜甫深厚的思想内蕴和老成的创作手法的结合体,意味着杜甫诗歌创作形成了自我的风格和特色。“当时体”则是杜甫诗歌美学主张的核心,是杜甫诗歌艺术取向的凝练,所要求的“亲风雅”、“转益多师”、“凌云健笔”的三个方面在创作实践上与“沉郁顿挫”的诗风恰好一致。因此,“沉郁顿挫”诗风的形成是杜甫“当时体”创作追求的体现,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完善了杜甫的诗歌理论,也共同作用于杜甫的诗歌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