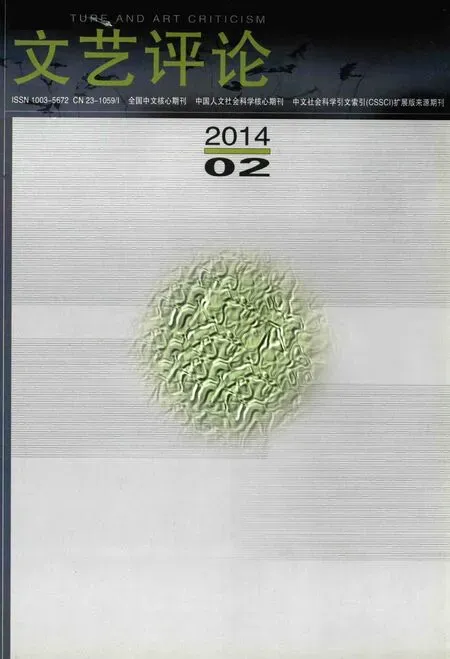先秦儒家音乐形式论对道德心的培养
吴 琪
先秦儒家非常看重音乐形式对道德内容的重要作用,主张在音乐审美和教化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统一。“美”是对艺术形式的评价和要求,“善”是对艺术内容的评价和要求,即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区分了美和善,但是又充分肯定了美和善的统一,即:道德评价与审美评价的统一;善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他提出“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为音乐的内容与道德形式的理想状态。他批评“郑声淫”、“放郑声”,这里的“淫”、“放”既指在内容上不符合道德要求,又是指在形式上过于繁、慢、细、过,僭越了对和谐的要求。本文将具体从音乐仪式、音乐节奏旋律、音乐和谐及无声之乐四个方面分析先秦儒家音乐对道德的作用。
一、音乐仪式与道德情感的培养
“礼”作为先秦儒家的音乐仪式——儒家音乐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对音乐仪式的重视,音乐仪式在儒家这里就是音乐中的“礼”。礼即是仪式性的形式,用以在外部规范一定活动中的行为方式,在内部引发人的尊敬、肃穆之情,从而引导人接近道德的境界。这种“礼”的形式的直接表现为对等级的重视。《周礼·大司乐》提供的礼乐便是关于天、地、人——先祖之间的等级结构的生动例证:
祭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
祭地示: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地。
祭四望: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
祭山川:乃奏宾,歌函钟,舞大夏。
祭先妣: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
祭先祖: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
先秦儒家以“礼”为音乐仪式的目的是为了表现“仁”的精神内涵,“仁”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所以“礼”是为“德”服务,而“乐”只有以“礼”的形式去表现,才可以把实质的“仁”的精神体现出来。
孔子有感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主张恢复周礼以期回到西周时期和谐道德的社会秩序。在音乐的情感上,孔子推崇“思无邪”的境界,认为诗歌音乐的思想与感情都应该纯粹端正、天然无邪、合乎礼制。荀子把孔子的思想进一步明晰化,他提出“礼乐”范畴,正式提出“一之于礼义”的对音乐的形式要求。《乐记》总结性的集成孔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礼乐思想,指出合乎“礼义”的音乐当使其声、气“皆安其位,而不相夺”,具体化为社会伦理即“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为了达到“和”的音乐的理想道德境界,先有作为主宰、君王的“一”,然后才能“审一以定和”,能“合和父子群臣,附亲万民”,能“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以礼制服。
儒家用礼乐思想对音乐做仪式化的规定,同时是一种对情感的节制。自由的抒发情感是逾礼的音乐行为,是绝对要被摈弃的。“思无邪”的要求本身就包含着对“淫声”、“放声”的否定。“一之于礼义”、“发乎情、止乎礼义”规定音乐对情感的表现必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体现在社会等级制度上就是反对下层对上层抒发不满之情,作不平之鸣的郑卫之音是孔子所讥讽和反对的。以礼制情走向极端便成了以礼抑情。
把礼作为音乐的仪式并不单纯是外在的规定,先秦儒家企图把礼和乐提升到同等的高度,以达到礼乐同一、礼乐并举的目的和效果。礼和乐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都是规范社会的手段,其中礼用来“分”,即区分等级尊卑的社会身份,使人各循其轨,不逾规矩,这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同尊卑等级的人毕竟也都是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下的人,如果只强调“分”就有加深阶层间鸿沟、造成阶层对立的危险。所以在“分”的前提下还得有“同”,即沟通和交流,乐就能起到沟通人们情感,造成共鸣的效果。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通“纹”,指纹饰图案的形象,引申演变为后天形成的文化,包括礼、乐对人的教化雕琢,表现为形式美;“质”是指一个人内在的品质。“文质彬彬”作为孔子提出的审美标准在音乐审美中的表现就是礼乐并举。荀子对礼乐的相互作用的重视在先秦儒家中非常突出。他提出“乐合同”、“礼辨异”,就是强调音乐能够沟通人的情感而礼能够区分人的社会等级。二者并用是达到“天下皆宁,美善相乐”理想世界的必要条件。
总之,礼和乐相辅相成,正好构成一对矛盾,二者的同一性表现为“德”。礼和乐共同维持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在这对矛盾中,礼由于直接承载着道德的精神从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主导地位;乐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为礼服务,唯礼的马首是瞻。乐的从属地位使儒家音乐最终失去了音乐创作天然的自由性,主旋律成为正声,沦为阶级统治的工具。
孟子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中政治性最直接最强烈的。孟子提出,“仁声”即雅颂之乐是一种理想的教化手段。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雅乐”是与“郑声”针锋相对的一种音乐形式。“雅乐”是为王朝服务、为统治者的统治秩序服务的一种音乐形式,它通过规定好的周礼制度来达到对被统治者进行道德教化的目的,约束人们的行为,反映王朝的政治风貌。而“郑声”代表了来自民间的音乐形式,体制自由放任,不是对情感的节制而是对情感的放纵。雅乐用以教化万民,郑声用来享乐自己。儒家摈弃郑声而推崇雅乐直接的看就是因为郑声不符合礼的规范。
我们还可以从儒家教育的模式看出礼乐的关系。儒家传统技能“六艺”是西周时期学校教育的内容,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其中政治、历史以及以“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都属于礼。乐是包括有音乐、诗歌、舞蹈的总和艺术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弟子们外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弟子们内在的情感。在礼乐教育中,礼为主,乐为辅,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
先秦儒家音乐思想还强调礼乐一体,二者共通的基础是伦理道德。所谓“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礼记·乐记》),无论是“相亲”还是“相敬”,都属于伦理的范畴。《周礼·春官宗伯》中直接指出乐和德的内在联系,“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孟子说:“闻其乐而知其德”(《孟子·公孙丑上》)。“德生礼,礼生乐”,从“德”到“礼”、“乐”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是一个逻辑链条上顺理成章的自然过程。礼乐在德的意义上实现了统一。
礼乐同德的另一个表现是乐和礼的基本精神分别是“和”与“序”。“序”是有条理、有秩序、有清晰稳定的时间结构。“和”是指社会各种事物以及事物内部的各要素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达到了一种矛盾平衡的状态,这是一种动态平衡。无论是音乐的“和”还是礼的“序”,其指向都不是矛盾冲突所导致的质变,而是在适度原则内的平衡状态,这种状态便是“德”的本体。
二、音乐的节奏旋律等形式因素对人心理、精神的调适与美化
音乐由节奏和旋律两大要素构成,音乐对情感的调适作用也可以归结为节奏、旋律对人心理、精神的调适。节奏是指运动过程中有秩序的连续。节奏的构成包含两种关系:一是时间关系,即运动的过程;二是力的关系,即强弱的变化。①旋律亦称曲调,是经过艺术构思而形成的若干乐音的有组织、有节奏的和谐运动。它建立在一定的调式和节拍的基础上,按一定的音高、时值和音量构成的、具有逻辑因素的单声部进行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对音乐的节奏和旋律的认识,尤其是其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调适与美化作用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言论和观点,其理论内涵与儒家音乐美学的思想是相通的。
1.“和”、“同”、“平”之辩
《国语·郑语》中记载了公元前773年周太史伯与郑桓公的一段对话。史伯提出“和”是万事万物向良好的状态发展的核心标志,如果不能做到“和”,事物就会衰败乃至灭亡。“和”不是单一元素一潭死水的简单状态,而是一种多样性元素的动态平衡。如果构成系统的要素种类不够多,那么系统就难以为继。史伯由此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命题。只有不同的事物之间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异类相杂,才有可能做到“和”的状态,因此“以他平他谓之和”。体现到音乐上,就是要有节奏和旋律的变化和丰富,“声一无听”,单一的节奏和声音不可能动听,应该“和六律以聪耳”。音乐的美不在于一而在于多,不在于同而在于和。
春秋时齐相晏婴对史伯的“和实生物”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发扬。《左传·昭公二十年》中记载他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反映了晏婴的音乐形式美学思想。晏婴首先认同史伯“和实生物”的理念,但他认为“和”是事物调适后的状态,晏婴提出调适的具体法则应该是“平”。“平”就是要“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平”的理念可以从音乐拓展到人心,从客体的“平”达到主体的“平”,能够“平其心”,“心平德和”,发扬到政治生活中则“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晏婴更加具体的提出“平”在音乐上的法则,“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这显然比史伯的“声无一听”单纯从听觉上谈音乐节奏与韵律的“和”要丰富具体得多。
2.“五行”、“六气”说
对万事万物作朴素系统论说明的阴阳五行学说在我国春秋时期颇为兴盛,推衍及音乐观上则成为对节奏、音律关系原则的完整理论。《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记载郑国子大叔引用子产的一段音乐美学观可以作为先秦五行音乐观的代表性思想。
子产认为,天有“六气”,地有“五行”,体现在人身上使得人有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世间万物都“协于天地之性”而效法天地“五行”“六气”的运行法则。音乐的“五声”就是五行的直接表现,应当和万物一样外守“礼”这一根本法则,内和天地之性,“既要‘奉五声’以节制其形式,又要‘制六志’以节制其内容”。②子产虽然主张“五声”及五声之间的相生相克的配合为音乐旋律所应遵循的至理,但他并不因此排除“七音”、“六律”。所谓“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只要音律学中的这些概念尊奉以五声为正统的基本原则即可。
3.器和与乐和
在音乐的诸形式中,除了音乐内在的节奏和旋律之外,不能忽视的是音乐外在的乐器、技法等因素。《国语·周语下》中记载周景王欲铸乐器大钟时单穆公对其进行劝谏时所说的一段话表达了先秦音乐美学中这方面的重要思想。单穆公说:
夫钟声以为耳也,耳所不及,非钟声也。犹目所不见,不可以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察色也,不过墨丈寻常之间。耳之察和也,在清浊之间;其察清浊也,不过一人之所胜。是故先王之制钟也,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
单穆公在这里明确的提出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乐器制作的尺寸法度要合乎人的听觉能力的限度。如果超出度量,没有节制,就会“耳所不及”,无法感受音乐,更遑论感受音乐的美,即“听之弗及,比之不度,钟声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节”。他指出制作钟这种打击乐器的尺度是“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心灵在审美活动中所感受到的音乐的和谐要以乐器制度的和谐为先决条件。
伶州鸠是周景王的乐官,《国语》中记录了他和周景王由铸大钟而引发的多次针对音乐的评论,其中也包括了单穆公劝谏周景王不要铸大钟的这次事件。伶州鸠继单穆公之后继续劝谏周景王时说:
臣之守官弗及也。臣闻之,琴瑟尚宫,钟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夫宫,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圣人保乐而爱财,财以备器,乐以殖财,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丝尚宫,匏竹尚议,革木一声。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乐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今细过其主妨于正,用物过度妨于财,正害财匮妨于乐。细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听声越远,非平也。妨正匮财,声不和平,非宗官之所司也。
伶州鸠在这段著名的谈话中首先从专业角度论述了乐器制作尺度和音律之间的关系,其中还谈到了乐器不同的质料与所演奏的音律之间的搭配关系。他指出乐器制造的一个基本法则是“故乐器重者从细,轻者从大”,这种法则本身是先秦音乐理论中“相成相济以为和”的一个体现。
接下来,伶州鸠进一步提出“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的音乐理念。他认为“平”比“和”更重要,恪守尺寸法度做到“平”这一点就能达到“中音”。伶州鸠也秉承“六气”学说,指出按照以上的规则制作乐器、创作、演奏音乐就能够“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
从先秦这些被儒家所认可和继承的代表性的音乐思想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贯穿音乐的形式和内容的链条:
三、音乐的和谐与人性的完善
在先秦儒家看来,无论是音乐还是人性,都是天地运行规律的具体体现形式,其本质都遵循“六气”、“五行”的天地自然之道。音乐的和谐与人性的和谐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由此可以相互促进,这是儒家音乐德育观的理论基础。具体说来,音乐的和谐可以由内及外的对人的内心完善、对人际关系完善、对政治生活完善。
1.音乐的和谐与内心的完善
完善的人性首先是情感的均衡与和谐,所谓“致乐以治心”。在《荀子·乐论》中荀子对音乐对情感的完善作用作出了明晰的说明。音乐是情感的内在需求。荀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人有好、恶、喜、怒、哀、乐六情,这些人之常情是人性的标志,是伦理道德所由产生的基础,缺一不可,但过犹不及,其中任何一种情感过度充斥都会造成心理失衡。如同音乐需要达到“和”的理想状态才能称之为美,人的情感世界也需要六情彼此之间相成相济、以他制他,达到“和”的状态才是心理健康的状态。然而,荀子从性恶论出发,认为人性不能放任其自由发展,“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放任情感恣肆必然就会发生混乱。因此,“先王恶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这样就可以“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完善的人性还需要认知能力的完善,荀子认为音乐的和谐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所谓“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荀子·乐论》)“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可见,先秦儒家认为和谐的音乐不仅可以平和人的情感,还能抒发远大的志向,帮助人明察事理、移风易俗。这些可以视为音乐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完善作用。
2.音乐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完善
音乐的和谐对人际关系的完善作用集中体现在音乐的德育作用上。因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道德的核心精神是“仁”,所谓“二人成仁”,“仁”是一个有关社会关系的范畴。
首先,表现在乐以安德——《左传·襄公十一年》中谈到,“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所谓乐也。”“乐以安德”是音乐的德育教化作用的基本命题,音乐可以通过稳定人的情感理智的内心世界外化为人的社会行为,使人处位有义,行教有礼,抱信守仁,心平德和。孔子说诗具备“兴”、“观”、“群”、“怨”的功效,这里的诗是音乐的一部分。其中“兴”是抒发内心的情感,“观”是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借诗能“观风俗之盛衰”,“群”就牵涉到了音乐的一个社会功效——加强社会群体的情感交流,这是德得以体现的基础。
其次,表现在礼乐弘德——儒家礼乐观围绕着弘扬儒家道德这一主题而展开。荀子指出,“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荀子·富国》)“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乐记·乐论篇》)礼乐是承载了道德教化目的的进一步社会化了的音乐。在儒家礼乐观看来,音乐不仅可以“安德”,而且还可以“耀德”、“风德”。“夫乐以开山川之风也,以耀德于广远也。风德以广之,风山川以远之,风物以听之,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夫德广远而有时节,是以远服而迩不迁。”(《国语·晋语八》)
礼乐对道德弘扬作用要结合先秦时代特征。在古代中国,信息传播的手段非常有限。先秦时期甚至连书写都缺乏后世那样轻便易用的载体,因此对道德思想的传播最有效的方式仍然只能是口口相传。在这种情形下,以声相传显然在形式上远不如以乐相传更具趣味性,所谓“乐者,乐也”,歌以载道成为先秦时期道德风气传扬最合理、最有效、最广泛的手段。
最后,表现在歌功颂德——“乐”与“德”的关系的第三个重要方面是音乐可以用歌功颂德的方式发挥其社会作用。在中国,尤其是先秦以后,这甚至成为音乐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左传·文公七年》),可见中国音乐几乎从呱呱坠地伊始就有了主旋律的社会功用。孟子称,“乐之实,乐斯二者(引者注:即“仁”和“义”),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这里甚至把歌颂仁义视为音乐产生和创作的源泉。《乐记·乐施》里也说:“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
“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致乐以治心者也。”(《乐记·乐化》)由于存在“致乐以治心”的效应,所以音乐成为德育最佳的载体,乃至于最终与道德同一,即“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乐记·乐施篇》)
3.音乐的和谐与政治生活的完善
音乐由社会关系继续外化就抵达了儒家全部思想所指向的终点——政治生活。德育的目的是为了美好的政治——德政服务,由内心情感到外在德行以致天下。《国语》中称音乐可以使民众“远服而迩不迁”,可见民众会因为一国音乐的作用而臣服其统治并沐化其中而不愿离去,这简直是《魔笛》中牧童手中那支摄人心魄的笛子。“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如是,则百姓莫不安其处,乐其乡,以至足其上矣。然后名声于是白,光辉于是大,四海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师。”(《荀子·乐论》)在这里音乐干脆在战场上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音乐是情声,是心声,是德声,是政声。音乐使人们心平德和,最终达到“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亦即“成其政”的至上效用。
四、无声之大乐与移风易俗的社会理想
先秦儒家音乐的精神指向从来不是音乐本身,而是指向礼,指向德,最终指向仁政。音乐是构建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的一个手段和途径。只要得到了儒家音乐的主旨,音乐的形式就可以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了。
1.“无声之大乐”的内涵
先秦儒家提出“无声之乐”的思想,把音乐美学上升到了本体论哲学的层面。《礼记·孔子闲居》中记录孔子曰:
无声之乐,气志不违,无体之礼,威仪迟迟,无服之丧,内恕孔悲。
无声之乐,气志既得,无体之礼,威仪翼翼,无服之丧,施及四国。
无声之乐,气志既从,无体之礼,上下和同,无服之丧,以畜万邦。
无声之乐,日闻四方,无体之礼,日就月将,无服之丧,纯德孔明。
无声之乐,气志既起,无体之礼,施及四海,无服之丧,施于孙子。
无声之乐的来源从本文前面的叙述中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乐记·乐本》中谈到音乐的起源,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可见,音乐的本原不在于构成音乐的形式要素——节奏和旋律——而在于人心。节奏、旋律只是把人心所感悟的音乐的内涵用有形的载体表达出来而已。如果悬置了音乐有形的载体,回归音乐直指人心的内涵,这就是“无声之乐”。
《礼记·孔子闲居》中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子夏的一段对话,进一步阐明了孔子关于“无声之乐”的内涵。子夏问孔子“何谓五至?”孔子回答:“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在这里,孔子把内心的志向(“志”)、诗、礼、乐、哀看做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概念链条,构建起“礼—乐—情”的儒家音乐理论体系。在这一系列彼此相扣的概念中,核心概念是作为“德”的代表的“志”,歌以咏志是音乐的目的,而志的精神本身是“不可得而闻也”的。那么只要得到了“志”的精神,就达到了音乐的目的,就不在乎音乐是不是有声。
子夏又问“何谓三无?”孔子回答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那么什么是无声之乐呢?孔子说:“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夙夜其命宥密”出自《诗经·周颂·吴天有成命》,这是一首歌颂文王、武王夙夜勤政,实行仁政以安民的诗歌。孔子在这里用形容文王、武王德政的诗句形容无声之乐,其本意在于说明音乐只是形式,其终极内涵直指政治生活的仁德精神。
2.“无声之大乐”的哲学意义
先秦儒家的“无声之乐”与道家的“大音希声”在哲学本体论上系出同源,均来自于《易经》的思想。儒家“无声之乐”中的“无”不是存在的对立面——没有,而是“无为”,是未被形式化的内容。孔子作的《周易·系传》中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经》中的“易”有简易、变易、不易三种不同的含义。“易无思也”中的“易”是“不易”,即世界不变的统一本体的意思。“无思”指世界的本体不具有主动性的思维,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无为”不是无所作为,因为谈到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作为的前提默认了该“无为”的主体具有主观思维性,这与“无思”是矛盾的。因此,“无为”指的是“不能成就”,比如液态的水“无为”容器,不能用液态的水作材料制成一个容器。“不能成就”就是尚不能被形式化。只有“感而遂通”才能成就天下万事万物。儒家“无声之大乐”就是这种非形式化的、作为天地万物本原的存在的本体“感而遂通”之后的一个体现。陈潞注《礼记集说》中解释“无声之乐”说:“无声之乐,始之以气志不违者,言内无所戾也,无所戾,则无所失;故继之以气志既得,得之于身,则人亦兴之;故继之以气志既从,人从之矣,则声闻于外:故继之以曰闻四方,日闻不已,则方兴而未艾;故继之以气志既起”。这里就把“无声之乐”看做是“气志”流溢的一个表现。
3.“无声之大乐”的现实意义
儒家的“无声之大乐”与道家的“大音希声”不同,后者是出世的、尚“无为”的、存在论的,前者是洋溢着入世精神的、尚“有为”的、道德本体论的。“无声之乐”是剥离了形式的儒家精神的内容,它不具有形式的直接现实性却在思想表达上比有声的音乐更加直接、更加现实,它指向政治生活,具体地说是统治者夙夜勤政为国为民的“仁政”,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相比道家的“大音希声”而富有现实性意义。
4.移风易俗的审美意义
先秦儒家提出“无声之大乐”的理念是为了剥离音乐的具体形式,直接宣扬音乐承载的内容——“德”,是为了改良社会风气,为达到“仁政”的政治理念服务。
孔子谈音乐时一向直指音乐的社会作用,他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这里是说,诗歌(音乐的一种形式)具有兴、观、群、怨四种社会效用,因此可以用来教化人民,移风易俗。
“兴”的作用是激发人的内在情感,从而引发兴趣,引起重视,这样才能打开人的心灵,为接下来的教化创造必要条件。一个人如果对一件事没有兴趣,就不可能对此事有深刻的认识,甚至连深刻的印象都不会有。“兴”就是利用人内在情感的作用激发人的重视和兴趣。
“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乐记》中说“乐行而民向方,可以观德矣”。通过对某国、某地人们音乐形式、内容、偏好的调查,可以间接而真实地了解到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活。《诗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衰以思。其民困。世治乱不同,音亦随异,故学诗可以观风俗而知其盛衰。”“兴”是从主体自身内心深处的规律出发,“观”则是置于主客体观察与被观察的认识实践中去把握社会关系,是一种社会性的认知活动。
“群”孔安国以为,“群居相切磋”为“群”,是说音乐能够促进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由此培养社会人的群体意识。《论语·述而》中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说明孔子很重视利用音乐作为与人加强情感交流,进而借此进行德育教化的手段。
“怨”据孔安国的解释为“怨刺上政”。在孔子的思想中,对“怨”的社会功用具有明显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孔子认可“怨”作为民声的必要性和积极意义,比如《诗经》中的很多篇目就是以“怨”为主题,音乐毕竟不能只有歌功颂德,完全成为统治阶级谎言和暴政的鼓吹。孔子自己也是一个感情充沛,遇到违反纲常礼制的现象不惜一“怨”的人,季氏用天子之乐,孔子怒曰:“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这就是“怨”。另一方面,孔子对“礼”的尊崇使他反对无条件的“怨”,所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而不违,劳而无怨”,对国君应该“勿犯之”,反映了孔子对“怨”的节制和有条件性。
《孝经·广要道》记载孔子曾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为政当兴礼乐以移风易俗,教化天下,这是先秦儒家“无声之大乐”的终极目标。
——由刖者三逃季羔论儒家的仁与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