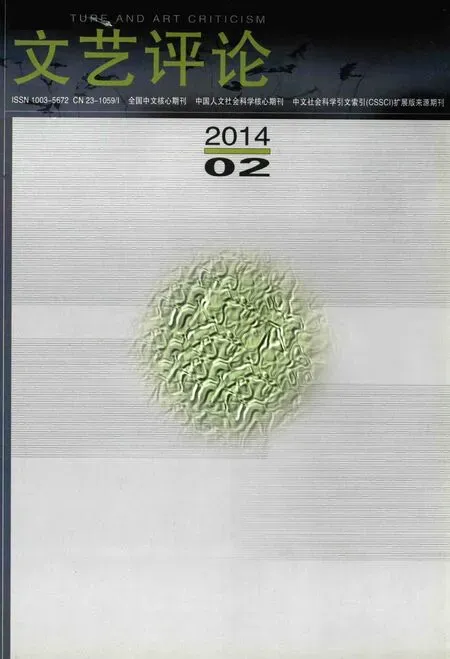石韫玉归田本末考
张淑贤
石韫玉,字执如,号琢堂,晚年自号独学老人。乾隆五十五年中得状元,授于翰林院修撰。自此步入官场,宦海浮沉十八载,对于一朝成名的状元石韫玉在官至三品却突然退隐的原因,历来学者未有深入探究。笔者根据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资料,与石韫玉的外甥吴嵰记载的《独学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吴谱》)和其学生陶澍为其撰写的《恩赏翰林院编修前山东按察使司按察使啄堂石公墓志铭》(以下简称为《墓志铭》)对比,探讨石韫玉罢官始末的真正缘由。
一、石韫玉办理柳氏案件的经过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资料
嘉庆十二年身为山东按察使、署布政使的石韫玉,因一桩民案突然辞官归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三份奏折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嘉庆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位山东栖霞县村民的状纸送抵京城:
具状人柳开生,系登州府栖霞县民,民年三十二岁。为大盗横行,强奸幼女,求伸奇冤,以正国法。事窃小的,住栖霞县东北乡东林村东南角,虽非村外,邻无几家。小的久雇工在外,家有孀母妻妹三人。上岁六月初二日夜,有强盗三人,抗门直入,明火执照。将小的母按住咽喉,刀戳面皮,不能出声。小的妻,潜藏磨底黑影,不敢出声。二贼将小的幼妹,刀押脖项,火速抢去,将睡鞋裹脚,俱已拉掉。及贼去后,小的妻母,惊死复生,扬叫四邻,合村人等,追寻无踪。黎明赴县具禀,县主公出门,上曹二阻报,不接禀告,捕听把总,一概告病不接,无奈回归。至初四日天明,小的妹袒卧村外,遍体是伤,不似人形。小的背负至家,问及来历。小的妹言,抢去山中,有一石洞,不知是何地方,贼等轮流行奸将明,绑缚不能动移,贼等回避无踪。更后又复轮流行奸,见其被奸将死,本欲杀害,又言奸骗两宿,将伊送回村外,任其死生。就是却说:“吾辈多人,左右探听,你归家若说实情,将你合家杀死。”
县主公回,情急授禀,立差捕厅,亲验是实,却视为平常,绝不理论。初十日赴府,具禀批,仰栖霞县,会同营汛,多差干捕,分路严缉,毋稍稽延。致干参咎,至六月二十二日拿获,捕头闫国烈,妻弟王三一名,供有蓬莱县宋二、毕聋子同抢同奸,县主并不差缉。王三屡供屡翻,县主任其游移。小的祖叔等俱在学校,几次肯催。县主口称,不知贼存何地,于何严缉?生等即系上告本县,甘被四参,料自不妨。不得已,小的又控府、控道、控臬宪,案下俱批:抢奸室女,罪不容诛。仰登州府,饬县勒缉逸犯,毋任漏网,府主转委黄县,县主赴栖霞县会审王三,不知是何情理,于九月十八日,差衙役王连元、赵庆、杨友贵等、押婆崔高氏,手执籖票。严拿小的妹,与盗对质,刻不容待。小的妹自思,既污于贼,又复当官出丑,自缢殒命。小的等,情急再投臬宪案下,不知因何情由,蒙批奸宿连宵,断无不识其面之理。只须到案一认,便可定真伪,自寻短见,且死于奸夫获案之后,难保其非,和诱同逃,恐事将败露,羞愧而死。姑候饬县,确讯实情,详到察夺,似此大逆无道,批成风流景况。
小的等,情实难容,急投院具禀蒙批,盗抢轮奸,不法已极。仰登州府,督同该县速究详报,此后屡控屡批屡搁,连绵二载。竟置指批,泣思人即廉耻尽无,谁肯以幼女被奸,误赖贼盗前禀,更后行奸,将明回避,焉能识面,何可对质?小的祖叔等,俱在学校,如果和诱同逃,隐讳不及,谁肯举露当官?此案延搁,现今栖霞县,贼盗风起,遗害益甚,世无王章,万民受害。小的实在求救无门,遵谕死达宪听。肯恩奏请,遣差秘访栖霞县,一并邻县等处,有不肤心切齿,愤激此事者,小的合族千罪不虚,求整国法,以释民情,生死顶祝万代。①
此外以左都御史广音为首的都察院,将对石韫玉弹劾的参本送到了嘉庆帝面前:
嘉庆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及其已死,控司又疑为和诱,是此案生死名节关系较重,未便凭空武断,致贼狡卸翻供,希图漏网。应请旨勅交钦差左都御史周廷栋,刑部侍郎广兴…并将该县延不究办,以致酿命,及该臬司于被污羞忿自戕之案疑为和诱,不加昭雪,是否有心讳盗及瞻徇属员之处,一并据实严参②
以及左都御史周廷栋、刑部侍郎广兴对石韫玉的参本中,记载了他对此案的批语:
嘉庆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柳氏闻传羞愧,即投缳殒命,伊族人生员柳儒赴省,在臬司石韫玉前控告。该司即以“该氏不死于被奸之时,而死于奸夫获案之后,难保其非和诱同逃,羞愧而死等词”批饬。③
嘉庆帝看到对石韫玉的不同参本,可谓是龙颜大怒,自此石韫玉曾显赫一时的官运急转直下:
嘉庆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前据都察院奏,山东栖霞县民人柳开生呈控,伊妹被盗抢劫轮奸一案,当经降旨交周廷栋、广兴亲提研鞫。因该县民呈内,疑窦甚多,且所闻该臬司批饬,情节甚属支离,谕令周廷栋等先行查明覆奏。兹据周廷栋等参奏臬司,石韫玉于此案并未亲提研审,即以恐系和诱同逃污词率行批饬,实属草率粗疏,请将石韫玉交部严加议处等语,并将该臬司批示,原呈进呈,朕详加批阅。及柳儒赴臬司衙门控告,该臬司率以该氏不死于被奸之时,而死于奸夫获案之后,难保其非和诱同逃羞愧而死等词批饬,是何言耶?试思,奸夫二字原指奸妇听从和诱而言,今柳氏幼年处女,猝为强暴所污,本非奸妇,安得据指强暴为奸夫?况该犯王三等同伙三人轮替行强,又将指何人为奸夫乎?是石韫玉掉弄笔锋,楷词失当,咎无可辞。该氏自缢身死,系因该县传讯时指,躯明志在未行,上控之先设。因该臬司批饬污词,该氏始羞愧自尽,则石韫玉之获戾益至矣!似此玩视命案凭空控臆,岂可从膺臬司之任,石韫玉着交部严加议处,即着来京候旨,钦此。④
随之嘉庆帝对石韫玉作出了如下处罚:嘉庆十二年六月初九日奉旨:
此案石韫玉掉弄笔锋,率将污辞批之案牍,设柳氏因此羞忿轻生,则石韫玉获咎更重,尚不止于草职。今柳氏自缢,系由该县差传对质所致,迨伊亲属上控,石韫玉身为臬司,即应速提犯证,亲为审理。乃转以凭空臆度之词,重加污辱,是其玩视命案,实属溺职,本应照部议革职。姑念伊前在川省军营着有微劳,着加恩赏,给编修在国史馆,效力行走,钦此。⑤
嘉庆十二年九月,嘉庆帝下诏旌表柳氏,“庚戌,旌表守正捐躯山东栖霞县民柳开生妹柳氏。”⑥这一诏令的下达,更加证实了石韫玉的错判。
根据现已搜集到的史料,虽未能完全掌握此案的始末,但可以得出石韫玉不是正常的归隐,确实因为官不慎,因事左迁,在京供职亦无颜面,不得已归隐林泉。
2.《吴谱》及《墓志铭》
从以上朝廷一系列奏章来看,嘉庆帝对石韫玉的处置确也情有可原。可为何对于状元石韫玉被罢官始末的因由会出现不同的记载,以致世人至今仍遵《吴谱》及《墓志铭》的说法,对比这两类历史文献对于此事的表述确有不同:
(1)《吴谱》
《吴谱》:“…公呼儒告之曰:‘尔不得咎县官。凡讼狱在官者,窃盗案须传失主,命案须传尸,亲奸案须传本妇质问。此照例办理,何谓逼也?’因于呈词批示曰:‘尔侄孙女柳氏,被人抢去,奸宿连宵,岂有不识之理?今该县既获犯到案,止须赴县一认即可,辨其真伪,有何畏惧?而遽短见轻生,且不死于被抢之时,而死于奸夫获案之后,其中难保无和诱同逃。今见事将败露,因而羞愧自尽,姑俟饬府审详察夺。’此生即俯首无词而去。…于是部议革职。”⑦
先看石韫玉对于柳儒告状的答话,“公呼儒告之曰:‘尔不得咎县官…此照例办理,何谓逼也?’”先说石韫玉的这段话的措辞未免太过于教条,盗案与奸案怎可相提并论,盗案只是丢失家财,奸案不只是对于受害者本人的终身羞辱,也会对家族门风起到不良影响,更可能使受害者因羞愧而寻短见。再者,在当时封建社会的风气下,女性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况且柳开生之妹,深受摧残侮辱,已难以面世,何况到公堂与犯人对质,这在当时是任何一个女性都难以接受的。
(2)墓志铭
学生陶澍在为石韫玉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载:“无何,而公缘事被劾,部议革职。”⑧
陶澍对于此事的评价更是含糊其辞,模糊不清。我们单从这种文献的记载中,当然是无法了解此事的历史真相。凭陶澍和吴嵰的身份及其与石韫玉的关系来看,石韫玉的这段个人历史转折真相,陶澍和吴嵰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但二人在撰写《吴谱》和《墓志铭》中,皆为其隐瞒,这在当时撰写墓志、碑碣和年谱的文章中,以歌功颂德为主,为尊者避,为贤者讳,是行文的宗旨。吴嵰为其舅父,陶澍为其恩师隐讳真相,以保留一份体面,亦情有可缘。
时值嘉庆十四年正月,广兴赃败,处斩;仁宗以周廷栋徇情包庇,事上不诚,予以革职,永不叙用。⑨但朝廷并没有让石韫玉官复原职,抑或是给他平反的任何旨意。
嘉庆十二年六月,嘉庆帝赐予石韫玉国史馆编修,说明嘉庆帝对他的惩处还是留有颜面的。而石韫玉在当时的权贵面前,摆出读书人的清高架势,毅然辞官归隐。在当事者看来,石韫玉似乎不屑于当一个编修,既然不屑继续在京供职,那就是间接地驳斥了嘉庆帝的颜面,似乎也不会感恩于皇帝。此后的他要想重返官场,显然不会那么容易了。
与政坛无缘的他,在本年十一月引疾乞归。足疾也许只是一个引由,单就石韫玉在京城作国史馆编修这一职位来说,在乾隆五十五年,因考得状元赐以翰林院修撰,为官十八载后变身为国史馆编修。原来那声名显赫的状元,又兼具文才武略,昔日的他在朝廷可谓是荣耀一时。情随事迁,如今变身闲职,既无领军权亦无行政权,今昔地位落差的对比,自身难免产生无限惆怅,想来同僚相见不免有几分惭愧。
随着此案的结束,我们不免遗憾,文武兼备的状元石韫玉,对于这起案件的处理未免过于失责,而嘉庆帝对他的处置较重又很是耐人寻味,且即使后续多人上书求情,终为让他重返政坛。
二、石韫玉未能复出之由
人,生来本是矛盾体。有着自我矛盾,所处时代的矛盾,又有着出生成长过程中,地域文化所赋予的特有的矛盾等等。人,就是这些矛盾的集结体。而这些矛盾又是通过我们的行为、语言及文字毫无掩饰的显露出来,古往今来无一例外。
自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的修养达到一定程度时,多数知识分子都会表现出特有的清高,无论是其为人还是其作品。而这种清高在封建社会与当朝权贵是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带着这种藐视权贵的心态走上仕途,必然导致他们将面对极其复杂的社会与人生矛盾。清代状元石韫玉就是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自我矛盾
石韫玉生于乾隆二十一年,舅舅徐元孚在他五岁时开始教他《孝经》,六岁时入私塾学习。十五岁开始参加童子试,参考三次,十八岁考入县学。十九岁开始参加省试,参考三次,二十四岁中得举人。二十五岁参加会试,参考六次,三十五岁中得状元。从政十八年,五十二岁辞官归乡。九年游荡之后,于六十一岁到苏州紫阳书院讲席,直至八十二岁终老。
石韫玉应时代之趋为求取功名,谋得官职的目标拼搏了三十一年,得到时却又逐渐厌烦官场的那种权势之争的险恶生涯。虽为状元又位及人臣,可做官刚满十年的他,已于嘉庆五年意于归隐。时隔三年,仍在重庆任知府的他开始于做官心生倦意。这也显示了他的自我矛盾,年轻时拼命求学科考,以期考取功名,一朝位极人臣。可为官时,因不能迅速地施展抱负,成就自己的梦想,就盼着归隐礼佛。而这种心理状态及梦想追求的转变,时限仅为十年。
直至嘉庆十二年,石韫玉拿准一个时机辞官归乡,这一做法可以说算是了了他多年的夙愿,可归隐不到三年他又积极返回官场,幻想重新得到朝廷的任用。入仕不愿同流合污且不能任由其发挥才能,出仕则不能名利双收亦不能体现其个人的人生价值,无论是选择出仕亦或入仕,都会伴随着石韫玉内心地矛盾与纠结。
这种摇摆不定的性情或许早被嘉庆帝看在眼里,即便他如何活动,包括同僚的求情,都未使得嘉庆帝心软,由此看出嘉庆帝深知石韫玉的不堪委任。石韫玉的这种在任时心系归隐,归乡后念着入仕,如此反复的矛盾心理伴随其一生。从石韫玉的身上,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那就是仕与隐之间的尖锐对立性。而在石韫玉身上又带有时代性的特点,即他生活于一个外族统治的时代。
2.民族矛盾
自清兵入关满族取得了中原政权后,满汉两族的民族矛盾一直是此起彼伏,且以不同的形式进行着,清王朝统治大权的重任多数以满族人担当,而为了拉拢汉人,以期得到汉族的拥护,也有汉人担当的职位,但满官与汉官之间不仅人数有比例,品级的高低也会有差别。
而清政府对大多数汉族官吏的态度依然是,当不得已委以重任时,却不信任。状元出身的石韫玉当然也不会例外。这种对比主要体现在石韫玉在四川为官时,满汉两族凭借因剿灭白莲教的功劳而提升的反差上。
勒保因采纳石韫玉制定的“坚壁清野”之策,致使白莲教节节败退,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而制定出这一策略的石韫玉却没有受到如此丰厚的嘉赏,只是因策略制定的好和他因军务受伤仍坚持随军作战而赏戴花翎。在白莲教基本肃清后,制定策略的他擢升陕西潼商道后又擢为山东按察使,虽三次召见可多是谈及军务,而赏与内宴,怕只是为了安抚这位有功不赏的状元吧。可执行策略的勒保回京作军机大臣,这种嘉赏的差距尤为明显。
且石韫玉因民案被贬为编修,无权无位,辞官后嘉庆帝再不任用。除去石韫玉的错误不说,单因在川的功劳,也不至于永不叙用。清政府轻视甚至于歧视汉族官员则显而易见。
对比勒保所犯的错误,“嘉庆十五年,召来京供职。坐在四川隐匿名揭帖未奏,降授工部尚书,调刑部。十六年出为两江总督。寻内召,复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改兵部,授领侍卫内大臣。十八年,充军机大臣,兼管理藩院。”⑩“坐在四川隐匿名揭帖未奏”,内有多少冤假错案,我们已不得知,对满族官员勒保来说,从发现降职到官复原职,再到升职,不过两年时间。而于汉族官员石韫玉的处置未免重了些。其个中缘由也许只差得一个出身满汉的关键点上了。
在他的诗作中虽未流露出对朝廷有任何不满,可单单对周、广二人落马后,他仅作一首《双旌谣》,从中即可窥出端倪,对于民族之间的差异,亦是有口难说。况且清代盛行文字狱,又有哪个文人墨客敢去挑战他呢,不过是意难平的接受现实罢了。
3.地域文化矛盾
长江流域下游,山水清秀,物丰民富,正是这秀丽的山川,孕育了不少文人逸士。历代文人中,有的通过科举飞黄腾达,也有藐视权贵遁隐山林不为统治者所用,过着清高闲雅的隐士生活。纵观历史,东晋时王羲之的遁隐山林、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宋代林和靖梅妻鹤子的孤傲,以及明代吴门四才子的清高,这些人在历史中的出现,对吴越文化后世文人性情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这一影响对于出生于吴越地区的石韫玉来说亦是潜移默化的,是不可避免的。
石韫玉虽为文武全才,可无论是自身特点,还是时代因素,都应归结到他是一个苏州人这个点上。因为无论是自身,还是民族矛盾,最后他都用江南人的特质化解了。自他执教于苏州紫阳书院,从此安于闲雅的生活,不在积极入仕的他,将仕与隐融为一体。由此看来,吴越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他的影响是最为悠远绵长的。
石韫玉一生起伏跌宕,三十五岁中得状元,五十二岁官居山东按察使,同年因事左迁,六十一岁执教于紫阳书院。人生四次巨大的转折,使得身心俱疲的他,转而用诗文戏曲来表达人生的不如意,将自身、民族与地域文化之间的矛盾,用其为人及诗文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石韫玉用诗文戏曲写照了他一生的轨迹,但在他的作品中对于当年山东柳氏一案却只字不提,而吴嵰与陶澍又积极地为其避讳,可见他在柳氏一案上确有错判,亦可推测出周廷栋广兴二人对于石韫玉的揭发并非诬告。从中可看出他是一个失败而自身又充满矛盾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