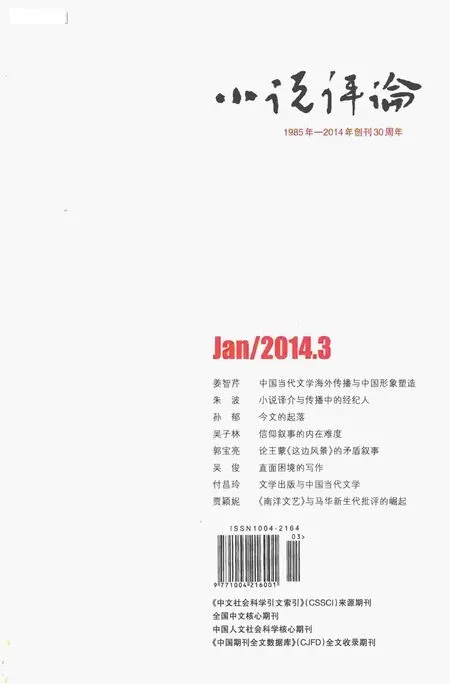论王蒙《这边风景》的矛盾叙事
郭宝亮
《这边风景》是王蒙写作于“文革”后期的一部70 余万字的长篇小说。据王蒙自己所言,这部小说最早写作于1972年,但只是“试写了伊犁百姓粉刷房屋等章节”。1974年作者四十岁时,开始全力写作这部作品,1978年8月7日完成初稿,然而,终因“政治正确”的问题,未能出版。如今,《这边风景》在尘封了近四十年之后的出版,不仅填补了王蒙在新疆16年写作的空白,也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文革”后期写作的空白。这部小说对我们进一步研究王蒙和中国当代文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对《这边风景》的阅读中,我感到了王蒙那无处不在的矛盾叙事现象,这种现象恰恰构成这部作品的价值。
一
如果把《这边风景》放置在“文革”结束前的27年的文学史链条上来考察,这部小说究竟与当时的作品具有怎样的关系,也许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文革”结束前27年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两类上,而现实题材作品尤以农业合作化为最。50年代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虽然已经形成比较雷同化的人物模式和情节模式,但还是较为真实地表现了农民在走向集体化过程中的心理风貌。到了60、70年代的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则明显地增加了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化的内容,显得不够真实了。但在“文革”年代,浩然的小说却是“最像小说”的小说了。王蒙在《王蒙自传·半生多事》一书中说:“比较起来,我宁愿读浩然兄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浩然毕竟是作家,而作家与非作家并非全无区别,虽然作家都是从非作家变化而来。经过这个过程与从未有这个过程,并不相同。我喜欢他写的中农,小算盘,来个客人也要丢给你一把韭菜,让你帮他择菜。我喜欢他写的京郊农民的俗话:‘傻子过年看隔(应读介)壁(应读儿化与上声)’。……当然,‘金光大道’就更有‘帮文学’的气味了,有横下一条心,六亲(指文学艺术之‘亲’)不认地豁出去了去迎合的烙印。另一方面,我看他写的英雄人物萧长春,高大泉,也为他的惨淡经营,调动出自己的全部神经与记忆,力图按要求写出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力图使自己的文学才能文学经验为上所用而摇头点头,这样的苦心使我感动,使我叹息不已。”由此可见,王蒙的《这边风景》也属于这一写作序列中的一环,而且也步着浩然等文革流行写作的后尘的。作品从1962年伊塔边民事件开始写起,一直写到“四清”运动,其人物设置、结构布局,情节模式均与以上作品类似就不难理解了。这说明王蒙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小说的人物设置明显分为对立的两派,以伊力哈穆为代表的正的一派和以库图库扎尔为代表的邪的一派的斗争,成为贯穿全书的主要情节线索。
主要人物伊力哈穆一出场就面临着严峻的自然灾害和伊塔边民外逃事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伊力哈穆首先拿出的是毛主席与库尔班叶鲁木的合影照片。这里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巧帕汗老太太误把库尔班叶鲁木认错为熟人,王蒙写到:“这是不需要纠正的,人们谁不以为,那双紧紧握住主席的巨手的双手正是自己所熟悉的、或者干脆就是自己的手呢?”然后作者又让伊力哈穆肯定地说:“这就是我们大家,”“毛主席的手和我们维吾尔农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毛主席关心着我们,照料着我们。看,主席是多么高兴,笑得是多么慈祥。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毛主席挑起了马克思、列宁曾经担过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担子。所以,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对毛主席又怕又恨。领导说,目前在伊犁发生的事情,说明那些披着马列主义外衣自称是我们的朋友的人,正在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利用我们内部的一些败类,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疯狂挑战,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猖狂进攻。但是,乌鸦的翅膀总不会遮住太阳的光辉,毛主席的手握着我们的手,我们一定能胜利,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样的情景、这样的语言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都不陌生。在第二十一章,伊力哈穆在大湟渠龙口的深思,我们似乎也曾见过,它与文革期间的样板戏中主人公在遭遇困难时的独白式的咏叹调多么地相似啊,当伊力哈穆面对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一筹莫展的时候,“伊力哈穆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毛主席接见库尔班吐鲁木的照片。毛主席!是您在解放初期指引我们推翻地主阶级,争取自由解放。是您在五十年代中期给我们又指出了社会主义大道。去年,又是您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现在,您在操劳些什么?您在筹划些什么?您将带领我们进行什么样的新的战斗?您在八届十中全会全会上完整地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基本路线,将武装我们迈出怎样的第一步?”如此这般我们在全书中还会找到很多,这充分说明王蒙的写作模式正是当年流行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当时意识形态的产物。王蒙夫人崔瑞芳女士谈到《这边风景》时说:“这本书写成于‘四人帮’统治时期,整个架子是按‘样板戏’的路子来的,所以怀胎时就畸形,先天不足。尽管有些段落很感人,有些章节也被刊物选载过,但总的来说不是‘优生’,很难挽救,只好报废。”
然而,王蒙的写作却没有滑向极左的泥潭,而是在作品中处处反左。第三章当库图库扎尔建议把萨木冬的老婆乌尔汗逮捕审讯批斗的时候,伊力哈穆却旗帜鲜明地为乌尔汗夫妇说好话,强调要重证据而不是动辄上纲上线的极左做法。第十七章上级要求麦收要突出政治,要求十天割完麦子,这种明显脱离实际的口号,也是那个年代极左思维的突出特征。
以左的写作模式来写反左,使我们看到了王蒙在文革后期的矛盾处境。小说的重点在写“四清”运动,“四清”作为文革的前奏,已经显现出政治生活中的强劲的左倾风暴,但王蒙却巧妙地抓住了反对“桃园经验”极左做法的“二十三条”作为挡箭牌,以获取政治正确的筹码。“桃园经验”被指陈为形左实右,而工作队的章洋又是极左路线的代表,如果说库图库扎尔的“左”是为了掩盖他的右的真面目而披上的皮,那么章洋的左则是骨子里的“真左”,在王蒙看来,这种真左恰恰是最为可怕的。因为这种左是毫无顾忌的,气势汹汹的,因而其破坏力也是无与伦比的。章洋实际上就是王蒙新时期小说中的宋明、曲凤鸣的前身。
我发现小说的上册与下册对极左批判的比例并不协调,下册对章洋的极左的批判明显坚决和彻底。这应该与世事的大变有直接关系。《这边风景》开始写作于1974年,1978年8月7日完稿,如果以1976年10月为界,这部作品恰好处于这两个时代的交界处。王蒙夫人崔瑞芳言,1974年10月15日是王蒙40 岁的生日,这一天王蒙真正受到触动,决心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整个1975年,他几乎一直在我们的斗室里伏案疾书”,1976年“四人帮”垮台,历史发生了巨变,反左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这一新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不对王蒙产生巨大影响。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8月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王蒙的写作心态正在发生变化,这在王蒙的《王蒙自传》里已有交代,1978年6月16日,王蒙应中青社邀请到北戴河修改《这边风景》的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此前写作发表的小说《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中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狠揭猛批来看,王蒙对极左的批判由隐蔽谨慎到公开坚定当是毫无疑问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边风景》正是两种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极左与反极左的内在抵牾龃龉,体现出王蒙内心的极大矛盾。正如崔瑞芳女士所言:“他在写作中遇到了巨大的难于克服的困难。当时,正值‘四人帮’肆虐,‘三突出’原则统治着整个文艺界。王蒙身受20年‘改造’加上‘文革’10年‘教育’,提起笔来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作品中的人物又必须‘高大完美’,‘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写起来矛盾。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雄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必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装傻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中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二
王蒙在酝酿写作《这边风景》时,就曾说过:“我也真的考虑起写一部反映伊犁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来。我必须找到一个契合点,能够描绘伊犁农村的风土人情,阴晴寒暑,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美丽山川,丰富多彩,特别是维吾尔人的文化性格。同时,又要能符合政策,‘政治正确’。我想来去可以考虑写农村的‘四清’,四清云云关键是与农村干部的贪污腐化、多吃多占、阶级阵线不清做斗争,至少前二者还是有生活依据的,什么时候都有腐化干部,什么时候也都有奉公守法艰苦奋斗的好干部。不管形势怎样发展,也不管各种说法怎么样复杂悖谬,共产党提倡清廉、道德纯洁是好事情。阶级斗争嘛总可以编故事,投毒放火盗窃做假账……有坏人就有阶级,有坏事就有斗争嘛,也不难办。就这样,以不必坐班考勤始,我果真在‘文革’的最后几年悄悄地写作起来了。”在这里,王蒙最关注的还是“政治正确”的问题。为了“政治正确”不得不“主题先行”、图解概念。然而,王蒙毕竟是一个在50年代就文名大振的作家,他的成名作《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引得议论哗然,连毛泽东主席都在不同场合五次谈到王蒙。因此,王蒙不能不追求小说的艺术真实性。长期的新疆生活积累,使他十分明白原生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于是,我们在《这边风景》里,看到了流行的先验的政治概念与原生态的生活真实纠结缠绕在一起的矛盾现象。
浓郁的伊犁边地风味,维吾尔人民的民族风情,文化习俗等在这部小说中都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成为这部小说的最为亮丽的风景。伊犁的电线杆子都能发芽成树,乌甫尔打钐镰,以及烤肉打馕酿啤渥等的维吾尔人民的日常生活描写,既显示了王蒙作为外来者的新奇眼光,又证明了王蒙新疆16年与维吾尔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的对生活的熟稔而信手拈来的自信和自由。由此带来的是鲜明生动的现场感,现场感是指小说场面描写和细节描摹的功力。曾几何时,我们的小说写作现场感减弱,代之以叙述人的讲述和议论,特别自先锋小说以来,纠正了文革前小说过分写实的问题,想象力得以张扬,但在一定程度是消弱了小说的现场感。现场感需要深厚的生活积累,想象力如果离开了坚实的生活积累的基础,有时候会变得模糊飘渺,也就失去了小说的厚重笃实。记得作家格非在某个地方说过:“小说描写的是这个时代,所有的东西都需要你进行仔细的考察,而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呈现出器物以及周围的环境。……你要表现这个时代,不涉及到这个时代的器物怎么得了?包括商标,当然要求写作者准确,比如你戴的是什么围巾、穿的什么衣服。书中出现的有些商标比如一些奢侈品牌我不一定用,但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向我提及,我便会专门去了解:‘这有这么重要的区别吗?’他们就会跟我介绍。器物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真实性。”“也可能有人觉得这是在炫耀,我毫无这种想法,而且我已经很节制了。《红楼梦》里的器物都非常清晰,一个不漏——送了多少袍子、多少人参,都会列出来。但《红楼梦》的眼光不仅仅停留在家长里短和琐碎,它有大的关怀。”格非在这里所说的表现“器物”的能力实际上就是作家生处理活经验的功力。新时期以来,我们的很多作品,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不熟悉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也不做案头和田野工作,只是靠想象和猜测来臆想当时的生活场景,古人的生活起居、服饰器物谁人敢于细致的描摹?结果只有靠议论和讲说来搪塞敷衍,历史的生活场景成为今人假扮的木偶,作品的现场感严重失实。《这边风景》现场感之所以鲜明丰厚,正是王蒙对新疆生活经验刻骨铭心的体验之深。王蒙把这种对生活经验的深厚称之为“迷失”,比如在谈到曹雪芹写《红楼梦》时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在他的人生经验里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的迷失。因为他的经验太丰富了,他的体会太丰富,他写了那么多人,那么多事,他走失在自己的人生经验里,走失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他的艺术世界就像一个海一样,就像一个森林一样,谁走进去都要迷失。”王蒙也迷失在他的伊犁生活中,他写维吾尔人民粉刷房屋打扫卫生,写打馕,写喝茶吃空气,写维吾尔人见面痛哭等如没有切身体验都将不可思议。
可以说《这边风景》重点写的就是边地人民的原生态的日常生活,但王蒙处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情势,使他又不可能挣脱政治概念的藩篱,我们也没有理由说王蒙不是真诚地相信这些政治概念的正确性的,但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又的确消解了先验的政治概念的正确性。
三
《这边风景》的这种矛盾叙事,实际上也不是王蒙特有的现象,而是“文革”结束前27年的许多作品共有的现象。“十七年”时期的几部有影响的作品“三红一创青山保林”都是如此。比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小说虽然书写的是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克服自身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而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分子的故事,但在小说叙事中我们处处感受到了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缠绕纠结,是这两种话语压制与反压制的矛盾。林道静离家出走、从反抗包办婚姻到爱上余永泽,这与五四时期知识女青年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一样,而后离弃余永泽爱上卢嘉川,并不意味着她走向革命,而是生性浪漫渴望冒险的林道静对卢嘉川的英俊外表与其背后神秘的革命的向往,经历了狱中锻炼最后与江华的结合,表面上是林道静皈依了革命集体,而林道静的内心仍旧并不甘心。也就是说,林道静并没有被彻底改造,她的内心始终处在启蒙与革命的两种话语的矛盾撕扯之中。同样,柳青的《创业史》也存在着一种难于克服的矛盾:即为政治服务的狭隘性与浓郁生活气息的宏阔性的矛盾,由先验的政治取舍的概念化与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性的矛盾。作为党员作家,柳青为政治服务的态度是自觉地。在“第一部结局”部分柳青引用毛泽东的批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但是,柳青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原生态生活非常熟悉,于是在对梁生宝等人物塑造上,虽然也不可避免地拔高(党的忠实儿子),但作者采取了让梁生宝围绕发展生产、靠多打粮食的优越性的方式与其他势力进行和平竞赛。小说虽然写了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但正面的、激烈的公开交锋几乎没有,而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交锋,是通过发展生产的和平竞赛来体现社会主义集体化优越性的较量。书中用县委杨副书记的话“靠枪炮的革命已经成功了,靠优越性、靠多打粮食的革命才开头哩”来作为点睛之笔,深刻概括了当时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特点。这是柳青《创业史》的独特之处,也是柳青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结果,以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原生态消解先验政治概念的一种并非自觉的表现。还有宗璞的《红豆》,革命与爱情的矛盾纠结,使作品具有了深厚的人性复杂性。
实际上,王蒙在50年代的写作,也是具有这种矛盾性的。他的《青春万岁》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但即便这样的小说,其中也隐隐约约地透出一种不自觉的矛盾心态。比如,苏宁的哥哥苏君批评杨蔷云时有这样的对话:
苏君掏出一条女人用的丝质手绢,用女性的动作擦擦自己的前额。收起来,慢慢地说:“……我不反对学生可以集会结社。但也不赞成那么小就那么严肃。在你们的生活里,口号和号召非常之多,固然生活可以热烈一点,但是任意激发青年人的廉价的热情却是一种罪过……”
“那么,你以为生活应该怎么样呢?”
“这样问便错了。生活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而不是‘应该’怎么样。人生为万物之灵,生活于天地之间,栖息于日月之下,固然免不了外部与内部的种种困扰。但是必须有闲暇恬淡,自在逍遥的快乐。……”
这里的批评,王蒙显然站在理想主义立场加以否定,但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让杨蔷云不能不“低下头,沉思”,“然后严肃而自信地向着苏君摇头”,发表了一篇宏大的庄严的议论,这时作品写道:“于是蔷云轻蔑地、胜利地大笑,公然地嘲笑苏君的议论。”显然,杨蔷云“低下头,沉思”的描写,实际上体现了王蒙对苏君意见的矛盾态度。
而后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这种矛盾已经到了不能克服的地步。比如“第六节写林震在党小组会上受到严厉批评,林震的辩解是:‘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刘世吾的批评是:‘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听到这种批评,林震的反应是:‘像被击中了似的颤了一下,他紧咬住了下嘴唇。’这里攻击‘应该’的刘世吾的声音显然比苏君的声音要强大得多,而林震的声音比起杨蔷云来也弱小得多,不自信得多,他的反应也比杨蔷云要强烈得多。而在作者的自我意识中,林震的来自书本的理想主义规范化语言是一条正途,刘世吾的基于现实的‘实际主义’显然是一种对乌托邦话语的偏离,但它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作者找不到驳斥的理由,他只有惶惑和矛盾,然而作者又渴望把刘世吾的‘实际主义’统一到林震的理想主义上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寻求最高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支持。”
王蒙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落马,被迫搁笔,自我放逐新疆,直到文革后期的重新提笔写作,王蒙思想中的这种矛盾非但没有消弱,反而愈发地强化起来。这正是极左政治与日常生活的严重不搭调的结果。王蒙凭借对现实生活的熟稔程度以及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通过这种矛盾叙事赢得了文学史的存在价值。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分抬高《这边风景》的艺术价值,它只是王蒙写作链条上的一环。严格地说,它其实还是一部颇有瑕疵的作品。但是,它对我们研究王蒙,理解王蒙乃至研究文革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部作品之所以有认识的价值,正是它的这种现实主义的矛盾叙事,真实地表现出了王蒙乃至那个时代人们对待政治与生活的态度。在那个时代,王蒙通过矛盾叙事写出了生活的复杂性,这也为新时期的王蒙写作开了先河。
注释:
①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一卷,第353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
②方蕤:《我的先生王蒙》,第11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③方蕤:《我的先生王蒙》,第10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④据崔瑞芳回忆:“1977年岁末他写完了短篇小说《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第二年1月21日定稿,24日寄往《人民文学》。五个月后,1978年6月5日,我在办公室随手翻开第五期《人民文学》,上面竟赫然印着王蒙的名字,《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发表了!”见方蕤:《我的先生王蒙》,第10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⑤方蕤:《我的先生王蒙》,第10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⑥王蒙:《王蒙自传·半生多事》,第一卷第358页,花城出版社2006年。
⑦邵聪:《格非: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8日。
⑧邵聪:《格非:这个社会不能承受漂亮文字》,《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8日。
⑨王蒙:《王蒙活说〈红楼梦〉》,第183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版。
⑩指《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
11郭宝亮:《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第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